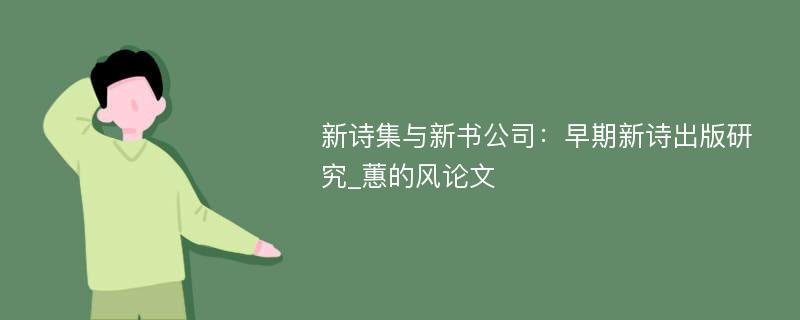
“新诗集”与“新书局”:早期新诗的出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书局论文,诗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文学的发生期,“新诗”出版的兴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据蒲梢所编《初期新文艺出版物编目》统计,从1919年到1923年间,共出版各类诗集18部,包括个人诗集,同人合集与诗歌选集。这个数字,现在看来并不惊人,但同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出品短篇、长篇加在一起只有13种。(注:参见文学研究会编《星海》(《文学》百期纪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月。)由此可见,“新诗”不仅是新文学的急先锋,而且在初期文学的出版品中也是中坚力量。有意味的是,早期新诗集的出版者虽有多家,但细分起来,影响较大的几部诗集的出版还是相当集中的,基本上被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三家包揽(商务三种:《雪朝》、《将来之花园》、《繁星》,亚东七种:《尝试集》、《草儿》、《冬夜》、《蕙的风》、《渡河》、《流云》、《一九一九年新诗年选》;泰东两种:《女神》、《红烛》)。其他书局或只偶一为之,或根本是由诗人自印。其中,商务版诗集属于文学研究会丛书系列,在出版品中份额不大,“新诗”并不是其“重头戏”。但是,对于亚东、泰东这两家规模较小、以新文化出版为主干的出版者来说,“新诗集”的出版却与“新书局”自身形象的确立以及生存和发展,有着相当紧密的关联;而新诗社会影响的扩张不仅有赖于和“新书局”的合作,新诗坛内在的分化,也隐约地显现于“新书局”的微妙对峙间。因而,在“新诗集”与“新书局”之间,一个可待开掘的论述空间便由此产生。
一
在新文化兴起之初,对既有出版业的批评便不绝于耳,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这两家出版界的龙头,无疑是火力的焦点。宗白华在《评上海的两大书局》一文中,就指责商务:“十余年来不见出几部有价值的书”,而中华则无评论价值。(注:1919年11月8日《时事新报·学灯》。)在个人的言论之外,《新青年》、《新潮》对商务旗下杂志展开的围攻则更是著名。(注:先是陈独秀发文抨击《东方杂志》反对西方文明,提倡东方文明,掀起东西方文化之争(《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新青年》5卷3号,1918年9月);继而是罗家伦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把商务旗下诸多杂志批得体无完肤。(《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虽然,商务、中华等大型书局也积极跟进,迅速与新文化的势力接轨,但在某些新文化运动人士看来:“其实他们抱定金钱主义”,商业利益是其第一位的考虑。直至1923年,还有人发表文章,认为出版界“混乱”的原因,是“出版界的放弃职责,惟利是图,实为致此恶象底是最大的动力”,而“本篇所论,还只是对几家较为革新的书店而言”,矛头所指仍以革新后的商务、中华为中心。(注:参见霆声《出版界的混乱与澄清》,《洪水》1卷3期与5期。)因而,在旧有的出版业之外,构想一种以新文化人士为主体的新的出版方式,吸引了一部分人的注意,(注:譬如,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就发生过关于“新文化书店”的讨论。讨论者在对出版新文化书籍的大书店,纷纷表示不满的同时,也认为“最好这种书店,即由各种学术团体集合资本开设”,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法、程序。(参见1920年3月间的《时事新报·学灯》))后来北新、创造社出版部、光华书局等新型书店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呼声的产物。但在这一构想实现之前,新文化的传播,必须依赖与出版商的合作,群益、亚东、泰东等书局都由此脱颖而出。群益发行《新青年》,亚东代理北大出版部,销售、代办或印行各类新杂志,后来又标点旧小说,而泰东则出版创造社丛书,都著称一时,被看做是新书局的代表,(注:宗白华曾评价当时的书局:“现在上海的书局中最有觉悟,真心来帮助新文化运动的要算亚东和群益。中华、商务听说也有些觉悟了,究竟是否彻底的觉悟,还不能晓得。”(见《复沈泽民信》,1920年1月19日《时事新报·学灯》)另:由毛泽东等人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当时与八家正式出版物有交易协议,其中头两家就是泰东和亚东。(王火《关于长沙文化书社的资料》,《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410页,张静庐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到了40年代,还有人将亚东与泰东,两位经理赵南公和汪孟邹并提,认为是当年上海四马路上仅有的纯正书商。(注:萧聪《汪孟舟——出版界人物印象之一》,1947年8月10日《大公报》;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04~208页转引了此文及汪孟邹的回文,北京: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新诗集”的出版,正是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在亚东、泰东那里,“新诗集”与“新书局”之间存在着饶有意味的文化关联。
在初期的新文艺出版领域,亚东图书馆算得上是一家新诗的“专卖店”。如上文所述,早期新诗的主要出品基本由亚东、商务和泰东三家包揽,而亚东出品占据了其中的大部,有七部之多,而且《尝试集》、《草儿》、《冬夜》、《蕙的风》等新诗史上的奠基之作,在当时都十分畅销:《尝试集》出版3年已出4版,印数15000册,据汪原放统计到1953年亚东结业时,共出47000册,数量惊人。(注: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53页、82页,北京: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蕙的风》也“风行一时,到前三年止销了两万余部”。(注:此说法出自汪静之《中学毕业前后》,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张静庐曾称早期上海新书业,可以销行的书一版印两三千本,普通的只有五百本或一千本。(注: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127~128页,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比照上面的销量,可见亚东诗集的畅销程度。其他几本出品,虽不似这两本风光,但销数都很可观。(注:《草儿》、《冬夜》、《新诗年选》初版3000册,《冬夜》据倪墨炎估计,至少有三版(参见《俞平伯早期的诗作》,《俞平伯研究资料》,第25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草儿》修正三版改名为《草儿在前集》后还有四版。)亚东成了新诗的“专卖店”,无疑是出版者看准了市场。然而,市场的鼓励,毕竟只是一个推测,“新诗”专卖还与亚东特殊的人事背景有关。陈独秀、胡适等人与亚东关系密切,亚东也由于有了新文化领袖的支持而兴旺发展,这方面的情况汪原放已有详尽论述。尤其是胡适,从提供书源,到选题指导,再到作序考证,可以说是亚东的幕后高参,他自己重要的著作,大部分由亚东出版,由他作序的旧小说标点本更是风行一时,让亚东收益颇丰。(注:到1922年底,亚东出版的胡适作品《短篇小说》、《胡适文存》、《尝试集》以及他作序的《水浒》、《儒林外史》等,都印行三版、四版,印数为一万以上,其后的销量还要多出许多。(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81~82页))值得注意的是,《尝试集》之后,亚东出版的一系列诗集,都与胡适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新诗集能够在“亚东”不断推出,胡适的作用不能低估。
在上述两方面之外,更值得探讨的是,新诗的“专卖”,其实还体现了亚东独特的经营理念。上文已述及,与商务不断遭受批评不同,亚东、泰东是以新书店的形象出现在上海出版界的。然而,新、旧书店的区分除了表现在“形象”上,其出版实力和经营范围的差别也相当关键。据王云五统计,民国二十三至二十五年三年间,商务、中华、世界三家占全国出版物的比重平均为65%,其中商务一家平均为48%,几乎独占了一半。(注: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335页,张静庐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这是从出版量着眼的统计,而陆费逵则从出版资本上做过描述,他称:“上海书业公会会员共四十余家”,资本九百余万元,其中大书店资本雄厚,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分别为五百万、两百万、七十万、三十万,此外都是一二十万元以下的。而非书业同业公会会员的还有五种,资本均在十万元以下,其中就包括“新书店”。(注: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印刷业》,《中国出版史料》补编,278~279页,张静庐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所谓“新书店”,就应包括亚东、泰东这样的小书店,在汪原放的统计中,亚东的年收入最高时不过七万多元,无疑是被排斥在资本雄厚的大书店“俱乐部”之外的。有趣的是,当亚东、泰东、北新、现代等书店组织“新书业联合会”时,商务、中华也被有意排斥在外。(注:沈松泉《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出版史料》1991年2期。)“小资本”与“新书局”,出版实力与文化形象之间的这种关联,其实表明了现代出版市场分层划分的形成。
在大书店雄厚的出版实力面前,尤其当它们也转向新文化出版时,小书店的压力可想而知。在发行上采取必要的措施自然有效,徐白民回忆1923年在上海办书店时,代售各书店的图书,以民智、亚东、新文化书店的书为多,而商务、中华几家大书店十分苛刻,代售可以,但不能退还。小书店与大书店在销售策略上也显出差异。(注:《上海书店回忆录》,《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62页,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1954年。)但与此相比,选题策划可能更为关键。还是据蒲梢《初期新文艺出版物编目》,1919~1923年间同是创作类,短篇小说商务出六种,泰东出两种;长篇小说商务两种,泰东一种,亚东则没有出品。翻译一类,小说商务出品二十三种,泰东八种,亚东只有一种;戏剧商务三十五种,泰东两种;诗歌商务两种,泰东一种。上述数字显示,除诗歌之外,在新文学的其他领域,商务都遥遥领先,而泰东似乎紧跟其后(虽然数目上差距很大),而亚东似乎并不着意四面出击。在其他门类,如文学史、文学概论、古典文学研究等,情况同样如此,只有标点旧书一项,亚东出版六种,一枝独秀,而泰东又是追随者,出品了一种。商务等大书局在新文化领域,主要以大型丛书为主,涉足创作,虽只由文学研究会丛书带动,但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份额。在此压力下,可见亚东是十分注重出版重点的选取的,无论是诗集还是旧小说标点,在效果上都找到了市场的空隙,形成系列,创造出自己的品牌。1923年,亚东曾与商务共争《努力》的出版权,此事让胡适很头疼,在日记里写道:“亚东此时在出版界已渐渐到了第三位,只因所做事业不与商务中华冲突,故它们不和它争。”(注:1923年10月16日胡适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4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与商务冲突不是一件好事,出于自保,亚东后来还是妥协了。不与大书店争夺,致力于独立品牌的经营,成了亚东成功之道,比如在出版广告上,就注意分类,将胡适著作合为一个广告,标点小说为一个广告,名人文存为一个广告,而新诗集更是排在一起隆重推出。(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81页。)有了这些品牌,再加上稳健的出版风格,在激烈的竞争中,亚东得以生存发展。譬如,亚东标点本看好后,其他出版商很快模仿,“先是群学书社,进而启智书局,新文化书社大量出版,数量达二三百种。”有趣的是,新文化版的销路极佳,挤垮了石印小说,但不能致亚东于死地,因为新文化版石印小说的读者是一个阶层:小市民和富裕户,而“亚东出版有讲究的分段、标点、校勘、校对和考证,对于爱好文学者有吸引力”。(注:汪家熔《旧时出版社成功诸因素——史料实录》,《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研究文集》,第357~358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10月。)上述出版策略的选取,当然是书局的经营之道的体现,但从书局回报率的角度看,“新诗”在出版、阅读中的特殊位置,值得玩味。这一点可以由“诗集”带来的经济收益上看出。
亚东版的新诗集虽然好销,但在赢利上,其实远远赶不上亚东出品大部头的标点本旧小说和名人文存:诗集定价只有几角,而《水浒》、《红楼梦》等每套要几元钱,价格相差十分悬殊,而亚东最赚钱的书还应是高语罕的《白话书信》,前后印过十万册以上。可以想见的是,诗集提升了品格,但不是亚东经济上的支撑,更多体现了新书店的自我定位,“经济考虑”之外的另一重出版逻辑在这里显露出来。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这是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里的逻辑,即:某种现代的、先锋的出版品正是以对“商业性利益”的疏远为起点的,一种特殊的“自主性”得以表达。(注: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98~102页,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在以“新诗”为标志的文化场域内,先锋性的出版品能够争取到的,主要不是看得见的经济利润,而是某种看不见的“象征资本”的积累,这一点对“亚东”这一类书局自身形象的建立,无疑至关重要。当然,“亚东”还算不上是“先锋”出版社,经济利益仍是其最主要的着眼点,随着书店地位的稳固和阅读市场的变化,诗集后来在亚东,似乎不再受到重视,1923年陆志韦的诗集《渡河》,在亚东出版时因稿费问题发生过一些磨擦,汪孟邹在日记里写道:“此后此种间接交涉,须要再三谨慎为要。”(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86页。)言语之中,已有不耐烦之意,而1929年出品的何植三的诗集《农家的草紫》,因销路不好,被店里人讥为“真是‘草纸’啊”。(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41页。)
二
虽然同以“新书店”自居,泰东图书局的情况与亚东却有很大的不同。泰东图书局的股东,原来多与政学系有关。民三创办时,出版计划注重在政治。后来讨袁胜利后,股东都到北平做官去了,书店经理赵南公一手包办,出了好几种“礼拜六派”小说,还靠杨尘因的《新华春梦记》赚了一笔钱。但到了新文化运动初兴之时,他看到鸳蝴小说不再走红,也准备改造泰东,向新文化靠拢。(注:引述自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91~92页,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如果说亚东从一开始就借上了新文化的东风,那么泰东或许就属于“投机”的类型。
然而,“新文化”的投机并不好做,泰东的一系列尝试都不很成功,“新”总新不到点子上,刘纳在《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中对此有过专章描述,其中的原因有多方面,一个重要原因是,泰东人缺乏新文化精英的鼎助。没有陈独秀、胡适这样的强大后盾,自然没有高质量的新文化稿源,发行的《新人》杂志就因外稿缺乏,常由主编王无为一人唱独角戏,而策划的几套丛书也似乎难以为继。(注:1921年4月16日,赵南公在日记里记下了编辑精简方案,其中丛书一项情况为“《新人丛书》无善稿,宁暂停;《新知丛书》已出几种,余以该社自组出版所,自难望其继续;《黎明丛书》已成交,而合同未立;《学术研究会丛书》本由该会自印,无关系。”(转引自陈福康《创造社元老与泰东图书局——关于赵南公1921年日记的研究报告》,《中华文学史料》1991年第1辑))至于泰东的编辑人员,也伐善可陈,《新人》主编王无为是上海滩上的“寄生”文人,曾自况说:“挂几块招牌,做什么新闻记者,教员,小说家,又是什么书局的编辑,及自命是文化运动者。”(注:《王无为赴湘留别书》,《新人》1卷6期,1920年9月。)《新的小说》主编王靖,译过托尔斯泰的小说,能力平平,在《创造十年》里郭沫若曾对其尽情讽刺,而当时的编辑张静庐也只是个初出茅庐,心里有自己打算的青年。泰东麾下的“新人社”,其实是一个编辑社,编辑“新人丛书”,成员编辑各地,十分驳杂,“有不少只不过是拿谈新文化运动当做职业,自己并不信仰,更不用说身体力行了。”(注:《<新人社>编者说明》,张允候编《五四时期的社团》3卷,第208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这种人员构成,自然影响到书局出品的倾向,应时的白话文刊物《新的小说》,最初销量尚可,“但到后来西洋镜拆穿了,遭受了一般读者的唾弃。”(注:郭沫若《创造十年》,《学生时代》,第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这就是《女神》出版前泰东的情况,形象不佳,加之经营不善,可以说是一个烂摊子。面对困境,老板赵南公也尝试进行书局的改革。1921年新年伊始,泰东租了上海马霍路的房子作为编辑所,赵南公等人商议起了新的发展计划。首先设定新的出版路线,“首重文学、哲学及经济,渐推及法政及各种科学”,但更重要的,是编辑人员的调整和新人的聘用。对现有的编辑人员,赵南公原本不满,曾言:“但深为无为忧,因其聪明甚好,而学无根柢,前途殊危险。静庐不及无为,而忌人同,尤危险。”(注:赵南公1921年1月9日日记,引自《创造社元老与泰东图书局——关于赵南公1921年日记的研究报告》。)郭沫若、成仿吾的归国,就由此而实现。在举目茫然时,苦于人才难觅的赵南公,是把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的郭沫若,当成了书局的救星:(注:郑伯奇曾说:“假使没有沫若在新文坛的成功,赵南公是否肯找他呢?”(《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第75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1921年4月,赵南公开始与郭沫若商议书局的总体规划,五月拟订《创造》的出版,并出资让郭回日本组稿,直至7月,更是决定将编审大权交给郭沫若,并多次在日记里表达了这种决心,甚至写道:“即沫若暂返福冈,一切审定权仍归彼,月薪照旧,此间一人不留,否则宁同归于尽”,(注:赵南公1921年7月28日日记,引自《创造社元老与泰东图书局——关于赵南公1921年日记的研究报告》。)一度欲将泰东的支配权交给郭沫若。
《女神》的出版,正是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泰东要革新,在一开始,却不改跟风的老路。起初赵南公提出的方案,是要出中小学教科书,但又没有充足资本,想走取巧路线,但遭郭沫若反对,(注:见赵南公1921年4月18日日记,《创造社元老与泰东图书局——关于赵南公1921年日记的研究报告》。)后来又眼红亚东的标点本走红,郭沫若便搪塞改编了一部《西厢》。赵南公一心想书局振兴,而郭沫若琢磨的是出版自己的纯文艺刊物,在决策未定的5月,郭沫若编定的《女神》和改译的《茵梦湖》,可以说是一份不错的见面礼,真正为泰东打开了“新书店”的正途。5月,《学灯》上登出《女神》序诗,《女神》出版的第二天,《文学旬刊》上又出现郑伯奇的长篇书评。此后的《创造季刊》和创造社丛书,也成了泰东的看家品牌,虽然起初并不畅销,但随着创造社影响力的剧增,还是为泰东带来了长线的回报。张静庐对泰东的经营有过如下描述:
说到营业,当民国九十年间,虽然有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类似创造社丛书的:沉沦,冲积期化石,玄武湖之秋,茑萝行等新书出版,但是,在那时候,书的销行却并不畅旺;直到民国十二三年,洪水半月刊出版前后,这初期的小说书,和创造周报合订本等等,都忽然特别的好销起来,在这时期中泰东似乎才获得了意外的收获,报答他过去难艰辛的劳绩。(注: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第100页,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
在讨论“亚东”经营思路时,上文已提到经济上“低回报”暗示的正是新诗集特殊的场域位置,在泰东这里,“长线的回报”同样是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的场域逻辑的体现,在20世纪,许多出版先锋性作品的出版社都以“非赢利”为始,随着先锋作品的经典化,又以最终的“赢利”为终,“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这种时间差距,有成为有限产品的场的一个结构性趋势”,(注: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99页,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象征性的文化逻辑,最终会返回商业的逻辑,落实为日后的回报。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尽情发泄了对泰东的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资本家的盘剥,实际上,是泰东经营上的混乱,(注:周毓英在《记后期创造社》中说:“老板赵南公糊涂,经理人换了好几个都是揩油圣手——同时外埠的烂账亦放得可惊,很少收得回来。”经营不善,自然谈不上优厚的报酬,但“创造社靠不到泰东书局的生活,却也不受泰东书局的拘束,甚至反过来还可以批评书店方面的人。”(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第7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才致使郭沫若等人生活无靠。泰东和创造社彼此相生相依的关系,其实更为重要,(注:沈松泉在《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中称:赵南公热心从事社会活动,但经营不善,“创造社和泰东断绝关系后,泰东在新书出版业中不再为文艺界所重视。”(《出版史料》,1989年第2期))而《女神》正是最初的契机。
由上述描述可见,无论亚东还是泰东,虽然新形象有异,但“新诗集”的出版,都发生在“新书局”自我形象的追寻中。在亚东,“新诗集”成为象征性的品牌;在泰东,《女神》开启了新书局的生路。二者都在不断分化的出版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新诗集”特殊的场域位置也随之有所表露:作为一种先锋性的产品,它的独立和自足都来自“新”这一价值标尺,而在读者的有限以及“颠倒的经济逻辑”正是这一形象的前提。作为参照,新诗在力主教科书和大型丛书的商务那里,受到的待遇明显不同。作为占有市场主要份额的大书店,商务等出版者虽然看重新文化的实力,但走的是一条稳健的出版路线,既不求新,也不趋俗。一般说来,对于新作家的处女作品很少出版,虽然一度出版文研会丛书,但后来“不注意此条路线了”。(注: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149页。)在这种路线中,新诗自然不受重视,刘大白的《旧梦》,在商务的遭遇可以为证:“从付印到出版,经过了二十个月之久;比人类住在胎中的月数,加了一倍。这在忙着‘教育商务’的书馆中一定要等到赶印教科书之暇,才给你这些和‘教育商务’无关的东西付印,差不多是天经地义,咱们当然不敢有异议。”(注:《<邮吻>付印自记》,《刘大白研究资料》,第133页,萧斌如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新诗”所代表的新文化品牌,对商务这样的大书局并不重要,而亚东、泰东则必须以“新”为自己生存的出路。
三
在新诗的“发生空间”拓展中,“新诗集”与“新书局”间的关系,显现了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奇妙交织:“新诗集”的印行、流布,无疑要依赖“新书局”的积极支持,而“新书局”从新诗集的出版上,不仅获得了经济上的回报,更重要的是,积累了“象征的资本”,提升了自己的新文化形象,一种特殊的文化逻辑得以显露。如果进一步考察,二者的互动关系,其实还不止体现在上述层面,在新诗集出版过程中,早期新诗坛的某种内在分化,也在悄然发生中。
在1922年出版的《新诗年选》上,编者曾有一段话被广为引用:“胡适登高一呼,四远响应,新诗在文学上的正统以立。”(注:《一九一九年诗坛纪略》,北社编《新诗年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在这段话中,所谓“正统”,不仅意味着形式、观念方面合法性的确立,也意味着社会影响力的扩张和一个新诗坛的出现。毋庸讳言,这首先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空间,不断吸纳着更多的读者和新诗人;但从反思社会学的角度看,它还是一个排斥性的、不断产生内在区分的空间,不仅要在与既有诗坛的区分中建立自己的边界,即使在新诗的“正统”内部,也有中心,有边缘,冲突和分歧也在所难免。
在这个充满吸引力和挑战性的新诗坛上,一个新诗人要占据一个正统位置,发表、出版似乎是“入场”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是“诗集”的出版,是最为有效的方式。在新诗发生的初期,由于出版品的稀少,出版一本诗集便可使诗人暴得大名,并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经典之地,有人就嘲讽说:“目下几位有集子的‘诗人’,既富于传世的勇气,又好取两个轻巧的字面,题为集名。”(注:齐志仁致沈雁冰信,《小说月报》13卷7期,1922年7月10日。)其具体的影射,可以大致揣测(《冬夜》《草儿》等诗集,都是以两个字为名)。苏雪林为此还曾为朱湘的《草莽集》抱怨:这本有价值的新诗集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就是因为出版得太晚了。(注:《论朱湘的诗》,《苏雪林文集》3卷,第143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诗集的有无,直接影响了个人诗坛地位的升沉,而诗坛的分化,更是暗含在其中。
上文已提到,作为新诗的“专卖店”,亚东图书馆几乎包揽了早期新诗集的出版,而胡适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具体说来,《草儿》、《冬夜》、《蕙的风》、《胡思永遗诗》等诗集的作者都是胡适的学生、晚辈或同乡,《渡河》作者陆志韦也是胡适的北大同人,其稿本出版前就由胡适看过,(注:见1923年9月12日胡适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4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其中的人事关联不言自明,其中许多诗集的出版,很可能与他的推荐有关。在亚东诗集序列里,胡适费心最多的应该是汪静之的《蕙的风》。汪静之与胡适的关系非同寻常,(注:汪静之与胡适既是安徽绩溪的乡亲近邻,汪未婚妻的小姑曹佩声(也是汪静之少时的恋人)还是胡适的女友,在曹佩声的牵线下,汪静之开始与胡适频繁交往。)作为一个中学生,汪静之最初能够在《新潮》、《新青年》上发诗,俨然成为诗坛上一颗令人艳羡的新星,特殊的人事背景自然增添不少的助益。(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黄艾仁《同路同乡未了情——胡适对汪静之的关怀及其他》,《胡适与著名作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蕙的风》当初是汪静之自己直接投寄亚东,但并不顺利,他转而寄给胡适,请他作序。(注:1922年1月12日,汪静之写信给胡适说:“拙诗集起先也是直接寄给原放先生的,现在因为种种困难,竟破例请你介绍,实有不得已的苦衷!”(《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7册,第632页,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得不到回音时还写信催促,在1922年4月9日给胡适信中,汪静之抱怨《蕙的风》音讯全无:“我们居于小学生地位的人要想出版一本诗集这点小事情竟遭了这许多波折,我实在不耐烦了。”(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7册,第639页。)可以说《蕙的风》能够被接受,多亏了胡适的介入。
相比之下,《蕙的风》的姊妹集《湖畔》(同是湖畔社的出品),却没有如此的幸运。最初,《湖畔》计划是由应修人带回上海,“准备找一个书店出版”。(注: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第18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而应修人最先找到的书店就是亚东图书馆,但遭到拒绝,理由是“因为诗集一般销路不大,无利可图”。(注:见汪静之《修人致漠华、雪峰、静之书简注释》,《修人集》,第24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无利可图”,大概只是《湖畔》遭拒的一个原因。虽然,湖畔诗人与他们的老师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关系密切,应修人在20年代初诗坛上的活动能力也相当可观,但还是缺少胡适这样能影响书局的靠山,最后只能由应修人自费出版。后来,当后期创造社的小伙计痛斥出版界的黑暗时,一条罪状就是“看情面收稿”:“你的著作,只要经过名流博士介绍吹捧,哪怕是糟粕臭屎,定令帮你出版。”言语之中,明显是在影射胡适与亚东的关系。(注:霆声《出版界的混乱与澄清》,1923年《洪水》1卷5期。)
胡适对后起之秀的接纳是很著名的,不仅推荐出版,还积极推介、评论,为《蕙的风》、《胡思永的遗诗》作序,(注:梅光迪就讽刺过:“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美。”(《评提倡新文化运动者》,《学衡》1期,1922年1月))《冬夜》、《草儿》出版后又做过重要的书评,在《谈新诗》、《尝试集》自序等文中,不忘对当时的新诗人进行一一评价。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点到的基本上都是他的朋友和北大的师生,“自家的戏台”里没有一个“外人”。海外学者贺麦晓曾从“文学场”的角度,分析了汪静之与胡适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传统的师生、同乡关系,是中国“文学场”形成的特殊方式。(注:见贺麦晓《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场”》,《学人》15期。)这一结论成立与否,还有待讨论,但确定无疑的是,胡适是将“亚东诗集”当成了“自家戏台”,并有意无意地将这一“自家戏台”放大成正统的“新诗坛”。
这一正统的新诗坛,还可以从20年代初出版的三本诗歌选集(《新诗集》、《分类白话诗选》、1919《新诗年选》)中见出,如果考察一下这三本集子中诗人及发表刊物的入选情况,可大致见出一个基本相似的分布:以胡适、周作人、沈尹默、康白情、傅斯年等北大师生为主的“北方诗人群”占据着正统诗坛的中心。(注:《新诗集》入选56位诗人,选诗最多的几人是胡适(9首),周作人(7首),康白情、刘半农、玄庐(三人都是6首);其他顾诚吾、辛白、王志瑞、沈尹默、郭沫若、俞平伯、王统照、戴季陶、傅斯年等均为二三首;《分类白话诗选》选诗人68家,与上集大致持平。选诗最多的是胡适(35首),玄庐(15首),沈尹默(14首),刘半农(12首),郭沫若、田汉(9首),俞平伯、罗家伦、傅斯年、戴季陶等为四五首。《新诗年选》选诗人40家,入选最多的诗人是胡适(16首),周作人(8首),傅斯年、刘半农、沈尹默、郭沫若(5首),康白情、罗家伦、俞平伯(4首),玄庐(3首)。)当时就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说《新诗年选》“所选的都是几位常在报章里看见的名字,因为他要应酬到所有出名的诗人,于是对于不出名的人底好诗,就不能容纳”。(注:猛济《<湖海诗传>式底<新诗年选>》,《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9月18日。)遭到责难的“选人”方式恰恰也说明了,上述选本对“诗坛”构成的反映。
四
以亚东图书馆和亚东诗集为中心,一个正统的新诗坛浮现出来,而出版《女神》的泰东图书局的位置颇有意味。上文已经分析,虽然同为“新”的书店,亚东、泰东的形象还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亚东”依靠的主要是北方的新文化精英,“泰东”周围聚拢的则是上海及周边地区、被排斥在精英阵营之外的城市文人,这种人员构成势必影响到了其出版品的倾向。泰东旗下王无为主编的《新人》杂志,曾辟出专号进行新文化运动调查,但主要目的是借此攻击陈独秀和北京大学,雄心勃勃,好像要争夺新文化领导权,指责北京最高学府出现不久,“就发生了包办文化运动,垄断学术等事实”;(注:《最高学府——万恶政府》,《新人》1卷5号,1920年8月。)爱与胡适为难,并自告奋勇为胡适“改诗”的上海文人胡怀琛,其《<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也由张静庐安排,在泰东出版;而当吴芳吉《新群》杂志上发表“以旧文明的种子,入新时代的园地”的另一种新诗,招致“反对之声四起”,泰东新人社的王无为等人,还为他深抱不平。(注:《吴芳吉集》,第543页,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10月。)给人的印象是,泰东在迎合新文化潮流的同时,其聚拢的文人中多有意要在“新文化”中争风,并且与出版《尝试集》的亚东隐隐形成对峙,(注:1921年,亚东标点本小说出版后,有人撰文攻击,攻击者之一就有胡怀琛的兄弟胡怀瑾,汪原放在写给胡适的信中称:“胡怀瑾,我起先只晓得他和泰东接近,却不晓得他便是勇于批评人的胡怀琛的兄弟。他骂我的那书信,我好好的把它保存起来了;因为里面有些话着实可以作参考的资料。”(《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7卷,第508页,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从这段话中,不难体味出“和泰东接近”与攻击亚东在态度上的牵连。)《女神》的出版,也发生在这一格局中。在后来的回忆中,郭沫若多次表达过对泰东的不满,但《女神》能够在“泰东”的出版,还是与某种相似的边缘位置相关。
《女神》出版之前,郭沫若已通过《时事新报·学灯》上的新诗发表,确立了自己在诗坛上的地位,但这种“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已进入“新诗坛”的中心,以下几方面的情况值得考虑:首先,在讨论新文化的展开过程时,一个被较少论及的问题是,初兴的新文化阵营的内部也包含着论辩,其中《时事新报》,作为研究系的刊物,从政治背景上,恰与“新文化”精英处于对立状态,为了争夺某种“正宗权”,《时事新报》和《新青年》间还发生过若干次冲突。譬如,宗白华曾在《少年中国》1卷3期上发文批评“时髦杂志”,引起陈独秀的不满,批评与反批评在南北之间随即展开;而傅斯年也曾与《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在《新潮》1卷3号上围绕“建设”与“破坏”问题进行过论战,傅斯年当时就指出《时事新报》的意思不过是:“只有我们主张革新是独立的,是正宗的,别人都是野狐禅。”(注:《答时事新报记者》,《新潮》1卷3号,1919年3月1日。)在这种的论争背景中,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字,本身就是一件敏感的行动,郑伯奇在谈到这一点时,就表示过自己的看法:“《时事新报》是研究系的机关刊物。五四时代的青年对于这样有关政治的问题一般还是比较严肃认真的。”(注:《忆创造社》,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第842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而郭沫若的诗在《学灯》上大量发表,给他人留下的印象如何,不难想象。
其次,郭沫若基本上只在《学灯》上发诗,其他重要的“新诗园地”中却见不到他的名字。即使是在宗白华、田汉、郑伯奇都有所参与的《少年中国》,郭沫若发表的文字,也只是一两次的通信转载、文后札记,(注:《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附白,《少年中国》1卷9期,1920年3月。)没有正式作品发表。相比之下,当时比较活跃的新诗人,一般都在多家刊物上发诗,南北两方也多有交流,譬如上海的《星期评论》与北方的胡适群体就来往密切,《星期评论》及《晨报》上,南北两地的诗人名字都会出现,而《新潮》、《少年中国》的诗栏,几乎是被康白情、俞平伯、田汉三人支撑,与他们相比,郭沫若“出镜率”明显不够。
再有,从交游上看,郭沫若与正统的新诗坛也有一定的距离。由于资料所限,从1919年至1921年回到上海,郭沫若具体的交游往来很难还原。但除了与宗白华、田汉的通信,及在日本与创造社元老们积极往来外,他与国内的文学界并没有太多接触,郭沫若为此还发过牢骚,说自己与创造社元老们,“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者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注:《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册,第2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还有一个现象值得考虑,那就是郭沫若与“少年中国学会”的部分成员关系十分密切,宗白华还曾向学会成员建议:“若果遇有英杰纯洁之少年,有品有学,迥出流俗者——则可积极为之介绍。”(注:《致少年中国学会函》,《少年中国》1卷2期,1919年8月。)但作为少中骨干的他和田汉,为何没有推荐“精神往来、契然无间”的朋友郭沫若加入这个精英群体呢?况且郭与少中成员曾琦、王光祁、魏时珍、周太玄等人还是成都分社中学的同学,不能说不相互熟识。据陈明远的记录,晚年的宗白华曾谈起此事,说1920年郭曾有意入会,但遭到了一些会员的反对(大约正是他那些中学同窗),没有被批准,理由是郭早年有过多种不良行为。(注:见陈明远:《郭沫若的忏悔情结》,《忘年交——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第108页,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当然,他人的记述不能当做确实的史料,但郭沫若始终被这一精英群体排斥在外,却是个事实。倒是不满于新文坛的吴芳吉、陈建雷等人,(注:吴芳吉对北京的新文化人士,多有不满,曾讥弹北大学生,记取一二时新话头,“便可自命为文化运动之健将”。(《吴芳吉集》,第1329页,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10月)陈建雷是泰东“新人社”成员,也与吴芳吉相识(见吴6月5日日记,《吴芳吉集》1354页),他加入“泰东”的“新人社”的理由,就与对新文坛的不满有关:“我赞美《新人》的地方,是肯骂新派”,并“立志想专做攻击假新人的文章”。(《陈建雷致王无为》,《新人》1卷3期,1920年6月))与他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注:吴芳吉与郭沫若、陈建雷有通信来往,吴于庚申6月14日日记:得郭沫若日本福冈来书,“评吾《龙山曲》、《明月楼》诸诗为有力之作,而《吴淞访古》一律最雄浑可爱。”(《吴芳吉集》,第1355页)另有1920年7、8月郭沫若致陈建雷信,见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上述几方面情况,或许并不能完全说明郭沫若的文坛位置,但至少暗示着,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其文学活动与“正统新诗坛”,是有某种游离关系的。作为新诗人,他的声名已远播四方,但“异军突起”却是其基本的场域形象。从这个角度看,《女神》由同样位于某种“边缘”的泰东图书局出版,并引起巨大反响,显然打破了以胡适及“亚东”为中心的新诗出版格局,在亚东诗集序列之外别立一家,似乎重设了“正统诗坛”的坐标系。《女神》出版后,对新诗集十分关注的胡适也读到了,在日记中写道:“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注:1921年8月9日胡适日记,《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寥寥数语,表明了他最初的傲慢与不满。虽然他曾说也要如对待《草儿》、《冬夜》那样,为《女神》写一篇评论,但一直并未见下文,(注:胡适1923年10月13日日记中记录和创造社诸人吃饭,席间“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四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自家戏台”内外有别,或许就是原因之一。与胡适态度的暧昧相比,刘半农的话更为清晰地表明了《女神》的位置,他曾在信中焦急地劝胡适多作新诗,担心其“第一把交椅”被他人占去,“白话诗由此不再进步,听着《凤凰涅槃》的郭沫若辈闹得稀糟
百烂”。(注:1921年9月15日刘半农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卷,第132页,北
京:中华书局,1979年。)在刘半农眼里,对胡适“第一把交椅”地位构成威胁的,正是
果然,随着《女神》的热读,郭沫若的诗坛地位处于不断上升状态,很快就从开始时的一个普通诗人,跻身于最重要的诗人行列,形单只影地与北大诗人们平起平坐。(注:在1920年1月出版的《新诗集》中,郭沫若诗歌入选2首,在众多诗人中并不突出,在1922年的《新诗年选》中,其诗作的数目仅排在胡适、周作人之后、与傅斯年、刘半农、沈尹默、康白情、罗家伦、俞平伯等北大诗人大致相同。)更为重要的是,在读者眼里,《女神》与其他早期新诗集——尤其是亚东系列——的反差也渐渐形成,遥遥构成了新诗坛的另一极。诗人冯至在20年代初,就是新诗的一个热情读者,他回忆说,当时“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我都买来读,自己也没有判断好坏的能力,认为新诗就是这个样子。后来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继出版,才打开我的眼界,渐渐懂得文艺是什么,诗是什么东西”。(注:《自传》,《冯至全集》12卷,第60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在冯至这里,“好”与“坏”,“诗”与“非诗”的区分,是显现于《女神》与“亚东系列诗集”之间。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1922年开始,由新的一代诗人发起的,针对早期新诗的“批判”便此起彼伏地发生了,有读者惊呼“近来批评新诗的文学,却也连篇累牍,到处飞舞”,(注:素数《“新诗坛上一颗炸弹”》,1923年7月9日《时事新报·学灯》。)闻一多、梁实秋的《冬夜》、《草儿》评论,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以及《京报·文学周刊》上“星星文学社”的发言,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事件”。而在上述整体性的批判中,《女神》的位置耐人寻味,它似乎总是位于攻击的视野之外(在这几篇整体批判的论文中,几乎没有《女神》的名字),还隐隐构成了新诗的合法代表。相比之下,亚东版的新诗集,则无一例外成为火力的焦点。这表明,在新一代诗人的笔下,整体的批判或许同时也是“新诗坛”历史坐标系的一次重设。
尤其有代表性的是,对《女神》十分佩服的闻一多、梁实秋在《<冬夜><草儿>评论》中,不时引述《女神》诗句,以衬托《冬夜》、《草儿》的浅露,闻一多随后撰写的《女神》评论两篇,则确立《女神》的文学史形象。不仅如此,在筹备自己的处女作《红烛》时,闻一多还将《女神》作为主要的模仿对象:“纸张字体我想都照《女神》样子。”(注:《致吴景超、梁实秋》,《闻一多全集·书信》第11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红烛》从编次、标题到序诗,整本诗集似乎就是《女神》的一个翻版,并最终交由泰东,与《女神》同在一家书局出版,这一并非“偶然”的巧合似乎表明,闻一多的《红烛》,在亚东诗集系列之外,有意要靠近了新诗的另外一个起点。
标签:蕙的风论文; 文学论文; 郭沫若论文; 读书论文; 尝试集论文; 创造社论文; 冬夜论文; 亚东论文; 经济学论文; 新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