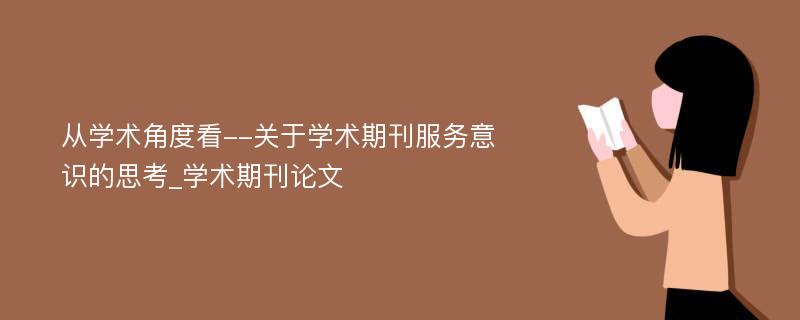
从学术的观点看——关于学术期刊服务意识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服务意识论文,学术期刊论文,观点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发生了什么变化?
20世纪关于思想史的叙述中,“终结”这个概念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语汇之一。贝尔等人常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指称现代思想的变化及其特点,他们所要强调的是,现代以来,意识形态作为统一的思想方式和价值理念已经“终结”,思想越来越多地受到某个事件或局部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梅洛—庞蒂等人更热衷于“身体”这个概念)的支配,并从而失去了统一性或某种类似“乌托邦”那样的价值和愿景。如果可以用贝尔等人的方式考察过去10多年来中国学术内部的一些变化,那么,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就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启示性概念。虽然这一做法会使那些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情有独钟的人——尤其是那些将其视为魔咒的人——受到较强的刺激,但是对于要真正认识中国学术变化中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方面来说,贝尔使用的概念及其考察方式则不仅是大有裨益而且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上,思想史的研究应当实际地考察学术和社会的现行过程,以期更加深入地理解学术与社会,而不应考虑某些人的个人偏好,更不应姑息或迁就他们的个人情感。这是这个领域最应当遵守但一直都没有很好遵守的一个原则。
如果把这个原则应用于进行中的中国学术实践,那么,至少可以获得如下现象描述:虽然中国学术的真正成果或有效性并不像我们在大大小小的论证或总结会上经常听到的那样显著,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变化实际地发生了。即使有着极为不同志趣的人也都不会否认,中国学术正在从“非学术化”操作及其评价方式中“脱胎换骨”,学术研究正从某些日常或政治性事件的附庸中摆脱出来成为一种逻辑自洽的专业活动(这一过程与其说是反思性的,不如是说跨越式的),从业者注销“集体户口”之后作为个体进入“后集体时代”,学术的自觉和自主性不断增强(在观念论层面比在实践中更为激进),所谓“规范性”和“专业化”也已——至少在“形式上”——大获全胜。
然而,不能不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深刻的思想运动并没有按其自身的逻辑展开,而正遭遇着表面化、外在化、形式化方面的危险,因为学界目前对于学术的形式方面的激情,远甚于对其内容的沉静追求。正因为如此,那场关于学术“规范性”和“专业化”的讨论,最终演化为学术期刊的形式方面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在“什么是合格的学术论文”这样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近年来开始流行的一个简单而顽固的标准却是:“有没有注释,尤其是有没有外文注释”。在教授们的学术活动中,在权威机关下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要求与规范及其实践中,这个标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学术论文之“形式要素”的凸显,如同在庄严而神圣的场所赫然树起一块“不准随地便溺”的金牌,造成令人哑然的学术景观。然而,问题的要害还不在于这一景观自身,而完全在于:在这张“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A Procrustean Bed)前,像柏拉图或维特根斯坦那样的思想者别无他途而只能在“学术的”神殿外徘徊、流浪了!
学术的这种变化对学术期刊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规范性”和“专业化”的要求不断地强化着学术自身的逻辑,“学术问题”本身具有的内在统一性影响或规定着学术的展开或进展,作为论文集散地的传统之学术期刊理念受到动摇,其操作方式也必须相应地加以改变。从而,学术期刊自身的定位及其在学术演进中的作用需要重新认识。这是深层次的影响。其次,“规范性”和“专业化”的要求和实践对编辑人员的知识背景和专业水平提出挑战,从而使编辑人员的资格及其对稿件的判断和处理方式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是浅层次的影响。这些方面的影响,使学术期刊与编辑工作处于前所未有的悬而未决之中。
二、反思:学术期刊的尴尬
随着学术的演进和学术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学术期刊在学界的地位一直在不断攀升。研究者越来越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否发表或在什么学术期刊上发表视为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不仅如此,而且各级学术主管部门也把能否发表或在什么学术期刊上发表作为最终的和惟一的评价指标。这种非学术的行政化评价方式,既增加了学术期刊自身的压力,又使学术期刊所具有地位与其在学术进展中的实际影响力分离开来,结果是:学术期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不是通过学术建立起来的,而更多是通过学术之外的其他手段建立起来的。这是学术期刊的一种尴尬之境。
所谓尴尬,指的就是学术期刊置身其中的那种“非学术化困境”,这一直是中国学术期刊的难言之隐,也是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主要根源。下面将从学术期刊的存在方式,结构方式和影响方式三个方面考察这种“非学术化困境”。
首先是存在方式。与国外许多学术期刊的存在方式不同,国内学术期刊并不隶属于某个学术团体或学术流派,而是隶属于某个行政机构。当然,有人会说是学术机构,但是从大多数学术机构的实际运作来看,还是用“行政机构”一语指称它们更为恰当和切中要害。这种存在方式,使学术期刊陷入一种“单位人困境”,就是说,期刊的主创人员并不像国外期刊那样来自不同大学或研究机构,而是一个单位,比如某个大学或学术机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单位人”,他的去留与任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取决于他所从事的学术,而是取决于学术之外的行政因素。因此,某个没有任何学术地位或学术素养不高的个体,在成为一个著名刊物的主编或编辑方面,不会遇到任何困难;而一旦这个某人占据那个位置,也不会遇到学术方面的质疑。显而易见,这种体制无法对期刊的自主性和学术性提供足够的保证。同时,局部利益或各种关系(政治学意义上而非哲学意义上)将轻易影响甚或左右编辑人员的行为,并借此渗透到稿件的选择、评审和刊发上去,客观性和公正性成为一个问题,学术期刊的评价功能遭到削弱而成为一种靠不住的东西。而在学术期刊把“话语霸权”进行“转包”或批发时,这一点更尤其如此。
其次是结构方式。国内有数以千计的学术期刊,分为所谓“综合类”和“专业类”两类。在研究者和世俗公众看来,这两类期刊都属于专业学术期刊。然而,从学术的观点看,这里所谓的“专业”,其程度是可以或应该受到质疑的,或者说,如果把所谓“专业期刊”理解为与“专业”有关也许更为合适。所谓“综合”,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把整体瓜分之后再加以组合而已;而所谓“专业”,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把整体瓜分之后再加以组合而已,不同只是在于,在后者那里,瓜分者不是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内部的各个分支。在瓜分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是“各学科或各分支学科间的平衡原则”(而不平衡则是一种潜在的禁忌)。如果一期刊物少掉一个学科或一个分支学科,那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有谁试图用一期刊物刊载一篇论文或讨论一个学术问题,那他若不是恶意捣乱也必定是个“棒槌”。因此,“组合”成为学术期刊惟一结构方式,而刊物自然成为某种“学科论文汇编”,而不是学术问题的研究。就大多数学术期刊而言,要想看出它们在关注什么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把它们半年或一年内的刊物加以综合考察,也很难发现它们在关注什么问题。因为那里仅仅汇集了一些观点或意见,而没有问题,更没有具有统一性的问题。这种方式,把学术期刊变成了不同观点或意见的零售柜台,对于学术发展而言,其意义和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第三是影响方式。学术期刊作为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不断受到研究者本人和管理机构的重视,对学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何考察和评估这种影响呢?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学术期刊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界,但恰恰对学术本身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影响,也就是说,学术期刊与其说是影响了学术的进展,不如说是更显著地影响了从业者的进退。一些著名期刊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早已成为行政部门关于研究者个人或单位绩效考核的工具。这种作为某种行政权力之延伸的期刊,对于研究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研究者能否在这类刊物上露面,就意味着他能否在权力结构和分配制度中获得更好的收益。正因为如此,一些名刊大刊在成就学者(或管理者)方面要比它们在推进学术方面做得更加成功。
上述三个方面的考察,对国内学术期刊的生态状况提供了一个简略描述。这一描述表明,学术期刊在运行方面过多地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困扰,而在一些最为基础性的问题上陷入混乱。这种混乱导致学术期刊以一种外在于学术的方式存在,从而没有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有机构成,没有成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没有在学术演变与推进中发挥它本应发挥的作用。这是学术期刊自身建设中需要正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结论:关于学术期刊服务意识的思考
学术期刊为学术服务,谁都不会否认这是学术期刊的内在规定性之一。对于学术期刊来说,服务意识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不为学术服务的学术期刊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但是,近年来随着期刊在学术评价体制中的扩张,服务意识成为一个现实性问题,并常常引起研究者的不满或批评。这些批评除了编辑技术方面的细枝末节之外,主要集中在研究者感到自身的自主性受到了伤害,在他们看来,编辑过多地介入了他们的工作,这既违背学术期刊的服务本性,同时也给学术造成了某种危害。这些批评和不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期刊运作中非学术化因素造成的。比如,在学术期刊的评选中有一条古怪的非学术化标准,不能留白,也不能跨页和补白。有鉴于此,研究者的论文必须压缩、限定在固定的篇幅之内。如果这项工作让作者本人来做,他通常是“压缩”到比原来的篇幅还长,编辑只得自己操刀进行删改。这常使作者大为不满。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批评反映出一个深层次问题,那就是对于学术期刊服务意识的严重误解。
如何理解学术期刊的服务意识呢?首先必须破除“自主性之幕”。“自主性”是近年来学术期刊内部和研究者个人各执一端大加强调的问题。在学术期刊内部,讨论最多是编辑的职业化、学者化、主体性和所谓“规范化”,尽管这些概念含混不清,但其含义是清楚的,那就是要把学术期刊“建设”成一种“自主性实体”,以实现它对学术以及研究论文的优先权。与此相反,在学术研究的共同体内部,研究者则大谈作为个体的研究者的个性以及研究工作自身的逻辑,从而把研究者想象或建构成“自主性个体”,以对抗某种令人厌恶的“话语霸权”。其实,讨论学术期刊的“自主性”或研究者个人的“自主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二者都不真正具有什么“自主性”,如果真有所谓如此这般的“自主性”的话,那也只是学术自身所可能具有的东西。总之,“自主性”的幻象遮蔽了学术期刊、研究者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与学术发展之间的联系。只有破除“自主性之幕”,才能擦亮眼睛,在学术期刊、研究者个人与学术发展之间的真实联系中,理解和定位学术期刊的服务意识。
显而易见,所谓学术期刊的服务,其全部含义只不过是说它是要为学术服务。这是它的内在性质以及它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知识的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由创造者创造,然后发表,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效果或作用,才最后完成。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始终是学术内部的一个事件。因此,只有从学术期刊与学术发展的关系中,才能恰当地认识和评价它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期刊不能为研究者服务,而只是说为研究者服务只是它为学术服务的一种感性形式。
那么,学术期刊应该如何服务呢?这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考虑。第一是它有责任和义务随时校正学术研究中的一些倾向。在学术研究中,个性化总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个性的强调,有时会使研究者忽略某项研究或其成果的社会意义,而学术期刊由于自身和社会受众的天然联系,能够容易地发现这种个性化偏差,并及时予以纠正。学术期刊的这种服务方式,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当研究领域成为“市场假相”或“洞穴假相”的剧场或战场时,这一点就更是如此。
第二是它必须选择学术和现实中的问题,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当然,这种问题的选择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完全建基于一个学术期刊对于学术的深刻理解和对社会生活深刻的把握之上的。它所选择的问题及其所组织的研究,能够有效地推动学术的发展,加深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它还必须具有一种十分清醒的“自我意识”,那就是在进行这种选择和推动与之相关的研究时,它还要充分地考虑学术传统的建构与形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