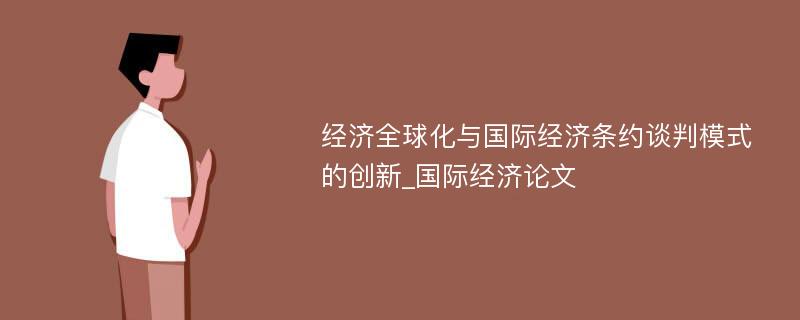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约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方式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推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或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法律途径是,各国通过谈判缔结或参加有关国际经济条约,共同承担减少对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及信息等跨国流动障碍的国际法律义务。然而,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或自由化给每个国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非一致。有鉴于此,各国在参加国际经济条约谈判之时,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势必寻求趋利避害的有效对策,从而导致各种新的谈判方式的引入和运用,使得国际经济条约的谈判方式日趋多样化。
一、经济全球化与双边、多边及复边谈判方式
以往,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远未达到全球化的程度,一国往往有相当的余地根据本国的利益和政策,通过“一对一”的双边谈判方式确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法律关系;相应地,传统的国际经济条约多表现为双边条约。最典型的是所谓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此类双边条约曾是各国处理相互间商务关系的最主要条约形式。以美国为例,从1778~1966年,共对外缔结了130多项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注:参见H.J.Steiner & D.F.Vagts:Transnational Legal Problem,3rd ed.,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86,pp.637-638.)然而,这种经双边谈判形成的国际经济条约架构,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1.通过双边谈判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缺乏稳定性 就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而言,其缔结往往以对等交易为前提,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缔约方随时可能予以废止。因而,“一般并不把这些贸易协定当作通常正规国际义务的那种严格承诺来看待。协定的脆弱性排除了任何稳定性。”(注:引自R.E.Hudec,The GATT Legal System:A Diplomat's Jurisprudence,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4,1970,p.617.)例如,20世纪初,法国和英国为了防止和转嫁经济危机,曾相继公开废除两国间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2.通过双边谈判形成的各种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缺乏应有的统一性 因各国经济利益的不同及谈判实力的差异,相互间在双边经济条约中确立的权利义务标准必然参差不齐。例如,虽有经合组织范本和联合国范本,但各国谈判达成的双边税收协定不可能完全吸纳这些标准条款,其所涉的避免双重征税的法则也无法统一。由此,在一缔约国从事商务活动的其他各缔约国居民所享有的税收待遇就会有高有低,以致造成各自竞争地位的不平等。此外,还可能带来第三国居民套用税约的问题,(注:所谓的“第三国居民套用税约”,是指第三国居民通过在某一特定税收协定的缔约国一方设立中介机构(通常是一家子公司),间接取得本无资格享受的该税收协定提供的优惠待遇。详见朱炎生:《第三国居民套用税约的法律管制措施评析》,载于《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427页。)等等。
3.通过双边谈判难以形成完整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在双边层面上,最终需要编织一个庞大的双边经济条约网络,才能全面地处理各国之间的经济法律问题,在实践中,这是难以企及的。仅以国际投资领域为例,从1959~1996年上半年,世界158个国家共缔结了1160项双边投资条约,其中近2/3是在20世纪90年代订立的。就这一现象,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曾精辟地评价道:“一个完整的双边投资条约网络的形成大概需要2万个双边投资条约(将花费许多年的谈判时间),这不但不能缓解问题,反而会使问题趋于恶化:如此广泛的网络给(来自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投资者以及各国政府带来的分歧、繁琐和不稳定,将变得更加严重,处理它们将需付出更高的成本,包括增加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和加大在一些国家投资的风险。”(注:引自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6,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1996,p.166.)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世界经济尚未进入全球化的阶段,多国间的经济联系也不可能被完全割裂。所以,各国在通过双边途径处理对外经济法律关系时,在双边经济条约的架构内,势必得考虑多边的因素,其中,联系各双边经济条约的纽带就是最惠国待遇条款。然而,近代各国普遍使用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虽然强化了其将双边法律关系“多边化”的功能,但有时会造成受惠国实际上从对方单方面受益的结果,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注:参见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Overview),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1998,p.8.参见杰克逊等(J.H.Jackson,W.J.Davey & A.O.Sykes,Jr.):Legal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West Publishing Co.,1995,pp,438-440。有关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多边化效应”的局限性,例见,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史上,从第1回合(日内瓦回合)到第5回合(狄龙回合),就关税减让一直采用的是“双边谈判,多边适用”的方式。在这种“产品对产品”的谈判方式下,谈判的任务主要由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来承担。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再通过关贸总协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将谈判结果扩大适用于全体缔约方。该方式把关税减让谈判集中于主要进出口方之间,虽然加快了谈判的进程,但是,一缔约方如果就某产品大幅度减让关税,而使所有的其他缔约方受益,在其他缔约方就另一些产品谈判减让关税幅度不大的情况下,那么,就会造成缔约各方之间利益的不平衡,以致最终形成各谈判国都不愿作出让步的僵局。为了打破这一僵局,从第6回合(肯尼迪回合)开始,关贸总协定改用了“直线减让关税”和“调和减让关税”等多边谈判方式。)从而使该项待遇原则的广泛推行受到限制。
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具有可预见性和透明度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二战结束前夕,各国深刻检讨和总结了战前双边经济条约制度失灵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谈判缔结了多边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创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留下了成为战后多边贸易体制支柱的关贸总协定。
20世纪80年代以降,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步入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各国经济相互间依存关系的深化,一国在制定对外经济法律政策时,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将对其他相关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因此,各国在对外经济法律政策的选择上,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利害关系,彼此间不得不进行协调,而且这种协调仅在双边层面上进行已远远不够,需要做出妥当的多边安排,共同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才能有效地处理全球性的经济法律问题。
如所周知,在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领域,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第8回合)一次性达成了25个多边协定。世贸组织成立后,多边谈判的领域更为拓宽,深度也不断加大。
在国际投资领域,20世纪90年代,通过多边途径制定一部综合性国际投资法典的构想,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经合组织从1995年开始《多边投资协定》(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on Investment,简称MAI)的谈判,该项谈判虽于1998年10月失败,但发达国家仍意图“移师”世贸组织,在新一轮回合(千年回合)中重开MAI的谈判;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下,联合国贸发会议也展开了制订多边投资法律框架的努力。这些多边谈判意在打破以双边投资条约作为跨国投资主要国际法律渊源的现有格局。
国际税收领域历来由双边税收协定独踞。截至1998年底,各国共达成了1871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注:参见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Overview),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1998,p.8.)为了消除现行双边税收协定存在的网络残缺、标准不一、解释各异及第三国居民套用税约等诸多弊端,国际间要求在多边层面上解决双重征税问题的呼声渐高。(注:详见M.Lang等,Multilateral Tax Treaties:New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Tax Law,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8,pp.85-103.)
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生的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多边化,是国际经济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总体上看,我国不能一如既往地依靠双边经济条约(如双边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条约等)维系对外经济法律关系。为了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经贸法律环境,我国不应消极对待国际经济条约的“多边化”谈判方式,即不能长期“游离”于国际经济法律体制之外。正因如此,一直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不懈地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并要求美方放弃不稳定的双边最惠国待遇关系,给予中国多边贸易体制下的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地位。与此同时,我国加入多边谈判这一国际经济立法过程,还可以积极、主动地团结与自己有着共同利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抗衡,争取在谈判中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当然,对于可能开启的对自己不利的某些国际经济条约的谈判(如世贸组织拟扩大的包括劳工标准、环境措施在内的新议题),我国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坚决予以抵制。
然而,应当看到,多边谈判涉及的参与方数量多,如各方对议题存在严重分歧,则谈判的进程将被延宕,且最终可能归于失败。因此,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多边谈判方式将“唯我独尊”,完全排斥双边谈判的途径。即使在世贸组织这样一个多边论坛,双边谈判方式仍有用武之地,在不少重要领域,传统关贸总协定“双边谈判,多边适用”的方法,继续得以沿用,并且有所扩大。例如,一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需要与有关成员方进行开放市场的谈判。这种谈判往往以双边的方式展开,因双边谈判的对手只有一个,从技术上而言比较容易成功,一旦达成协议,即可通过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之“多边化”。中国“入世”谈判因循的就是这一程式;(注:参见罗昌发:《国际贸易法》,(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20-121页。)又如,在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项下,就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具体承诺义务的谈判,也可采取双边途径,最后经由最惠国待遇原则,将双边谈判的成果扩大适用于其他所有成员方。
对于某些艰难的谈判议题,一般难以一步到位,在世界各国间取得共识,求得妥协。于是,便产生了所谓的“复边”(plurilateral,又译“诸边”)谈判方式,即先在部分利益相近的国家之间达成协议,然后对外开放,通过各种手段促使其他国家参加或由它们自愿选择参入,以便最终实现此类国际经济条约的“多边化”。在实践中,复边谈判方式常见的情形是,发达国家共同坚持权利义务的高标准而不愿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以致无法达成多边协议。例如,在乌拉圭回合中,就减让关税的谈判,美国、前欧共体、加拿大、日本曾组成“四边集团”(quadrilateralgroup),相互协调立场,将若干工业品的关税削减至低水平,乃至零关税,然后进一步说服其他发展中国家接受其减让方案;又如,在关贸总协定的东京回合(第7回合)中,就限制若干非关税措施的谈判,为了强化大国决策的重要地位,在美国的策划下,最后制定了9个守则,供各缔约方自由决定是否接受,而实际参加者多为发达国家;(注:这些守则涉及技术壁垒、政府采购、反补贴、牛肉、奶制品、海关估价、进口许可证手续、民用航空器贸易、反倾销等领域。)后经乌拉圭回合谈判,其中的5个守则现已“升格”为多边货物贸易协定,但仍有民用航空器贸易、政府采购、奶制品及牛肉等四协议继续以复边形式存在;再如,在制订MAI的过程中,经合组织采用的也是复边谈判的方式。发达国家第一步拟在其“俱乐部”内达成一个高标准的复边协议,之后再运用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将该协议渐次“推销”给作为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集团这种试图将自己惬意的规则“多边化”的过渡措施,发展中国家应保持充分的警惕。
二、经济一体化与“分项”、“一揽子”及“构组”谈判方式
以往,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活动,如贸易、投资、金融及技术转让等,虽有联系,但尚未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程度;相应地,各项国际经济条约的谈判通常是各行其是,分开进行的,亦即“分项”(sector)谈判法为缔结有关国际经济条约的主要方式。
对于不同领域的各项国际经济条约,一般采取分别谈判、各国自愿参加的方式。1944年7月,在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会议”首先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在贸易领域,各国又于1945年11月启动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哈瓦那宪章》)的谈判。这项谈判后虽夭折,但从中暂时剥离,单独谈判达成的关贸总协定,则从1948年1月开始“临时适用”,并经数度修改,一直沿续至今;二战之后,在国际投资领域,一些国家政府、国际组织、民间机构及个人也不断致力于国际投资法典的谈判和制定工作。
同样,对于相同领域的各项国际经济条约,也多采用分议题谈判的方式。如前所述,东京回合达成的有关规制非关税壁垒的9个守则,便由各缔约方自愿选择参加,缘此,人称关贸总协定成了一份可供“挑选”(pick and choose)的“菜单”(a la carte)。(注:参见杰克逊等,注[5]引书,第302页。)
晚近,与时俱来的经济一体化浪潮,不但意味着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块状”融合,而且不断推动各领域国际经济活动的“条形”整合;反映在国际经济法律渊源上,首先出现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与国际经济法制接轨的趋向;与此同步,在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内部,贸易、投资、金融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国际经济条约,相互交融,联系程度空前紧密;换言之,各国需要在综合平衡多领域、多方面利益的基础上,彼此妥协,以求建立比较完整的国际经济法律体制。于是,“一揽子”(a single package or single undertaking)协议方式便应运而生。所谓的“一揽子”协议,是指缔约各方就多个领域、多种议题展开谈判,并应同时全盘接受谈判达成的所有协议,不能只挑选接受其中的部分协议而拒受其他协议。乌拉圭回合首开这种谈判方式之先例。
无独有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出现金融危机的成员国提供贷款时,其与成员国磋商达成的“备用安排”,形式上虽非国际经济条约,但作为包含贷款条件的双边文件,内容也越来越具有综合性,涉及金融、投资、贸易等各个领域。(注:详见拙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利益分析和法律性质》,《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第113-116页。)
在同一领域,晚近国际经济条约谈判的议题也更为“综合化”。例如,传统的国际投资条约,包括60年代以来签定的众多双边投资条约和1965年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华盛顿公约》)、1985年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汉城公约》)等单项多边投资条约,基本上只涉及投资保护问题;乌拉圭回合虽将投资管制问题纳入了谈判的范围,但仍只限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这一狭小议题。而其后经合组织有关MAI的谈判,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投资保护(投资待遇;征收、汇兑及战乱等政治风险保证和投资争端解决)和投资管制(投资准入;业绩要求;主要人员流动和私有化、垄断、国家企业及特许权等)议题,此外还把触角伸向投资鼓励问题。
相对于传统的“分项”谈判方式,“一揽子”协议方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的优点:
一方面,通过“一揽子”协议方式有助于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国际经济法律体制。既为“一揽子”协议,所涉领域当然比单个国际经济条约的适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就乌拉圭回合而言,除4个复边协议之外,达成的“一揽子”协议共有25项,加上各成员方承诺书及附件,篇幅近3万页,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自由化及争端解决等诸多部门,构成了一部宏大的国际贸易法典。(注:参见The WTO Secretariat,Guide to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Foreword,1999.)
另一方面,通过“一揽子”协议方式有利于求得各方权利义务的综合平衡。这种平衡可能会产生的功效主要有:
首先,“要么全有,要么全无”(all or nothing)的谈判规则,有助于防止一些国家按照单方面的利益逃避某些议题项下的国际经济法律义务。例如,在以往的“分项”谈判中,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对农产品和纺织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这两项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贸易项目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乌拉圭回合则将《农产品协议》和《纺织品和服装协议》打包入“一揽子”协议,促使发达国家据此作出承诺,逐步将农产品和纺织品贸易回归总协定。
其次,利用综合平衡的“杠杆”,谈判实力较优的一方可能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迫使对方接受与谈判主题相关的其他议题。自乌拉圭回合以来,发达国家极力主张将投资、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政策乃至商业腐败等归为与贸易“有关”的议题,纳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议程。总体而言,开启这些议题的谈判大门,对发展中国家可谓弊大利小,(注:就这些与贸易有关的议题的谈判,其中,实现国际投资自由化,意味着发达国家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最为有利的投资场所。无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将促进发展中国家吸收更多的外资。然而,急速的和高度的投资自由化将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调控外资的能力;提高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水平,固然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但发展中国家也将因此失去许多廉价仿制外国技术的机会;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和提高劳工标准,诚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改善人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因均需大量投资,将带来发展中国家产品成本的高涨,从而严重地影响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贫困化;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政策,将有利于发达国家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过,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对本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采取的扶持政策也将受到严重限制;清除商业腐败(如贿赂),将为外国产品提供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准入机会,但发展中国家也不无忧虑,发达国家将藉此干涉其立法、司法和执法等内部事务。)假如在世贸组织之外分别组织各议题的谈判,必遭发展中国家抵制。而只要引入“一揽子”协议方式,发达国家便可舍贸易领域的某些利益为对价,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让步,以同意在世贸组织内接受这些新议题;待这些议题“登堂入室”之后,再谋求在后续谈判中扩大“战果”。例如,对于投资议题的谈判,发达国家就充分运用了这一谈判策略;申言之,在乌拉圭回合中,发达国家开始力争将这一议题纳入谈判的范围,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以便取消那些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投资措施。然而,在发达国家看来,该协议在实现投资自由化的深度和广度上,还远未尽如人意,于是,它们利用TRIMs协议实施5年期满的评审机会,从投资与贸易有着广泛联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主张,在世贸组织新一轮回合的谈判中,对国际投资法律问题展开全方位的谈判。对于发达国家利用“一揽子”协议方式采取的这种“先得寸,后进尺”的策略,发展中国家要有清醒的认识,应从长远的角度评估引入这些新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避免为了从发达国家那里取得眼前的某些利益,而轻易接受对方提出的新议题,以至因小失大,贻患无穷。
此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借款国磋商达成的“备用安排”中,发达国家经常借发展中国家情势危困之机,将一些与解决借款国金融危机及国际收支问题并无直接联系的“有关”调整措施,如要求借款国维护社会公平、保持政治稳定(包括清除腐败)、尊重人权、改善立法和司法等作为贷款条件,“搭售”给这些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注:参见杨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性”法律问题分析》,载于《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357页;另见拙文,同上,第116-117页。)
再次,采取“一揽子”协议方式,可使谈判成果通过尽可能的交叉赢得多数参与方的支持,即谈判各方可以一些领域的妥协换取对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注:详见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组织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刘平、洪晓东、许明德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中译版,第50-59页。作者采取博弈论分析了多边贸易谈判中议题挂钩的成败与得失。)例如,在乌拉圭回合中,发达国家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以及清除投资措施等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在这些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少有利益;反之,对于纺织品和农产品贸易,发展中国家较之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假如就各项议题采取“分项”谈判的方式,因双方利益存在严重分歧,恐难有成效;只有通过“一揽子”协议,以“交易”的方式,方能使各方接受在“分项”谈判方式下本来不愿接受的协议成果。(注:参见P.Demaret,The Metamorphoses of the GATT:from the Havana Charter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34,1995,pp.133-134.)
最后,在世贸组织体制的框架内,通过“一揽子”谈判法达成多领域的协议,还有利于实现“交叉报复”。例如,在发展中国家违反《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未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实行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因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低,其存在于发达国家的专利、专有技术、商标、著作权等数量有限,发达国家如采取“同态复仇”的方式,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不依TRIPS协议予以保护,几无实际意义;只有通过其他领域的报复,如撤回其在有关货物贸易协定项下的减让,限制进口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出口产品,方有实效。反之,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强势而违背协议的各种做法,也可运用“交叉报复”的手段,予以制约和制裁。
当然,“分项”谈判方式和“一揽子”协议方式各存利弊。在后一方式下,只有待多数参与方全部接受形成的协议,谈判才告终结,这样将会拉长谈判的进程;相反,在“分项”谈判方式下,可以采取“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战术,就一些容易谈判的议题先达成协议。故此,在实践中,各谈判方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主张选择“分项”谈判方式或“一揽子”协议方式。例如,就服务贸易的谈判,在世贸组织成立之后,发达国家挟其优势,一改过去在乌拉圭回合中坚持的“一揽子”协议方式,力主“分项”谈判法,并在金融服务、基础电信、信息技术等领域,推动相关协议的达成;而在海运等对自己相对不利的领域,发达国家则不愿做出让步,致使谈判迄无成果。为了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况,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指出,在今后的服务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争得“一揽子”协议方式,迫使发达国家在一些领域做出整体妥协。(注:参见M.Mashayekhi & M.Gibbs,Lessons from the Uruguay Round Negotiations on Investment,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3,1999,p.19;A·Kawamoto,Regulatory Reform 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Agenda,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1,1997,pp.102-103.)
在拟开世贸组织新一轮回合谈判之前,各国曾就谈判方式产生相当大的歧见。欧盟和澳大利亚认为,“分项”谈判不能解决世贸组织成员面临的问题,唯有“一揽子”谈判法有望获得成功。这种主张得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赞同;美国尽管在乌拉圭回合中曾主倡“一揽子”协议方式,但时过境迁,此次却凭其雄厚的谈判实力,在支持以广泛的议题展开多边谈判的同时,偏好“分项”谈判方式,认为“一揽子”谈判法将不必要地拖延达成协议的时间;作为一种折衷方案,加拿大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谈判方式——“构组”(clustering)谈判法,即在特定期限内,汇集各关联议题,组成若干组展开磋商。诚然,这种新方法有利于在一些比较容易的议题上早日斩获成果;相对于“分项”谈判方式而言,也可能产生“成片”收获的效果,但它忽视了把相关议题汇集构组的具体办法,因为构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需以一定方式进行谈判才能解决的难题。(注:详见薛荣久:《新贸易课题——世贸组织新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议题与前景》,《国际贸易》1999年第7期,第5-6页。)
三、经济自由化与“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及“逐步回归”谈判方式
经济自由化将使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及信息等跨国的自由流动及其保护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经济自由化的程度和步骤必然存在分歧。正因如此,晚近,国际经济条约多把促进经济自由化作为基本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因对自由化进程安排有异,各国际经济条约的谈判方式就此也将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其一是“自下而上”(bottom-up)谈判方式的采用。在这种谈判方式下,允许各缔约国对国际经济条约进行宽泛的保留,形成一个较低起点的标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续谈判,逐步提高自由化水平。在服务贸易领域,世贸组织所使用的即属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谈判方式。由于服务业竞争能力的高低取决于资金、技术、信息、管理、人才等因素,故各国尤其是南北双方之间,对服务贸易自由化所持的立场大有冲突。为了扩大本国服务的输出,发达国家力促服务贸易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为保护和扶持民族服务业,多对服务业的开放持谨慎态度。审时度势,在起始阶段,世贸组织不可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定调太高”,否则,只会“曲高和寡”,导致发展中国家抵制该领域的谈判。就此,乌拉圭回合引入了“自下而上”的谈判方式,其达成的GATS将成员方的义务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义务”,即所有成员方均应承担的相对比较容易履行的义务,如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及例外条款等;另一类是“具体承诺义务”,构成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核心部分,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方面内容。但是,每一成员方只在各自提交的“承诺表”(作为GATS附件)划定的范围内承担上述两项义务;详言之,承诺表将列出成员方同意开放的服务部门,其他部门则暂不承担自由化义务;即便在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成员方仍有权对这两项义务的履行设置条件或进行限制。可见,GATS项下的具体承诺义务是一种非统一的、低水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义务。(注:例如,在乌拉圭回合达成GATS之时,发达国家承诺开放的服务门类不过半数左右;至于发展中国家,约有1/4成员方在承诺表中只承诺开放3%的服务门类。参见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8页。)这种承认各国差异,并削低“门槛”的做法,使得GATS易为各成员方所普遍接受。但此举并非一种永久性的安排,在世贸组织成立之后,各成员方仍有义务通过双方或多边谈判,逐步减少乃至取消各种限制性措施,以不断提高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水平。
其二是“自上而下”(top-down)谈判方式的采用。在这种方式下,先在国际经济条约中设定高层次的自由化标准,再允许缔约国经谈判对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作有限的保留,且缔约国应承诺逐步取消这些作为例外情形的限制性措施。在MAI的谈判过程中,经合组织“大胆”引入了“自上而下”的谈判方式。从MAI的草案来看,其在投资自由化的领域和高度上,较之现行的双边投资条约,都有质的飞跃:对受保护的投资及投资者作了宽泛的定义,如包括各种形式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在投资待遇方面,如规定国民待遇原则既适用于外资经营阶段,也适用于外资准入阶段;采用了高标准的投资保护制度,如要求对征收和国有化实行“充分、及时、有效”(赫尔公式)的补偿;对于市场准入,主张取消各种业绩要求,限用投资激励措施,实行主要人员的自由流动,以及确立私有化、垄断、国家企业和特许权方面的公平竞争规则等;就投资争端的解决,赋予外国投资者最终选择国际仲裁的权利,等等。(注:详见赵宏:《略论〈多边投资协议〉》,载于《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293页;陈辉萍:《论多边投资法律框架发展新动向》(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99届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2-8章。)为确立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义务,MAI本意要对缔约国的保留限制有加,就其中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义务,缔约国可开列清单附于协议之后,给出拟予以保留的若干投资措施和投资部门;清单之外的投资部门,均应无条件地实行自由化。但无论如何,各缔约国不得对征收、一般待遇标准和取消业绩要求等条款提出保留;而且,对于缔约时所作的保留,各国应做出逐步予以取消的安排。
与GATS所采用的“自下而上”的方法相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就服务贸易自由化采用的则是“自上而下”的方法,除非成员国在附表中列明除外情形,否则该协议高度自由化的标准适用于所有的服务部门。(注:参见J.H.Jakson,The World Trading Svstem,2nd ed.,The MIT Press,1997,p.308.)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国际经济条约的谈判方式在追求自由化这一最终目标上并无二致,同属一个动态的过程,但二者的区别也非常明显。就推行自由化的“起势”而言,“自下而上”是一个从低水平到高标准的谈判过程,而“自上而下”谈判方式本身以高标准为起点,只是允许缔约方暂作有限的偏离而已;就自由化的“进程”而言,“自下而上”是一种“渐成”的谈判方式,比较务实;而“自上而下”则是一种“速成法”,在实践中,往往欲速而不达,致使谈判失败。GATS和MAI可谓这两种谈判方式获得成功与遭致失败的例证。然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谈判方式的区别并非绝对。在后一种方式下,虽有名义上的高标准条约义务,但如果允许每一缔约国对各部门都享有保留的权利,或保留的范围过于广泛且含糊不清,那么,缔约国实际承担的仍将是低水平的自由化义务,这就造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的混同。(注:参见Y.Kodama,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and Its Legal Implications for Newly Industrialising Economies,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2,1998,pp.28-29.)例如,在MAI的谈判过程中,为了抵消高标准自由化带来的沉重负担,各谈判国主要是发达国家提出的保留就达近千项,而且所作的保留多带有预设性,即为本国以后采取相关的投资措施留下后路,从而破坏了MAI拟有的“自上而下”谈判的原意。(注:P.Ford,A Pact to Guide Global Investing Promises Jobs--but at What Cost?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International,Feb.25,1998,at http://www.csmonitor.com.)
不难看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谈判方式均运用了条约的保留制度,无非前者比后者更为严格罢了。然而,这两种谈判方式对传统的保留制度均有重大发展,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传统的保留可以是永久性的安排,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项下的保留只是一种过渡措施,最终实现高度自由化为相关国际经济条约的既定目标。为此,在实践中,这两种谈判方式一般与“逐步回归”(rollback)方法并用。所谓的“逐步回归”方法,是指缔约国在提出保留的同时,承诺通过各种途径逐步减少直至消除所保留的反自由化措施,使其最终回归条约原定的标准义务。归依的途径包括:(1)缔约方按确定的时间表逐项取消保留的措施(定期淘汰法,phase-out)或在过渡期届满时使有关保留自动失效(落日条款,sunset clause);(2)对缔约国保留的措施进行定期审查,以便消除或限制其中某些措施的适用;(3)通过后续谈判逐步清理缔约国保留的措施,等等。承上例,GATS明确规定各成员方应承担“逐步自由化”的义务;(注:GATS第19条第1款规定:“为实现本协定目标,自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生效之日起不迟于五年内,所有成员方应就旨在使服务贸易自由化逐步达到较高水平进行连续多轮谈判,并在以后定期举行,此类谈判应以减少或取消对服务贸易有不利影响的各种措施为目标,以期达到有效地开放市场的结果。……”)MAI草案更是要求未来的缔约方通过各种途径,逐步消除其在附录清单中保留的例外措施。(注:参见Commentary to the MAI Negotiating Text,Chapter IX,Rollback.)
无疑,对于那些无法回避的国际经济自由化谈判议题,发展中国家应量力而行,力主“自下而上”的谈判方式,并争取放慢“逐步回归”的步伐,从而给自己留足沉着应对的时间和空间。
国际经济条约采取的保留形式通常有二:(注:这种分类法参见L.Wallach,For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The NGO Pocker Trade Lawyer,Feb.25,1998,陈辉萍,前引注[20]博士学位论文,第32页。)一是“封闭式保留”(closed reservations),又称A型保留。此类保留允许缔约方继续实行与条约义务相冲突的现行国内法律,但禁止该缔约方进一步扩大保留的范围和程度,如关贸总协定的“祖父条款”即为A型保留;二是“开放式保留”(open-ended reservations),亦称B型保留。此类保留既允许缔约方对本国现行有关法律实行保护,也不禁止缔约方日后通过新的法律或强化现有法律,即继续加大保留的力度。例如,1965年世界银行主持签订的《华盛顿公约》对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仲裁的争议范围,就允许各缔约国进行B型保留。(注:《华盛顿公约》第25条第4款规定:“任何缔约国可以在批准、接受或认可本公约时,或在此后任何时候,把它将考虑或不考虑提交给中心管辖的一类或几类争端通知中心。……”)
无疑,B型保留实际上赋予各缔约方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低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的权利。然而,对这种保留方式的使用,晚近签订的国际经济条约均严加控制,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缔约方在实现自由化过程中“开倒车”现象的发生。例如,MAI的谈判方曾就该协议是否采用B型保留有过很大的争议;不过,即使允许,也仅限于个别领域,则为谈判各方的共识;又如,在GATS项下,成员方虽有权修改承诺表,包括撤回某些具体承诺(即扩大保留),但利益受影响的其他成员方仍有权提出补偿的谈判要求。(注:参见GATS第21条。)
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谈判方式下,普遍采用的是更为严格的A型保留制度。例如,MAI的谈判引入了所谓的“锁定”(standstill)原则,从而将A型保留的“冻结”特性更加具体化。该原则要求:(1)缔约方应在协议附件中列明全部保留的措施;(2)应明确界定保留措施的性质和范围,以免提出的保留带有预设性;(3)禁止采用新的保留措施;(4)修改现行的保留措施不得更加背离协议设定的标准义务,(注:参见Commentary to the MAI Negotiating Text,Chapter IX,Standstill.)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锁定”原则加“逐步回归”方法就会产生所谓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即每一次取消保留的措施之后,一概不得恢复,并应成为下次“逐步回归”的起点,如此“只进不退”,从而使缔约国踏上自由化的不归路,步步向条约确定的标准水平靠拢。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各国通过缔结大量的国际经济条约建立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相应地,也带来了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创新。无疑,谈判方式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属于国际经济立法方式的范畴,它对国际经济条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成为谈判各方能否达成妥协的关键因素之一。(注:详见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组织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刘平、洪晓东、许明德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中译版,第58页。作者采取博弈论分析了多边贸易谈判中议题挂钩的成败与得失。)首先,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应更多地从多边的角度处理国际经济法律问题,从而导致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多边化,辅之以传统的双边及复边谈判方式,有助于构筑稳定的、标准统一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其次,经济一体化使得各国更加追求多领域国际权利义务的平衡,从而在原有的“分项”谈判法之外,衍生出“一揽子”协议及“构组”等新的谈判方式。这些谈判方式的引入有助于形成系统的、内联紧密的国际经济法律体制;再次,经济自由化是晚近各国缔结国际经济条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然而,这一基本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从而促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等谈判方式的产生,并推动条约保留制度的发展,最终有助于建立明确的、纲纪严明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总之,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创新,将推动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制化进程。随着国际经济谈判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协调立场,争取对自身有利的谈判方式,以防止发达国家利用预设的某些谈判方式,操纵乃至控制谈判的进程和结果。
标签:国际经济论文; 乌拉圭回合论文; 关贸总协定论文; 国际经济与贸易论文; 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会议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wto论文; 国际法论文; 经济全球化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一揽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