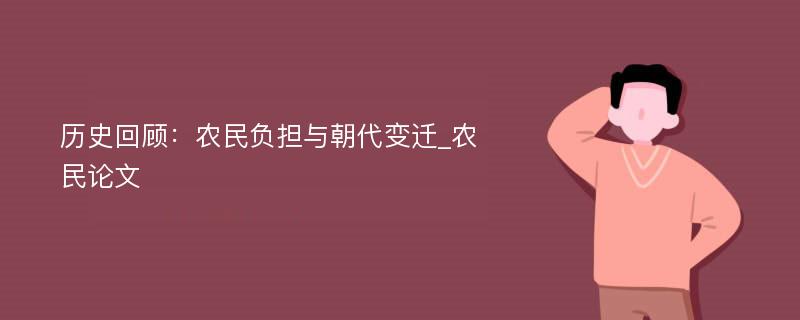
历史回眸:农民负担与王朝更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农民负担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反复不已的周期性更迭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实。这些如走马灯似变换的封建王朝,长的二三百年,短的二三十年,有的甚至昙花一现。那么,这些封建王朝为什么会更迭不已呢?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农民起义的冲击。自从秦末陈胜、吴广首次揭竿起义之后,几乎每一个封建王朝的中后期都发生过类似的农民大起义。历史上那些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如秦、汉、隋、唐、元、明等,无一不是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之下瓦解的。可以说,周期性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导致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直接力量。
农民大起义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呢?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周期性的社会经济大波动与周期性全国规模的大起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封建经济的周期性大波动格外强烈。仅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先后发生过三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此后又先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破坏和大战乱、隋唐五代时期社会经济的反复波动以及宋代经济的局部波动和文化的大倒退。(注: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42页。)每次大波动不仅中断了经济上升的势头,而且使之顿然下降,并常常是一落千丈,陷于全面崩溃。经过浩劫之后,等到新王朝建立,社会秩序有所恢复,社会经济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但导致经济大波动的因素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加,并最终打断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封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曲折起伏的波浪式。从现象上看,这种波动是一种周期性的循环,尽管周期的长短并不相同,但实质上则是社会经济不断地被破坏、破坏之后又不断地重建恢复,破坏与恢复反复交替出现,正如马克思深刻揭示的那样:“这种自给自足的共同体,是不断的同一的形态再生产;如偶然被破坏,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树立起来。”(注:《资本论》第1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正是周期性的社会经济大波动,引发了周期性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前一王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崩溃和农民起义的冲击倾覆下去,后一王朝又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农民起义的消失而强大起来。社会经济的波动周期、农民起义的爆发周期以及封建王朝的更迭周期,三者惊人地吻合。
为什么社会经济会出现周期性的大波动?其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农民负担的沉重不能不居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农民负担的周期性轻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周期性起伏涨落。以隋朝为例,隋朝的建立是在魏晋南北朝长达360年之久的大分裂、大动乱、 大破坏之后,战争创伤至深至痛。为了迅速恢复社会经济,隋初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短短20年间,就出现了“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注:《隋书·食货志》。),“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注:《贞观政要·辩兴亡》。)的盛世景象。对这一奇迹产生的奥秘,著名史学家马端临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有以为富国之术也,盖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年而并罢之……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免除)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亦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广赋税复阔略如此。”(注:《文献通考·国用一》。)可见,“赋税阔略”是隋朝前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然而,隋朝后期,统治者不顾农民承受能力,开运河,伐高丽,征西域,营东都,征发调遣,飞粮挽秣,肆意加重农民负担。《隋书·食货志》云:“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横征暴敛引发了经济的大崩溃,“黄河以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注:《隋书·杨玄感传》。)隋朝前、后期在农民负担政策上的一减一增及其在经济上的一起一伏的强烈对比说明:减轻农民负担,社会经济则上升、繁荣;加重农民负担,社会经济则衰退、崩溃。事实上,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经济走势莫不与农民负担政策紧密联系,举凡新王朝建立之初,农民负担一般相对较轻,社会经济处于上升态势,并出现某种程度的繁荣;到了王朝中期,农民负担日渐加重,社会经济发展趋缓并开始逐渐出现停滞的衰势;到了王朝晚期,沉重的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社会经济逆转并陷入崩溃。可以说,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元嘉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之治”,无一不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效应,而历代王朝中后期经济的衰败又无一不是加重农民负担政策的恶果。对此,不少封建政治家已有清醒的认识。唐人李翱说:“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注:《全唐文》卷六三八。)唐太宗则更深刻地认识到:“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显然,农民负担的轻重直接关系到封建经济的起伏和封建王朝的兴衰。
二
农民负担状况之所以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经济的状况,其重要原因是因为农民负担状况影响甚至决定着自耕农生长的状态。
我国封建社会在任何时期,总有数量不等的自耕农存在。自耕农占有主要的生产资料,又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劳动热情较高,自主性强,一般可以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这就使得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快慢与自耕农数量的多寡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页。 )如何保证小农经济的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就是先决条件。唐太宗在分析贞观之治时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今省徭薄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则其富矣。”(注:《贞观政要·论务农》。)反之,肆意加重农民负担,则会使自耕农民处于绝对贫困境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寒耕热耘,霑体涂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注:《宋史·食货志上》。)这是重负之下自耕农民生活的写照。个体小农的绝对贫困使得自耕农经济极度脆弱,马克思指出:“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注:《资本论》第3卷第678页。)如此脆弱的小农经济根本不能抗拒自然灾害的侵袭,一旦遇上水、旱、虫、蝗等天灾,短时间内有可能造成巨大灾害。打开二十四史,因各种灾害而出现的“人相食”、“死者泰半”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如汉武帝元鼎年间,关东洪灾,“人相食,方二三千里”。(注:《汉书·食货志》。)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只因冬天冷了些, 就出现了“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注:《西京杂记》卷二。)的惨剧。这样一些自然灾害,只有对于竭泽而渔下已经力尽财竭的农民,才能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对此,曾有人一针见血指出:“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而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馁死于道以百万数。”(注:《汉书·谷永传》。)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肆虐与个体小农经济的绝对脆弱有关,小农经济的脆弱又与农民的负担过重紧连。
农民负担状况影响乃至决定社会经济状况的深刻原因是因为农民的负担状况影响甚至决定着再生产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这两种再生产,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当扩大再生产得以进行时,社会经济则加速发展;当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时,社会经济则停滞不前,当简单再生产也无法进行时,社会经济则萎缩衰颓。在中国封建社会,两种再生产能否进行,取决于农民对剩余劳动分配和使用的状况,以及农民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状况,而农民对剩余劳动的分配和使用以及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又取决于农民的负担状况。一般在王朝前期,国家奉行轻徭薄赋政策,有利于农民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农民得以保留部分剩余劳动用于扩大再生产,并且国家将从农民身上剥夺去的那部分剩余劳动较多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如兴修水利等),这时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社会经济也就呈现快速发展的好势头。到了王朝后期,国家越来越加重农民负担,农民不仅不能保留剩余劳动,就连部分必要劳动甚至全部必要劳动也被侵占,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为转徙沟壑的流民。与此同时,统治者的腐朽又使得掠夺去的农民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被挥霍一空,这时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无以为继,社会经济也就呈现出急剧衰退的可怕景象。
三
如果说社会经济走势是随着农民负担的轻重而起伏的话,那么,农民负担的轻重又随着吏治的清浊而起伏。换言之,吏治是制约农民负担的主导性因素。吏治清明,苛暴较少,农民负担则较轻;吏治败坏,敲骨吸髓,农民负担则沉重。
一般而言,中国史上的每个封建王朝在开国之初,由于承当丧乱之后,统治者多少还保持一点戒惧之心,对官吏和乡绅压榨农民的非法行为尚予以限制和防范,因而农民也能获得休养生息的时机。等到安而忘危,统治阶级的奢侈挥霍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加剧,吏治懈弛,贪污、索贿、敲诈的毒流就迅速蔓延,而广大农民则被逼到了“被损害与被勒索的生死关头”。(注:王亚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可以说,有多少朝代, 这样的轮回就重复过多少次。
无疑,吏治与农民负担之间存在着前后呼应、同步耦合的强对应。那么,腐败吏治是怎样加重农民负担的呢?
第一,在封建社会,农民所承受的国家法定负担固然不轻,但总是有限的。而他们因其所处不利的社会地位而招致的法定负担以外的种种隐性的、不确定的、随时可能遭遇到的无情剥削则是无限的,而农民的负担主要来自法外负担,法外负担又主要来自官吏的巧取豪夺。明末崇祯帝在一份《罪己诏》里曾痛切指出:“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注:《明季北略》卷一三。)在国家正式编制以外的无数吏员更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在从事缉拿犯人、催租收税、管理户口等等事务的过程中,无不极尽敲诈之能事。有些“地头蛇”虽什么也不是,在乡村则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农民婚丧嫁娶、打斗争讼、遗产纠纷等任何一种机会去勒索农民,大发横财。由此可见,腐败吏治给农民增加了怎样沉重的负担!
第二,在封建社会,“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因而冗官冗吏之灾愈演愈烈。每个王朝初期,官吏相对较少,但到后来无不恶性膨胀,至王朝后期,官吏量常常是开国之初的数倍乃至几十倍。如北宋真宗朝内外官员1万余人,徽宗时增至4万多人,增加了3倍。胥吏增加更为惊人。宋初三班院吏员300人,真宗时增至4200人,仁宗时竟突破万人,增加了30多倍!冗官冗吏在经济上极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为作为公共权力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价值,而要靠百姓捐税以维持其生存。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有“经费莫大于禄饷”(注:《明史·食货志》。)之说。北宋“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九。)。明朝正德以后,领取俸禄的官吏超过百万,累计俸粮几千万石,而当时全国夏税秋粮总计才2668万石,结果入不敷出,“王府之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廪俸”(注:《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五四。)。巨额的官俸山一般压在小农头上,这种猛增不已的官俸负担,足以置小农于死地。
第三,在吏治败坏不堪的背景下,任何减轻农民负担的解救措施,都难以奏效,相反会成为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的弊政。无可否认,为了封建政权的稳定,统治者有时也采取种种有力措施以减轻农民负担,但腐败的地方官却“悖旨私征”(注:《明季北略》卷一三。),尽入私囊,此所谓上恩而不下达。王朝末期,常常流民潮涌,政府往往派官吏去赈济难民,然而,这些“救民”使者却变成了“劫民”歹徒。如汉末王莽之乱,“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赡官以禀之。吏盗其禀,饥死者什七八。”(注:《汉书·食货志》。)此所谓泽未下而累已及民。
四
从宏观上将中国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考察,可以看到五个层次的运动。第一个层次的运动:吏治清明(王朝初期)→吏治趋于腐败(王朝中期)→吏治败坏不堪(王朝晚期)→农民起义推翻王朝→吏治清明(新王朝初期)→吏治趋于腐败(王朝中期)→……由第一个层次的运动产生相对应的第二个层次的运动:轻徭薄赋政策(王朝初期)→加重农民负担政策(王朝中期)→竭泽而渔政策(王朝晚期)→农民起义推翻王朝→轻徭薄赋政策(新王朝初期)→加重农民负担政策(新王朝中期)→……由第二个层次的运动又产生出相对应的第三个层次的运动:农民能保留一部分剩余劳动(王朝初期)→农民剩余劳动全部丧失(王朝中期)→剩余劳动全部丧失,同时必要劳动部分或全部丧失(王朝晚期)→农民起义以对抗形式要求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农民又能保留一部分剩余劳动(新王朝初期)→农民剩余劳动又全部丧失(新王朝中期)→……在此基础上又产生出相应的第四个层次的运动:经济复苏与繁荣(王朝初期)→经济停滞(王朝中期)→经济衰退(王朝晚期)→农民起义推翻王朝→经济复苏与繁荣(新王朝初期)→经济停滞(新王朝中期)→……由第四个层次的运动又产生相对应的第五个层次的运动:政权稳定(王朝初期)→政权动摇(王朝中期)→政权倾覆(王朝末期)→政权稳定(新王朝初期)→政权动摇(新王朝中期)→……上述五个层次的运动可归纳为这样一组逻辑关系:吏治腐败→竭泽而渔的农民负担政策→农民剩余劳动全部丧失,同时必要劳动部分或全部丧失→社会经济崩溃→农民起义→王朝更迭。
上述逻辑关系昭示人们:第一,治国即治吏。只有从严治吏,苛暴才得以禁止,民生才可望安定,国家政权才有坚实的基础;反之,疏于治吏,放纵苛暴,民生凋敝,国家必然动荡不已。减轻农民负担必须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进行。第二,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只有下大力气真正减轻农民负担,才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反之,若刻意追求高发展速度而不顾民力,苛暴于农民,则经济不仅不能上去,还会激化各种矛盾,危及政权。第三,发展经济是巩固政权的根本,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因牺牲农民利益,加重农民负担所引发的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发展的平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