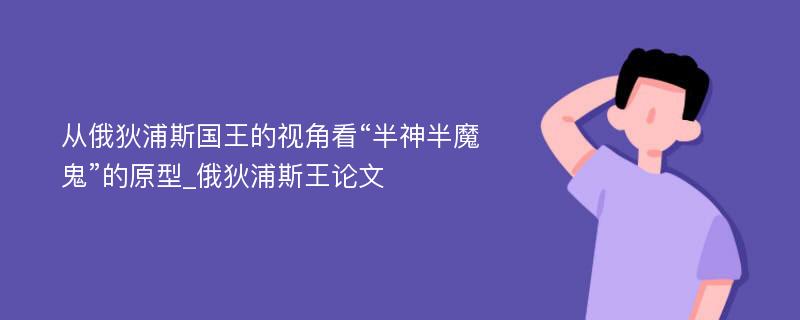
《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型论文,俄狄浦斯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Ⅰ106
文学艺术就像空气和流水一样能跨越时代与国界。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和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从表面上看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如果我们对《天龙八部》进行原型分析,就可以透过两部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看到它们深刻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天龙八部》中隐含着俄狄浦斯悲剧的原型。
“向后站”:悲剧原型的发现
俄狄浦斯的悲剧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最具有命定色彩的悲剧,俄狄浦斯越是想逃避命中注定的不幸,越是更深地陷入悲剧命运的魔圈,他对命运的逃避与抗争只不过是一次次悲剧性的努力。古希腊著名的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根据这个神话创作了震撼心灵的剧本《俄狄浦斯王》,他通过俄狄浦斯的悲剧展示了人与命运的冲突:俄狄浦斯未曾出世,阿波罗的神示便规定他要“杀父娶母”,他的父母忒拜城的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特得知神示后就在婴儿脚上钉了钉子,把他抛在喀泰戎山上,想让他死去。后来科任托斯的国王和王后收养了他,并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不幸的俄狄浦斯自己也受到神示的折磨,为了逃避命中注定的不幸,他离开了科任托斯的父母,然而在流浪途中他与一位老人发生了争执并杀死了老人。他来到忒拜城时,城邦正遭受斯芬克斯的灾难,他解决了斯芬克斯的难题,拯救了忒拜城,并娶了丧夫的皇后伊俄卡斯特。可是忒拜却再次遭到了瘟疫和旱灾,神示是因为杀害拉伊俄斯的人还没有受到惩罚。正直的俄狄浦斯决心捕捉元凶,但结果却发现罪犯是自己,而且伊俄卡斯特就是他的生母,他戳瞎了双眼,自我流放,以消除城邦的灾难。然而俄狄浦斯是无辜的,他是在无意中犯了逆伦的大罪,而且这完全是阿波罗预言过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他所遭受的惩罚却是那么残酷。在此,索福克勒斯向人们揭示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命运是如此捉弄人,在压倒一切的命运的力量之前,人是那么渺小、无力、无法把握自己。这个从远古时代就令人困惑的命题又被后世的作家们反复探讨,俄狄浦斯的悲剧也因此被原型批评家公认为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原型,并且用它对众多的文学作品作出解释。本文正是用俄狄浦斯的悲剧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进行原型分析。
要找出《天龙八部》中所隐含的原型并不难。原型批评主张在精细的阅读中把握作品的结构,但不注意作品的文学结构,而是站在高处和远处看一部具体的作品。弗莱就主张把作品视为“稳定图像”,“向后站”来观察。他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让我们这样去发现原型:“在看一幅画时,我们可以站得很近,分析笔触和刀痕,这大致相当于文学中新批评派的修辞分析,站得稍远一点,构图就显得较清晰了,我们可以研究它的内容,例如,对于荷兰绘画来说,这是最佳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阅读这幅画。再站远,我们就能更清楚地感知到构图的整体。假如我们站在——比如说,离圣母像很远的距离,我们看不到别的什么,只能看见圣母的原型,一团蓝色的蓝块聚向中心。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常常需要‘向后站’,远离一首诗去看它的原型组织,如果我们‘向后站’看斯宾塞的《变化无常》,就可以看到背景上秩序井然的光环和一块不祥的黑色色块从下部突出来。如果我们‘向后站’看《哈姆雷特》第五场开头,就可以看见舞台上张开大口的坟墓,英雄、敌手、女英雄都走下坟墓,接着上界展开一场决战。如果我们‘向后站’看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如托尔斯泰的《复活》或左拉的《萌芽》,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标题所显示的神话诗般的构图。”(注:弗莱:《批评的解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现在,让我们“向后站”,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杰作,这部作品虽然人物众多、头绪纷繁、场面阔大、背景复杂,但是当我们超越《天龙八部》的具体细节,从一个较远的地方观察它,并逐渐剔除枝叶,留下主干,就会发现作品中三个主人公段誉、乔峰、虚竹身上都有俄狄浦斯的身影。他们都在与命运的不幸作抗争,但他们无法战胜命运,最后都和俄狄浦斯一样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以玄妙不可解而又必然不可避免的方式操纵着走向更深的不幸的故事。如果我们再向后退一步,从整体上把握作品,则会感受到一种古希腊悲剧中所特有的恐怖与悲悯,金庸似乎和索福克勒斯一样在讲述一个由命运之神造成的古老而又遥远的不幸的故事。在“向后站”的体验形式中,我们显然可以发现《天龙八部》中所隐含的俄狄浦斯悲剧的原型。弗莱认为,原型在每个
原型与变体
历史时代都会发生“置换变形”,后世出现的文学形态实际上是“一系列置换变形了的神话”。(注:弗莱:《批评的解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显然,从《俄狄浦斯王》到《天龙八部》,原型也经过了“置换变形”。而“置换变形”之后,相对于《俄狄浦斯王》,《天龙八部》已经发生明显的内容的更新和故事架构的调整。在《俄狄浦斯王》中,索福克勒斯主要是通过俄狄浦斯一人的悲剧展示了人与命运的冲突和命运对人的捉弄。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则塑造了三个主人公:段誉、乔峰、虚竹,这三位主人公都和俄狄浦斯一样在邪恶命运的摆布下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他们各自具体的命运悲剧虽然不能等同于俄狄浦斯的神话,但是在他们身上都能找到俄狄浦斯的身影,也可以说在他们身上都有俄狄浦斯原型的显现,而金庸正是通过这三位主人公的命运悲剧共同揭示了与《俄狄浦斯王》同样的主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天龙八部》中的主人公段誉、乔峰、虚竹的命运悲剧分别看作俄狄浦斯神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三个不同的变体。下面我们将对这三个变体进行具体分析,并探讨它们与原型的关系。
《天龙八部》中的第一位主人公段誉是大理国的皇太子,与俄狄浦斯对“弑父娶母”的恐慌一样,他的江湖之行使他不断地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的恐惧,段誉先后爱上的几位姑娘都被证实为同父异母的妹妹。当母亲临终揭开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生身之父不是段正淳而是“四恶之首”段延庆时,乱伦的恐惧才消失了。但是,命运把段誉的不幸安排得天衣无缝,他还没有获得从旧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喘息机会,便又陷入了新的痛苦。段誉虽然没有像俄狄浦斯一样犯下逆伦的罪孽,可当他发现自己的仇人——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段延庆正是自己的生身之父时,邪恶身世的负罪感使他陷入了同俄狄浦斯一样的悲苦和绝望的境地。
乔峰是《天龙八部》乃至金庸全部武侠小说中最完美、最有魅力的侠义英雄。但他与俄狄浦斯一样,在身处人生最辉煌境地之时遭受到了命定的苦难与不幸。乔峰本是中原武林个个倾慕的英雄、丐帮上下人人拥戴的帮主,但是在杏子林中却突然有人揭露他不是中原子民,而是与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突如其来的现实灾变使乔峰难以置信,像俄狄浦斯查找杀害拉伊俄斯的元凶一样,乔峰开始了追索身世之谜的艰难历程。但是,他矢志追索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纯粹失去的过程。因为种种事实证明了当年他家世的惨变和他无法改变的契丹血统,他由乔峰变成了萧峰(生父是契丹人萧远山),由丐帮帮主变成了丐帮及中原武林乃至整个宋的敌人,甚至被辱骂为“大辽番狗”,而他的恩人、师长又都变成了当年误杀他父母的仇人。乔峰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向了毁灭的边缘,在痛苦与茫然中,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成了孤苦无依的流浪英雄。他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他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无尽的诬陷、侮辱、误会也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他的头上,天地之大,竟无乔峰的容身之地。最后在宋辽两军阵前,乔峰以一己之勇协迫辽王百年之内不犯宋境,以保辽宋边土平安,之后悲壮地自尽身亡。乔峰和俄狄浦斯一样以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国家的灾难,当他在雁门关前把两截断剑插入自己的心口时,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俄狄浦斯用两枚金别针刺瞎双限,走向喀泰戎山的身影。然而,乔峰也和俄狄浦斯一样是无辜的,他的契丹血统并不是他的罪过,而是父辈的罪孽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天龙八部》中的第三位主人公虚竹从小在少林寺出家,自以为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神功,被迫当了逍遥派的掌门人,接着身不由己地连破荤戒、酒戒、杀戒和淫戒,进而成了灵鹫宫的主人,最后被逐出少林寺门。然而对于虚竹来说,神功、权势、富贵并不是他的追求,少林寺才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可当他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地想回归少林之时,他的身世之谜揭开了。他的生身之父就是从小就与他近在咫尺的玄慈方丈,而生母却是杀人魔王“无恶不作”叶二娘。玄慈方丈与叶二娘的结合犯了禅家之戒,而虚竹也就成了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之而去,虚竹解开身世之谜之日,也是他与父母永别之日,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他只有离开少林寺,回到灵鹫宫。然而,豪华舒适的灵鹫宫对于他来说就像俄狄浦斯的喀泰戎山,如同一座天然的坟墓。虚竹的悲哀在于他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生自由和选择,就像俄狄浦斯一样在命运的捉弄下,变成了不能掌握自己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孤立无助的人生长旅中,他就像一个被厄运挟迫的羔羊,控制不了自己的方向。
可见,《天龙八部》中三位主人公的命运悲剧作为原型的变体都各有其不同于俄狄浦斯的独特的“神话模式”。但是,原型批评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找出完全一致的神话模式,正如魏伯·司各特在他的《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中所说:“原型批评并不一定要追溯到某些特定的神话,他们可以只发现基本的文化形态,这些形态在某些特定的文化中显示出神话的特点。”(注:魏伯·司各特:《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前面我们对段誉、乔峰、虚竹的命运悲剧的具体分析已经表明,这三个变体虽然具有自身独特的神话模式,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它们与俄狄浦斯神话之间的深刻的内在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就表现在三个变体都以自身独特的“神话模式”反映出了俄狄浦斯神话的基本文化形态。可以说它们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分别揭示了原型的一个方面,也可以说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同一个原型,而三个变体之和则基本上展示出了原型的完整形态。
作为批评的途径,弗莱称原型批评为“超越之路”。在这样的结构中,如果我们对三个变体进行一次整体观照,就能够超越每一个变体而达于更深层次。《俄狄浦斯王》是原始人与命运发生冲突,并困惑于命运的神话表现形式。而当我们把三个变体整合为原型时,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就表现为一部现代人的神话,一部人生的悲剧寓言,它反映了现代人对命运的思考和面对命运的不可知的困惑。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天龙八部》是《俄狄浦斯王》的“神话性思维习惯的继续”,(注:弗莱:《世界之灵:论文学、神话与社会》,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它延续着千百年来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心和求索。
集体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浮现
神话作为上古时代社会、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参与构建原始人的思维模式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正如荣格所说,神话是原始氏族的心理生活,“原始人的智慧并不‘制造’神话,而是体验神话,神话是前意识心理的启示,是关于无意识心理事件的不由自主的陈述,以及除了物质过程的寓言之外的其他一切。”(注:荣格:《集体无意识和原型》,载《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因此,神话作为原始人的思维是一种人类普遍的集体无意识,它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会以心理积淀的方式遗传下来,并组成一种超个性的共同的心理基础,并普遍地延续下来。然而集体无意识一直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它既独立于意识又超越意识,虽然“神话的原型与今日个人的原型非常可能以很相同的方式出现”,(注:荣格:《集体无意识和原型》,载《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它绝不能通过意识的选择来引起,而只能是间接地通过意识来引起或自发地出现。也就是说,不是来自可以察觉,可以说明的意识根源。这种原始意象即原型的自发显现可以用来解释创作中的非自觉性现象。荣格就认为原始意象和原型的存在为艺术和文学提供了基本的创作主题,伟大的作家之所以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是在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不自觉地表现了一些原型,触动了种族之魂,触动了读者的深层无意识。《天龙八部》中的原型显现也正是如此,金庸之所以能将俄狄浦斯的悲剧自然地承袭为自己作品中的原型,并不是他对《俄狄浦斯王》进行了有意识的模仿,而是他在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不自觉地表现了俄狄浦斯悲剧的原型。
在《俄狄浦斯王》中,命运表现为一种无法逃脱的神秘而可怕的力量。一些西方哲学家看来,这种神秘可怕的力量就是异化。当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成为人的时候,就开始与异化自身的力量作斗争,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社会斗争的历史。然而在斗争中,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强大,人类不断地遭受着无可逃循的痛苦、折磨乃至死亡,这些在人的头脑中会很自然地转化为命运观念。正如朱光潜在谈到古希腊悲剧时所说:“从整个古希腊悲剧看来,我们可以说它们反映了一种相当阴郁的人生观,生来孱弱的人类注定了要永远进行战斗,而战斗中的对手不仅有严酷的众神,而且有无情而变化莫测的命运,……既没有力量抗拒这种状态,也没智慧理解它,他们的头脑中无疑常常会思索恶的根源和正义的观念等,但是却很难相信自己能够反抗神的意志,或者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在各种异化自身的力量面前, 人是那么渺小、软弱,在不可知的命运面前,人是那么无能为力,难以把握自己。
命运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古希腊,远古先民在对人与命运的冲突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体验到个体的脆弱以及生命的无价值、无意义,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悲观和困惑,并用上帝和天神解释命运的神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并不是人人都相信上帝和神话,可是人类并没摆脱那种异己的力量对自身的威胁。虽然人类不再由于对自然力难以控制而感到自身的软弱,不再寻求在想象中征服自然,但恰恰相反,人害怕的是他自己所创造的社会力量。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人们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人们在失掉上帝的同时,也失掉了自身的价值感。人的心灵在科学的冲击下倾斜了,文明的进步与人类精神的恐慌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人类深深感觉到生命的痛苦和人性的压抑,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看见,这是由人建造的迷宫,冰冷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舒适的表面上的各得其所越来越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和尊严。”(注:《卡夫卡对我说》,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战争的威胁、金钱的诱惑、情感的物化等构成的综合病症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价值的失范、精神家园的丧失,使人们失去了生存的精神依托。现代人所面对的主要威胁是精神上的贫穷,而不是物质上的贫困。那些失去正确生活目标的人们犹如生活在丧失了精神生命的现代“荒原”,感觉自己正在被巨大而令人昏乱的变化之轮带向不可知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人在异化自身的物质中体会到了与远古先民同样的孤立、无助、茫然、恐慌与绝望。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的生命体验便很自然地接通了远古先民的心灵深处。许多作家的创作开始不自觉地转向了曾被视为与理性和科学背道而驰的远古神话、仪式、梦和幻想,20世纪的文学出现了明显的“回到神话”的趋向和强烈的“寻根”意识。也许“我们的时代离开生命的本原越远,艺术和诗就越坚决地渴求回到那里去。向往原始模型、榜样,向往藏在深处的不变的东西。”(注:转引自班澜、王晓秦:《外国现代批评方法纵览》,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原载丘·勃列克尔:《新的现实》,第10页。 )金庸就以他的小说《天龙八部》向人们展示出了一部现代人的神话。也许金庸在塑造段誉、乔峰、虚竹三位主人公时并没有想到俄狄浦斯的悲剧,但是当他在作品中对现代人的命运进行思考时,面对异化自身的物质世界,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与索福克勒斯同样的悲观和困惑,而当他带着这种情绪寻找悲剧命运的根源时,便自然而然地激活了潜意识里的原型,唤醒了沉睡于他思想深处的俄狄浦斯。
金庸作为一个通俗文学作家,自称讲故事的人,他自己说:“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注:金庸:《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由》。)然而,当金庸在他的作品中不自觉地表现出俄狄浦斯悲剧的原型,并以无法摆脱的偶然和近乎命定的绝对向现代人昭示了生命的悲哀和无望时,《天龙八部》早已远远超出了他“讲故事”的目的。在荣格看来,艺术代表着民族和时代生活中的自我调节活动,它在对抗异化、维护人性完整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艺术家以不倦的努力回溯于无意识的原始意象,这恰恰为现代的畸形化和片面化提供了最好的补偿。”(注:参阅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载《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同样,当金庸从无意识深渊中把渗透着远古人类深沉情感的原型重新发掘出来时,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传奇的故事,它已经不自觉地对异化自我的现代物质世界作出了某种对抗。正如荣格所说,原型具有强烈的影响力,作家一旦表现了原始意象,……同时将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永恒的王国之中,把个人的命运纳入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摆脱危险、熬过漫漫长夜的亲切的力量。(注:参阅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载《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收稿日期:1998-12-05
标签:俄狄浦斯王论文; 天龙八部论文; 金庸论文; 原型批评论文; 文学论文; 批评的解剖论文; 虚竹论文; 神话论文; 段誉论文; 萧炎论文; 金庸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