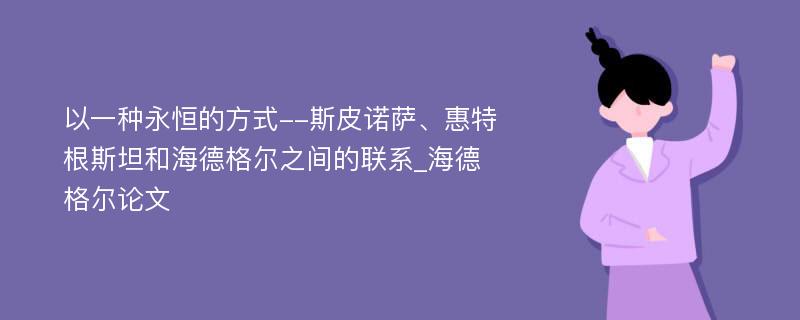
在永恒的方式下——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一种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海德格尔论文,方式论文,斯宾诺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6-0017-05
在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眼中,世界是偶发事态的总和,价值必定伏于世界之外,所以事态自身并不具备诸如善或美的价值。如果人们要追寻某种确定与永恒的维度,那么人们必须升华自己,与“更高者”建立起关系,它可以让人们在偶然、有限的诸事态之中形成一种觅求永恒的意识。如何与“神秘之域”建立起关系呢?显然,在前期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种关系并不能以语言或者命题的方式建立。前期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另一项建议是,人们应当在“永恒的方式”(sub specie aeterni/aeternitatis)之下来观察世界,即在世界之外、连同整个时空来直观世界,它能够让人们在这个世界中重新发现善与美的价值。本文将首先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追溯“永恒的方式”的概念历史,然后再以某些文本为依据来考察和对比这一概念在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那里的运用情况。本文的一个尝试性的结论是,无论是前期维特根斯坦还是早期海德格尔,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以“永恒的方式”来运思他们的哲学。
一、永恒的方式
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中,从永恒的方式来观察事物,这一提法可以追溯至斯宾诺莎。斯宾诺莎认为,理性只有站在永恒的维度,才能认识到事物中的必然本质:
理性的本性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并且理性对事物的这种必然性具有真知识,或者能够认知事物的自身。但事物的这种必然性乃是神的永恒本性自身的必然性。所以理性的本性在于在这种永恒的方式下(sub quadam specie aeterni)来考察事物。并且,理性的基础是表示事物的共同特质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并不表示个别事物的本质,因此必须不要从时间的关系去认识,而要在某种永恒的方式下去认识事物。①
在斯宾诺莎看来,理性把握的是事物的必然性质,他将这种必然性质等同为“真知识”或者事物自身。从一种泛神论的角度出发,斯宾诺莎进一步将事物自身的必然性等同于神之永恒本性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无限者上帝的必然性乃是事物必然性的本质与源泉。从认识论上说,这就意味着,理性如果要认识事物本身(即必然性),它就必须从神出发,借助永恒的方式来考察事物。在斯宾诺莎看来,“永恒”本身也被认为是一种出自于神的存在类型。上述理论给当时人们的提示是,如果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或者必然性,也就同时认识到了上帝的奥秘。人们可以凭借着理性,通过了解事物的本质来通达无限的上帝。因此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高扬了理性的地位。但我们可以看到,斯宾诺莎仍然强调,理性无法仅仅依靠自身来把握这种必然性,在认识“真知识”的过程中,理性并不是理性自身的最终根据。理性需要与至高的实在相关联,在一种永恒的方式的指引下来考察事物。换一种方式说,理性需要在一个有限物“集整体于一身”的前提下,才能通透地把握它的本质。惟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有限物的本质才会朝向观察者的理性“脱颖而出”。倘若没有无限与永恒作为背景,事物的本质对于理性而言就是沉寂与封闭的。
在斯宾诺莎这里,理性与上帝处在这样一种张力关系中:一方面,斯宾诺莎确信,人类可以凭借理性,通过认识世界的本质来认识上帝。另一方面,斯宾诺莎又认为,理性必须首先依靠上帝,即以无限和永恒为依托或背景,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在这种张力关系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理性必须以一位无限者为根据和起点,并以回到这个无限者为归宿。在他那里,理性还没有完全从神学的俘虏中获得解放,理性不能脱离无限者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它仍然需要借助神圣的永恒视角来引导自身寻求知识。斯宾诺莎的这种说法是信仰与理性、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互相结合、纠缠的产物。
可见,斯宾诺莎与近代不少基督教传统下的西方思想家相似,也诉诸一个无限的终极范畴——上帝来引导理性,尽管他的上帝范畴已较难与自然相区别。在这里,理性的权威虽然没有达到它在后世启蒙哲学家那里的高度,但由于神这一概念本身的弱化(即神与自然的同化),使得在之后的思想史中,理性开始寻求以自身为目的,它于是逐渐从无限者的背景与依托之中,抽离出并成为一个封闭、自立的实体。同时,自然或者世界本身也不再被看作是神意的展开,而是被认为是自因(causa sui)和自为的;这种“去位格化”的目的论就消除了自然-历史进程中的神意因素,世界只被看作是世界自己的活动。如文德尔班所说:“……如果natura naturans[能动的自然]有时又被称为事物的动力因,那么这种有创造性的力量绝不可被认为与其本身活动有什么不同;因此不存于别处只存于自身的活动中。这就是斯宾诺莎完整的直言不讳的泛神论。”②
与斯宾诺莎相似的地方是,维特根斯坦同样主张以一种永恒的方式来观察对象。他说:
通常,我们好像是在诸对象之中来观察它们,永恒的方式则是从它们之外来观察它们。
由此它们以全部世界为背景。
这样是否可能?——在永恒的方式这种观察方式下,一个对象不是在时空之中被观察的,而是连同时空一起被观察的?
每一个物都决定了整个逻辑世界(即全部逻辑空间)。
(我不禁有了这样的想法):从永恒的方式来观察物就是连同整个逻辑空间来观察它(NB 7.10.16)。③
这段话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方法以及视角上的转换是:一般的哲学只是在时空之中来观察对象,这就意味着时空自身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整体连同对象被一起观察,对象乃是在一种“真空”般的抽象环境中被看待的。而在永恒的方式下,我们观察事物的同时,还要求观察对象所处身的“时空”(人世间-世界)本身,因此永恒的方式就是一种把事态放置于具体的“在-时-空-中”并“连同时-空一起”来观察的方式。需要说明的是,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自身是不可以言说、而只能自行显明的,因此,从永恒的方式(即连同全部逻辑空间)看待某一事态,有助于将它显现的逻辑结构揭示出来。只有在整个逻辑结构背景的衬托下,该对象的逻辑结构才能更加清晰地向观察者凸显。
“每一个物都决定了整个逻辑世界”(NB 7.10.16)则说明,这个物的存在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体的逻辑结构,因为它的存在要以符合整体的逻辑结构为前提,不符合逻辑空间整体结构的事态是不可能在其中存在的。比如,“方的圆”就不可能在逻辑空间中存在。因此,某事态的逻辑结构要受制于逻辑空间的整体结构,它不能逾越这种整体的结构界限而存在。当我们连同整个逻辑空间来看待某个事态的时候,这一事态就以整个逻辑空间为背景,从而成为了一个“有限的整体”。
引起本文注意的是,虽然讨论的对象不同,但维特根斯坦也运用了类似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方法。即他们都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聚焦于一个有限的事物或偶然的事态,来窥探上帝、宇宙、逻辑世界的奥秘,从而达到有限与整全的统一。并且,斯宾诺莎和维特根斯坦都认为,从永恒的方式来观察世界都只能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发生,这种方式的结果——即世界作为有限的整体——这种感觉也是神秘的。因此,他们的这一提法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文德尔班在讨论斯宾诺莎的神秘主义时甚至认为,“sub specie aeterni”下的认识,就是某种意义上的“docta ignorantio”(有学问的无知),从而将斯宾诺莎与神秘主义大师库萨的尼古拉联系了起来。④维特根斯坦也指出,从永恒方式出发对世界的直观,就是把世界直观为一个有限的整体,而把世界当作为一个有限整体的感觉是神秘的(TLP 6.45)。总之,在斯宾诺莎与维特根斯坦看来,“整体”可以“显明”在“有限”之中,人们也可以通过直观的方式,从“有限”通达“整全”。
而维特根斯坦与斯宾诺莎的分歧表现在他们对于“必然性”的看法上。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个世界之中实际上是没有必然性的,任何一件看似必然发生的事况都有其它的逻辑可能性,因此他认为这个世界之中的必然性并不是一种“本质的必然性”。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就为“更高者”和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了地盘。而斯宾诺莎强调理性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他的自由观念也是建基在对这种必然关系的认识之上(“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正是由于事物都在一种必然关系中被理解,因此在斯宾诺莎哲学中并没有自由的真正位置。潘能伯格准确地指出:“斯宾诺莎由于在他自己的哲学中不给有限的、偶然存在的事物的独立存在留下位置,所以也就没有给这些事物的自由留下位置,同样也就没有给上帝在其创造活动中的自由留下位置。”⑤
二、有限的整体
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永恒的方式下”的直观是一种神秘的体验,它是善与美的综合:“艺术品是在永恒的方式下观察的对象;善的生活就是在永恒的方式下观察的世界。这就是艺术和伦理间的关联。”(NB 7.10.16)从伦理的角度看,“在永恒的方式下”首先意味着个人关注点的转移——从世界中的事实转移到生命更高层次的价值与意义;从自我中心转向一种整体的视角。站在这一维度来思考与生活,人们便有可能在有限、平凡的事物中直观到其超越、永恒的一面;或者说,只有从事实的洞穴中转身而出,人们才不会扼杀与生命本源的直观和交流。从审美的角度看,在永恒的方式下可以让人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件“艺术品”,从而对其感到惊讶。可见,维特根斯坦还赋予了“在永恒的方式下”一种伦理、审美和生存的含义,在这种方式下观察对象与世界,就不仅是一种智性的认知方式的转变,更加重要的一个维度是,它还包含一种生活态度上的决裂性“倒转”。如前文所述,这种倒转性的认识就是从对象与世界外部的某个“更高处”、而不是“诸对象”之中来观察它们。并且,正如斯宾诺莎和维特根斯坦所强调的,这一倒转必定要与神圣性或者更高者,即上帝的属性相关联才有可能产生。这就是说,只有在更高者的指引下,人们才会真正寻求善与美的生活方式。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人们要在对象之外,把世界作为背景,才能将对象直观为一个“有限的整体”。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说,好比人只有在太空中观察地球,才能把地球看作为一个“有限的整体”,就像我们在从太空中拍摄的地球照片里看到的那样。人在世界之中是无法把地球看成为一个有限的整体的,既看不到其“有限”的一面,也看不到其“整体”的一面。这一比喻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当我们以无限的时空为背景来观察一个对象时,这一对象的整体轮廓便会清晰地呈现出来,而当这一整体轮廓呈现出来之际,它的界限(有限性)也就被“揭露”了。因此,“有限”与“整体”其实是同一和必然相联的:有限代表了整体被呈现出来,整体也代表了其有限的边界被展现。在永恒的观察方式下,有限与整体只能同时性地被给予到人的直观之中,人无法分别直观到两者之一。所以,整体的意识必然与一种有限的意识相关联,这种意识在语言中只能被表达为一种“有限的整体”。值得再次强调的是,这种直观意识只有在无限背景的衬托之下才可能发生,类似地球要在广袤的宇宙太空背景中才成为一个有限的整体。没有无限为背景,没有一种永恒的眼光或者视角,就没有对有限整体的直观领会。
倘若按照这番论述,我们或许会有一种印象,即维特根斯坦似乎更加重视有限的整体中“整体”的一面。事实上,有限的整体还带有一种特殊的生存关怀,即要在简单事物中寻求超越的意识。维特根斯坦笃信这样一个道理:简单而平凡的东西里面,却往往蕴藏着不可思议的能量。当维特根斯坦主张人们用一种“永恒的方式”来直观“有限的整体”时,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去追求玄之又玄的复杂观念和理论,而是应当更加关注身边细小、有限的事件;同时,这还意味着人们应该要关注直觉而不仅仅是推理。因为正是以一种直观的方式,人们才可能在有限的事物当中发掘出无限与永恒的能量。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神秘的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Nicht wie die Welt ist,ist das Mystische,sondern daβ sie ist)”(TLP 6.44):人们并不需要艰深的知识去了解宇宙的构成和运动,或者成为天文以及物理方面的专家洞悉到世界的存在方式才能感叹造物主的伟大。实际上,这个世界的存在本身——这是一般人都可以感受到的最为平常的事件——就足以让人惊叹了。前文曾经提到,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从一种审美的角度,我们才会觉得这个世界的存在是一个奇迹。当人们在永恒的方式下将世界看作为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时,人们自然就会对此感到惊奇。总而言之,当维特根斯坦提倡在永恒的方式下观察世界时,他并不是要人们去过一种放弃尘世的生活。相反,在永恒的方式下,一件细小的事情或许都拥有神圣的价值,它都可能隐藏着神性。这引带出了布莱克的一首诗:
Auguries of Innocence 天真的预言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一粒沙看出一个世界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一朵野花里有一个天堂,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永恒就在片刻闪现。
从上面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到:同一个物理世界在不同的看待方式下是不一样的,人们对于世界的态度与他的观察方式相关。例如,在同样一件艺术品面前,某个人可以被感动,但另一个人也许会觉得它毫无价值。因此,人们对世界的回应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某些人可以感觉到世界的奇妙,而另一些人会觉得世界没有意义可言,而这种态度显然会对人的实际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者克拉克(Clack)先生认为,在这里已经能够发现维特根斯坦对于宗教信念思考的萌芽:信徒与非信徒的分歧,并不是争论某件事实。这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是一种审美格调上的差异。⑥有神论与无神论之间的冲突,是由对同一个世界在不同的观察方式下产生的冲突,或许有神论者就是从“永恒的方式”下来观察世界的。
三、瞬间的永恒
《天真的预言》这首诗对于“有限的整体”、“瞬间的永恒”的描写可以说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它对上述哲学意象的描写还是略显机械(沙粒与野花都是固定的)、抽象(如何把“无限”放在手掌)。相比之下,强调本源生存境域的海德格尔,在这方面就可能会表达得更加具象与生动。他的风格是,不急于告诉我们“是什么”,而是让它们自行显明之所“是”。据说,海德格尔深受其同乡、著名的德语世界的布道者亚伯拉罕(Abraham a Sancta Clara,1644-1709)的影响,并以之为终生楷模。而海德格尔最欣赏亚伯拉罕的一句诗是:“过来,你银白色的天鹅,在水面上来回游动,用翅膀护持着雪花。”⑦海德格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这句没有使用任何时间性术语的句子中,读出了瞬间和永恒的关系;或者说,海德格尔让此前处于隐蔽之中的“瞬间中的永恒”,以一种“互戏”的方式自行敞明。
在这一景象中,从天而降的雪花是不能持久的,当它飘落于水中,会因为温度的升高而在不久之后融化。好奇的天鹅们却不忍心看到雪花溃散在水面,她们希望通过游动并挥动白色的翅膀,来不断地激起水流与波纹以维持雪花不变的纯白。在海德格尔看来,天鹅要以她们白色的羽毛来维持雪花的纯白,之前片刻便会消逝的纯白,在不停地流动飘浮中达到了永恒。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最短暂(Vergaenglichsten)中的永恒(Unvergaengliche)意象(Bild)”⑧。
可以说,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不少方法特质在这一解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这点上,西方现代思想中也许再无人可出其右,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种哲学方法的独特优势。但是,正如斯宾诺莎和维特根斯坦所强调的,只有首先具备了一种“永恒的观察方式”,人们才可能直观到“有限的整体”,或者产生“瞬间的永恒”这样的神秘领会。在这里,“天鹅于雪中的湖面游水”作为一种物理事件是偶发的,许多人都曾经观察过这类事件的发生,但他们不一定都能产生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体会。为什么呢?如果从维特根斯坦的立场来解释,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永恒的方式”下来观察这一事件。维特根斯坦说过,“艺术品是在永恒的方式下观察的对象。……在永恒的方式这种观察方式下,一个对象不是在时空之中被观察的,而是连同时空一起被观察的”(NB 7.10.16)。可见,不在永恒的观察方式下观察的事件就会平淡无奇,它不会成为一件艺术品。而当某事件“连同时空一起被观察”时,就可能引导观察者领会到“瞬间的永恒”。因此,正是海德格尔首先处在了“永恒的方式”之下,他才能从这一事件中看到“最短暂的永恒”。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海德格尔继续在这种“永恒的方式”下来观察这个世界,继续在这样一种观察方式下生活,那么,他就可以在其它的事件中,不断地领会到“最短暂中的永恒”。⑨总而言之,海德格尔观察事物的“永恒的方式”,使得他可以将一件永恒的“外袍”披挂到“天鹅雪中游水”这一有限、偶然的事件上,从而让它具备了某种“永恒的形式”。诗词的原作者亚伯拉罕创作这首诗时,不一定是在表达“最短暂的永恒”,数百年之后的海德格尔却能注意到这句话,并从中发掘出上述的意义。⑩
最后,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在这一“天鹅雪中游水”事件中,事件本身并不带有价值,它也没有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它的价值与特别意义还是“潜在”的,尚未实现出来。是由于海德格尔在一种“永恒方式”下观察它,它才具备了一种与海德格尔这一“此在”相关联的独特价值(即“最短暂中的永恒”)。换言之,不是海德格尔通过他的现象学方法阐明了“最短暂中的永恒”,而是因为他首先具备了一种朝向“永恒”的意识,一种从永恒眼光来看待问题的视角,他才有可能在某一“最短暂”发生的事件中,寻觅到“永恒”的踪迹,所以,在整个意义阐发的过程中,“在永恒的方式下”无疑是更为基本和决定性的。
注释:
①[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4-85页。译文稍有改动。
②[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62页。
③字母“NB”代表《战时笔记》Notebook 1914-1916(NB)ed.G.E.M.Anscombe and G.H.von Wright,tr.G.E.M.Anscombe,Oxford:Blackwell,1979.后面的数字表示此段文字的写作日期(依次表示日月年),如7.10.16表示写于1916年10月7日。“TLP”代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1.
④[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61页。
⑤[德]潘能伯格:《神学与哲学》,李秋零译,香港:道风书社,2006年,第165页。
⑥参见Brian R.Clack:An Introduction to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Religion.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p.38.
⑦⑧张祥龙:《海德格尔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0、30-31页。
⑨或许可以这样说,海德格尔这样一个“此在”,由于在一种“永恒的方式”下观察在雪中戏水的天鹅,从而很有“缘分”地领会到了“瞬间的永恒”。这个时候,他就成为了与“天鹅雪中游水”这一事件相关联的“缘在”。而当海德格尔亲身体会到“天鹅雪中游水”这一事件中“最短暂的永恒”时,实际上是将自己先行的价值取向(即永恒的观察方式)植入了这一事件中,从而成为了一种“亲在”——海德格尔亲身参与了“天鹅雪中游水”这一事件的存在和发生,成为了局内人或当事者,从而赋予了这一事件“最短暂中的永恒”的价值。
⑩这种跨越了数百年的理解“时差”,也解释了伽达默尔释义学中的“与时性”(Zeitlichkeit/contemporarity)概念:一件真正的艺术或哲学作品,只要它表达了人性,则它与所有时代的相关性都不会减少,它在所有时代都具有宽广的释义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