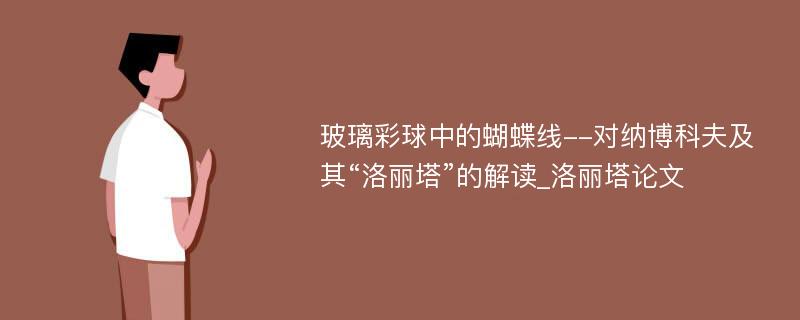
“玻璃彩球中的蝶线”——纳博科夫及其《洛丽塔》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彩球论文,玻璃论文,洛丽塔论文,博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无疑是当代美国作家中最具争议的一位。他复杂而特殊的生活 背景、奇谲多变的文学叙述以及他那部声名遐迩的小说《洛丽塔》(1956)一直是文学评 论界和广大读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小说出版至今已近半个世纪,而一些评论家们仍强 调指出,纳博科夫与《洛丽塔》留给我们的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特别是这部小说表面之 下所蕴含的意义有待进一步探讨,正如著名的纳博科夫专家、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L.L.李所说的“《洛丽塔》包含了许多东西,至今尚未被发掘。”(注:L.L.Lee,Vladimir Nabokov,Boston,Twayne Publisher,1976,p.27.)
一
我究竟犯了什么样的罪恶?“教唆犯”或“犯罪者”——这就是我为整个世界写出了一 个梦幻中的可怜的小女孩后所得到的字眼。 (注:R.Karl,The American Novels,New Y 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6,p.115.)
这是1959年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俄译本出版时针对那些道德批评家们对小说的曲解 而写下的句子。他担心,如同这部小说在欧美所经历的遭遇一样,它在俄国出版也会招 来普遍的责难与非议,因为大多数人们“未能真正读懂它”。(注:Smith Peter Dwval ,What Vladimir Nabokov Thinks of his Works,his Life,New York,Vogue,March 1,1 963,p.155,p.157.)
事实上,《洛丽塔》的难解,首先就在于这部小说的道德主题。这是探讨纳博科夫及 其《洛丽塔》不可回避的问题。小说构建于一个性变态的中年男子对一个12岁的“性感 少女”的迷恋与追逐并最终为之付出了生命这样一个故事框架之上。这个情节难免令50 年代的读者大为吃惊,大多数人恐怕都会相信这是一本色情之作,讲的无非是一个下流 的故事。但一些批评家则开始注意到这部小说非同一般的地方,他们试图从作家的写作 动机、他的创作经验等方面来解释作品的意义。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离不开对作家 本人的生活经历及他创作灵感的来源的探讨。
纳博科夫的生活经历确实复杂,他1899年4月12日生于俄国首都圣彼得堡。贵族的家庭 背景使他们一家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惊恐不已。1919年,纳博科夫随家避难来到英国,他 先在剑桥著名的三一学院学习了4年,接着移居德国一直住到纳粹夺取了政权。在柏林 ,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俄国移民的社区,他在那儿曾用母语写了不少小说。但因战乱在即 ,这些作品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的干脆未见天日。随着欧洲政治形势的变化,纳博 科夫过着四处飘泊的生活。离开德国后,他又来到法国住了3年,最后,他举家迁居美 国。40至50年代在韦尔斯理和康乃尔大学任教,主讲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并开始了 他真正的文学创作的生涯。60年代以后,纳博科夫重返欧洲,居住在瑞士直到1977年逝 世。对于自己奔走四海的一生,纳博科夫后来曾自嘲地说,“一个俄国人,在法国受教 育,用英文写作,却住在瑞士。”(注:Andrew Field,Nabokv:A Bibliography,New Yo rk,Mc Graw-Hill,1993,p.73.)
纳博科夫的人生经历曲折离奇,但文学评论家更感兴趣的,还是他个人的生活,特别 是他情感方面的情况,因为除了《洛丽塔》之外,人们很快就发现类似《洛丽塔》式的 “不伦”题材在他以前的创作中也屡见不鲜。尤其是1938年他以俄文写成的小说《魅人 者》,简者可以说是《洛丽塔》的雏形,而更早的自传体小说《天资》讲的也是一个类 似的故事。从这些小说相贯通的情节来看,《洛丽塔》无疑带有作者某些生活经历的影 子或者一个时期的心理特征。但遗憾的是,从现存他的生平资料以及他的传记中,人们 似乎又找不到相应的证据,这种情况更为《洛丽塔》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刘易斯· D·拉宾教授甚至认为,这部小说应该是“艺术家的生活与他的艺术作品并无直接联系 的明证”,并断言“《洛丽塔》并不是一部自传性的著作,因为没有作家自身的东西包 含在内。”(注:Louis D.Rubin,Gogol,1976,p.119.)
而另一方面,人们所指望的作者本人所阐述的创作意图也令人失望。纳博科夫不止一 次谈起有关本书最早的创作冲动:“第一次洛丽塔在我心中的悸动是1939年末和1940年 初。当时在巴黎,最初的灵感直接来自一份报纸上所载的故事。讲的是一只类人猿在一 位科学家数个月的调教下,用木炭笔画出了世界上第一张由动物所作的画。画面上所展 示的是一些木栅栏样的东西,犹如这可怜的动物的囚笼。”(注:Vladimir Nabokov,On A Book Entitled Lolita,Yi Lin Press,Annotated English Literature Series,199 5,p.277,pp.278-279,p.280,p.277,p.277.)
纳博科夫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触发了他写作的灵感,他当时用俄语写下了一个短篇 故事,讲的是一个中欧的魔术师为了追猎一个“性感少女”而与她的母亲结婚,魔术师 经历了在旅馆中试图对少女非礼的失败后,偶然撞倒在卡车下丧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 情节与《洛丽塔》相去甚远,人们显然不会满足于他的说法。即使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 看,两者也很难找到共通的基础。而除此之外,人们所了解的纳博科夫还是一位多才多 艺的人,有许多的嗜好与专长,他是一个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个生物学家和昆虫学家, 一个国际象棋的高手和网球教练。他一生最大的嗜好,莫过于捕捉奇异的蝴蝶,对此简 直到了痴迷的程度。移居美国后,每年暑假,纳博科夫总是和他的妻子一起去中西部捕 蝶,至今我们仍可以在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的比较动物博物馆以及一些科学院的陈列 室内看到纳博科夫采集、捐赠的一些珍贵的蝴蝶标本。纳博科夫也曾说《洛丽塔》一书 即是50年代他于捕蝶的闲暇之时断断续续地写成的,对他来说,捕蝶是:“一种没有时 间限制的最高享受——一个随机挑选的景点——我站在珍稀蝴蝶与它们喜爱的植物中间 ,这是一种狂喜,在这狂喜背后还有更多的但却是难以言述的东西,就像一瞬间我所喜 爱的东西突然袭来,感到天地合一,一种对人类命运对位的精神或者对温和的幽灵嘲笑 幸运的生物的感激之震颤。”(注:Diana Butler,Lolita Lepidoptera,New York,New World Writing,1960,p.58,p.70.)
1952年,纳博科夫因采集到一种特殊的雌性蝴蝶而荣获一项殊荣:蝴蝶以他的名字命 名。他把这种蝴蝶分为二类,其中一类叫“多洛斯”(Dolores),而小说中洛丽塔的名 字也叫多洛斯。于是,纳博科夫的“恋蝶情结”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有人专门研究 、比较洛丽塔与蝴蝶的相似、对等的关系,他们把蝴蝶看成是美少女的象征并试图在书 中找到佐证。如洛丽塔与蝴蝶一样,最喜欢的食品是水果;那个奎尔蒂在跟踪洛丽塔与 亨伯特的沿途中所用的许多化名几乎都与蝴蝶有关;更有甚者,他们把洛丽塔上学时的 学号与大百科全书中蝴蝶的序列同为22而看成是彼此同一的象征……。这些论者最后几 乎断言《洛丽塔》中亨伯特追逐“性感少女”实质上即作者捕捉蝴蝶的另一种形式,其 不正当的情欲与作者对蝴蝶的特殊嗜好相等同。这种孤立地把作家的创作看成是个人嗜 好的渲泄如同视本书为淫书的观点一样,显然都未能解读《洛丽塔》真正的涵义。
二
早在《洛丽塔》尚未问世之时,纳博科夫似乎早已感到这部小说将被误读的命运。他 的一位朋友因此建议他可以“非常低下地与出版社约定用匿名的方式出版。”(注:Vla dimir Nabokov,On A Book Entitled Lolita,Yi Lin Press,Annotated English Liter ature Series,1995,p.277,pp.278-279,p.280,p.277,p.277.)但几经思考之后,纳博科 夫觉得“这好像套了一个违背我意志的面具。我决定署名出版这部小说。”(注:Vladi mir Nabokov,On A Book Entitled Lolita,Yi Lin Press,Annotated English Literat ure Series,1995,p.277,pp.278-279,p.280,p.277,p.277.)但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纽 约有四家出版社提供了打字稿,他们分别请一些特约的读者过目,以决定到底是否采用 这部书稿。结果所有的读稿人,包括两位纳博科夫的好友在内,都一致对此书感到震惊 ,有的人只是匆匆看了一下开头便认定此书为宣扬色情的淫书,根本不属于纯文学作品 。一位出版商声称,“如果出版这部小说,他(指作者)与我都得进班房。”(注:Appel Alfred Jr,The Annotated Lolita,New York,Mc Graw-Hill,1970,p.4.)在美国出版商 的共同抵制下,纳博科夫只能联系欧洲国家的出版商碰碰运气。最后,巴黎的奥林比亚 书局同意出版《洛丽塔》。这是一家专门出版淫秽书籍的出版社,曾出过不少这方面的 “禁书”而名声在外。《洛丽塔》一经出版,顿时读者踊跃,反响巨大。欧洲的读者在 从中感受异国情调之外,更多的还是为小说的情节所吸引。紧接着,英国和美国本土精 明的书商们都看到了此书所蕴含的商机,他们决定马上跟上。1958年由美国普特南图书 出版公司把它“引回”美国,这一出口转内销的经历反而使它名噪一时。尽管《洛丽塔 》此时的名声并非是纳博科夫所希冀的,他写了几篇文章想辩白一下,但铺天盖地的广 告炒作使作者也万般无奈,他心目中真正的知音只有英国作家格雷格姆·格林等少数人 ,格林曾把这部小说列为1955年最佳的三部小说之一。他和《洛丽塔》“引子”中的编 辑约翰·雷博士一样,把这部小说看成是具有积极的道德主题的作品。但遗憾的是,像 格林这样的读者在当时太少了。《洛丽塔》中这篇至关重要的“引子”常常被读者所疏 漏,有的出版社甚至干脆把它删去(最新中文版译本敦煌文艺出版社所出的即是一例)。 事实上,要对本书的思想主题、道德倾向作一个全面、严肃的探讨,缺了这一篇“引子 ”,是很难奏效的。
在“引子”中,纳博科夫借用小说的“编辑”雷博士之口交代了一些人物的结局,更 重要的是,这位先生为小说的道德倾向定下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的基调—— “这出悲剧坚定不移地导向一个道德的顶点。”(注:纳博科夫《洛丽塔》,于晓丹译 ,“引子”及正文,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53、2、3、4、164页。)他 明确指出:
作为一个病例,《洛丽塔》毫无疑问在精神病领域会成为一个典型。作为一部艺术品 ,它超出了它赎罪的方面。而且对我们来说,比科学和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将 会对读者所产生的伦理意义上的影响……它们(指亨伯特、洛丽塔和她的母亲)提醒我们 注意危险的倾向,他们指出了潜在的罪恶……(注:纳博科夫《洛丽塔》,于晓丹译, “引子”及正文,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53、2、3、4、164页。)
很显然,这段以约翰·雷博士的名义所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纳博科夫本人对小说主题 的诠释,也为我们理解本书的道德涵义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尽管纳博科夫又躲躲闪闪 地辩白说,“我不是一个说教的作者,也不是这类书的读者,不管约翰·雷博士的断言 如何,《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的成份。”(注:Vladimir Nabokov,On A Book En titled Lolita,Yi Lin Press,Annotated English Literature Series,1995,p.277,pp .278-279,p.280,p.277,p.277.)而我们知道这种有意把自己隐藏于人物背后的做法,在 文学创作中并不少见。
《洛丽塔》在美出版后,引起轰动,畅销不衰,正如文学评论家约翰·谢达(John Sha de)所说的,《洛丽塔》如一股强劲的飓风,从佛罗里达一直刮到缅因州。纳博科夫则 又特意写了一篇文章附在书后,说明自己的写作动机,也驳斥了当时流行的几种看法。 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头尾二篇文字影响力却有限。有关《洛丽塔》的争议一直未断 。时至今日,评论界仍然在疑惑:这部小说是否真如作者自称“并无特殊的目的”,只 是“一种灵感的反应或混合”。(注:Andrew Field,Nabokov,His Life in Part,New Y ork,1967,p.315.)更多的读者还会不解地问,此书被认为是经典之作的依据是什么?纳 博科夫对蝴蝶的迷恋与小说究竟有何关联?本书是一部道德的还是非道德的小说等。而 要解决这些问题,势必要从对纳博科夫的世界观、审美观和道德观的观照中探讨小说本 身的内涵。
三
《洛丽塔》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小说的前半部中有不少对病态情欲的描写。把本书视 为淫猥小说的人大都指责作者以此招徕审美情趣低下的读者。但纳博科夫本人则完全不 同意这种说法。他指出“在古代的欧洲,直到18世纪,喜剧、讽刺作品,甚至一个诗人 在俏皮嬉戏情境中的作品,都故意含有淫荡的成份。在今日,‘色情文学’一词含意则 是平庸、商业化……”(注:纳博科夫《洛丽塔》,于晓丹译,“引子”及正文,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53、2、3、4、164页。)纳博科夫主张把文学作品中 的有关性爱的描写与作为煽情的色情文字区别开来。前者是整部文学作品中的有机部分 ,是内容与题材的需要;而后者只是一种直接的,露骨的渲染,只能引起读者粗俗的感 官满足。纳博科夫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不必忌讳对性爱的描写,从古代的英雄史诗到卜 伽丘的《十日谈》,卢梭的《忏悔录》,莎士比亚的剧作甚至《圣经》的“雅歌”部分 到现代的乔伊斯的《尤里西斯》,D·H劳伦斯的小说,亨利·密勒的作品都有类似的描 写。纳博科夫描写《洛丽塔》中亨伯特的那种畸形的情欲,揭示亨伯特身上那种变态、 丑恶的心理,似乎想达到一种道德上的“警世”作用。从小说的总体内容与人物塑造等 方面看,作者的这种意图得到了成功的表达。纳博科夫相当贴切地把握了亨伯特这个人 物的病态性心理,恰如其分地暴露了其可鄙之处,最后还带给了他毁人毁己的结局,这 些表明了作者严肃的创作主旨与道德观念。他始终把亨伯特置于鞭挞的位置,他还通过 “雷博士”告诉读者,“他(亨伯特)是极其可怕的,他是卑鄙的,他是道德堕落最突出 的典型,是残暴和诙谐的混和体,……”(注:纳博科夫《洛丽塔》,于晓丹译,“引 子”及正文,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53、2、3、4、164页。)他让这个 性变态者在生前最后56天的监狱生活中痛述自己的“经历”,让他时时刻刻处在自我谴 责的痛苦之中,为自己的罪孽付出惨重的代价。
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纳博科夫在刻划亨伯特这个人物时,把握得相当有分寸,他并 没有让这个人物简单化。亨伯特是一个病态的、有着特殊癖好的登徒子;但同时他又是 一个痴情与坦诚的人。纳博科夫力图使读者通过亨伯特的这份“自白书”,相信这个人 物的真实性,让他们“一边憎恨本书的作者(亨伯特),一边又为此书而神思恍惚。”( 注:纳博科夫《洛丽塔》,于晓丹译,“引子”及正文,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 年,第4、53、2、3、4、164页。)
在探讨《洛丽塔》的道德主题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常被忽视的关系,那就是亨伯 特、洛丽塔及她母亲夏洛特三者之间的关系。亨伯特要夺得洛丽塔,不受干扰地享受他 那畸形的欲望,自然就得除掉夏洛特这块绊脚石,这一点他很清楚并在他的日记中曾加 以详细的分析。但当一个绝佳的机会来临,也即他与夏洛特在滴漏湖游泳时,周围的环 境可以说给他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下手机会,但亨伯特却没有这样做,他的选择显示了他 内心道德力量的胜利。纳博科夫用这样一个细节来表明亨伯特还不是一个全无心肝的恶 魔式人物。另一方面,他与洛丽塔之间的这种肮脏关系,也不应由他一个人负责。他与 洛丽塔的初次性关系,竟是这个任性、轻浮的女孩子“主动的结果”。小说中这样叙述 道:“我(亨伯特)将要告诉你们一件怪事,是她诱惑了我。”(注:纳博科夫《洛丽塔 》,于晓丹译,“引子”及正文,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53、2、3、4 、164页。)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们三人的关系中,亨伯特既非夏洛特后来死 于意外的直接元凶,也非对洛丽塔施暴的强奸者。他对洛丽塔那种如痴如醉的邪恶情欲 ,源自他病态的心理以及所谓的“唯美”嗜好。小说真正的主题即在于此,它揭示的是 某些病态色欲者危险的行为倾向,描绘了亨伯特这个另类人物的典型的危害。我们从小 说得知,这个人物一直患有某种精神失常症而多次住院治疗,在去拉姆斯代尔之前,他 曾在医院里逗留了一年多。但他更大的问题是在性心理方面,他一直钟情于未成年的少 女,并把所谓的“性感少女”的年龄限制在9至14岁之间,甚至还希望她们永远不会长 大。他为她们“魅人而狡黠的神态,恍惚的眼神,鲜亮的嘴唇”所迷惑;而另一方面, 他又本能地讨厌乃至虐待周围每一个成年的女性,包括他的前妻瓦莱里亚,洛丽塔的母 亲、也是他再婚的妻子夏洛特以及后来的女友丽塔等。亨伯特对自己的变态行为也有一 定的认识并视为一种罪恶,但他却欲罢不能。为此,他把这种危险的倾向界定为“诗人 的气质”,认为古已有之,从而为自己开脱。从彼特拉克疯狂地爱上一个12岁的、金发 耀眼的少女劳琳到但丁爱上当时年纪仅9岁的贝亚特里采以及埃德加·爱伦·坡与未及1 4岁的表妹结合等,都成了他自我安慰与辩解的例子。这其中,坡对亨伯特的影响不可 低估,这不仅因为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唯美”意识的相通 。亨伯特坚持认为一个如同他一般的诗人或者艺术家,必须为美的东西所倾倒。在他看 来,艺术惟一的目标就是美感愉悦,这种愉悦是由美的召唤引起的。爱伦·坡的笔下不 乏类似的疯狂人物,他们为了追求自己所认定的美,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亨伯特就 是一个“美”的追猎者,他与爱伦·坡之间密不可分的亲和力是基于他们那种对“美” 的同一反应。这种“美”的本质对他们来说既具有美感,又具有色欲上的发酵因素。《 洛丽塔》中许多细节如亨伯特初见洛丽塔时的强烈反应,他在与洛丽塔打网球时的心理 活动以及失去她以后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处处表达了这种欲望与“美”感。正因为亨 伯特与爱伦·坡之间心有灵犀,《洛丽塔》中多处明里暗里提到了这位唯美主义的大师 ,还把他的诗句原封不动地搬用过来。亨伯特就像坡所塑造的人物威廉·威尔逊一样, 他杀死了自己的双重人格,然后在死亡之前写下绝望的自白,其目的也相同,为自己的 行为辩护,希冀他人的同情与谅解。而《洛丽塔》中克莱尔·奎尔蒂家的那幢旧房子, 也使我们想起了坡笔下的厄舍故屋,在古老的砖墙背后隐藏了许多的罪恶。
除了爱伦·坡,亨伯特还在他的“自白书”中提到了普鲁斯特与济慈等作家。尤其是 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有关爱情与欲望的描写令他大为赞赏。这几位风格迥异 的作家在亨伯特看来却有着同工之妙。他在他们当中敏锐地找到了气息相通的地方,因 为他们都认为终极的美感与愉悦都是超越凡夫俗子的经验之外的。很显然,这种观点源 自尼采的“酒神精神”,它张扬强烈的激情,宣称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必须摒弃理 性。而亨伯特则由此来表明自己对洛丽塔的迷恋虽涉及道德罪恶,但仍属审美的范畴。
如果说,亨伯特这个人物多少带有点纳博科夫本人的影子,是作家试图通过他来探究 或寻找个别人内心最隐密的某种渴求与欲望的话,那么,我们不禁会问,表现在《洛丽 塔》中的这种情欲是如何发生的?作者的写作动机究竟是什么?
尽管我们知道《洛丽塔》中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也即亨伯特迷恋“性感少女”的情节与 纳博科夫本人的情感生活相去甚远,但纳博科夫还是承认,“运用我的综合技能来创作 它给了我一种特殊的愉悦。”(注:R.Karl,The American Novels,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6,p.115.)也就是说,作者本人的感觉并不完全游离于小说之外。 纳博科夫在他的文章中曾坦言:
对我来说,创作一部小说,仅仅是因为它能给我——恕我直言——一种美的狂喜。那 是一种说不清的,在某些地方来说是与艺术的正常形态如离奇古怪、多愁善感、仁慈如 意紧紧相关的一种感觉。(注:Vladimir Nabokov,On A Book Entitled Lolita,Yi Lin Press,Annotated English Literature Series,1995,p.277,pp.278-279,p.280,p.277 ,p.277.)
他把追求这种狂喜(ecstacy)的行为看成是一种生命的原动力。他说这种感觉,他在艺 术创作、捕捉蝴蝶以及复杂的游戏如国际象棋中找到过。由此可见,我们虽然不必把纳 博科夫对蝴蝶的迷恋与洛丽塔等同起来,但也应看到彼此间的有机联系。纳博科夫可以 说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蝴蝶迷,虽然他是一个昆虫学家,但他对蝴蝶的兴趣已超出了科 学的范畴。他自认为那是一种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迷恋之极的情怀。他在自传性质的文 章《终结性的证词》中写道,“我在自然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追寻的那种喜悦,两者都 有魔力般的形式,都有一种错综复杂的魅力与幻象。据我所知,很少有在情感欲望、野 心或成就感等方面能超过对昆虫学的探索的。”(注:Diana Butler,Lolita Lepidopte ra,New York,New World Writing,1960,p.58,p.70.)对纳博科夫来说,捕捉蝴蝶时感受 到的“狂喜”已是他欲望的重要部分,如同他在艺术中寻找喜悦一样,他在字典中把ny mpholepsy一词界定为一种“入迷的狂乱”,而小说中亨伯特对洛丽塔的那种痴醉与狂 喜,就是这种状态的典型表现。那是一种由无法实现的欲望所引起的、失魂落魄式的迷 恋。但纳博科夫也注意到,这种狂喜与痴迷,倘若以一个男人对早熟女孩的欲望表现出 来,则是病态的,也是危险的。纳博科夫把洛丽塔看成是一只蛹——尚未完全蜕变的幼 虫,就如文学评论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指出的“最近一期《交心》杂志(Encoun ter)中,在《洛丽塔》中,纳博科夫把自己对蝴蝶的痴迷转变成为主人公对早熟女孩的 追猎。至少在一个层面上,作为这部精心制作的文学游戏中的一个部分,小赫兹(洛丽 塔)是一只蝴蝶。”(注:Diana Butler,Lolita Lepidoptera,New York,New World Wri ting,1960,p.58,p.70.)
《洛丽塔》令读者“神思恍惚”的原因,除了它的主题之外,还与作品的叙述有关。 这不仅因为他受到现代作家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的影响,擅用意识流或追忆往事的方 式来表达自我世界的场景,更与他的语言背景密不可分。《洛丽塔》是他第三部用英语 写作的小说,也是他第一部以美国社会背景进行创作的小说。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处处 可以感受到传统的英国文学以及剑桥那种高标逸韵式的文风对他的影响。纳博科夫常常 用一些绚烂雕饰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感觉,这种文采甚至连美国本土的作家也相形见绌 。尽管有人对纳博科夫的这种风格加以嘲讽,说成是作者刻意做作的结果,目的是掩盖 自己弊脚的英语表达能力,但纳博科夫却不以为然。他说“有一位美国批评家(约翰· 荷达伦)说《洛丽塔》是我与罗曼蒂克小说相爱的纪录。我想若用‘英语’一词来取代 会使这一老生常谈更为贴切。”(注:Smith Peter Dwval,What Vladimir Nabokov Thi nks of his Works,his Life,New York,Vogue,March 1,1963,p.155,p.157.)这段话表 明纳博科夫对此书的语言运用能力充满了自信与喜悦。正如现在大多数文学评论家所指 出的,纳博科夫文字的魅力,足以给美国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他另辟蹊径的陈述方式 以及略显铺张典雅的文字,乃是传统与现代的一种融合。
无论如何,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以一种全新的观察角度和表述方式,在文学作 品中探索了人性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洛丽塔》与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 朵玫瑰》、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等作品一样,在表达另类人物的痛苦 与隐私方面,具有发人深省的独特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