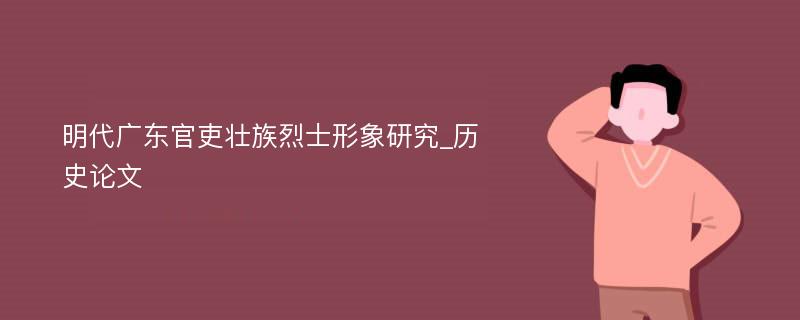
明代广东仕宦形塑庄氏烈女形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仕宦论文,烈女论文,广东论文,明代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1.012 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多以王侯将相为主角,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能进入史家法眼,多为节义贞烈而已。即便如此,一位乡村女性若要成为王朝旌表的烈妇(女),尚需经过多重型塑与包装,才能进入旌表行列。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勃兴,更多学者开始把目光聚焦于传统乡村社会,对生活在底层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女性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但已有论著大多侧重于贞节烈女的群体研究,笼统而模糊,①单独考察某个乡村女性的论著并不多见,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是研究乡村女性日常生活的罕见专著,②全书围绕17世纪山东郯城村妇王氏之死展示了乡村女性日常生活的复杂面相。其实,类似于郯城王氏之死的女性在明清正史和方志中俯拾即是,这些被士人模式化书写的女性,其背后隐藏了各地仕宦向朝廷争取政绩和文化资源的动机,目的是彰显地方教化有成。本文以明代广东海康濒海村妇庄氏因避难而死于新会,经仕宦按照王朝烈女的要求不断书写,最终被朝廷旌表的描述性分析,试图揭示地方与国家互动联手推行教化的过程。 一、庄氏之死的社会背景 庄氏之死,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献为明弘治年间官修《明宪宗实录》卷115,成化九年(1473年)夏四月辛巳条: 诛广东新会县民刘铭、梁狗,枭首示众,旌表海康县民吴金童妻庄氏为烈妇。初,铭、狗同往海康卖谷,将还,海康民吴祁与其弟金童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会,止于铭家。祁既远出佣工,铭、狗见金童妻庄氏色美,屡欲犯之,辄见拒。二人乃谋与金童拿舟捕鱼,夜缚金童,斫其脑杀之,投江中……及二人归,绐庄氏曰:“汝夫溺死矣”。庄氏号哭不已。自是铭愈欲犯之,而拒益力。居数日,忽见尸浮至铭门,适庄氏出汲,识其为夫尸也,哭视之,斫瘢宛然,始得其谋死状。顾力不能报仇,乃先投其幼女于水,即自投水附其夫尸死焉。已而三尸随潮上下,旋绕铭门不去,其乡邻李逢春辈异其事,为买棺收葬。铭又乘夜潜发其尸,弃之大海中。于是事寖传于人,而吴祁亦自外至,乃诉于官……③ 从这段史料可知,庄氏一家原居于广东西部沿海的雷州府海康县,因“避寇”迁徙到广东中部的广州府新会县,最后一家三人死于新会。庄氏一家从海康迁徙新会,属较长距离的迁徙,他们乘坐的商船是新会人刘铭、梁狗在海康做生意的船只。庄氏一家抵新会后,暂时落脚在刘铭家,并受雇于刘铭。庄氏的夫兄可能未婚,故到新会后又独自“远出佣工”。从“三尸随潮上下,旋绕(刘)铭门不去”判断,刘铭等也居住在海边。 新会刘铭等到海康“卖谷”,是庄氏一家与之发生关联的源头。明代以来,广州府和雷州府已存在着频繁的贸易交流,史载,“雷无万金之产,即称素封者,不过免饥寒而已。贩易惟槟榔、鱼菜,米谷、食物、木石拔作俱自广州。”④据陈春声研究,自宋元以后至明代万历年间,珠三角农业迅速开发,大量的米粮不断输往邻近省区,雷州半岛也是其中之一。⑤明代珠三角还与粤西保持着频繁的贩柴贸易。⑥这些贸易均以船只为运输工具,商人们在停泊码头时,多会和水上或滨水地区疍民发生联系。从庄氏一家搭刘铭船迁新会看,他们的结识或正缘于此。但船只毕竟空间狭小、男女混杂,有违“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原则,故刘铭等到海康“卖谷”的情节在广东旧方志中几乎均被省略,如《广东通志初稿》记载说:“庄氏,雷州海康人,随夫吴金童避荒,佣于新会刘铭、梁狗家。”⑦嘉靖年间,海康人冯彬撰《庄节妇传》说,成化元年(1465年)瑶人掠雷州,庄氏居住的“荇洲去城二十里,残尤甚”,遂跟着丈夫“赴广州,避难于广。时持舟者曰刘铭、梁狗,俱广之新会人,见庄色而悦焉。”⑧ 庄氏全家从海康迁徙新会的外在推力,应与成化年间粤西不时爆发瑶乱有关。这在嘉靖《广东通志》有模糊说法,“成化初,广西流贼劫掠乡邑,人民饥馑,庄氏随夫避难于新会,寄寓刘铭家,佣以自给。”⑨这里也省去了刘铭等经商海康的环节,将庄氏“避难”时间定在成化初。黄佐所说“流贼”和实录中的“避寇”,均为瑶乱,此在《雷州府志》有明确记载: 庄氏,海康吴金童妻,吴世居邑之荇洲里。成化初,猺贼害甚。六月间,值新会县民刘铭、梁狗同卖谷海康,将还,吴祁与其弟金童携家避寇,附铭舟至新会,止于铭家。庄年二十二,有丽色,铭屡挑之,庄不从。⑩ 这是目前所见庄氏在海康生活的较清晰版本,不仅交代了庄氏在海康的具体生活地、年龄,而且交代了成化初瑶乱甚烈,以及刘铭等六月在海康卖谷。同时说,庄氏因“有丽色”而引起刘铭后来的屡屡挑逗。这里的成化初,上引冯彬表述为成化元年。另据《雷州府志》记载,成化元年正月,广西大藤峡瑶乱寇雷州、高州等府。(11) 成化前后,粤西地区瑶乱不断,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新会县志》收录有成化年间陶鲁《奏立两广总督疏》中说:“两广地方自正统年间,被蛮贼聚众流劫厢乡,攻破城寨,烧毁房屋,杀掠人财,连年屡岁,民受荼毒,无所控诉。”(12)正统以后,朝廷面对持续不断的瑶乱,不得不派重臣南下平乱,成化元年巡按御史龚晟、按察佥事陶鲁等上奏:“两广残贼日炽,必得大臣提督兼巡抚斯济,”(13)朝廷遂派韩雍为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赴梧州讨两广“蛮贼”。很显然,海康庄氏背井离乡,与此时瑶乱有密切关联。据《新会县志》记载,成化初,瑶乱流劫雷州、高州等府,所到之处“无完庐”。(14)《雷州府志》记载,成化元年瑶乱袭雷州,大批民众“俱奔入城,相持日久,城中疫起,十死六七,田野荒芜,户口顿渐”。(15) 成化前后屡屡发生的瑶乱,对珠江三角洲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一方面,朝廷从这里调拨粮食运往粤西,刘铭等到海康卖谷即可能与此有关;另一方面,珠三角又成为战区难民的避难地。在瑶乱笼罩的大环境下,刘铭等前往战区从事谷物贸易,或许受到了官府的保护,但也可能与刘铭、梁狗的个人势力有关,据《广东通志》记载,庄氏丈夫被杀后,乡人开始“未知(刘)铭之杀也。后梁狗与人言其故,人始知之。然畏刘铭强暴,亦未敢发也”。(16)而《明史》记载是“梁狗漏言”(17)而泄密。不管梁狗是故意还是无意透露这个信息,都显示他们在新会有实力,故乡民不敢告发。明代广东沿海社会一方面受乡豪左右,另一方面又存在“民”、“盗”界限模糊的现象。(18)刘铭等大约属于乡豪,这在明代新会不属孤证,《新会县志》记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大岭村贼乱,民众“率乘舟逃窜,日则海洋中,夜则泊岸”,有数股盗贼乘舟“往阳江诸县剽掠”,(19)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新会与粤西海洋往来的便利。 从上可知,庄氏在成化初年因瑶乱而抵新会,并在刘家佣工,因年轻漂亮而常受刘铭等骚扰,但她没有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丈夫,并因此埋下隐患。刘铭和梁狗合谋骗其丈夫金童出海捕鱼,在夜深人静时,捆缚金童,“斫其脑,杀之投江中。”之后,又屡次对仍住其家的庄氏“愈欲犯之”,庄氏“拒益力”。数日后,庄氏外出汲水,发现漂浮在刘家门口的丈夫尸首有明显“斫瘢”,明白丈夫并非溺水身亡。她意识到一个弱女子要为丈夫报仇已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而刘铭又不时骚扰自己,遂投水自尽。不过,其他文献记载庄氏之死与《明实录》有所不同,如《广东通志》说她在丈夫三日未归时,主动到海滨寻找丈夫的尸首,“即归,携其女赴水,抱夫尸而没。”(20)《雷州府志》说她“号哭,回力不能报,乃自梳洗,抱三岁幼女至江边,先投幼女于水,即自扶夫尸投水而死”。(21)《新会县志》则说庄氏在发现丈夫死后,“是夜,庄潜出,负女赴水死。”(22)可见,关于庄氏之死的细节,多为士人的想象。但庄氏之死确实惊天动地,以致出现“三尸绕门”的异象。 上述《雷州府志》说,庄氏“有丽色,铭屡挑之,庄不从”,(23)即使在其夫遇害后,刘铭也未停止对其骚扰,但庄氏并未作出剧烈反抗。这与方志记载类似女性被调戏时多主动自尽不同,如《新会县志》记录华萼东村卢氏16岁嫁给林宗为妻,平时“慎出入”,村人“鲜识其面”。但方志又说她与邻妇合纱召工织布,某日丈夫外出,男工秽言调戏她。她将遭遇告诉丈夫,希望丈夫出面教训男工,但其夫怕事未加干预,25岁的卢氏失望投江自杀。(24) 万历年间不同士人编纂的地方志对卢氏自尽与庄氏屡遭调戏而无过激反抗的书写,反映了书写者的不同心态。新会仕宦甚至没有把庄氏列入万历《新会县志·贞烈传》,仅记载在该志卷6《陵墓》中。此缘由可能与庄氏不是本地人有关。而万历《雷州府志》对庄氏遭调戏的描述,似乎暗示庄氏的疍民身份。明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里甲制,限制民众自由流动,“人民的移动、迁徙,是受限制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行动,都要得到政府发给的‘路引’(即通行证)。”(25)明初广东编制户籍,对生活在江海间的疍户除自愿附籍者外,一般不硬性列入户籍管理之内。(26)庄氏一家居住海洲,极可能是没有附籍的疍民,万历《雷州府志》记载,“庄氏,海康吴金童妻,吴世居邑之荇洲里”,查现存最早的《海康县志》记载,荇洲里“在县南一十五里,以洲多荇菜,故名。吴林二姓世居”。(27)这个“洲”显然指海中由泥沙冲击形成的岛屿,吴姓至少从明代开始就一直在此居住,庄氏婚后随夫吴金童居荇洲里。以此推测,庄氏及其夫家应为疍民。现存康熙、嘉庆《海康县志》均列有“疍户”名目,“调洲,城东二十里海中,周围三十余里,为疍户泊息之所。”(28)疍民漂泊海上,即使官府也难管束,清初屈大均则说:“广中之盗,患在散而不在聚,患在无巢穴者,而不在有巢穴者。有巢穴者之盗少,而无巢穴者之盗多,则疍家其一类也。”(29)从庄氏全家自由流动看,极可能是尚未被官府编入户籍的疍民,但他们一旦上岸居住,就可能被视作编户齐民。明代已经濒海陆居的疍民甚至能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明末袁崇焕家就是疍民,后到广西藤县冒籍科考。(30) 二、仕宦在舆情鼓噪下对庄氏形象的形塑 庄氏一家死于非命后,舆情对这个悲烈故事的传播,在当时士大夫的记录中略可管窥。庄氏一家到新会后,刘铭因庄氏美色,不仅留宿庄氏一家,而且还“厚遇之”。刘铭在屡次挑逗庄氏不果后,就试图让吴金童外出耕作,“一日发怒语吴曰:而就吾舍若几何?而食吾给若几何?而负吾值若几何?而懒慢守若妻,以玩若日,曷不代吾耕以酬吾负乎?”看得出,刘铭一开始想通过恩惠占有庄氏,受挫后,又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而刘铭乘吴金童“耕于亩”时,又对庄氏进行挑逗,庄氏仍不从。刘铭于是想强暴逼迫庄氏就范,结果被“庄持刃以之决”。刘铭的欲望最终没有得到发泄。(31) 根据冯彬的记载,当庄氏将刘铭侵犯自己的行为告诉了丈夫吴金童,其夫却让她“姑忍之,徐计归耳”。这个“归”,含有离开刘家另谋生路,也有回海康之意。而“忍”字则说明这个家庭尚不具备回家的条件。就在庄氏夫妇计划离开时,刘铭和梁狗却合谋哄骗金童夜晚出海捕鱼,而将其在海上杀死,“刘欲图庄氏,因谋杀金童于海上,而庄氏不知。”(32)两人回家后欺骗庄氏说,金童因“风急溺焉”。庄氏将信将疑,“抱女讯于江干,而哭之哀。”刘铭面对此情此景,又邀村里老妪对庄氏“宽慰以辞”。就在此时,吴金童的尸体被上涨的潮水“荡及岸”,庄氏看到丈夫脑袋、两肋、手足皆有伤痕,“惨不可言”,恸哭着说:“冤哉伤乎,吾以色而陷吾夫耶!吾孤茕,义莫克报,吾其生耶?”庄氏认为是自己的美貌害了丈夫,但自己“孤茕”无法为丈夫报仇。她用衣服覆盖好丈夫的尸体,回到村里“遍投里中”,就是把丈夫遇害的事实公之于众,然后以死殉夫。她抱着女儿又回到丈夫尸体旁,“先投女于江中,乃从容附夫尸而投诸流焉。”庄氏的所为惊天动地,乃至出现“三尸随潮进退绕铭门”的异象,乡民李逢春等募资埋三尸于石碑都吴村,新会生员李启等出于义愤和使命感,将庄氏之死上报知县,最后层层申报到朝廷,“白是事于邑大夫,转达于部使者。部使者廉其实,置二凶于法而籍其家,且旌庄氏以烈云。”(33) 上述记载的情节与《明实录》和地方志的记载有所不同,其对庄氏一家的死亡过程记述较为清晰,逻辑上也较为连贯。庄氏在发现丈夫遇害的尸体后,即回村里求助乡民,因而出现集资安葬的情节。关于乡民安葬庄氏的说法在当时地方志中也有反映,《广东通志初稿》说“乡人葬之吴村”,(34)这可能是庄氏在新会的生活地。《广东通志》则说乡民“感伤惊讶,共殡祭之”。(35)乡人“共殡”说明这一事件受到社会的普遍同情。李逢春应该是这次行动的为首者,“其乡邻李逢春辈异其事,为买棺收葬。(刘)铭又乘夜潜发其尸,弃之大海中。”(36)也就是说,刘铭将乡民埋葬庄氏一家的墓挖毁,将尸体扔进大海。那么这个墓修于何时?《新会县志》记载,成化四年(1468年)“佥宪陶鲁命工立墓于邑西吴村里”。(37)这表明庄氏死于成化四年前,李逢春等或许是在官府干预下才率乡民将庄氏一家安葬。这个墓被刘铭破坏后,直到成化九年又在官府干预下重在吴村庄氏墓原址竖石碑。稍后再加分析。 然而,庄氏一家死因何在?除了庄氏生前在乡村诉说外,乡民并不了解真情。乡民们在埋葬庄氏一家三口后,估计无人去追究他们的死因。将此事暴露出来的恰恰是加害人,“后梁狗与人言其故,人始知之”。但乡人因害怕刘铭“强暴”,一直不敢告发,只能私下议论,于是庄氏一家死亡之“事寖传于人”,“乡人哀之,闻于官,时御史钟晟闻其事于朝。诛刘铭、梁狗于市。”(38)换句话说,庄氏之死由普通的刑案而在乡民的议论中演变为社会事件,激发了新会籍儒生们的正义感,儒生李启、李蕃及关道安(39)等“争述庄氏节义”,更多士人以文字表达对庄氏之死的哀悼,出现“士人吊哭诗章”现象。(40)儒生的加入,尤其是他们对庄氏之死的书写,进一步扩大了该事件的社会影响,《广东通志》记载:“既而传闻渐著,骚人墨客竞为诗歌以吊之。有司闻焉,遂捕刘铭、梁狗询实,处以极刑。”(41)但官府的真正介入,估计与吴祁归来状告有关,“吴祁亦自外至,乃诉于官,”(42)《雷州府志》则说:“吴祁自外归,得弟尸于海滨,乃诉于官。”(43)这个记述若真实,就可能是刘铭再次抛尸。而吴祁回到村正赶上村民议论频繁之时,他从中获知弟弟一家死亡的原委,遂向官府告发。但吴祁何时状告则史料缺失。 在新会籍士人的参与中,硕学大儒陈白沙表现最为活跃,他在成化年间与时任新会知县陶鲁等在宋元海战的崖山成功倡导建立了大忠祠、全节庙等宣传臣民对王朝的忠诚。(44)成化六年,时年43岁的陈白沙前往吴村祭拜陶鲁修建的庄氏墓,并作《吴村吊庄节妇墓》五律二首,后被《广东通志初稿》收录,一曰:“豺狼何由近,风涛浩若无,行人看墓榜,英爽在清都,江暝云长合,原寒草不枯,乾坤不朽事,持此报君夫。”二曰:“此里有此墓,千年亦不磨,世方逐蔡琰,吾甚敬曹娥,淫盗死殊色,良人及逝波,江翻练裙带,激烈有遗歌。”(45)此二诗除了展示庄氏铮铮不屈的义烈形象,还在于昭示“行人看墓榜,英爽在清都”的价值观。诗中的蔡琰系三国才女蔡文姬,一生改嫁多次;曹娥是东汉孝女,投江救父,受历代景仰。很显然,陈白沙贬蔡琰褒曹娥,就是要向社会大众传递忠孝的教化思想。陈白沙吊唁庄氏的诗作,在《雷州府志》记载为《挽庄节妇诗》三首,字句与上述有些微不同,第一首的开头为“节妇有此庙,千年亦不磨”,后面完全一致。第二首曰“盗贼轻人命,纲常杀此躯,也能作厉鬼,不问葬江鱼。骨肉他乡尽,英灵此庙居,乾坤不朽事,持以报君夫。”第三首曰“痴子啼复急,良人暮不还,彷徨妾心悸,负儿岀门看,死者为妾身,暴尸门外湾,匍匐往视縳,割裂肠与肝……稽首告青天,饮恨赴奔湍,湍水照妾心,湍日照妾颜,妾恨何时终,岁岁如转环。”(46)第三首带有写实色彩,描述庄氏在丈夫死后忠贞不贰的悲壮心情。据《新会县志》记载,陈白沙的诗作以“草书”刻石立在雷电山庄氏墓旁。陈白沙后又撰《书韩庄二节妇事》肯定庄氏节义行为,借机讽刺饱读诗书者在忠孝抉择时的口是心非,他说: 呜呼!二氏之生,其相去且千载。韩,故相国休之孙女;庄,雷郡庶人妻,贵贱虽殊,其死于义一也。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辞气如大冬严雪凛乎,其不可犯,是岂资学问之功哉?是岂尝闻君子之道于人哉?亦发于其性之自然耳,今之诵言者咸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故临利害,比二氏乃能之学者,故不能于此,然则从事于诗书,反无所益,彼之弗学,乃能不坏其性,何邪?是必有所以然者,学止于夸多斗靡,而不知其性为何物,变化气质为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于禽兽者几希矣。余读二氏之辞有感,故录而藏之。(47) 陈白沙以议论的方式将庄氏与韩氏比对,以“庶人”表示已经上岸居住的庄氏普通民众身份。据元人胡炳文《纯正蒙求》卷上记载,韩氏为唐代相国韩休之孙女,节度使柳公绰妻,她身处富贵之家,但教子甚严,留下“和丸教子”的典故。陈白沙通过韩庄身份对比,讲述“义”乃人之本性,并无贵贱之分,与学问深浅无关,其用意应是“存天理灭人欲”,借此倡导忠义理念,以巩固王朝统治。 与此同时,新会官绅也纷纷加入到形塑庄氏烈女形象的队伍中。《新会县志》记载了一些官绅祭拜庄氏墓留下的诗作,如成化知县丁积诗云:“一死纲常系匪轻,三人夫妇子同茔。可堪避难还遭难,不肯偷生是得生。恶贯群凶终授首,义高匹妇也成名。东风远吊吴村墓,绿野无烟草树馨。”又天顺三年(1459年)新会举人李荣诗云:“一死报君妇与儿,乾坤纲纪类支持。寒江千古消还长,犹是贞魂不息时。”(48)这些诗作突出了庄氏“义高”的形象,为宣传节义树立了榜样。 在新会民众与官绅的共同努力下,庄氏案在成化八年水落石出,清人汪森记载说,这一年,朝廷派刑部员外郎冯俊到广东“清狱”、“审囚”,他经过对地方官府已审案情的“核实”,坐实了刘铭等是害死庄氏一家的罪魁祸首,并上报朝廷“处(刘)铭等极刑,奏旌庄氏烈”。(49)但《广东通志初稿》却记载是御史龚晟将庄氏案“闻于朝”的说法。(50)还有文献认为是冯俊和陆瑜分别上奏,“刑部员外冯俊特为具奏,上令有司即诛铭、狗,枭首示众,旌表庄氏。刑部尚书陆瑜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尸,诚为义举”。(51)笔者以为,冯俊先将奏折呈给时广东巡按监察御史龚晟,由龚晟呈递朝廷。因庄氏案属刑案,再经刑部尚书陆瑜(52)呈递给明宪宗。 可见,地方民众和仕宦对庄氏节义的舆论明显影响着朝廷的评判。明初以来,士大夫基于教化的关怀,逐渐形成了一种主动书写节妇烈女的“社会仪俗”,这些节烈文字在“士-宦”网络中流动,形成一种道德舆论,具有补充国家教化疏漏的功能,并成为地方官员行政上的参考。遵循这一脉络,庄氏殉夫原本只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与行为,但士大夫对其“吊哭诗章”的舆论造势,无形中促使该案件演变为社会事件,庄氏也因此成了万众瞩目的节义女性。但明代旌表列女的呈请有一套严格的行政流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旌表呈请由有司正官举名具奏礼部,待监察官核实后,还须有府州县以及里甲的保勘。(53)其实,真正操作起来又相当繁琐,崇祯年间,冯梦龙主修的福建《寿宁待志》记载当地向朝廷申报旌表童生叶从式妻吴氏屡经反复。吴氏18岁结婚,数月后夫死,孀居守节达36年,历经四任知县“采众议举报”,申请朝廷对之旌表,但得到的都是“复勘,又奉查”的回复,最终以“入‘情最苦’一册,仅蒙赐匾,尚虚旌扬”。(54)于此可见王朝对旌表的重视。而庄氏获得王朝旌表,也是冯俊在地方舆情基础上的审实呈请,黄佐在庄氏传后附有“审录员外郎冯俊上庄氏事略”记载说: 庄氏生长田野,出配蓬门,礼义自明,非由姆教,遭窘不能聊生,随夫流离异境,衣食既资于人,居处罔由于己,夫尚存时,刘铭梁狗将欲犯之,依然拒绝不从,夫既被害,忿刘梁无可奈何,慨然抱女同死,事出非常,心本无二,如此秉德不回,奚让古之烈女?上则感动天地,俾三尸流绕于原犯之门,下则兴起人心,致众口称扬于百里之邑,儒士作歌吊挽,父老捐财殡埋,伏乞旌表,以励风俗。(55) 冯俊上奏中的“下则兴起人心,致众口称扬于百里之邑,儒士作歌吊挽,父老捐财殡埋”,正反映了庄氏事迹在乡村社会已产生广泛影响,而且也具有明显的“励风俗”作用。冯俊何许人也?嘉靖十年(1531年)刻本《广西通志》卷44《人物传》和乾隆《庆远府志》卷8《人物志》记载,冯俊为广西宜山人,天顺年间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以仁恕折狱,成化十一年(1475年)擢福建按察司副使,后任广东布政使,又升副都御史,弘治九年(1496年)七月卒于官。他认为庄氏尽管没有接受教育,但对“礼义”了然于胸,而新会民众和儒士在她死后的作为,恰恰印证了王朝教化在乡村的推广与普及。可见,在地方舆情和官府的互动运作下,庄氏成为了由皇帝下令褒扬的全国性道德楷模。随后广东官绅不断书写庄氏的故事,并为之建祠修墓立牌坊,使一桩原本单纯的命案上升为地方公共记忆中的女性节烈符号,进一步放大了烈女在社会中的教化功能,突出了王朝对认同国家话语之天下子民的关爱。 三、官府用固态建筑彰显庄氏烈女形象 庄氏案历经数年,终于在成化九年获得朝廷旌表。庄氏生于动乱频仍的海滨之地,朝廷之所以旌表庄氏,一方面是地方官绅鼓噪其节义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为了吸引更多疍民自愿入籍,服从王朝国家的善恶准则。 广东官府在接到朝廷旌表庄氏的诏令后,立即开始行动,通过一系列工程建设,以固化物表达了庄氏的烈女形象,以起到睹物思人的教化作用。成化九年广东官府在已被刘铭等破坏的庄氏墓重建并竖立石碑,“今已遭发掘,宜命有司即其处立石,而大书其夫妇姓名以志,庶可垂示永久。”(56)《广东通志》明确记载,朝廷“檄新会县于殡埋处立石,表其墓,仍行原籍一体旌表”。(57)如此看来,成化四年陶鲁命工修墓以及李逢春等率乡民埋葬庄氏一家是同一回事了。王朝一方面要求在庄氏死难的新会吴村墓地立石,另一方面要求庄氏原籍的海康县也要有所表示。树碑立传是传统社会推广教化的一种手段,因为墓与碑作为一种实物形态,能让民众睹物思人,进而想到王朝借此的象征寓意。这一点在岭南硕儒湛若水为顺德贞女吴妙静撰《宋贞女吴氏墓表》一连用了五个“过之曰”,即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等经过吴妙静墓时,凡是因自己的言行与之不符者,“则必愧死于墓下矣”。(58)其用意就是让全社会人只要看到吴妙静的墓及牌坊,就应自觉检讨自己的言行,如此则可收到“一振举而万化从之”的社会效果。湛若水身兼朝廷大员和硕学大儒的双重身份,其为贞女吴妙静书写墓表所要阐释的重点就是吴贞女对夫家的贞和对父家的孝,赋予了列女具有的重要教化意义。(59)这一意图也是广东仕宦为庄氏修墓立石的重要缘由。 从文献记载看,新会和海康建庄氏祠和牌坊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新会反映快速,海康相对滞后。上述冯彬《庄节妇传》显示,“时白沙陈公甫与丁尹积议建贞烈祠于新会之南门,以庄并韩氏祠焉。当士夫咸挽有诗,雷始闻其事,争传之。好事者演为戏以劝世,世始知雷有庄氏云。”(60)这说明,新会士大夫建祠挽诗之后,有关庄氏的故事才传遍全省,甚至被搬上戏剧舞台,进一步扩散了庄氏故事的社会影响。《广东通志》也说:“今新会有庄节妇祠”;(61)又据《雷州府志》记载,新会官民在接到朝廷旌表令后,“乃建祠于新会之南门,名贞烈祠。”(62)不过,有关新会为庄氏建贞烈祠的具体情况,史料无更多记载,本文无法深入讨论。 与新会相比,海康不仅没有为庄氏建祠,官府也迟至嘉靖初才行动起来,据《广东通志初稿》记载,雷州府出面为庄氏建了一座叫节妇亭的牌坊,“在城中正坊,知府杨表为海康吴金童妻张氏立。”(63)张氏应为庄氏之误写,杨表任雷州知府具体时间不详,但又必须弄清楚,否则难以知晓节妇亭建立时间。据《雷州府志》专列“旌表节义”条说:“宜稼坊,成化间知府杨表为贞烈庄氏建于城中,岁久倾坏。知县沈汝梁移建于东城外。”(64)该志又说:“至嘉靖丙戌(五年,1526年),雷守杨表复建亭于阜民桥南,立碑纪之。”(65)这两条资料给人的印象是海康为庄氏建立了牌坊和亭两座建筑,且杨表出现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同一部方志对杨表记载的混乱,本身已意味着海康官府对庄氏旌表的应付。查《广东通志》记载,杨表为福建龙溪人,嘉靖五年知雷州府事,如此则海康庄氏节妇亭应由杨表建于此时,位置在阜民桥南,且立有碑。(66)杨表所建之亭位于城内,万历初年知县沈汝梁将之移至东城外,《雷州府志》记载,沈汝梁系福建漳浦人,万历九年(1581年)任海康知县。(67)此后,雷州文献罕见庄氏的新记录,《海康县志》说,节义坊在宜稼坊,“为贞烈庄氏建于城中,年久倾坏,知县沈汝梁移建东城外,久圯。”(68)这说明海康为庄氏建立的牌坊,没有给予有效的管理,故到清代又“久圮”了。 新会县对庄氏烈女形象的实物建构,除了上文提及建贞烈祠外,并没有建牌坊,其建构庄氏烈女形象的重点是修墓置祭田,《广东通志初稿》记载,庄节妇墓在新会县雷电山,原吴村,墓为陶鲁立,“知县丁积割废田六十余亩,命邑人立其祀。”(69)事实上,戴璟之说过于简略,据《新会县志》记载,庄氏墓以后有所迁移,且知县丁积割废庙田也有明确时间,如下: 成化戊子(四年)佥事陶鲁命工立墓于邑西吴村里,成化辛丑(十七年,1481年),知县丁积割废庙田六十余亩,命邑人主其祭事。弘治中,知县罗侨迁于雷电山,与萧氏墓并谓双节墓。嘉靖中有夺其祭田者,知县张文凤追复之。(70) 可见,自成化四年至嘉靖中叶,庄氏墓和祭田均有所变化,但最终因有官员干预而得以完满。这里出现的萧氏,名乌头娘,香山人,据《香山县志》记载,她在景泰年间黄萧养叛乱时仅18岁,“有容色”,被官军以“乡民之胁从者”捕之,押往新会,至东亭驿时因不堪侮辱,被官军杀害,时新会人李彦英、谢齐祖“构钱买棺葬于邑西象山”。成化十七年(1481年),知县丁积命人重修其墓,“且割废庙田六十亩,命人岁守祭事”。弘治十七年(1504年)知县罗侨“以守非其人,墓将就堙,乃改葬于雷电山”。(71)陈白沙为这次改葬撰写了《止迁萧节妇墓赋》,附录在道光《新会县志》卷7《冢墓》中。应该说,丁积的作为使庄、萧二墓祭奠在制度上得到了物质保障。但据《新会县志》说:“丁积割废庙田六十余亩,命人主祭双节墓,”(72)则说明60亩是为庄、萧二墓所为。 丁积之所以如此卖力,除了知县身份外,还与他贯彻老师陈白沙的意图有关,据《新会县志》记载:成化十五年(1479年)“进士丁积为新会令,闻献章名曰:‘吾得师矣’。甫下车,求执弟子礼。”(73)陈献章在家乡积极推行礼仪,自然赢得门徒丁积的响应,《新会县志》收录《四礼仪式》就是丁积在新会知县任内制定并推广的礼制,“择年高有德者”作为都老、乡长,“以教其民”。(74)陈白沙在《丁知县行状》中说:“节义所关,或庙或墓,各置祭田,择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余亩,节妇何氏庄氏萧氏等墓置田共一顷六十余亩。”(75)丁积在新会整肃礼仪的做法取得了成效,他的后继者一直维持着对庄氏墓的祭奠。弘治十七年(1504年),时任知县罗侨将庄氏墓由吴村迁移到雷电山,与萧氏墓并列形成“双节墓”格局。罗侨对庄、萧二氏墓的迁移,或许是为了便于官府集中管理,或许是为了突出两位外地女性在新会节烈的形象。清顺治三年(1646年)又将新会人利烈女也葬在雷电山双节墓旁,道光十七年(1837年)知县黄定宜在雷电山竖“三烈”墓碑,以致有“未知其孰为萧庄孰为利氏也”的现象。(76)陈白沙、丁积等仕宦联手,通过对双节墓等一系列事关“节义”人物的祭祀活动,从而将国家礼仪贯彻普及到乡村社会。 成化年间,新会知县丁积不仅割废庙田供“双节墓”祭祀,而且还“命人岁守祀事”,道光《新会县志》卷10《列女》记载说:“萧庄二烈,本非邑人,但其死葬皆在邑地,设有祭田,岁时祀事”。(77)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正月,庄氏的守墓人番禺古冈容贯为了向社会大众传达仕宦对庄氏重视的信息,专门将陈白沙的二首诗和丁积的一首诗刻石立碑,竖立在庄氏墓前,而且“皆为白沙行书”。(78)容贯为此还撰写了后记:“庄氏以流离异乡之佣妇,仓卒遭变,而能以身殉其夫,不污于淫盗之手,其死有足称者。白沙先生二诗可当一传。厥后邑丁侯有吊墓之作,贯承命守墓,因具石乞先生书以冠焉。呜呼,名以诗传,诗因人著,其所表高谊,振春风何可少哉,何可少哉!”(79)这在《粤东金石略》也有说明:“吴村里吊庄节妇墓,邑人陈献章二诗,宁都丁积一诗……皆白沙行书。”(80)容贯为番禺人,系陈白沙的门生,此在万历《新会县志》卷6《白沙弟子传》中有载,且附有陈白沙为容贯所写的小记。 “双节墓”的祭田在嘉靖间曾被人侵占,经时任知县张文凤的干预而追回。嘉靖十一年(1532年)三月,邑人李江撰《庄萧二节妇墓田记》,由庠生谢忠在雷电山萧庄墓旁刻石立碑,此碑到道光年间已模糊不清,但从中仍可辨出其原委,《新会县志》收录此碑记云:“万世纲常所系匪轻也……奈何时渐变田渐改,识者恨之。庚寅(嘉靖九年1530)张公来知,则曰:贞节所当记也,田渐改则祭渐废而墓渐荒,何以激励风俗乎?于以□□□数复之,修其墓而新之……扶植纲常固非作意而为之也。”(81)可见“激励风俗”、“扶植纲常”,是新会仕宦重视庄氏等烈女墓及其祭祀的重要缘故。明代新会祭拜庄氏的制度在清代仍被延续,《新会县志》记载:“今查萧、庄二氏祭田共七十八亩八分零,坐落本县归德六图土名坡下苑、石冈、麦郊场、白皮冈、大皮头、横基萌等处四十亩一分零,石碑二图豆冈四亩一分零,石碑三图乾滘沙路酸等处六亩四分零,石碑五图高嘴贵村、崩坳肖村、背津子尾望片大三塘等处十七亩一分零,承管祭田区姓。”(82)可见,双节墓祭田并未因改朝换代而消逝,也意味着明清王朝烈女观的连续不变。 庄氏的故事在明末已经由广东传播到全国各地,各类史籍对其记载不断增多,明代广东纂修的通志《人物》卷多收录庄氏故事,且相互抄录补充,使其烈女形象更加丰满,如黄佐在《广东通志》庄氏传后即说传文“据《新会志》《雷州志》参修”,而以后的《广东通志》又多抄录黄佐通志。与此同时,广东之外的士人也开始关注并书写庄氏故事,如万历二年刻本《宪章录》、万历三十年(1602年)刻本《皇明大政纪》、万历刻本《明政统宗》、天启二年(1622年)刻本《涌幢小品》、天启四年刻本《国朝典汇》、崇祯刻本《皇明通纪集要》、崇祯九年刻本《昭代芳摹》、崇祯刻本《名山藏》、明末刻本《皇明从信录》以及小说《情史》等,均有庄氏故事的记载。这些士人在编写庄氏事迹时或在以往基础上压缩,或增加新的情节,以增强故事的可读性和感染性,但对庄氏节义的情节却不断规范,尤其是方志的编写越来越模式化。(83)这些书籍对庄氏故事的书写,一方面显示了书写者对庄氏故事的接受,另一方面随着这些书籍在社会上的流通,无形中又进一步传播了庄氏节烈的社会形象。 本文分析表明,庄氏之所以能得到王朝旌表,首先是其一家三口死于非命而引起乡民的同情,并由此引起当地士人的关注,进而引起官府的介入,正是在“士人社群的动员”下,(84)庄氏殉夫最终得到了朝廷旌表。因此,尽管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庄氏故事的文献是《明宪宗实录》,但这并不意味着庄氏故事最早是由朝廷旌表才引起地方关注。 宋代以来,儒家思想已经进入广东的中心地广州,但直到12世纪,却看不出此刻已经形成的广东士绅有多少效力王朝的热情。直至明初,儒家思想再度在广东发生影响力,不仅培养出大批士绅队伍,也使广东士绅认为自己与全国的士绅同属一脉,愿为王朝效忠。(85)随着景泰年间黄萧养事变至成化年间广西瑶民起事,广东士绅推行王朝礼仪和教化就成了工作重点,而忠孝节义又是教化的重心所在。广东仕宦在书写庄氏殉夫节义时,尽管会打上时势和自身理解的烙印,他们编写的人物对话场景等细节,也出于各自不同的理解而发挥和演绎,但最终目的是将庄氏型塑为具有教化的烈女形象,使人在阅读过程中,对庄氏产生怜悯,对刘铭、梁狗之徒无比痛恨。仕宦作为王朝推行教化的实施者,充分发掘庄氏故事可能产生的道德资源,既可以讽励末俗,又可以彰显地方与王朝意识形态的同步走向。 庄氏由村妇进入被王朝旌表的烈女行列,与陈白沙等为首的一批广东籍士大夫刻意挖掘及型塑密切相关,他们的积极参与使庄氏更加符合王朝的烈女形象,直接影响着王朝对庄氏的旌表。之后,广东士人在此基础上对庄氏故事不断层累书写,最终使庄氏进入《明史·列女传》中,在这部由皇帝钦定的官修正史中广东烈女仅6人。广东仕宦在得到朝廷旌表庄氏的尚方宝剑后,新会和海康两地在不同的时间内为庄氏建立祠与坊表,新会还修墓、拨田祭祀,在空间上为百姓建造了烈女典范的实物形态,并在时间上开始了延绵不断地书写庄氏故事的历史。应该说,在广东地方社会与王朝的互动下,庄氏最终被型塑成明代全国性的烈女典范。明代仕宦对女德的要求已经完全标准化,描写和赞美家乡的方式也标准化,节妇和烈女成为他们“乡里荣耀”的常用标志。烈女的理想原型是宁死不失节,这样的女人对于男子的自我写照是一个十分有用、非常有力的象征。(86) 注释: ①安碧莲:《明代妇女贞节观的强化与实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年;费丝言:《由典范到规范——从明末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8年;衣若兰:《史学与性别:〈明史·列女传〉与明代女性史之建构》,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蔡凌虹:《明代节妇烈女旌表初探》,《福建论坛》,1990年第6期。 ②[美]史景迁著,李璧玉译:《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③另据嘉靖三十四年刻本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22记载,庄氏被旌表的时间为成化九年二月。 ④郑俊修,宋绍启纂:《海康县志》上卷,《民俗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刻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⑤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9页。 ⑥刘正刚、陈嫦娥:《明清珠江三角洲的燃料供求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⑦戴璟修,张岳纂:《广东通志初稿》卷15,《烈女》,嘉靖十四年(1561年)刻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301页。 ⑧参见许衍董:《广东文征》第3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74页。另据万历《雷州府志》记载:冯彬系雷州卫人,嘉靖八年进士,出任过平阳、上海县令,邃于理学,著《桐冈集》,嘉靖二十三年与知府叶尚文辑《雷州府志》(已佚),后祀于乡贤祠。参见欧阳保等修纂:《雷州府志》卷17,《乡贤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刻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⑨黄佐:《广东通志》卷63,《列传二十·列女》,嘉靖四十年(1561年)刻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658页。 ⑩欧阳保等修纂:《雷州府志》卷19,《贞女志》,第274页。 (11)关于庄氏避难于新会的时间,文献的表述不一,除了上述不同说法外,又如明天启四年刻本《国朝典汇》卷127《礼部》记载为成化九年四月。很显然,这是抄录《明实录》中的旌表时间。参见欧阳保等修纂:《雷州府志》卷1《舆图志》,第17页。 (12)贾雒英修,薛起姣等纂:《新会县志》卷17,《艺文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刻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759页。 (13)钟芳:《钟筠溪集(下)》卷24,《夷情要览》,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527页。 (14)王命璿修,黄淳纂:《新会县志》卷4,《列传·陶三广公传》,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15)欧阳保等修纂:《雷州府志》卷1,《舆图志》,第17页。 (16)黄佐:《广东通志》卷63,《列传二十·列女》,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第1658页。 (17)张廷玉等:《明史》卷301,《列传第一百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702页。 (18)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2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汤开建:《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9)林星章修,黄培芳等纂:《新会县志》卷13,《事略》,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刻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381页。 (20)黄佐:《广东通志》卷63,《列传二十·列女》,第1658页。 (21)欧阳保等修纂:《雷州府志》卷19,《贞女志》,第274页。 (22)王命璿修,黄淳纂:《新会县志》卷6,《陵墓》,第299页。 (23)欧阳保等修纂:《雷州府志》卷19,《贞女志》,第274页。 (24)王命璿修,黄淳纂:《新会县志》卷5,《人物传·贞烈传》,第254页。 (25)梁方仲:《明代赋税制度》,《梁方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53页。 (26)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5、42页。 (27)郑俊修,宋绍启纂:《海康县志》上卷,《地里志》,第23页。 (28)刘邦柄修,陈昌齐纂:《海康县志》卷1,《疆域志·山川》,嘉庆十七年(1812年)刻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2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人语·蛋家贼》,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页。 (30)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1)参见冯彬:《庄节妇传》,载许衍董:《广东文征》第3册,第74页。 (32)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313卷,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第7页。 (33)参见冯彬:《庄节妇传》,载许衍董:《广东文征》第3册,第74页。 (34)戴璟修,张岳纂:《广东通志初稿》卷15,《烈女》,第301页。 (35)黄佐:《广东通志》卷63,《列传二十·列女》,第1658页。 (36)《明宪宗实录》卷115,成化九年夏四月辛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37)王命璿修,黄淳纂:《新会县志》卷6,《陵墓》,第300页。 (38)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313卷,第7页。 (39)据《明宪宗实录》记载,刘铭、梁狗等谋杀吴金童时,“时江滨民有关道安者,闻金童被缚叫呼,欲趋救之。不果而还。”参见《明宪宗实录》卷115,成化九年夏四月辛巳,第2233页。 (40)《明宪宗实录》卷115,成化九年夏四月辛巳。 (41)黄佐:《广东通志》卷63,《列传二十·列女》,第1658页。 (42)《明宪宗实录》卷115,成化九年夏四月辛巳。 (43)欧阳保等修纂:《雷州府志》卷19,《贞女志》,第274页。 (44)参阅拙文:《明代祭奠宋亡的活动:以崖山祠庙建设为中心》,刘正刚主编:《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18辑,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 (45)此二首诗在《白沙子》卷7《五言律诗》(四部丛刊三编景明嘉靖刻本)及所有方志均无写作年月。据清阮榕龄编《编次白沙先生年谱》卷1(咸丰元年新会阮氏梦菊堂刻本)记载为成化六年。 (46)参见欧阳保等修纂:《雷州府志》卷19,《贞女志》,第275页。 (47)陈献章:《陈白沙集》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 (48)王命璿修,黄淳纂:《新会县志》卷6,《陵墓》,第300页。 (49)汪森辑,黄盛陆等校点:《粤西文载校点》5卷69,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0页。 (50)戴璟修,张岳纂:《广东通志初稿》卷15,《烈女》,第301页。 (51)薛应旂:《宪章录》卷34,《续修四库全书》第3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2页。 (52)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47(天启刻本)中说,陆瑜为刑部尚书十五年,“明习法令”。 (53)费丝言:《由规范到典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变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9-163、91-101页。 (54)冯梦龙纂,陈煜奎校点:《寿宁待志》卷下,《劝诫·节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55)黄佐:《广东通志》卷63,《列传二十·列女》,第1658页。 (56)《明宪宗实录》卷115,成化九年夏四月辛巳。 (57)黄佐:《广东通志》卷63,《列传二十·列女》,第1658页。 (58)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31,《墓志铭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册,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237-238页。 (59)刘正刚、乔玉红:《“贞女遗芳”与明清广东仕宦塑造的女性形象》,《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 (60)参见许衍董:《广东文征》第3册,第74页。 (61)黄佐:《广东通志》卷63,《列传二十·列女》,第1658页。 (62)欧阳保等修纂:《雷州府志》卷19,《贞女志》,第275页。 (63)戴璟修,张岳纂:《广东通志初稿》卷38,《宫室》,第629页。 (64)欧阳保等修纂:《雷州府志》卷8,《建置志·坊表》,第97页。 (65)欧阳保等修纂:《雷州府志》卷19,《贞女志》,第275页。 (66)阮元修,陈昌齐等纂:《广东通志》卷252,《宦绩录》,道光二年(1822)刻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4047页。 (67)欧阳保等修纂:《雷州府志》卷6,《秩官志》,第63页。 (68)刘邦柄修,陈昌齐纂:《海康县志》卷2,《建置志》,第181页。 (69)戴璟修,张岳纂:《广东通志初稿》卷38,《陵墓》,第632页。 (70)王命璿修,黄淳纂:《新会县志》卷6,《陵墓》,第300页。 (71)邓迁修,黄佐纂:《香山县志》卷6,《列女》,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94页。 (72)王植修:《新会县志》卷3,《建置志》,乾隆六年(1741年)刻本,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00-101页。 (73)林星章修,黄培芳等纂:《新会县志》卷8,《人物志》,第222页。 (74)林星章修,黄培芳等纂:《新会县志》卷11,《艺文志》收录《四礼仪式》,第323页。 (75)陈献章:《陈献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2页。 (76)林星章修,黄培芳等纂:《新会县志》卷7,《冢墓》,第196-197页。 (77)林星章修,黄培芳等纂:《新会县志》卷10,《列女》,第274页。 (78)阮榕龄编:《编次白沙先生年谱》卷2,咸丰元年新会阮氏梦菊堂刻本,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88页。 (79)林星章修,黄培芳等纂:《新会县志》卷7,《冢墓》,第196页。 (80)翁方纲:《粤东金石略》卷1,《陈白沙吊庄节妇墓诗碑》,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9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1页。 (81)林星章修,黄培芳等纂:《新会县志》卷12,《金石》,第355页。 (82)王植修:《新会县志》卷3,《建置志·陵墓》,第101页。 (83)刘正刚:《明代方志书写烈女抗暴“言论”模式探析》,《暨南学报》,2014年第2期。 (84)费丝言:《由规范到典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第157页。 (85)[香港]科大卫著,卜永坚译:《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62页。 (86)[美]凯瑟琳·卡利兹著,蒲隆、杨士虎译:《欲望、危险、身体——中国明末女德故事》,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