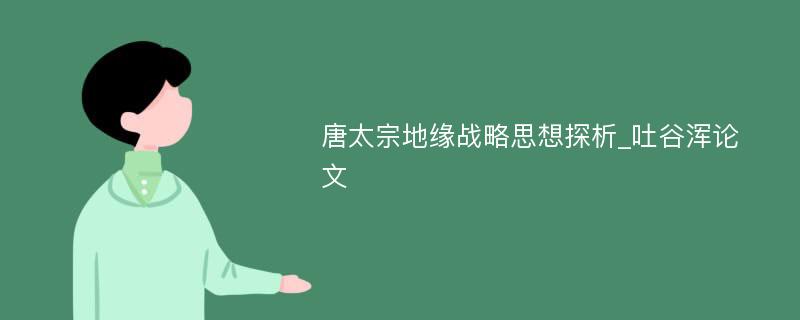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探析论文,太宗论文,战略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文治武功均臻于极致。唐太宗在长期的军事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其中即包括值得后人借鉴和总结的地缘战略思想。
所谓地缘战略,是从战略的高度研究地理环境对战略的影响,从而利用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方略。地缘战略思想则是关于地缘战略问题的理性认识。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唐太宗关于地缘战略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唐太宗利用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唐王朝利益的战略思想。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中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现代的独具特色的思想内容。
唐太宗在位期间国土广大,边界线绵延曲折,地缘形势复杂,并随时间推移而发展变化。历观这一时期唐与周边所发生的诸多地缘关系,既有与唐军事利益攸关的,也有与唐政治、外交利益攸关的,还有与唐经济利益攸关的,更多的则是几种利益兼而有之,错综复杂。唐太宗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与北方突厥、西面吐蕃、西北高昌及西域诸国、东北高丽、新罗、百济等国之间的关系。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正是在处理与周边地缘关系的实践过程中逐步产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具有他个人的独有特色,两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贯穿于他的地缘战略思想的始终。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积极进取。这是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的最显著的特色,也是其思想中最成功、最可取的地方。唐太宗的雄大豪迈是历代许多帝王所不可比拟的,这也是他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二是灵活应对。唐太宗在重大变故面前不惊慌失措,他能够依据客观形势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较大程度地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三是冷静务实。唐太宗鉴于隋亡教训,努力克服以往帝王急功近利、穷兵黩武的缺陷,注意结合现实需要,量力而行,在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推行务实政策。四是措置有序。无论是北击突厥,还是西平高昌,尤其是经略西域,都是先急后缓、由近及远,有条理、有次序地进行,从中亦可见唐太宗地缘战略决策之成熟。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其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业绩斐然。史载:“(贞观十四年)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注:《资治通鉴》第195卷,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九月条。 )唐太宗的突出成就正在于他以超越前人的英武雄迈之气魄,重新开拓了中华民族的疆土,为后来中国版图的确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这一辉煌业绩的获得,是与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密切不可分的。即使今天看来,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里面也不乏可取之处。
探讨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无疑会加深对唐太宗军事思想的认识,对今天的军事思想研究同样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包含丰富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着眼于争夺关中、巩固“中国”的固本思想。其中居重驭轻的关中本位思想,乃是唐太宗成就帝业的“根本”,也是其地缘战略思想的出发点。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建国的历史,大凡起兵争取天下者,都必须熟谙天下山川形势,确定战略方向。一旦丧失地利,则可能招致无可挽回的损失。唐太宗能够夺取天下,先得地利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唐太宗在起事之前即对天下大势明了于胸,对关中(今河南灵宝县及其以西、陕西关中盆地和丹江流域)的地缘战略地位始终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看到了它在军事上的特殊而重要的地缘价值。起事之后,他积极进取关中,使它成为统一天下的巩固的根据地;登基即位后又致力于关中建设,使其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唐太宗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始终注意抓住“根”、“本”,在太原起事、入据关中的过程中,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太宗即位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深根固本的思想。从唐太宗的一系列言论及其实践来看,他的固本思想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笼统到透彻,从模糊到明了,显示出唐太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渐趋成熟。正因为他的这一固本思想,才使唐朝在当时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下进退从容,攻守有方,措置裕如,这不可不谓唐太宗眼光之深远。
关中本位思想是唐太宗一个重要的地缘战略思想,也是其固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地缘背景,既受到传统地缘战略的影响,也与当时的地缘形势密切相关。
关中地区四周山水拱卫,群山环绕,地形完固,自古即被称为“四塞之国”。其南有挺拔巍峨的秦岭,西有峰峦起伏的陇山,北为梁山,东有黄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渭河及其支流流经八百里秦川,平原上土地肥沃,河渠纵横,物产丰富,自古有陆海之称,为我国古代开发较早的文明地区。丰厚的经济物产和内部完固的山河大势,使关中成为经济和军事上的必争之地。
就关中的对外交通而言,它恰好处于中枢地带。长安犹如轴心,呈扇状向四周辐射出去。关中的东面为华北平原;南经栈道与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相通;西拥陇东,与河西走廊相接,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东南沿汉水盆地入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关中地区的政权可利用南面的巴蜀之饶、北面西面的胡马之利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与东面华北平原的政权对抗。
唐太宗首先看中了关中险要的地理位置与便利的交通条件。从地略上讲,它北托长城,西依陇右,东阻潼关,南靠秦岭,易守难攻,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开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的直接威胁和关东军事力量的进攻;其次关中地区受战争破坏较小,人力、物力资源较丰富;再次从人事关系上讲,李渊出自关陇贵族,关中亲属故旧较多,容易得到支持。这些因素为唐太宗形成关中本位思想提供了客观依据。
唐太宗关中本位思想在军事力量设置上有较明显的体现。从当时折冲府的地区分布特点,可清楚地看出其所采取的重首轻足的方略,即重关中而轻四方,当然这里的“重”与“轻”是相对而言的。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因山川形便,将全国分为十道。贞观十年(636年),确立军府的专名为折冲府。折冲府在全国的分布极不平衡,这种地区分布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太宗应付当时军事斗争的地缘战略构想。
从当时军府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折冲府的设置首在保障关中。折冲府很大部分分布于京城附近,其中关内道(今陕西秦岭以北、甘肃祖厉河流域、宁夏贺兰山以东和内蒙古阴山狼山以南地区,治所在今陕西西安)所拥有的折冲府占折冲府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关中成为府兵最为集中的地区,这就是所谓“重首轻足”、“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注:陆贽《陆宣公奏议》第11卷,《论关中事宜状》。)。当然,这里还要考虑到人口因素。因为折冲府是府兵制,依人口密度而设置。关中在隋末战祸小,从而成为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以关中为中心的府兵配置,是因地制宜的固本地缘战略。
由上观之,太宗“深根固本,治安中国”之思想,既有传统政策沿袭之因素,又有出于当时初唐政治、经济背景考虑之因素,特别是对地缘因素的考虑,为巩固政权、密切中外关系、发展经济进而增强国力而不得不为之。
(二)以夷制夷、保藩固圉的地缘藩屏思想,主要体现在以“怀辑”政策绥纳归附民族,并将其内徙安置在唐周边地区的一系列行为上,从而达到令其“世作藩屏”的目的。
这里的地缘藩屏,系指与唐边境直接发生关系的周边民族政权中充当唐王朝藩屏角色的那一类。考察这一藩屏之由来,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夷狄内属,并为唐州县,充作藩屏,如 突厥等;二是唐对周边民族政权抚顺伐叛,扶植亲唐势力,作为唐周边缓冲地带,如吐谷浑等。唐太宗对周边民族政权的处置,基本上还是成功的,至少在当时已经收到了一定成效。唐太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让“外夷”甘作大唐江山的藩屏。突厥李思摩(后被册为俟利苾可汗)帅部落建牙于故定襄城后奏言:“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徙家属入长城。”(注:《资治通鉴》第 196卷,唐太宗贞观十五年正月条。)后一句话表明李思摩深知自身使命,所谓“守吠北门”,即可视为其向唐廷表忠,也实属当时无奈之举。
唐太宗的地缘藩屏思想主要有如下两个内容:
1、置内属少数民族政权于周边,以作藩屏。贞观四年, 李靖率唐军击灭东突厥,生擒颉利,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仍然有十万人。就如何安置突厥降户,太宗曾召集朝臣廷议突厥处置问题。当时群臣展开激烈争论,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①大多数朝臣主张将突厥降众迁至河南兖(今山东兖州)、豫(今河南汝南县)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注:《资治通鉴》第193卷,唐太宗贞观四年四月条。)。 ②温彦博否定了前一种意见,“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注:《资治通鉴》第 193卷,唐太宗贞观四年四月条。)。③颜师古、窦静、李百药等主张降户须居住河北,“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注:《资治通鉴》第193卷, 唐太宗贞观四年四月条。)。④魏征独言突厥世为寇盗,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不能将其置于内地,尤其不可让他居处河南,“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地”(注:《旧唐书》第194卷,《突厥传》。)。 最后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对突厥降户采取怀辑政策,即将这些离开其聚落故地、款塞内附的降部徙之于临界内地的河南、朔方(治所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之境,实际上成了唐北方的屏障。
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史称“于时务在怀辑”,但更根本的在于温彦博的“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这番话打动了他。这番话充分考虑了地缘因素在巩固唐边疆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将突厥降众徙于内地或边州安置,从此成为唐朝绥纳归附民族的一项重要政策(注:参见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所收林立平《隋唐的边疆政策》一文。)。后又有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等各率其部落来降。唐太宗均用内徙方式安置他们,其地缘考虑与前相同。
2、在唐周边地区扶植亲唐政权,以作藩屏。吐谷浑位于唐西南、 青藏高原东北一带。史载:“吐谷浑,其先居于徙河之清山,属晋乱,始度陇,止于甘松之南,洮北之西,南极白兰,数千里。”(注:《旧唐书》第198卷,《吐谷浑传》。)随着吐谷浑渐趋强大, 多次侵入河西走廊,构成对唐边境安全的极大威胁。由于吐谷浑主要聚居于青海沿岸附近地区,与唐边界接壤,故凉州(今甘肃武威)、兰州(今甘肃皋兰)、岷州(今甘肃岷县)、鄯州(今青海乐都)等地常被其侵扰。唐为保障陇右之地及河西通西域之道的安全,对吐谷浑或者以和亲实行羁縻,或者质其子以求控制;和亲、质子无效则出兵征讨之。
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诏唐军征讨吐谷浑,大获全胜, 随后拥立亲唐朝的慕容顺为可汗。同时,唐太宗担心他“不能静其国”(注:《旧唐书》第198卷,《吐谷浑传》。), 乃遣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之声援。唐太宗之所以要在征服吐谷浑之后扶植一个亲唐派执政的政权,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解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二是仍让归附的吐谷浑居其故地,作为唐西南边境的屏障。其最终目的,无非是籍此以解决整个西南的边境安全问题。当然,随着后来吐蕃的迅速崛起和壮大,吐谷浑不足以抵挡来自吐蕃的进攻,这样一来,吐谷浑也就不能胜任唐西南藩屏之使命了。
(三)纵横捭阖的地缘制衡思想。其主要内容有:①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如联薛延陀制突厥。②扶弱抑强,保持地区势力均衡,如联新罗攻高丽、百济以及联合铁勒诸部扼制薛延陀。③联近抗远,服近慑远,稳定近邻以攻击或威慑远方政权,如联合吐谷浑以对付吐蕃。④另外,唐太宗还有针对某一特定政权内部制定的制衡思想,旨在分化瓦解其势力,造成内部争权夺利,削弱统治实力,这尤其体现在对薛延陀的问题上。
唐自立国以来就处在四夷的包围之中:北有东突厥,西北有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县)、西突厥,西有吐谷浑、吐蕃,西南有南诏,东北有契丹、奚、高丽等。如何巩固新生的大唐政权,如何对广土众民实施有效的统治,始终困扰着唐太宗。在与周边民族政权的政治、外交、经济交往及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唐太宗找到一条“驭夷之道”,即灵活选择战略盟友,对远近政权实行地缘上的互相牵制,以收平衡地区势力、稳定地区安全之效。
唐太宗实行地缘制衡的策略思想及其基本情况大致有如下几种:
1、远交近攻,拉拢与孤立并用——唐与东突厥、 薛廷陀的地缘制衡关系。贞观初年,唐北方的主要威胁来自突厥,此外还有铁勒。史载:“铁勒,本匈奴别种。自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分散,众渐寡弱。”(注:《旧唐书》第199卷,下《铁勒传》。)铁勒诸部一度称臣于突厥。 到贞观二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时正“遇颉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属反攻颉利,大破之。于是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注:《旧唐书》第199卷,下《铁勒传》。)。是时, 唐太宗看到了北方这两支力量的此消彼长,决计采取远交近攻之策略,拉拢薛延陀以孤立突厥,借薛延陀之力在北面牵制东突厥,为唐军攻打东突厥起战略钳制配合作用(注:参见胡如雷《李世民传·六》。)。史载:“时太宗方图颉利,遣济南将军乔师望从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注:《旧唐书》第199卷,下《铁勒传》。)次年又遣使入贡,颉利可汗因此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注:《资治通鉴》第193卷,唐太宗贞观三年八月条。)。 由此可见唐太宗这一远交近攻策略对突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扶弱抑强,保持地区均势。为维持地区力量平衡, 保持和平友好之现状,唐在必要之时讨伐欲图割据称雄、野心膨胀的地区强权势力。这一思想与其它思想均有所不同。它强调借力打力,“以夷制夷”,唐廷并不公开出面扮演角色,仅在幕后操纵而已;如方法得当,措置适宜,则能费力小而收效大,显示其特有的优势。
现在就来考察一下唐太宗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做法及其指导思想:
①联众弱而制一强——唐与薛延陀及铁勒余部、东北诸族的地缘制衡关系
贞观四年唐灭东突厥后,北方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原置于颉利可汗统治下的薛延陀取代了过去突厥的地位,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薛延陀的坐大根源于唐太宗的扶植政策,即大力扶持薛延陀以制东突厥。孰料去了一突厥,又来一薛延陀,令太宗大为伤神。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乘唐平突厥、朔塞空虚之际,“率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慰犍山北,独逻河之南,在京师北三千三百里,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注:《旧唐书》第199卷,下《铁勒传》。)。 为此,唐太宗在“(贞观)十二年,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注:《旧唐书》第199卷,下《铁勒传》。)
唐太宗巧妙地利用了薛延陀的内乱及铁勒内部的混乱,乘势取之。史载:“朝议恐其为碛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与九姓敕勒共图之。”(注:《资治通鉴》第198卷,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六月条。 )唐太宗这时出于地缘安全考虑,“恐其为碛北之患”,因此采取与九性敕勒联合的战略,达到了联众弱而图一强的目的。联系之前及之后的军事行动,可知太宗迅速击破薛延陀,乃是希图彻底解决北方战事,为后复讨伐高丽保证侧翼安全,免除后顾之忧,从而使唐避免两面作战的不利处境。
②扶一弱而抑多强——唐与高丽、百济、新罗的地缘制衡关系
唐太宗奉行“扶弱抑强”的地缘政策,这既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又有地缘背景上的考虑。
首先从地缘位置来看,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唐不接壤;从距离上讲,是三国中离唐最遥远的,其北面是高丽,西面是百济。唐之所以扶植新罗,正因为新罗居于高丽、百济的侧背。新罗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高丽、百济的一种牵制。即使新罗暂无力量发动进攻,终究是高丽、百济的后顾之忧。正因有了新罗这一盟友,才使得高丽、百济有所顾忌,不敢倾其全力、明目张胆地出兵攻唐。百济视新罗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便有了百济对新罗的战争。
其次从历史上考察唐与三国间的关系,在贞观十八年底(644 年)太宗亲征高丽之前,唐与高丽、百济、新罗基本上是友好往来,没有兵戈相见。唐与三国之间的关系是因高丽、百济与新罗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的关系向来就错综复杂,非常微妙。《旧唐书》载:“(百济)因讼高丽闭其道路,不许来通中国,诏遣朱子奢往和之。又相与新罗世为仇敌,数相侵伐。”(注:《旧唐书》第199卷,上《百济传》。)可见三国之间是勾心斗角的, 尤其是百济与新罗积怨甚久。在唐太宗前期,主要是百济进攻新罗,新罗频频遣使向唐告急;太宗后期,百济、高丽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又处于危险境地。唐王朝派大军支援新罗。这种三国内讧的局面为唐势力的介入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路途遥远,且气候与中国有异,不便直接出兵统辖,于是唐太宗改取怀辑政策。
新罗不仅与百济世为仇敌,而且与高丽也向来不和。史载:“(唐太宗)又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斋玺书往说谕高丽,令勿攻新罗。盖苏文谓玄奖曰:‘高丽、新罗,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罗乘衅夺高丽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罗皆据有之。自非反地还城,此兵恐未能已。’玄奖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苏文竟不从。”(注:《旧唐书》第199卷,上《高丽传》。)
以上史实表明,愈到太宗晚期,朝鲜半岛的形势愈是险恶,也愈不利于唐对三国实行地缘制衡。因为百济不仅袭占新罗城池,导致唐之藩臣——新罗岌岌可危;而且百济干脆断绝了对唐的朝贡。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若再袖手旁观,任由事态发展下去,唐太宗苦心经营的宗藩体系在这里有可能遭到瓦解。在此情势之下,唐太宗决定出兵,首先打击毗邻唐朝且势力强大的高丽,其着眼点正在于抑强扶弱,以保持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均衡,便于唐控制该地区局势。
3、联近抗远,服近慑远——唐与吐谷浑、吐蕃的地缘制衡关系。唐太宗平定吐谷浑后,在其国扶持亲唐派建立政权,牢牢控制了吐谷浑。籍此唐可保障丝绸之路通畅,打开唐朝与西方联系的通道。当此时,吐蕃日渐强大。据《资治通鉴》载:“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世浸强,蚕食它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其王称赞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论,宦族皆曰尚。弃宗弄赞有勇略,四邻畏之。上遣使者冯德遐往慰抚之。”(注:《资治通鉴》第194卷, 唐太宗贞观八年十一月条。)但后来吐蕃与吐谷浑关系交恶。
在此种情形下,唐太宗全力支持吐谷浑,不仅因吐谷浑已完全置于唐控制之中,而且在地缘位置上吐谷浑处于唐与吐蕃之间,吐谷浑之得失对于唐实在是至关重要,否则唐太宗联近抗远、服近慑远之打算将落空。正由于此,唐太宗对吐藩之侵扰实行坚决反击方针,“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督步骑五万击之”(注:《资治通鉴》第195卷,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八月条。)。最后,唐军大败吐蕃, “弄赞惧,引兵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上许之”(注:《资治通鉴》第195卷,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九月条。)。
值得肯定的是,唐廷与吐蕃因文成公主和亲而建立起密切的地缘关系,尽管这一关系持续时间并不太长,并且双方各有自己的打算,但在当时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这是唐太宗在处理国家与民族间地缘关系上的一个较成功的事例。贞观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出使天竺,天竺诸国都遣使奉送贡品,但为中天竺所掠,王玄策被打败,逃到吐蕃境内请求军事援助。松赞干布发精兵一千二百人,归王玄策指挥,一举击败中天竺军,喜讯传来,松赞干布“遣使来献捷”(注:《旧唐书》第196卷,《吐蕃传》。)。
唐、吐谷浑、吐蕃的关系趋于正常化,这正是太宗联近抗远、服近慑远之地缘制衡策略获得成功的生动而有力的证明。
综上所述,可知唐太宗的地缘制衡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持唐周边地区的势力均衡,不容许出现任何一个足以威胁唐政权的势力集团。其途径是:对各少数民族实行分化,扶持弱小方,牵制强大方;一旦某一势力日益坐大,打破地区势力均衡之时,即予抑制。这是唐太宗一个重要的地缘思想。
(四)隔断南北、积极进取的地缘隔绝思想。这里所涉及到的平高昌、定西域、设四镇等一系列军事活动,犹如一根链条上的铁环,一环扣一环,既相独立,又相关联,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其中至关重要的则是设置四镇。安西四镇恰好处于西域的中枢地带,又是唐、吐蕃、西突厥三方力量的交汇处。控制了四镇,则控制了西域;控制了西域,则隔绝了吐蕃与西突厥的联系,阻止了南北夹击唐朝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唐太宗自然不得不严控四镇,倾其全力来经营西域。
西域地处中西要道,北接强大的游牧部落,南邻青藏高原,地缘位置非常重要。早在西汉时期,为抗击匈奴,汉王朝执行“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大力经营西域。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区。西汉末年,汉王朝无暇西顾,匈奴卷土重来,至东汉初年,匈奴完全控制了西域。他们屡寇边境,攻掠河西,使得河西诸郡城门为之昼闭。西域俨然成为匈奴南侵汉朝的后方基地。若想保住河西,则非得控制西域不可。西域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地缘战略地区。
唐太宗在位期间,西域面临着来自南面吐蕃、北南西突厥的威胁。
唐太宗非常重视经略西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着眼于切断吐蕃与西突厥的联系,改变唐在西域被动的地缘态势,为最终牢固控制西域创造条件。值得指出的是,唐以伊吾地为西伊州,后来成为唐太宗进图西域的前进基地。贞观初年以来直到十三年唐出兵攻打高昌的这段时间内,西域数国与唐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唐太宗采取和平地缘方式与西域诸国交好,使他们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保持均衡现状。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唐与高昌之间却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利益上的分歧,最终导致双方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唐与高昌之间的冲突还牵涉到另一支不可忽视的西域力量——西突厥。要想继续贯彻唐太宗的地缘制衡战略,就非得先平定高昌、征服西突厥不可,否则西域诸小国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也势必影响唐对西域的控制。不平定高昌,则无法打开西域之门;不征服西域,则无法隔绝西突厥与吐蕃的联系,当然更无法将唐势力推进到中亚地区。
1、唐太宗平高昌的地缘考虑
高昌地处河西走廊与西域交接处,控西域出入中原之要道,“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涂经高昌。”(注:《旧唐书》第198卷, 《高昌传》。)如果从军事地缘上看,高昌是西域通向中原的必经之路,是联系西域与中原的纽带。高昌失则河西危,河西失则关中危!此种利害关系对于熟悉边情且当初曾领兵平定陇右、统一西北的唐太宗来说,当是再明白不过的。
唐征讨高昌的直接起因是高昌为贪图私利而控扼道路,进而影响西域各国向大唐朝贡。根据史书记载,可将唐出兵理由归为五点,也即高昌在以下五个方面触犯了唐王朝的利益:①遏绝西域朝贡;②与西突厥联合攻打伊吾等小国;③蔽匿奔高昌之中国人;④朝贡脱略;⑤无藩臣礼(注:参见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八册。)。这些都严重动摇了唐对西域的统治,也损害了唐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声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维持西域势力之均势,保证唐对西域的有效控制,攻打高昌,势所难免。
唐太宗出兵攻打高昌,也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随着唐朝国势强盛,国威远扬,唐王朝的商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并向周边延伸。隋时对西域之商业,以张掖为中心,长安、洛阳为总汇。唐时以武威为中心,据严耕望在《中国历史地理》唐代篇云:“凉州西控西域,北控回纥,南控吐蕃,为自陇以西之军政重镇。而其时安西入西域道之交通又极发达,凉处要冲复为回鹘、吐蕃贸易之所,故形成一大商业中心,元宵之夜,灯树万点,赛于长安,其盛可知,度其繁盛,恐仅次于荆、扬,而在幽、广之上。”由此看来,唐太宗经营西域,虽说是为了远扬国威、慑服西夷,同时也有向周边开展商业活动的考虑。
唐讨伐高昌,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屡屡跟唐对立的西突厥与高昌结成盟国,不仅共同遏绝往来西域的商贾行李,而且攻打内属唐朝的西域小国。史载:“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注:参见《资治通鉴》第195卷,唐太宗贞观十三年二月条。 )西突厥是远比高昌更可怕的潜在对手,其与高昌结盟,更增加了西域地区的不稳定性。为最后打击西突厥计,首先需断其右臂、除其盟友高昌,而后向前推进,俟时机成熟,剪灭西突厥。
2、唐太宗统一西域并设安西四镇的地缘考虑
唐太宗经营西域的关键在于设置安西四镇。四镇的置废于西域关系极大,而统一西域则是前提。只有在西域建立巩固的政权,才能有效地对付西突厥与吐蕃,才能确保河西的安全,从而维护唐王朝的稳定与统一。
唐太宗统一并经营西域可分为三部分:①平定焉耆;②统一龟兹;③设置四镇。其实质则是与强大的吐蕃和西突厥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唐太宗一旦得手,则不仅能够阻绝“南羌北交”之势,而且可将唐朝势力向西推进到中亚地区,进一步扩大唐帝国的影响,伸展其势力范围。唐与西突厥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贞观十六年九月,唐太宗欲经营西域,以凉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镇抚高昌,并图龟兹,以经营西域诸国。
史载:“焉耆国,在京师西四千三百里,东接高昌,西邻龟兹,即汉时故地。”(注:《旧唐书》第198卷,《焉耆传》。)贞观初年,焉耆一度与唐友好,后被西突厥拉拢,结成姻亲,“由是相为唇齿,朝贡遂阙”(注:《旧唐书》第198卷,《焉耆传》。)。 “相为唇齿”说明西突厥与焉耆结成密切的地缘关系,有着共同的利害认识,遂成唇齿相依之势。贞观十八年九月,郭孝恪率部夜袭焉耆王庭,生俘其王。平定焉耆是唐太宗统一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贞观二十年(646年), “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注:《资治通鉴》第198 卷,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六月条。)唐太宗借西突厥阿汗求婚一事,不失时机地使其割让西域五国予唐,实质上可视之为唐与西突厥对西域地缘主导权争夺的胜利。从一个侧面看出太宗对西域地缘位置的重要性有着较清醒的认识。自唐平定焉耆之后,西突厥加紧控制龟兹。唐太宗为进一步打击西突厥并统一西域,遣阿史那社尔等将率部进讨龟兹,生擒龟兹王。
唐太宗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虽未直接与西突厥交锋,然而次第平定高昌、焉耆、龟兹,犹如断其双臂,从而遏制了西突厥南进势头,消除了北方对西域的威胁(注:参见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之后,唐太宗在西域设置四镇。《新唐书》卷221 上《龟兹传》载:“(阿史那)社尔执诃黎布失毕、那利、羯猎颠献太庙,帝受俘紫微殿,拜布失毕左武卫中郎将。始徙安西都护府于其都,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安西四镇的职责在于“抚宁西域”,而要达此目的,须北防西突厥之南侵,南防吐蕃之北犯,更重要的是切断吐蕃与西突厥的联结,以免四镇受到南北夹击(注:注:安西四镇正式设置时间应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而非贞观二十二年; 参见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唐代前期安西都护府及四镇研究》。)。安西四镇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唐太宗主动经营西域的战略意图。
还有一点需在此指出,即唐太宗较好地选择了进取西域的时机。贞观后期,吐蕃虽逐渐强大,但还无力进攻以龟兹为中心的天山以南地区;在天山以北的西突厥,因内部不统一,力量互相削弱,不能向南发展。这一时机对唐是有利的。因此从贞观十四年(640年)到二十二年(648年)的八年期间,太宗把唐帝国的军事政治力量牢固地安置在西州地区,并发展到天山以南的龟兹地区,设置四镇,初步控制了西域(注:参见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唐代前期安西都护府及四镇研究》。)。唐太宗经营西域之能取得如此成功,很大程度须归因于此。
贞观后期,唐太宗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西北,全力经营西域。从灭高昌,设西州、庭州及安西都护府,到伐焉耆、征龟兹及南迁安西都护府,基本上都是他自定的,甚至是力排众议的决定。由此不仅说明太宗对西域的特殊关注,更表明其对经营西域深思熟虑,当有通盘考虑。
分析唐太宗设四镇以经营西域的地缘决策,必须将其与在此之前的积极经营河西、灭高昌设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南迁龟兹等一系列军事活动联系起来考察,而绝非一个个互不关联的孤立的事件,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若要打个比喻,如果说关中是唐的首脑的话,那么河西地区是狭长的臂膀,安西四镇则是伸出去的手掌。尽管安西四镇远离唐统治中心,但通过河西依然忠实地贯彻着唐统治者的意图,置于唐太宗的绝对统治之下。唐朝廷在这里仍然享有极高的威望。
安西四镇的设置是由当时的客观形势和西域独特的地理位置综合造成的。唐太宗于贞观四年和贞观九年分别解除了北方东突厥和西南吐谷浑的威胁以后,开始将目光投向西北。贞观十四年,“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注:参见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唐代前期安西都护府及四镇研究》。)。安西都护府的设置是唐太宗经营西域政策的重要内容。尽管当时唐太宗还未控制西域,但在河西走廊与天山及西域地区的交接处——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并有为以后全面统辖西域预作行政组织准备之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至龟兹,始设四镇。 当时的西域形势是:南方的吐蕃已经崛起为一支力量强大、屡犯唐边境的高原民族政权,北方的西突厥虽遭挫折,但其力量仍不可小视。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安西四镇成为唐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四镇恰处于西域的中枢地带,又是唐、吐蕃、西突厥三方力量的交汇处。控制了四镇,则控制了西域;控制了西域,则隔绝了吐蕃与西突厥的联系,阻止了南北夹击唐朝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唐太宗自然不得不严控四镇,倾其全力来经营西域。
王永兴先生曾经指出,唐代经营西域的方针策略,多为太宗所制定:以凉州为经营西域的总部,以西州为前沿根据地,以在龟兹的安西都护府为前方指挥机构。从凉州进至西州,从西州沿银山道经焉耆进至龟兹,形成自经营西域的总部到前方指挥机构的大动脉(注:参见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论唐代前期北庭节度》。)。这一席话可谓道中要害,虽然不能说这时唐太宗对西域的经营很完善,但至少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为奠定了西北军事的基本格局,也影响了其后统治者的地缘战略决策。
当然,在肯定安西四镇的地缘隔绝作用的同时,绝不能仅局限于西域地区,而应将之与河西地区联系起来考察。河西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西域。如果要想准确理解唐太宗的地缘隔绝思想,无疑应当既研究安西四镇,更不可忽视河西。史载:“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兹、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注:《资治通鉴》第215卷, 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条。)。尽管这是就玄宗时期的节度而言,但其所涉及安西、河西节度之职能也适用于太宗朝安西都护、凉州都督。
综上所述,可用一句话表述西域与内地的地缘关系:守长安必须守河西,守河西必须镇西域。
二
唐太宗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地缘战略思想,并在执行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概而括之,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的积极意义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根据周边地缘态势,灵活制定策略,调整战略方向和重点
从唐太宗的主要军事活动来看,约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自贞观元年至四年,平定东突厥,着力巩固北方;第二时期自贞观五年至九年,主要是征服吐谷浑,安定西部边境;第三时期自贞观十年至十四年,坚决反击吐蕃,平定高昌,尤其重视高昌的地缘战略地位;第四时期自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以西域地区为重点,兼顾北方和东北,平焉耆、征高丽、灭薛延陀,又平龟兹,这是战事频仍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各自地缘战略重点,且每个地缘战略重点都有一定的方位指向性,大体上符合当时斗争的实际需要,并收到一定成效。太宗曾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注:《资治通鉴》第192卷, 唐太宗贞观元年正月条。)此话很能反映他的这一特点。
第一时期的地缘战略的重点是东突厥,其方向来自北方。从地理位置及距离、威胁而言,东突厥的侵扰对唐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直接关系着新生的唐政权的存亡兴替。正因如此,唐高祖、太宗都对东突厥深予关注。其中地缘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时期,吐谷浑成为唐的地缘战略重点。东突厥败后,西面的吐谷浑渐趋强大,多次侵入河西走廊,威胁唐与西域的政治联系与经济交往。贞观六年,“吐谷浑寇兰州,州兵击走之”(注:《资治通鉴》第194卷,唐太宗贞观六年三月条。)。又据《新唐书》卷221上《吐谷浑传》载:“太宗时,伏允遣使者入朝,未还,即寇鄯州。”“有诏止婚,遣中郎将康处真临谕。又掠岷州。”
第三时期,吐蕃与高昌相继成为触犯唐利益的周边政权。唐太宗没有坐视不管,而是恩威兼施,文武并用,或胜而后和,或先礼后兵。这一时期由于高昌阻绝西域诸国与唐的关系,开始成为破坏唐帝国体系的一个地缘障碍。唐太宗果断出兵平定高昌,稳定了西北地缘格局。
第四时期,唐太宗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意欲在有生之年将之纳入唐宗藩体系之中。贞观十九年(645年), 太宗征高丽前曾对侍臣说:“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注:《资治通鉴》第197卷,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条。 )这可视为太宗晚年用兵频仍的重要动机,同时也可看出在这一时期,太宗的地缘战略呈现多方向、多重点的特色。一方面努力经营西域,先后平焉耆、龟兹,一方面先后两次击败薛延陀,将其彻底扫灭;另一方面又东征辽东伐高丽,后贞观二十二年仍然准备讨伐高丽。这一时期的地缘战略既有成功之处,也有许多教训。多个方面出击,兼顾几个战略重点,其效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
2、治内与服外并举,相互为用,因时制宜的地缘战略思想
大凡任何一个王朝,若要长治久安,莫不励精图治,注重内政外交双管齐下。一旦内、外关系处理失调,则危及社稷,有损国家利益。唐太宗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得出了“治安中国,四夷自服”的理性认识,而其卓有成效的服外之举,又有力地促进了内部的发展与稳定。内外兼修,国势昌盛,这正是其超越前人之处。
唐太宗治内与服外思想主要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治内与服外相互为用,高度统一。探讨这一思想,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其中有两点需在此指出:一是唐朝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得到很大的恢复,经济上有显著的起色;二是唐军军力有较大的提高,取得了对梁师都作战的胜利、突利可汗主动入朝并正式出兵对突厥作战。第一点是对内而言,第二点是对外而言,而后一点又是以前一点为基础的。唐王朝国力的壮大为反击侵略、威慑四夷提供了条件。可见,治内与服外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承,高度统一。这种内、外的高度和谐统一,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统一,而且是地缘意义上的统一。
二是治内与服外主次分明,因时制宜。若从内、外关系的角度来观察唐太宗的军事实践活动,大致可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其指导思想是立足内政,力避战事;后一阶段主要是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其指导思想是谋定而后战,修文不偃武。唐太宗非常注意内、外关系的有机结合,但并非不分轻重缓急,而是轻重有别,因时而异。前一阶段以治内为主,先“治安中国”而后威服四夷;后一阶段则侧重于服外,治内次之,尤其是在对外关系中持积极进取精神,不筑长城即为有力说明。史载:“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注:《资治通鉴》第193卷,唐太宗贞观二年九月条。 )后来他又多次有类似言论,如他在贞观十五年曾说:“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注:《资治通鉴》第196卷,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十月条。)由此亦证明唐太宗所采取的是一种带积极性的安边之策,既不放弃武备,示之以弱,也不穷兵黩武,好战成性。正如他自己总结道:“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妄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注:《贞观政要》第9卷,《征伐》。)
唐太宗在安边问题上突破了传统的思路,不拘泥于旧有的地缘范畴的限定,对修筑长城作了一番新的诠释,强调以人为长城,这显然高于一般意义上的以长城为长城,变单纯性的消极防卫为主动性的积极防卫。唐太宗积极进取,不筑长城,内外兼治,正是他深刻理解地缘战略而又不为地缘因素所束缚的生动体现。
3、先急后缓,由近及远,既持重又果敢的全方位地缘战略思想
对于关乎国家利益的众多的战略性矛盾,唐太宗能够有条不紊地按问题的轻重缓急逐个解决。立国之初,最先对唐构成威胁的是东突厥。隋末丧乱,突厥乘势崛起,开始成为中国主要边患。唐初经济凋弊,国力不济,强盛的突厥迫使唐太宗仅以固守幽州、太原、绥州(今陕西绥德)、延州(今陕西延安)、泾州(今甘肃泾州)、灵州、凉州为北方之边防线,更无力反击突厥(注:参见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八册。)。尽管唐还与其它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存有冲突,但轻重缓急之下,显然颉利可汗乃是此时唐太宗首先要对付的敌手。解决东突厥后,唐朝换来几年的和平,国力也蒸蒸日上。吐谷浑、高昌次第成为影响唐太宗实施地缘战略的制约因素。唐太宗果敢出兵,迅速平灭吐谷浑、高昌,并力排众议,在高昌设州置府,为后来将大唐势力向外推进到西域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前进基地。之后亲征辽东,尽管未能达成预期目标,但遏止了高丽向西蚕食的势头,其影响也是极其深远,为后来高宗取得征高丽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唐初经营西域之步骤,首先以凉州为基地,随后推进到伊州和庭州,由近及远,逐步推进。贞观初李大亮为凉州都督,贞观四年命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安抚西突厥部落散在伊吾者,此即唐开始经营西域。同年,伊吾归附,唐以其地为西伊州,于是唐经营西域又进一步。贞观八年唐征吐谷浑,乃一面求陇右之安全,一面在廓清通西域道路上之障碍。至贞观十四年灭高昌,置西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以凉州都督郭孝恪为都护兼西州刺史,于是唐经营西域之基地又推展到西州。同时唐在天山之北已取得浮图城,以其地为庭州,庭州遂为天山北路经营之基地。贞观二十二年灭龟兹,又将安西都护府移置此地,葱岭以东诸国莫不慑服。于是唐经营西域之目标,此时亦已完全达到目的。然后乃以安西、北庭为基地,长驱直入,远征西突厥。
4、善于用多种策略手段配合地缘战略的实施,以加速扩大其功效
唐太宗善用离间分化及争取盟国、孤立敌人之计,乘其弊而取之。如对突厥,当其势力强盛之时,“倾府库赂以求和”,不轻启战事。待其离乱之势已成,乃从而离间以孤立之,最后方出兵一举将其击灭。具体言之,唐太宗的主要策略有:①贞观元年唐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议亲,以削弱突厥内部势力。②贞观元年十二月,太宗以书谕梁师都,师都不从。于是遣兵就近图之。因为突厥与梁师都互相结盟,攻打梁师都等于断突厥右臂,所以这一举动可视作唐太宗为以后征讨突厥提前作的准备,同时也是向突厥传出了一个信号。③贞观二年(628 年)利用颉利与突利的内部矛盾,拉拢突利可汗。④同年利用薛延陀酋长夷男叛颉利,册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以上均是在征讨颉利之前所实施的非军事辅助策略,对于最终达成战略目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外,唐太宗运用“以夷制夷”策略征伐西实厥,获得极大成功。如利用乙毗射匮、阿史那贺鲁、真珠叶护等,使西突厥内部分裂,利用回纥、东突厥之兵与唐兵联合进攻。他还经常用外夷之大将以攻夷,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等,都建立了赫赫战功,取得良好的效果。
5、从地缘角度并结合实际需要出发的务实政策
唐太宗在处理各类内政外交问题时,具有冷静的现实主义思想,也注重从地缘角度予以分析,作出决策。贞观五年,地处中亚的康国求内附于唐。太宗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倘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注:《资治通鉴》第193卷,唐太宗贞观五年十二月条。)按康国君姓温,本月支氏,始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乃西越葱岭,支庶分王,世称昭武九姓。其地土沃宜禾,出善马,兵强,隋时臣于西突厥,贞观元年曾入贡于唐,此时唐太宗并非不想得到康国,但因为这时唐朝立国不久,国力尚未恢复,加上康国与唐相距遥远,以唐初之国力、军力控制西域尚且不行,又怎么能够“师行万里”“求服远之名”呢?唐太宗拒绝康国内附是一种务实态度,符合当时唐之国情。后来康国在唐高宗时期归附中国,可视为太宗地缘战略的继续。
综上所述,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产生了较大的历史影响。尽管如此,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仍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阶级性质决定了他必然要实行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唐太宗的主观努力和客观历史条件造就了他的较为开明的民族观,但他又未能摆脱历史的束缚,有时甚至认为“戎狄人面兽心”(注:《资治通鉴》第197卷,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六月条。),所有这些也必然会影响并反映到他的地缘战略思想里面。如他曾经说过对少数民族要“抚以恩信”、“不必猜忌异类”(注:《资治通鉴》第197卷,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条。); 但他又往往对其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拜薛延陀真珠可汗之子皆为小可汗,就是显例。凡事都有其两面性。地缘制衡一方面可以造成均势状态,维持暂时的和平,但同时也制造或扩大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或为个别怀有野心的少数民族政权首领所利用,酿成祸乱,尤其是多立可汗,不仅使少数民族政权内部不和,而且往往会发生互相倾轧、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唐太宗之所以特别引人瞩目,在于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战略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他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其积极防卫的思想就成为唐代统治者制定国防政策的一个指导性原则。唐高宗守太宗之成,基本上遵循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取得了东服高丽、西平西突厥的巨大成果,唐朝疆域达到空前广阔的程度。武则天在国防问题上也秉承了太宗遗风。唐玄宗在其统治后期则将太宗积极防卫的国防思想推向极端,走向穷兵黩武,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从此一蹶不振。此后历位皇帝大都仅图内顾,已无力向外发展,但唐太宗的国防思想对宪宗、文宗仍有一定的影响。如唐宪宗即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辣慕不能释卷”(注:《旧唐书》第15卷,《宪宗本纪·史臣曰》。)。宪宗以太宗为标榜,力图有所作为,后来取得了削平藩镇之乱的业绩。
标签:吐谷浑论文; 突厥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西突厥论文; 唐朝新罗战争论文; 唐朝论文; 贞观元年论文; 高丽论文; 旧唐书论文; 李世民论文; 高昌论文; 百济论文; 新罗论文; 关中平原论文; 西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