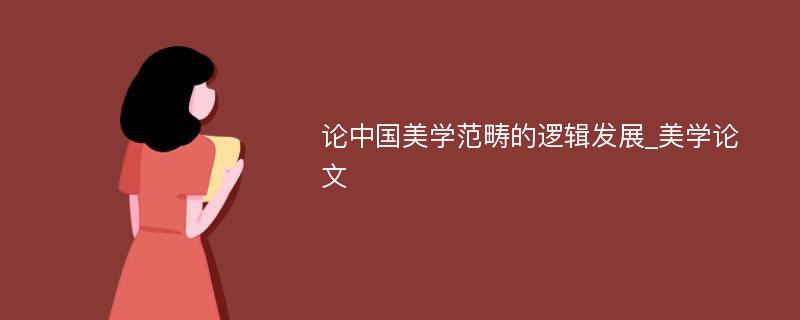
论中国美学范畴的逻辑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范畴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西方古代美学的重视概念、判断、推理和范畴的演绎运动不同,中国古代美学更重视直觉和感悟。严格地说,中国古代美学并没有科学意义上的美学范畴,只是到了近代,自王国维将优美、壮美、喜剧、悲剧作为美学的基本范畴明确提出之后,人们才日益重视美学范畴的研究,并普遍使用美、优美、崇高、丑、悲剧、喜剧等美学范畴。中国美学发展的这一特点,给中国美学研究、尤其是古代美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怎样从错综纷纭的美学现象中把握中国美学的本质规律?我以为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美学范畴的发展逻辑。只有这样,才能从复杂丰富的美学现象中把握主潮,昭示规律,预测未来,达到纲举目张的理想效果。
研究中国美学范畴,首要的问题便是以什么为逻辑起点。按照辩证思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起点必须是最简单最一般的抽象,是事物整体中的一个细胞,包含着事物发展的一切矛盾的胚芽。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美学范畴的逻辑起点乃是广义的美。这是因为,作为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必然与自由、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体,广义美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当它偏于和谐、均衡、稳定、有序时,便构成了狭义的美,包括优美和壮美;当矛盾双方偏于对立、斗争、动荡、无序时,就构成了崇高、丑、悲剧、喜剧等美学范畴。不过,按照辩证思维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美学范畴是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运动中产生的。因此,它不仅是逻辑的范畴,还是历史的范畴。
一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受封闭的自然经济、古典的社会阶级斗争和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美表现出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古典和谐。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以和谐为美的。中国古代依据“执两用中”的朴素辩证思维,强调在矛盾双方中不走极端,相成相济,以取其中。凡合乎这个尺度的,就是和,就是适;凡违背这个标准的,就是过,就是淫,这就是所谓中和之美。“中和”这一美和审美的最高标准,一直影响、制约着中国古典艺术,中国古典艺术中形与神、情与理、意与境的统一,以及戏曲中对大团圆结局的偏好,都是这一审美标准的具体体现。
由于中国古典美学以和谐为审美理想,所以,概而言之,中国古典美学中只有两个基本范畴:优美和壮美,亦即所谓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从优美与壮美这两个范畴产生的时间顺序来看,壮美早于优美。一方面是因为中唐以前思维偏于外向,更关注外部世界和社会生活,艺术则偏于客观写实,这样就出现了更多矛盾、对立、冲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原始崇高性艺术的影响,象《离骚》受楚文化的影响就十分明显。
中国古典美学以和谐为审美理想,强调再现与表现的统一。但总的说来,更偏于表现,又以中唐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偏重壮美和写实,后期偏重优美和写意。先秦两汉时期,受外向型思维的影响,审美关系偏于外向的和谐,强调人统一于对象。《尚书·尧典》中“神人以和”的命题,奠定了以“和”为美的古典美学理想的基本模式。“神人以和”就是指人通过原始的艺术形式“乐”达到与“神”的协调和谐。这里,“神”是古人对不可理解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解释,兼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神”被恢复了本来面目,“神人以和”的美学理想也便合乎逻辑地向两个方向发展:其一表现为儒家的审美理想,注重审美主体与社会的和谐,要求个体统一于社会,情感统一于伦理,造就积极入世的圣贤人格。其二则表现为道家的审美理想,注重审美主体与自然的和谐,要求顺应自然,“无己”、“齐物”,让有限的自我通过与自然合一达到无限的境界。这样,一方面,主体对于外在自然对象、社会群体的服从,使得个性、主观心理的因素极为淡薄;另一方面,由于主体努力追求与外在对象的和谐,体现了主体的力量,表现出积极、亢奋、高昂的壮美风貌,主体内在的力量通过外在的感性对象得以呈现。这种外向和谐反映在艺术形态上,表现出偏重对对象的再现、写实的倾向。无论是楚辞对客观必然和群体价值的推崇,《诗经》冷静理智的写实精神,秦始皇兵马俑的逼真塑造;还是汉大赋、画像、石刻等对于自然对象的感性真实的摹拟,都是如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玄学人格本体论和佛学心理本体论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出现了大的转折。以辩证否定的形式刷新了先秦两汉的主导美学传统,审美理想从人统一于对象的外向和谐,逐步向对象统一于人的内在和谐转化,从外在实践性追求转向内在智慧性自守,审美形态则从外在感性世界的壮美转向内在理性人格的伟大。反映在艺术领域,则是个性价值论和情感表现论的崛起,艺术成为个体协调或摆脱同社会的直接冲突,从而满足和实现自己的独特方式。文论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经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到陆机的“诗缘情”说;画论从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经谢赫标举“气韵生动”导向宗炳的“畅神”说①;书法理想从卫夫人的“多骨微肉”说经王羲之的“骨力”与“圆润”兼备到王僧虔的“骨肉丰润”说。从艺术实践看,诗歌从田园诗到山水诗和“言情”诗,绘画从人物画为主发展到以山水画为尚,书法从以隶楷为主发展为以行草为妙,以及普遍对形式规范和韵味的追求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审美理想正从重形象、重阳刚之壮美逐渐向重心理重神意之优美演变,表现出心对物、情对理的超越。但是,这种超越还不能在主体自身中实现,还没有达到直抒胸臆的程度。它仍然需要返回客体,通过再造和驾驭客体来实现。因此,这一时期的表现论仍未脱离再现论,对优美理想的向往仍包含在实现主体壮美性格的总体系统之中。这一特点又正好体现在刘勰以刚为主,刚柔相济的审美理想之中。
在中国美学史上,唐代是壮美盛极而衰和优美确立的时代。唐前期作为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正处于上升时期,表现出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和敢作敢为的自信精神。另一方面,唐初统治者比较开明的政治经济政策,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国力日益强大。在这样一个繁荣富强的时代,人们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投向社会生活和宏大的物质对象,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因而,审美理想便表现出对六朝美学的扬弃,对秦汉传统的复归,形成了偏重社会生活,偏重阳刚之美的“盛唐气象”。诗论从初唐四杰到陈子昂,书论从虞世南、欧阳询、李世民、孙过庭到张怀,重扬“风骨”旗帜,确立了新的壮美理想。在艺术实践上,盛唐诗人多以“建安风骨”为创作的楷模和审美标准。李白的放声歌唱,以无限的激情冲破了有限的形式,其诗多以七言为主而又常常打破这一格式;杜甫则在有限的形式中开拓着无限的意境,形成雄浑深沉的品格。绘画方面,吴道子的作品笔力劲险,神采飞动;李思训的作品则色彩浓重,金碧辉煌。书法领域,张旭的草书酣畅淋漓,如行云流水;颜真卿的楷书则整肃严正,端壮雄伟。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两种不同风格的壮美。此外,规模宏大的建筑,色彩艳丽的雕塑,热烈壮观的舞蹈等等,都表现出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那种史无前例的壮美风貌。至此,中国古典美学的壮美范畴发展到了它的极至,完成了强(秦汉)——弱(六朝)——强(唐前期)的螺旋结构。
二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发展到巅峰之后,必然会走向反面。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中唐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是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进入后期的转折阶段。社会意识和人的精神状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文化和审美理想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每况愈下的社会形势,文人士大夫大量南渡所带来的北方以刚烈粗犷为主的文化传统与南国纤柔细腻气质的融合,以及禅宗以心为本,心即是佛思想的影响,使得封建社会前期那种朝气勃勃、奋发向上的热情一去不返,代之以剪不断理还乱的重重忧患和顾虑;先前那种对外在物质世界能动的探索与开拓精神,渐渐为受动的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感受和体验所取代;审美活动中那种雄健奔放的阳刚之气,逐渐让位于细腻纤柔、含蓄朦胧的阴柔之韵;艺术中那种再现客体、干预生活的入世追求,不得不让位于表现主体、玩味情致的出世精神。当然,这是一个曲折渐变的过程,古典壮美理想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寻找着新的突破点。韩愈的“物不得其平则鸣”的思想,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受他影响的“险怪派”诗人,将古典壮美理想中的不和谐因素发展到了接近崇高的临界点。但由于缺乏产生崇高的社会土壤,因而不但不会走向崇高,反而导致了壮美自身的瓦解。白居易则用政治、伦理功用吞噬了诗的审美价值,将再现倾向发展到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壮美理想的蜕变和再现倾向的终结。
唐后期是优美得以确立的时期。司空图在皎然标谤“文外之旨”的基础上创“韵味”说。从此,追求“味外之旨”的“韵味”说便逐渐取代了“骨力刚健”的“风骨”论,而李商隐的含蓄朦胧的诗风和温庭筠细腻温柔的词境,则体现出深厚的表现色彩。这一切都标志着古典美学由前期壮美向后期优美的历史性转折。优美与壮美的不同在于,壮美的深沉内涵是主体对客体的渴望和追逐,主体要求在对象界实现自己,但遇到对象的抗拒,产生一定程度的对立和冲突。但这种不和谐最终被主体克服,主体在对对象的把握和占有中显示出刚强的人格和伟大的生命力。由于壮美是在外向性的主客关系结构中呈现出来的,这就规定了壮美的艺术必然是偏于摹拟写实的,即表现统一于再现。优美的深层内涵,乃是主体在内向静守中同对象形成的自由关系,主体不是通过外向的追求来实现同对象的和谐统一,而是在内心的自省,直觉的感悟中达到物我两忘、意境相融的境界,亦即在对对象的超越中达到同对象的统一。优美的这一特点,规定了优美的艺术必然是以表情写意为主,再现统一于表现之中。
宋元至明中叶是古典美学的优美理想不断深化圆熟而走向蜕变的时期。从政治机制上看,对内专制集权,对外保守妥协,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意味着封建地主阶级自信心的萎缩,生命力的衰竭和进取精神的失落,造成了时代性的恐惧不安心理和脆弱感伤性格,导致极为矛盾的社会意识:一方面特别重视伦理纲常对个体的绝对权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个体命运、人性情感的强烈关注。从哲学思潮方面看,宋明理学克服过去的门户之见,将佛、道引入儒学体系,形成外儒内佛,儒佛互补的理论结构,并将前期儒学的“天”演变为“理”和“心”;将儒学以伦理实践行为为重的外向思维定势,转变为主体自省的内向性思维;将客观物象看作表现主体内在世界的自由形式,形成以内为本,以内御外的心理结构。在美学理论上,欧阳修的“会意”说,苏轼的“外枯中膏”论,黄庭坚的“妙心”说,吕本中的“悟入”“说,严羽的“兴趣”说,王若虚的写“真情”说,赫经的“内游”说,方回的治心”说,王世贞的“格调”说等等,都表现出对优美理想的追求和再现与表现统一的前提下对表现写意的偏好。在艺术实践上,首先是宋词取代唐诗,既而元曲代替宋词而崛起。一般说来,“诗庄词媚”,含义阔大的诗境利于表现中唐以前的阳刚之美,细腻精致的词境则便于表现晚唐以降的阴柔之美,这也是宋词取代唐诗的根本原因。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李清照、周邦彦等的词作,都让人感受到寂寞孤独的愁苦。但这种惆怅之情又不使人紧张亢奋,更无压抑之痛,而是和婉温柔,给人以赏心悦性的和谐自由之感。即使是在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那里,也已没有了李白式的无拘无束,英豪狂放,其壮豪之气总是笼罩在沉厚的抑郁伤感之中。相对来说,绘画从再现到表现的演进要稍落后一些,特别是北宋绘画仍以客观描绘为主,显示出一定的壮美特征。但总的看来,无论是人物画还是山水画,都以水墨白描代替了金笔彩绘,而且重意境心趣的山水画成为画坛主流,表现了绘画由实而虚、由浓而淡,由形而神的发展历程。元至明中叶艺术,重心进一步偏向主观意兴的表现,绘画追求所谓“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耳”。②相对于宋词,自由活泼的散曲更适于直抒胸臆,而指向社会现实的元杂剧,已经带有一定程度的近代批判色彩和悲剧因素,但总的说来,仍未脱离古典和谐的大团圆理想。
综之,封建社会后期的写意倾向和优美趣味在达到高峰期之后,便日益走向僵化和呆滞,显示出内在生命力的枯萎,并导致自身的解体,一场更大的历史转折将勃然兴起,审美意识将跨入更高的历史阶段,美将面临崇高的挑战。
三
明中叶以降,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力量的成长,启蒙运动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大一统的封闭型社会结构内部出现了否定自身的革命因素。长期以来处于和谐统一的主体和客体、情感与理智、伦理与心理、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开始出现裂纹,走向分化对立和矛盾冲突,审美理想由古典和谐向近代崇高迈进。首先表现在以宋元以来写意表情思潮为基础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崛起,包括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主“情”论,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枚的“性灵”说,杨州画派以及《西游记》的浪漫特色等等。其次是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思潮的兴起,主要体现在明清小说美学之中,诚如明清文论家们指出的那样,《水浒传》是“发愤之作”③,《金瓶梅》是“悲情鸣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④。更为突出的是,金圣叹腰折《水浒》以加强作品的悲剧气氛,砍去《西厢记》最末一本,变古典和谐的大团圆结局为悲剧结局。这些具有近代崇高色彩的观念,一直到王国维和前期鲁迅才得以完成。崇高不同于壮美,壮美是优美在量上的增加而非质的转变,壮美中的矛盾冲突并不破坏整体的和谐,它使人振奋激越,但并不超出快感的范围。崇高则是将壮美中主客双方的矛盾因素无限地扩大,引起质变,和谐变为对立。壮美给人的快感是直接的,不掺杂痛感的,而崇高给人的快感是由痛感转化而来的。
由于近代崇高的诞生,才产生了严格意义的丑、悲剧和喜剧。在古典时代,丑基本上是形式的、表面的、部分的,与美并无本质上的对立,而是被统摄于美的整体和谐中,丑并未上升为美学范畴。只是随着近代崇高的崛起,丑才上升为独立的美学范畴。因为崇高是美与丑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产物。随着丑的升值,崇高中美丑的矛盾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开始是以美为主导,丑是美的陪衬,结果总是导向美、否定丑。当丑发展到占绝对优势时,丑便取得主导地位并扬弃崇高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郑燮第一次将丑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提出来,引入绘画美学,旨在从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的形式走向矛盾冲突、动荡无序的无形式,追求丑怪的美、残缺的美、紊乱的美。他说:“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生。”“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⑤他画破盆兰花,偏侧之石,创“六分半书”体、“乱石铺街”法,都是为了实践这种美学追求。《金瓶梅》更是陈列丑展览丑的艺术画廊,小说中人物无一例外都是恶人。《红楼梦》、《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继续发展了这一倾向,对丑的人物丑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近代悲剧是美与丑不可解决的对立冲突的产物,是指在强大的丑恶势力面前,美的事物遭受不幸、苦难和死亡。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以及鲁迅所说的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就是这种悲剧。它不同于古典悲剧,古典悲剧以壮美为基础,剧中人物不管经过多少悲欢离合,最后总是出现大团圆的和谐结局,即使是感天动地的《窦娥冤》,也未能脱离这一模式。近代悲剧以崇高为基础,是丑压倒了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清忠谱》、《桃花扇》、《红楼梦》都属于这一类悲剧。喜剧同悲剧一样,是美丑对立斗争的一种新形式,但与悲剧不同,喜剧是美压倒丑。喜剧中丑的力量已经处于劣势,成为美所戏弄和扬弃的对象。近代喜剧不同于古典喜剧,古典喜剧中的丑被统摄于美的整体和谐之中,大体上限于闹剧(形式上的丑)和幽默喜剧(部分的丑)。而近代喜剧则是一种严肃辛辣的讽刺喜剧,其中的丑是一种本质上的有害的丑,它虽然在走向坟墓,但还相当有力量,还在垂死挣扎,美对丑的否定还相当吃力和严峻。鲁迅说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就是指的建立在本质丑的基础上的近代喜剧。马克思说:“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⑥这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了近代喜剧中丑的社会历史本质。中国的近代喜剧,滥觞于徐渭的《歌代啸》,发展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辉煌于鲁迅的《阿Q正传》。
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真正首倡崇高的乃是王国维,而导致这一基本范畴展开的是蔡元培、周作人以及鲁迅的美学思想。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人和个性问题的强烈关注。通过这三个环节,主体上升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主体的感性方面第一次争得了与理性同样的尊严,个体由此从社会伦理的抽象普遍性中挣脱出来,显示出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区别,素朴的古典和谐圈被打破了,相峙对立的矛盾关系取而代之,于是中国近现代美学思想向主观论和客观论两极发展。客观论主要由茅盾、吕荧、胡风、蔡仪的美学思想组成,重视对美的本体或客观本质的探讨。主观论主要由郭沫若、朱光潜和高尔泰的美学思想构成,重视对审美感受或主观心理问题的探讨。但是,矛盾并不是消极的,而是在双方的相互作用中将提高对立一方的质量,并在此基础上趋向新的和谐统一。客观论者初步提出了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认识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的问题,并表现出艺术社会学向审美心理学靠拢的倾向。主观论者提出了美是自由的象征,接近了美是自由本身即人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规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命题,对审美感受的社会内容的关注也表现出审美心理学向艺术社会学靠拢的倾向。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现代美学正面临着一次新的综合。这一综合首先体现在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中。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个性与群体、内容与形式、现实与理想相结合的艺术和美的理想,预示着对立崇高向辩证和谐的必然发展,标志着中国美学由近代向现代的伟大飞跃。之后,实践派美学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的观点,论证了美的本质是人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规律的统一,提出了美感的二重性理论,显示出综合艺术社会学和审美心理学的倾向。近期美学则提出了审美关系的理论,使美从普遍本质的层次上升到现象形态。审美观照、意志实践、理智认识三大关系的辩证,突出地提出了审美特性问题,并在审美意识的特质问题上,对艺术社会学和审美心理学进行了综合,表现出对崇高起点的螺旋回归。
但是,由于中国美学思想和艺术发展的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中国现代美学呈现出古典和谐、近代崇高和现代辩证和谐相互斗争、相互融和、错综交织的局面。一方面,辩证和谐制约着崇高不可能重复西方近代崇高的发展轨迹,走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和艺术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近代崇高作为由古典和谐到辩证和谐的中介环节,还需要充分发展,只有在充分裂变的基础上,才能创造真正的辩证和谐,避免向古典和谐的复归。
从以上逻辑的和历史的考查来看,中国美学范畴经历了由壮美经优美到崇高的逻辑发展过程,大致说来,中唐以前偏重壮美,晚唐以降偏重优美。随着明中叶浪漫思潮的兴起,萌发了近代崇高因素。近代崇高的诞生,也就导致了丑、悲剧、喜剧等范畴的出现。随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普及,中国美学将走向扬弃了古典和谐和近代崇高的新型的辩证的和谐。
①按历史顺序,谢赫位于宗炳之后,这时根据绘画从人物画向山水画的发展和绘画美学的逻辑递进关系,作了逻辑的调整。下文个别地方亦作了类似调整。
②倪云林:《答张藻仲书》。
③李贽:《焚书》卷3《忠义水浒传序》。
④张竹坡:《竹坡闲话》。
⑤《郑板桥集》第16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