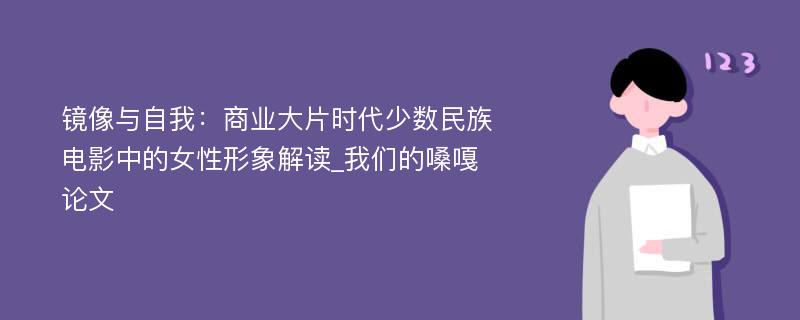
镜像与自我:商业大片时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镜像论文,少数民族论文,题材论文,大片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商业大片时代,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商业电影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主流方向。作为中国电影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无疑也受到中国电影环境变化的影响,在电影创作中呈现新的方向。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变迁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女性形象的变化。 少数民族电影第一次大发展是在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这一时期涌现了四十多部展现少数民族地区风貌的优秀电影,其中《阿诗玛》《刘三姐》《天山的红花》《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塑造了不少家喻户晓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多与政治诉求和文化认同联系在一起,女性通常作为社会历史巨变的见证者。第二次大发展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在探索中前进,电影题材更为丰富,少数民族女性从迷茫中苏醒,寻找在社会中的定位,开始以区别于男性责任的身份存在。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受到全球化电影市场影响,女性形象开始突破过去民族身份的限制,向都市女性学习,展现独特的女性魅力。但是,随着中国电影进入商业大片时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无法与商业大片争夺票房,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处境十分尴尬。2009年以来,电影创作者抓住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片和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两大契机,创作了一批优秀电影,其中不乏以少数民族女性为主体的电影。在这批以女性为主体的电影中,既有复归的传统女性,又有融入都市的新兴女性,多元化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带来了新生机。 纵观60多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女性形象的变化绝不是偶然,它是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注意力经济与商业电影环境的产物。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文明程度和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女性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符号,多种因素综合导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变化。本文选取2009年以来的12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雅克·拉康镜像理论作为依托,将当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划分为模糊的女性自我、女性面具下的镜像、女性的真实存在三大类进行分析,为今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提供借鉴。 一、众人目光之镜下的异化世界——模糊的女性自我 第一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由民族地区旖旎的自然风光、多彩的文化和婀娜多姿的女性等元素勾勒出美丽的画面,建构了对少数民族记忆的基调。时隔半个多世纪,在现代化进程加速和旅游业大发展的浪潮中,原本宁静淳朴的少数民族风貌正在远去,唯有身着民族服饰、头戴各式饰物的少数民族女性以活态方式保存了少数民族的韵味与风情,这些承载少数民族美好记忆的女性正逐渐成为电影创作者们抒发民族情怀的载体。于是,近年来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从艺术与现实的角度建构起了多种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她们或美丽灵动,或执着专一,或勤劳上进。透过电影荧幕这面巨大的“镜子”,对少数民族地区陌生的观众们似乎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女性清晰的形象与个性,然而,运用拉康镜像理论进行深入探析,这些在导演、电影主创者和观众观望中塑造起来的少数民族女性,距离现实少数民族群体生活与情感经历较远,她们这种通过与他者交汇而形成的脱离真实自我的形象,使得少数民族女性始终处于“面目不清”的境遇。 2009年和2010年上映的两部藏族电影《新康定情歌》和《寻找智美更登》是两位藏族导演对少数民族女性镜像的阐释。两部电影用不同方式讲述着藏族女性追逐爱情与自我的故事。“自我的存在是幻想,是非真实的存在。因为自我无法靠主体本身得以确立,它必须是主体依赖于自身在外界折射出的镜像关系才能够得以确立”①,这意味着人只有在“他者”的帮助之下才能建构自己的主体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定情歌》导演选择了以汉族男青年李苏杰返回康定寻找60年前初恋的视角,来讲述三位女性的故事;《寻找智美更登》陆续出现的剧组导演、老板、嘎洛大叔、男友等角色,都是为了映衬女主角卓贝而存在。“他者”是拉康哲学的核心词。其中,小写他者是镜像阶段中迷惑主体的虚幻形象,而大写他者是象征域中掏空主体的语言符号。在拉康那里,“他者”是一种存在之缺失②。电影的影像世界中,小他者是一种在场的想象,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小他者与主体互动,甚至是主体进入由小他者建构的虚无中,而大他者通常在电影中无处不在,但剧中人却毫无知觉,被动接受大他者改变主体命运。《康定情歌》中三位女性的故事,起源于李苏杰带着孙女婷婷回康定寻找初恋达娃,在此期间结识了达娃的孙子扎西和他青梅竹马的爱人格桑梅朵。两段感情纠葛中,观众看到了三位女性对待人生与爱情的不同态度。60年前的达娃给我们展现了率真、执着、专一的藏族女性形象,60年后格桑梅朵延续着藏族女性对爱情忠贞的态度,而从苏州来的都市女孩婷婷则显得格格不入。汉族女孩婷婷在整部电影中既是跟随爷爷来寻找自我的主体,也是藏族女性世界中的他者。婷婷是一面让人们发现藏族女性与众不同之美的镜子,那么达娃和格桑梅朵之于婷婷就是唤醒她“照镜子”欲望的“小他者”。婷婷在对达娃和格桑梅朵产生认同感的同时,也将自己交付于“他者”,跟随“他者”的步伐完成了她的康定之行。影片的最后,婷婷受到了扎西和格桑梅朵的感染而学会对爱情放手时,观众终于看清了影片中主体同镜像关系的脉络。不论是李苏杰和达娃的跨历史之恋,还是三个年轻人三角之恋,女性都被塑造成忠贞、执着、奉献的形象,而这种行为模式不应是藏族女性存在的唯一姿态,相反缺乏个性与自我的女性背后往往留有男性他者的深深烙印。 《康定情歌》中镜像阶段的小他者被导演用镜头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而《寻找智美更登》中从未出现却贯穿于整部影片的女性他者,则默默地引导着女主角的蜕变。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在《寻找智美更登》讲述了藏族女孩卓贝追寻自我的故事。作为影片唯一的女性角色,卓贝从头到尾没有摘下蒙面的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寻找智美更登》中的曼达桑姆和老板的爱人都是缺席的存在,但为爱执着与奉献的曼达桑姆与无名的老板爱人又像是镜子一样,让卓贝看清了爱情的真面目,她们引导着卓贝从懵懂无知到做回自己。当卓贝见到男友后,毅然取下了那条阻隔她与外部世界的面巾时,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卓贝。卓贝取下面巾同过去告别时,这个藏族女孩或许即将开始一段新生活。导演万玛才旦在整部电影中围绕卓贝展现了新旧两种藏区生活,不管卓贝是否愿意,导演都揭开了卓贝的面巾,将卓贝引向了新生活。藏族女孩卓贝更像是导演万玛才旦这位“他者”尝试对现代化藏区生活的妥协。 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导演宁才执导建国60周年献礼片《额吉》,讲述了蒙古族母亲琪琪格玛与她抚养的一群来自上海孤儿的故事。影片中琪琪格玛不顾丈夫反对坚持收养了两个孩子,而影片中这群孩子的亲生母亲,从抛弃孩子到认领孩子却从来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母亲”形象就是琪琪格玛式善良、坚强、无私的草原女性。上海母亲的缺席,既是导演对草原以外女性形象的保护,也给了我们一次完整领略草原女性魅力的机会。另一位蒙古族导演拍摄的电影《尼玛家的女人们》,导演卓·格赫似在讲述尼玛家两代三位女性的故事,实际上这三位在卓·格赫的镜头下展现的是同一种形象——豁达、开朗、孝顺、体贴的蒙古族妇女。两部影片中男性作为重要的小他者,对女性形象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马背上的蒙古族自古以来都是男性处于权利社会的中心位置,而影片中反对琪琪格玛收养孩子的丈夫、尼玛家女儿花钱雇佣的“丈夫”,男性均从镜头的中心被放置到衬托女性的角落。来自同一个生活空间的男性的反对或嘲笑,都使得女性对于自我认知更加深入,她们期望自己是不同于周遭环境的女性,这种影响与拉康描述的“他者作为自己的形象”对自我形成影响所不同,其更多的是借助他者的反面形象建立与他者差异化的自我。当我们所有人都为导演精心刻画的蒙古族女性而欢呼时,拉康却在一旁黯然神伤:这里没有我,只有他!在镜像世界中,主体的身份确认必须依靠他者,这种无法主导的自我身份认同在拉康看来是可悲的,几位蒙古族女性的存在实际是满足了导演和观众的欲望。如此一来,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多多少少被烙上了他者的影子,这些女性自然无法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 2010年上映的傈僳族电影《碧罗雪山》让导演刘杰在上海电影节和台湾电影金马奖载誉而归。电影围绕着怒江沿岸傈僳族女孩吉妮展开。吉妮与迪阿鲁相爱,却因为当地风俗不能在一起,而吉妮为了救出牢中的哥哥,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主动上山将自己献给了熊。吉妮作为女性被傈僳族传统文化秩序与信仰剥夺了话语权,从追寻爱情到失踪,她一直被环境所影响,被动地存在与付出。当吉妮走进大山,对着黑熊一笑,说了句“熊孩子,我来了”,我们看到了一个面对父系系统强势话语的女孩对命运的无奈。电影中“小他者”很容易被捕捉到,而“大他者”——作为文化结构和社会法则的符号秩序却总是悄无声息,在传统傈僳社会中,女性作为家族财产而存在,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傈僳族宗教礼治就是拉康所言的大他者。吉妮渴望用她的奉献在家族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但是这种无知的付出使得她在宗族内的地位越发卑微。吉妮更像是一个沉默的他者,被傈僳族族父系系统排斥在外,被家庭中的小他者和象征界的文化秩序所束缚。透过镜头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女性,却无法窥探她的内心世界。 二、现代与传统冲突的超越——女性面具下的镜像 抽象的文化秩序与社会结构,使得“女性”符号变得与以往不同。在拉康的象征界理论中,“女性”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被剥离,女性外表特质得以保留,但实质上只是女性面具之下去性别化的行为体。拉康认为,一个说话的存在物是在心理层次上建立性特征的,它和生物学意义上的性没有关系,每一个说话的存在物都可以选择加入任何一方③,因此,女性在符号系统内只是一种防御性的存在。在男权中心社会,隐藏在男性光芒之下的女性只能以羸弱附属的形象出现,而改造社会、拯救世界都是男性的职责。如今,在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席卷之下,女性开始从沉默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世人瞩目之下去性别化的“女性”,在颠覆性的符号系统中才有了替代男性成为家园建设和文化传承践行者的可能。“花木兰式境遇”是现代女性共同面临的性别/自我的困境。而对当代中国妇女,“花木兰”——一个化妆为男人的、以男性身份成为英雄的女人,则成为主流文化中女性的最为重要的(如果不说是唯一的)镜像。于是,当代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准分享话语权力的同时,在文化中却失去了她们的性别身份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④。 由各种声、画符号构成的电影媒介,在编码与解码中建构起了一个超越时空与地域的世界。隐藏在电影世界“符号之镜”中女性身体/男性视角的二元对立模式依然存在,女性身体作为一种消费符号从视觉角度上比男性更具吸引力。于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不少中外电影中诸如黑寡妇、劳拉、霹雳娇娃等睿智、勇敢女性英雄形象,她们在体力与智力方面超越了同片中的男性角色,站在镜头中央的女性承担着与男性同样的职责。在这些电影中她们像伊丽莎白·赖特所描绘的一样,带着性面具,将自己隐藏在身体场所中,大胆地颠覆男权文化,以“女性”代码的形式去完成使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曾在十七年时期获得过长足发展,而今,此类型电影因无法追赶电影市场变化而被挤到了夹缝中处境艰难。商业电影中以“去性别化的女性”为主题的电影文本,将人们从男性救世英雄的审美疲劳中解救出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者似乎也从中找到了创作灵感,创作出了一批致力于本民族发展与家园建设的女性主体,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注入活力。 哈萨克族电影《鲜花》中女主角鲜花将她的一生都献给了阿依特斯。作为阿依特斯传承人的爷爷突然离世,阿依特斯传承面临危机,从小失语的鲜花却突然开口唱歌,从此接下爷爷手里阿依特斯的传承之棒。最终鲜花为了阿依特斯和奶奶,放弃了外面的世界和爱情,成为草原上的音乐老师。美丽的外表,灵动的眼神,还有手中那只动听的冬不拉,让观众不得不把关注点放在了“鲜花”这个哈萨克族女性身上。乍看之下电影歌颂的是一个“女人”,而从导演致力于哈萨克族文化传承的角度,传承者的生物性别在传承链断裂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保留鲜花的女性特质,更多的是吸引观众目光的噱头。鲜花对本民族命运的关注超越了她对自我命运的关注,大他者——哈萨克族文化现状无形中将其异化。“鲜花们”看似距离这个时代哈萨克女性十分遥远,她们被令人堪忧的哈萨克文化传承现状紧紧束缚。在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的困窘中,少数民族女性承受着性别与人格分离的压力,妻子与母亲是社会赋予她们的自然角色,而在男性普遍外出务工的民族地区,她们还需要填补男性在本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缺失。 《尔玛的婚礼》中羌族姑娘尔玛依娜与汉族老师刘大川被放置在同一个叙事空间,由一场婚礼展开了镜像归属的争夺。究竟是汉族婚礼还是羌族婚礼,实际上是尔玛依娜进行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过程。为了体现这两种镜像力量之间的尖锐矛盾,导演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羌寨婚礼上,身着羌族新娘服看似幸福的尔玛依娜和身着名牌西服郁郁寡欢的刘大川进行着羌族婚礼仪式。尔玛依娜坚持自己的羌族身份,拒绝现代生活方式的诱惑。在这个关于羌族女性婚礼形式争夺的故事中,尔玛依娜通过奶奶和大川姑妈这两面内涵截然相反的镜子,一步步矫正了自己羌族女性形象。鲜红的羌族新娘服饰、夜晚载歌载舞的火塘、羌族祝酒歌这些羌族符号见证了现代羌族女性对传统的回归。导演韩万峰期望通过文化秩序无意识的影响来塑造一个文化传承者的镜像,引导大众社会对羌族文化境况的关注。 《我们的嗓嘎》和《好花红》中侗族姑娘黄月娇、布依族姑娘阿秀虽然来自不同的民族,但却走着相同的人生认证之路。侗族姑娘黄月娇为了侗族大歌放弃上海的工作和丈夫,布依族姑娘阿秀为了传承布依族山歌拒绝了北京演艺公司签约的机会。这两部电影在书写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的同时,也揭示出当代少数民族女性与本民族文化传承之间不可回避的矛盾。《我们的嗓嘎》导演韩万峰在谈自己的创作初衷时提到:“我们尝试把对侗族文化危机的认识隐藏在电影故事之中,让故事主人公的命运影响着观众的判断,让观众获得感官愉悦的同时,对侗族文化危机意识产生认同感,从而关注濒临危机的侗族传统文化。”⑤电影中少数民族女性担任着电影创造者传声筒的职责,导演将他们放置在本民族普通群众以外的高点,呼吁和践行文化传承,而这些少数民族女性的个人幸福与未来也为此做出让步。女人作为女人存在于电影中,与女人仅仅作为一个人存在于电影中完全不同,性别身份、情感命运等方面都已淹没在本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之中。影片中无论是尔玛依娜还是黄月娇都宁愿放弃自己的理想与情感,回到家乡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大旗。而从整个民族的角度来看,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现代化大潮中,她们的形象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在本民族群体其他成员的眼中,她们扮演着缺少自我的“他者”角色。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陈述的是他者对自我的影响,而“我”相对于他人也是“他者”,“我”在主体确认时可能被他人左右,也可能成为那个影响他人的范式。《鲜花》中卡德尔汗穿回了哈萨克族的坎肩、头戴“吐马克”,带着女儿“小鲜花”来参加古尔邦节;《尔玛的婚礼》中刘大川对羌族婚礼仪式的妥协;《我们的嗓嘎》中弟弟黄正宇开始探索侗歌现代演绎方法……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女性对他者的影响。这些标杆式的女性对影片中其他形象的影响是显性的,而隐藏在这背后——强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对女性“自我“根深蒂固的影响却是一种隐形的存在。此时的“我”只是“女性”面具之下的个体,我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作为女性的“我”如何作为,而是作为一个人的“我”有没有去行使我的职责。 三、自我与他者的交融——女性的真实存在 少数民族女性正在走过一段艰辛的自我确认之路,她们中的大部分刚从民族旧俗中解脱。这些女性不仅要面对外界为她们建构的“镜子”里的“他者”形象,还要承受不能言表的性别之痛,她们比同时期的汉族女性甚至是本民族的男性要经历更长的镜像阶段。而今,随着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加快,民族地区女性地位得到改变,女性在本民族的定位也发生了变化。她们开始突破象征界符号秩序的束缚,通过外出求学与务工的方式走出闭塞的村寨,像都市女性一样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少数民族女性与时俱进的新形象也引起电影创作者的注意,他们开始按照这些新现象与潮流文化要求塑造少数民族女性媒介形象。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的亮点是女性与时俱进,渴望贴近都市生活,实现个人理想抱负,掌握自己人生的话语权。这一被社会秩序大他者影响的少数民族女性人像,从镜像阶段的想象式认同上升到了象征式认同,她们不再只期望做理想的自我,对自我理想的追逐成为新的奋斗目标。 少数民族族群作为一个群体,具备格式塔“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特征,群体中的成员之间能产生相互影响的作用,他们因相似的习俗与信仰集聚在一起,群体中的“镜像”对于整个群体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电影中构建的女性镜像,正在逐步贴近当代民族地区女性生存实况。游走在本族群与现代社会中的少数民族女性,搭建起了自我与他者重合之路,为少数民族群体树立了积极融入现代新生活的榜样。曾经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女性也从荧幕中的被看,转变为其他女性甚至是男性的行为范式。 彝族电影《倮恋》中漂亮能干的彝族姑娘乌玛索,是葫芦苼传承人乌和老爹的孙女,爷孙俩居住的花倮寨由于大部分人外出打工成了空巢,聪明能干的乌玛索通过县政府和在北京的姑妈帮助下成立了花倮寨旅游开发公司,乌玛索自己担任旅游公司经理,带领村寨发展致富。在电影中观众看到了不同以往的彝族女性,作为葫芦苼传承人的乌玛索并没有在葫芦苼面临传承危急关头去承袭葫芦苼演奏,也没有沉迷于比阿乌的爱情。乌玛索的姑妈是整部影片中乌玛索确认自我的领路者,从小离开花倮寨到北京闯荡并有了一番事业的姑妈便是乌玛索行为的参照者,虽然乌玛索没有走出花倮寨,但是对姑妈的认同将乌玛索指向了花倮寨以外的世界。乌玛索身着彝族服饰的女性经理形象让观众眼前一亮,这部电影中彝族服饰和彝族村寨只是民族身份确认的标签,在乌玛索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都市女性形象与彝族女性形象的融合。少数民族女性步入新生活、自己掌握命运的新形象并非出于对观众与现实的妥协,电影镜像对于整个少数民族女性群体的镜像引领作用才是导演创作的初衷。 对于少数民族女性来说,村寨以外的陌生世界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她们。2014年上映的另一部彝族电影《俐侎阿朵》,围绕一个热爱舞蹈、梦想当舞蹈家,并且想靠上大学改变命运、走出大山的彝族姑娘秀美展开。秀美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却因为家庭贫困无奈辍学,但她没有放弃,再次考取学费便宜、有助学贷款的大学。影片中秀美把白族知名舞蹈家杨丽萍作为自己的偶像,杨丽萍成为了秀美的影子,她在认同这个偶像他者的同时为自己构建起新的人生之路。为了表现秀美成长之路以及对抗周围彝族文化环境的艰辛,影片一方面塑造了执着于与黑狗婚事的女孩树果与秀美对照,另一方面选择父亲与爱人两位男性来检验两种女性形象。无理取闹的树果、作为传统彝族俐侎人的父亲对秀美的坚决反对,以及在外打工的青年黑狗对秀美的痴心等待,这三个人物符号都是彝族女性在追寻“自我”的漫漫旅程中的见证者。从表面看,秀美只是彝族追梦女性的典型,实际上,我们隐隐约约从屏幕上看到许多同秀美一样的身影,秀美的经历之于其他偏远民族地区女性更像是一种召唤,期盼她们能早日摆脱处于劣势地位的“他者”身份,踏上寻找自我之旅。 壮族电影《天琴》是《刘三姐》之后又一部以壮族音乐元素为题材的民族电影,围绕两个热爱天琴艺术的壮族青年展开。主人公阿罗和良美在对歌中相识相爱。结婚前,良美前往深圳实现音乐梦想,放弃了与阿罗的爱情。她用阿罗赠送的祖传天琴在深圳唱出了壮族山歌的韵味,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演出舞台。良美完成了她从家乡出来时的梦想,但是她却不快乐。良美完整的自我镜像重构还差一步,这一步,要回归家乡去完成,这是典型的中国式重构。在深圳获得自己的事业,歌手的身份并不能完成良美自我镜像的重构,她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还缺少一些女性特质。“他者”——爱人阿罗,在这里凸显了意义。良美回到家乡与阿罗团聚,弥补了少数民族女性爱情的缺失。电影的前半部分,我们看到了一个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坚强女子,当她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的那一刻,我们都以为看到了少数民族女性建构自我之路的胜利。但是,良美在深圳孤独无依的失落感让我们开始怀疑胜利的真实性。当落寞的良美选择重返家乡时,我们知道,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女性的良美不会那么简单就做到真正的“我”。 少数民族女性在现代社会中追寻真实自我的旅途十分艰辛,能否取得事业、学业或者人生的成功并不是鉴定她们自我确认之旅是否完成的唯一标准。女性为了爱情或者建设家乡而返回,是当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主旋律。其他少数民族群体面对电影镜像时,能够通过这种荧幕形象认清自己的处境,并且修正自己的行为,完成电影镜像与现实人像的又一次重合,才是影片的真正意义所在。 本文所选的十二部电影只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冰山一角。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被寄予厚望,独特的文化蕴涵不仅丰富了国内电影市场,同时电影创作者也希望通过电影媒介所构建的人物形象来弘扬少数民族美德、重拾民族自信、重塑民族形象。在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作为影片主角的少数民族女性处于被凝视的焦点,通过她们见证着少数民族女性的成长,拉近了观众同遥远的少数民族女性的距离。但是,纵观本文所选电影,不难发现主旋律影片的创作模式,当其他因素凌驾于电影艺术之上,便不能真实还原少数民族女性形象,这或许是当前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如此,以女性为主体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依然从全新的视角为观众展示了商业大片以外的新景象。 ①拉康:《拉康选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5页。 ②李一君:《雅克·拉康哲学视域里的岩井俊二电影》,《艺术百家》,2013年第8期。 ③曾胜:《视觉隐喻——拉康主题理论与电影凝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④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当代电影》,1994年第11期。 ⑤韩万峰:《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下的民族题材电影与民族文化传承——首部侗语电影〈我们的嗓嘎〉研讨会发言摘录》,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11036-1.htm,2009年12月4日。标签:我们的嗓嘎论文; 商业论文; 寻找智美更登论文; 羌族论文; 藏族论文; 康定情歌论文; 剧情片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