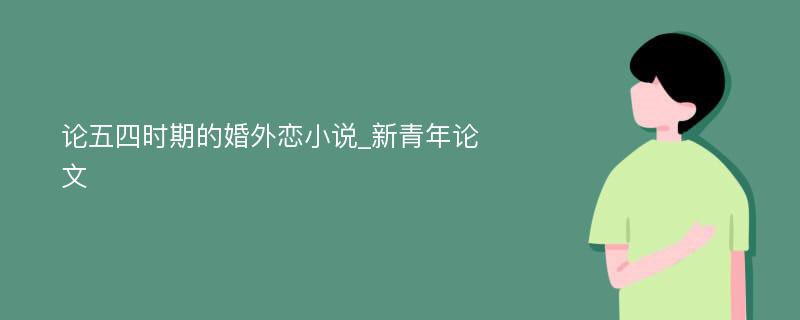
论“五四”时期的婚外恋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婚外恋论文,时期论文,小说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婚外恋现象作为社会问题,婚外恋描写作为文学现象,在“五四”时期受到如此广泛、深入的关注,皆离不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两性道德的破除和新两性道德的建立。或许,这是形成“五四”小说集中描写婚外恋题材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
“五四”时期,《新青年》首先发起“贞操问题”讨论。从《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起,不断有人撰文讨论妇女解放问题,初步涉及到两性道德内容。不过,“贞操问题”讨论真正引起全社会广泛注意,是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译载日本谢野晶子《贞操论》之后。在《贞操论》中,作者以决绝的口气写道:“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既然是趣味信仰洁癖,所以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这种现代贞操观不啻晴空响雷,震撼了人们的心灵。随后,《新青年》刊出的胡适的《贞操问题》、《美国的妇人》,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在抨击旧两性道德上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这些文章从男女平等出发,指出了旧两性道德中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压迫,提倡女子自立,主张建立一种“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无疑,这种批判旧两性道德的视角和方法,在当时的影响、作用和意义都不可低估。
现代性爱意识的觉醒,是“五四”个性解放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曾经关注、讨论过现代性爱意识,以对抗中世纪神权禁欲主义,把人从神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五四”呼唤、张扬的现代性爱意识则是为了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把人从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如此以来,“五四”时期关于两性道德的讨论,既有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学者对现代性爱意识的论述,也有针对中国文化背景、现实生活发出的言论。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关于贞操观的讨论。在封建社会,贞操观一直是封建伦理道德束缚妇女心灵、阻碍妇女解放的重要道德教条。千百年来,难以数计的妇女在这种观念逼迫下做了贞妇烈女,演出了一幕幕最悲惨的人间活剧。欲求妇女解放,“首先就要打破贞操的迷信。……中国的社会,还没有脱离宗法的遗迹,而且偏重男统,所以贞操一事,经过多少年的陶养,已成了中国妇女的宗教了!”(注:罗家伦《妇女解放》,《新潮》第二卷第一期。)由于贞操观讨论直接关联着妇女解放问题,甚至是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尺度,所以,反对封建男权主义、要求男女平等,便成为“五四”思想文化界破除封建贞操观的基本视角。胡适曾言:“我以为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注: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语丝》上也有人撰文说:“贞操,是在有感情的两者间的东西,那里在决绝了的人还有贞操可守。”(注:微霉《劝婚与劝不婚》,《语丝》第五卷第九期。)虽然这种新贞操观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旧两性道德毕竟第一次受到真正、有力的挑战,建立符合现代意识、现代社会生活准则的贞操观已经为时不远。
其二,对贞操观与爱情、现存婚姻关系的讨论。对新贞操观的探索、建立,必然涉及到如何处理与爱情、现存婚姻之间的关系。对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回答非常干脆:贞操只与爱情发生关系,与现存婚姻无关。这只要浏览一下当时大家的言论,问题就一目了然。胡适说:“夫妻之间若没有爱情恩意,即没有贞操可说。”(注: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另一位作者在《新青年》上撰文说得更为通俗易懂:“所以吾尝说,两个男女有爱情,便可共处。爱情尽了,当然走开。这本没有什么奇怪,可羞耻,可惊骇。更用着发什么恼?爱情原与天气是差不多一样的自然现象。”(注:张崧年《男女问题》,《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这不免有爱情、贞操虚无主义倾向,但对破除旧两性道德确实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五四”时期,大家对“新性道德”的理解似乎非常宽容:“甚至如果经过两配偶者的许可,有了一种带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的。”(注: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妇女杂志》1925年“新性道德号”。)“新性道德”宽容到连最能体现旧两性道德的传统婚姻都能够理解、包容,令人触目惊心,难以理喻,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宽容”、“理解”态度,又推动着大家在破除旧两性道德上走得更远。
“五四”时期对于贞操观与爱情、现存婚姻关系的认识,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景宋于大革命失败后,劝告友人说:“在恋爱上,对方无论是天神菩萨般本事,或猫狗般恶劣,只要双方相爱,那就拚命爱吧!那是最尊贵的自由呀!不爱了,大家认为有走散的必要,就走散罢,用不着丑诋,无须乎死掉。”(注:景宋《送学昭再赴法国》,《语丝》第四卷第五十二期。)这种论调在“五四”时期的报刊上俯拾即是。于此,可以窥见“五四”时期关于两性道德问题讨论,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和社会行动准则产生的深远影响。
应当承认,“五四”时期对于两性道德的讨论,主要是在知识阶层展开的,最初的影响和作用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识阶层。例如,“五四”小说婚外恋描写的男女主角,其身分大多数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如同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革命一样,“五四”道德革命的成果终将转化为普通群众的行动。中国幅员辽阔,社会经济、文化水平落后和封建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客观上阻碍了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但是,从“五四”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图景看,这场道德革命还是影响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到了偏远的农村。许杰《台下的喜剧》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私自相恋在村民中掀起的轩然大波,其中,以村上“有名的辣货”松哥嫂的议论最为引人注目:“就是双双捉住又何妨呢?难道不是人吗?……我说得好:现在是民国了,讲自由,偷得来情人也是本领,——被人们捉住也没有什么。——也说不上贞节不贞节,只要他两人不会三心两意,不会再偷七个八个就好了……”虽然不免过于直率,也未必能够得到大多数村民的赞同和拥护,但是,这毕竟预示着“五四”自上而下的道德革命,已经开始在基层社会和广大民众中发生作用,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
“五四”小说把婚外恋概括为两个基本模式:(一)先有“外恋”,后有“婚姻”。青年男女在自由交往中倾情相恋,正当从恋爱向婚姻过渡时,封建家长出面,用各种理由和方式拆散这对自愿、自由的婚姻,使自由恋爱只开花不结果。诚如陈独秀所言:“盖恋爱是一事,结婚又是一事;自由恋爱是一事,自由结婚又是一事;不可并为一谈也。”(注:陈独秀《答刘延陵》,《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象王统照《遗音》描述的婚外恋就属于此类模式。公立小学教员主任与一女学生产生恋情,母亲却在家里为其包办了一位亲戚的女孩,他“不能舍弃了他母亲,便不能毁了这个婚姻”,最终接受了母亲的包办婚姻。庐隐《一个著作家》也是这样。沁芬原先和青年著作家邵浮臣倾心相爱,父母却为了她的“前途”和“幸福”,将其许配给富足的罗濒。在这种婚外恋模式中,自由恋爱之所以不能自然地发展成为自由婚姻,主要原因就是父母对婚姻的干涉。(二)先有“婚姻”,后有“外恋”。父母根据“门当户对”、“亲上加亲”和家产、相貌等外在条件,把儿女圈定在预先设计的婚姻中,而且儿女必须终生遵守这种体现出父母权威、意志的婚姻约定;由于通过这种方式缔结的婚姻漠视、戕害青年男女的自由、幸福,他们往往在婚姻之外,又去寻求“外恋”。郭沫若《飘流三部曲·十字架》属于此类。在这种婚外恋模式中,婚外恋的起因是对包办婚姻的痛苦和失望,所以,最终根源还是在作为封建家长的父母那里。总之,无论在“五四”小说展示的哪一种婚外恋模式中,婚外恋所代表的个性主义思想与父母所代表的封建父权都构成了直接冲突,因此,封建父权是青年人追求婚姻自由的主要障碍,也是扼杀婚外恋的主要对立力量。
封建父权压制、剥夺青年人自由婚姻的做法,由来已久。象陆游和唐琬的婚姻之被母亲拆散,贾宝玉被骗进薛宝钗的洞房,都集中体现了封建聘婚制度中父权的意志和权威。“举凡天下一切暴政苛刑,父母皆可一一施诸子女之身。其罚子女也,又从无规定之刑律,往往以父母之气平怒息为止。”(注:张耀翔《论吾国父母之专横》,《新青年》第五卷第六期。)在封建社会里,儿女被视为父母的私有财产,封建父权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统治力量;青年人反抗父权的力量总显得单薄、软弱、无力,怎么也不会冲破“铁屋子”式的封建壁垒。“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封建父权赖以生存的封建大家族制度及其“发达体”君主专制制度遭到批判和否定,(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个性主义力量日益强大,彼消此长,形成了新的封建父权文化语境。对父权而言,此刻只要能维护封建家长权威、规范、道德,往往“委屈求全”,基本上不再以威严庄重、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对儿女婚姻,它不仅予以“关心”、“爱护”,而且还与儿女共商婚姻大事,在某些细枝末节上,甚至做出一些让步,因而,它们较传统宗法制家庭中的父权,具有更大的蒙蔽性和欺骗性。何植三《D君》中的母亲为儿子包办婚姻时, 征求过儿子的意见。庐隐《一个著作家》,冯沅君《隔绝》、《隔绝之后》、《误点》等小说中,父母包办女儿的婚姻,也都是为了“疼爱”女儿。其实,父权的妥协和宽容是有条件的,甚至暗藏着杀机。首先,封建家长对儿女婚姻的让步、默认,总是有一定条件和前提的,即不违背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而且它的让步、默认极其有限,不可能越过由父母决定、包办婚姻的界线。其次,既然婚姻与儿女共同商量过,那么,这桩包办婚姻就被裹上了一层自由婚姻的外衣,一旦出现背叛婚姻或发生婚外恋现象,青年人便会千夫所指,永无立足之地。所以,即便在新的父权文化语境中,父权仍然是迫害婚姻自主、婚外恋的主要力量。
“五四”小说婚外恋描写批判的另一重要对象是封建夫权。在封建宗法制家庭中,父子关系是家庭的主体和核心,父亲死后,长子便承担家长的职责,这种职责和功能甚至延伸至女婿身上,以所谓的“半子”身分在被姻亲联系的两个家庭之间,对妻子的父家长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同时,这种身分又使他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在自己家庭代行妻家父家长的责任。因此,在封建婚姻关系中所反映出来的夫权,在本质上是父权的延伸。许杰《隐匿》描述了青年女子彩珠的婚外恋故事。丈夫外出谋生,多年未归,并且音信杳无,彩珠的生活和情感无以寄托,便与一木匠发生了婚外恋。突然,丈夫从上海回来,全家立即惊慌失措;丈夫发现妻子的不贞行为后,便不辞而别,远走他方。这个故事告诉读者,夫权在旧婚姻中具有无可撼动的主导地位。庐隐《父亲》所塑造的庶母,是一位深受封建父权和夫权双重迫害的人物典型。庶母的父母为了女儿的幸福,将其包办给了容貌英俊和满口花言巧语的“父亲”,可是,“父亲”与庶母之间根本不存在爱情,他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下的“父亲”对钱财和庶母美貌的占有。如果说封建父权在包办婚姻中经常充当、并且满足于充当法官角色,对形形色色的婚外恋,做出合乎封建伦理道德的裁定,有时,由于血亲原因也作些敷衍、掩饰,如彩珠的母亲、舅舅之类,那么夫权则不仅要监督、规范妻子的婚姻行为,而且还具有消费功能,即利用在家庭中的有利条件和地位,强制妻子充当奴隶、仆役,甚至为自己守节。因此,“五四”小说所描述的婚外恋者在反抗夫权时,其强度和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反抗父权,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死向封建夫权发出了绝望的反抗。这是生活在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下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夫权戕害妇女自由、幸福和生命的罪证。
“五四”小说婚外恋描写还把批判视角瞄准了封建伦理文化。社会化、文化化的封建父权、夫权,是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对付婚外恋的捷径。因为,在婚外恋与父权、夫权的较量中,具体的父家长在性格、能力、地位等方面的差异,都制约和影响着他压制婚外恋的能力,包办婚姻的背叛者一旦逃出父家长的视野,甚至立刻就能够获得自由,对此,父家长似乎无能为力。相反,父权、夫权如果通过思想道德形式向社会渗透,以社会伦理文化形态表现出来,使其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思想、行为规范,那么,它对包办婚姻、婚外恋的控制显然更为有效。含星《苦闷的灵魂》中的D君和W女士,逃出了父母的监视和控制,却没有能够逃脱社会法制力量的网罗和社会舆论的谴责,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婚外恋,却是封建势力成功扑灭婚外恋的典范。其次,父权、夫权思想进入社会文化视野,加强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并把本来由父权、夫权对婚姻的单向度强制,改变成为社会自觉遵守的法则,因而,对婚外恋监督、控制的力度得到极大的加强。汪静之《被残的萌芽》中并没有出现父家长,围绕福培嫂的是一群普通妇女,如“老妇人”、“祖母”、“阔嘴娘”等,她们如同福培嫂一样,也是深受封建父权、夫权压迫的女性,可是,她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父权、夫权对女性的压迫,相反,她们严厉谴责福培嫂与秀逸的婚外恋。福培嫂之死,并非因为父母或丈夫的直接威逼,而是死于一群封建父权、夫权的忠实维护者之手。从“五四”作家在理论上的表述看,他们对封建伦理文化的危害性和摧残性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子荣(周作人)曾言“……就是我们为父母的也不必而且不能管了——然而所谓社会却要来费心。他们比父亲丈夫更严厉地监督她们,他们造作谣言,随即相信了自己所造作的谣言来加裁判。”(注:子荣(周作人)《抱犊谷通信》,《语丝》第十二期。)欲以婚外恋打破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求得个性解放,必须摆脱封建伦理文化的监视、禁锢,否则,婚外恋难以获得成功。这是“五四”作家在婚外恋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共识。
“五四”小说婚外恋描写产生于个人与家族对立、西方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伦理道德对立的文化语境之中,个人要求自由解放的迫切性与封建家族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顽固性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五四”小说婚外恋描写探讨的中心主题。在这里,婚外恋实际上既被当做个性主义武器,向封建势力发出挑战和攻击;又被当做“婚姻自主”、“自我解放”的有效途径,向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人的权利”。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看,那些思想先驱们似乎“忽视”了婚外恋所具有的反封建功能,并未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正因为如此,“五四”婚外恋小说所提供的东西,便是其他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三
在文学史上,“五四”小说首次超越了古代文学的婚外恋描写,把自发式婚外恋描写模式转变成为自觉式婚外恋模式,重新认识和评价为封建伦理道德所鞭斥的婚外恋现象,充分展示了“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而且,“五四”小说所确立的审视婚外恋现象的视角、方法,对新文学继续探讨婚外恋及其个性解放、人性主题,奠定了基础。
在古代文学中,自发式婚外恋始终含有纵欲主义成份。潘金莲背弃武大郎,与西门庆寻觅欢爱,虽然包含了普通妇女追求爱情、幸福的愿望和要求,表现出对抗封建夫权和对不幸命运的抗争,但是,她毕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婚外恋行为所具有的反封建内容,似乎仅仅满足于通过“外恋”对性爱的追逐。为了达到长期偷情的目的,潘金莲和西门庆合伙毒死武大郎,使这桩婚外恋中原本就十分微弱的反封建意义荡然无存,相反,潘金莲的纵欲主义却被凸现出来。无可否认,婚外恋中含有两性之爱的成分,它反映了人们在生理方面的自然需求,但婚外恋更反映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如果婚外恋仅仅止步于纯粹的两性之爱,没有反映出任何历史文化内容,那么,这样的婚外恋只能被视为人性的堕落,是在更深层面上对个性解放的消解、诋毁。周作人曾经揭露说:“极端的禁欲主义即是变态的放纵,而拥护传统道德也就同时保守其中的不道德”,“非难解约再婚的人也就决不反对蓄妾买婢。”(注:周作人《谈虎集上卷·重来》。)所以,婚外恋中的纵欲主义实际上是封建禁欲主义的一种存在形式,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旧道德。对此,“五四”婚外恋小说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俍工《暴风雨的夜》是“五四”小说中唯一一篇反映旧式人物婚外恋的作品。二奶奶为了达到长期通奸目的,与奸夫一起溺死寡媳,并拿出二石干谷让邻居三爷父子,在大雨中埋葬寡媳的尸体。作者对二奶奶的“婚外恋”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抨击,因为,这并非个性主义的婚外恋,它与“五四”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在中国文学史中,二奶奶形象比较接近潘金莲,从人物思想道德水准,特别是婚外恋的方式、结局上看,两人基本上可以划归同一人物系列,但是,作家对待二者的态度却迥乎不同。前者揭露了二奶奶婚外恋的纵欲本质及其荒淫无耻的特性,批判了纵欲式婚外恋对人性的践踏,后者则站在封建伦理道德立场上彻底否定潘金莲的婚外恋。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古代文学和“五四”小说在描写婚外恋上的区别。
在“五四”小说中,象二奶奶这种旧式人物的婚外恋并不多见,婚外恋者基本上都属于“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五四”作家对这些新派人物“借婚外恋之名,行旧道德之实”,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庐隐《时代的牺牲者》中的张道怀是一位留洋学生,满口法律名词;腾固《壁画》中的崔太始是一位留洋画家;林守莊《扫墓》中的鹃小姐是从上海回来的时髦女郎;方光焘《业障》中的婚外恋主角更是坚持“恋爱没有肉的证明,算不得恋爱”的现代青年……。这些新派人物虽然言必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可是,他们所理解的“自由”、“解放”实际上是对性欲的放纵和各种贪欲的满足。抹杀“性的解放”和“肉欲的解放”、“爱情的自由”和“通奸的自由”、否定旧道德和道德虚无主义之间的界线,是新派人物“借婚外恋之名,行旧道德之实”的惯用伎俩。以激进者自命的高长虹就蔑视“恋爱”,大谈超历史超时代的“性”。他说:“性的真实的个性只有它自己能够而且愿意表现出来。是的,它已经这样做了,那便是杂交。”(注:高长虹《论杂交》,《狂飙》第二期。)高长虹的“高论”,立即遭到鲁迅先生的严厉批评。“五四”小说婚外恋描写以生动逼真的感性形象,揭露了新派人物的丑恶灵魂。张道怀口口声声对妻子说:“我们虽然是由父母作主定的婚姻,然而我们的爱情是不在那自由恋爱的以下。”对爱情似乎无限忠贞,可是留学海外时就与一位外国看护妇“结婚”,回国以后,又抛弃妻儿,追逐“家既富有,貌亦惊人”的林女士。他标榜的高尚的志趣和神圣的爱情,是为了掩盖他的虚伪本性和丑恶灵魂;他的朝秦暮楚,更谈不上个性解放,而是封建士大夫玩弄女性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小说剖析婚外恋现象的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了古代文学,它标志着这一新文学题材创作已经走向成熟。
自从“五四”小说在婚外恋中揭示出个性解放、人性主题之后,新文学就没有停止对这种社会现象的进一步探讨。以三十年代以后的作品为例,描写婚外恋现象的新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出现了叶紫《星》、许地山《春桃》、曹禺《雷雨》、巴金《憩园》、《寒夜》以及新时期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刘恒《白涡》、《伏羲伏羲》、霍达《未穿的红嫁衣》等一批成功之作。如果仅仅从作品的美学品格和文学史上的地位看,上述作品都超过了“五四”时期的婚外恋题材作品,但是,从这一题材在新文学进程中的演变、发展看,二者之间显然存在密切的源渊关系。后者的进步和成功,离不开前者奠定的基础。首先,婚外恋题材没有象新文学主流题材一样,发生题材否定、转移。如果说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以后,革命题材否定和代替了“五四”时期的启蒙题材,实现了新文学主流题材的第一次大变迁,那么,这次主流题材变迁对婚外恋题材影响不大。以《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婚外恋题材小说为例,1927年第18卷上发表了行余《两封遗书》、含星《苦闷的灵魂》和许杰《出嫁的前夜》共3篇,1928年第19 卷上发表了施蛰存《绢子》和甲辰《或人的太太》。仅从数量上看,第19卷上似乎减少了一篇,但是,《绢子》和《或人的太太》在小说技巧和人物心理刻画方面明显超过前者。这就说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没能改变作家继续描写婚外恋题材作品。其次,审视婚外恋的视角、方式基本一致。三十年代以后描写婚外恋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继续用个性主义思想探讨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和人性主题。如许地山《春桃》,就以成功地塑造了春桃形象而闻名。八十年代的《白涡》描写了新时期科技干部周兆路的婚外恋,展示了他的双重人格的复杂矛盾,基本上也属于这一视角。另一类作品在描写其他题材时,涉及到婚外恋现象。这类作品的思想主题较为复杂,有用革命主题否定婚外恋意识的,如《小二黑结婚》描写三仙姑;也有革命主题、抗战主题和个性解放主题并行不悖的,如叶紫《星》描写梅春姐、巴金《寒夜》描写曾树生都不乏个性主义、人性因素。纵观本世纪中国文学,婚外恋作为新文学的一个基本题材并没有被描写完,人们不断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不断地理解这个问题,从而不断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领悟。如此看来,“五四”文学的婚外恋描写,首先把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引向了科学健康的发展方向,是本世纪乃至下世纪文学描写婚外恋现象的先导和基础。其价值、意义和作用都不可低估。
收稿日期:98—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