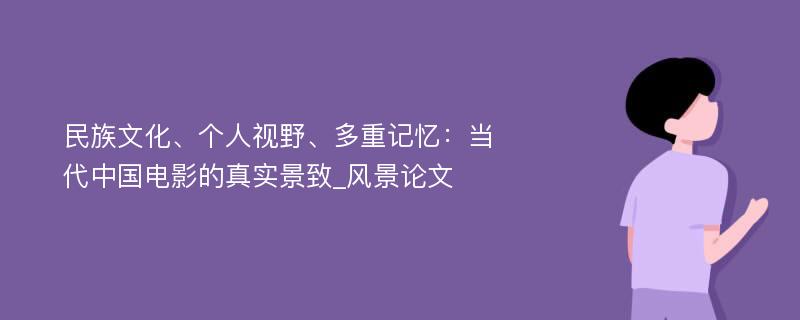
民族文化,个人视野,多地记忆:当代中国电影的真实风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中国电影论文,视野论文,当代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实及其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银幕上的重新发现
在电影风景中,真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从外部世界直接转换而来或可以转换而来的本体。一百多年前,路易斯·鲁米埃尔和奥古斯塔·鲁米埃尔兄弟在他们早期的纪录短片《工厂大门》(1895年)和《火车进站》(1895年)中捕获到巴黎的真实,因此倍感欢欣鼓舞。几年后,乔治·梅里埃很快在《月球旅行记》(1902年)这一类虚构电影中发现了早期电影技术在操纵影像和视觉幻觉方面的巨大能力。尽管电影人倾向于将真实视为电影的最终目标,而虚构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但梅里埃的迷幻(凭借虚构)和鲁米埃尔的真实(借助纪录)却被公认为早期电影中的两种不同传统①。学者们认为它们最终融合为好莱坞片场时期的经典电影模式。
但是,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真实却不再能够作为一个其意义可以通过对原本的直接模仿而获得的不受争议的固定所指而发挥作用。相反,它被认为是借助于技术设备和人类干预而被媒介化重构的。的确,后现代理论家声称“‘真实’,在人们的观念中一直是作为原本的仿制品、模型、或者拟像而出现,但事实上这些观念却先于真实而存在,甚至生产了真实。”②在对记录电影的研究中,真实和表现之间的张力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的解决,斯特拉·布鲁奇(Stella Bruzzi)就曾生动地描述“巴赞(Bazin)和波德里亚(Baudrillard)的持久争辩,他们从相反的角度对影像和真实之间的差别的消失进行争论,巴赞认为真实能够被复制,而波德里亚则认为真实只是另一种影像。”③如同纪录片一样,我们在虚构电影中也同样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真实的回归并不是指它回归真实本身,而是回归成“虚构的真实”(reality fiction),即媒介化了的有关真实的影像④。
在当代中国电影的语境中,真实作为一个创造性的经过重构的影像而不是政治假设的、可由外部经验世界证实的“客观”的意义,对后毛泽东时代电影制作留下了巨大影响。在经历三十年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和经常性粗暴的政治压制之后,1980年代早期,中国电影人逐渐学会在官方授权的范围之外扩大他们的真实视野⑤。1970年代末以来的三十年,尽管官方仍然通过审查维持着监视的权力,但真实在中国电影中显然更多的属于个人视角而不是意识形态传声器。也正因此,真实风景也就成为一个备受争论的语域,各种各样的真实在话语和视听领域经历了持续的重构,经常针对目前已认为不真实的或不再真实的概念。
在后毛泽东时代的银幕上,国家认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其公式化的典型特征和历史目的论的视角成为一个“不再真实”的个案,而遭到两个主要的先锋电影制作群体的质疑⑥。首先,在1980年代中期,第五代导演,如陈凯歌(1952年生)和张艺谋(1950年生),开始将他们的摄影机镜头投向壮观的乡野自然风景,从而远离现实政治的城市中心,企图以此挽回被遗忘或被压抑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其次,在1990年代初期,第六代导演,如张元(1963年生)和王小帅(1966年生)开始探索异化城市灵魂的心灵风景,以恢复他们自己的个人真实感知。同时,他们明确地挑战了主流权威关于真实的陈词滥调和第五代在国际影展中备受欢迎的“民俗电影”中所再创的传统⑦。进入21世纪,一些年轻的独立导演,如贾樟柯(1970年生)和应亮(1977年生),尝试通过重访乡村和内陆的风景来重构电影的真实,但并不是把它们凝固为轻易可解密的中国符号(就像第五代导演近来所拍摄的大片中的东方象征)⑧,而是为了突出流动中的自然风景的不确定意义。
“流动中的自然风景”这一观念来源于这一双重的认识:在目前的全球化时代,特定地域的自然和文化正不断遭到跨国、跨地资本和人力流动的征服,在某些时候电影视听成为捕获处在转换期、甚或灾难中的真实的最终手段,就像《三峡好人》(贾樟柯,2006)这部获奖的具有纪录片风格的虚构电影所有力呈现的那样。资本和劳力的流动进一步驱使独立导演转向“民生景观”(ethnoscape),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将之定义为:“构成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变化世界中的人的景观,这些人包括旅行者、移民、难民、背井离乡者、外出劳工、以及其他流动群体和个人,迄今为止,他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景象,并且影响着国家和国际间政治。”⑨除了民生景观之外,阿帕杜莱还勾勒了其他四种景观:媒体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为了在中国电影研究的语境中整合阿帕杜莱对当前全球流动的分析框架,我建议将官方电影视为以宣传政权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风景,将商业电影视为地位于资本和利润的媒体风景,将艺术电影视为倾向于审美和名誉的心灵风景,而将独立电影视为与边缘和真实结缘的民生风景⑩。
在接下来的三个部分,我首先讨论第五代导演面对乡村自然风景而重新发现真实,这使得他们能够突出一种不同于共产党历史所认可的民族文化视角。其次,我分析第六代导演对个体性的热情,他们对城市青年人心灵风景的探讨,以及他们对真实、现实和感知的坚持。再次,我转向一个年轻的独立导演群体,他们强调跨地性(translocality),并刻意混合虚构和记录模式,描述迁移与记忆的民生风景。通过分析自然风景、心灵风景和民生风景这种表达方式和自然、真实、多地性(polylocality)这三个聚焦主题,本文进一步推进我们对中国电影艺术、真实和视觉技术之间错综复杂、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的理解。
第五代的自然风景:寻找民族文化
正如马丁·勒菲弗尔(Martin Lefebvre)在2006年所观察到的那样,尽管风景在早期电影(尤其是旅行电影)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风景和电影”迄今仍然是电影研究中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领域(11)。勒菲弗尔引起我们对两种被忽略的传统的注意。首先,根据爱森斯坦(Sergei M.Eisenstein)的观点,风景是“影片中最自由的因素,最少承担实在的叙事任务,并最能灵活地表达情绪、感情状态和内心体验”(12)。换句话说,电影风景享有某种脱离叙事的自律,并因而引发某种诠释和情感,这些诠释和情感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由电影情节所驱动的行动和事件。其次,对于文化地理学家而言,“风景并不独立存在于人类对空间的投资,这是将它们跟‘大自然’的概念区分开来的一种方法。(因为大自然)在没有人类的干涉之下,将可能继续存在(甚者可能繁盛)。”(13)自然环境只有通过人类的努力才能转变为风景。
“风景”(landscape),连同它更早的变体“landskip”和“landtskip”,其词源可以追溯到它的后缀‘-shaft’,‘-scipe’,‘-ship’以及其他相关的术语,如gesceape,gescape和shapen,所有这些都是“给某物以形式或形态”的意思。勒菲弗尔推理说,人类的感知能力正是借助某种智力上的“取景(构架)”,才给予其它“无形式”的自然环境以形式:“通过那种构架,自然转变为文化,大地转变为风景。”(14)风景因此反映了人类的经验。在此意义上,西蒙·斯卡玛(Simon Schama)断言,“风景是自然背后的文化,是通过树木、水和石头表达的人类想象力。”(15)
第五代导演问世的头两部作品是先锋电影,其风景的重要性盖过叙事情节和对话。《一个和八个》(张军钊执导,1984)和《黄土地》(陈凯歌执导,1984)实验性地将情节和对话降到最低程度,促使观众凝视中国西部令人敬畏的贫瘠风景。《黄土地》尤其凸现陕北黄土高原的土地和峡谷,以及蜿蜒其中的黄河。在无法抗拒的视觉影像的剧烈对比中,《黄土地》却没有多少叙述或性格发展方面的内容,壮观的自然风景使当时那些固守几十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坚持要对电影的每一个细节进行解读的观影者充满困惑。
陈凯歌这么指导他的制作团队:“在电影结构方面,我要我们的电影丰富多变,要自由地表现那种无拘无束……能用一个简练的词来完美地概括我们电影的风格:‘含蓄’。”(16)在1980年代中期,这种“含蓄”的风格其实相当激进,它使第五代导演可以拒绝遵循主流创作方针,却不必明确表明他们颠覆社会主义电影制作传统的意图。他们表达含蓄的自然环境正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地理上接近1930年代后期中国革命总部的延安地区。正如这部电影的摄影张艺谋所展望,一种特殊的风景成为现实:“高天厚土”,“黄河汹涌”所有这些使得电影的视觉和观念比人物更重要,因为对黄土和苍天不成比例的构图使人物相形见绌(17)。
《黄土地》风景的激进影像使当时的电影权威相当困惑。导演于彦夫就抱怨说,“视觉上给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却与电影内在的发展或人物的行动没有任何联系……有很多固定机位的镜头,人物长时间保持不动或沉默,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18)作为高级电影官员和资深电影编剧,夏衍也承认他对电影所描述的“广大群众”感到反感:“我就无法理解如此接近延安的人怎么能够完全不受来自延安的新精神的感染。”(19)
很显然,陈凯歌的含蓄风格成功地掩盖了电影挑战共产主义革命神话的意图,这一神话保证农民一旦受到共产党的动员,就立即表现出革命的精神。电影的最后一幕把这种经过伪装的挑战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共产党员顾青回到遭受旱灾的村庄,在一大群向龙王雕像祷雨的迷信的男性农民后面,缄默的男孩憨憨似乎看到了顾青,他逆着疯狂的人流奔跑去迎接顾青,可是在镜头的几次剪接中,顾青在地平线上多次出现,似乎成为苍天和大地之间若隐若现的一个幻影。影片落幕之际,憨憨的姐姐翠巧的歌声响起,可是这仅仅只起到视觉幻像的作用,因为观众这个时候已经知道,翠巧早就被迫嫁人,在她企图游过黄河逃婚的时候溺水而亡,没能唱完革命歌曲中“救万民靠的是”之后的“共产党”一词。
史蝶飞(Stephanie Donald)通过上述“一个无情而反复的远景”来诠释顾青的姗姗来迟,指出这暗示了从电影人物到观众,从过去到现在的功能的转变:“顾青的凝视从自身复原回到风景中,他成为了地平线的一部分。他那种在电影中始终受到讽刺的主动性,最终在电影中被消除并交给了观众。”(20)对于获取主动性(agency)的观众来说,转变的结果就是“民族,大众和风景可以自由地重新开始”(21)。
尽管史蝶飞并没有指出大众和风景重新开始了什么,但有两种可能性值得参考。首先,邱静美暗示了《黄土地》中的一种顽强存在——“简单的道家哲学通过肯定、否定文本的说和看来赋予、取消文本的权力。”(22)道家经典《道德经》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支持了电影对沉默和虚空的广泛使用,它使观众能够远离由现实政治宣传话语所引发的错觉,并在面对大自然的无声凝视中重建与真实的联系。胡敏娜(Mary Ann Farquhar)继而认为,“对《黄土地》的道家式解读提供了一种可以直接被看到和感受到的意义,这种意义超越了意象和文字。”(23)
其次,尽管第五代导演最初着迷于在自然风景中复现道家哲学,但他们最终关心的仍然是人间世界。正如爱森斯坦在风景中找到了传达情感状态和心灵体验的理想手段,张艺谋承认,他们创造出来的风景影像是用以捕获“坚韧的力量和民族的忍耐”:“来自纯朴底层的人们的呼泣……民族的命运,他们的感受,爱和怨恨,力量和弱点。”(24)通过无声的影像和其他先锋技术(25),第五代寻求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建构的历史和现实的新的真实意义,他们最终盼望成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历史的代言人。
因为历史的后见之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五代导演首先发现他们的电影观众是在海外而不是在中国国内(26),他们日渐增长的国际声誉很快削弱了他们借助壮观的风景重新定义电影真实的激进姿态。在《红高粱》(张艺谋执导,1987),这是1988年柏林电影节上中国电影首次获得金熊奖的电影,成功之后,自然和文化风景在国际银幕上呈现出不同的意义(27)。充满异国情调的文化图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第五代的作品中,充满色情意味的性欲也获得越来越多的突出展示。从《菊豆》(1989)到《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张艺谋的海外资助艺术电影对自然和风景的展示越来越少,相反,庭院和卧室这一类封闭空间则越来越多(28)。就像张艺谋的电影主角很快从造反者变为尊奉者,观众也被剥夺了主动性,并被诱惑进入一个貌似中华民族文化精髓这一类东方主义主题的华丽的梦幻展示之中。同时,自然风景在第五代手中甚至丧失了变革的力量,中国西部荒凉地区那令人眩晕的美丽风景,也只是提供了一个扮演献祭、欲望和失意的神秘故事的空洞舞台,就如《边走边唱》(陈凯歌执导,1991)中所刻画的那样,其故事的意义突出了民族寓言的层面。
第六代真实的心灵风景:捍卫个人感知
在1990年代初期,一代新的电影制作人开始质疑第五代和他们的模仿者所构造的文化传统的真实性(29)。例如,章明(1961年生)就哀叹当时电影制作中真实感的缺失,尤其质疑了诸如黄土地、高粱地和腰鼓这些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典型意符的“北方的旧物老事”在银幕上无休止的展示(30)。对刚出道的第六代而言,回归真实就是从历史回到现实,从乡村回到城市,从超重的象征回到变化的情境,从确定固化的自然风景回到游移模糊的心灵风景。
作为1990年代初期的领军人物,张元强调他当下的立场:“我拍电影是因为我关注社会问题和社会现实。”(31)对于张元和他的独立同事们来说,重新捕获真实的第一步就是直接从“真人真事”中引发灵感,就像他的首部电影《妈妈》(1991),影片表现了被冷漠的社会抛弃的患语言迟钝病的男孩和他那极为痛苦的母亲的真实生活。第二步是让真人表演他们自己的故事,就像张元在记录性故事片《儿子》(1996)中所跟踪的酗酒家庭。跟张元一样,王小帅在《冬春的日子》(1993)中表现了一对真实艺术家夫妇的生活,而在《极度寒冷》(1997)讲述了一个经过艺术虚构的真实故事,以一种纪录片风格再现了北京行为艺术家齐雷令人震惊的自杀事件。
的确,记录风格已经成为第六代电影的普遍特征。在《妈妈》中采用了镜头访谈之后,张元又在《北京杂种》(1993)融合进中国第一个摇滚歌手崔健的排练的纪实片段,这部电影立即使他在海外获得“中国被禁”的反叛的“非法”(outlawed)导演的称号(32)。然而,尽管他们有意采用纪录片技术以将自己跟之前几代导演区别开来,但是第六代的早期的电影并非是追逐真实本身的典型。就像第五代电影着迷于自然风景背后或之外的真实,第六代电影意图通过对城市影像的记录风格的呈现来传达某种具有精神深度的真实,某种心灵风景或心灵真实。
必须承认,真实是每一代新导演用来照亮自己崭新的道路的武器,但章明宣布他并不想要那种“像生活本来一样的真实”。他问道:“谁曾得到过真实?在艺术作品里面,真实本身永远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作者逼真的想象,他的态度、趣味、感觉和品格。”(33)章明坚持艺术家的想象和激情在重构真实方面的独立地位,这在当代中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贾樟柯同样主张,一部电影最重要的并不是真实本身,而是“呈现真实感”。他进一步断言,“真实感就不一定是直接获取的,有可能是主观想象的。”(34)毫不令人意外,贾樟柯“想象”一词回应了章明的说法,而贾樟柯的形容词“主观”则吻合了姜文(1963年生,著名男影星兼导演)的看法:“一个导演拍东西越主观越好”,因为“一切都是主观的,客观存在于主观里面。”(35)
对第六代而言,真实不可避免地经过主观视觉的过滤,他们电影中的风景因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心灵风景的投影(36)。以贾樟柯为例,他的故乡三部曲——《小武》(1997)、《站台》(2000)和《任逍遥》(2002)所想要传达的,是以一种他所理解或记忆的山西汾阳的真实的“生活状况”(37)。与此类似,章明在他的首部电影《巫山云雨》(1995)中所要捕获的,是他的家乡四川省巫山的“生命状态”的特征,这是“一种眼睛所不能见到却可以用精神去感觉到的真实存在。”(38)
第六代对真实的这种主观立场引发一种类似宣言式的表达,“我的摄影机不撒谎”,这可以用来概括这一群体关于真实的特征。这个表述首先来自于娄烨对自己的电影《苏州河》(2000)的出乎寻常的辩护。这部电影揭示各式各样的谎言、背叛、不可靠的记忆和理想主义的消失。然而娄烨声称,尽管电影缠绕着各种骗局、叙事悬念和视觉幻觉,但是作为一个导演,他并没有撒谎。毕竟,《苏州河》是作为一个纪录片计划而开始的,他想要记录下隐藏在上海全球化迷人表象后面、曾经极度污染的苏州河周边的人们生活的“真实面貌”(39)。尽管同时包含纪实和虚构的元素,娄烨还是认为,该片“能够准确地传达我对《苏州河》的真实印象。我的摄影机不撒谎。”(40)按照娄烨的表达逻辑,真实是由“我的印象”(视觉),“我的摄影机”(技术)和“我的真实”(文本)所构成。
在“我的摄影机不撒谎”这一表述中,最显著的位置“我的”是给予导演的,其真实感在电影表现和在促使心灵风景和自然风景的融合方面起到有力的作用。进一步说,贾樟柯和章明的关于状况或状态的真实感透露了真实是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变化的和多义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将其象征意义固定在自然风景中的本质。因而对第六代来说,真实的心灵风景是向矛盾敞开的。这就是贾樟柯为什么将《三峡好人》的地点(即三峡地区)的现实,描述为一个“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进步性和落后性,人的那种困难和人的乐观,人的生命力和人的生命的被压制”(41)的充满反讽、甚至荒谬的混杂共存。
作为一种特殊的真实的心灵风景,自然风景的多变性和多义性因而召唤着导演的创造性发挥。《三峡好人》中就有两个场景阐明了贾樟柯对自然风景和心灵风景的想象性融合。第一个场景是,男主角韩三明(贾樟柯的表兄,来自山西的煤矿工人)举起一张人民币,夔门峡作为民族风光印在钞票的一面,其背对的正是韩三明所看到的真实风景。本来韩三明最初看到的是钞票的另一面,上面印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慈祥面像,他诗人般地预见了“高峡出平湖”,由此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三峡发电工程。当韩三明翻过钞票时,现实背景以及钞票上的风景平行进入视线,我们不仅意识到长江的水位涨高了,而且意识到贾樟柯的创造性主要不在于视觉对比,而在于象征性地突出政治权力对自然风景的征服。由于得到政治和资本的援助,经济的发展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个地区的自然风景和文化风景,一百多万人迁徙他方,古老的文化也将从此消失。
第二个场景中,在韩三明困惑地看这已被改变的风景之际,一个闪烁的UFO(不明飞行物体)从夔门峡上空迅速飞过,似乎有感于大自然发生的巨大变化。贾樟柯插进的这一超现实的一刻起到了连结两个平行叙述的麻烦婚姻故事的作用。通过UFO的画面,银幕上的主角换成了沈红(赵涛),一位来自山西的护士,如同韩三明一样,由于这废墟中的风景而显得焦虑。《三峡好人》中的其它超现实片段还包括一座造型古怪的混凝土移民纪念碑,突然在无人观看的时候向火箭一样喷火起飞;还有一处是韩三明带着一群当地的工人前往山西去当煤矿工人,路上为眼前看到的一幕所惊呆:一个人影在一根悬于两栋正在拆毁的楼房之间的紧绷的钢丝上行走。
《三峡好人》中的这些超现实时刻满足了贾樟柯试图融合人物的心灵风景与正在消逝的自然和文化的意图:就如心灵风景是根据感知和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夔门地区的自然风景也处于流动之中。事实上,“流动的风景”不仅增强贾樟柯电影中一再出现的移动主题——正如罗伯特·科勒(Robert Koehler)所准确观察到,“流动性贯穿了贾樟柯的电影世界”(42),而且指明了第六代电影中不确定的、甚或模棱两可的心灵风景的一种普遍倾向。像他的同代导演挖掘“一种内爆式的反省”一样(43),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也选择了沉默寡言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沉默而拒绝给真实下论断,以此敦促观众去理解流动中的自然、心灵风景的信息。
不愿意通过语言下判断是第六代电影的普遍特征。即使他们能够借助电影影像为正在消失的自然和文化进行干预,但他们不再承担起民族发言人的责任。相反,他们主要关心个体真实感的探索,并将他们的个性视为区别于之前几代导演的地方。引用章明的话说:
我们就不应再是巴尔扎克的全景视点。我们不能什么都看见,什么都知道,我们不是民族的代言人。大全景的电影已经过时了……作为普通人,我们从人的内心往外看,站在具体人的视点,带着个人的品格、好恶和个人的局限性,这种真实性是难以掩盖的。(44)
并不令人惊讶,第六代在真实方面与人性的结盟驱使一些导演将他们的艺术心灵风景扩大到足以包容为数众多的普通人,尤其是贫困阶层,以保证他们在保留私人记忆方面有自己的声音,并重构处于全球化之中中国的多地性的民生风景。
独立导演的多地性民生风景:以私人记忆的名义
在《三峡好人》中,流动、废墟中的风景是通过移动中的人们的相互影响而描绘,这就使得电影的英文标题(Still Life,意为“静物”)具有反讽意味,因为夔门峡周围的原始风景,副有标志性的静物图像,也在政治和资本的侵袭下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民币上的象征符号就描述了上述发生的一切。在渡船上的一个魔术展中,魔术的力量和民族与全球流通的可交换性得到展示,而资本的跨国流通的影响则在移民劳动力的跨地流通的模式中被感知。在电影的开头,韩三明从山西南下到了即将被淹没的古老的河边小城奉节,成为当地一名拆卸废屋的临时工;到了电影快结束的时候,他正领着当地的工人往北前往山西,到那里,从生命时刻受到威胁的煤矿开采工作中可获得比在奉节危险的拆卸工作更高的收入。参照全球化时代中国正在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多地性(包括进一步往南的广东工业以及往东的上海中心),《三峡好人》暗示了一幅流动的民生风景,当地人不再能够留居故乡,而他们绝望的情感构成了以毁灭中的自然风景为镜像的荒凉而忧伤的心灵风景。电影中韩三明和他的前妻蹲坐在一栋被拆去一半的废房子的空荡荡的地板上,彼此沉默相对,这一幕阐释的正是这一双重风景(45)。
诚然,由于聚焦于缄默的人物,《三峡好人》呈现的一些心灵风景相当晦涩,而人物的情感只能靠间接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可与《黄土地》含蓄的风格相比美,后者靠无声的自然风景诉说着一切。有趣的是,贾樟柯在下一部电影《二十四城记》(2008)中,通过结合两种不同的纪录片方法——环境观察和人物访谈,抛开了他在《三峡好人》所采用的缄默风格。贾樟柯不再描述沉默的人物,而在八个扩展的访谈中让他的人物在镜头前说出他们的心事,其结果是脱离通常情况的口若悬河,是以唤起一副更加丰富的流动的民生风景来触动心灵风景。
贾樟柯将《二十四城记》设计为一部“充满话语的电影”,“一部回到话语的电影”,他承认,“我们就是想借助话语来透露记忆和过去。”(46)电影的标题指的是一个由一家真实的中国著名房地产公司华润集团开发的新楼盘,其原址是国营军工厂420厂,它成立于1958年,最近重组为成发集团。贾樟柯在《二十四城记》中想要保留的记忆涵盖这个社会主义机构的五十年历史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变迁,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呈现与420厂有关的几代人的个体证词。贾樟柯和他的团队联系了130个工人,并拍摄了其中50人的访谈。尽管他只用了当中五个真实的故事,电影还是成功地描述了多地性的民生风景:它的八个章节包括了工厂从东北的沈阳到西南的成都的大规模迁置及其工人和他们家庭的故事,以及旧厂房拆毁的那些痛苦日子和退休、下岗工人无法言说的困境。
贾樟柯对日常环境(如车间、办公室、公车、剧院和教室)采用一种类似纪录片的现场采访增强了真实感,他对旧厂房设备、危险的工作环境和拥挤的宿舍楼的观察镜头极大地增强了电影的真实效果和厚重的历史感。观众在一个紧接一个的近距离访谈中为访谈者私人记忆的辛酸叙述所迷惑,直到电影播到一半,他们突然认出退休的全国“三八红旗手”郝大丽(在1958年工厂从沈阳迁到成都的途中她三岁的儿子在奉节丢失),原来就是熟悉的影视明星吕丽萍(1960年生)所扮演。《二十四城记》原来不是一部纪录片,这种突然的发现为继续认出电影中其他明星的表演所进一步证实:陈冲(1959年生)扮演了以前的厂花,她来自上海,并通过业余表演流行于上海地区的越剧来保留她上海人的身份;陈建斌(1970年生)扮演了办公室副主任宋卫东,他对在那个全社会大范围匮乏的文革时代,他在420厂大院成长的幸运经历记忆犹新;还有赵涛(1977年生)扮演了时尚女性苏娜,她重述了父母在离开他们工厂的工作之后不幸福的生活,以及她自己作为一个在成都受到阔太太信任的高端产品“买手”的体面生活。陈冲因为同事们说她跟流行的战争电影《小花》(张铮执导,1979)中同名主角长得很像而兴高采烈,而事实上这一角色就是陈冲本人当年所扮演的。这一幕最好地说明了这种虚构和纪实的交织:当导演在幕外询问《二十四城记》中陈冲扮演的角色的名字时,这种虚构化的访谈片段坚持了它真实的表面价值,她说“我的名字叫顾敏华”,但这种回答并没有使《二十四城记》中的小名“小花”和陈冲在29年前扮演的另一个小花失效。
当然,人们也许会说,《二十四城记》中著名明星的表演,怀旧时代歌曲的非剧情使用(包括流行电影歌曲和音乐),以及引用中外诗人的诗句作为各章节标题,所有这些都凸显了这一貌似纪录片的电影的虚构性(47)。我认为对贾樟柯而言,虚构和纪实的混合是用来激发他的观众重新判断他们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淹没了人的认知和记忆的时刻的真实感知。新的商品房在以前420厂厂房所在地高高耸立。正如赵涛扮演的角色坐在她娇小的大众甲虫汽车中,背景深处就是作为全球化确切标志的摩天大楼,社会主义时期徘徊不去的记忆似乎与此格格不入。虚构的纪实提供了陌生化的有效方式,它鼓励观众跟随这八个人物的私人记忆,并从这些记忆中重构处于剧变中的中国的集体记忆。贾樟柯扼要指出,“我所拍摄的不是个人事情而是集体记忆。”(48)换句话说,《二十四城记》中,由镜头访谈所透露的个人心灵风景是刻意与转型期间巨大的民生风景粘合在一起的。
贾樟柯并不是通过纪录片方式来拍摄虚构场景以重构一种新的真实感的唯一实验者。早于《二十四城记》公映的两年前,应亮就推出了他的第二部剧情片《另一半》(2006),这是一部类似于纪实的虚构电影,完全由他的九十分钟电影工作室独立出品,并因为“它对立于绝望的那份宁静的安详、甚至快乐的意识”而受到海外影评人的欢迎,称它那种迷惑人的直接的拍摄风格“在现代电影史上很少有与之相似的”(49)。《另一半》对小芬进行跟拍,她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勤快的书记员,并通过她的观察提供了观察当代中国民生变化的珍贵的移动视角。很多当事人因为他们陷入困境的婚姻来寻求法律咨询,他们的案例从淘金者(年轻的妻子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想要和富裕的丈夫离婚)和家庭暴力(受虐的妻子由于法律保护军队婚姻而被禁止提出和她军人的丈夫离婚),到浪费青春(老婆婆急切地要与已经相处了大半辈子的、因包办婚姻而没有爱情基础的丈夫离婚)和小孩监护权(一位母亲没能力骗自己年小的儿子说前夫虐待孩子)。随着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加入这些在镜头前敞开她们想法的妇女,很明显,《另一半》隐藏了一种在一系列简短而生动的访谈特写中对广泛的社会问题进行报告的雄心勃勃的目标。随着镜头拍摄来自不同年龄群体和社会背景的人们讲述他们案例,不时还加上律师画外旁白的提示,观众逐渐开始接受一种正在发生并通过分段访谈所呈现的特殊的真实。
毫无疑问,《另一半》中的分段镜头采访增强了转型期民生风景的真实感,而当地一家化学工厂爆炸之后军警强制的撤退命令这段电视新闻片断有力地增强了电影的真实效果。此外,看不见的毒雾恰当地隐喻了受到像公共健康危害、环境污染、交通事故、失业、赌博、酗酒、早孕、卖淫、人口贩卖、抢劫和谋杀等如此广泛的社会问题感染的内陆城市(四川省自贡市)。电影还通过小芬自己面向镜头说话,并为她消失的男朋友——一个谋杀悬疑犯寻求法律咨询这一场景进一步模糊了虚构和纪实之间的界限。她的那个梦想着移民美国的妓女朋友的不适时谋杀死亡给小芬的命运投下了不祥的阴影。由于慢性哮喘,她最终在电影末尾瘫倒在空无人烟的桥上,来自她那位已经移居上海并在那里从事餐饮业的男朋友的手机留言铃声打破了这一座被众人遗弃、肃静得令人毛骨悚然的城市的长久沉默。
多地性是中国转型期民生风景的一个固有特点。与跨地性意味着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在地点之间的联系或运动所不同,多地性表明了多样的地点以及地点之间的不均衡状况,这类不均衡的产生是由于许多地点被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拖进跨地性,而且有些地点(包括这些地点的某些人)则可能被拒绝进入跨地性(50)。在《二十四城记》中,退休和失业的人们就是当地处于困境中的人,他们的有形存在正被新的摩天大楼所摧毁和取代,而他们的记忆也只能通过口头重构的方式来恢复。在《另一半》中,小芬在毒雾中倒下,他的男朋友则在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自她幼年就离家出走的父亲则在遥远的新疆边境工作。通过混合纪实和虚构,两部电影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将全球化中国重构为剧变中巨大的民生风景的独特方式。
结论:流动和移置中的真实
贾樟柯这样评论《二十四城记》:“我越是想记录,就越觉得需要虚构……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整合那些真实,才能整合这种最深层次的文化情感。历史就是真实和虚构共同形成的,历史不代表毫发无误的真实记录,历史是包含虚构的。”(51)换句话说,电影手法和技术不但对于重构和传播导演所认为的真实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他们重构一种建立在多地性和跨地性的个体的众多故事基础上的历史。这种历史有着丰富的私人记忆和情感,并最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产生了的集体想象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于电影真实有着完全不同的各种理解,但在后毛泽东时代的银幕上,电影真实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大部分影片中,它不再是来自于上层所下达的旨意,而明显地是由下层所自发构成。在1980年代,真实是被假定为一种形而上的本体,并被具体化为自然风景,以与现实政治的城市中心保持距离,这种距离使第五代能够寻回民族文化历史的影像。在1990年代,真实被定义为一种存在主义的状态,并内化为城市青年人不断变化的心灵风景,这些年轻人的挫败和追求使第六代能够想象出不断被疏离、沉思、叛逆和重合所打断的真实生活的临时状态。在2000年代,真实能够在口述过去和现在的记忆的表演过程中被发现,这些个人的记忆在表现快速变化的社会所留下的历史痕迹的观察影像中得到了回应,这种观察影像被独立电影导演呈现在一系列转型期民生风景中。
饶有意味的是,虽然中国的独立导演一直坚守他们对真实的主张,但他们却极少谈论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realism)的论题。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在中国几十年里为官方所认可的概念,带有陈词滥调和宣传鼓吹的消极内涵(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另一个原因是,与其受某种审美的表现模式所限制,独立导演宁可保持他们对于真实的感知和表现的创造性,融合各种不同的表现方法,而不是将它们分为相互冲突的或不相兼容的(如《三峡好人》中的纪实和超现实两种方法的融合),并利用各种电影类型和技术,包括动漫场景,如《世界》(贾樟柯执导,2004)。对于他们来说,真实不仅仅存在于流动中,而且也存在于移置之中。虽然有些学者还是从现实主义方面来讨论中国独立电影的制作问题(52),但我相信,年轻导演们之所以一贯偏爱“真实”和“纪实”(纪录真实),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这两个概念中维持一个他们能够最好地表达他们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观点的想象空间。他们对真实的偏爱远远盖过现实主义,这使得他们能够并将继续有能力重构不同电影的自然风景、心灵风景和民生风景。
本文提交于2010年6月广州暨南大学举办的世界华语电影研讨会,由郑焕钊翻译自英文,作者自校。感谢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聘作者为兼职研究员。
注释:
①Epharaim Katz,The Film Encyclopedia,2[nd] edition,New York,HarperCollins 1994,pp.854,p.927.
②Nitzan Ben Shaul,"Morphing Realities:Current Status of the Real in Film and Television",Framework,2008,Vol.49,Issue 1,p.48。沙乌尔引用波德里亚这个论点:“经验客体……并不是别的,而就是客体周围各种关系和不同意义聚合以及环绕的结果”。参见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St.Louis:Telos,1981,p.155.
③Stella Bruzzi,New Documenta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Routledge,2000,p.4.
④Thomas W.Benson and Carolyn Anderson,Reality Fictions:The Films of Frederick Wisema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9.
⑤谢晋的电影事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⑥关于银幕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见张英进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London:Routledge,2004,pp.202-205。另可参阅这个观察:“官方的现实主义电影走向其对立面,走到了现实主义的边缘,遗忘了现实主义的批判是质疑已经确立的传统和现实的潜能和能力。它不再是真实的、并且已经脱离了社会的现实状况。”见Ban Wang,"In Search of Real-life Images in China:Realism in the Age of Spectacl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8,Vol.17,Issue 56,p.498.
⑦关于民俗电影,见Yingjin Zhang,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2,pp.207 239。
⑧“独立导演”指的是那些完全或大部分依靠私人(即非国家)投资生产电影的艺术家,他们有时也可能在名义上获得官方机构的厂标。见Yingjin Zhang,"My Camera Doesn't Lie? Truth,Subjectivity,and Audience in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Paul G.Pickowicz and Yingjin Zhang,eds.,From Underground to Independent:Alternative Film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6,pp.23-45。近来的国产大片包括《无极》(陈凯歌执导,2005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执导,2006年)。
⑨Arjun Appadurai,Modernity at Large: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33.
⑩关于政治、资本、艺术和边缘性的互动,见Yingjin Zhang,Cinema,Space,and Polylocality in a Globalizi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2009,pp.43-47.我在英文中同时使用“truth”和“the real”来表示“真实”,这是第六代导演和独立导演的关键概念,虽然我更倾向用“the real”,因为它具有知觉概念上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而“truth”则暗示了一种固化的定义。
(11)跟西方不同,中国早期虚构电影并没有对自然风景有多太投入,见Peter Rist,"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Landscape in Silent East Asian Films",in Martin Lefebvre,ed.,Landscape and Film,London:Routledge,2006,pp.189-212.
(12)Sergei M.Eisenstein,Nonindifferent Nature,trans.Herbert Marsha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217.
(13)(14)Lefebvre,ed.,Landscape and Film,p.xiii,p.xv.
(15)Simon Schama,Landscape and Memory,New York:Vintage,1996,p.61.
(16)(17)(18)(19)(24)Geremie Barmé and John Minford,eds.,Seeds of Fire: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New York:Hill and Wang,1988,p.259,p.259,p.261,p.267,p.259.
(20)(21)Stephanie Donald,"Landscape and Agency:Yellow Earth and the Demon Lover",Theory,Culture & Society,1997,Issue 141,p.111.
(22)Esther C.M.Yau,"Yellow Earth:Western Analysis and a Non-Western Text",Film Quarterly,1987-1988,Vol.41,Issue 2,p.32.
(23)Mary Ann Farquhar,"The 'Hidden' gender in Yellow Earth",Screen,Summer 1992,Vol.33,Issue 2,p.164.
(25)Xudong Zhang,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Cultural Fever,Avantgarde Fiction,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246.
(26)Bonnie S.McDougall,The Yellow Earth:A Film by Chen Kaige with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Filmscript,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1,pp.25-130.
(27)关于《红高粱》的分析,见Zhang,Screening China,pp.208-220.
(28)Wendy Larson,"Zhang Yimou:Inter/National Aesthetics and Erotics",in Soren Clausen,Roy Starrs and Anne Wedell-Wedellsborg,eds.,Cultural Encounters-China,Japan,and the West:Essays Commemorating 25 Years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Aarhus,Aarhus,Denmark: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5,pp.215-226.
(29)类似自然、民族风景的例子包括《黄河谣》(滕文骥执导,1989年),《五魁》(黄建新执导,1993年)和《二嫫》(周晓文执导,1994年)等。
(30)(35)(37)(38)(39)(40)见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生于1961-1970)》,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1页,第77页,第362页,第25页、第34页,第258页、第265页,第265页。
(31)Bérénice Reynaud,"New Visions/New Chinas:Video-art,Documentation,and the Chinese Modernity in Question",in Michael Renov and Erika Suderburg,eds.,Resolutions:Contemporary Video Practic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236.
(32)David Chute,"Beyond the Law",Film Comment,1994,Vol.30,Issue 1,pp.60-62.
(33)章明:《找到一种电影方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34)贾樟柯、饶曙光、周涌、陈晓云:《三峡好人》,《当代电影》,2007年第2期,第24页。
(36)比较王斑的说法:“被赋予了纪实美学和社会信息的故事片能够更好地见证历史,见证当下的自然风景和心灵风景。”见Wang,"In Search of Real-life Images in China",p.503.
(41)贾樟柯等:《三峡好人》,第19页。
(42)Robert Koehler,"The World",Cincaste,2005,Vol.30,Issue 4,p.56.
(43)将反叛视为一种内爆式反省,见Zhang,Cinema,Space,and Polylocality in a Globalizing China,pp.61-64.
(44)章明:《找到一种方法》,第9页。
(45)《三峡好人》的政治、资本和劳动力方面的详细讨论,见Y.Zhang,Cinema,Space,and Polylocality in a Globalizing China,pp.94-98.
(46)Dudley Andrew,"Interview with Jia Zhangke",Film Quarterly,Summer 2009,Vol.62,Issue 4,p.80.
(47)有人称《二十四城记》为“演纪录片”,见张赞波:《〈二十四城记〉:贾樟柯完整的影像实验》,《电影艺术》,2008年第6期,第56-58页。
(48)Andrew,"Interview with Jia Zhang-ke",p.82.
(49)第一个引文来自Variety杂志,第二个引文来自Richard Brody在The New Yorker上的文章。两段引文都选印在由美国Generate Films公司发行的该片的DVD封背上。
(50)关于跨地性和多地性的进一步区别,见Y.Zhang,Cinema,Space,and Polylocality in a Globalizing China,pp.6-9.
(51)吴冠平:《寻找自己的电影之美:贾樟柯访谈》,《电影艺术》,2008年第6期,第74页。
(52)关于“纪实现实主义”和“图像现实主义”,见Wang,“In Search of Real-life Images in China”,pp.497-512;关于“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见Jason MeGrath,Postsocialist Modernity:Chinese Cinema,Literature,and Criticism in the Market Ag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29-164.麦杰生将贾樟柯的“纪实的方法”(见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第357页)翻译为“this realist method”(这种现实主义方法),与原文有相当的差距,因为“纪实的”跟“现实主义的”其含义并不相同。
标签:风景论文; 三峡好人论文; 第六代导演论文; 二十四城记论文; 贾樟柯论文; 黄土地论文; 苏州河论文; 韩三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