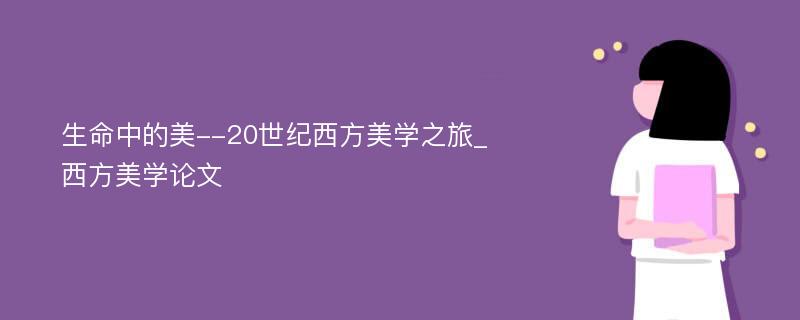
美来自生命——20世纪西方美学巡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生命论文,世纪论文,美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的美学是理性的美学,理性的美学对来自人性中的生理的因素是蔑视的。“美”总是拖着把生命的胴体埋伏得严严实实的长裙彬彬有礼地向我们微笑,似乎她永远高居于世俗人情之上,没有烦恼,没有忧伤,自由自在,让人把握不住,捉摸不定,因为她没有任何目的,居无定所。
18世纪博克从人的生理——心理机制谈美和崇高的区别,认为美与人的爱的本能有关,崇高与人自体保存的本能有关,被指责为“把社会的人几乎降到动物的水平”。(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48页。)康德在谈崇高时, 很明显地强调了人的生命和生命在审美过程中的变化,但是,康德思想的精神面被后人突出了,而对生命的关注与体验,却被相当长的历史所忽略。19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美是生活”,被批评为是在“人类学原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美学,往往陷于“纯粹生理学的说明”,(注:参阅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60~564页。)叔本华强调“意志”,这明显来自生命冲动的东西被人们不断理解为“唯心主义”的精神性的东西,而其中所含的物质生命的特点却被哲学史和美学史不屑一顾。尼采的“强力意志”更含有强烈的生命意识,但几乎一直被掩埋在人们给他的“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标签之下。
我们看不见达尔文,看不见生命的蛹动对美的制约,看不见生命中的爱与死在美学的殿堂里占有什么样的位置,看不见米开朗基罗男人体的骠悍,乔尔乔内、安格尔女人体的柔媚何以会闪射出那样夺目迷人的光芒。一面人类理性的伦理道德的墙,罩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对美的真谛的认识总是隔着一层推不倒的障碍。
打开20世纪西方美学的门户,一股股劲烈的生命之风习习吹来,人类真是按照理性来审美和创造美的吗?更进一步论,人类真是按照理性来行动的吗?许多现代派艺术回答,不一定!许多审美经验回答,不一定!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学理论在回答这个问题。
一
乔治·桑塔亚那是美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也是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他是20世纪上半叶主要流行于美国的自然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自然主义哲学继承的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传统。它试图超越旧有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标榜哲学上的“第三条道路”。在哲学上,桑塔亚那反对黑格尔把人类的思想史描绘成精神的自我发展史的做法,而把人类的各种精神活动严格地置于生物学的基础上加以描述,以此来调和传统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在他1896年发表的美学专著《美感》中,提出了“美是在快感的客观化中形成的,美是客观化了的快感”(注:《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的著名观点时,就提出了“人体的一切机制都对美感有贡献”(注:《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3页。)的思想。他说:“人体是一部机器,凭借某些机能组合在一起,新陈代谢,乍看起来是不觉得的。然而,这些基本过程一有什么重要的紊乱,都会立刻在意识上引起巨大的、痛苦的变化。即使轻微的变化也决不会没有意识上的反应;我们心灵的性情和情调,我们激情的力量,我们习性的牢固和持续,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想象和情绪的活跃,都是由于这些生命力的影响。也许它们并不构成任何一个观念或感情的基础,但是它们却是决定这一切存在和性质的条件。”(注:《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他的逻辑关系很清楚,人的感情由生命决定,而美由感情的客观化决定,生命对美有着根本的制约作用。1905年,桑塔亚那发表的又一美学新著《艺术中的理性》,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这个观点。他突出地强调了艺术与本能的关系,甚至把筑巢的鸟和创造艺术的人类相提并论,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使人这样生物性的冲动得以实现,也就是得到快乐,所以艺术是使人愉快的最好手段。当然他同时也强调理性是艺术和愉快这两者的原则,但是他所谓的理性,无非是“变得有思考有见识的本能。”对于艺术创作中经常显示的“无目的”性,他说:“艺术和本能一样是不自觉的,如同亚里斯多德注意到的,通常它并不完全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因为那些遗传下来和存在于天生的结构中的本能,必须节省地和深入地组织起来,如果它们出了大毛病,就造成一种既不可能摆脱,也不可能忍受的负担。……因此,生命的更高级的产品总是无缘无故的。”(注:蒋孔阳、朱立元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美和艺术的根基在于生命。
二
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是名震天下的人物。他是从精神分析学说涉足审美和艺术理论的。1895年,弗洛伊德与布劳尔合作,出版了《歇斯底里研究》。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的诞生。1900年,他出版《释梦》,1904年,他出版《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之后连续出版了《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图腾与禁忌》、《快乐原则之外》、《自我和本我》、《幻想的未来》等搅动世界思想界的名著。弗洛伊德认为心理活动有生理的基础,“弗洛伊德的目的,在于了解人的激情,就是从前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而不是心理学家或神学家所关心的激情。弗洛伊德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时关于内分泌对于精神的影响所知甚少,生理与心理相关的现象有一种是人所熟悉的,那就是性。如果我们认为性是一切内驱力的根源,那么生理上的要求就可以满足,精神力量、生理基础也可以被发现了。(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页。)弗洛伊德说:“我们以为先将本能区分为两大类, 使相当于人类的两大需要——即饥和爱,想必不至于有重大错误,我们在其他方面,虽不愿使心理学依存于他种学科,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下面一个生物学的事实,就是生物个体服务于自存及传种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似各自独立,其起源也各不相同,而就动物而言,其利害更常相冲突。我们在这方面实即讨论生物学的心理学,而研究生命历程的心理的附属物。”(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页。)在弗洛伊德这里,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那种超物质性荡然无存。正是从生命出发,弗洛伊德揭示了普遍存在于人而又被人类“理性”熟视无睹的心理现象——潜意识。这种潜意识是人的本能需求受到人的理性所压抑,返回从本能到意识的中间地带贮藏起来,它或者使人生病,或者通过梦或艺术的方式得到渲泄或升华。艺术,实际上就是人的潜意识升华的产物。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主要讨论的是性。正是因为他讨论了人人都关心而又不便言及的性的问题,他才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排除他讨论的具体问题,我们发现他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精神活动,实质上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产物;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是生命需要得以满足以实现平衡,保证健康与生存的手段。这个思想,对西方美学的影响即使不是明显的也是潜在的,但是是十分有力的。弗洛伊德撕开了披在人身上那层遮羞的“理性”和“社会性”的面罩,让人们看清了,自己原来是一个蛹动着无数细胞,创造着不竭的欲望的生命。人的任何高贵的品质,都是从这堆物质里出来的。他说:“生活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太艰难了;它带给我们那么多痛苦,失望和许多难以完成的工作。为了忍受生活,我们不能没有缓冲的措施,……这类措施也许有三个:强而有力的转移,它使我们无视我们的痛苦;代替的满足,它减轻我们的痛苦;陶醉的方法,它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迟顿麻木。……科学活动也是这类转移。代替的满足正如艺术所提供的那样,是与现实对照的幻想,但是由于幻想在精神生活中所担负的这种作用,他们仍然是精神上的满足。……陶醉的方法作用于我们的身体,并改变它的化学过程。”(注:弗洛伊德《论升华》,转引自蒋孔阳、朱立元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第395页。 )三项方法艺术和审美占了两项:“代替”和“陶醉”。而科学,不过是疲劳战,使我们忘却痛苦。这说明美在人类的生存中是何等重要。弗洛伊德常常把美与性相联系,有时牵强,但有时,却论得比较精彩。“生活中的幸福主要得自于对美的享受,我们的感觉和判断究竟是在哪里发现了美呢——人类形体和运动的美,自然对象的美,风景的美,艺术的美,甚至科学创造物的美,……美的享受具有一种感情的,特殊的,温和的陶醉性质。美没有明显的用处,也不需要刻意的修养。但文明不能没有它。……看来,所有这些确实是性感领域的衍生物。对美的爱好象是被抑制的冲动的最完美的例子。‘美’和‘魅力’是性对象的最原始的特征。”(注:弗洛伊德《论升华》,转引自蒋孔阳、朱立元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第397页。)
三
柏格森是从反对唯理主义角度切入生命问题的。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大步发展,因此刮起了持久的理性主义旋风,“知识就是力量”,一切事物都要经过理性的检验、科学的实验来得出判断。柏格森从文学与人的生命的关系这个角度指出科学不能包打天下。他宣称科学和逻辑不能透入实在的外表;在生活和运动面前,概念思维无能为力。概念思维最能适应在死寂、静止的世界中,在由机械性统治的惰性物质世界中运用。科学所向往的,是一种静态的物质世界,它把流动的时间化归为空间关系;在它看来,绵延、运动、生命和进化不过是虚构,对它们都作机械的解释。柏格森提出生命现象来反驳唯理主义观点,他指出,生命和意识不能从数学、科学和逻辑方面来探讨,用通常数学——物理方法根本无法理解它们。“宇宙中有类似诗人创造精神的东西,一种活生生的推动力,一种生命之流,这种生命之流是数学才智不能掌握的,只能由一种神圣的同情心,即比理性更接近事物本质的感觉所鉴赏。”“我们只能通过直觉的能力来了解实在的、‘变化的’和内在的‘绵延’,生命和意识。”(注: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51页。)就是说,生命是一种割不断的流, 把它切断就不是活的生命而成了死的尸体或尸体的局部了,任何分析都不对了。柏格森认为,整个世界是体现着“生命的冲动”的一种“创造的进化过程”,而静止的物质不过是这种过程的中断,是“生命冲动”的障碍物。因此,要认识和把握“实在”,就不能靠静止僵死的解剖分析,而只能靠直觉。只有直觉才能本能地、直接地,整个地把握生命的精神实质,并进入“意识”的深处。柏格森正是强调生命的运动变化,反对用经验和理性的方法来认识世界,才把直觉放在“唯一能认识生命的方式”位置上。而直觉的真正所在之处就是艺术。艺术实质上仅仅是对艺术家的生命的精神体验的认识。这就把艺术和人的生命之流统一起来了。我们欣赏艺术实际上是在观看艺术家的生命之流。他说:“艺术家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和他们共享这种如此丰富,如此具有个性,如此新颖的感情,并使我们也能领受他所无法使我们理解的那种经验。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在他的感情的迹象中选择那一部分,它容易使我们一见之后,便引起对它做机械的模仿,即使这模仿是轻微的,结果就把我们立刻转到产生这种感情的心理状态中去。这样,就可以打破时间与空间在艺术家与我们的意识之间所造成的疆界。我们将会发现,艺术家在感觉的范围内带给我们的观念越丰富,孕育的感受和感情越多,这样表现出来的美就越深刻,越高尚。美感所具有的连贯强度就这样和我们内心发生的变化状态相一致,其深度也就与我们在根本的感情中朦胧看到的初级精神现象的多少相一致。”(注:蒋孔阳、朱立元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就是说,艺术家展现他的生命之流, 我们通过模仿和转换,变为我们的生命之流,获得多少不等的美感。观念、感情越多,美感越强烈。“小说家可以堆砌种种性格特点,可以尽量让他的主人公说话和行动。但是这一切根本不能与我在一刹那间与这个人物打成一片时所得到的直截了当、不可分割的感受相提并论。有了这种感受,我就会看到那些行为举止和言语非常自然地从本源中奔流而出,它们就不再是一种附加在我对这个人物所形成的观点上面,并且不断地充实这个概念,却永远不能达到完满地步的东西。我就一下子得到了这个人物的全貌。”他认为,“描述,历史和分析只能让我们停留在相对的事物中。唯有与人物打成一片,才会使我们得到绝对。”(注:蒋孔阳、朱立元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这就是说,柏格森认为, 如果我们不通过直觉展现我们的生命之流,我们创造不出艺术,如果我们不使自己的生命之流汇入作品中人物的生命之流,我们无法欣赏作品。那么,很明显,美也就存在于这生命的绵延与流动之中了。
四
30年代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对唯理主义旧哲学深恶痛绝,紧扣人和人的生命来讨论美的问题。1934年他出版的《艺术即经验》一书,在西方一直产生着长时间大面积的影响。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詹姆斯提出,说“凡是合理的”就是实在的,这不对,凡是为人所经验的才是实在的。(注: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0页。)他认为,“如果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 都由原始星云或无限的实体而来,那么,道德责任,行动自由,个人努力和愿望会怎么样呢?的确,需要,不确定,选择,新奇事物和奋斗会怎么样呢?无论是把绝对的实体看作是宇宙物质或宇宙精神,在它手里个人不会变成一纯粹木偶吗?这种体系不能满足人的本性的一切要求,因此不可能真实。关于一种理论、信仰和演说的检验,必须是它对我们的影响、它的实际结果。这就是实用主义检验。”(注: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38~339页。)就是说,人的思想行为,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人不是由“宇宙物质”或“宇宙精神”支配的木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詹姆斯认为,真理的标准在于对人类是否有用。杜威发挥了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观。他把思维看成是消除现实和愿望之间的冲突的工具,即实现人的愿望,使那意味着满足、实现和幸福的事物得到安排的手段。如果我们所形成的观念、观点、概念、假设和信念成功了,达到协调和适应的目的,我们称之为真实的。“成功的观念是真实的。”(注: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4页。 )“思维为人的目的而服务,有用处,能消除冲突,满足欲望;它的效用,它的目的论,就是真理。”(注: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5页。)在杜威看来, 没有绝对客观的让人不掺合主观意识的事物。“事物是为人所检验的那样被认知的东西,但是它们在美学、道德、经济和工艺方面为人所经验;因此要恰当地论述任何一事物,就要指出那事物为人所经验的情形。这是直接经验主义的基本公设。”没有人经验过的事物,是不可知的事物,就不是真实的事物。把这个哲学观点运用在美学中,杜威特别强调经验在艺术和审美中的核心作用,而杜威所指经验又主要是指人的生命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矛盾与协调。所以,在他的美学观点中,艺术、美,与生命扣得很紧密。杜威说:“经验是有机体在客观世界中进行斗争、取得成果、完成使命,因此,经验也是艺术的萌芽。即使是原始的,初级的经验,它仍然包含了可以获得愉快感受的希望,那就是美的经验。”(注:蒋孔阳、朱立元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 342页。)就是说,美的经验是生命有机体在求生存的过程中获得的愉快的经验。所以他反驳说,“一种意见认为,把艺术与美感经验联系起来,标志着贬低艺术与美感的意义与尊严,这纯系出于无知。正是经验所具有的确实程度,使经验具有了强化了的生命力。”(注:蒋孔阳、朱立元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 342页。)杜威认为,获得愉快的经验是人与客观生存条件的协调或和谐,这种协调或和谐就是美。他说:“只有通过某种方式与外界环境取得妥协时才能得到内在的和谐。”(注:蒋孔阳、朱立元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页。)他指出, 生命存在各种需要,“例如对新鲜空气或食物的需要,表明我们有所缺少,表明至少暂时未能与周围环境充分协调。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一种要求,要求进入环境中去,补足这种缺少,也就是通过建立至少暂时的平衡,以恢复协调。生命本身由许多阶段组成,在各个阶段,有机体与周围事物会产生不协调,后来由于努力或出自偶然,恢复了一致。然而在生命的发展时期,恢复不仅仅意味着回复到原来的状态。因为胜利地通过了不协调状态及其阻力已经丰富了恢复的内容。如果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差别太大,生物就要死亡;如果暂时的不调和未能增强生物的活力,生物就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如果暂时的不协调只是一种过渡,使有机体的力量与它的生活环境的力量取得更为广泛的平衡,那么生命就会发展。”杜威认为,正是这种生命与环境的从不协调到协调,从不和谐到和谐的关系,“触及了经验中的美的根本问题。”(注:蒋孔阳、朱立元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340页。)就是说,生命存在有各个不同的阶段,当它从不协调的痛苦获得了协调,便产生愉快或幸福的经验,这种愉快和幸福的经验是一种美的体验。他说:“通过偶然的接触机会与刺激,可能获得乐趣,这样获得的乐趣在充满痛苦的人间是不应该受到鄙视的。”当然,人不同于动物,在人的意识中,过去、将来与现在往往同时受到经验,“由于我们常常不考虑现在而考虑过去与将来,他对过去的记忆与对将来的期望加入经验之中,这样的经验就成为完整的经验,这种完整的经验能带来的美好时期便构成了理想的美。只有当过去不再困挠一个人,而将来会发生的事也不致使他不安时,这个人才有可能与周围环境真正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活生生的人。在一些时刻,过去加强着现在,而将来又是现在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时刻正是艺术所特别强调歌颂的。”(注:蒋孔阳、朱立元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342页。)在杜威这里,我们完全看不见黑格尔抛射的那种悬空的“精神”的气球,美存在于实实在在的人的生命过程之中,只是,当人从过去到将来都与环境水乳交融地协调,才是理想的美,而这种理想的美,只有在艺术中能够发现。
五
本世纪50年代前后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哲学和美学,其基础也是放在人的生命存在之上的,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对生命的关注尤为明显。海德格尔是从人的存在来思考“存在”这个哲学的基本概念的。他把人的“存在”称为“此在”,他认为,只有“此在”,通过自身的体验和行动才能够将“存在”显示出来。离开了“此在”,哲学本体论问题就不能说明,离开了人的存在,整个世界就不存在。海德格尔说:“具有生存方式的存在物,就是人。唯有人存在。高山是有的,但它不存在。树木是有的,但它不存在。马是有的,但它不存在。天是有的,但它不存在。上帝是有的,但它不存在。‘唯有人存在’这个命题,决不是说:只有人是真正的存在物,而一切其余的存在物不是真正的存在物,只不过是人们的假象或想象而已。‘人存在着’这个命题是说: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这种存在物的存在是通过存在的无遮蔽状态的敞开的内在性,从存在出发,在存在之中标志出来的。人的生存本质,是人之所以能想象存在物为一存在物,并能对所想象的东西具有一个意识的根据。 ”(注:《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 《哲学译丛》1964年第2期第47页。转引自陈炎《反理性思潮的反思》第212页。)这就是说,只有通过对人自身存在过程的体验才能真正认识“存在”。而其他的事物都无法揭示“存在”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事物,但不昭示“存在”。
而人的生命是流动变化的,其生活内容是无法预知的,人生没有模式。怎么能从变化的人生来把握“存在”呢?因为人生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死亡”。“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向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为此在开发出它的最本己的能在,而在这种能在中,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存在。”(注:《存在与时间》第315页, 转引自陈炎《反理性思潮的反思》第212页。)就是说, 人是在面对死亡的过程中展开自己的“可能存在”。这种可能存在,尽管千变万化都不过是生与死之间的变化。这就是存在的本质。所以,海德格尔认为,人只有在畏惧、焦虑、死亡状态中才能真正领悟到自己的存在,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得不畏惧死亡,因为只有自由地去死,才能赋予存在以至上的目标。要么就借助宗教和上帝的力量来抗拒畏惧。而艺术的美,就是要揭示人的这种状态。比如梵高画的一双农鞋,“从农鞋内部磨损了的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者步旅的艰辛。在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的农鞋里,显示着在寒风凛冽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一的田垅上的脚步的艰韧和迟缓。鞋面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当暮色降临之际,这双鞋底在田野小路上踽踽而行。在这鞋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弥漫着对于面包来源的无怨的焦虑,以及一再战胜了贫困的无穷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迫近时的战粟。”(注:海德格尔《诗歌·语言·思想》英文版第33~34页,转引自陈炎《反理性思潮的反思》第219页。)一双丑陋的农鞋,本来不具有什么美感, 但海德格尔把它与穿鞋的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与人的生存斗争联系起来,立时就展现了它的美的光彩。
比之于海德格尔,萨特更注重人的精神自由。但他的“精神自由”,明显是以物质存在着的人生命的人的存在为前提的。黑格尔的“精神自由”不依赖于肉体存在的人,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存在。萨特把“自由”的权利交给了现实存在的人自己,当然同时也就使人肩负起了“自由”所带来的责任。萨特把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区别开来,人是“自为的存在”,自然是“自在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其所是”,是必然的,而“自为的存在”却“是其所不是”或“不是其所是”,因而是自由的。就是说,自然的东西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它是一生下来就被设定了的。而人则不同,人是“存在”先于本质,即肉体存在先于社会本质。人仅有肉体存在还不能说是人,只有产生了社会行为,才能说是人。人的肉体存在只是一种动物存在,它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是一种“虚无”,然后他通过他的行为显示他的本质,他做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人命定是自由的。(注:《存在与虚无》第565、670、698及701页。参阅自陈炎《反理性思潮的反思》第240页。 )而人的“自由”又是通过人的一个一个人生选择来实现的。无论做什么,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不选择也是一种权利,那是你选择了“不选择”。因此,对人而言,能够实现其自由选择是美的,阻碍实现其自由选择是丑的。众所周知,萨特所说的“选择”自由只能最大限度地在想象中现实,而想象的产物艺术品就是有了较高的审美价值的。虽然萨特的自由理论是一个怪圈,无论怎么样绕圈子,都通不过现实存在的人要生存要死亡这一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尽管萨特强调主体意识,强调想象,他的意识是以承认现实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的。萨特很清楚,任何一个自由的人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因而不可能不受客观处境的条件限制。为此,他专门从“我的位置”、“我的过去”、“我的周围”、“我的邻人”、“我的死亡”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客观处境对主体自由的限制。比如,人的出身和人的生理条件对人的选择的限制,“事实上,由于别人涌现,一些在我并未选择的情况下我所是的某些规定便显现出来。实际上,我在这里不管是作为犹太人或雅利安人,不管是美的还是丑的,还是独臂的,等等,所有这些,我都是为他的,并没有希望领会这种我外在地具有的意义,也没有希望拥有更充足的改变它的理由。”(注:《存在与虚无》第565、670、698及701页。参阅自陈炎《反理性思潮的反思》第249 ~250页。)但是,萨特坚持说, 这一切并不能妨碍我们在伦理意义上的自由选择。再比如“死亡”。每人必死,这是海德格尔早已论定的。但是萨特认为,“死亡”作为一种非现实的处境,也不可能妨碍人的自由。因为尽管死亡作为人的将来,而且是唯一的将来,是所有结果的结果,是一切自为的否定,但死亡和生是一样,是偶然的,荒谬的。“于是我们应该得出与海德格尔相反的,结论即死不是固有的可能性,它是一个偶然的事实,作为事实它原则上脱离了我们,而一开始就属于我们的散朴性。”“由于死总是在我们的主观性之外的东西,所以它在我们主观性里没有任何地位。”(注:《存在与虚无》第565、670、698及701页。参阅自陈炎《反理性思潮的反思》第250页。)我们看出, 萨特极力想“超越”或绕过这些人生的限定而使其“自由选择”理论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他没有否认或无视人的生命存在。正因为他费尽心力想超越或绕过人的生命存在这道门槛,反而使这道门槛显得那样清晰、那样稳固、那样不可逾越。
六
20世纪的哲学家、美学家,要想象柏拉图、黑格尔那样在绝对精神的殿堂里构筑美的体系,已经不可能了。正如萨特所说:“他们想不到去严肃的思考也就算了,思想遮敝了人,而我们感兴趣的只有人。”(注:蒋孔阳、朱立元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佐说得更明白:“ 人类是生命的存在。无论哪种社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这都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的命题,而由于不同的时代、民族、国家,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也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相信,要想象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生活,首先当然应该从人类是这种生命的存在这一点来考虑问题。而且我认为,人类正视这一点,才是建立一种现代所需要的普遍价值观念的出发点。”(注:汤因比、池田大佐《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0页。)从池田大佐的话生发开来可以说, 人类只有从人是生命这一点来考虑问题,才可能真正揭示美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