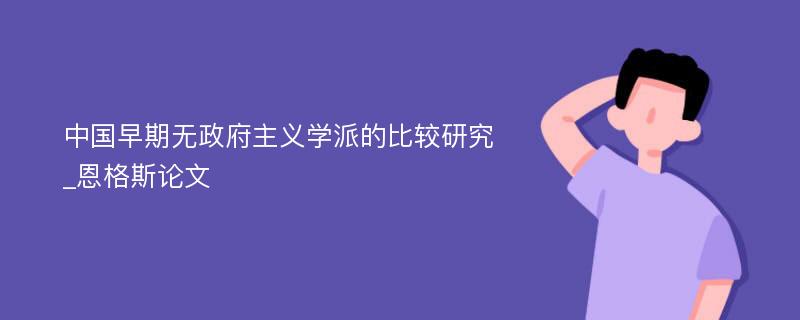
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流派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政府主义论文,流派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27(2000)01—0067—04
中国史上首先吸收、接受、并打出无政府主义旗号的是中国留日、留法的部分学生。他们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1907年留日中国学生创办《天义报》、留法中国学生创办《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这是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产生的标志。
同时出现在东京的天义派和巴黎的新世纪派,在其宣介无政府主义的活动中,展示了他们各自相异的多彩侧面。比较这两个派别的不同特点,我们将会看到文化传播的内在历史逻辑。它既是民族文化兴趣对新文化接受的触角,又是外来文化携有的自身社会印痕与中国传统文化交互影响、在社会中构成不同文化解释、派别分歧的写照。本文试对天义派、新世纪派在宣介无政府主义思想时的不同表现及原因作一探讨。
第一,天义派在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间作了区别,在中国最早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作区别比较的,大概应属天义派。天义派的代表人物刘师培认为:“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可分为两派,都是当今欲改造世界者。又分析说:社会主义仅重财产平等,承认权力集于中心,不废支配机关国家,由于支配权“仍操于上”人们仍会失去平等权、自由权,这是社会主义不如无政府主义圆满之处。(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有鉴于这种认识,他在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时,就标明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
《新世纪》派在宣传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时,往往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如李石曾在其《革命》一文中宣称:“社会主义,一言以毕之曰自由、平等、博爱、大同。欲致此,必去强权(无政府),必去国界(去兵)。(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天义派在表达自己所主张的言辞上采用过无政府说、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则主选“社会主义”一词来传达心声。“社会主义,以无政府冠其前,亦非根本之名辞,因能使无政府者惟教育之力也”,论者在反复推敲后,认为用“无政府教育的社会主义更为确实”。(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与天义派一样,新世纪派对自己的学理解释也不是众口一辞,只是总倾向一致而已,但总体看来,新世纪派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定、思路一直没有天义派清晰。这是勿庸置疑的。
第二,天义派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新世纪派则几乎没有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天义报》刊载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译文:恩格斯1888年为该书英文版所作序的译文:该书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以及该书第二章的某些段落,刊载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婚姻的基础在于经济的段落。此外,它还介绍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不仅如此,它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表示称颂和赞同,说它们的创立“其功不殊”;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得出了“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钮”的结论。(注:《社会主义经济论案语》,《天义报》第16—19期合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认识,达到了那个时候的最高水平。
天义派和新世纪派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时出现这种相异之处的原因主要是:日本和法国的社会政治情况和无政府主义在两国的活动状况的不同影响。当时天义派和新世纪派的成员都身处日本和法国,两国不同的影响,连他们自己也感受得到。天义派成员张继,从日本到巴黎至伦敦后,给《衡报》致函说:“中国学生一入彼境,遂习染其风,与留日学生之性质决不相似,此则地气之移人也。”(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我们知道,在欧洲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马克思主义便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1872年第一国际将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巴枯宁开除出去,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进一步加强了分裂活动,还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与马克思、恩格斯争夺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同第一国际相对抗。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先后相继逝世,而无政府主义在欧洲有所复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不会再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西欧(包括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必然要影响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提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著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与巴枯宁曾与第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上述关联也不无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传播并发生重大影响,当时谈论社会主义学说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主张公平分配,主张把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资本收归公有。这些主张,与马克思的学说有共通之处。正是由于这种表面的共通,幸德秋水,畍利彦这两个主要的近代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在学习和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后,又转向无政府主义。(注:《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 卷,【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页。)受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天义派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很大关系。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列强的侵略,清政府腐败的封建专制统治,为改变这种状况人们还在立宪与共和制间徘徊,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还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天义派在寻找反政府、反权威的盟友时,宣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壮大自己的声势,又不会同其无政府主张有直接冲突。甚至还有一点“由社会主义进为无政府主义”,在学理上相接续的模糊想法。(注:《亚洲现世论》,《天义派》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这也是他们将其无政府主义区别于社会主义,又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因所在。
第三,天义派以“平等”作为其政治理想内核,新世纪派则将“平等、自由、博爱、进化”等近代民主思想素材涵盖于其“至公”的畅想曲中。
刘师培在《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中指出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当以平等为归”。他确信人类有三大天赋,不言而喻的权力,这就是:平等权、独立权、自由权。对于这三大权力,他又进一步分析说:“独立自由二权,以个人为本位,而平等之权必合人类全体而后见。”(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因此,认为三权之中平等权应当是最重要的。 因这种观点,天义派宣传其主义的几个侧重点:废政府、倡共产、均贫富、除资本制、女子解放、均可觅到追求平等,强调平等精神。他认为政府“以上凌下”,倡共产是因为私产制“以富制贫”。除资本制,因其只利少数富民,“富者按其资产以竟利”,选举权操于富人,法律保护富人,物质文明只造福于富人。“可谓失平之尤者矣”。不平等到极点了。主张女子解放,谋求参政,就业权的平等,达到男女平等。“均力说”是天义派最具特色的主张,也是其平等思想发挥的极至。他们认为:人人做工还不平等,要人人做同样的工才平等。(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认为:个人、社会的无政府主义,重在“恢复人的完全之自由”,而自己主张的无政府主义,重在“实行人类天然的平等,消灭人为的不平等”。(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由这种思想认识出发,刘师培自认其废政府,废国家无政府学理“主平等立论”,即以“平等”为其立论之基础,也是必然的。
《新世纪》派是在“至公”的言谈中,走上了实践的悖论。新世纪派在自己的宣传中,公理、公德、公平、公道、公益、至公等言辞使用频繁,他们认为世上争斗不息的原因是“有彼我之别”。而无政府主张“至公”,“不计利害”。(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吾等所抱之主义为至公无私”(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他们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 把道德分为“私德公德”。认为私德:“重为人之道,不自暴自弃,俨然立于世界上,不失其自由,平等之权,与时进化而已;”。(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页。 )这是自古已有思想素材与近代民主思想的混合。新世纪派认为传统的公德观念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因有家国、天下之别,则道德会有所不公,会出现亲疏、利害之偏依,进而认为公德应包括,共同、博爱、平等,自由智识等等。(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新世纪派以“公”为衡定万物之标准, 以与“私”相对,但他们的“公”论简单化,流于概念。只是由于无政府理论中共产制,互助说,与中国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接受的“公”念相通,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便推而广之,匆忙地牵强附会起来。如“家庭生私利之心,应毁掉,使人类中皆公民,无私民”,合于公道。法律出于少数人之手,使之“图自私自利”,“终不能合公理”;(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页。 )军队是牺牲平民的财命,保护强权者的私产私利,也是废除。又认为:无国界,才公道,不产生强权。而皇帝资本家掠夺垄断之心,就是由于私利所引起,因此要灭资本、灭专制;政府是少数人依特权成立的,不符合公道、真理、应去除。而资产阶级共和制,虽比专制、立宪进步,但其“建立新政府”,是追求利禄、名誉、铜像峨峨的自我主义。无政府革命则无私利,专尚公理。新世纪派不知客观分析,只于“公”字作高远清淡,在其种种主张上均贴一“公”字标牌。此为新世纪派一大特点。
总体看来,天义派称“平等”以去“利”为主,新世纪派号“公”,以去”“私”为主,他们都没有看到产生“利”“私”的根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将目光放在浅层面上,财产的分配,道德的教育。脱离实际。因此,一实践起来就走向自己的反面,做官为宦投敌者均有之。
第四,天义派的保守停滞与新世纪派尊今薄古。
天义派代表人物刘师培出身于历史悠久的学者门弟,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19岁即中举人。他在宣传中使用简单的比附手法(这是中国传统学术手法,思维方式之一),类比,附会中国东汉以后的社会状态为无政府,“中国自三代以后,名曰专制政体,实则与无政府略同。”(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甚至大言曰:“中国政府不负责任, 为极端腐败之政府,不知中国人民正利用其政府之腐败,以稍脱人治之范围,而保其无形之自由”。大有以腐败为幸事之嫌。又说欧美的文明是“伪文明者,如警察陆军及实业未尝不稍为进步”。但人民的幸福并不在于伪文明,而在于安乐和易,如果中国效法西方政府干涉政治,“文明日增,则自由日减”,人民的安乐和易会“远逊于前”,民间的无形自由会“今不若昔”。(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对于刘师培的这些言论, 有人说是复古倒退,如果联系他废君主,反封建伦理等级观念等思想倾向,这种评价就有些简单。如说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天义派,显现出了保守停滞的思想倾向则更中肯。当然并不是简单的学术比附手法能说明刘师培复杂的的思想源流,还有社会历史条件及个人社会历验基础上对各种文化思想的取舍,阶级眼界的局限,对自由的曲解,物质文明的理解,等等因素在起作用。
《新世纪》派主张“尊今薄古”,“行孔丘革命”、批评国粹主义。在《新世纪》上他们发表了《三纲革命》、《祖宗革命》、《尊古薄今与尊今薄古》、《好古》、《国粹之处分》、《排孔征言》等文章。认为统治者利用好古,可使人民安分守己,而使自己之安富尊荣,好古又阻碍人们接受“新理新学”,古人没有的今人不敢有。或必附会于古人的话,才可流行。否则视为异端邪说。因此,好古是进化的敌人。“不可不破好古之成见”。(注:《祖宗革命》,《新世纪》第2期, 1907年6月29日。)
新世纪派的上述主张决非偶然。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潮已逐步兴起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纲常伦理及阻碍革命迅速发展的封建文化。势必遭到涤荡,新世纪派主张通过“共和革命而进为无政府革命”, (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而提倡“尊今薄古”反对封建文化。 是为推进共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政府扫清道路。另外,革命派中有人欲以“复兴古学”来提高民族自尊心,这种思想减弱了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因此,新世纪派指出:“虽新理新学,有一二同于古说,然同于一部分,而非全体也”。指出这种附会必然会阉割菲薄新学说,阻碍人们对新学说的接受。
第五,天义派视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为敌人新世纪派则视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为同路为过渡。
天义派认为,实行无政府主义,在清朝封建政府的统治下,比在“共和政治”下更容易,清政府统治是放任,不干涉和腐败,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易行的因素。而共和政府一旦建立,由腐败政府变为责任政府,干涉政治加强,那时“政府之势力足以制人民死命而有余”,无政府革命会更难行。因此“满洲政府颠覆后不必另立新政府。”(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
新世纪派也曾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但与天义派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新旧主义之相代,其间必有过渡之一物”(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共和政治为不得已之过渡物”(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宣传革命党同无政府党在倾复清朝政府上的“志愿及作用同”,只是在有政府和无政府问题上“各怀主义”。因此两者“不过稍有异同耳”“非背驰者”。应团结合力推翻清政府。
总之,在天义派看来,专制立宪与共和没有区别,都是“因自利而谋革命”,(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从政治角度看欧美日的共和政治,“则较中国为尤恶”,它使政府压制人民的势力加强,无政府革命就更难实现了。因此,“惟望中国革命以后,即行无政府”。(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在新世纪派看来,专制、立宪、共和处在进化的不同阶段。(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三者中以共和为较善良。(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而无政府时代虽无统治组织, 但不能没有关联的组织,用关系的组织代替统治的组织,不可能立时臻于完备,只好取共和政治“为一时之作用”。因此,在新世纪这里,资产阶级革命被暂时视为同道。
天义派与新世纪派的这种区别首先在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影响不同,则认识不同,如前文所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是由接触社会主义后转入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共同是依靠普选的议会主义方法。后来成为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幸德秋水在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又看到议会主义在国家权力面前软弱无力,“终究不能完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后,产生了思想变化。1907年2 月他在《日刊平民新闻》上发表了《我的思想变化》一文,说明了这一点。(注:《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 卷,【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页。)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思想轨迹无疑会影响在日本的中国政府主义者,天义派对资本主义议会制的屡屡批判,及刘师培共和制下无政府会更难行的观点,都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至于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共和革命的优容与身处法国有关。法国是个资产阶级革命较彻底的国家,曾出现了许多民主革命思想启蒙家。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深入人心。锗民谊在《无政府说》中写道,在法国、自由、平等、博爱三字无不大书特书于公共建筑上。“表其为共和国,尤夸其为世界独一无二之美政体也”。当然新世纪派看到了并指斥了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但他们对这一资产阶级共和思想的推崇并未减低,而是溶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理念中。此外,正如游于法、英的张继所言,日、法风气大不相同,在欧洲留学界抱革命主义者众,“决无希望立宪者”。中国立宪在那里被当作笑谈之资。(注:《衡报》第4号1908年3月28日)并对比了日本人的“官本位”,“即议员中人‘放一屁’,亦以为神圣不可侵犯。至欧洲则不然”。(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这些情况都说明,日本与法国的不同社会条件,必然会发出不同的社会认识,身历欧风的新世纪派,虽不满于共和政治,但认为它较专制和立宪为善,也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我们能得出这样一些认识,而对一种新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寻取共通寻取联结点,是人类心理的共同趋向。如天义派与新世纪派对社会主义的区别与混同,他们的“平等”与“至公”,无不包含着中华民族“均平”“大同”的文化兴趣及道德治世的向往。另一方面,每一种外来思想文化都带有其自身社会的印痕。在同本社会的思想文化整合过程中,泛化为对与外来思想略有衔接的本民族的某种思想文化传统的强调,或不同角度的阐释和理解。因此研究国内每一种新思潮,或新文化现象,还应结合考察其各种文化传播源的社会状况,才能真正找出文化传播的规律。事实上,日本和法国给天义派和新世纪派提供了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这是导致两派政治观点有所区别的重要因素。这一历史启示,告诫我们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情中,应该注重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兴趣,积极地找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通、相联之处。比较对照传统文化与新型文化在时代功能上的差距,才能自觉的调理民心,完成文化转型和过渡。走上文化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任务之一。
【收稿日期】1999—11—30
标签:恩格斯论文; 无政府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刘师培论文; 天义报论文; 思想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