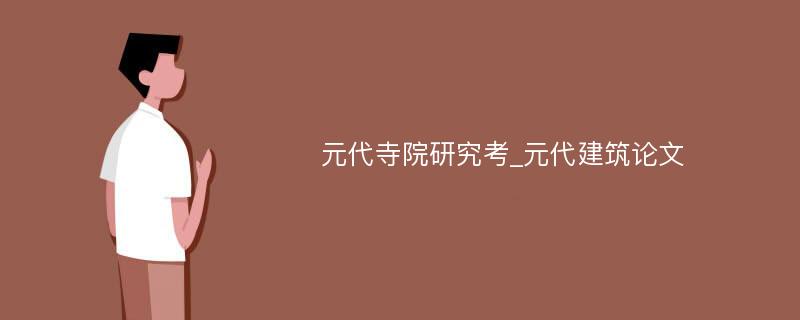
元代庙学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庙学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2)02-0022-05
何谓庙学?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解释为:设于庙内之学校。这种解释是否符合元代庙学的实际情况呢?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基本上肯定的态度。日本学者牧野修二认为:“庙学(元代)即郡县学,它是以文庙(先圣庙、宣圣庙、孔子庙)为精神中枢,并依附于文庙而设置的儒学”。[1]国内学者胡务也认为:庙学即儒学,[2]是依附于孔庙传授儒家理论为宗旨的学校。[3]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程方平先生在《辽金元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4月)中认为:元代存在着“确确实实的庙学”,它与地方学校不同,是“一种类似佛教俗讲的教育形式”,它是“以祭奠为中心的一种暂时性的教育,类似于今天的讲习班,讲座等形式”。1994年4月出版的百卷本《中国全史·元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的作者欧阳周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元代的庙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形式,它是如何进行儒学教育的?本文根据元代的史料并结合前人的研究,谈谈个人的看法,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元代有关庙学的史料很多,笔者仅在元人文集以及各地金石碑传中,就检索到72处之多,现选出几条摘录如下,且为了明确反映史料中的庙学所指,将有关史料的题目列于前。
《处州路重修儒学教授厅记》:“余友天台童君教处学三年,废必兴,弊必革,……于是庙学严整。”[4](卷三)
《江阴州重修学记》:“皇庆改元暨阳,庙学告成,孰成之,东平曹侯也”[5](卷七)
《大元国学先圣庙碑》:“至元四年,作都城,画地东北之东为庙学基”。“成宗建庙学”。[6](卷六)
《陕西等处转运盐使司作新孔子庙记》:“今有庙学,亦尚昭圣治哉”。[7](卷二十八)
《藕泽村孔庙记》:“藕泽里之有庙学,有藕塘宋思约者……自输己材,创建庙学”。[7] (卷三十九)
《吉水州修学记》:“吉水乡校自至元中,县令多东鲁儒生,凡致美于庙学者,靡不毕用其至”。[8](卷六)
《武卫新建宣圣庙碑》:“吾卫庙学未立师弟子教学无所……乃以庙学告成请于上。”[9](卷二十三)
以上所引史料中的“庙学”分别指的是:处州路学,江阴州学、国子学、陕西等处转运盐使司儒学、藕塘里社学、吉水县学(吉水后改为州)、武卫军(元京师侍卫亲军之一)儒学。此外,据《山左金石志》,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司下辖的19所盐场之一的西由盐场的儒学也称庙学。[10](卷二十三)由此可见,元代庙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它几乎可以指元代出现的一切儒学。胡务“庙学即儒学”的提法是有道理的。而程、欧二先生所提出的“与地方学校不同的”“确确实实的庙学”,则没有史料证明其存在。
为什么元代将儒学称为庙学?这主要归因于元代的儒学教育体制。据胡务考证,“庙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文学家韩愈所作的《处州孔子庙碑》一文中,文中有“惟此庙学,邺侯所作”[3]之句。据《崇仁县孔子庙碑》,唐开元(公元713-741)年间,“定孔子为先圣,庙而兖冕南面,每岁春秋祀焉,由是庙学之礼益备,凡有学者必有庙,示其尊也”。[11](卷十五)可见,庙学之制起源于唐代,它是庙与学二位一体的有机结合。孔子庙是祭祀先圣孔子的场所,学校是传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地方,二者的合二为一是中国古代的儒学教育与重视祭祀的传统(“天下大事,惟在祀戎”)的结合,表明了唐以来儒学教育的初步完善。这种唐代出现的庙学,至宋代逐渐增多,并成为定制。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诏天下皆立学,于是“凡郡邑无不有学,学无不有大成殿”。[12](卷三,“南安路大成殿记”)上述情况,可以从宋元的方志中得到印证,宋宝庆年间(公元1225-1227),庆元府(今浙江省宁波一带)所辖的三县学包括府学在内也全为庙学。[13](卷二,“学校”)
元代庙学如何?首先看一下元人对庙学制度的看法。元代著名教育家程端礼认为:“孔子庙遍天下,其制度沿革多有不同,然皆所以尊崇圣人而阐明其道,使君子小人有所瞻仰感化,同归于学则一而已矣。是故殿廷庑门有常度,容貌佩服有常仪,尊垒簠簋有常数,师弟子有常员,祭祀有常礼,苟奉天子之命,司牧民之寄者必有志于其间也”。[14](卷五,“枣强县学修饰两庑及从祀先贤像记”)元著名文士,曾任国子祭酒兼翰林直学士的虞集认为:“夫庙无与于学也,然而道统之传在是矣,学于此者诵其诗,读其书,习礼明乐于其间,诚其道也”[9](卷八,“新昌州重修儒学记”)上述看法反映了元人对庙学认识的深入。实际上,元政府对庙学的发展可以说是比较重视的,元代曾多次下达儒户免役和禁止骚扰庙学的诏令,南宋遗留下来的学田得到承认,南宋的一套学校管理和祭祀制度也得到继承和发展。这样,元代的庙学在前代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自国都郡县皆建学,学必有庙以祠先圣先师而学所以学其学也。”[9](卷三十六“南康路都昌县重修儒学记”)而庙学之制“莫备于今,诏书屡下,风厉作成,视昔有加,可谓盛焉”。[15](卷九,“义乌县学明伦堂记”)
元代庙学的发展表现在庙学制度推广到更广阔的区域和范围。在以前庙学影响从未达到的边疆地区,一些庙学建立起来,如云南,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16](卷一百二十五,“赛典赤瞻思丁传”)在距上京700里的诸王封地全宁路,泰定二年(1325年)“皇姑鲁国大长公主和驸马济宁王创建庙学”。[17](四,“全宁路新建庙学记”)庙学在元代也推广到一些特殊的区域,如军队驻地、转运司治所、盐场以及乡里等等。当然,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有一些地区存在有庙无学的现象,如山西的潞城县,垣曲县等,但这些地区后来逐步建立学校,完善了庙学制度。[7](卷二十八,“潞城修学记”)
二
元代庙学的结构如何?这是认识庙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说,元代庙学的建筑结构是比较完善的,典型的庙学是国子学和地方路、州和县的官学,由于是政府办学,学田有一定的保障,经费相对充足,因此,其庙学的各项设施也比较完备。元代庙学有三部分:庙(也称礼殿、大成殿、夫子庙、文庙等)、学宫以及其他辅助设施。“庙以观其礼,学以育其士”,[7](卷三十三,“高平归正学田记”)而教学辅助设施则是庙和学实现其职能的必要条件。元人虞集在其文集中将这三部分称为:礼殿、学宫和学都。[9](卷三十五,“奉元路重修宣圣庙记”)庙位于学校的中心,一般是前庙后学和右庙左学(元人尚右)以示尊崇。庙内塑孔子像,正中南面而坐,孔子以下为四配(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东坐西向,[18](卷二十七,“四位配享封爵”)十哲分列左右。庙的东西两边有从祀廊庑,绘七十二子像(后增至一百零五人)于其中。由于绘画时间久远模乎不清,北方一些庙学将画像画在布帛上,祭祀时挂出,平时收藏,元中后期江南很多地方则将绘画改塑像。学宫由明伦堂(名称不一)、学斋及尊经阁组成。明伦堂居中为讲堂,学斋位于东西二庑之中,数量为偶数对称排列,是诸生修业诵习之所。也有一些起学校将学斋设于学校东西二边的僻静之处,以利于诸生修习。尊经阁在明伦堂之后,为学校藏书庋经之所。庙学的第三部分为辅助设施,包括:会食之堂,仓庚(库),直舍(宿舍)、学官之厅、浴室、碑亭、杏坛等。庙学周围有围墙,外为棂星门,内有学门,学门里面凿湖为泮池,池上修桥通往孔子庙。关于元代庙学建筑结构方面的内容,已经有专文发表,可以参考,本文不再详述。(注:见牧野修二《元代庙学和书院的规模》、胡务《元代庙学的建筑结构》,另外还可参考袁冀《元代之国子学》(《元史研究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
除国学及地方路、州、县庙学以外,元代还有其他形式的庙学,如社学、义塾、军队及转运司庙学等,它们有的为私人办学,有的虽是官办,但分布不广,数量较少,因此,其庙学的规模远逊于国学及地方路州县学。
元代社学的数量很大,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大司农司上奏说,全国有社学20166所。五年以后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社学数量增至21300余所。[16](卷十四,“世祖本纪”)但有关元代社学的详细史料并不多见。据《藕泽村孔庙记》,该村的社学“正殿两庑轮焕晕飞,流丹耀碧,相貌,门皆悉备”其西边“文构讲堂,为弦诵之所。”此处社学虽然简陋,但是有庙有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春秋二祀则“行释奠之礼”,[7](卷三十九)可以说它具备了庙学的功能。
元代的京师驻军及地方驻军中,都有设置庙学的记载。据《元史·职官志》元代侍卫亲军诸卫中有儒学教授一职的设置。由于“凡卫必有营,营有城廓、楼堞、门障、关禁、官治、行伍庐舍,库庚衢巷而特立先圣孔子之庙,儒学在焉”。驻地在涿州的武卫庙学“广袤八十亩”,有“礼殿以奉先圣像,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从祀,十哲分位殿中东西乡(向),七十二弟子绘庑下”其“讲堂、斋庐、庖廪、垣墉、门术卫皆如常制”。[9](卷二十三“武卫新建宣圣庙碑”)位于湖广行省南部的武冈路儒林乡的城步寨,是元政府屯兵以镇抚苗、侗等溪洞的八十四团之一部的驻地,皇庆二年(1313年)这里也建立起庙学,“正殿、讲堂、门径斋庑、墙垣、厨壁内外完具,先圣先师十哲从祀塑绘有严,庙貌相称”[19](卷十六,“儒林书舍记”)
义塾也是元代分布较广的一种庙学形式,它是由私人捐资修建,因为其规模不大,并大多处于州县治所以外的乡里,一般方志将其作为社学对待。义塾在教学方面与社学并不相同,它是“延德师,招来学”,[20](卷二十三,“学政”)与书院相似。义塾的建筑规模不大,如上海横溪义塾:有礼殿供奉孔子及四哲像,“设两斋栖师弟子,具祭器,严春秋二丁”。[21](卷十一“上海横溪义塾记”)安福州的安田义塾也是“构礼殿奉先圣先师,设堂立斋舍,门庑庖廪悉具”。[11](卷四十一,“安福州安田里塾记”)而嘉兴县的白牛镇义塾规模较大“广袤可二十亩”有“先圣先师之殿峙其中,论堂踞其后,斋庐翼其旁,邃庑穹门下至庖库庚直舍之属为屋四十有五间”并且其“图史之藏,什器之须悉毕备”。白牛镇义塾设有围墙,并种花木,引溪水于校园,环境非常优雅。[20](卷二十三,“学政”)
元代的转运盐使司及其下属盐场有创办庙学的记载。据《陕西等处转运盐使司新作孔子庙碑》,在其治所陕西行省运城县的路村,大德三年(1299年)建立了庙学,内有礼殿,塑先圣先师之像,“置讲堂后以居师生”。[7](卷二十八)庙学有围墙和棂星门,庙学设施基本完备。
可见,“庙学”这一称谓与宋元以后儒学教育的体制有关。首先庙学化的是国学和地方官学,受其影响,元代的一些社学、义塾等也建立起孔子庙,将祭礼与教学结合起来,成为庙学。那么,元代众多的书院算不算庙学?胡务认为,书院从广义上说应该算作庙学,但书院与庙学在元代有一些区别。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元代的史料中至今还没有发现将书院称作庙学的记载。
三
程、欧二先生在《辽金元教育史》和《元代教育史》中有关庙学的观点,依靠的是《庙学典礼》卷一“官吏诣庙学烧香讲书”。现将四库全书本《庙学典礼》中的这段史料摘引如下。
“各路遍行所属,如遇朔望,自长次以下正官同首领官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礼毕,从学官主善诣讲堂同诸生并民家子弟愿从学者讲议经史,更相授受,日就月将,教化可明,人才可冀。”
这则史料非常清楚地说明塑望讲书的地点是讲堂而非庙里。所谓“诣文庙烧香”,实际是到庙学的文庙烧香,也就是到路州县学的文庙烧香,然后至讲堂(一般称明伦堂)讲书。所以说它“是在孔庙中进行的”,“是一种类似佛教俗讲的教育形式”[22](30) 是没有史料根据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现引绍兴路学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订立的《学式》中的“朔望讲书”来说明。
(朔望)殿谒退,升明伦堂,诸司存官与乡之有齿德者列坐,诸生从其后,大小学生班立,推一人唱揖平身,鸣鼓,请讲书。朔旦教授升讲座,望日正录轮讲,另立于坐之西口,演绎经旨不用讲义,文字讲毕,大小学(先)讲所习四书命题,课口义、诗对,定其优劣,以示激励[23](卷七,“绍兴路庙学图(至元壬辰重定学式”)
这则史料除了说明讲书是在路学中进行以外,尚有二点值得注意:第一,朔望除了讲书以外,还测试大小生徒;第二,史料中未提民家子弟或一般老百姓听讲的问题。那么,朔望讲书是不是像程、欧二先生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类似于今天讲习班或讲座”的面向群众的教育呢?我看未必。庙学中讲堂的空间是有限的,如镇江路学讲堂(称成德堂)为5间;[14](卷五,“枣强县修饰两庑及从祀先贤像记”)庆元路奉化州讲堂(称彝训堂)为5间,鄞县为3间。[24](卷十三,“学校考”)参加讲书的诸官员僚属、乡贤、学官以及大小生员动辄百人,官员僚属、乡贤、学官要“以次列坐”,大小学生只能“班立”,即使这样,很多地方的生徒也不能全部容下,何况一般老百姓?况且讲书是学校教学活动的一部分,不是节日庆祝活动,它需要庄严肃穆,当时没有扩音设备,因此不适合更多的人参加。所以,元代史料中找不到有关一般百姓参加朔望讲书的例证。这样看来,元代庙学的朔望讲书不是面向一般百性的社会教育。如果说庙学多少有点社会教育的因素,这只能表现在庙学春秋二祀这样大的祭祀活动中,老百姓可以从“四方来观”并“失喜赞叹,以为衣冠礼乐尽在是矣”,[25](卷三十二,“东平府新学记”)从中得到感染,受到激励,这与“社会教育”又差之甚远。
其实,庙学的朔望讲书,每月二次,应是很平常的事情。讲书的不仅是学官,有时“所属上司官或省宪官至自教授学官暨学宾斋谕等皆说一书”。[18](卷三十,“学宫讲说”)如定海县尹汪汝懋“旦望深衣幅巾,升堂行礼率逢掖士,召诸生亲为讲论道德性命礼乐之懿,申以孝悌揖让之义及正刑法度之详未尝少懈”。[27](卷六,“定海县兴修儒学记”)由于地方官文化水平不一,能亲自讲论的不多,大多数只能听别人讲。即使这样,在听书的过程中也闹出一些笑话。如泰定元年(1324年)元政府开凿吴淞江,“省台宪僚咸集”。当时的治书侍御史刘泺源到松江府学,殿谒毕,学官詹肖岩讲书。这一年是闰年,他讲的是《尧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结果刘御史听后大不乐,申斥曰:“学校讲说,虽贱夫皂隶,执鞭坠镫之人皆令通晓,今乃稽算度数,何为?”肖岩由是“悒悒而卒”。[18](卷三十,“学宫讲学”)
朔望讲书对一些贤能的官员来说,还是体察民情,交流感情的一种手段。至顺二年(1331年)庐江县尹成克敬“祗谒先圣先师,退即明伦堂,教官以下以序列坐,历问风俗臧否,吏民所疾苦,今古贤士孰贵孰孝”。[26](卷十一,“卢江县学明伦堂记”)另外,这一活动给了学官通过讲书讽议时政的机会。至元十六年(1297年)有分宪老老公到某地“以复熟粮为急”,学官陆宅之讲省刑罚,薄税敛,使老老公“色变而作”。在“钱先生伯全父(疑有衍字)作训导时,行刑官至”,他讲恤刑法,讲毕,行刑官则“称赏不已”。[18](卷三十,“学宫讲说”)
最后,朔望讲书还有议事的功能,特别是有关庙学整修、增建或收复被侵学田、学产等大事。一方面地方官在殿谒时看到庙学弊坏,劝学官修整,并讨论修缮和筹集资金的办法;另一方面,学官也趁此机会向上级请求帮助和支持,这样的例子很多,兹不再列举。
元代随着庙学的推广,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得到完善。元中后期,庙学出现了重祭祀,轻教学的现象。为此,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尖锐的批评。身为学官的朱德润认为:“庙祀盖始于梁世,用浮屠之法,近代因之,恬不为异。今则典学者以修造祠像为先务,而以教养次之,是可嗟也”。[28](卷四,“送长州教谕序”)元荆门知州聂炳批评说:“世之所谓兴举学校者,不过丹护庙貌,粉泽虚文,鄙俗相侉,若浮屠老氏这所为,谬谬然号于人曰报本云者,岂知本哉?[19](聂炳,“刘侯兴学记”)元辽阳行省参知政事杨仁风也对元代惟庙貌精舍之惟严,丁祭朔望之惟谨表示忧虑,认为如果这样下去,“中人之材三年能有成乎”?[7](卷二十九,“瀛路斯文楼记”)然而这些批评并没有改变元代庙学重祭祀的情况。元中期,很多地方的庙学置大成乐,设专门的乐户或训练乐主在祭祀的时侯演奏,于是庙学祭祀之风更甚。整个元代,这种情况都未改变。洪武三年,明太祖即下诏令,停止庙学的春秋祭祀(后来又恢复),朔望讲书也改为考查生员射箭水平的活动[19](卷一,“国初学制”),这应该是对元代庙学弊端的修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