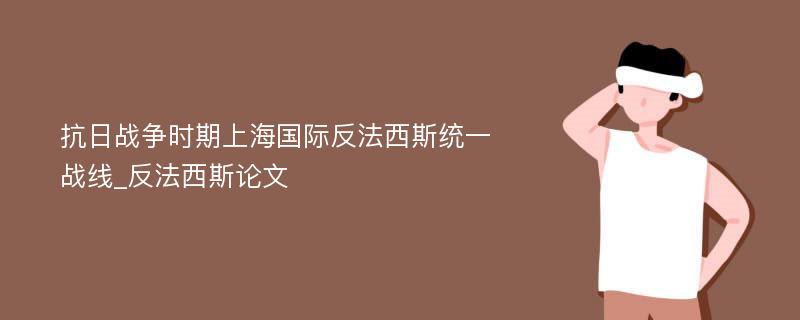
抗战时期上海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战线论文,上海论文,反法西斯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8-0152-06
到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已有常住的外籍人士近10万人,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涌入,又使这一数字直线上升。上海的中外人士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支持,使这个东方大都市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要战场。本文旨在对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作一些考察,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3周年。
上海以实际行动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救助来沪犹太难民
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抗日、反法西斯情绪日益高涨,不但积极声援中国各地的抗日斗争,而且还声援和支持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斗争,如全力声援并积极支持朝鲜人民的抗日独立运动、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正义斗争、埃塞俄比亚人民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斗争、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等。如果说对这些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主要还是道义上的,那么对来到上海的数万犹太难民的鼎力救助,便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的重要贡献。
犹太难民为什么要跑到万里之外的上海来?这里有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原因。从历史上看,犹太人早在唐代(还有观点认为在汉代或周代)就来到了中国,宋代以后的开封犹太人社团更是众所周知的。近代以来,香港、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城市又成为犹太人在中国的主要聚居地。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从古代到现代有这么多犹太人生活在中国,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土生土长的反犹思潮和反犹运动。因此,备受苦难的欧洲犹太人对中国人民以及上海这样的城市抱有友好、亲近的感情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和犹太(希伯来)文化传统具有许多接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在欧洲,反犹主义的思想基础在于由文化差异导致的对犹太人的宗教偏见和种族歧视。而在中国,这样的思想基础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生活在中国的犹太人有一种宽松感和安全感,这对饱受法西斯迫害的欧洲犹太人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现实的原因。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部分地区及其周围地区,使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日本占领区内的一个“孤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无法在上海地区继续行使自己的职权。结果从1937年秋到1939年秋近两年时间里,外国人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这给犹太难民的移入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对于许多被关过集中营又身无分文的欧洲犹太难民来说尤为重要。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由于遍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各国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使欧洲的犹太难民越来越难以找到逃生之处。英国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联合阿拉伯国家对付德意法西斯,于1939年5月发表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①。拥有世界上最大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的进入做出了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限制②。在1938年召开的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埃维昂会议上,所有参加国都对犹太人的处境表示同情,但没有一国明确表示愿接收犹太难民。就是在这样一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情况下,面临死亡威胁的欧洲犹太人不得不亡命上海——当时世界上唯一向他们敞开大门的东方大都市。结果,从1933年到1941年,特别是从1938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总人数几达3万,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000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③。
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纳粹的反犹暴行,并积极救助避难来沪的犹太难民。早在1933年5月纳粹德国掀起反犹恶浪之时,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派代表团前往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代表团以宋庆龄为首,团员包括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中外知名人士。他们义正词严地指出:“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征象。”④ 上海犹太人的报纸《以色列信使报》于6月2日以《文明世界反对希特勒主义》为题报道了此事,并刊登了埃兹拉主编写给宋庆龄的感谢信,信中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身处纳粹德国骇人恐怖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的有力声援,希望能够唤醒德国冬眠的灵魂⑤。
“八·一三”事变后,许多上海市民自己也沦为难民,不得不在难民所中栖身。但即使在这种困境下,当大批欧洲犹太难民涌入上海时,上海人民仍然克服种种困难,给予他们无私的接纳和真诚的帮助。在犹太难民聚居的虹口地区,上海市民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帮助犹太难民寻找工作,为犹太难民提供生活上的各种帮助,如临时照顾犹太小孩、借给犹太难民一些生活用具,安排犹太儿童同中国儿童一起学习等。当时,虹口霍山路小学接收了不少犹太难民儿童进校读书。在犹太难民医院建立之前,中国医院还收治了许多犹太难民,抢救了其中不少人的生命。中国教会和上海救援或慈善团体,如上海难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等也都捐房捐款帮助犹太难民。1939年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刊文指出:“虽然我们在上海尚有十多万难民的生活不易维持,但我们只要能力能办到,总可以尽力帮助犹太难民……我们应站在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上,一致对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敌人。”⑥ 1939年2月17日,有鉴于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越来越多,安置越来越困难,当时的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孙科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更多无家可归的欧洲犹太难民。孙科在议案中指出,最近欧洲法西斯势力张盛,犹太民族更饱受了无情的虐待,其中以德国为最甚。德国藉口德驻法大使秘书遭到犹太人的杀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排犹运动,其手段之毒辣亘古未闻。上海最近因被逐犹太人汹涌而至,苦于无法容纳,正计划限制欧洲难民的进入。为此,拟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⑦。虽然由于经费缺乏等原因,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全面实施,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民对危难中的犹太民族充满同情和援助之心。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博士,克服重重困难向犹太难民发送签证,使他们能凭此签证离开纳粹占领区,其中许多人后来到了上海。他现在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德国反犹政策影响下,上海的日本占领当局开始对欧洲犹太难民进行限制和迫害。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虹口设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强迫犹太难民迁入该隔离区。此后,犹太难民经历了他们居留上海期间最艰难的两年半,在这期间,上海人民给予犹太难民以大力救助,与他们的交往在患难中更为紧密。犹太难民莉莉·芬克尔斯坦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发现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我们的困境牟利。不要忘记,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和他们中的一、二个妇女还交上了朋友。”⑧ 战时与犹太难民一起居住在虹口的王发良老人回忆道:“那时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日本人迫害我们中国人,我们与犹太难民同处患难之中,大家在一起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到战后他们离去时,我们之间都有些难分难舍了。”⑨ 犹太难民肖特曼认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要是在欧洲,若犹太人遭难之时,周围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利用犹太人的困境趁火打劫,落井下石⑩。在1942—1945年这段最艰苦的时期,犹太难民与他们的中国邻居互相帮助,同甘共苦。1945年7月,美国飞机误炸虹口区犹太难民居住区,造成31名犹太难民死亡,250名难民受伤,周围的中国居民虽同样伤亡惨重,但仍奋不顾身地冲入火海,抢救出许多犹太难民,在中犹关系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
1986年,一批曾居住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为了感激上海人民,提出要在虹口原难民旧址立匾纪念,匾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地区曾有2万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幸存下来。谨以本匾献给所有幸存者以及施加援手的热情好客、宽宏大量的中国人民。”(11) 当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对此表示支持。1994年,上海市政府在战时犹太难民居住的虹口地区的中心——霍山公园(旧称汇山公园)内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碑。率领美国犹太名流代表团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阿瑟·施奈尔拉比激动地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12) 此后,包括以色列历任总统和总理、德国总统和总理、奥地利总统、美国第一夫人等贵宾在内的各国来宾均来此献花,以缅怀那段历史,并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感谢。
在上海的国际友人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931年后,特别是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外国人也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声援中国抗日斗争,全力救助中国难民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外侨均掀起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不但发表声明谈话,而且纷纷捐钱捐物,还积极救助中国难民。如“八·一三”事变后,震旦大学法籍教授饶家驹神父在法租界建立了6所难民收容所,又四处奔走,建立了南市难民安全区,总计救助难民超过10万(13)。淞沪战事发生后,旅沪西方国家侨民中慷慨解囊者也络绎不绝,中法工商银行经理,法国侨民巴尔特一次捐法币1000元,指定以500元救济难民,500元救济伤兵(14)。许多上海犹太商人,如,A.J.阿夫拉莫、M.斯皮尔曼、R.D.亚伯拉罕夫人等积极向中国红十字会和国际救济委员会捐款,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15)。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德国侨民也投入了捐助热潮。据报,1937年8月26日,德国旅沪侨商总会主席普尔兴氏,就将上海全体德商捐助之法币17510元捐赠给上海救济难民机关(16)。
波兰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积极支持中国抗日运动,不仅以私谊关系致电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先生,痛陈反共摩擦必须制止,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17)。1938年秋天,他以记者身份到皖南新四军驻地进行采访,见到了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此后写了大量宣传新四军的文章在国外发表(18)。德国犹太人汉斯·柯尼希(Hans Koenig)战时担任塔斯社上海分社记者,积极向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后来曾任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加拿大人莫里斯·科亨曾任孙中山先生的副官,后成为中国军队的将军,以“双枪科亨”著称,长期居住在上海。抗战爆发后,他奔走于南京、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在国民党军队的对外联络和军备采购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41年,他在香港被日军作为“敌侨”关押,后遭遣送回国。他仍然不忘宣传中国的抗日,积极寻求国际支援。1944年6月,他向世界呼吁道:“中国的抗战已进入了第8个年头,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一场令世人瞩目的战争。但是,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她还需要加强空军力量和重型武器装备。请相信,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但这更说明她需要更多的装备。”(19)
奥地利记者魏璐丝于1933年10月抵达上海,随即写了几篇报道中国情况的文章发回维也纳发表,因其中有谴责日本侵略者的内容,遭到日本驻维也纳领事馆的抗议。此后,她暂搁写作,到上海一家犹太人办的学校教书,同时着手对中国进行深入考察。后来,她成为史沫特莱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助手,担任史沫特莱与苏区红军秘密会见时的翻译,并协助史沫特莱进行抗日宣传。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她受史沫特莱之托采访和报道上海学界为抗日救国向南京国民政府的请愿活动。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魏璐丝协助创办了英文报纸《成都新闻》,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另外,她还协助宋庆龄指导保卫中国同盟的抗战工作。
上海外侨团体也多次组织抗议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集会和示威,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上海犹太人和部分外侨还冲击纳粹分子在上海庆祝“胜利”的活动,发起抵制“德国制造”商品的运动。1943年初,日本当局在虹口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犹太团体曾组织犹太难民,特别是波兰犹太难民对此进行抵制,迫使日本人做出一些让步。这无疑都是对中国抗日斗争的间接支持。
2.直接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不少在沪外国人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中国人民并肩抗日,浴血奋战。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旅沪的朝鲜爱国志士十分愤慨,决心与中国军民一起,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4月29日,在抗日的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亲自指挥下,“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将炸弹装进水壶混进了戒备森严的虹口公园。当白川大将等日本在沪军政要员登上检阅台时,尹奉吉将装有炸弹的水壶奋力扔向检阅台,随着一声巨响,白川大将等日酋30余人当场被毙或被伤。此事使上海人心振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同时,旅沪韩侨各团体还组织了救护队支援中国抗日军队。如上海韩人独立运动青年同盟组织救护队,奔赴前线救护与日寇血战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受伤官兵。又如旅沪朝鲜侨民团组织慰劳队,分批募款,数日之内,即募得千余元,他们购买了药棉花200包、纱布50包、碘酒200余瓶,及其他日用品数十箱,送往十九路军前线。再如旅沪朝鲜爱国妇女会,在淞沪抗战中也积极从事反日援华工作。她们有的演出革命剧,增强上海民众的抗日情绪;有的分散在上海各马路张贴反目标语(20)。
在旅沪俄国侨民中,也有许多人加入中国军队助战,其中一些人直接参加了国民党的飞行大队,驾驶飞机与日寇作战,有的还为了抗击日寇捐躯沙场。据外刊报道,至1937年底,外国人士在中国军队中从戎者,共有451人,计美国152人,法国124人,苏联115人,英国55人,其他国籍5人。此451名外侨中,飞行员居十分之九,年龄自21岁至39岁不等,大都来自上海。此外,还有原无国籍的俄侨300余人,后来均加入中国籍,他们与苏联侨民一起为中国作战,其中大都也来自上海(21)。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俄侨莫洛契科夫斯基将军等人亲自驾装甲车上阵参战,后又掩护中国军队撤退,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10月,前面提到的波兰记者希伯到山东根据地考察,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1月30日,希伯在山东沂南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中国人民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碑文上铭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奥地利犹太医生罗生特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被投入集中营,后几经周折来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开了一家泌尿科和妇产科诊所。1941年3月,罗生特来到苏北盐城,加入了新四军,担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就此写道:“在苏北,参加新四军的国际友人,罗生特大夫还是第一个。”(22) 在新四军中,他除了医治抢救了许多抗日军民外,还为部队培养了大批医护人员。1942年,罗生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4月,为诊治罗荣桓同志严重的肾病,罗生特转赴山东担任了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罗生特积极培养医药卫生人才,他还经常给当地老乡治病,被人们誉为“再世华佗”、“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
另一位奥地利犹太医生傅莱早在儿童时期就加入了维也纳少儿革命组织。1938年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后,奥地利共产党人、革命分子和犹太人遭到残酷迫害,傅莱也不得不告别父母,于1939年1月15日来到上海,经过多方探询,终于与晋察冀根据地取得了联系。1941年秋,在八路军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他经北平到达了平西根据地,见到了肖克司令员。两周后,他到达了晋察冀军区的中心地区。聂荣臻司令员对他表示热烈欢迎,亲切地为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傅莱”,并安排他在白求恩卫生学校任教员。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傅莱始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战斗。1944年,他调往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从事传染病和内科教学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生产粗制青霉素的实验室,解决了部分药品短缺问题,为此受到了毛主席亲切接见(23)。
3.在秘密战线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
著名的苏联英雄里夏德·佐尔格曾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领导情报工作,他的情报小组里有一批住在上海的德侨、英侨、美侨、犹侨、日侨和俄侨,其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佐尔格情报组织为苏联搞到了大量日本高层及军方的最机密情报,包括日本进攻中国的计划和部署,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等重要情报,为打击德日法西斯,支持中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小组也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1941年12月后,日本与英美开战,但因与苏联签定了《日苏中立条约》,仍保持非战关系。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持有苏联护照的俄侨便利用其“中立国侨民”的合法地位为苏联和其他盟国做情报工作,为反法西斯事业出力。前面提到的俄侨莫洛契科夫斯基将军1941年后移居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559号D,为中国某重要机关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1941年10月26日晨,日本宪兵队探知其在法租界内设有秘密电台,即突袭其寓所,莫氏在危急关头开枪自杀,年仅45岁(24)。
上海犹太人也在秘密战线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上海犹太组织领导人J.汉瑟冒着被捕的危险,替国民党军队传送抗日情报,为此曾多次遭到日本宪兵队传讯(25)。在日本当局建寺的虹口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内,犹太人的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也十分活跃,曾出现过反法西斯地下刊物和传播盟军获胜消息的传单。弗兰克·塞莱格是上海犹太难民中的一位工程师,当日本当局要他帮助指导生产手榴弹时,他便与中国工人密切配合,设法使生产的手榴弹不能爆炸,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26)。最近的调查又发现,上海犹太难民中的左翼人士还组织了一个地下反纳粹小组,经常在一起聚会,其骨干有瓦尔特·舒列克和岗特·诺贝尔等人,大多是德国共产党党员(27)。所有这些活动,无疑应视为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及对中国抗日斗争的重要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日本和德国官员也参与了秘密战线的反法西斯斗争。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在得知纳粹德国梅辛格上校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屠杀上海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计划后,立即通知了上海犹太社区领导人,使他们有时间采取应对措施。后来他被逮捕并遭严刑拷打。德国驻上海的海军谍报军官路易斯·西夫金上校暗中进行反希特勒活动,将日德合谋迫害犹太人的计划通报上海犹太社团,还将日本人在犹太人中收买的奸细名单告诉地下组织。战后他因此受到赞扬和表彰。
结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第一,上海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战场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早在1932年初就开始了抗日斗争,直到1945年9月,历时近14年。在这艰苦和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和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始终与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密切结合,使上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战场。中国人民、上海人民的全民抗战,得到了在沪、在华外国侨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同时中国人民、上海人民也大力支持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斗争,而且以实际行动救助来到上海的各方难民。这种互相援助,充分体现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第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伟大凝聚力在于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而言,上海的中外居民千差万异,如外侨中一些人(特别是欧美国家侨民中的上层人物)是靠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起家的,另一些人(如部分白俄代表人物)曾经是坚决反苏反共的。然而,当全人类面临法西斯的威胁时,上海中外居民中的大多数人,即使是上述两类人都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坚决抗击日本法西斯一边,为支持中国抗日斗争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伟大凝聚力和重要意义。
第三,研究上海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研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上海的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海史、二战史、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等领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重要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一些人妄图否定历史、篡改历史的时候,这一现实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收稿日期:2008-05-05
注释:
① [美]胡里维茨(J.Hurewitz):《近东和中东外交文件集》第2卷(1914—1956)(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A Documentary Record Vol.II 1914—1956),普林斯顿1956年,第218页。
②③ [美]格罗曼和兰迪斯(A.Grobman & D.Landes):《大屠杀研究评论集》(Genocide,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caust),洛杉矶1983年,第298、299页。
④ 宋庆龄:《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载《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9-51页。
⑤ 《以色列信使报》1933年6月2日。
⑥ 贺益文:《犹太民族问题》,《东方杂志》第36卷第12号(1939),第12页。
⑦ 《民国档案史料》1993年第3期,第19页。
⑧ 潘光、李培栋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第163页。
⑨ 采访王发良记录,1994年4月18日,上海。
⑩ 采访威廉·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记录,1996年6月16日,纽约。
(11) 潘光、金应忠主编:《1990以色列·犹太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12) 潘光、王健:《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13) 参见瑞斯迪阿诺(Marcia Ristaino)《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The Jacquinot Safe Zone,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 《立报》1937年8月31日。
(15) 《以色列信使报》1937年10月25日。
(16) 《申报》1937年8月27日。
(17) 《大众日报》1942年7月7日。
(18) 黄瑶、张惠新:《一个大写的人——罗生特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9) [美]列维(D.Levy):《双枪科亨》(Two- Gun Cohen,A Biography),New York:Thomas Dunne Books,1997,p.238。
(20) 崔志鹰、潘光、汪之成:《旅沪外侨及国际友人对上海抗日斗争的支援》,《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21)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1938年1月5日。
(22) 《江淮日报》1941年3月25日。
(23) 冯彩章、李葆定:《红医将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页。
(24) 《申报》1941年10月27日。
(25)(26) 潘光、李培栋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第65-77、150页。
(27) 采访岗特·诺贝尔(Gunter Nobel)记录,1997年8月21日,柏林。
标签:反法西斯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中国犹太人论文; 德国难民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上海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同盟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