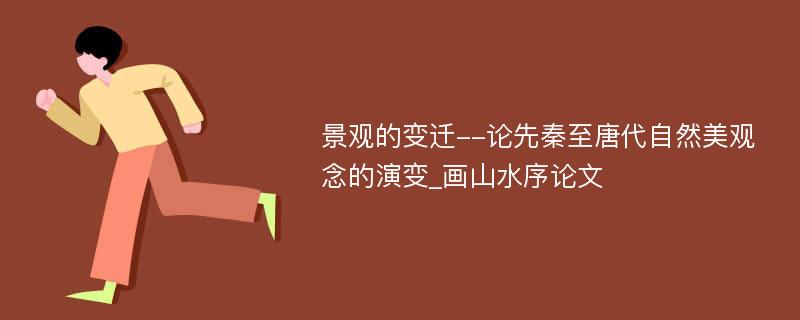
山水之变——论先秦至唐代自然美观念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美论文,先秦论文,唐代论文,之变论文,山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试图勾勒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变化的历史流程与美学指向,并在此背景上澄清山水文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者认为,中国艺术中对自然的认识,从先秦历晋宋再到唐代,经过了正、反、合三个阶段。作者侧重运用纵向比较的方法,指出从晋宋到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满足自然景物的外在形式,到探究山水的内在意蕴与意趣;由物我并峙,转变为物我交融,情景合一;就美感认识层次而言,由属耳流目,极视听之娱,上升为怡神悦志,通过礼赞自然,获得对宇宙人生的审美顿悟。
关键词 自然美 变化 先秦 晋宋 唐代 比德 视听之娱 怡神悦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式中均含有变量。一方面,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影响、征服和改变着异己的原始蛮荒的自然界,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成为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对自然的态度。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不断变化着的关系,才使自然由巫术礼仪、宗教祭祀的对象,由伦理道德的比附和象征,转变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人对自然的态度,也有一个从宗教态度到功利态度(实用功利和精神功利),再到审美态度的转变。在中国艺术史上,这种转变的历史流程经过了1000多年才得以完成。
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望秩于山川”、“山川之望”、“望祭”,实即人们在原始宗教观念作用下的自然崇拜仪式。《尚书·舜典》:“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诗·大雅·吋迈》:“怀柔百神,及河乔岳。”都是把山川当鬼神一样来祭祀。唐代张守节在《史证正义》中说:“望者,遥望而祭山川也。”在这时,高山大川还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物。人们在登临眺望时,所获得的也不是愉悦身心的美感享受,而是庄严肃穆的宗教情绪。其次,这种活动是最高统治者和诸侯贵族少数人祈福禳灾的仪式,而不是普通的观赏游乐活动。秦汉以来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举行的“封禅”活动,实即受“望祭”仪式影响而形成的最隆重的国家典礼。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脱离蒙昧,发现自然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诗·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便是对大禹治梁山、除水患的歌颂,禹所说的“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尚书·益稷》),也反映了人们征服山川的智慧与成就。《荀子·王制》中从人与自然的物质功利关系出发,认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天地万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舟楫之利,财用之源,反映了自然从“神化”向“人化”的转变和过渡。
除了认识到人与自然的这种实用功利关系外,人们也感到了自然与人的精神生活的密切联系,自然对人的道德精神的象征与暗示意义,于是产生了“以物比德”的观点。“比德”说最早见于《管子》,管仲认为禾“可比于君子之德”。《论语》中所说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都是从伦理道德的观点去看自然现象,孔子还曾明确指出:“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刘宝楠《论语正义》引)比德,即用山水的自然特性来比拟人们的美好德性,把自然景物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将山水看作是人的某种道德品质的表现和象征,看作人的某种精神拟态。“比德”说第一次揭示了人与自然在广泛的样态上可以互相感应交流的关系,在美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诗经》中描写景物,或状桃花之鲜,或尽杨柳之貌,或拟雨雪之态,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古简浑成,对后世影响极大,但多为比兴发端之词,即景物是情感的媒介与陪衬,是人事活动的背景,这种写法即受比德思想的影响。《楚辞》写景比《诗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瑰怪之观,淡远之境,重沓舒状,曼长流利,情韵悠悠。但总的说来,仍然是景为情役,而非独立自在,如《橘颂》虽通篇状物,但句句都是拟人,《离骚》中的美人香草,恶禽臭物也都具有比兴之义,与“比德”说的关系亦甚为密切。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构成自然界的美的是使我们想起人来(或者,预示人格)的东西,自然界的美的事物,只有作为人的一种暗示才有美的意义。”〔1〕不难看出,车氏此论与“比德”说有相同之处。它们都从社会性角度理解自然美,注重自然的象征意义,但又都忽视了自然美的形式特征和自然属性,忽视了人对自然具体生动的审美感受。同时,对象征与暗示意义的强调发展到了极端,就易流于简单的比附,如汉儒将自然景物与政教国运相比拟,就显得牵强,将自然现象的变化与瑞应凶兆相联系,就更荒谬了。“比德”说的这种缺陷,在庄子思想中得到了补充和矫正。《庄子·知北游》中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种“乐”并不是以自然山水为道德伦理的象征,而是外物触发起的具体感兴,是一种直观的愉悦和满足,与孔子所说的智者、仁者之乐很不相同。这种认识,较之于“比德”说,是对自然的一种更为纯粹的审美感受。但这种思想在先秦两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在魏晋玄学出现后,才重新为人们所重视,被引申发挥,成为整整一个时代“悦山乐水”的思想根源。
二
魏晋以来,社会现实的动荡不安,促使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就对自然美的认识而言,包含着两个层次的理论意义。首先是指理性的觉醒。玄学和老庄泛神论体系关于“天道自然”理论的重新认识与阐发,冲破了两汉谶纬神学和烦琐经学的桎梏,廓清了长期蒙在山水上的神秘灵怪和政教比附的迷雾,成为促使人们领悟自然美的契机。其次是感性的觉醒。生命的短暂,使人们更珍惜现世生活,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密度的利用。社会的黑暗,又使人们不能通过建功立业的渠道实现个人价值。于是,汲汲顾影,游放山水,属耳流目,极视听之娱,在苦难悲惨的现实之外追求片刻的快适愉悦,与先秦儒家否定或轻视耳目视听的感官娱乐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被扭曲的自然形象得以拨正,合理的感性追求第一次被充分肯定。这是思想的解放,同时也是自然的解放。
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层次性的逐步展开,山水也由人们赖以谋生的致用之所和取资之源,由个人品德和社会政教的比喻与象征,一跃而为独立的审美观赏对象。在诗歌中,山水原来仅作为人事的背景衬托、比兴发端的媒介,物色多而景色少,片断局部多而通篇整幅少,虚构想象多而记实写真少,变为身历目见的观赏和描写对象。朱光潜先生说:“兴趣由人事而移到自然本身,是诗境的一大解放,不特题材因之丰富,歌咏自然的诗因之丰富,即人事诗也因之得到较深广的义蕴。”“所以……是诗的发达史上的一件大事。”〔2〕登临赏玩名山胜水,不仅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而且用自己的感官领略到了山容水态,鸟语花香,获得了与井邑都市旨趣大异的快适和愉悦感,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述:“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羊祜镇守襄阳时,“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晋书·羊祜传》)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此外,如曹操的碣石观海,七贤的竹林放性,石崇的金谷邀游,王羲之的兰亭集聚会,陶渊明的采菊东篱,都是一时盛事,千古佳话。左思《招隐诗》其二说:“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山水胜过了丝竹,自然胜过人为,在诗歌史上,这确实是破天荒的新发现,它预示着诗歌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田庄环境的园林化,是晋宋以来庄园地主和贵族文士生活的一大追求,选择山水佳境营建别墅池馆,或在田庄内造园构景,这样就可以使远近胜概,历历在目。西晋的谢安、石崇、潘岳,东晋的王羲之、许询,刘宋时的谢灵运都有著名的别墅园林,就经济实质而言,这些当然都是庄园主侵占山林川泽,实行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结果,但从诗歌创作的生活积累角度来说,却对文士诗人熟悉热爱园中的峰林泉石,进一步观察发现山水自然美,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园林一方面可以实用居处,另一方面又可观照自然,不仅可以观赏园内的微型山川,袖珍林泉,而且,还可以通过“借景”的造园创作方式,观赏礼赞园外大自然。
关于自然山水对人的作用,在此时也有许多新的探讨,王羲之《兰亭集序》中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张华《答何邵诗》:“属耳听莺鸣,流目玩倏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榆。”谢灵运也说:“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这种娱乐,既不同于获得某种物质享受时的满足,又不同于道德追求时的欣慰,更不同于宗教礼拜时的迷狂情感。这是物的感性形式作用于人们的视听感官所产生的愉悦身心的快感,即美感。晋宋以来,文士诗人雅集,喜欢游山玩水,当然隐含着许多复杂的时代、社会和历史原因,但是,属耳流目的感性追求,能产生生理快适与心理愉悦,也当是重要的因素。
基于以上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把高山大川作为自然美来观赏完成于晋宋六朝时期,此时,“人们对自然的观念趋向成熟”〔3〕。山水文学“兴起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4〕。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魏晋以来,虽然玄学家从思辨的角度讨论言意、形神等问题,宗炳提出了山水“畅神”(《画山水序》)理论,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审美实践,就会发现人们更注意和沉醉的是茂林修竹、清流激湍、莺鸣燕语等物的外在形式,属耳流目,游目骋怀,主要为的是“极视听之娱”,为的是感官娱乐。《列子》一书,今已公认为魏晋时所作,其中《杨朱》篇宣扬的纵欲肆志,追求感官娱乐,可视为贵族文士纵酒放诞,属耳流目的理论说明。这种娱生恣体的享乐之风和纵欲思想,导致了对声色美的热烈追求,服药求仙,希冀生命绝对长度的延长。终究有些虚幻;于是尽量地把握住这现存的一刻,最大限度地发挥享受,以求得生命相对密度的增加。《抱朴子·崇教》非难汉末晋初的风气“唯在于新声艳色,轻体妙手,评歌讴之清浊,理管弦之长短,相狗马之剿驽,议遨游之处所,比错途之好恶,方雕琢之精粗”。虽有些偏颇,但却切中了时弊。新声艳色,饮酒纵欲为的是究欢尽娱,自然山水也是了为玩闻取乐。《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山水胜景竟然能使人“卒当乐死”,一方面说明自然对人的感性作用;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自然被降低到与药酒食性一般地位,仅供贵族文士作为满足欲求,尽情享受的代用品。再看《晋书·谢安传》的记载:“(谢)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这就更明显地说明山水丘壑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与艳色新声具有同等的作用。换言之,晋宋以来,人们更多地满足于山水景观的形体、色彩、音响等外在形式所引起的娱乐和快适,其实质说穿了是在声色狗马之外寻求感官的满足,构成这种渴望的基础是属于生理学意义上的追求。主客体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自然山水并没有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并没有与人发生相互感应交流的关系。
这种现象不光在自然山水欣赏上,在文学创作中也存在,刘勰从理论上提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要求写物抒情,互相结合,随物宛转中有情在,与心徘徊中有物在。但在创作实践中,却是:“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同上)极貌写物,穷力追新。山水画创作中,从理论上,自然美观念已萌芽,但山水画仍未从人物画科中独立出来,仅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宗炳《画山水序》中已提出“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但在作品中却往往“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历代名画记》卷一)甚至到了隋代展子虔、杨契丹,诏初阎立德、阎立本“尚犹状石则务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梧宛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同上)没有把握住客观对象的内在特征,所花功夫越多,反而愈显笨拙和呆板,带有严重的匠气,并不能高于自然美本身,达到神化的境界。
三
属耳流目,是感知自然的出发点,而不是终极目标;悦山乐水,极视听之娱,是山水美感的基本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和最高层次。直到盛唐,由于理论思维的发展和艺术实践的丰富,人们对观物审美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山水自然美观念才最后形成,并对唐代山水田园诗和宋元山水画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人对自然山水的新认识主要表现在:
一、由满足自然景物的外在形式,到探究山水的内在意蕴和意趣。在王、孟山水田园诗中,不光铺陈描写大自然的美景,而且更注意探究自然山水的“趣”,自然的奥秘。在孟浩然的诗中,经常用“探讨”一词:“探讨意未穷,回舻夕阳晚。”(《登鹿门山怀古》)“轻舟恣往来,探玩无厌足。”(《春初汉中漾舟》)就是说不光耳目玩赏,还要探讨求索,“不仅要在表面上的感觉,而且要在内心攀登解释的高峰”〔5〕。那么,究竟要探求解释什么呢?是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还是空洞的玄理禅机?诗人明确告诉我们,是山水所蕴含的意趣,是自然景物焕发的生机与灵气:“如何石岩趣,自入户庭间。”(《宿立公山房》)“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王维《晓行巴峡》中说:“赖谙山水趣,稍解别离情。”《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进一步认为:“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倏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名雊,斯之不远……然是中有深趣矣。”谈到他的山水画,前人也多以为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山水纯全集·后序》),“发景外之趣”(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四)。南朝宋时的宗炳就曾谈到“山水质有而趣灵”,峰岫云林,“万趣融其神思”(《画山水序》),但从哲学高度立论,且神秘玄虚。谢赫说:“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古画品录》)虽非专谈山水,但确是准的之矢。唐代皎然明确主张描写山水景物要写出它的“飞动之趣”(《诗评》)。可见,趣是自然界勃发出的盎然生机,是山川灵气回荡吐纳、卷舒取舍所呈现的律动,同时也是作者诗心观照澄映自然流露出的律化情调,在表现自然美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更深的艺术境界。在欣赏和表现自然时,如果“拘以体物”,就不能得物之“精粹”深趣,山水景物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若能取之象外,“度物象取其真”(荆浩《笔法记》),即可华奕照耀,动人无际。这种思想在西方文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华滋华斯《不朽的形象》中说:“我看最低的鲜花都有思想,但深藏在眼泪达不到的地方。”他的素体诗《丁登寺旁》表现“自然界最平凡、最卑微之物都有灵魂,而且它们是同整个宇宙的大灵魂合为一体的。”〔6 〕梵高说:“我在全部自然中,例如在树木中,见到表情,甚至见到心灵。”〔7 〕黑格尔则说:“外在因素——对于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贯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那外在形状的用处就在指引到这意蕴。”〔8〕
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由物我并峙对立,转变为物我交融、情景合一。晋宋诗人,除陶渊明外,大部分未能在山水诗中解决物我与情景的关系问题。对于六朝的贵族文士来说,自然只是他们属耳流目的玩赏对象,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远、神超理得的手段。用形象来谈玄论道,把山水作为体道悟玄的媒介,所谓“敷陈形而上者,必以形而下者拟示之”,自然界实际就并未能真正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主客体在这里仍然与观赏、思辨对峙着,于是出现情与景、心与物“截分两橛”的弊病。在唐代山水田园诗中,则多采用直寻兴会、缘物起情的方式:“悉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兴来无远近,欲去惜芳菲。”(于良史《春山夜月》)“竹屋临江岸,清宵兴自长。”(姚合《夏夜宿江驿》)心情意绪,兴寄内容往往因山水景物触动感发,从形象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即景造意,很少通篇说理而无具体形象,或整首形似之言,而无感兴之情,力求主客体的统一,心物的感应。并且,逐渐由相互外在的感兴交会,发展到相互内在的融契渗透,体合妙有。“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唐音癸签》卷二引)。如孟浩然《宿建德江》这首绝句,融情入景,思与境偕。“移舟”两句,随着缓慢疲惫的桨声,我们仿佛被摇入一个微茫惨淡、凉气氤氲的渚头,小舟系缆泊定,结束了一整天的漂流。然而诗人的一颗愁心却似乎要化入那一片空旷寂寥的暮色中,飘荡不定,无处着落。“江清月近人”,月影与人互相激射,彼此交流,在作者那落魄失意、索漠悲凉的心田上,洒进一缕慰藉的光,使人感到一丝的温暖,片刻的惬意。但是,当我们再仔细品味,就会感到,天野空旷,则显得诗人渺小孤独;与明月亲近,自是与人世疏远,在空间的大小远近对比中,潜含着诗人的隐痛和暗愁,表现出客居中的游人的被弃置的心境。这样,清江明月非但没有冲淡拂散诗人的愁云,反而和诗人的客愁因依含吐,交融复合,涯际不分,笼罩在整个建德江头。简短的四句,犹如亭阁楼台的四根擎柱,一方面,架构成了一个立体形象,凝固为一个空间景观,自成天地;另一方面却又涵濡着心灵,吞吐着宇宙,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是物的泛我化与人的拟物化的统一,是个人情思与自然景物的媾联结合。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写人与自然的感应交流,传达出独坐之神,与“江清月近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杜甫的“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亦体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三、正因为诗人观于山水,而不滞于山水;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不是满足沉溺于山容水态的感性形式,而是试图进一步探究山水之中的“灵气与生机”,以直观的方式体合宇宙人生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因此,就美感层次而言,已不仅仅是晋宋时期的“极视听之娱”了,而是怡神悦志——通过感官,获得一种超感官的享受,“在道德的基础上达到的一种超道德的境界”〔9〕。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主体的知觉分析与认知加工,经过整合而呈现的一种心态。如孟浩然的《春晓》,首句破题,第二、三句虚实相生,写出啁啾鸟鸣,潇潇风雨,此起彼落,远近应和,构成一个美妙而又缥缈的音乐世界。第四句则是诗人对大自然花开花落、变动不居的顿悟。全首从听觉引发想象,通篇猜境,诗人将自己的心灵沉浸到大自然的律动里,领略户外缤纷万象活泼跳跃的机趣,在人世烦扰之余,获得无所关心的满足,“如此等语,非妙悟不能道”(《唐诗合选详解》)。王维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则进一步展现山中景物的本等实相自由映发,天机毕露,活泼无碍,人与自然本样自存,无言独化,饮之太和。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说:“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幽人空山,过雨采萍。薄言情语,悠悠天钧。”说明唐人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已从具体步入抽象,从有限趋向无限,从空间进入时间,从人生跃入宇宙,从实有遥接虚空。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勿听之于耳,而听之于心,勿听之于心,而听之于气,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声,独闻和焉。”(《庄子·知北游》)抛开其神秘虚幻的外壳,正揭示了这种深层的审美境界。诗人可以在感性自身中求得永恒,在这时空中超越了时空,身与物化,达到所谓“至乐”“极乐”的境界。恩格斯谈到自然美欣赏时曾意味深长地说:“当大自然向我们展示出它的全部壮丽,当大自然中睡眠着的思想虽然没有醒来但是好像沉入金黄色的幻梦中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在大自然面前什么也感觉不出来,而且仅仅会这样感叹道:‘大自然啊!你是多么伟大呀!’——那么他便没有权利认为自己高于平凡和肤浅的人群,在比较深刻的人们那里,这时候会产生个人的病痛和苦恼,但那只是为了溶化在周围的壮丽之中,获得非常愉快的解脱。”既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虽超脱,但又非出世,唐人和唐代山水诗文中对自的态度,即此可见其大指。宋元写意山水画、明清造园艺术的空灵意境和独特神韵,亦与此观念息息相关。
注释:
〔1〕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第10页。
〔2〕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
〔3〕石夷《从“望秩于山川”到“悦山乐水”》,《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
〔4〕崔承运《试论山水文学的兴起及原因》,《学术月刊》1985年第5期。
〔5〕今道友信《关于美》,第165页。
〔6〕王佐良《英国文学论文集》,第79页。
〔7〕《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第38页。
〔8〕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480页。
〔9〕《李泽厚哲学美学论文选》,第41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册,第3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