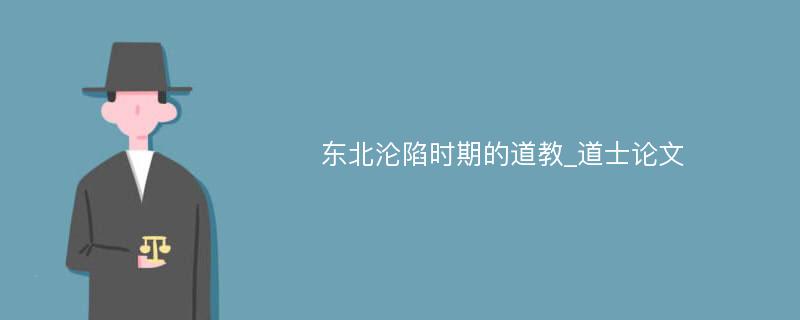
东北沦陷时期的道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教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宗教,是中国的儒、释、道三大宗教之一。它在古代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融汇了巫祝、符录、神仙方术及黄、老道家的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一种多神教。道教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风土和地域条件下,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中产生与成长的,并形成了具有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宗教。是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综合性文化形态。道教经典总集《道藏》,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它涉及哲学、伦理、政治、军事、文艺、音乐、美术、医药、养生等诸多方面,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
道教传入东北地区,始于唐代,兴盛于金朝,在清代和民国年间流传较广。在东北沦陷时期,深受日伪政权的残酷统治和高压控制,亦趋衰落。
道教的传入
唐代崇重道教,是因唐朝皇帝与老子同姓,故重道胜于佛。唐代因此而道教盛行。624年(唐武德七年),道教已由中原传入朝鲜半岛,由此间接传入东北地区。在698年震国(渤海国前身)建立后,道教传入了东北地区。渤海国受唐册封与唐朝往来密切,道教具有较强的汉民族文化特点,因而渤海国在大量吸取汉唐文化的历史背景中,道教得以盛行发展。传入初期,道教先后在五京等地广泛流传。道士、女冠在信徒中从事“降魔治病,祈福禳灾”等道教活动。
辽灭渤海国后,道教仍受青睐。从辽至清,朝代更迭,道教兴衰起伏,却一直延续下来。金代,《大金国志》记载:“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滹南集》载:“太乙之教兴于金朝天眷间,崇重道流,金时独盛”,可见道教在东北地区流行的一斑。
道教大量流传东北地区是在清初时期,清顺治年间,清政府虽然对道教采取了控制和削弱政策,但是后来在开关放边疆、巩固大后方和引进中原文化等策略下,却放宽了东北地区的道教限制。1653年(清顺治十年)清政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施行16年后停止。其间,汉族人士、各种工匠的进入,东北地区人口的汉族比例上升,道士和道徒也随之增加,道士逐渐在境内积资兴建道观。旧《铁刹山志》载,东北道教缘起于“三山”,即辽宁本溪的铁刹山(云光洞)、辽宁千山(无量观)及锦州北票的医巫闾山(海云观)。
东北地区最古老的道观是本溪铁刹山云光洞,据考证是明末年间,道教龙门派第八代传人郭守真(道号:静阳法师)从山东省墨县马鞍山聚仙宫渡海来到东北,开辟了铁刹山云光洞,与弟子八人宣道布教。康熙二年(1663年)北京城内将军乌库礼请去求雨,其功显著,深得将军崇拜。此后,在辽宁省沈阳城外创立了道宫“三教堂”,后改为“太清宫”作为十方丛林。
太清宫是东北区最大的道观,也是东北地区道教的中心和入道得度受戒的唯一道场。从清代道光三年(1828年)起,开始传戒,至1944年间,太清宫传戒约10次,先后有传戒弟子三千三百余人。它对清代末年及近代中国道教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太清宫建立初期收度弟子六人,其中名为刘太静的道徒继承祖师入了铁刹山成为道教关东龙门派第九传人。之后太清宫道师开创了辽宁千山的无量洞道观和医巫闾山的海云观等道教圣地。并且分别派遣弟子主持日常勤行。太清宫的宣道布教活动逐渐发展到了黑、吉两省地区。
千山道观是铁刹山云光洞教主郭守真的道统支派。作为道教的灵域不仅在东北地区,而在中国和朝鲜半岛乃至日本都是闻名遐迩的。据考证,千山共有六寺、五庵、六宫、二十观。六寺五庵是佛教圣域,而六宫、二十观正是道教的代表。千山的佛、道融合表现最为突出,有些庵内的主持则由道士担任,千山形成道教势力的天下。在千山道观中最有影响的是“无量观”,而“无量观”管辖了太和宫、清云观、洪谷庵、南泉庵、慈祥庵、圆通观、凤朝观、五龙宫等二十余观。千山道教法统是郭守真太师的两位弟子王太祥、刘太琳,于清朝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创建的。这两位始创祖师按照道教龙门派“百字辈”法规,将千山道场相传至今,形成金诚泽监院著名道场。
医巫闾山位于锦州北票。地处新县、义县、北镇县的三县境内。雄据一方的医巫闾山脉,共有二十余道观。北部山峦邻近三县交界,景致绝佳,苍松翠柏,山青水明,雅趣幽深。是当时东北地区的著名景观之一。宏伟而古意盎然的道观建筑群,修建在古柏苍松复盖的山峦之中。面向县崖峭壁、耸立山顶的道观群,隐居着数百名道士。在望海山、尖山、空隆山、老爷岭、千家塞、大芦花等山峦之中,散在的道观有被世人誉为“蓬莱仙境”的大猗观音阁、大芦花海云观、玉泉寺、千家塞圆通观、大朝阳三清观、老爷岭圣清宫等。
道教派别、宫观、法事及节日
东北地区的道教内有着隶属门派谱系的师承关系。虽然各派在信仰上均以老子为道祖,及张陵为天师为教祖,但是又师承各自的门派祖师、祖庭。形成了地方性的法统师承关系而沿袭传承,因而产生了道教的宗派。据考证旧志谓:中国“道教宗派复杂,有36宗、72派之说。”但是普遍之说有六十四派,还有六十八派、九十九派和一百零二派等传说。东北地区的道派清朝以前大多属于天师道派系,清代开拓边疆后,发展起来的道教基本为全真道派系。
道教的宗教活动场所统称“道观”或“宫观”,有别于佛教寺庙的称谓。具体的名称尚有宫、观、阁、庵、洞、坛、院、祠等。由于道观的大小、功用、宗派的不同,称谓亦不一致。唐代传入渤海的天师道其所有道教场在家里设坛,还有在山林专设道坛、道舍。全真道派在清朝传入东北地区后,两道派的道场,可概括为正一派道观和全真道派道观两大类型。两派共有子孙庙观,而全真道派尚有十方丛林道宫和以男女之别的外堂道观、里堂道观。
道教十方丛林是道教规模大的道场。主要特点是向天下道徒开放,设坛传戒。不论何方道士,均可前来“挂单”,在此留宿、生活并可以参加受戒,道教称之“律门”。东北地区在伪满时期道教十方丛林仅有三座。即:黑龙江省尚志县帽儿山的太和宫、吉林省桃源山的蟠桃宫、沈阳市小西关的太清宫。
子孙庙观是同宗派师徒世袭相承的道教场所。东北地区的正一道除了自家设坛,均是世代传承的子孙庙观。全真道派出家住观修行,他们所住的道观,除十方丛林之外,都是师徒相传的子孙庙观。伪满时期的东北地区的道观据考证,共有1860所。正一道派的子孙庙观是男女道士同居一庙观;而全真道派的子孙庙观则男女有别。男道士所居道观称为“外堂道观”、“居乾道”;而女道姑所居道观称为“里堂道观”、“居坤道”。然而男女道观却又无严格的界线。有时乾道坤道交换住持。如1930年建于黑龙江省绥化县的蟠桃宫,先以男道士为主持,后换成女监院任主持。
道教法事,即如法行仪,规定严格,且内容繁多。除了道士个人修行炼养、习施道之外,主要有皈依、玄门日课、祀典、斋醮、开光、传戒等活动。
道教的节日是以神仙诞寿为庆典仪式活动的,其节日均使用农历纪年,每年的节日庆典活动颇多。主要节日有“三清节”;即冬至日元始天尊诞辰、夏至日灵宝天尊诞辰、2月15日道德天尊诞辰。正月初九日玉皇大帝诞辰。三月初三王母娘娘诞辰。三元节:正月15日上元天官节、7月15日中元地官节、10月15日下元水官节。6月24日关帝圣君诞辰。3月15日张天师诞辰节。
东北地区道教节日对民间社会影响较大的是每年农历4月18日、28日和6月24日的3个节日和7月15日中元节(佛教称孟兰会)。是国内其它地区所不同的。每年这三个重要节日,道观门外一带商旅云集,百货、食品摊床林立,民间艺人也临场献艺,吸引游人过客,俗称“庙会”。这三个节日是道观每年收入最多的时候,并且盛况不减。东北地区较为有名的道观“庙会”有:黑龙江省铁力县关帝庙、吉林桃源山的蟠桃宫“庙会”等等。
然而,到了清朝后期和民国年间,道教受到中国社会急剧的革命性的变动出现了生存危机,道教理论的停滞落后和活动方式的陈旧杂沓成为衰颓的重要内在因素,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团体,亦趋衰落,不复昔日壮观气象。但是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在民间影响则有增无减,已成为普遍性的国民文化。特别是,东北地区道教从明清时代起已形成的社会性民族信仰的基础上沿袭下来。长期以来,与官民大众的婚丧嫁娶喜庆祭祀紧密相连,成为社会风俗习尚,而且相沿成习的民间行业的宗教风格,以民间习俗的强大惯力发展流传。并成为国家政府行为。例如:黑龙江省的黑河朝阳观是民国步兵第三旅司令巴英额创建,黑龙江省的延寿的关帝庙中保存镌刻的《延公德政碑》、《谢公德政碑》、《李公德政碑》等,借助道教政府表彰和记念保境安民的地方官。而且当地政府的军政部每年春秋两季在本地关帝庙举行阅兵典礼,十分隆重、盛大。
东北沦陷时期的道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强占了中国东北地区,为了统治文化传统悠久、文化意识较之高于自己的中华民族,深知仅凭借军事力量进行镇压而取得的暂时成功是远远不够,必须采取相应的文化殖民主义政策,达到消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的独立性,使其成为永久的殖民地被奴役者。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寻求“西方列强文化侵略模式”的启示中,得出了“弱肉强食”和“皇道主义”的殖民扩张主义的指导理念。在“伪满洲国”殖民统治过程中,以这种理念为统治方针,极力推行了政治“存异”、文化“求同”的殖民扩张主义政策;即以弱肉强食的原则为依托的政治“存异”和以“皇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求同”的殖民政策。使之达到全面、彻底地殖民统治目的。
日伪政权统治时期,是东北地区道教被进一步抑制和削弱时期。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1年至1939年间,是逐步纳入殖民化监控的时期。这一时期,其特点是在政治“存异”殖民政策指导下,作为政治“存异”而保留加以严控并利用。日伪政权深知“与满洲国精神相距甚远的道教,不能寄希望于他们教化世道人心,…但是作为满洲固有宗教,由于它能在无意识之中与民众心理融合,其作用不可轻视。”因此须小心防范,控制其一切活动。从1932年至1938年间,日伪政权指派一些所谓的“学者”或“僧侣”之徒,对东北地区道教的各种活动进行详尽的调查,1938年9月出笼了《取缔满洲国寺庙及布教者暂时规定》的取缔令。在《暂时规定》取缔令的第一条至第十条里:“凡建立和现存的寺院及所属财产、布教方法、同国内外的联系、经费来源及支出等等宗教事务必须呈报民生部大臣审核,寺院的道士、主持等人也经民生部大臣登记准许,方可活动。民生部大臣认定存有违反公益事项或其它不应准许存立之事由,则可加以取缔和施以处罚。”第十一条:若有寺院代表人消极抵抗,本条例按上述条例进行取缔及处罚。将东北地区的道教禁锢在“暂时规定”的取缔令和后来频繁发布的统治训令的严格监控之下,限制了道教的各种活动。
与此同时,日伪政权的民生部厚生司还指令沈阳太清宫筹建伪满洲道教总会,迫使与全国道教总会分离。1939年于伪满洲新京(现长春)正式成立。会长为沈阳太清宫方丈纪至隐,副会长为沈阳太清宫监院金诚译和医巫闾山海云观监院马崇还。下设若干名理事和常务事理,会址设在长春。总会下设若干分会,其中王圆方道长任伪满洲新京市道教总会会长。为此日伪政权设立半公开的官方机构协和会进行直接控制。警察署、宪兵队及协合会的人经常监视并限制各地区道观及道教的一些宗教活动。因此道教举行的一些宗教活动,规模和盛况已不如往年,例如:黑龙江省唯双城无量观被日伪政权指定为“特殊寺庙”,“北满”(黑龙江)地区唯一可以传戒的道观。但是仅在1933年,经日伪宗教部许可下,由日伪指令的道教总会主持,举办了一次规模颇大的传戒活动。前往参加的高道有沈阳太清宫龙门派22代传人金诚泽方丈,并为传戒法师;医巫闾山海云观马崇还道长为证盟大师;铁岭园通观罗崇礼道长为监戒大师;双城无量观宋从吉道长为保举大师;千山无量观越诚藩道长为演礼大师;千山青云观杨诚山道长为虬仪大师;千山慈祥观赵宗衡道长为提科大师;拉林关帝庙刘明哲道长为登录大师;哈尔滨正宫娘娘庙许信友道长为引请大师,各科大师共三十余位。此外还有纠察、导值大师多人。传戒活动受日伪政府所限制,百日戒期仅仅做法30天。此次受戒道士共有五百余名,也是黑龙江地区近代道教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宗教活动。
第二阶段是从1939年至1942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把日本神道思想强加于中国道教之上的文化“求同”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把东北道教强行植入“皇道主义”,使之达到文化整合的范围之内。从1939年以后,日伪政权强迫道教各地的道观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三拜九叩大礼,改为行日本式三鞠躬。并在道教的节日里强令加进“纪元节”、“天长节”、“建国神庙创建纪念日”等协合式的祭祀活动。强制东北道教总会以维护“一心一德、日满亲善、王道乐土”为宗旨。在各地庙会中,以宣传日本“皇道主义”为主,庙会其它活动为辅,利用庙会活动为“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的殖民政策服务。在东北地区所限定庙会中,大量的协和会人员进行着日本宗教的宣抚工作。1940年的伪满洲国民部社会司的《宗教调查资料》中,详尽地报告了各地的庙会活动情况,其中就协和会工作不尽满意而提出指导:“在娘娘庙、关帝庙的庙会期间,民众聚集,对庙会所做工作仅局限于放焰火、放电影、设置免费休息处等,使庙会更加隆重则远远不足,这是宣传‘皇道’新宗教的重要时机,应努力通过新宗教去发扬国民精神,以纠正错误的宗教观,显现新宗教的真正价值。”由此可见,日伪政权在推行“皇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求同”时,以期达到“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的同化东北民众之目的,是多么处心积虑地利用当地的宗教文化活动。
第三阶段是从1942年至伪满政权垮台,协和会组织渗透到各种宗教活动之中,使道教活动全部纳入日本的“战时体制”之下。日伪政权从1943年春颁布了“东南亚战争时局刑法”后,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的短短两年时间里,通过协和会迫使道教进行了各种支援“大东亚圣战”的活动。例如:日本侵略军在东南亚地区每侵占一处,协和会立即指令各道观为庆贺“胜利”做祈祷仪式。协和会还经常以战时军需为由,强行收缴道观、道士的财产,充为军备品。例如,“铜铁金属献纳”支持圣战活动,迫使道士将道观里的门窗及箱柜上铜铁饰物卸下来“献纳”,甚至铜佛像和道观牌匾也不放过。同时,强迫道士“勤劳奉仕”义务劳动,为战争效力。以“献身国防”、“勤劳奉公”为名,强令青年道士参加战争工程施工,如:擦炮弹、修公路、修碉堡等,直接为关东军服劳役。并且将壮年道士集中各地,名为“宗教报国挺身队”,规定秋收全部上交“出荷粮”。除协和会要人之外,宪兵、特务经常公开对各地道观加紧搜寻盘查,并且盘查愈加频繁严厉,道观的主持和监院数次被传讯,令其交待活动,言行稍有不慎,定遭到处罚杀戮。
在日本军国主义强占中国东北地区十五年间,他们为了消除中国民众的传统观念和宗教信仰,灌输“皇道主义”的殖民精神,培养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意识”,所强制推行的殖民政策,极大的伤害了中国民众的宗教感情,而且使趋于衰颓的东北地区道教团体遭受更大的摧残。据1945年满洲铁道总部调查科《满洲宗教调查报告书》所统计,东北地区的道观仅剩一千八百六十座,其中相当一部分名存实亡已占为其它用途,道士仅存二千八百余名,已严重衰微,呈末世光景。
战争结束已经过了五十余年,日本少数极端分子仍坚持错误的历史观念,否认危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事实与责任。因此,了解与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宗教文化,探讨当时的社会网络和历史轨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批驳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侵略有功”之谬论。
标签:道士论文; 太清宫论文; 道教门派论文; 日本道教论文; 中国节日论文; 东北文化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庙会论文; 千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