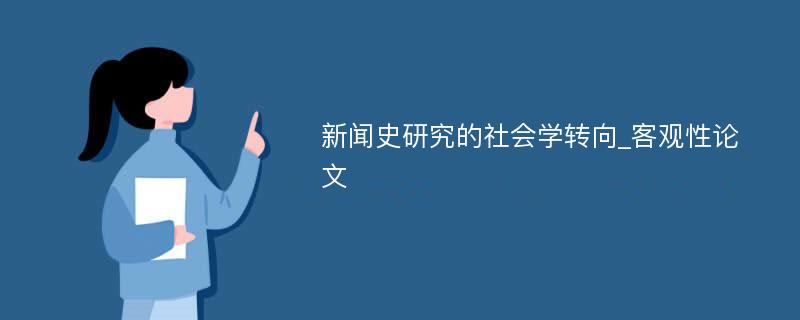
新闻史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史研究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国际传播学会(ICA)第66届学术年会(日本福冈,2016)上,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教授于1978年出版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Discovering the News: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一书,获得国际传播学会的最高学术奖“国际传播学会院士图书奖”(ICA Fellows' Book Award)。在该奖项自2000年创设以来获奖的13部著作中,除了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的《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外,这部著作是出版最早的一部。[1] 新闻与传播学界都知道,舒德森教授的学术作品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出版和发表,他本人在学术界也十分活跃,仅在日本福冈举行的这次ICA学术年会上,他就发表了一篇论文、参加了一场会前会(Pre-conference)并做了精彩的点评。在ICA发表的论文中,他研究了战后美国新闻理念的变迁—关于透明度的问题,与38年前研究客观性的《发掘新闻》刚好同在一个逻辑,是他2015年的新著《知情权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ight to Know)的提炼成果。他个人也曾表示他的学术已经比起初出道时的《发掘新闻》要进步了许多,2008年他为我和常江翻译中译本而写的序言,就明确说明过这一点。但是,为何他的这部出版了38年的著作,能得到评委会的青睐而独获此奖呢? 一、ICA院士图书奖及对《发掘新闻》的评价 ICA院士图书奖(ICA Fellows' Book Award)是目前国际传播学会的最高奖,该奖项设于21世纪初,是由全体ICA的院士(ICA Fellows)[2]自由提名,再由评委会投票议决。本届评委会的组成,是来自世界各地的5位著名的院士:主席是美国的Steve Jones,委员包括美国的Sandra Calvert,英国的James Curran,丹麦的Kirsten Drotner以及中国香港的陈韬文。评委会的意见认为:[3] 我们觉得这部著作富有创意、睿智、自信,写作精良。运用情境化的媒介史研究方法,该著作提供了一个沿着新闻与报纸的不断进化来理解美国新闻业的思路。它充分运用一手、二手的资料加以研究,清晰地表明了社会、文化、政治、商业与媒体的互动驱动了美国报纸的进化,而不是关注个人或机构。该著作强调媒介史上的变革是清晰地与嵌入其中的更宏大的文化的、社会的时刻相交融的。该著作激发了后面几代媒介学者去探究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形态下的新闻业和媒体。 与此同时,五评委之一的陈韬文教授在仔细斟酌之后,给笔者发来了他自己的评价。[4] 除了评委会的评价外,我想强调的是此书以多层次的历史资料回答新闻客观性以至专业性出现的过程及成因,个中讲究实质证据及逻辑推理,为研究的理论提问提供具有说服力和想象力的答案,成就了一个社会史模型,无疑是以历史方法研究传播理论的时代典范。 从如此高的评价中,可以了解《发掘新闻》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获得ICA院士图书奖的作品必须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出版5年以上)、在传播研究领域产生过与众不同的、根本性的影响,[5]作者必须是传播学的学者。也许是由于要求很高,2000年开始创设此奖以后,首届奖颁给了已故学者罗杰斯(Everett M.Rogers)的《创新的扩散》,但之后有几年该奖项空缺,17年来仅有13部著作获奖。而舒德森教授尽管有多部著名而有影响力的著作,但获此殊荣的,唯有这部处女著作《发掘新闻》。 二、舒德森其人 首先,还是想说明一下,美国人读Schudson时的发音,其实更近似“夏森”,或者至少更接近“夏德森”,而不是我们现在采用的“舒德森”。我在2002年写过的一篇文章,当时称呼他是“夏德森”。不过我们翻译《发掘新闻》时还是采用了“舒德森”,而中国的读者都已经习惯了“舒德森”的译法,所以现在就约定俗成了,这一点与Wilbur Schramm被称为“施拉姆”、Times被称为《泰晤士报》是一个意思。 迈克尔·舒德森是当代美国也是当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史、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资深教授,2006年以来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同时兼任哥大社会学教授。他本科就读于著名的文理学院索思摩学院(Swarthmore College),于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博士,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76-1980)、加州大学(圣迭戈)(1980-2009)。 舒德森教授迄今著有8部专著:《发掘新闻》(Discovering the News,1978)、《广告:不舒服的劝服》(Advertising,the Uneasy Persuasion,1984)、《美国人记忆中的水门事件》(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1992)、《新闻的力量》(The Power of News,1995)、《好公民》(The Good Citizen,1998)、《新闻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News,2003)、《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Why Democracies Need an Unlovable Press,2008)、《崛起的知情权》(The Rise of the Right to Know: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Transparency,1945-1975,2015)。此外他还参与主编了3部著作。他的著作有5部已有中文译本,有的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书。 舒德森教授得过多个奖项,包括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端研究中心”的Guggenheim Fellowship、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genius” fellowship)等。1990年他被提名为麦克阿瑟学者时,该基金会对他的评价是“公共文化的阐释者,集体记忆和公民记忆的阐释者”。《美国历史》杂志认为,他的《好公民》一书“中肯、富于创造力,而且实事求是”,《经济学人》杂志敦促所有的美国人都应去读一读。《泰晤士高等教育》认为《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意味深长、充满智慧”。当然,最近也是新闻与传播学界最“正宗”的奖,要数“国际传播学会院士图书奖”(参见图2)。 舒德森教授在他的中译本序言里,“很高兴地看到在今日的中国,人们重拾对新闻学的热忱和对新闻业历史研究的兴趣。”2015年春,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上海访问4天(其中一天去了杭州),在复旦大学的讲座开场时,他提及他的父亲是一名美国空军杂志编辑,曾于1944-1945年来上海,作为美军人员参与了日本向中国投降过程中的相关工作。他虽然没有更多时间亲身了解中国,但他在上海期间还是挤出时间接受了中国学者和记者的采访。他对笔者也表示他很愿意将来到中国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 三、《发掘新闻》历久不衰之谜:新闻史研究的转向 《发掘新闻》是舒德森教授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三十多年来历久不衰。他在为中译本写的序言里也说到了他三十多年学术生涯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广、口碑最佳的,便是这部《发掘新闻》”,虽然,他自己觉得后来写出了更好的书,但是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其他地方,却没有任何一本他的其他书如《发掘新闻》这样赢得如此热烈反响的。他显然表现出一种困惑:为何人们对这部书这么热衷?他甚至用很严肃的学术态度,深入审视并批判了自己的这部成名之作,认为该书忽略了政党政治对新闻业的影响力;反省自己是用社会学的框架去做的设想和问题,只是道出了各种相似行业的普遍性,而缺乏新闻业的特殊性;只是分析了美国特色的新闻界及其规则的形成,没有充分重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为此他对该书为读者贴上了“警示标签”。当然,他的《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和《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于2010年和2014年先后在中国出版中译本后,其实也很快在学界畅销,不仅新闻学界,而且非新闻学的学者们纷纷撰写评论、引发讨论,甚至众多学界以外的人们也争相阅读。 而《发掘新闻》的意义,不仅讲述了新闻界唯一可称作旗帜的原则“客观性”在美国从无到有的故事,而且它开创了美国新闻史研究的社会科学路径。 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新闻史研究在西方和中国有着不尽相同的地位,但却面临着共同的困境,那就是如何锚定自身在历史学科和新闻学科中所据有的地位。 在西方,新闻史研究长期以来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明确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更为宽泛的媒介史(传播史)区分开来。不妨说,由于长期受限于媒介史的思路,新闻史研究始终缺乏某种可为学界普遍认可的独特价值。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在1974年《新闻史》(Journalism History)杂志的创刊号上曾专门刊文,尖锐地指出:“新闻史研究迄今始终是一个捉襟见肘的领域。”[6]凯瑞的这番锐利的评述,是针对当时美国新闻史研究的三个普遍性倾向而言的:第一,研究者大多持有改革派的立场,并在此立场上对新闻业的历史做出不无偏颇的阐释;第二,一味深掘史料,而缺乏足够的现实关怀,与新闻的天性相抵牾;第三,“纪传体”色彩强烈,自始至终十分关注著名出版人、记者和编辑的经历,缺乏科学的规律性梳理。实际上,长期以来对新闻史和新闻学研究持悲观态度的知名学者不仅凯瑞一人。舒德森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曾用“老古董”(antiquarian)一词来形容新闻史研究,意指该领域始终存在的显著的价值判断和人文主义色彩;[7]在他看来《发掘新闻》的成功似乎并未令美国新闻史研究出现根本性的起色——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事实。 上述问题直到现在也仍然困扰着世界新闻史研究的某些领域。例如,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马丁·康博伊(Martin Conboy)便在2010年撰写的反思文章中指出,当下的(西方)主流新闻史研究存在五方面的问题:缺乏对“新闻”及“新闻业”等核心概念的普遍共识、以回顾历史的方式考察着眼于未来的新闻这一行为的内在分裂性、无法兼顾国家和全球语境、过分强调新闻的流行品质有可能导致对新闻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功能的不正确认识,以及总是倾向于对技术变迁进行“驯化”(domesticate)而不能正视新技术所驱动的行业创新。[8]在康伯伊看来,对于新闻本体认识的含混和新闻史研究方法论的保守性,自始至终都是该领域须不断警惕和反思的“原罪”。 但事实上,今时今日的情况已与70年代初不可同日而语。由于社会学对传统新闻学的大举“入侵”以及大量接受过严格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进入新闻研究领域,并在80年代出版有影响力的著作,新闻史研究也开始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新的著述越来越多地将新闻业置于社会、文化和政治史的宏大脉络中加以考察,而且工作量浩大的内容分析法也开始成为新闻史的重要方法。”[9]这一“社会学转向”的发生,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新闻史研究的面貌,也为该领域的发展演进提供了新的标准;而这一“转向”的发生,无疑以迈克尔·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的出版为滥觞。 本文重顾《发掘新闻》一书的文本,并尝试从理论视角、方法论和观念遗产三个角度,对本书的内容、主旨和价值进行深入的“发掘”,从而反思前沿社会学对新闻史研究可能具有的潜力。 四、理论视角:超越描述与阐释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新闻史研究的视角主要有描述性研究和阐释性研究两大类。前者以曾供职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雷德里克·哈德森(Fredrick Hudson)于1873年出版的《美国新闻业》(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为滥觞,多按报刊、广播或影视媒体的产生、发展和演进脉络,广泛搜集史料、事无巨细地呈现史料,尤其注重对重要机构和人物的介绍。而后者则以莫特(F.L.Mott)于1941年出版的《美国新闻史》(American Journalism)和爱默里(E.Emery)于1954年出版的《报刊与美国:大众传媒解释史》(The Press and America: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为代表,这种视角强调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情境中去解读新闻业的发展,超越了从新闻业自身的史料出发去总结新闻业发展规律的狭隘思路。[10] 从描述视角到阐释视角,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种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倾向的产生,那就是研究者逐渐正视新闻业与其他社会机构和社会领域之间相互构成,甚至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不再试图将新闻视为一个绝对独立而自洽的领域。对此,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安迪·塔克(AndieTucher)教授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她说:“新闻既是文化的参与者,也是文化的后果,研究新闻史的本质也就是研究社会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告诉自己哪些故事是重要的,并且将这些故事作为真理来接受。”[11]当然,新闻史研究的主流视角在20世纪中叶从描述式研究转向阐释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叙事(narrative)方式的改良,而远谈不上是理论视角的革命,这是因为,新增的阐释性的内容,其实仍无法脱离人文主义的价值判断色彩。由于无法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故这些史料翔实、适于作教科书的著作,其实无法对行业发展的规律做出科学的总结。其中一个最显著的问题,便是新闻史研究者对新技术及其可能给行业带来的改变的忽视。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电视机开始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进行家庭普及,但作为新媒体的电视对业已成熟的广播新闻生产可能产生的颠覆性的影响,却并未受到当时的绝大多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大多将方兴未艾的电视新闻简单视为广播新闻的“视觉形式”。[12]持人文主义倾向的研究者仍认为新闻业的一些基本价值规律,如“新闻价值”(news values),始终具有超越媒介平台的普适性,不因印刷、广播和电视等媒介技术的不同而有本质的差异。1959年的一项针对(早期)电视新闻的研究甚至对电视媒介本身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指责其“为视觉而视觉”的特性违背新闻价值规律,导致了大量时间被浪费在不重要的新闻事件上。[13]针对媒介的文化批判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这不应当是历史研究者的任务。 因而,阐释式研究思路最主要的问题体现于,在认同新闻业的非中心化特征的同时,却又认定新闻业存在高度稳定、不会被社会变迁所改变的价值内核。这一问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第一,新闻史研究由于始终倾向于将“新状况”和“新语境”纳入某种“永恒”的规律中加以解释,甚至认为前者应当对自身加以改变去适应后者,一如约瑟夫·弗兰克(Jeseph Frank)于1961年所斩钉截铁指出的: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政治)新闻的基本规律,早在1655年于英国出现的报纸雏形阶段便已形成了。[14]第二,所谓的解释,其实是带有强烈人文色彩的价值解释,而非科学的、理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因而成了一套关于新闻业的带有伦理学色彩的规训性话语,它所强调的是新闻业和新闻从业者“应当如何”,而在这套话语的支配下,对新闻业发展演进规律的准确归纳也便无从谈起。 但《发掘新闻》的出版,超越了上述思路。它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以社会科学而非人文科学为主导性理论视角的新闻史研究著作。在此书中,舒德森开宗明义,直接将矛头对准了被传统新闻学视为一般性规律的“客观性法则”。他反问:“为什么批评人士认为新闻业就理所应当应该客观呢?商业性机构的第一要务就是生存,要求它们客观真是很奇怪。同样的,由于沿袭历史的原因,这些机构有的公开支持某党派,本身便带有政治性,对其提出客观性的要求也是很奇怪的。编辑、记者并没有似医生、律师或科学家那样的专业性机制,要求他们客观,也真是奇怪。”[15]事实上,这部著作之所以在新闻学和新闻史研究领域拥有巨大而持续的影响力,主要原因便在于其对美国新闻业的一项通常被视为“不言自明”的行业价值标准——客观性法则——做出了冷峻的考察。通过深掘史料,舒德森发现,滥觞于便士报时代的美国现代新闻业,其实长期以来只是强调新闻事实信息的准确(accuracy),以及事实(fact)与观点(opinion)区分开来这两项操作性的准则,所谓的客观性则无从谈起;在1894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新闻业入门》(Step into Journalism)的业务手册中,甚至强调优秀的记者应当“持重和文采并重”,即使记者没有目睹事件,没有当事人的直接陈述,也可以运用想象力创造出一幅幅画面来。[16]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现代报业得以迅速成形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美国新闻业经历了两个巨大的变化:新闻职业的出现以及报纸的工业化。以纽约地区为代表性个案,舒德森归纳出不同种类的报纸为迎合工业化转型社会中的人的不同需求,而做出的两种不同的风格选择:他将以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报团旗下的《世界报》为代表的娱乐化风格称为“故事模式”,而将奥克斯(Adolph Ochs)主持下的《纽约时报》所倡导的严肃、庄重的风格称为“信息模式”。舒德森并未如传统新闻史家一般对两者做出高低优劣的判断,因为这两种风格的形成在他看来都是社会变迁导致的报纸功能分化和读者社会分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世界报》……对新近接受教育的群体、刚从乡村进城的群体、工人阶层和中产阶级而言……恰好忠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时报》奠定其‘高级新闻’的基础则在于它迎合了特定社会阶层的生活体验,这类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较强的操控力。”[17] 在舒德森看来,即使在报业迅速发展、高度发达的19世纪末,美国也未能出现得以哺育客观性法则的土壤。但毫无疑问,“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的差异和矛盾,预示着美国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程度正在日趋加深,这种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特定外力的刺激下,则完全有可能导致共识的分裂,乃至冲突的产生。舒德森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富裕的中产阶级逐渐搬离城市、移居近郊,“前所未有的阶级隔离”出现了,这一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以新的方式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地理学局面”。[18]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导致的惨绝人寰的后果,使得民主市场社会的价值和内在逻辑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质疑,极端怀疑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和精英阶层中弥漫,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民主制度和“公众”(the public)的尖锐质疑。反理性思潮波及新闻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公共关系行业的崛起,以及“事实”的衰落和记者职业的存在危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新闻业被迫做出了自己的反应:这种反应体现在业务层面上,是阐释性报道的兴盛;体现在观念层面上,则是客观性理念的滋生。用李普曼的话来说:“当我们的头脑深刻意识到人类思想的主观性时,我们的心灵却前所未有地迸发出对客观方法的热情。”[19]以李普曼为代表的新闻从业者和以普利策为代表的报业巨头,开始呼吁新闻专业主义教育,主张以“方法的统一”而非“目的的统一”来推动新闻业的专业化。至此,“客观性理想至高无上”的信念开始在新闻从业者中深入人心。 舒德森对客观性理念在美国新闻业出现过程的考察,与其说是对传统新闻史研究思路的简单反驳,不如说是一种探求(美国)现代新闻业发展规律的尝试。由客观性法则的从无到有,舒德森发现,新闻业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决定论式的;新闻业的发展演进既是社会互动的一部分原因,也是社会互动的一部分结果。他选择客观性理念作为归纳和挖掘这种规律的切入口,原因便在于该理念恰恰是新闻区别于其他纪录性社会机构和文本形态的核心所在。于是,不但现代新闻业的变迁规律得以厘清,新闻史相对于一般性的媒介史的独特性也得以彰显。他明确指出新闻业有其独特的使命,至今他依然强调新闻在一个民主国家是必要的,至于是印在报纸上,还是发在网站上,或者出现在APP里,在他看来无关宏旨。他不久前还强调美国的新闻业这么多年来不断发展,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市场本身以一种复杂的机制在运作,促进了媒体间的竞争,激发优秀报道的生产;二是记者开始讲求新闻专业主义,并持续加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记者不再以熟知体制内幕的知情者为荣,而开始追求监督的功能。这一观念引领着美国的记者,也深深影响了全球新闻行业和新闻教育领域。他的观点,与《发掘新闻》以来的研究成果,是一脉相承的,重视新闻的独特性。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那种狭义的客观报道已经越来越减少,今天采用的多是分析解释性的报道,要挖掘事件背后的内容。[20] 抓住新闻业的独特属性,在社会变迁的脉络中以点带面地深掘新闻业发展的规律,是《发掘新闻》在理论视角上对新闻史研究领域做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贡献。一系列以之为参照系的社会学视角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并使得新闻史研究在西方日趋成为一个兼顾史料记载与现实观照的、充满活力的领域,即使到了近十年间,仍佳作频出。如马塞尔·布罗斯玛(Marcel Broersma)2007年主编的文集《新闻的形式与风格:欧洲报业与新闻的再现(1880-2005)》中收录的多篇文章,便分别从政治经济、技术革新以及叙事传统等角度,阐释欧洲近现代新闻业发展的一般规律;[21]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在其2010年出版的《网络国家:发明美国电信业》一书中,将承载新闻的电信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视为美国商业新闻业从19世纪末期开始逐渐发展壮大背后的重要规律性因素加以深入阐释;[22]而近两年来好评如潮的乔纳森·希尔博斯坦—洛波(Jonathan Silberstein-Loeb)于2014年出版的《新闻的国际流通:美联社、报联社与路透社(1848-1947)》则深入挖掘知名国际新闻通讯社如何以联合的方式对新闻采集工作进行补贴,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如何对大通讯社之间的联合予以应对的策略,从而归纳国际新闻流通的一般过程。[23]这些带有鲜明的社会科学色彩的新闻史研究成果,无不“强调在经济和技术的话语内实现对于新闻业的深入的历史性理解”;与此同时,又始终坚持“新闻作为一系列传统和实践的独特性”。[24]而这种理论视角上的重要转向,始自《发掘新闻》。 五、方法论:社会史 《发掘新闻》一书的副标题是“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这标志着该著作在方法论上对传统新闻史研究的革新。正是对社会史方法的采用,使得《发掘新闻》在形态和叙事上令人耳目一新,并对后来的同类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社会史(social history),也称新社会史(new social history),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与传统的“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侧重于关注政权和领袖人物的活动不同,社会史将目光对准历史中的普通人,并尝试通过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描述和阐释,来归纳历史演进的规律。社会史方法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全面进入西方主流史学研究视域并保持持续的影响力,2014年的一项针对英国和爱尔兰大学历史学者的研究表明,26%的受访者以社会史为主要研究方法,而坚持传统政治史研究方法的人则为25%。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柯卡(Jürgen Kocka)曾对社会史方法做出两个层面上的界定:在表层上,社会史可以被视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其关注的议题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在深层上,社会史则是一种看待历史的全新方式,主张严肃审视被传统历史学方法所忽略的东西,包括“阶层与运动、城市化与工业化、家庭与教育、工作与休闲、流动、不平等、冲突与革命”,即强调“结构和过程加诸人物和事件的影响”。[25] 《发掘新闻》无疑是最早出现的“新闻社会史”的一本重要著作。一如舒德森在该书的绪论中所言:“我深信在新闻业和美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中蕴含着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未有过答案,甚至未被提及。传统的美国新闻史研究谈到社会背景时只是一笔略过,我这本书却将重点放在研究现代新闻机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上。”[26]这意味着,在写作该书时,舒德森对美国新闻史的主流研究传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受政治史方法影响,传统的研究方法多侧重于知名新闻从业者和知名报人的活动,以及重要新闻机构的“成就”。而舒德森选择了一套理念,一种价值观、道德观作为自己首要的研究对象;这套观念为全体新闻从业者所信仰和尊奉,是一套根植于新闻业日常生产和新闻从业者日常工作的话语,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与社会语境之间保持着密不可分的互构关系。一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新闻既是作为一种叙事类型(genre)发展变迁的,也是作为一个职业(profession)发展变迁的,这意味着新闻既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条件的冲击—公关行业的大规模发展、诽谤法的修订,以及政权对新闻业的约束,都应当被纳入考察的范围。[27] 在舒德森看来,作为美国新闻从业者普遍奉行的“圭臬”的客观性法则,其实也是一种既有其内在逻辑,也须在社会互动中不断改变形态的观念。例如,在该书的第五章,舒德森深入探讨国家的新闻管理政策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风起云涌的批判文化对人们看待和评价客观性法则的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并借此指出的任何行业理念都是自塑与他塑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事实。他归纳了六七十年代社会舆论对客观性理念的三套批评话语:新闻报道的内容建立在一整套从未被质疑过的基本政治假设之上、新闻报道的形式构成了其自身的偏见,以及采访新闻的过程本身建构出了一种旨在巩固官方观点的现实。[28]这实际上是精确地阐述了客观性理念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某种终极命运:从一套新闻从业者旨在拯救“衰落的事实”的话语策略,到一种最终被权力所吸纳并为既存社会秩序服务的话语资源。实际上,客观性理念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互动的结果,是将自身转化成了一种如福柯所言之“真理的暴政”(regime of truth)。[29]由是,舒德森得出结论:“有一些职业实践中的仪式和程序会受到某种广义意识形态的保护。”[30]他还表示了对另一位媒介社会学家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的赞同:“客观性就是一套具体的惯例习俗,之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可以降低记者为其文章负责的程度。”[31] 可以说,正是由于采用了在当时仍相当前沿的社会史方法,《发掘新闻》得以成功地从观念演进而非机构变迁和人物经历的角度,更为深刻地揭示美国新闻业的内在规律,并使历史研究的成果真正能够用于解释现实问题。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曾指出,社会史方法能够使历史成为“一种预测性的社会科学”,[32]这一不无争议的说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发掘新闻》在新闻史领域变成了事实,它证明了“环境……和结构是新闻的内容及新闻业实践的主要塑造者……必须将新闻业置于社会语境下,才能真正理解新闻的独特性及其与大环境之间的关系”。[33] 在《发掘新闻》的影响下,社会史成为西方新闻史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新闻业自身复杂的政治经济属性,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英国历史学家乔治·特里维廉(George M.Trevelyan)曾指出:“离开了社会史,经济史会变得贫瘠,而政治史则会变得莫名其妙。”[34]这对于新闻史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正是无数普通新闻从业者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经验,构成了作为美国新闻业价值基石的客观性理念,以及由此理念支撑起来的新闻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这一过程中,自由市场的发展、民主制度的勃兴、世界大战的冲击、文化传统的浸润,都是不能被忽视的社会过程,因为每一位新闻从业者的观念,都是在这些社会过程中被培育和塑造出来的。事实上,舒德森的野心不止于此。社会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在于揭示社会的某些断面,而在于从特定领域切入社会变迁的总体脉络,甚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做出“自下而上”的科学描摹。一如舒德森在《发掘新闻》的序言中所说:“我认为,在当代各专业、行业将知识和权威正规化的过程中,客观性是一种主导性理念;如果在某一行业内能发掘出其根基,我就有希望揭示其他行业的基础。”[35]这也便是《发掘新闻》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传统的新闻史研究范畴,进而在新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保有其地位的原因。 六、观念遗产:走向科学的新闻史研究 对《发掘新闻》留给新闻史乃至新闻学研究的观念遗产做出评价,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是由两个方面的问题造成的。第一,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中对某一行业的历史加以透析,不可避免要受制于研究对象所处的那个特定的社会语境,因此《发掘新闻》对客观性法则的考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其他国家和制度下的研究者所参考。舒德森在为该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也坦言:“这部书对美国之外的读者而言可能无关紧要……美国新闻界及其规范的形成,具备一些独特的美国特色。”[36]如何正视一种学术思路和学术观点的“跨语境接受”问题,是决定《发掘新闻》在中国学界能够发挥何种作用的关键所在。第二,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若不能得到明确的回答,对于《发掘新闻》的“社会学转向”及其给新闻史研究方法论领域带来的革新的意义的评价,也便无法做到客观公允。舒德森本人在2015年所接受的一次访谈中坦言,自己从未接受过历史学的专门训练,因此“有些事情对有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而言,理所当然,但对我却不那么不言自明……但这也让我因此能提出历史学家不会或不能提出的问题”。[37]这意味着,《发掘新闻》所关注的历史及其使命,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及其使命,可能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否也会影响到我们对这部著作的评价? 当然,对于上述两个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此时给出确切的答案。事实上,如前文所述,《发掘新闻》对新闻史研究做出的贡献,主要还是视角和方法论意义上的。亦即,在假设所有的新闻史研究者都能获得同样的史料和素材的前提下,社会学出身的舒德森发现了一条重新组织这些史料和素材,并以之为基础讲述了一个“新故事”、阐释历史规律的路径。这条路径在史料搜集的过程中并未真正打破传统的描述式研究思路,在对现象的解释上也未彻底跳出阐释式研究的框架。《发掘新闻》所做的工作,其实首要在于令新闻史脱离了人文学科的传统,而投入了社会科学的怀抱。只有如此,对史料的描述和解释工作,使新闻史上的现象能够上升到一般性的规律,甚至上升为理论和科学。 在社会学的“科学化”改造下,美国新闻史和新闻学研究者的工作最终突破了新闻文本和知名新闻从业者经历的束缚,他们开始切切实实地走进新闻业生动而波澜壮阔的发展演进的社会进程中。在回顾70年代开始从事新闻学研究的经历时,舒德森说:“甘斯和塔克曼当时整天就泡在新闻编辑室里,而吉特林则……通过采访了解他们,然后从更大的政治、社会学角度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解释……对我而言,真正听新闻记者、编辑自己谈,谈他们的工作,谈他们的实践,这更能够吸引我和说明问题……如果中国有学者这么做新闻学研究,这就是一个突破。”[38]也就是说,在社会学的指引下,新闻不再仅仅是作为文体和媒介内容产品的新闻,更是作为文化(即生活方式)的新闻,只有切实深入作为文化的新闻的历史变动之中,才能对人类社会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形成准确的理解。然而,这一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即在美国新闻学研究领域变得不言自明的主流路径,在当下的中国新闻学和新闻史研究中却仍较为稀罕。是否从切实的经验出发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释问题,是否从事实本身推衍结论而非依赖某些既有的价值或道德评判标准对现象做出判断,实乃社会科学取向的新闻史研究和人文思路的新闻史研究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正是在社会学路径的指引下,“不擅长历史”的舒德森得以实现了“新闻学内部史、论、业务的融通”,[39]使新闻史研究的结论具有了理论价值和指导行业实践乃至预测行业前景的潜能。 当然,正如上文所提的那两个问题所预示的那样:舒德森在美国社会语境下使用的思路、方法和结论究竟能对中国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研究具备多大的启发价值,以及从事历史研究的目的究竟在于冷峻描摹、供后人评说,还是对研究对象有着更为积极和深度的参与,这都是我们在借鉴和评价《发掘新闻》一书的观念遗产时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但至少,舒德森的研究为整个新闻史领域打开了一扇窗、揭示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历史与科学之间并不存在无法打通的樊篱。“社会学转向”令美国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研究焕发了青春,也对其他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的新闻史研究充满启发。 七、后记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舒德森教授的友爱和周到。在福冈的2016年ICA年会期间,我在6月10日他宣读完他的论文后跟他说起这部《发掘新闻》的中译本已经售罄,即将出第二版,他便告诉我第二天有一场活动与该著作相关。第二天即6月11日下午我和我的好友、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张咏教授[Yong Z.Volz,新闻史专家,曾任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新闻史分会的会长]早早就赶到了他所记录的活动地点,原来他说的就是ICA的年度颁奖会和会长离职前的演讲会(The ICA Annual Awards Ceremony and Presidential Address)。我和张咏占到前面中间第二排的座位、置身于ICA的前主席们之中,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更清楚地了解与舒德森教授《发掘新闻》相关的活动。会后我立即跑到右侧第一排,希望拍一张舒德森教授的奖牌和他拿奖牌的照片,舒德森教授非常配合地从众多围着他祝贺他获得院士图书奖的学者群中,走到ICA会议背板前,抱着他刚刚获得的奖牌让我给他照了相。很庆幸我去了现场获得了一手信息,否则连二手信息都无法获得——ICA并不重视他们自身活动的对外传播,因此什么学界大咖获奖、学会主席致辞,他们都没有报道,即使到现在,我在网上都搜不到一条舒德森教授获此奖的信息——只搜到了两条我自己在现场发的微博。 还要特别感谢一下舒德森教授在2008年常江和我翻译这部著作时,他给予的热情帮助。他在百忙之中为我们2009年出版的第一版中译本写了一篇十分用心的序,他非常中肯地甚至非常严厉地审视、批判了自己的作品,并且梳理了自这部《发掘新闻》出版后他的学术脉络。后来在2011年10月他的《新闻社会学》第二版出版后的一周,他还曾委托正在他那里访学的富布莱特访问教授黄煜老师致信于我,很希望我们再翻译一下他的《新闻社会学》第二版,或托付我找人完成此项任务。由于版权等方面的原因,我未能完成他的嘱托,甚是遗憾。他待人的诚恳与热忱,一如他对待学术,成为我们的楷模、榜样。 感谢国际传播学会院士、“国际传播学会院士图书奖”2015/2016评委、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对我关于图书奖评选机制、程序、评委会意见的采访邮件的认真而细致的回复,感谢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黄煜教授通过微信帮我确定“院士图书奖”的译名,感谢《发掘新闻》中译本合译者常江博士的努力和支持。当然,还要特别感谢亲爱的张咏!她的友谊、对学术的执著和热忱不仅感动着、帮助着我,而且鞭策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