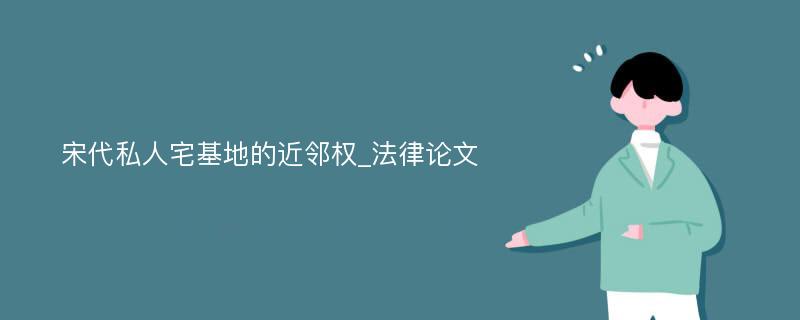
宋代私有田宅的亲邻权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法律明确规定,私有田宅交易,亲邻享有优先购买权;原业主在出典产业之后,如果他本人亡故,其亲邻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执赎权。此外,亲邻还有权参与私有田宅产权的确认。研究私有田宅亲邻权利的意义何在呢?可以肯定地说,不研究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私有土地的性质。
一、田宅交易中的亲邻优先
宋朝法律规定:“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注:《宋刑统》卷一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宋太宗雍熙三年(986)二月诏:出卖产业, “据全业所至之邻皆须一一遍问,侯四邻不要,方得与外人交易。”(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五六、六一之五八,《民产杂录》。)北宋初年关于典卖田宅须先问亲邻的法律,既承认亲、同时又承认邻有优先权。出卖田宅物业,房亲的优先购买权更在四邻之上。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是聚族而居(注:徐杨杰《宋明家族史论》一书,在论及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时说:“这种聚居的小家庭,一般都是只包括二、三代的数口之家,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若干个这样的同姓小家庭聚居于同一村落或者蝉接分居于邻近的几个村落。这些村落聚居的同姓小家庭,追踪溯源,都是同一个男姓祖先的子孙。”(见该书第13页。)本文所称的“宗族”,“族人”都是指这种父系亲属。)所以四邻也多半是族人。因此亲邻优先也就是本族人优先。在同族之内,优先购买权则是依血缘关系由亲而疏递减的。这一法律一直沿用到南宋宁宗时期才作了较大的修订。
宋代田宅典卖,的确有不问亲邻、不承认其优先权的情况,但这是违法的。天圣五年(1027)八月,太子中舍牛昭俭上言称:“准敕,应典卖田宅,若从初交易之时,不曾问邻书契,与限百日陈首,免罪,只收抽贯税钱。”(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五六、六一之五八,《民产杂录》。)这是说,按照法律,田宅交易如果当初不曾问亲邻,“限百日陈首”。有违法行为才需要“陈首”,可见当时视典卖田宅不问亲邻、不书契为违法。同年二月梁州同判李锡还曾上言:“本州典卖田宅多不问亲邻,不曾书契,或即收拾抽贯钱未足,因循违限,避免陪税,是致不将契书诣官,致有争讼。”(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五六、六一之五八,《民产杂录》。)所谓“抽贯钱”也就是土地交易税。买卖双方书契以后,买主准备足额抽贯钱,才能诣官过户、割税。不曾问亲邻,无法书契,当然也就无法持契书诣官办理过割;凑不够抽贯钱,也同样无法办理过割。
法律规定的亲邻优先权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被否定。一是“若亲邻着价不尽,亦任就高价处交易者。”(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五六,《民产杂录》,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秘书丞知开封府司录参军事张存上言。)二是拟出卖的田宅事先已典当与人,再要卖断时,则不须问亲邻,而是“先须问见典之人承当。”(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五六、六一之五七,《民产杂录》。)承典人在买断产权时之所以优先,是因为事先已经购得了不完整的产权。这与亲邻优先并不矛盾:在原业主出典时,亲邻已经享有或放弃过优先权。三是承佃人所佃田产户绝,在购买产权时也享有优先权。天圣元年(1023)七月敕:“户绝庄田检覆估价晓示,见佃户依价纳钱,竭产买充永业或见佃户无力即问地邻,地邻不要,方许无产业中等已下户全户收买。”(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五六、六一之五七,《民产杂录》。)不过这只限于购买户绝田产,见佃人比原业主的亲邻更优先。户绝田产的产权实际上已归官府,因此是由官府处理的,已不属于私有田宅交易的范围。
亲邻优先权还由法律规定的田宅典卖一系列手续确保。首先,法律规定典卖田宅,双方要立“合同契”。乾兴元年(1022)正月开封府上言:“今请晓示人户应典卖、倚当庄宅田土,并立合同契四本,一付钱主,一付业主,一纳商税院,一留本县。”(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五六、六一之五七,《民产杂录》。)合同契是土地所有权变更的依据,所以买方或承典方(钱主)以及原业主要各执一份,双方都应谨防书契时失于检点,以至日后发生产权纠纷。有的业主,书契时“或浓淡其墨迹,或异同其笔画,或隐匿其产数,或变易其土名,或漏落差舛其步亩四至。凡此等类,未易殚述。其得业之人或亦相信大过,失于点检,及至兴讼。”(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争业·物业垂尽卖人故作交加》。)关于书契格式,法律上更有明确规定。绍兴十九年(1149)户部曾提及“旧来臣僚申请,乞今后人户典卖田产,若契内不开顷亩、间架、四邻所至、税租役钱、立契业主、邻人、牙保、写契人书字,并依违法典卖田宅断罪。(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六六,六一之六四,《民产杂录》。)民间买卖田宅,确有书契不如式的情形,而且宋朝政府明确规定这种不如式的契书不能执用。
其次,田宅买卖契书,还必须有亲邻签押,亲邻签押,又称为“亲邻批退”。绍兴二年(1132)闰四月十日诏:“典卖田产,不经亲邻及墓田邻至批退,并限一年内陈诉,出限不得受理。”(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六六、六一之六四,《民产杂录》。)同年八月二十九日,臣僚又上言:“典卖田宅批问邻至,莫不有法。比缘臣僚申请,以谓近年以来米价既高,田价亦贵,遂有诈妄陈诉,或经五七年后称有房亲、墓园邻至,不曾批退。乞依绍兴令,三年以上并听离革。又缘日限太宽,引惹词诉,请降诏旨并限一年内陈诉。”(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六六,六一之六四,《民产杂录》。)所谓“批退”,也就是亲邻在契书上签押,表明放弃依法享有的优先购买权。没有他们的“批退”和“签押”,田宅交易即不为合法。
第三,交易双方要持有亲邻签押的合同契到官府办理“过割”。“过割”,即是将交易田地的税赋由原业主一方割除,过录给买方或承典方,然后官府在双方所立契约上加盖官印,买主就正式取得了该地块所有权,故这一手续又称“税契”。官府办理“过割”、“税契”,都有底帐,称为“割受簿”,“其簿于县令厅置柜收掌,三年一易。”“诸税租应割移归并者限当日以簿批注开收(簿不在县,权别置簿,候到限次日当官尽数腾入),造新簿日,仍以印契簿历照对。(注:《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十七,《赋役令》。)关于“过割”程序,宋朝还明确规定,交易双方要亲自赴官府对批凿砧基簿。“不对批凿砧基簿,难以杜绝减落税钱及产去税存之弊。”(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六六、六一之六五,《民产杂录》。)“人户遇有交易,即将契书及两家砧基照乡县簿对行批凿。”(注:《条奏经界状》,《朱文公文集》卷一九,又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二《田制》。)砧基簿是土地所有权的凭证,其上绘图标明本户田地形状、丘段,写明面积、四至及来源,报本县审查核实后盖印发还本户。如发生产权变更,则必须经官修订,即所谓“对批凿”。为了防止过割、税契过程中的舞弊,绍兴十五年九月三日,夔州路转运判官虞祺建议:“今后人户买卖田宅,人未曾亲身赴县对定推割,开收税簿、而先次印给契赤者,官吏重立法禁。”(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六六、六一之六五,《民产杂录》。)熙宁五年修定方田法,对土地产权进行清理,“其分烟所生、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注:《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历代田赋之制》。)这就是说,民间所有的土地,不论是得自分烟,还是得自典卖,都得凭契书到官过割和批凿砧基簿。为此,更显出亲邻批退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亲邻批退就不能办理过割。
二、土地交易中的亲邻收赎
出典的田宅,原业主收赎时,要以经官办理“过割”并加盖官印的“赤契”为凭证。因为办理税契,要交纳“田契钱”,百姓不愿出这笔费用,于是就出现许多未经官的“白契”。“大率民间市田百千,则输于官者十千七百有奇,而请买契纸、贿赂官吏之费不与。由是人多殚费,隐不告官,谓之白契。”(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田契钱》。)白契是不能作为执赎凭证的。禁止执用“白契”不仅为了防止赋税流失,同时也为了杜绝产权纠纷,不致于以典为卖:“至有不识书计之人,饥寒切身,代书售产,阅时既久,富家管业已深,或为书人已死,或牙保关通,乘放限之便,改移契券,以典为卖,他日子孙抱钱取券而不得,则饮泣县令之庭而己尔。”(注:《北山文集》卷一,《论白契疏》。)
田宅既经出典之后,原业主亡故,其亲的子孙享有无可置疑的执赎权,而且其限甚宽。《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五六《民产杂录》载太祖建隆三年(962)十二月臣僚建言称:
欲请今后应典当田宅与人,虽过限年深,官印元契见在,契头虽己亡没,其有亲的子孙及有分骨肉,证验显然,并许收赎。若虽执文契、难辨真伪、官司参详、理不可定者,并归见主。仍虑有分骨肉隔越他处别执分明契约、久后尚有论理,其田宅见主只可转典、不可出卖。
“契头”是指原立契书人,其“亲的子孙及有分骨肉”所执文契真伪难辨,在这种情况下,虽不准其执赎,但现主亦只可转典而不准出卖。这实际上是为原业主的亲属长期保留收赎权,根本没有时限。
已行均分的兄弟之间,有执赎权。《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争业·吕文定诉吕宾占据田产》载:
吕文定、吕文先兄弟两人,父母服阕,己行均分。文先身故,并无后嗣,其兄文定讼堂叔吕宾占据田产。今索到干照,系吕文定嘉定十二年典与吕宾,十三年八月投印,契要分明,难以作占据昏赖。倘果是假伪,自立卖契,岂应更典。县尉所断,己得允当。但所典田产,吕文定系是连分人,未曾着押,合听收赎为业。
吕文定与其弟文先已行均分。文先生前将田出典,因文定未曾着押,故文先死后,文定仍有权收赎。
因为兄弟间依法可相互执赎,所以有人往往在分析财产时就开始觊觎对方产业,“兄弟分析,有幸应分人典卖而己欲执赎,则将所分旧产丘丘段段平分,或以两旁分与应分人而己分处中,往往应分人未卖而己分先卖,反为应分人执邻取赎者多矣。(注:《袁氏世范》卷一,《分业不必计较》。)
不仅兄弟之间互有执赎权,其他亲属也可执赎,“邻赎之法,先亲后疏”(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四,《争业·漕司送邓起江淮英互争田产》。)不过,收赎时,对“亲邻”的认定,则是越来越严格。《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取赎·亲邻之法》载:
照得所在百姓多不晓亲邻之法,往往以为亲自亲,邻自邻。执亲之说者,则凡是同关典卖之业,不问有邻无邻,皆欲收赎;执邻之说者,则凡是南北东西之邻,不问有亲无亲,亦欲取赎。殊不知在法所谓应问所亲邻者止是问本宗有服纪亲之有邻至者。如有亲而无邻与有邻而无亲,皆不在问限。见於《庆元重修田令》与嘉定十三年《刑部颁降条册》,昭然可考也。
所谓“亲邻”是指“本宗有服纪亲之邻至者”,这是宁宗庆元间(1195—1200)及嘉定十三年(1219)的规定,与前述雍熙年间的规定,确实有明显不同。《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取赎·有亲有邻在三年内者方可执赎》又载:
准令:诸典卖田宅,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者,以帐取问:有别户田隔间者,并其间隔古来沟河及众户往来道路之类者,不为邻。又令:诸典卖田宅满三年,而诉以应问邻而不问者,不得受理。
根据新规定,土地典卖中的亲邻优先权会大大缩小,同时,由亲邻执赎引发的纠纷也必然会显著减少。这都说明小家庭拥有田宅的权利是进一步加强了。不过,尽管如此,亲邻权利仍然继续存在。不仅出典、而且既卖田宅亦可收赎。“阿章绍定年内,将住房两间并地基作三契,卖与徐麟”。“律之条令,阿章固不当卖,徐麟亦不当买。但阿章一贫彻骨,他无产业,夫男俱亡,两孙年幼,有可鬻以糊其口者,急于求售,要亦出于大不得己也。越两年,徐十二援亲邻条法吝赎为业。”(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赎屋·己卖而不离业》。)徐十二系寡妇阿章之夫的从兄弟,在阿章己将田产出卖两年后,仍可援亲邻法收赎。《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四《争业·陈五诉邓楫白夺南原田不还钱》载:
陈世荣绍兴年间将住屋出卖与邓念二,名志明。志明生四子,其地系第四子邓谋受分。邓谋于淳熙十一年,复将卖与长位邓演,明载有火客陈五居住。陈五乃陈世荣之孙。邓演诸子又各分析,离为三四,多系陈五赎回,但内邓楫一分未曾退赎。见得陈五犹是邓楫地客,且当元陈世荣既作卖契,倘非业主情愿,无可强令收赎之理。
陈世荣将住屋卖与邓志明,后由其子邓谋继承,复卖与邓演,并经邓演诸子分析,历年既久,产权又一再变动,陈世荣之孙陈五仍能将其祖父出卖住屋之大部分产权收赎。不过,既经出卖的田宅物业,收赎的前提条件是要出于买主情愿。
“律之以法,诸典卖田宅,具帐开析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及墓田相去百步内者,以帐取问。”这是说典卖田宅时要问亲邻及墓田邻。所谓“墓田邻”,是指该地块与别姓墓田相邻,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块典卖时,邻至即可以有墓相邻为由执赎。这样,亲邻收赎即有两种:一是本宗缌麻以上亲都可以赎,二是以与同宗墓田相去百步为由亦可要求执赎。所以如此,是因为“父祖田业,子孙分析,人受其一,势不能全。若有典卖,他姓得之,或水利之相关,或界至之互见,不无扞格。”“墓田所在,凡有锄凿,必至兴犯,得产之人倘非其所自出,无所顾藉,故有同宗,亦当先问。”“墓田之于亲邻两项,俱为当问,然以亲邻者,其意在产业,以墓田者其意在祖宗。”(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四,《争业·漕司送下互争田产》。)同宗之人以与本宗墓田相近为由要求执赎,被视为理所当然。《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赎屋·执同分赎屋地》载:
又据(毛)永成诉,(毛)汝良将大堰桑地一段、黄土坑山一片,又童公沟水田一亩、梅家园桑地一段,典卖与陈潜,内大堰桑地有祖坟一所。他地他田不许其赎可也,有祖坟之地,其不肖者卖之,稍有人心者赎而归之,此意亦美,其可使之不赎乎?此人情也。使汝良当来己曾尽问、永成己曾批退,则屋虽共柱、地虽有坟,在永成今日亦难言矣。今汝良供吐,既称当来交易,永成委不曾着押批退,则共柱之屋,与其使外人毁拆,有坟之地与其使他人作践,岂若仍归之有分兄弟乎。今官司从公区处,欲牒唤上毛汝良、陈自牧、陈潜,将屋二间及大堰有祖坟桑地一亩,照原价仍兑还毛永成为业。其余黄土坑山、童公沟田、梅家园桑地,并听陈潜等照契管业,庶几注意人情,两不相碍。
典卖土地,一般地段买业者可以拒绝原业主收赎,但如有原业主祖坟在内,这样的地段是不能拒绝收赎的。
“亲邻执赎”须是有邻在先,事后置业为邻者不能执赎。吴元昶将田卖与徐六三,后又以所卖之田与自有田地相邻为由要求收赎,知县认为不当赎,理由是“徐六三得产之后,吴元昶方买邻地”(注:《名公书判清理集》卷之四,《争业·使州索案为吴辛讼县抹干照不当》。)这说明,如果卖主所保有的土地仍与所出卖的土地为邻,则即可以此项理由随时收赎。因此,宋代法律规定,同一处田宅不得分割典卖;既经典卖之后,原业主必须离业。这都是为了避免原业主要收赎,以至引发产权纠纷。
三、亲邻有权参与田宅产权的认定
典卖田宅既然是亲邻享有优先权和执赎权,因此,不免在同族范围之内发生土地兼并,再加上兄弟之间分析财产,于是族内产权纠纷便层出不穷。天圣七年(1029)五月,桂州通判王告上奏称:
昨通判桂州,每岁务开,民多争析财产。洎令追鞫,多是积年旧事。按伪刘时,凡民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始娶,便析产异造。或敏於营度,资业益蕃;或惰不自修,田亩芜废,其後尊亲沦逝。及地归中国,乃知朝廷编敕,须父亡殁始均产。因萌狡计,以图规夺。或乡党里巷佣笔之人,替为教引,借词买状,重请均分。洎勾捕证佐,刑狱滋彰,或再均分,遂成忿竞。故每新官到任,动须论诉。游手之辈,侥幸实多;勤恳之民,冤抑无告。(注:《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三,又观《续资治通鉴》卷一0八。)
南宋末年,高斯得在闽中所见,则是“往往父子相残、兄弟相贼、夫妇相弃、亲戚相雠,较锱铢之财而兴讼至历数载,因纤芥之忿而交诉殆遍诸司。虚造事端、伪立契券、欺诬良善、渎紊公私,泯泯棼棼,何所不有。”(注:《耻堂存稿》卷五,《谕俗文》。)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好多方设法预为防备。北宋官员皇甫鉴在并州,遇到一件兄告其弟非同父的讼案:
曲阳县民兄弟讼者,兄告其弟非同父,不分与田产,弟不能自明,县邑久不决。府使君(皇甫鉴)治之,君使人按视其父母葬,告曰“彼虽无石铭,棺椁外当有题志者。”于是验之,果悉书其子孙名字,而其弟在焉,讼者于是首服。(注:《彭城集》卷三十八,《上骑都尉皇甫君墓志铭》。)
兄告其弟非同父,最后以其父墓中题志所书子孙名字为证。当时普通百姓死后即使无石铭,棺椁外也要悉书子孙名字,其重要用意即在于以防日后子孙之间有人企图排斥其他应分者。
不过产权纠纷并非都是如此简单,官府在处理复杂案件时,则需亲邻、族人参与。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秦州曹玮言:“州民多讼田者,究寻契书,皆云失坠,至召邻保证验,重为烦扰。”(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五七,《民产杂录》。)当时买卖土地不按规定赴官税契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这使得产权不明,赋税负担不清。要解决这类问题,首先要“召邻保证验”,这是重新确认产权的第一个步骤。
官府在解决这类纠纷时,坚持亲邻和宗族全体皆有权参与产权的确认。北宋时韩亿知洋州,就处理过这样一件财产讼案:
郡有公校李甲者,豪于里中,诬其兄之子为他姓,赂里妪之貌类者使夺以为己子,又醉其嫂以嫁之,尽取其赀。嫂流离历诉于州及提刑转运使,每置对,甲辄赂吏,常掠使自诬服,杖而去者前后十余年。公至,复出诉。察妪色冤甚,遂索旧牍视之,皆未尝引乳医为证。一日,尽召其党,出乳医示之,甲遂伏辜。(注:《苏舜钦文集》卷一六,《赠太子太保韩公行状》。)
李甲者于其兄死后,诬其兄之子为里中另一妇女所生,从而剥夺其继承权,自己霸占其侄应继承的财产。其嫂的冤情得申,最终是靠“乳医”即“收生婆”在全体宗党面前作证,证明这位被迫害的妇女确实是其子的生母,亦即李甲兄之子非外姓。这里不仅说明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宗族关系具有排他性,而且说明所有权本身也必须经亲邻、宗党确认方能成立。(注:类似这种嫁寡嫂图谋产业的事,朱熹在漳州时也遇到过:“某往在临漳,丰宪送一项公事,有人情愿不分,人皆以为美。乃是有寡嫂孤子,后来以计嫁其嫂,而又以己子添立,并其产业。”,见《朱子语类》卷一0六《漳州》。)
既然亲邻有权参与确认产权,所以就不免有人买通亲邻,以图达到掘取并非自己当得的赀财。孝宗时吏部侍郎李椿上奏:
自国家南渡以来,时有建议立法者,或父母在日,许令标拨产业。既分便不同造,或致互相兼并,有父母见在一贫一富者,有弃父母别居者,又有母受一子之分者,以致身后词诉纷纷,皆是。或有产业而无子孙,许令身后立继,多是意在图其产业,本无继绝之义。或寅夜葬埋,强行举挂;或计嘱亲邻,掩有赀财。论诉尤多,连年不决。(注:《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七,《风俗》。)
族内甚至亲兄弟之间互相兼并,以至一贫一富。“计嘱亲邻,掩有赀财”,即兄弟之间争夺产业,因为亲邻权利的确存在,有的竟设计事先争得亲邻站在自己一边。
四、亲邻权利与土地私有权的性质
土地既然是私有,为什么法律还要赋予亲邻这些权利呢?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从对中国中古时期土地所有权性质的考察中获得解释。
在历史上,最先成为私有财产的不是土地,而是动产,然后才是人们一家一户的房屋及其四周的园田地。人们对居室、园宅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起源于游牧民族作为起居处所的帐幕及大棚车。也就是说,居室、园宅的所有权归根结底还是起源于动产的所有权。耕地成为私有财产,在一切民族的历史上,都是最后才发生的。因此,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其发育都是不成熟的。这一点反映在法律上就是土地财产不象其他动产那样受到无条件的保护。例如《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云:“诸盗耕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疏议》云:“田地不可移徙,所以不同真盗。”同卷还规定:“诸妄认公私田,若盗贸卖者,一亩以下笞五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疏议》云:“地既不离常处,理与财物有殊,故不计赃为罪,亦无除、免、倍赃之例。”在这里,作为不动产的土地,与其他财物、动产,是严格加以区别的。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土地作为私有财产之所以不成熟,归根结底是因为它还脱离不了共同体的“脐带”。“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一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的。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论的。同样,财产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89页。 )人们只有属于某种共同体,才能占有土地财产。纯粹的个人财产,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才有存在的可能。资本主义以前的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区别也就在于此。在中世纪的欧洲,马尔克成员的土地所有制“在整个中世纪里,它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典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3页。)森林和牧场归全体公社成员占有,耕地和草地归私人占有,但马尔克对分配给各家各户的耕地实行强制轮作制:每一块休耕地在休耕期间又成为公共财产,所有的公社成员都可以在那里放牧。
在中国,这种农村居民的共同体也同样是他们占有土地的前提。我们姑置上古时期的土地公有制不论,战国以来,土地公有制瓦解以后,邻里、乡党这类组织仍然是人们占有土地的前提和基础。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王莽代汉以后,“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注:《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王莽利用土地公有制解体以后乡党九族共同体仍然制约着土地所有权这一既定的历史事实,规定“乡党九族”有权得到团体内某些人多余的土地,这种规定可说是事出有因。但是从法律上禁止土地买卖、不承认土地私有权,却是开历史倒车。东汉末年以后,北方长期战乱造成大量无主荒地。如果邻里、乡党中只有个别人户流亡或户绝,这些人户遗留的土地实际上是归邻里、乡党所共同占有的。北朝至隋唐时期所谓均田,就是在邻里、乡党范围之内调济耕地。北齐河清三年(564)定令, “乃命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为中,六十六以上为老,十五以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注:《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河清三年均田令中不仅关于老小丁中的年龄规定与受田、还田有关系,其中关于比邻、闾里、族党的规定也同样与受田、还田有重要关系。这一点,只要与历代均田令中“宽乡”、“狭乡”的规定联系起来,就可以发现,还受土地,一般情况下都是在邻、里、党范围内进行的。每家每户都属于一定的邻、里、党组织,而且只有是这类组织的成员才有资格受田。受田、还田都在这样固定的范围内进行,因此才会有宽乡和狭乡的区别。
自从唐中叶均田制瓦解以后,原来属于集体支配的土地财产,绝大部分都变成了私有财产。不过,各地也都还有相当数量的族产,包括宗族墓地和义田等,此外还有所谓“义役之田”:“谓随役户之多寡,量事力之厚薄,输金买田,永为众产。遇当役者,以田助之”,(注:袁甫:《蒙斋集》卷三,《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伏》。)这些都是集体所有的公产,是不许典卖的。宋代所谓“民产”实际上是包括民间集体所有及民间私有两部分土地财产。为集体所有的族产当然是以宗族共同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前提和基础,而受亲邻权利严格制约的私产也同样是以宗族共同体作为土地所有制的前提和基础。
宗族是父系亲属集团,《尔雅·释亲》称父宗为“宗族”,而异姓亲则称为“母党”、“妻党”。于是,在财产权上同姓、同宗自然要排斥异姓,排斥外亲。范仲淹手订的《义庄规矩》规定:“乡里、外甥亲戚,如贫窘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注:《范文正公集》附录。)在这里,“外甥亲戚”只被放在与“乡里”同等的地位。
排斥异姓的财产纠纷,实质上是宗族作为所有权的前提和基础的反映。仁宗天圣元年(1023)二十八日,淮南路提点刑狱宋可观上言:
伏睹编敕,妇人夫在日已与兄弟伯叔分居、各立户籍,之后夫亡,本夫无亲的子孙及有分骨肉、只有妻在者,召到后夫,同共供输,其前夫庄田且任本妻为主,即不得改立后夫户名;候妻亡,其庄田作户绝施行。只缘多被后夫计幸,假以妻子为名立契破卖,隐钱入己;或变置田产别在,后夫为户,妻殁之后无由更作得户绝施行。臣欲乞自今后或有似此,召到后夫委乡县觉察前夫庄田,知在,不得(?)私破卖隐钱入已,别买田产转立后夫姓名。事下法寺,请如所奏。从之。(注:《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五八,《民产杂录》。)
根据上述可知,妻子有权承袭丈夫的田宅,但只限于她本人在世时。不仅她的后夫不能与该项产业有染,就是她与后夫所生的子女亦无权继承,这实际上还是不承认妻子有权继承丈夫的财产。
随母改嫁之子,是否能与其他兄弟均分财产,完全视其同继父的关系而定。《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四《争业·随母嫁之子图谋亲子之业》称:
李子钦甫数岁即随其母嫁于谭念华之家,受其长育之恩凡三十年矣,其与的亲父子何异。而李子钦背德忘义,与其母造计设谋,以离间谭念华之亲子,图占谭念华之家业。谭念华愚蠢无知,妮于后妻之爱,堕于李子钦之奸,遂屏逐其前妻所生之子,勒令虚写契字,尽以田产归之于李子钦……所合将李子钦赍到契书十道并当厅毁抹,送县行下本保,唤集谭氏族长,将谭念华所管田业及将李子钦姓名买置者,并照条作诸子均分。李子钦罪状如此,本不预均分之数,且以同居日久,又谭念华之所钟爱,特给一分。
李子钦作为谭念华的养子,之所以也能与其亲子均分财产,是因为“同居日久,又谭念华之所钟爱”,而不是因为其母与谭念华的婚姻关系。财产是丈夫一人的,而不是夫妻共有的。
毫无疑问,在宋代,亲邻权利制约着土地私有权。官府不仅根据有关法律保护亲邻的权利,同时还根据同样的法律分摊不合理的负担。神宗时,将26000多处原由衙前经营的酒坊、河渡收回, 用“实封投状”的办法,卖给私家经营,后来“坊场多有破败,乃至出卖抵产以偿官钱。或抵产价高,出卖不行,则强责四邻承买;或四邻贫乏,承买不尽,则推及飞邻、望邻之家,抑令承买。”(注:吕陶:《净德集》卷二,《奏乞放坊场欠钱状》。)所谓“飞邻”、“望邻”当然实际上皆非邻,但是,官府要向这些人强行摊派,即妄认其为邻,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确认他们在财产方面与那些因承买坊场而破产的人拥有同一个前提和基础。
通过对宋代私有田宅亲邻权利的考察,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宗族关系(或曰宗族共同体)在当时就是所有权的前提和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