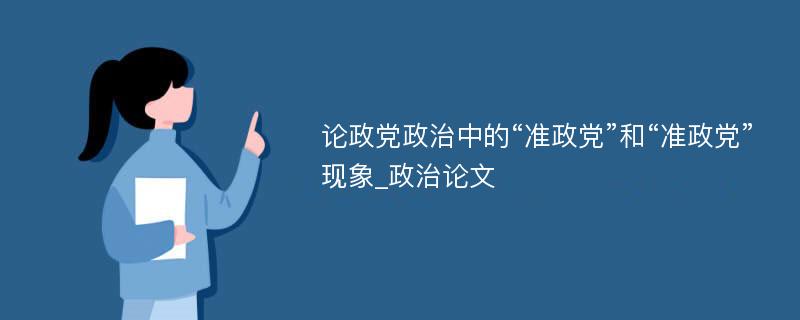
简论政党政治中的“类政党”与“准政党”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现象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6)02-0021-06 在庞大的政党群中,大党和强党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的选票分布决定着选举的走向,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影响着一国政治和政策的走向。但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又是一个大党与小党、强党与弱党共生的时代,从数据上看,全世界在册登记的5000多个政党中,小党数目远远超过大党。今天,无论是在两党制、多党制还是一党主导制下,都有数量远远多于大党的众多小党在体制内外存在。 从政党一般理论和定义的标准来看,许多小党并不同时满足政党一般定义中所具有的政党要素。它们有的缺少稳定的、一定数量的组织成员(最小的政党只有3个人,比如2005年注册的美国“房租过高党”);有的缺少稳定的政治纲领(小党往往会随着社会关注热点变化而改变其纲领);有的缺少独立的组织活动(与别的政治组织合作行动);有的则没有涉及国家政治权力的最高目标(这与很多规模虽小但要素齐全的小党有区别)[1]。这些要素不全的政治组织出现的越来越多,在许多国家达到法律规定的政团组织注册要求,以政党形式存在、活动并发挥着作用。宽容些的学者把它们视为政党;苛刻些的学者甚至不用政党的视角观察它们和要求它们。但无论学者或者社会怎么评价这些所谓的“政党”,它们都真实地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本文把这种非典型性政党,分别称为“类政党”和“准政党”。 一、“类政党”与“准政党”的类型学意义 类型学(Typology)在社会科学的最早应用一般认为是在考古学领域。在面对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动物遗骸时,考古学学者使用了根据它们的形态特征分成不同类型、研究其发展序列和相互联系的方法,这一方法后被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广泛采用。分类,成了许多学科门类的首要的基础工作,并促成比较学科的兴起和发展。 早期的政党是少量而简单的,因此分类并不显得十分必要。但在当代,政党现象日益复杂,分布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个政党,形态性质各异,需要进行分类研究。根据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等不同目的以及对政党认识的程度,学者采用相应的分类标准。这些分类按照类型学的方法,根据不同研究需求,列举了各种标准和维度,把政党分成多种类型。比如按阶级基础或者阶级属性把政党分为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阶级联盟政党、农民党等;按政党的法律地位把政党分为合法政党与非法政党、执政党与在野党(包括反对党)、执政党与参政党(联盟党)等;按政党的组织类型分为大众党与干部党;按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分为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按政治倾向和政治态度把政党分为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激进政党和保守政党;按政党功能或活动方式把政党分为选举型政党、革命型政党、治理型政党、参与性政党;按活动范围把政党分为国际性政党和民族国家政党、全国性政党和地区性政党;按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指导分为科学社会主义政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保守主义政党和自由主义政党、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政党等等,最多的分类多达十几个类型。①上述政党类型划分的对象都是在法律上被认可为政党,或经过注册声称是政党的一切政治组织。但这套分类体系还没有一个针对政党的“政党属性强弱”和“政党的要素与功能完整程度”的分类。本文提出的“准政党”和“类政党”则是针对传统典型政党而言的非典型政党,其划分标准是要素完整程度和政党属性强度。这种类型划分着眼的是政党的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以及政党活动的特殊方式和作用的不确定性。 二、“类政党”与“准政党”的描述与界定 “类政党”与“准政党”是本文为了从新角度观察政党尤其是小党而使用的新概念。“类”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种类和类别;二是类似和相似。这里借用医学概念来进行说明。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关节红、肿、热;二是疼痛游走不定,但疼痛持续时间不长,治愈后很少复发,关节不会受损。还有一种病与风湿性关节炎症状非常相似,但发展到晚期会导致骨关节强直、变形。这种病曾经长期也被叫做风湿性关节炎。但后者实际上是以关节慢性炎症为表现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与风湿性关节炎的表现类似但病理不同,是风湿病的一种临床亚型。1859年就有医学专家建议采用“类风湿关节炎”以与风湿性关节炎相区别,上个世纪这一名称被世界各国普遍正式采用。“类风湿”的命名,体现了两种疾病的大类归属及亚型本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它们表现类似但病理不同的本质特征。 使用“类政党”(similar party)概念的目的是想描述这样一类“政党”:它们在法律程序或手续上并不是正式政党,但它们的一些政治功能、组织特征、活动方式等与政党类似(similar),比如组织成员有准入机制即门槛,有政治追求和利益诉求,有政治宣传、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表达方式,在某种政党体制框架内生存与活动等,具有一定的政党特征。 准政党(quasi-party)是与“类政党”有所不同的另一类非典型“政党”。虽然“准”也有类似的意思,但相比上述只是“类似”政党而言,它还包含有“部分”(partly)是、即将成为、准备成为(to be)和预期、先期(pre-)意思。类似常用“准”的概念有准货币、准市场等等。“准政党”指的是两类组织:第一,从法律角度看,它们经过政党组织的法律注册或者法律承认以政党组织形式存在着,但政党要素缺失,比如缺少稳定的明确的政党纲领和独立对国家权力的要求,缺少成员对政党的高度组织认同和纪律要求等等,在规模、组织化、专业化、制度化程度等等方面存在不足和缺失;第二,没有经过政党注册,只是一般的社团登记但以政党方式活动的政治组织。“准政党”与“类政党”有相似的地方,区别是“准政党”的政党意识、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要高些,它们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事实上进一步发展成为完全意义、经典意义上的政党的条件、潜能和自觉意识比“类政党”大些,“to be”和“pre-”的意味更强些。 总体说来,在世界政党之林中,虽然从数量上看有5000多个政党存在,但是无论按照哪种政党定义,都有一些“政党”不是标准和完全意义上的政党。在当今时代,这些要素不全的、不具备完全的经典意义的政党越来越多,它们越来越追求提出某些政治议题,造成政治影响并实现政治表达的片面政党意义。如果按照经典意义的政党来研究它们会遇到分析困惑。因此,对这类“政治”组织作一种新的定位不失为一种视角和方法。 三、多样性、碎片化、极化与政党政治发展的新常态 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后现代社会的碎片化,政党数量越来越多,政党政治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一些灵活的议题党不断闪出涌现;一些压力集团、院外集团、选举集团甚至NGO,越来越多地做着类似政党的事情。而在碎片化和分散化出现的同时,政党政治出现了由原来的政治立场中间化、政治主张趋同化演变为“极化”(polarity,polarization)的趋势。“政党极化”在政治上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左右极化,在组织形态上则表现为松散和严密的极化。 可以把“类政党”与“准政党”现象看作是后现代社会碎片化导致政党政治发展多样化的一种反映,即政党政治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现在很多政党并不是按照传统的经典政党定义那样组党与活动,甚至连政党的最终追求也发生了变化。观察今日世界上那些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大多数国家没有提高政党注册的门槛甚至是在降低,最多只是对政党竞选规则加以改变和调整。虽然在各种竞选规则下,小党很难杀出重围成为获胜党,但小党包括上述那些实际上的“类政党”与“准政党”,却以“提出议题”的方式影响政治;以代表特定人群的方式获得支持者;以“搅局”的方式影响选举走向,事实上积极地参与政党政治并发挥作用。 传统的政党研究,经常从政党是特定社会阶级、阶层的代表的角度研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但随着现代化、后现代化社会的出现,在代表性的政党之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单一议题(话题)性政党,即从政党的成员属性和政治属性中很难区分出是属于哪个特定的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他们的临时聚合是基于某个社会性政治性议题。这类要素不全的“政党”并不一定是对应着哪一个特定的阶级和阶层。在传统各党所对应的阶级和阶层基本已经划分囊括完毕后,越来越多的新阶层政治诉求或者一些从传统阶层中产生的新诉求都借由这些灵活性的“政党”来表达。这些政党或许规模很小,或许不讲究组织边界,或许不谋求正规性;但他们提出的议题,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话题。这些话题,由于反应快、内容新,往往具有更强的政策创新的动力,会引起一些大党的注意。从现实看,许多国家的小党的确是在大党提出某一议题之前而先于大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提议。所以,美国有学者认为“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小党几乎是一切重要政策创新的源泉:女性的普选权、个人所得税、直选参议员等等几乎首先都是由小党发起的”[2]。而当小党所首创的议题被证明具有足够支持时,大党就会积极将这些议题作为自身的政策纲领甚至与小党建立联盟。借助大党,小党的利益表达同样可以完成。也正因为此,使得一些“准政党”“类政党”的小党就渐渐失去成为“正式”的“经典的”政党的动力。 有许多案例证明着这种趋势。2009年美国一个按照经典意义算不上政党的“茶党”,成功地搅局了美国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2011年9月,德国一个年轻人组成的倡导网络自由下载合法化的小党——“海盗党”,利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靠着“拇指”“键盘”的方式号召与动员,使其所提出的15名候选人,全部成为议员。虽然在2013年的德国大选中没有进入联邦议院,但这一被称为“虚拟党”的组织以“准政党”的“流动民主”方式向传统政党政治发出了挑战。 又比如,2013年美国纽约市长竞选中,一个叫“房租简直太高党”(The Rent is Too Damn High Party)的党首麦克米兰参加了竞选。这是一个2005年注册,正式党员只有3名的党。这个党是一个极不规范的“党”,没有什么组织网络,竞选也是惨败,但是党首麦克米兰留着大胡子穿着奇异服装的竞选演讲视频却被浏览了460万次,他的个人网站点击数达到了2150万。他以个人成为网络红人的方式使“房租简直太高党”要求降低房租的主张广为选民知晓。 这种众多的要素不全的“准政党”、“类政党”以轻骑兵的方式,“不按规矩出牌”,影响政党政治的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除了提出“小党”(small party)、“微型党”(Minor party)、“第三方党”(Third Parties)、“新党”(new party)、“次要党”(minor party)、相关政党(related party)等概念外,在2015年3月出版的美国的《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杂志总第21卷第2期上,梅耶和米勒在《The niche party concept and its measurement》[3]中提出了niche party的概念和测量标准。什么是niche party呢?Niche这个词本意是佛龛或者神龛,就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放一尊佛。过去在经济学上使用比较多,多指市场上那些有专门用途的小摊位,或者有特定要求、顾客群和产品的专营市场、有利可图瞄准机会的小市场。学者们对niche party的描述,是指那种不同于主流政党的、单一政策主张的、“更善于决策的政党”、能讨价还价的政党[3]。这一概念界定,不完全用规模来指称过去学术界定的小党,不强调它的小,而是强调它的政策主张的灵活、政治诉求的单一以及不以传统的阶级或阶层立场来划分政策方向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和使用niche party这一概念,意味着原来容易被称作小党或非主流政党的新式政治组织,其组织形态作用发挥和功能设置的实际变化得到学术界的承认。niche party比较接近本文所提出的“准政党”和“类政党”概念,其共同之处在于,这些“政党”按照过去经典的政党定义,其实达不到“政党”标准,但是它们的确又获准在目前政党体制中大量出现、活动和产生影响。在政党政治的未来,它们由“类政党”和“准政党”“升格”为标准意义基础上规范的政党,还是就以这样的非典型政党身份活动对政党政治发展的格局影响空间更大?还要再观察。 四、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的非典型政党 对于当代中国实行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尽管已经有很多著作、论文甚至是白皮书这样正式的文件对这一制度进行解释和说明,但还是有不少人不能全面准确理解这一制度的内涵。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运作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和环节是:中国共产党对有关国家大政方针、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事项,采取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形式,向合作协商的其他政治主体通报、讨论、征求意见。参加这一层级座谈会的范围一般是“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这里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作为参政党的8个民主党派,还有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参政党是什么性质?“无党派人士”是什么角色?全国工商联是什么地位?尤其是对同时纳入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的8个民主党派之外的“无党派人士”,就更少人知晓。学术界对“无党派人士”的定位已经有过许多讨论②,总结这些讨论,可以形成共识的是,都认为“无党派人士”的特点是这些特定的人不加入任何党派,但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平台中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具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权利、地位和作用,是参加参政议政多党合作的政治力量之一。 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之所以具有制度效率,其内部结构是一种有创意的制度安排。表面上看,是1个执政党、8个参政党以及一群无党派人士。实际上在这个制度结构中,包含着“类政党”和“准政党”的政治力量来丰富这一制度。 第一,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的“无党派人士”,以“类政党”的角色发挥着超越一“群”个人的作用。 从法律地位看,“无党派人士”并不是一个组织或政党,但它也不是无党无派的一般群众和一般的一“群”人,而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派别,具有不是党派但又具有党派性的特征。“无党派人士”进入中国的政党政治体系,经历了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三个发展阶段。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非组织政党或政治团体”的形式进行抗日救国的“社会贤达”,还是在抗战胜利后领导民主人士进行集体民主活动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都不是简单的个体组合而是特定的一“群”人。在1949年6月的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周恩来提出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③的经典论断。他认为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参加具有“党派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活动,因而应归为“有党派性的”代表[4]。同年9月,无党派民主人士作为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在内的14个党派单位之一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200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于加强新时期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意见》中首次明确“对无党无派人士群体称无党派人士,对无党派人士中的代表人物称无党派代表人士”。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明确,“目前,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5]。但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可以成为“无党派人士”是要经过甄别和认定的。 在现实国家政治生活中,在所有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合作的政治场合都包括有“无党派人士”这一政治派别;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中,“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被统一称为“党外人士”代表④。在政治协商这个平台上,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与民主党派代表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作用,它们不仅指代爱国民主人士个人,还具有指代这些人士集体的含义,显然它是处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结构中的,是具有政治性和党派性的。[6] 从组织特征看,“无党派人士”虽然不是政党,甚至不是组织,但它又是有明确边界的,与其他统一战线人员不存在交叉,其成员需要按照标准认定并具有一定的准入程序;有特定的培养和发展计划⑤;有相应的组织构架和协调机制进行对内管理和对外活动;其管理具有组织化特征,其活动是在统战部的统一安排下。比如无党派人士的活动是按“无党派人士”的“组别”,组织成相对独立考察团、学习班、建言献策小组等形式进行,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无党派人士”与其他民主党派在组织上的不同特征是,这个政治力量没有政党领袖、没有中央组织和基层组织以及各级代表大会等组织构架。 从“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安排看,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无党派人士”除了出席多党合作的会议、参与讨论协商外,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也有制度化的机会和渠道来担任各级政府职务的政治待遇。 所以,“无党派人士”虽然没有正式成为一个参政党,但是这部分特定的代表性人群,以与参政党类似的政治身份和活动方式,成为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一部分。 第二,在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中,“工商联”以“准政党”的组织类型,发挥着超出一般社团组织的参政议政功能。 被中国共产党统一并称为“党外人士”的政治力量中更特殊和醒目的是工商联组织。这也是在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中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工商联是各级工商界联合会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具有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的社会群众团体组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于1953年,是在中国众多人民团体组织中唯一具有高行政级别和特别待遇的组织。虽然它不是政党,但它在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享有与民主党派一样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平台上,中共在重大事项上需要告知并协商讨论的政治力量代表是“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某种意义上说,“工商联”可以说是一种“类政党”,但因为与“无党派人士”相比,它的组织化、制度化程度明显要高得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有会员代表大会为其最高权力机关,有独立的章程,工商联依照法律按国家行政区划设置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机构,有全国性的中央级组织全国工商联负责指导地方工商联和民间商会的工作。工商联有严整的基层组织,全国共有县以上工商联组织3119个,形成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工商联会员362万多[7]。全国工商联还有自己的国际联系,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会建立了关系,其组织形态与参政党最为接近,与“无党派人士”相比,它更像“准政党”。当然,准政党并不是一定要升级为政党,只是说它与政党最为接近。 “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的政治角色和活动方式,使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形成了成熟、稳定、有效以及独特的制度结构,使用“类政党”和“准政党”解读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内部结构,一方面可以从学术角度探讨中国这一制度的创新在哪里,这种结构为什么会有包容性和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讨论这一政治体制需要完善改进和释放能量的空间在哪里?“准政党”和“类政党”的状态怎样才能在制度包容、制度均衡的情况下同时提供制度活力? 在目前复杂的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过去着眼于大党研究的一些经典定义、经典理论已经不能够有效地解释现实。因此,无论是对世界政党政治复杂现象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前景的研究,提出“类政党”和“准政党”的概念都具有意义。 ①参看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王韶兴.政党政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赵晓乎.政党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②比如贾德忠.从现代政党的特征看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3):128-131;胡俊峰,常泓.无党派人士的界定和称谓的历史演变[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13(2):26-27,30;宋俭.关于无党派人士及其政治参与的若干思考[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1):39-42;王永庆.关于无党派人士工作几个问题的思考[J].中国统一战线,2011(8):19-20;范前锋.应将无党派人士工作纳入参政党理论研究范畴——兼谈无党派人士工作的研究方法[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6):33-35;陈喜庆.关于无党派人士的几个问题[A].交流研讨谈心——从无党派人士关注的理论问题谈起[C].2009.这些讨论,尤其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直接援引中央文件明确表述了无党派人士的历史渊源与官方定义。 ③关于无党派认识的称谓与实质,参看《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选集》(上卷)等. ④比如:“日前,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受中共中央委托,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结合各自实际,畅谈学习体会”。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凝心聚力,《光明日报》,2015-06-03. ⑤《关于“无党派人士”政治面貌规范使用的意见(试行)》(2007)通知发布后,各级统战部门开始重视无党派人士“政治面貌的规范使用,具体包括联系和培养、登记、通报、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