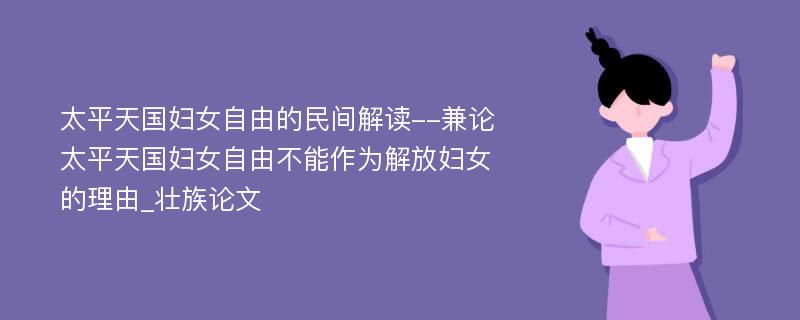
太平天国妇女自由问题之民俗释论——兼论妇女自由不能作为太平天国妇女解放之论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妇女论文,自由论文,论据论文,民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天国妇女与传统妇女相比,在生产劳动、恋爱婚姻、社会交往、人际关系、女性追求美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呈现出难能可贵的自由精神,得到当时许多正直人士和后人高度赞扬,最典型的意见是:“那时候,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妇女,正呻吟在封建礼教重重束缚之下,她们被关在家庭里面,终日伏处深闺,造成一种卑怯的畏缩的心理,正眼也不敢瞧一瞧男子。而在太平天国的妇女则大大不同,她们是解放后的中国新妇女。她们有独立自尊的人格,她们有男子一样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地位,所以她们得毫无拘束地自由自在地驰骋在那通衢大道上,即对罕见的外国军人也满不在乎。太平天国新妇女的表现,正标志着太平天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就。”[1] (P339)长期以来,妇女自由被看作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一大措施。虽然有些专家学者对诸如婚姻自由等问题提出过一些异议,但总的说来,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和深入讨论,也没有对妇女自由问题作过系统论述。本文试从民俗之角度对太平天国妇女自由问题作一专门论述。
一
(一)广大妇女具有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自由,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男女分工模式
几千年来,在封建“三纲五常”礼教束缚下,中国妇女的传统社会角色主要是从事“家内劳动”、“相夫教子”、“男主外,女主内”等等。女子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但在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战争的客观需要和广西妇女的劳动习俗以及妇女身体素质的影响,广大妇女广泛参加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和后勤物资运输工作。劳动范围广、种类多、规模大、劳动强度重,“一切劳动苦工似乎都由她们承担”。[2] (P813)根据众多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统计,太平天国妇女担负的生产劳动和后勤工作主要有:“开挖壕沟”、“送竹签子”、“割麦”、“割稻”、“抬砖挖沟”、“背米盐”、“负米舂稻”、“获稻负盐”、“担水”、“肩米负煤”、“掩埋死尸”、“捉草以饲马”、“搬移物体”、“抬水挖泥”、“斫柴”、“搓麻绳”等等。(注:对于太平天国广大妇女广泛参加各种社会生产劳动情况,史料记载众多。主要参阅:谢介鹤《金陵癸甲记事略》;汪士铎《乙丙日记》;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张德坚《贼情汇纂》;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冯氏《花溪日记》等。)很显然,广大妇女充当了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和后勤物资供应保障工作的骨干力量。不仅表现了妇女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勇挑重担的高尚美德,而且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广大妇女已经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与封建社会妇女深居闺阁、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相比,已具有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自由,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男女分工劳动生产单一模式。
(二)积极追求自由,广泛参加多种社交活动,开始走出单一的家庭交往模式
在传统封建社会中,为了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防微杜渐,女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范围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不能参与公开的社交活动,甚至在家庭中也不能参与男子接待客人的活动。而太平天国的妇女却可以自由交际。[3] (P185-186)除前面所谈到的妇女大量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外,在社会和家庭的人际交往活动中也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各贼馆中,贼妻亦时相往来”。[4] (P66)太平天国恢复家庭生活后,更进一步允许男女之间自由交往。太平军每到一处,就有许多女子就前往军营一睹太平军的风彩。1856年,元勋殿左二十一检点赖裕新发布的“安民晓谕”中一再强调:“尔民间妇女,恐未必尽识道理(男女之别),必须潜居各慎闺阃,不得游荡前来,以致有乖天情”,[5] (P120)妇女们对异性的大方坦然可见一斑。在苏州,令封建文人感到“更怪者”是妇女“见长毛则仍巧妆艳饰,立于门首而不知避”。[4] (P27)在绍兴,更令封建文人感到“妇人之居心行事,有出乎情理外者,可畏可笑”的是朋友之妻居然带着太平天国战士到他家来招他到太平天国中去做事。[6] (P798)在常熟,“男女淆乱,不忌内外”。[7] (P837)特别是在与外国人的交往过程中,更表现得落落大方,令外国人常常惊叹不已。据缪维廉先生记述,他在传道过程中,遇到一群妇女在路上行走,“不少妇女停下来听我们讲道,她们的举止总是极有礼貌。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他认为这“打破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8] (P385)1861年英国军官吴士礼在谈到对天京访问的最大感想时说:“这里(南京)跟全国我所曾游的其他城市大异的地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而又绝不装模作样害怕外国人如其他中国妇女所常为者,亦不回避我们。”[1] (P339)另一个外国人在他的《通讯》中写道:“在丹阳见有妇女骑马,一如男子驰骋路上,乃以为给妇女以自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大的特色之一。”[9] 而呤唎一次经历则使他对中国妇女的社交自由更为赞叹。有一次,太平天国直王在武汉设宴款待呤唎,“酒过数巡,直王夫人携子女前来入席(按照欧洲人习惯,这时正是妇女儿童退席的时候),她们的出席使我大为诧异,因为这跟中国妇女深居闺中的风俗是恰恰相反的”,“直王的妻子、两个女儿以及家中其他妇女,全都参加谈话,毫无拘束,这是我在中国人中间从所未见的”。[3] (P185-186)
(三)太平天国妇女追求自由生活还突出地表现在恋爱婚姻自主上
太平天国实行的是“严别男女”制度,禁止男女交往。不允许官兵与民女之间有任何正常的接触,不允许卖淫嫖娼,不允许男女亲属之间正常走动,也不允许夫妻同居和男女谈婚论嫁,男女交往一度成为太平军之最大禁忌。1854年10月,东王杨秀清宣布恢复家庭生活后,男女交往得以解禁。“使男女双方首先有各种机会相互熟悉起来”,从而使结婚变“成了爱情的结合”。[3] (P253)“少女们尤其爱慕军中青年”,[10] (P2249)主动与太平军将士自由恋爱。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就记载了柴大妹和祝大妹两人分别与太平军战士李大明和翟合义自由恋爱、结婚、夜夜盼夫归的故事。[10] (P2249-2252)至今还流传在上海和苏南地区的两首民歌,充分表达了妇女对太平军丈夫的忠贞不渝的爱情:
新年盼哥郎,妹倚桑树望断肠,
“长毛”哥哥你走后,十家倒有九家亡。[11] (P207)
碗豆花开花蕊红,太平军哥哥一去影无踪,
我黄昏守到日头上,我三春守到腊月中,
只见雁儿往南飞,不见哥哥回家中。
碗豆花开花蕊红,太平军哥哥一去影无踪,
我做新衣留他穿,我砌新屋等他用,
只见雁儿往南飞,不见哥哥回家中。
碗豆花开花蕊红,太平军哥哥一去影无踪,
娘娘哭的头发白,妹妹哭的眼睛红,
只见雁儿往南飞,不见哥哥回家中。
碗豆花开花蕊红,豌豆结荚好留种,
去年种下小豌豆,花儿开得更加红,
太平军哥哥五个字,永远记在人心头。[11] (P211)
这凄楚哀婉的情歌将一个个渴望与丈夫团聚、追求幸福生活的女子形象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这是传统封建买办婚姻制度下所无法想象的。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天国的寡妇有再嫁的自由。在公开举行的“讲道理”时,向广大人民群众明确宣传:“尔辈生逢太平日,举足便上天堂梯,夫死自有夫,妻死自有妻。[12] (P736)对此,地主文人嘲讽为“寡妇频言与丈夫,柏舟节义笑为迂”。[7] (P835)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在杀了男犯人后,还往往用国家行政命令办法,将罪犯之妻改嫁他人。正因为太平天国不主张妇女守节,所以才出现了呤唎听到的“一些妇女一听到她们的丈夫被‘满妖’所杀的消息,就立刻跑到街上去找新的丈夫”的现象。[3] (P241)这与“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烈女不更二夫”的封建贞洁妇女形成了鲜明对照,表现出与那些所谓的封建“烈女们”截然不同的自由精神。
(四)太平天国妇女表现出追求女性美的自由
在封建纲常礼教下,妇女的行为举止受到传统伦理的严重制约,妇女必须压抑自己的爱美之天性。“笑不露齿、行不露足、衣不露体”长期以来一直是女子做人的教条。太平天国妇女通过自身的外表、外貌和行为举止,直观形象地展示出广大妇女追求女性美的自由精神,与清统治区域妇女那种萎靡不振的形象相比,完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从妇女的化妆打扮上看:蓼村遁客在杭州看见“妇女皆调朱傅粉,妖娆冶容”;[4] (P31)在苏州看见妇女“巧妆艳饰”;[4] (P27)在绍兴,鲁叔容“见缝衣妇皆郡人,艳妆浓抹,言笑自如”;[6] (P792)在武昌,江夏无锥子见到太平天国“伪王眷属,皆服宫装,施脂粉”;[13] (P38)在金陵,马寿龄看见妇女是“脂粉馨香肆涂抹”;[12] (P732)李圭看见妇女“不挽髻,用采线结辫盘额上,抹粉涂脂,乘马得得行”;[12] (P491)在平城,顾深所见妇女“皆涂脂抹粉”;[6] (P736)张德坚见妇女“插戴满头珠翠”。[14] (P174)从这些记载的情况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太平天国广大妇女是十分注重化妆打扮的。从妇女的着装打扮方面看:由于妇女要参加军事战斗和劳动生产,太平天国妇女服饰的样式、颜色都与传统妇女的着装有较大的不同。通常穿短衫长裤,禁止穿裙,因此,服饰看起来干净利索和相当清爽,不拖泥带水。“当腰横长刀,窄袖短衣服,骑马能怒驰,黄巾赤其足”。[15] (P17)在颜色上,太平天国妇女特别喜欢五彩斑斓的衣裳。“掳得城中华丽女衣裳,皆贼妇穿著,头扎各色包巾”。[12] (P622)有的记载她们“衣服鲜华”;[6] (P736)有的描述她们“服饰都丽”;[12] (P594)有外国人记载“她们几乎人人都穿着苏州产的奇巧的绸缎丝服,美丽之极”。[1] (P339)太平天国妇女追求服饰美的行为使得那些死抱传统伦理的封建人士惊呼“可笑”,[16] (P67)“青黄红绿,错杂纷披,丑恶之态,难以言喻”。[14] (P174)在一些地方,太平天国妇女的装束打扮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标志,在当地妇女当中流行起来,如“女人梳头,以广西式为上,湖南、北次之,余皆不贵”。[17] (P400)在天京还出现了妇女为了穿裙爱美而受处罚的事情。咸丰四年大年初一,“金陵城中女馆,着裙共相庆贺”,[12] (P659)虽然被发现受到了杖责或枷锁,但却表明了女人的爱美之心和爱美之天性是多么的强烈和不可阻挡。正因为如此,连许多外国人对太平天国妇女的装束也赞叹不已。缪维廉先生夸她们“全都穿着很好的衣服,态度庄重”。[8] (P385)卑治文在南京见到妇女的外表当然也“感到新奇”了。[3] (P167)从妇女的体态和步态来看:由于太平天国服装的变化和废除缠足陋习,使得妇女体态和步态与传统的“小脚女人”相比有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广大的劳动妇女,有不少的史料记载她们是“颇矫健”,“勇健过于男子”,“摇旗行走”,“走如风”。就连太平天国各王的女眷也和传统的“官夫人”有了很大的区别。江夏无锥子在武昌见到太平天国六王的女眷入城时“稳坐官轿”,“轻盈体态”,“手持便扇”。[13] (P37)她们不再像“三寸金莲”那样走路摇摇摆摆,站立不稳。因此,呤唎感叹道:“许多太平天国的妇女非常美丽,和清朝妇女适成鲜明的对照,这大概由于太平天国妇女是天足的缘故。中国妇女的天足十分好看自然,从而步态也极为优美。”[3] (P241-242)“使她们从而改善了自己的外貌”,“和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外貌显示了巨大的区别,并表现了巨大的改进”。[3] (P240)
(五)在宗教生活方面,妇女可以参加宗教祭祀活动
凡礼拜日,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在同一礼拜堂敬拜天父。“军队中男女分营,只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不分男女”,[3] (P241)“在宗教上她们受到了谆谆的教诲,在宗教礼拜中她们也享有适当的位置,许多妇女都是热心的《圣经》宣讲师”。[3] (P241)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所留下的一幅《一个太平天国的礼拜堂》插图中,就十分清楚地看到男女分列两边,女人全神贯注听讲并时而私下交谈的图画生动具体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与中国传统妇女在宗教方面连进入宗祠寺庙都是对祖先和神灵亵渎的“女人祸水论”相比,无疑表现出太平天国妇女的参教自由和在宗教上的特有地位。
二
与传统妇女相比太平天国妇女为什么在社会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女性美、恋爱婚姻和宗教生活等方面享有较高自由度?这的确值得深入研究。如果说妇女自由是太平天国实施妇女解放所为,那么仅仅依据以上中外人士的记载还不足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认为,太平天国妇女在社会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和恋爱婚姻等方面的自由主要与太平天国发源地——广西地区妇女崇尚自由的风尚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广西客家、壮族妇女的自由习俗在太平天国内一种自然而然的继承和发展。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于广西客家人和壮族人民的主要聚居区。无论是运动的发源地桂平县紫荆山,还是起事建号之地金田地区,“多为由粤迁居之客家人”,[18] (P69)“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占优势”。[19] (P76)就太平天国最主要领导人的身份来看,天王洪秀全以下六人的领导集团中有五人是客家人。[20] (P174)据学者考证,紫荆山东王冲的杨秀清、武宣东乡的萧朝贵、桂平金田村的韦昌辉、贵县北山里的石达开也均为客家人。[21] (P371-372)其中,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等人不仅仅是“客籍来人”,而且其祖辈大都居住在客家人的核心区域广东嘉应州一带。太平天国后期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洪仁玕、陈玉成等也是客家人。就参加金田起义的团营民众来看:“上帝会教徒多数为客家人”,[6] (P870)其中参加团营的紫荆山烧炭工“几尽是原从广东迁来的客家人”。[22] (P26)在太平天国中,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教徒民众,客家人都占了很大一部份。同时,广西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壮两族人数最多。清代以后,桂平县就是“民瑶杂处”,“壮居其半,其三瑶人,其二居民”。[23] 早在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时,紫荆山地区参加拜上帝会的烧炭工和农民中,就有许多是壮族人,如最早加入拜上帝会的嘏王卢六。贵县、武宣、石龙、象州等地均有不少壮族农民加入拜上帝会。据建国后的调查,仅石龙县东乡参加拜上帝会的人数就一百三十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壮族。[24] (P147)据学者考证,参加金田起义的群众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少数民族,其中壮族最多,瑶族次之。参加起义的韦昌辉所部几乎全是壮族;石达开所部,包含了贵县龙山、奇石、中里和桂平武平、庆丰等地的壮族;桂平县军营村一千多壮族全部加入了太平军;石龙县的新寨村参加太平军的壮族人民就占了全村80%;大瑶山石龙村一千多壮族也纷纷加入太平军。[25] (P1320)太平天国的女军中也有许多壮族、瑶族妇女。“贼素有女军,皆伪王亲属,瑶壮丑类,生长洞穴”。[14] (P111)在太平天国领导人中北王韦昌辉、慕王谭绍光也都是壮族。可见,在太平天国领导和将士之中,除客家人之外,壮族也占相当一部份比例。关于客家人和壮族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学界已有许多学者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对客家妇女和壮族自由习俗对太平天国妇女自由度的影响论及不够。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专门论述。
(一)从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自由来看
客家妇女广泛参加各类生产劳动,无论是上山砍柴耕种、下田翻土插秧,还是赶墟采购做生意等等,都充当了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其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精神,为世界所公认。可以说自有客家以来,妇女便一直是家庭日常生活、社会经济生产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据史料记载,客家妇女生产劳动的情况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奉俭约,绝无怠惰骄奢之性,于勤俭二字,当之无愧。”[26] (P2211)“客家妇女真是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妇女中最值得赞叹的了。在客家中,几乎可以说,一切稍微粗重的工作,都是属于妇女们的责任。如果你是初到中国客家地方住居的,一定会感到极大的惊讶。因为你将看到市镇上做买卖的,车站、码头的苦力,在乡村中耕田种地的,上深山去砍柴的,乃至建筑屋宇时的粗工,灰窑瓦窑里做粗重工作的,几乎全都是女人。她们做这些工作,不仅是能力上可以胜任,而且在精神上非常愉快,因为她们不是被压迫的,反之,她们是主动的。”[27] 以上资料充分反映了客家妇女不仅劳动时间长,从早到晚,劳作不停,而且从屋内家务劳动到野外的各种生产劳动,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壮族妇女同客家妇女一样勤于劳动。据现有文献史料记载和民俗传承来看,由于广西壮族母系社会解体较晚,壮族妇女自古以来,就担负起耕织和家政的双重重任。甚至出现“男不知力田,女独苦井臼”和[28] (P301)“春耕力作趁圩贸易多妇女”[28] (P317)的独特现象。
正由于广西客家和壮族妇女自由劳动精神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在广西各地,妇女广泛地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和商业贸易活动。胡朴安在《中华全国风俗志》中收录的广西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妇女劳动情况主要有:在梧州,“市多妇女,椎髻跣足,粜谷卖薪”;(《粤西丛载》)在横州,“荷担贸易,百贷(货)塞途,悉皆妇女,男子不十一”;(《日询手镜》)在镇安,“春夏男女耦耕”;(《镇安府志》)在北流,“农力于田,妇人勤纺绩”;(《金志》)在兴业,“妇女纺织耘耔,兼樵牧负担之事”;(《兴业县志》)在罗城,“男不知力田,女独苦井臼”;(《柳州府志》)在玉融,“女务纺绩”;(《柳州府志》)在怀远,“女兼樵织”;(《柳州府志》)在思恩,“市廛多妇女贸易”;(《一统志》)在武缘,“女业纺绩”;(《金志》)在田州,“妇女贸易墟市”。(《金志》)由此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广西妇女不仅要从事纺织等工作,还同男人一样上山砍柴放牧,下地耕田犁垦,在集市贸易中更是充当了主力军。作为长期浸润客家、壮族文化的太平天国领导人和广大将士,将客家、壮族妇女自由生产的劳动习俗以及客家、壮族男女分工模式引入太平天国,并大力鼓励和倡导妇女参加劳动,出现“一切劳动苦工似乎都由她们承担”的结论是不值得奇怪和大书特书的。
(二)从社会交往来看
由于家庭、经济事务的需要,客家妇女没有其他民系女子那样的繁琐的闺阁之规。她们大量地出入于社区之中,是客家社区文化和社区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如赶墟采购、宗族庙会、山歌对唱、做小生意等,“阗溢于廛肆之间、田野之中”,[29] 正可谓“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不仅如此,她们还可以远渡重洋到国外去打工。据美国著名作家米切纳的《夏威夷》一书,美国人魏经到广东雇三百华工到夏威夷种蔗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妇女准许到香树国(当时我国人对夏威夷的称呼)去吗?”得到的回答是“也许客家妇女可以,闽南妇女则不行。”于是魏医生想道:“也许有一天夏威夷会需要中国妇女,不过一定要客家人去。她们看起来又强健又聪明。”最终魏医生招募了一位名叫夏美玉的客家妇女,到夏威夷的魏家去做女佣。米切纳笔下的这位客家妇女,就是一名妇女自由劳动者的典型代表。[30] 1911年纽约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指出:“客家妇女比纯中国人漂亮,不缠足,在公共场合自由活动。”因此,太平天国妇女在与外国人交往中表现出落落大方的态度和“打破了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的结论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三)从追求女性美来看
由于自然环境、生产劳动及生活习俗的影响,客家妇女的装束打扮通常是粗衣薄妆、不事雕饰,追求一种自然朴素美和崇尚自然健康的习俗。但这并不意味着客家妇女没有爱美之心。在一些特殊和重大日子里,她们也“盛妆始脂粉,常饰惟綦巾”。[31] (P11)黄遵宪曾记载他的曾祖母李太夫人喜欢用艳装和脂粉来打扮小孩:“头上盘云髻,耳后明月珰。红裙绛罗襦,事事女儿妆。”[31] (P153-154)客家妇女常带的“凉帽”,虽然是用薄薄的篾片或麦秆编织的,但上面绣着梅花等纹饰。帽沿吊着五颜六色的垂布,黑色、蓝色、白色、花色等等,特别是年轻未婚姑娘们还在垂布的两端编织着五颜六色的彩带,垂布随着身体摆动在风中飘舞摇曳,女人爱美天性之强烈可见一斑。客家妇女除少数富贵人家的闺秀外,大多不缠足。史料记载:“岭南妇女多不缠足,其或大家富室闺阁则缠之,妇婢俱赤脚行市中,至人家,则袖中出鞋穿之,出门即脱置袖中。下等之家,女子缠足,则皆诟厉之,以为良贱之别”。[28] (P293)劳动妇女大都是“戴笠跣足”或“跣足不履”。[28] (P306)黄遵宪称她们“半是赤足仙”。[31] (P258)可见,客家妇女不仅不缠足,而且有的还赤脚而行,即便有鞋,也只是到了别人家出于礼貌才穿上,劳动妇女如果缠足反而会遭人耻笑和责骂,甚至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姑婆”。客家妇女亦不束胸,黄遵宪先生曾引用一位外国传教士的话对此习俗表示赞赏:“西人束腰,华人缠足,唯州(嘉应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完全无憾云。”[31] (P291)没有半点江南女子“婷婷复袅袅,纤步殊可怜”的娇态。红润的面容、黝黑的皮肤、丰盈的体态、健美的身材和稳健的步态,使客家妇女能像男人一样参加各种劳动和战斗。郭沫若先生于1965年去梅县时,曾挥毫写出:“健妇把犁同铁汉,出歌入夜颂丰收”的名句。因此,在太平天国史料中频频出现的“大脚蛮婆”、“颇矫健”、“勇健过于男子”、“摇旗行走”、“走如风”等感叹是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四)从恋爱婚姻自由来看
太平天国妇女的恋爱婚姻自由明显受到客家妇女和壮族妇女恋爱婚姻自由习俗的影响,具有相当的自由。客家妇女尽管同样受到指腹婚、童养媳、换婚及买卖婚姻陋习的残害,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独立生活所形成的独立人格,使她们在婚姻问题上也具有一定的自由。客家人素有对歌风气,无论劳作还是歇息,都习惯于随口大呼大唱,以山歌互诉悲欢哀喜。客家农村妇女大都是唱山歌的能手,许多姐妹可以通过对唱山歌表达爱情,与自己中意的男子缔结良缘。黄遵宪留下的80多首客家妇女诗,真实地反映出大多数客家妇女无视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于率直痴情地追求爱情与婚姻幸福。有的表现了客家妇女敢于追求爱情的勇气:“一声声道妹相思,夜月哀猿和竹枝。欢是团圆悲是别,总应肠断妃呼豨”。[31] (P292)有的表现了时刻相随、形影不离的亲密情侣形象:“人人要结后生缘,依只今生结目前。一十二时不离别,郎行郎坐总随肩。”[31] (P20)有的表现了妇女率直迫切地呼唤丈夫疼爱自己:“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夫容五枣子,送郎都要得郎怜。”[31] (P21)有的表现了妇女忠于爱情、日夜盼夫归的相思之情:“邻家带得书信归,书中何字侬不知。等侬亲口问渠去,问他比侬谁瘦肥。”[31] (P20)有的表现了含情脉脉而又娇羞万状的客家新嫁娘风貌:“脉脉春情锁两眉”、“相看霞脸转生羞”、“半含娇态半含颦”、“一抹轻红傍脸斜”、“脸波一笑向人红”。[32] 这些诗歌不仅毫不掩饰地反映客家妇女出乎天性的正当要求,而且毫无疑问地反映出客家妇女一反封建礼教之闺训,表现出对“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教条的蔑视。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客家地区“夫死可嫁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根据文献史料记载和当代田野调查的口碑资料情况来看,客家地区不仅允许寡妇改嫁,而且妇女在改嫁中还拥有相当的自主权,主要取决于她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并不是任人摆弄和宰割。笔者曾撰文专门论述,此不多言。(注:客家寡妇再嫁问题,参见拙文《广西地方婚俗与太平天国寡妇再嫁问题》,《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壮族妇女和客家妇女一样在男女交往和恋爱婚姻上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权。以下几个典型的壮族婚姻习俗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第一、“倚歌择配”习俗。这是壮族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习俗。女青年通过对唱山歌表达爱情,选中自己的如意郎君。“赶花街”是壮族青年一年一度最隆重的歌会,每年农历3月初3举行。青年男女一般先是在街上走走串串,寻亲访故,相互寒暄问候。在这个过程中,男女慢慢各自结队,开始酝酿对唱。花街进入高潮时,男女青年不约而同地手拉手围起大圆圈跳舞,舞兴未尽,男女青年便散到河边、桥头、路旁和树下进行对歌。随着对歌的深入,男女双方慢慢靠近,若两相有意,则双双离开,另寻两人天地去了。这种习俗不仅说明了男女自由交往无禁忌,而且更充分体现了妇女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权力。第二、“串寨”婚俗。壮族姑娘走村串寨唱歌选“上门郎”,找到称心如意的郎君便交换信物,确定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歌形式选中郎君,并非事先征得父母同意,而是私定终身后,才正式告诉父母,再由父母按照壮族礼俗操办婚事即可。第三、“抛绣球”、“红蛋”等习俗。这也是壮族妇女自由择配的一种表现形式。壮族妇女把绣球抛向自己的意中人或将手中的红蛋让意中人撞破,这些均由妇女自己选择,主动权也完全在女方手中。第四、“不落夫家”婚俗。指青年女子到夫家举行婚礼后即返回娘家居住,经过3至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直到怀孕后才回到夫家长住,其间只以客人的身份在年节或农忙时到夫家帮忙,住3至5天。妇女在不落夫家期间还可以有社交的自由,可以和婚前一样和异性对歌和交往,有的甚至可暗中与丈夫以外的其他男子产生新的恋情。许多青年女子由于不满自己的婚姻而通过长期的不落夫家以示抗争。这无疑是对封建夫权和家长权的一种蔑视和挑战,表现出女性在婚姻上有较强的自由风尚。另外在壮族许多地区,无论死了丈夫的寡妇,还是离婚的女子;无论是已为人妻的妇女,还是未上门的准媳妇;无论是女人守寡,还是男人守鳏,都可以再嫁再娶。自己决定自己的婚事,只要不引起众怒,社会和家族都不会给予过分干涉。(注:壮族寡妇再嫁问题,笔者曾发表文章作过专门论述,参见拙文《太平天国寡妇再嫁问题辨析》,《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所以,作为长期受广西壮族社会文化熏染的太平天国,将男女自由交往和妇女恋爱婚姻自由之俗引入到太平天国内,可以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延续。
(五)从宗教习俗和信仰来看
客家人多住在偏僻山区,由于客家地区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大多外出谋生,有的甚至远涉南洋,少则几年,多则半世,才能归家,客家妇女在传统的宗教活动中自然而然地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做社”习俗中,一个族的族人通常一年要两次祭拜社官,做社“头”的大都是女性(家娘),而且将象征女祖宗地位的“凤头”树枝放入祭祀品之中,更显得妇女在整个宗族中女性的重要性。在“祭祖”习俗中,祭拜祖宗一年通常也举行是两次。在传统社会中,宗族祭拜祖宗是男人的专利,妇人只能协助挑祭品、摆祭品等杂务,妇女是被排除在外的。但在客家地区,有不少宗族祭祖时是由女性“户主”主持。在一年一度的除夕或正月初一的祭典活动中,最重要的上香仪式多由女性“户主”拿着香烛到祖宗香炉传燃香火,然后再分发给家庭成员并带领他们一起向祖神叩拜。每年踏青扫墓时,妇女也要带领家人到祖先墓前拜祖,“爆竹响墓背,墓前纸钱烧”。[31] (P155)这些民俗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宗族妇女在敬祖、敬神的活动中的地位,妇女不但可以参加,而且往往是这些活动的主持者。
三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33] (P1)民间社会的各种行为,具有教化、规范、维系和调节等功能。太平天国爆发在广西客家和壮族聚居的地区,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和广大起事将士又长期受到广西地域民俗文化的熏陶。客家和壮族妇女的自由习俗在行为模式、道德准则、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价值标准等方面,对太平天国妇女的习惯和模式,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妇女在生产劳动、社会交际、恋爱婚姻、女性美和宗教活动等方面的自由毫无疑问与太平天国发源地——广西地区妇女崇尚自由的风尚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广西客家、壮族妇女的自由习俗在太平天国内一种天然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民俗的传承性、规范性、扩布性、集体性、稳定性所决定的。
事实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确没有将妇女崇尚自由的风尚上升到妇女解放的高度。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还仅仅是战争条件下男女分工的一种表现,无论从劳动规模、劳动种类、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劳动强度,还是从劳动待遇看,妇女还只是被当作太平天国的一种劳动工具而已。(注:参见拙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与太平天国妇女解放问题之辨析》,《天府新论》2000年第3期。)妇女社交和男女自由交往在民间大量存在,在太平天国高层来往中也不鲜见,但同时太平军却一直坚持“分男行女行”,而在洪秀全的后宫更则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对于后宫“娘娘”,1853年洪秀全专门颁布一条《严别男女整肃后宫诏》,明确宣布“男理外事,内非所宜闻。女理内事,外非所宜闻”,“外言永不准入,内言永不准出”,甚至“后宫而(面)永不准臣下见”,“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不赦”。[5] (P38)对于自己的儿子洪天贵福,洪秀全还专门撰写了一本《十救诗》作为他言行举止的金科玉律,涵盖“妈别崽”、“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哥别婶”、“爹别媳”、“孙别婆”等“严别男女”的内容,其中有些规定近乎于荒诞无聊,如男童7岁就不能再与母亲同床,姐姐也要与他保持一丈远的距离,妹妹5岁后哥哥就不能再拉她的手。[34] (P798-799)洪秀全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后宫为治化之原,宫城为风俗之本”。[5] (P38)其实早在太平天国起事前,洪秀全对广西地方流行的男女通过对歌自由交往、“倚歌择配”的习俗就深恶痛绝,斥责为“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34] (P44)因此,“在对待两性关系问题上,洪秀全的真实思想要比他所公开推行的政策更为严苛和偏执”,[35] (P25)其“真实思想”本身就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传统伦理观念。太平天国有男女自由恋爱婚姻的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军中的婚姻“基本上属于违背女方意愿的强制性婚姻”。[35] (P20-21)1855年,东王杨秀清“传令贼伙,有能烧我师船者(清水师),每人赏银一百两,即封为指挥总制等官,城中妇女听其选配”。[36] (P440)庚申十年(1860),干王洪仁玕在《劝谕清朝官兵弃暗投明檄》中宣称“无室者亦婚配以各遂”。[5] (P150)用女人作诱饵去引诱、拉拢清兵归降,真可谓“用心良苦”。1861年,忠王李秀成在绍兴为奖励有功之臣,下令允许他们从女馆中“自择”女人。[6] (P798)1862年,“苗家老寨”的“苗大人”归顺了天朝,洪秀全便馈赠、恩赏“苗大人”王娘数名,并“派专员护送前去”。[5] (P236)更有甚者,由于长期实行“别男女制度”,引起了太平军将士的不满和骚动。为了安定军心,以防暴乱,太平天国答应士兵以婚配。但这是怎样一种婚配呢?“设伪媒官,令伪巡查遍稽女馆,年十五至五十者若干人,列诸册簿;贼众报名伪媒官所,制签领配。伪丞相得配十二女,伪国宗八女,余依次递减,无伪职者,人配一女。”[37] (P310)这哪里是所谓的正常婚配,纯粹是动物式的交媾。当时妇女“被迫自尽者甚众”。[37] (P310)那种结婚需要结婚证书,结婚“变成了爱情的结合”所赞美的却完全是地地道道的古代奴隶制下男奴和女奴动物式的配种行为,是极其丑恶的。因此,如果将太平天国妇女自由问题作为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一大依据,并认为是一种解放妇女的自觉行为,显然是值得讨论和进一步商榷的。
标签:壮族论文; 太平军论文; 壮族服饰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习俗论文; 客家风俗论文; 客家建筑论文; 客家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传统民俗论文; 男女婚姻论文; 百越论文; 南宋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