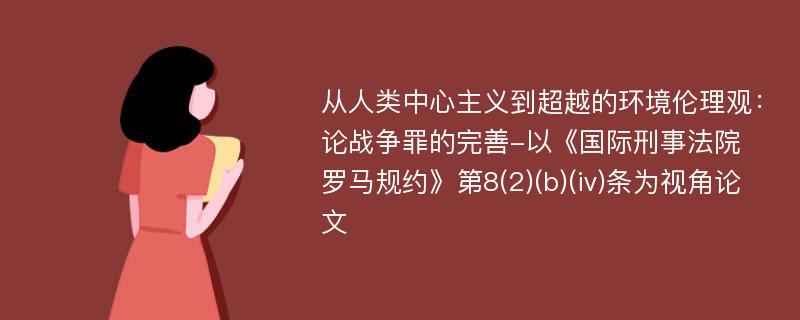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超越的环境伦理观:论战争罪的完善
——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2)(b)(iv)条为视角
孙世民
摘 要: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条是当前国际社会关于战争罪最为完整和全面的解读,其中的第(2)(b)(iv)项内容规定了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构成战争罪,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保护自然环境的关注和重视。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分析,第8(2)(b)(iv)条的规定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是这种基本立场存在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误解,不利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环境伦理学理论的新发展,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可以从添加过失要件、完善对严重损害自然环境标准的认定、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扩大适用范围等方面对现有战争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完善。这种完善不但有利于在理论上实现环境伦理学对国际环境保护有关条约的发展,还有利于在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而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 人类中心主义;超越的环境伦理观;战争罪;《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战争一直在折磨着人类,(1) 本文认为,“战争”与“武装冲突”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而不需要加以区别。 虽然早在1928年就已经否定了战争作为国家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的合法性,然而,人类中的癫狂者却一直如同战争一样魔鬼般使用着恶魔的手段。(2) 林灿铃:《国际环境法》(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2页。 战争不仅会对人的生命和健康以及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严重破坏,还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有鉴于战争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1977年的《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以下简称《第一附加议定书》)中明确规定了在战争中应当保护环境的条款:第35条第3款规定了禁止在战争当中使用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和手段的基本原则(3) Article 35 of 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It is prohibited to employ methods or means of warfare which are intended,or may be expected, to cause widespread,long-time and severe damag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第55条进一步规定了禁止使用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而损及居民健康和生存的作战方法和手段以及禁止以报复的名义攻击自然环境的内容(4) Article 55 of 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 of 12 August 1949 and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1.Care shall be taken in warfare to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gainst widespread, long-time and severe damage.This protection includes a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methods or means of warfare which are intended or may be expected to cause such damag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reby to prejudice the health or survival of the population.” 。但是,《第一附加议定书》中并没有直接规定在战争与武装冲突当中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也没有研判武装冲突所致环境损害责任的具体性质,更没有将这种行为规定为国际环境犯罪。历史上第一次把在战争当中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明确规定为国际罪行的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一、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构成战争罪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第8条是当前国际社会关于战争罪最为完整和权威的解读,其中的(2)(b)(iv)项内容是当前《规约》中既存的唯一明文规定在特定情况下严重破坏自然环境行为构成国际犯罪的条款。该项的具体规定是:“故意发动攻击,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其程度与预期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的。”(5)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第b项(iv)。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第8条整体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因而通过第8(2)(b)(iv)条的具体规定,《规约》纳入了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时期的环境保护条款,这表明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时期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属于严重破坏1949 年《日内瓦公约》行为之外的严重违反国际法既定范围内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规和惯例的其他行为之一,可能构成战争罪,《规约》因此成为了国际上第一个通过战争罪的方式保护自然环境的现行和有效的国际条约。
仔细分析《规约》第8(2)(b)(iv)条的规定可知,以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方式成立战争罪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攻击自然环境的行为会发生严重的损害后果却依然发动对自然环境的攻击行为,并对所发生的损害后果置之不理,即存在主观故意,无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第二,攻击行为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当是广泛、长期和严重的,不是任何程度的损害都可能构成战争罪,而且《规约》当中对损害采用的是并列标准,即广泛、长期、严重必须同时具备;第三,自然环境所遭受破坏的程度与预期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即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军事行为应当严重地违反《武装冲突法》中的军事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第四,该行为发生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从而排除了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之前和之后成立战争罪的可能性,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适用范围可以由《规约》第8条的整体规定分析出,虽然该要件并没有被第8条第2款第b项(iv)具体条款所规定,这也同时排除了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当中成立该国际罪行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第8(2)(b)(iv)条是《规约》当中唯一明确规定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造成自然环境严重损害的行为人需要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条款,对于在武装冲突当中预防和规制破坏自然环境的国际罪行具有重要的意义。这表明,随着传统国家责任和跨界损害责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了进一步保护国际环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关注到通过建立国际刑事责任的形式保护全球自然环境的积极意义。这个新的关注点对于规制在战争与武装冲突中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环境治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第8(2)(b)(iv)条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还需要从构成要件方面进行深入的完善。这是因为,通过分析该条款的环境伦理学基本立场可知,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该条款的具体内容并不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保全。
二、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战争罪
环境伦理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伦理原则、伦理范畴和德行规范的知识体系,是研究人与自然如何协调发展的知识体系。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伦理学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该理论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环境伦理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并以此构建环境价值体系和范式。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的稳定运行,所以人类有必要将道德关怀扩展到自然这样一个客体,但是作为客体,自然的价值体现在人类这样一个主体之上,离开了人类这样一个主体,自然就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所以人类作为主体自身的利益才是自然这个客体存在的基础。(6) 裴广川、林灿铃、陆显禄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规约》第8(2)(b)(iv)条中关于在战争当中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构成战争罪的规定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理念和观点。
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高峰期,兴奋与抑制不平衡时期身体发育迅速、骨骼、肌肉快速增长逐步完善且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自我心理[3]。同时智力发展和知觉越来越敏感、精确、快速。根据最新的学生体质调查,当前的中学生由于家庭环境都比较好动手能力多数较弱,体现出柔韧性、协调性较差,反应能力、动作速度逐年下降。但该阶段学生身体正处于全面发展阶段,如有科学有效的运动刺激就可以促进其骨骼肌肉的生长和身体各机能的完善,使其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在传统教学中的问题是:
(一)故意要件的建立
《规约》第8(2)(b)(iv)条将“故意”作为战争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即行为人需要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并且在这种认识下仍然发动对自然环境的军事行为或者命令下级进行这样的行为。在武装冲突当中,无论是上级责任者,还是具体实施者,都需要明确知晓自己的命令或者行为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否则便不构成战争罪。这种规定将人类放在俯视自然的位置,本质上是把人作为主体、把自然环境作为客体,从人类主体的角度对自然环境这个客体进行保护,自然客体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它对人类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之上,通过提高战争罪主观构成要件的标准来减少行为人成立战争罪的可能性,最大程度地实现对人类主体利益的保护,在保护人类主体的利益之后才考虑环境作为客体对人类的价值,这种人与自然环境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平等地位的划分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
(二)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标准
《规约》当中规定,构成战争罪需要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这种并列式的列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程度。这个客观的构成要件表明,《规约》已经认识到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的稳定运行,这是对以往人类肆无忌惮地对自然环境进行索取和破坏的反思。因此,人类应当对自然环境施以道德思考、道德关怀,从道德代言人的角度有限度地利用自然环境。但是,这种采用较高损害标准的做法仍然是把人放在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首位,因为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在现实当中是较为困难的。不仅如此,《规约》当中并没有对“广泛、长期和严重”进行明确的定义,只是抽象地规定了这样的损害程度构成战争罪,这种模糊的规定体现了虽然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但是人类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当中依然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也是有差别的,其基础还是人类作为主体、环境作为客体的认识,这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在《规约》当中的体现。
(三)军事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适用
军事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作为战争与武装冲突法中的两个基本原则,要求在对军事目标进行军事攻击时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和民用物体所造成的附带性损害,并要求这种附带损害不应超过在军事行动中所要达到的直接的军事利益。(7) 周忠海主编:《国际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6页。 《规约》第8(2)(b)(iv)条的规定体现了这两个原则,即构成战争罪的行为必须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超越了军事上的需要,否则这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就不构成战争罪。这是一种人类的军事利益与环境利益的衡量,而《规约》优先选择的是人类利益中的军事利益。这表明,在战争进行的过程当中,为了实现军事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自然环境的行为是不违反《规约》的,这和人类中心主义中实现人类自身利益才是最终目的的观点不谋而合,尤其是表现出人类自身利益是环境道德的基本立场,即相比于环境的内在利益和价值,人类自身的利益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人类保护自然环境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追求,这种将人类为了取得军事胜利而获取的利益视为高于自然环境存在利益的观点,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理念。
(四)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范围
《规约》仅规定发生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构成战争罪,却没有将发生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也列入其中。可是,无论是在国际性武装冲突当中,还是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当中,都可能会发生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军事行为。《规约》的这个规定虽然保护了国际性武装冲突时的自然环境,但这种保护还是出于对人类自身利益的保护,是从人类作为主体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把自然环境视为客体,有选择地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将发生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行为排除在外,对两者进行差别对待。《规约》的这个规定不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自然环境,最终也不利于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全面保护,应当在日后的《规约》缔约国大会当中被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规约》第8(2)(b)(iv)条之所以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契合,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人类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环境伦理观,这种环境伦理观指导着《规约》的起草、制定和通过。囿于当时国际社会发展的局限,《规约》制定时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关注,环境伦理学也已经诞生,但过多地考虑的还是人类的利益问题,忽视了自然环境的独立价值和内在价值,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的现实需求尚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共识。尽管国际社会在那时已经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生态系统的稳定不辍,人类的各项活动应当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全面地考虑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没有完整地考虑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至于人类应当如何面对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如何善待自然、保护自然、发展自然,以及如何实现自然的生存权等这些与环境伦理学有关的哲学问题也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因此,当下需要以一种崭新的环境伦理观来实现以《规约》第8(2)(b)(iv)条为代表的战争罪的完善,以实现人类之间的公平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崭新的环境伦理观就是超越的环境伦理观。
三、以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完善战争罪
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超越的环境伦理观是一种能够同时接纳和包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开放的环境伦理学。超越的环境伦理观认为:1.人应当用道德来约束自己对待生态系统的态度,自觉承担起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道德责任,人是生态系统的道德代言人;2.环境问题的本质其实是人类自身的问题,是由人类造成的问题,而不是生态系统造成的问题,人应当认识到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和独立价值;3.人有道德上的义务为后代留下一个适宜他们生存的自然空间,这也是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4.人与自然环境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但并不代表二者有相同的道德重要性,要区分道德地位和道德重要性;5.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生态环境,离不开生物的多样性,只有保护了生态环境,人的生存才有保障。(8) 同前引[6],第63页。
之所以应当采用《公约》中的“长期、广泛或严重”的损害标准作为认定在武装冲突中因破坏自然环境而成立战争罪的构成标准,而不是《规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中现有的“长期、广泛和严重”的损害作为认定损害程度的标准,在于“长期、广泛或严重”的认定标准比“长期、广泛和严重”的认定标准低,(11) C.D.Stone,The Environment in Wartime :An Overview in J .E .Austin ,C .E .Bruch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1.后一种标准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这就使得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变得狭窄,增加了行为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难度,使得现实当中难以实现这种标准,不利于保护环境的内在价值。(12) M.Bothe,C.Bruch,J.Diamond,D.Jensen,International Law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gaps an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Red Cross ,2010,vol.92,pp.569-575.而实际上,同时满足这三个要求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这就使得原本难以认定的在武装冲突中造成自然环境损害的国际刑事责任变得更加难以认定,最终使得关于行为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规定成为一纸具文。而至于时间的具体长度、空间的实际范围和严重范围等标准的认定,则应当结合现实发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认定,满足一个认定标准即符合战争罪的构成要件,可能构成破坏自然环境类型的战争罪。简言之,这种认定标准更有利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也是超越的环境伦理观所倡导的。
由此可知,超越的环境伦理观是指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时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和不足,在吸收他们优点的基础之上,以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观。(9) 蒲昌伟:《国际环境法的环境伦理学依据及其伦理基础探索》,载《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第5期。 超越的环境伦理观是环境伦理学的最新发展,而环境伦理学是一种开始于20世纪初期的哲学思潮,其思考的问题本质上属于哲学问题,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生态学、环境科学与伦理学交叉的学科。环境伦理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伦理原则、伦理范畴和德行规范的知识体系,是研究人与自然如何协调发展的知识体系,是关于环境道德问题的学说,是环境道德思想、环境道德观念的知识体系,其产生于人类对环境问题的深度反思,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发展,为国际环境保护事业提供了伦理基础。环境伦理学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这是指导人类正确处理与大自然关系的最为有效的理论前提。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应该是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只有用处理伦理关系的准则来处理才可能实现。
超越的环境伦理观体现了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等几个流派的整合。例如,人类中心论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环境伦理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并以此构建自己的环境价值体系;动物权利论认为动物和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具有相同的地位,人类不能在拔高自己地位的同时贬低动物的地位,应当平等地对待动物,不能残酷杀戮动物;生物中心论扩大了动物权利论的关注范围,把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从动物扩大到所有的有机体,要求对所有的有机体进行道德关怀和帮助;生态中心论是一种主张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和独立价值,应和人类具有同等的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人类应当帮助生态实现这种独立和内在的内容价值以及存在和发展的自然权利的理论。(10) 同前引[6],第1页。
1)建设厂级数据中心的硬件支撑架构。根据顶层的规划设计,建成能够支撑未来3-5年的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计算、数据分析应用开发所需的硬件支撑环境,确保新技改完成前的数据增长及数据分析环境的硬件支撑需求,支持动态扩容,随时能够增强整个硬件体系的服务能力,包括未来数据中心要承担的“实时数据处理”的能力,如设备实时运行数据、实时生产数据、实时环境数据等的采集、处理能力[3]。
由前文的论述可知,《规约》中对损害标准的规定和《第一附加议定书》中对损害标准的规定是相同的,即都是要求所造成的损害是“广泛、长期和严重”的。但是,作为同样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中的规定,与这个损害标准不同的是1976年12月10日的《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后文简称“《公约》”)中的规定,该《公约》中规定造成“长期、广泛或严重”的自然环境损害才是应当受国际法规制的、在武装冲突中损害自然环境的认定标准。从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角度分析,该《公约》的认定标准更加科学,更有益于实现环境的内在价值和独立价值。所以,应当将《规约》中关于造成自然环境损害的现有认定标准修改为“长期、广泛或严重”。
(一)补充过失要件
简言之,军事必要原则和比例原则不能成为交战方肆意破坏自然环境的免责事由,可持续发展原则才是《规约》应当采取的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理论基础。鉴于武装冲突所致的环境损害会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造成的严重破坏,环境利益与军事利益相比对人类具有更高的价值。因此,不能为了实现军事利益就放弃环境利益,应当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肯定环境的内在价值和独立价值,采用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这些内容既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要求,也是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体现,理应被《规约》所吸纳。
(二)建立长期、广泛或严重的损害标准
但是,单纯依靠超越的环境伦理观,从人的主观认识和道德自律去应对战争对环境的严重破坏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在一个利益至上的社会,超越的环境伦理观作为一种伦理观念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仅通过有强制拘束力的《规约》第8(2)(b)(iv)条把在武装冲突中破坏环境的行为列为战争罪而进行规制也是片面的,因为这并不能从本源上解决把环境作为人类附庸的观念。如果说超越的环境伦理观解决的是为什么要保护环境,即使是在战争当中也要保护环境的问题,那么《规约》第8(2)(b)(iv)条则解决的是如何在战争当中保护环境的问题。良好的战争与武装冲突法需要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指引,超越的环境伦理观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这其中也包括保护受战争和武装冲突所影响的自然环境。这体现了超越的环境伦理观与国际法之间的互动,二者相得益彰,共同保护国际环境。因此,对《规约》第8(2)(b)(iv)条规定的战争罪的构成要件的完善应当建立在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基础之上,从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视阈对该条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
此类反应很容易进行,但一般只生成分子内具有酯的羧酸,业内戏称为“单边外交”。如果需要进一步酯化,则需在酸催化下进行一般的酯化反应。
(三)适用可持续发展原则
XI,作为交换架构,其目的是为SAP系统与非SAP系统搭建交流桥梁,使二者无障碍交换信息数据。但不管怎么说,接口技术都是必不可少的,它是SAP内部之间、SAP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基础。为此,我们对接口技术的基本原理、如何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接口技术、接口技术的优势与不足等都做了研究分析。高级企业应用编程语言是接口技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常说:说话是门艺术,话要好好说。但相伴多年的老伴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人:越陌生,越礼貌客气;越亲密,越无所顾忌。因为我们心里认为对方永远不会责怪自己,反而常常将言语的刀子冲向他(她)。每个人并不是坚不可摧的,美好的夫妻生活需要经营,即便你们已经相伴多年。
《规约》第8(2)(b)(iv)条当中规定的是“故意发动攻击,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正如前文所言,《规约》这种规定对主观要件的证明标准要求过高,行为人只需主张不存在故意,就可以逃脱国际罪行的制裁,而对于非故意造成的自然环境破坏的后果与责任,该《规约》并未加以规定。这种规定可能使得《规约》的效果不会十分明显,因为在实践当中,由过失造成的自然环境破坏的后果也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可能是十分严重的。理性的个人和作为自然利益的代言人以及其他物种的道德代理人是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基本立场,这就要求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自然环境利益的保护。而且,鉴于人类和自然具有相同的道德地位,但是二者的道德重要性不同的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基本理念,通过设置过失这样一个主观构成要件,可以较好地在避免既非出于故意又非出于过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国际罪行,保护人类的利益,因为规制这样的行为需要考虑人类的道德重要性高于自然环境的问题,同时实现保护环境与尊重人类价值的目标和理念。因此,需要通过增加过失的构成要件使得在武装冲突中的自然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把发生在武装冲突当中的虽然严重破坏自然环境但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军事行为排除在战争罪成立条件之外,最终在保护人类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基础之上,实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
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与超越的环境伦理观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认为,可持续发展原则是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在指导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时最完美的体现。因此,应当在《规约》当中适用可持续发展原则而不是军事必要原则和比例原则。但是目前,国际社会主要是从武装冲突法的角度看待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问题,这就是在武装冲突与战争中军事必要原则和比例原则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也是《规约》中规定环境破坏的程度与预期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的才构成战争罪的原因。然而,在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看来,由于武装冲突法与国际环境法立法宗旨和目的不同,前者注重的是在军事活动中考虑环境因素,而后者关注的是环境问题是军事活动必须考虑的因素,两者的重点不同,后者更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单独从武装冲突法的角度考虑环境因素不利于更好地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应当利用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可持续发展原则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环境保护形势的新动态也体现了从可持续发展原则认识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明显趋势。例如,2016年5月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关于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地区环境的决议”,强调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保护环境,尤其是在武装冲突当中,不仅如此,还应当加强武装冲突之后环境的恢复工作。(13) UNEP/EA.2/L.16/Rev.1. 又如,联合国环境大会曾呼吁全体会员国尊重和遵守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法律规范,并采取一切措施确保这些国际法律规范能够被实现,这是联合国环境大会首次提出要在武装冲突当中保护环境。再如,2016年8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再次呼吁各国应当加强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工作,并表示将继续向受武装冲突影响国家和处于冲突后局势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14)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areas affected by armed conflict,UNEP/EA.2 /Res.15,1 August 2016. 这表明国际社会在武装冲突中适用可持续发展原则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而作为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条约,《规约》应当规定可持续发展原则。
(四)扩大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正如前文所言,无论是国际性武装冲突,还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都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因此,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环境的内在价值和独立价值,就要树立一种整体主义的立场,把人与自然看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发展的共同体。这种整体主义的立场要求不区分武装冲突的具体类型,对处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自然环境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自然环境施以同样的道德关怀。这也是人类尊重自然、最大程度地通过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以保护自然这样一个有着复杂内容关系有机体的现实需要,以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最终促成一个更合理、更健全、更全面的文明时代的到来。
结语
《规约》第8(2)(b)(iv)条的内容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将关于环境保护的内容纳入国际罪行中的尝试,虽然这次尝试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之上,但是这对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不是指各国兼有之利益,而是特指不能够将其分配给哪一个特定国家的利益,是各国之间不可分割的“集体的利益”,是不能归属于哪个国家或特定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属于国际社会(人类整体)的集体的“整体利益”。国际环境法就是为这种整体利益而制定的国际规则、原则和制度的总和,是建立在“只有一个地球”原则基础之上的国际法新领域、新分支、新学科。(15) 同前引[2],第42页。
现实当中已经出现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转变的征兆。2016年9月15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案件选择及优先性的政策文件》(以下简称《政策文件》)。在该《政策文件》中,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将特别考虑起诉,通过破坏环境、非法滥用自然资源或非法占有土地的方式实施的,或造成这样结果的罗马规约犯罪”。(16) Policy Paper on Case Selection and Prioritisation,Available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official website:〈https://www.icc-cpi.int/itemsDocuments/20160915_OTP-Policy_Case-Selection_Eng.pdf.〉last accessed: 1 Mar.2019. 这表明,未来《规约》当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尤其是第8(2)(b)(iv)条的内容将会得到国际刑事法院更多的关注,《规约》将会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发挥自身的作用。因此,以超越的环境伦理观改造和完善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之上的《规约》第8(2)(b)(iv)条的规定就显得十分亟需和必要。
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自然环境,人类在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开拓了一个人造环境,环境伦理学将为我们营造一个新的伦理环境。当自然环境、人造环境、环境伦理协调一致的时候,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时代就会到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梦想就会实现。今后,我们必须抛弃过去那种对地球可以任意攫取的思想,必须运用集体的智慧把力量集中起来,为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做持久不懈的努力,这就需要从超越的环境伦理观的角度认识环境问题。
2.报名条件资格的问题。从资格限定上看,有的过于宽泛,不同职位同一标准和条件,难以体现职位需求的差异性;有的限制过于严格,致使一些职位报名人员较少,构不成有效竞争。很多岗位由于过于强调年龄、学历、资历和工作经历,使一部分工作经验丰富、业绩良好的干部由于年龄或学历问题被划在圈外,一部分优秀年轻干部由于资历和工作经历被挡在门外。同时,设定标准和条件的科学性、公性度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对人类自身的行为进行约束,其中包括作为自律规范的伦理与作为他律规范的法律两大手段。二者看似两种力量,但却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即伦理是法律的根基和前提,法律则是伦理的载体和升华。由此,治理环境的国际立法必须着眼于环境伦理在法律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功用,明确并维护国际环境法的公益性,进而保证法律作为一种行为导向能够得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为此,要在正确认识环境价值的基础上,建立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对环境施以道德关怀,依靠道德的力量,对人类的思想观念进行内在自律。当然,作为一种文化态度的改变,超越的环境伦理观在全人类意识中的形成自然不会一蹴而就,因而需要发挥环境教育的作用以促进环境理念的育养。不仅如此,环境教育的内容应当既包括超越环境伦理观,也包括环境法律法规,二者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职业都会影响被调查者对于“河长制”的认知程度。如专门从事负责“河长制”相关工作的政府人员与尚未成年的小学生两者之间的数据信息便存在较大出入;由于在当地的居住时长以及居住地与河湖水域的距离远近等因素,被调查者对附近水域的了解和关注程度也不尽相同。样本选取时已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发达程度的城市,以及填写者具有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学历等因素考虑在内。
作者简介: 孙世民,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标签:人类中心主义论文; 超越的环境伦理观论文; 战争罪论文;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