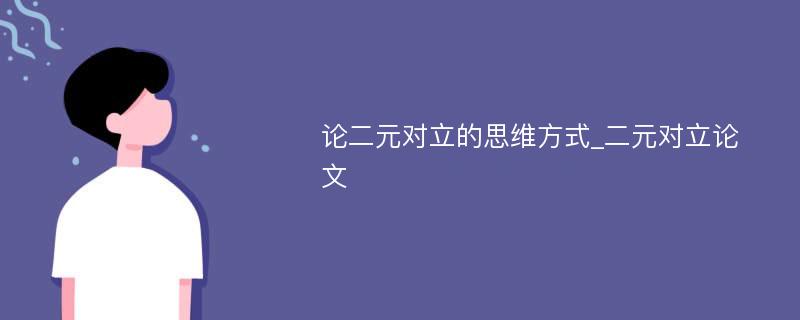
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立论文,思维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播扬人类精神价值的文学艺术受到巨大冲击而处境维艰,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扶持高雅艺术的政策实是救文艺于水火、功在千秋的善举。然而在高雅艺术的认定上,却难以妥贴并服众口。交响乐芭蕾舞西洋歌剧这些泊来艺术归之高雅,国人虽不服气也无话可说。京剧由于早被祭在国剧的崇高地位,说它高雅,人们更难说什么。但是同为地方戏曲的越剧和沪剧在高雅与否的判定上截然有别,却使沪剧界人士大呼不平。
当局如何画出高雅“线”自有他的道理。但好事未能获得众口一词的叫好,实在跟语言使用的简单二分不无关系。按照精确的语义,高雅是和低俗对立的,业内业外的通常用法是和通俗相对。通俗文艺得到商品经济的雨露甘霖,近年来在文化市场大展鸿图,令人好不羡煞,不过骨子里仍难逃为人轻视的底蕴。所以有人尽管沾通俗之光大赚其钱,却绝不肯在自己的大作上署自己的大名。现在既有高雅政策,有些艺术样式和剧种荣膺其榜,那么其他艺术自然不能不入通俗了。象沪剧这样的剧种若仍广有观众,担个贱名倒也罢了,有得必有失。可它的日子实际比越剧还不好过,一入通俗连“救济粮”都吃不上,难怪圈内人士要怨有司不公若此了。
海德格尔说,语言意味着人和历史的存在,也把人拖进历史的陷阱。语言的简单二分,是思维的二元对立模式的产物。按照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值思维逻辑,任何事物非好即坏,非对即错,非革命即反动。整个世界楚河汉界,判然分明,谁敌谁友,实为革命首要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虽然政界合纵连横,朝秦暮楚,从来也没有谁严格遵循过。然而在日常伦理是非判断中,这种思维方式却是深入人的骨髓,溶化在血液里了。因此,交响乐或京剧虽然也可演轻音乐和《纺棉花》之类,还定是高雅艺术;而沪剧和别的地方剧种虽然同样可演《碧玉簪》和《沙家浜》,非通俗艺术而何!王蒙写通俗小说,没有人说他是通俗作家;而通俗作家写的作品即使不比高雅作家更不严肃,通俗这顶铁帽是戴定了。线性思维这把利刃一刀切下去,文艺界清浊两判,省了多少罗索。
二值逻辑的好处就是省事,干脆利落。然而我们这个世界偏偏多事,就是我们人自己也不是省事的主儿疙里疙瘩,牵丝攀藤,吃着碗里看着盆里。因此省事恰恰省不了麻烦,天下总是不太平。譬如这个东西不是白的,你说那只能是黑的,这个东西不是香的,你说那只能是臭的。其实颜色在黑白之外无有穷尽,气味在香臭之间亦难以尽数。不要说无限复杂的世界不能揿入线性思维的印模一分为二,就是文艺现象又怎能简单二分呢?为了区别于泛滥书肆歌厅的大众读物和流行歌曲,称一些比较严肃的文艺作品为高雅也没有什么不妥,对此加以扶持更是功德无量。但是把文艺的样式或体裁本身判为高雅和通俗,则实在不足为训。殷鉴不远,“四人帮”把几乎所有传统的民族文艺形式都说成是低级下流的,结果拥有八亿人口的中国便只剩下芭蕾交响电影和京剧演的八个样板戏,可说创了世界文化艺术史之最。
二值逻辑的武断背谬,在专制时代人们无话可说,说也白说,说不定还会白搭上一条性命。朕即国家,一言定邦,一句顶一万句。但到了讲民主的开放社会,就断少不了人们七嘴八舌,议论蜂起。尤其当触及人们的切身利益时,人们定然要据理力争,辩个水落石出。大概也只有当人们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人们才会真切理会线性思维的弊端。西谚云:几何学如果危害人的利益,人也会抛弃它的。我们受线性思维之苦有日矣,何时才能真正抛弃它呢?
二
流行真是个奇怪的现象。一旦流行,什么都会点铁成金。一条裤子,不上褐边,毛穗错落的,膝盖处还割上三五个洞,就象是人家扔在垃圾桶里的货色,然而一流行到俊男倩女身上,却有媒体赞其自有潇洒的神彩;外衣露腹,内衫过膝,长袖没指飘摇,纤纤足下套一双又厚又笨的大头鞋,怎么搭配怎么不协调,可是一穿上街头女郎们的玉体,即有媒体夸其大有撩人的风韵。九十年代流行张爱玲,这个身前寂寞的女作家也就变得热闹诱人了,各种传媒竞相把各种赞词慷慨地堆在这位新偶象头上。
张爱玲有她的优秀处,作为都市生活写手,其对市民情态体察之微,至今国人还难出其右。圈点张爱玲的精彩,揣摩张爱玲的成功,以为今日市民生活描写的参照,当然是评坛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一流行,偶象身上的脚癣似乎也发出了灿烂的金光。如果说,有人把出身名宦之后的张爱玲所过的贵族有闲生活,视为这位女作家文化气度和诗意悟性的心理渊源,以和缺乏这种精神悠闲的今日作家相对照,多少还含有对当前文学界的悲悯之情。那么,把这位性情怪僻、人格多少有点变态的女性的有些乖谬言说,也奉为不刊之论,就不免有点捧明流的大脚丫了。
例如,张爱玲对母爱就很有点她个人的想法。她认为母爱“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既然母爱是一种源于动物祖先的最一般的情感,那么它应该是建立在超乎男女之别的基础上的,但张爱玲又自相矛盾地将它归之为男性自私的产物:“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张爱玲对母爱的排击,貌似激进,实际上是《圣经》中妇女以生育痛苦作为惩罚的陈腐教理,和没落贵族女子的自我中心阴暗心理结合的产物。把母爱从女人剥离开来的女人是什么女人,这且不论,男人尊敬母爱的感情,决不是因为这种感情是来自女人,如果它来自男人(如父爱),人们也同样尊敬。母爱是施于所有子女甚而延及他人子女的一种广博的感情,并不只限于男性后裔。这是迄今为止的两性不平等社会里保留的最合乎人性的珍贵感情,如果有一天真正能够实现两性的完全的平等,人们真正健康的感情可能也是以母爱为生长点发展起来的。对这种感情的尊崇,从来不以性别为界。对母爱的排斥,如果不是出于个案中童年精神创伤的遗留,便是神经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这是在动物试验中都可以观察到的规律。当然,作家都是从个人的独特角度去感知世界的,张爱玲的身世遭际使她产生这样的观点,虽然不幸,我们也难以对她多所指斥。
可是在有些评论者的笔下,这些更多带着个人经验色彩的言说,却被捧到了深刻揭露男性阴谋的理论辉煌高度。如说母爱是男性虚构出来的神话,将母爱神圣化意在欺骗妇女,让她们满足男性为她们规定的身份角色,放弃女性本位价值的追寻,说张爱玲则看穿了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制造的这一阴谋,并为她没有找到女性本位价值在何方而深感遗憾……在这些评论者的漆刷下,张爱玲被涂上了女权主义的绚烂油彩。我们知道,西方女权主义者是从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思维开始她们的猛烈批判的,因为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妇女总是不平等地被置于低级的否定的地位。这种批判有很多精彩深刻的地方。但有些女权主义在反对父权制二元对立的权力话语时,极力强调女性的本质差异,实际上如德里达所指出的是重新捡起了她们所反对的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只是把对立的男女双方位子对调而已,所以也是一种使用压迫权力的机制。因此另一些女权主义者竭力要消解这种对立结构,用多元化的完全的差异来取代为等级制的二分法所束缚的“男/女”性别差异。
国人由于对二分法的癖好,一直对二元对立结构情有独钟,所以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世界象小葱拌豆腐一样,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引进的女权主义也多为前一种。现在阶级斗争不讲了,人们便用“男/女”二元对立来取代“敌/我”、“资/无”等二元对立,倒也阵线分明,省了许多脑筋。 只是把帐笼而统之完全算在男性头上,有的时候反而把真正的元凶模糊掉了。所以有的当权者对别的主义都很苛严,对这样的主义却乐得装聋作哑。西方有些女权主义者已经醒悟到这一点,说句不恭的玩笑话,东方女子太纤弱,不象她们西方人高马大的同道为所欲为,使她们不敢对压迫权力机制中真正损害她们利益的那些东西挑战,而是满足于用二元对立模式糟践自己的美好感情来获得向男性报复的快感而已。
三
记得有个哲人曾经说过,人类与其说是在成功中发展,不如说是在失败中进步。通过对挫折和失误的反思,人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孔夫子这样的大圣人也教导我们要“吾日三省吾身”。但反思是检讨自己的过去,拣出所犯的错误,挖掘错误的根源;而不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历史,把自己好的东西也一锅端到污水潭里。伟大的五四运动留给后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它在掀翻中国旧的文化体制时,用西方思想对中国自己的传统作了完全的否定。中国什么都不行,连医学和文学都不如人家,因此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文化应该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全部的拒绝。五四先驱的激进做法,割断了我们民族的“根”,给后来的历史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星转斗移,在五四精神导引下的二十世纪走到了它的尾声,我们理应对此作一世纪性的回顾和反省。
五四运动是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面大旗,去冲决封建思想罗网的。但五四以后一个自由民主的新社会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产生,相反,专制主义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把中国拖入越来越浓重的黑暗之中。这确实是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对科学和民主慷慨赴死的努力,赢得的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愚昧和钳制?这一世纪之问,应该由全体国民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军事心理宗教等所有领域作出全方位的思考,并且还应该不仅仅停留在思考的层面。对这样的大问题,作一种大而化之的、仅从某一个方面就企图为整个社会开出全面的最终药方的想法,是根本不切实际的,也是于事无补的。
然而人们往往喜欢大而化之。可能是因为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研究很费力,现代社会的人也很少有可能精通一两个以上领域的知识,特别是有的领域根本就不允许知识分子过问他的闲事。九十年代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上腐败盛行。有人既不从政治经济法律等体制上研究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不看看国外是怎样防止官员贪贿败行的,远远一望,就断然下结论说:腐败是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伴生的现象。王元化先生已经指出这种研究作风的鄙陋。这也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思考方式,它给我们人民带来什么结果呢?既然是必然的,那我们就忍受做官的鱼肉百姓吧!五四以后中国社会没有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原因是极为复杂的,而且相当主要的原因还在政治本身。这也不是五四以后才出现的问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人士学西方的技术没能改变国家的落后,学人家的制度也没能自新中国的面貌,遂导致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幻想“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整休观思想模式(林毓生)。今天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层面还是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软弱无力,所擅长的无非一枝笔几张纸。纸上得来终觉浅,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对此读书人应当抱一种清醒的自觉,以保持研究可以向未涉领域进一步探进的开放性和张力。可是本应反省五四前辈整体观思想模式的吾辈,常常也抱着整体观思想模式不放,经常只从自己所擅长的知识文化领域就给五四开出了一张无病不治的大药方。这一次是和国际同步接轨的最新的后殖民主义千金方。
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出当今世界在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传递中,发达国家和其他地区存在着不平等现象,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把落后地区向先进文化学习,一概视为帝国主义的精神侵略和文化殖民,就有违人类健全的理性了。精神侵略和文化殖民是存在的,对此提高警惕加以防范也是需要的。可是不加区别地把学习发达国家文化,都看作丧失“自我”、自居“他者”,是“殖民化”,统统予以否定,这实际上是一种愚昧的文化自闭主义。它和当今世界文化大交流的历史趋势相逆,也跟人类择善而从以求发展的愿望相背,只会给落后地区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起到帮忙的作用。五四一辈知识分子由于对中国痼疾的愤激,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是有全盘西化的极端性,这是我们今天要予以梳理的。但是有人搬来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给学习西方套上一顶“殖民化”的帽子,把其中合理的东西也作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毒果,然后以后殖民主义的名义统统判处死刑。
这真叫人不知说什么才好。西方确实不是什么都好,就连科学和民主也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的。西方科学用我们发明的火药制造枪炮杀人。可他们也制造炸药用来开采矿山,这总比我们用火药做炮竹驱鬼强。西方民主造成“多数的暴政”,使社会时有混乱。可民主也让人人有决定自己生活的自由,这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强。民主固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但民主是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在没有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以前,一个国家从独裁走向民主,是最可庆贺的进步。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拥护这种进步的,鲁迅时代就有人反对死刑用枪决、法庭审案不打屁股。但是这种原产西方的制度毕竟在中国落了脚,就是反对者自己如果犯了案,大概也是不希望屁股挨板子、服刑割脑袋的。如果这一切都不能学,中国人直到今天还见官下跪、娶几房小老婆,算是保住了文化的“自我”,没有沦落到文化的“边缘”,这样的文化本位岂不是太可悲了吗?
五四要民主要科学,但没要来民主科学的现代中国,这是中国的悲哀。可是这责任不能让民主科学来负,就象许多烈士为创造一个现代中国而杀身成仁,但未果,你不能要烈士为此负责一样。不去寻找真正应该为此负责的原因,潇潇洒洒地站在后殖民主义的远处,挥鞭遥遥一指,将民主科学等西方思想定为“殖民化”而加以嘘弄,这对充满太多创痛的中华近代史来说是一种轻佻,对舍身求仁以使中国立于世界之列的五四先辈是一种不公,对于戕害科学扼杀民主的真正历史罪主,更是表现出了文人难以原谅的怯懦。
从思想方式上说,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密执安大学教授安·麦克林托克在《进步之天使:“后殖民主义”的迷误》中非常深刻地指出:
假如“后殖民”理论试图靠召唤其“二元纵队”(自我—他者,都市—殖民地,中心—边缘,等等)来迎战西方历史主义的大进军,“后殖民”这个语词却把世界绕单一的二元对立关系重新定位:殖民—后殖民,它的理论基点因而从二元轴心的时间,而时间作为轴心的政治意义则更为反动,因为它不区分殖民主义的受惠者(前殖民者)和牺牲品(前被殖民者)。
而后殖民主义在理论上的更大危险,是它把多态的历史存在形态和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关系用时间约简化了,使它成为围绕时间(而且是欧洲时间)单元的单一化的历史;这种单一化的历史无益于思想和政治的研究,因为它以范畴的抽象消抹掉了政治上的全部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