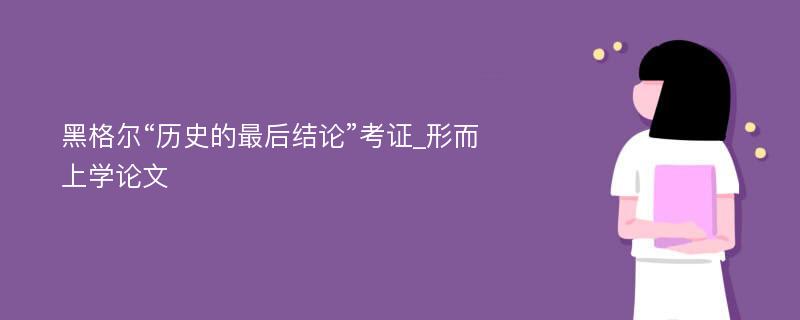
黑格尔“历史终结论”考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有其起点,又有比较确定的行程;自由是世界历史的目的,这个目的的另一个名称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但这些说法只是一个大的原则。对于历史终点的问题,黑格尔原本就交待得不够清楚,加上《历史哲学》各版本差异较大,没有一个经过黑格尔亲自审订的版本;历来的学者又聚讼不已,使得讨论这个问题变得困难重重。本文打算区分“历史终结论”的各种含义并逐层讨论,确定黑格尔究竟在哪个层面上认为历史终结了(如果有的话)。
在经验层面上,黑格尔从不认为具体事件的发生终止了,否则他怎么还会说美洲是“未来之地”(Hegel,1996,S.94.下引黑格尔外文文献仅注年份和页码)呢?因此这一层面无需多言。那么,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黑格尔是否认为历史终结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呢?
《历史哲学》将从东方、希腊、罗马到日耳曼的四个世界分别对应于专制、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四种政制形式,以君主制为最高的形态。(ibid,S.355)西方是以绝对精神自我回归的形式存在的,“终结”是西方的本质规定,而《历史哲学》对诸民族的考察也终止于普鲁士。从这种种迹象来看,人们极容易推出上述“历史终结于普鲁士”的结论。然而这种做法似乎对以下两个问题缺乏考虑:(a)当时的普鲁士是否符合黑格尔心目中的理想君主制的形象?(b)即便普鲁士是理想的君主制国家,它就一定能保证绝对精神在其中达到了完满的自我认识吗?
拿破仑之后,欧洲掀起了一股复辟的风潮,正如法切尔所言:“自拿破仑的统治终结以来,在欧洲政治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动因登场了”,这在客观上为黑格尔进行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总结”提供了可能,使得他能以此来把握历史运动的整体。(Fetscher,S.227)黑格尔开始将目光投向普鲁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成老朽,看不到法切尔所说的“由法国革命所触发的,持续振荡世界的骚动”;恰恰相反,他将普鲁士走向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uesse)、最终走向他去世后威廉二世治下的新封建主义的趋势称作德国政制的“败坏”(Verderben)(S.-Weithofer,S.165),甚至还隐隐约约看到了无产阶级问题,亦即工人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由外在力量规定的劳动分工和商品分配这一状况。(ibid)黑格尔关注普鲁士,更不意味着黑格尔仅仅停留于“保守还是革命”这种二者择一的政治运动层面,他还有更深的考虑。
黑格尔在政治上所向往的对象几经变迁。他之所以选择接掌费希特留下来的教席,的确与他将理想政制的希望寄托于普鲁士有关。但只要看看当时的状况,就不难理解黑格尔的态度了。黑格尔青年时期的《论德国政制》一文就对德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多有不满。在《法哲学原理》中,他更是直接指出,德国的公共法权还一直是基于“封建体系”上的,这样的公共法权“通过官位的继承”成了“私产”(Brauer,S.37-38),所以黑格尔怎么可能把这样的国家作为“历史的终结”呢?正如鲍威尔所说,黑格尔并不认为政治史达到了终点,因为理想的国家还没有实现。(ibid,S.383)薛华先生在详细地考证过《历史哲学》原文后得出的结论是,至今无法找到黑格尔直接断言普鲁士当时已是历史发展之顶点的材料。(薛华,第22、55、60、91页)
黑格尔说过,不能抽象地比较各种政制,只有世界历史的行程才是政制的批准者。(1995,S.181)这也反过来证明,黑格尔看重的并不是关于政制的那些抽象规定,而是它背后所体现的某种更大的力量。“当黑格尔称赞普鲁士政制为一种相对较好的国家政制的典范时,谈的其实是那个经过改良的、或许部分被理想化了的普鲁士。”(S.-Weithofer,S.165)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很少将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现实的某种政制形态和他所看重的政制形态背后的力量这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福山(F.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和末人》一书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但这部书失之浅薄。珀格勒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差不多同名的小册子,反驳福山将“历史”概念从包括宗教、艺术等方方面面丰富的人类生活整体运动,狭窄化为只包括单纯的市民社会(Poeggeler,1995),并将福山引以为傲的关于历史背后的动力——对承认的欲求的说法,上溯到科耶夫、施密特、施特劳斯等人的争论中去,直接驳斥科耶夫对黑格尔“承认”概念的解读。他说,黑格尔那里的“承认”不光是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承认,更重要的是指个人进入一个超出这个人和那个人的整体,就像工匠们加入一个协会,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其他那些具体的会员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想通过他们的承认,在一个整体中得到归属感一样,因为这个整体可以克服单个人的孤独。也就是说,承认是突破(个体式)主体主义的关键一步。像科耶夫那样置黑格尔的这一伦理与思辨含义于不顾,用来构建人种发生学和历史终结说,他笔下的黑格尔已经不再是真正的黑格尔了。(ibid,S.24-25)
珀格勒对科耶夫的批评可谓直击要害。承认自始就至少是一个主体间性的概念;而主体间性在黑格尔那里也不能抽象地被看待,它本身还是以民族、国家这些伦理共同体为预设的;而伦理共同体要达到其真理,则又要回到更深的预设——绝对精神。这意味着,即便某个国家达到了黑格尔的理想国家标准,它也不会仅仅因为具有这种理想的政制形式,而使得世界历史终结于它。
那么,世界历史作为包括政治、经济、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整体,不管处于其行程的哪个阶段,是否都含有未来向度呢?它是否在某个时间点上便穷尽了其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之后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重复以往的活动亦即回忆了?这个问题将我们从政治哲学的层面引向了存在论的层面。
在第三个层面上,我们才算开始接触到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真义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只有一处明确提到了“历史的终结”:“世界历史从东方走向西方;因为欧洲根本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亚洲则是开端。”(1917,S.243)这里说的意思并非是历史有一种对东方、西方都保持漠不相关的、自成一统的开端和终结,像一条线段,碰巧拿东方(或东方的某个时间点)来作为线段的起点,拿西方(或西方的某个时间点)作为终点。这里说的不是具体的时间或空间,而是对两种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的规定。就是说,西方本身就是以终结的方式存在的,西方人就是以绝对精神自我回归这种方式来生活的,而东方人则只是以开端的、近乎于自然界的方式在生活。另外要注意的是,不论终结是否又蕴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里的“das Ende”都兼有“终结”和“目的”两种意思;黑格尔在单独强调“目的”义而不谈“终结”义时,则往往只用“der Zweck”,不用“das Ende”或“der Endzweck”。鉴此,关于前一层面的讨论末尾提出的两个问题,笔者的回答是:黑格尔从未断言过有一个从它开始只剩下回忆的时间点。在他看来,在世界历史的每一瞬间都有未来向度,但与此同时,每一瞬间都可能是一次终结,因为每一瞬间都可能是绝对精神回到自身的一次努力,尽管在这些终结与终结之间存在着一定限度内的质的差别。理解了这一点,才算是抓住了黑格尔历史观的精髓,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艺术终结论”、“上帝死亡论”以及世间万物所具有的历史性。
但在深入这一思想之前,我们必须先将它与犹太传统下的末世论区分开来,否则很难避免对黑格尔的末世论解读。这种解读不仅将黑格尔那里的和解推到了未来,更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彻底误解,因为黑格尔强调的是中点,是当前的绝对精神,而不是超越于当前的某个未来的终点。当前固然含有对未来的预期,但那只是当前衍生出去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当前的根据;在根本点上,黑格尔坚持的是希腊的逻各斯,而不是绝对超越的只通过其声音与面容和摩西一人交流的耶和华。当然,只是在与末世论对照之下,黑格尔的逻各斯和古代逻各斯的亲缘关系才显现出来。
区分末世论与黑格尔历史观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主张历史会终结,也不在于历史是终结于当下还是未来;而在于意义是内在的(即由过去传承到当前的整体运动当下地生成的)还是外来的。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末世论阐释者们当然了解黑格尔的“精神是绝对当前的”这一说,因此他们往往不会将典型的犹太末世论模式硬搬到黑格尔身上,说历史终结于未来的、人永远不会真正达到的上帝,而是采取一种变通的形式,说黑格尔认为,在理论上历史已经终结于自己的哲学了,因为在这一哲学之后再不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历史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它说尽了;然而在实践上现实的政制还不够完满,还有待完善化,在未来会有类似“普遍同质社会”一类的状态,赋予当前的努力以意义。
不管犹太传统还是希腊传统,都不是只讲时间的某一维;在两种传统中时间都是三维的。关键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历史中的意义何来的问题,而强调时间的哪一维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表现形式。
以上两段延展开去讨论起源问题,是为了给当下的讨论提供一个背景,以便为末世论在西方的影响进行一个初步的定位,为下面的比较提供方便。在黑格尔那里,当前是时间三维的统一和真理。这就是说,在时间的任何一个瞬间,通过思想,时间都有可能达到以下这种自我认识:时间的三维并不是外在地并列在一起的,而是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向前运动,将三维统一起来;这种力量本身在性质上不同于三维中的任何一维,却是赋予三维以意义者。过去是与上一瞬间的联系,是在变为僵死之物的同时又获得新生的过程;现在就是由过去生出、同时又导向未来的永不停息的自我否定活动,它本身没有坚固的存在;未来则从过去与现在的共同作用中生出,它不是单单由现在凭空生出的,它是对下一瞬间的预期。当前不同于现在,它是指三维作为整体,当下生成意义,是时间通往永恒的连接点。而永恒不是别的,正是这整体得以凝聚成为整体的力量本身,它是整体内部自有的,是整体的核心与本质,而不是外在于整体的。当前并不是在静态地将时间看作一条线的情况下,将这条线从任何一处任意截断所形成的节点,它除了是这种运动自身外,并不具有任何实物性的存在。这样看来,每一瞬间在其可能成为绝对精神自身的回返的意义上,都是一次终结,也都是历史的中点,(Kayser,S.82-83)因为它既有过去,也有未来。毛勒说得更彻底,他是这样解读黑格尔的“历史的中点”一说的:每个个体的每个生的瞬间或死的瞬间之中的一种可得到实现的当前。(Maurer,S.177)
这决定了黑格尔的哲学既不是本原论(Archaeologie)(该词现通译为“考古学”,本文取其原始意义),也不是末世论。(Kayser,S.82-83)
黑格尔明确地说:“真的东西,永远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它不在昨天,也不在明天,而是绝对在当前”。(1955,S.182)“哲学的世界历史,其普遍的观点(Gesichtspunkt)并不是抽象普遍的,而是具体的和绝对当前的(gegenwaertig);因为正是精神,是永远在自身这里的(ewig bei sich selber ist),对于它而言,没有任何过去”。(ibid,S.22)绝对精神永远是从自身出发,在当前就从作为运动整体的自身获取意义的;这个运动整体是从过去来的,并走向未来。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过去”,指的并不是绝对精神处处和过去斩断关系,只剩当前,而是说,即便和过去发生关系,也是立足于当前而发生关系的,通过这种关系,每一瞬间都将过去扬弃于当前的意义发生之中。这样,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他的另外一句话了:“当我们穿越(durchlaufen)过去,如其总还是那般伟大地存在一般(看待它),我们处理的只是当前之物(Gegenwaertigem)”。(1995,S.183)这里的“当前”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充分地投入绝对精神自我回返的运动之中),比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就说过,在哲学史研究中,“我们不用与过去打交道,而是与思,与我们自己的精神”(打交道)(1940,S.133)。我们不难看出,黑格尔的想法并不是“古为今用”,以一种实用的态度利用过去的材料,以便得出一些教训,更不是一味沉溺于古物。
关于世界历史的当前与过去、未来的关系,尤其是与未来的关系,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重申,因为这涉及如何证明“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既是立足于每个当前的,也是并非没有未来的”。黑格尔在《小逻辑》里说过:“哲学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通过我们的反思所提出的看法,已经是人人具有的直接信念”。(黑格尔,第67页)这就是说,哲学思考的始终是绝对精神本身,这一点从过去到当前没有任何改变,而且当前的思考有过去传承下来的因素在。世界历史的当前与过去的关系同样如此。那么与未来的关系呢?黑格尔一向认为,预测不是哲学的事情。(Jaeschke,S.303)珀格勒曾说,黑格尔不足以成为我们考察未来的开端,他所做的工作只是面向过去,进行总结。(Poeggeler,1999,S.28)但我们不必被这种说法吓倒,珀格勒说的只是现实工作的层面,并没有讲存在论层面的当前不含有对未来的预期。这种预期是有的,黑格尔在谈到时代精神的时候曾说,精神的活动一般有三个步骤:建立世界;抛弃活动,丧失兴趣,进入老年;自己准备自己的衰落,这种衰落同时也会产生一种新的生命。(1996,S.46,48)这是从民族与时代这些大的角度而言的;从小的角度来看,也有对未来的期待,而所期待者并非某种完全超越性的事物,而是过去与当前共同作用构成的运动整体自身的某种可能性:“通过对当时的进展进行重构与评价,历史事实上创造出对某些行动可能性的期待,并且事实上正如黑格尔所表述的,产生了当前‘与’过去之‘否定之物’的一种‘和解’(Versoehnung)”。(Hueffer,S.128-129)
这只是“期待”的一般性含义,对世界历史的一切阶段都适用。在黑格尔这里,“期待”——以及相应地,“和解”——还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即上帝道成肉身之后,上帝与世界的和解虽然直接存在,却还没有现实地存在,即在现实的政制与生活中达到和解。虽然黑格尔在后期谈到法国大革命时,仍然为大革命的景象所鼓舞,说那时精神的热情震动世界,仿佛神与世界的现实的和解已经开始来临了(1976,S.926),但他那样说只是因为大革命表面显得如此而已;而实际上,即便在出现黑格尔哲学之后,也只是在理论上达到了和解,在实践上仍然没有达到,因为普鲁士仍然不是理想国家。用托因尼森的话来说就是,观念性的和解就在当前,实在的和解尚待完成。(Theunissen,S.438)这就需要一种基督教所特有的期待。在讨论这后一种含义的“期待”和“和解”时,黑格尔常常并不明确地将它们与第一种含义区分开来。其中的原因表面看来好像是《历史哲学》文本不严密,实际上是因为这两种含义根本是一致的,无法彻底区分开来。上帝道成肉身只是给了绝对精神进行自我认识一个契机。在黑格尔那里,这个契机和艺术的契机、哲学的契机相比,并没有绝对至高的地位:它们同属于一个世界历史行程,都可归于前一种意义的“和解”之下。
有了以上对犹太末世论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当前”概念的梳理,再考察这一历史哲学是不是末世论,就不难了:末世论追求的是终结和通过历史摆脱现实性,而黑格尔则追求中点和通过历史实现与展开现实性。(Jaeschke,S.33)可以说末世论的盼望和黑格尔的和解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ibid,S.305),因为它们的根本前提就不一样。
以上只谈了黑格尔本人的观点,实际上后人往往将黑格尔哲学在哲学史上扮演的角色和他的历史终结论混起来谈,这就迫使我们必须从存在史的角度谈谈黑格尔哲学本身与历史终结问题的关系。
前面说过,黑格尔将世界历史当作绝对精神追求自我认识的过程,而绝对精神最高的三种形式是艺术、宗教和哲学,哲学又是这三种形式中最适合体现真理的,其他两种则已属于过去。黑格尔似乎认为其哲学体系至少在原则上——因为在体系的具体细节方面,黑格尔一向允许自己和后人进行改进——已经达到了绝对精神最高的自我认识。那么,黑格尔究竟是否这样认为呢?而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又是否可以说“历史终结于黑格尔的体系了”?黑格尔的体系是否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为未来新的历史时期提供了可能性?
就在自己几乎名满天下,有人开始吹捧他的哲学达到了对绝对者的概念性把握的时候,黑格尔表示推辞,或者准确地说,他将这项名誉普遍化,赋予所有哲学了。在1819年夏季的一封信中,黑格尔写道:“谈到另一个问题,即(在人们当中)产生了一种想法(即绝对者在我的哲学中才从概念上得到了把握),关于它有许多话要说;但简单一点说就是,(人们)谈论这样的哲学时,所谈的不是我的哲学,但一般而言,每一种哲学都是对绝对者的概念性把握——同时也不是对一种外来者的概念性把握,而且,对绝对者的概念性把握因此当然就是绝对者对其自身的一种概念性把握”。(1953,S.215-216)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也说过,虽然哲学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最高点,但无人能宣称达到了最高点。(1940,S.129)他自己的哲学当然也不能例外,至少从黑格尔本人的观点来看是如此。他一向允许对自身哲学的不断改进,他在死前还在修改《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
尽管如此,我们若从黑格尔本人的自我评价跳出来,站在当代的一个研究者的立场,就仍然可以认为黑格尔的体系达到了某个顶峰,仍然可以考察历史是否终结于他的体系这个问题。
黑格尔的哲学是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这已是学界不争的事实。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它代表了形而上学的终结。笔者以为,它也代表了形而上学时代的终结,当然这里所谓的“终结”不是指时间静止了,没有事情发生了,而是指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再也不会有新的可能性出现了。在它之后,哲学细节方面的修补并不能扭转这一终结。但它并不代表一般时代的终结,亦即不能阻止一种非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出现。布劳尔的话很好地表达了这个意思:“黑格尔的哲学并不处在一般时代(der Zeit)的终结处,然而却处在一个时代(einer Zeit)的终结处,虽然如此,它也是作为对一个世界的意识(而存在的),这个世界走向衰落,而且在意识到了衰落的情况下,准备了新时代的原则”。(Brauer,S.192)
如果说在黑格尔描述下的世界能准备新时代的原则,那么他的哲学能准备这样的原则吗?
黑格尔认为过去时代的哲学都能准备这样的原则,这与《逻辑学》中一个阶段蕴含着产生下一个阶段的动力的情形是一致的。黑格尔说,哲学产生于时代的分裂之中,其任务在于在旧时代的衰落中认出新时代的精神(ibid,S.180-181),但相对于新时代而言,哲学往往又来得太早,因此它总是以抽象的、尚未发展的形式出现的(ibid,S.187)。
但这一切都不代表黑格尔的哲学能为后代准备原则,因为它本身是整个形而上学的终结,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中间阶段,这决定了他的哲学与中间阶段的那些哲学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也决定了他的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开端形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可能有着比那些哲学更深的交流。他之后的时代,倘若不满足于对他的体系进行修修补补,就必须从突破形而上学本身起步。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虽不能为一种反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指示方向,但它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为后者提供养料呢?这需要另作专文讨论。
总之,在经验层面和政治哲学层面上,黑格尔都不认为历史终结了;在存在论层面上,黑格尔认为自己的时代与以前的西方历史的每个阶段,作为绝对精神向自身的回返,都在同等的程度上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黑格尔从未有过“历史的唯一终结者”的自傲;在存在史层面上,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代表了形而上学时代的终结,但并不代表一般时代的终结。另外,黑格尔并不阻止后人对他的体系进行细节上的改进。更重要的是,他并未断言他之后的时代无新事,并未阻止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到来;但与此同时,他也并未明确规划这个时代,他的任务主要是对过去进行总结。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看重的不是个体、某个民族、某个国家、超越之神,而是使这一切——包括“超越之神”这一观念——具有意义或得到可能的历史本身;或者更深入一点说,是历史之中的逻各斯。而且从纵向时间意义上来看,他更看重的是总结过去;对于未来他选择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智上的诚实与开放的姿态。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绝对精神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终结论文; 历史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