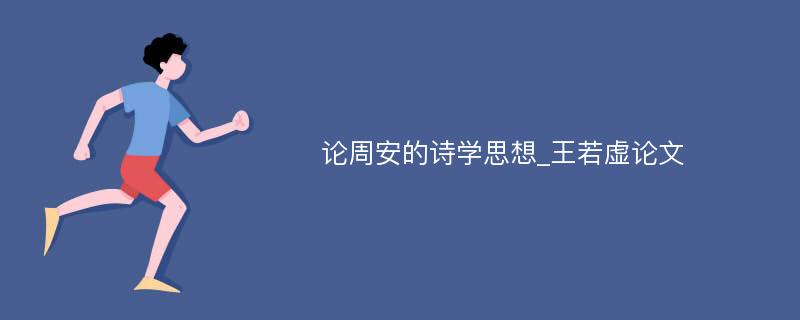
论周昂的诗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思想论文,论周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昂主要活动于金代世宗大定、章宗明昌时期,是金源诗坛上有自觉的诗学意识、存留作品较多的诗人,诗学思想颇为丰富。周昂的论诗之语基本上保存在他的外甥、金代著名诗论家王若虚的诗论著作《滹南诗话》之中,并通过这部诗话的流传对金代及后来的诗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他的创造中也有一些论诗之作,颇有精辟之见。
周昂(?—1211)(注:关于周昂的生年,诸本均作不详,然可根据其进士及第的时间大致推算而出。元好问《中州集》卷四周昂小传中记载:“大定禄第进士,仕至同知沁南军节度使事。德卿年二十一擢第。”查《金史·选举志》载:“大定四年,敕宰臣,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世宗在大定初年只有这次进士录取的敕命。可知大定初年进士开科是在大定四年(1164)左右。以周昂二十岁进士及第可推知其生年大致应在1144年(即海陵王皇统四年)前后。),字德卿,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他21岁中进士,时为大定初年。历任南和簿、良乡令、监察御史等职。后因路铎被贬,周昂“送以诗,语涉谤讪,坐停铨,”(注:路铎(?—1214),字宜叔,金代中期诗人。明昌三年,为左三部司正,迁右拾遗,以正直敢言著称。承安二年(1197)授翰林修撰。因弹劾宰相胥持国而被贬,出为景州刺史。周昂在此时作《送路铎外补》诗,坐讥讽而遭贬。)谪东海上十余年。“久之,起为隆州都军,以边功复召为三司官”(注:《中州集》卷四。)。他不愿出佐三司,自请从宗室完颜承裕军。大安三年(1211)承裕军被蒙古军击溃,周昂与其侄周嗣明同死于难。
周昂在当时文坛上声誉甚隆,“昂孝友,喜名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注:《金史·艺文志》下。)。他创作颇丰,当时著有《常山集》,丧乱之中散佚颇多,然王若虚尚能记住300 余首,《中州集》录其100首整。周昂是《中州集》里存诗最多的诗人。
周昂有明确的诗歌创作观,首先是“以意为主”,他与王若虚论诗时说:“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注: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上。)这是周昂诗学观念的基点。所谓“文章”,这里主要是指诗。这与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答庄充书》中的说法十分相似,都强调在诗歌创作中“意”为根本、为主导,而语言表现应该服从于“意”。其实,“以意为主”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一个久已有之的优秀传统,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范晔在《狱中与诸熏甥侄书》中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但在杜牧和周昂之前,这个命题尚不固定,也未能就作品的立意与文辞表现的关系作出这样深入准确的阐析。周昂以“主”与“役”的关系为喻,说明“意”与“字语”的关系,指出“意”如能起到统帅“字语”的主导作用,就会“无使不从”,达到一种充沛和谐的境界。又指出文坛之弊往往在于“骄其所役”,专力于文辞修饰,不问其是否能恰当地表现作者之“意”,乃至于“反役其主”,也就是倒过来削足适履地让“意”适应文辞的修饰。这里突出地强调了内容对艺术形式的决定性作用,侧重点是在“意”上,这在当时是有为而发的。
大定、明昌时期是金源文化最为繁荣兴盛的高峰期。世宗偃武修文,提倡文治,重视典章礼乐方面的建设,同时也相当看重文学艺术等审美文化。时常命群臣赋诗,引起社会上对诗赋创作的普遍重视。其后的章宗在崇尚文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进一步完善典章礼乐、科举取士,使金源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对诗赋艺术等审美文化,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而且,章宗特别喜爱文辞华美的篇什,他本人便“博学能诗”(注:《金史·章宗纪》。),有数首作品传世,其诗即以文辞优美典丽著称。章宗对有“文采学问”的臣下十分欣赏奖拔。金人刘祁评价章宗朝政治时说:“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然学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注:刘祁:《归潜志》卷十二。)指出了章宗对于诗赋美文的高度重视,同时也看到了章宗对文采辞华过分强调带来的弊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章宗朝形成了一种尖新浮艳的诗文创作风气。“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注:刘祁:《归潜志》卷八。),“尖新”的体现,便是对辞采的过分追求以及对“意”的忽略。这在南渡以后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扭转。而周昂在明昌时期即提出“文章以意为主”,其实所针对的正是这种“尖新”的创作风气。
从“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念出发,周昂提出了“就拙为巧”的创作思想:“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巧者,乃能就拙为巧。所谓游戏者,一文一质,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注: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上。)在中国古代诗学中,“巧”与“拙”是一对相对的审美范畴,它们既互相对立,又可以互化、互融、互补。这对范畴的源头在老庄哲学,这种带有辩证法因素的思维,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巧”、“拙”范畴用之于诗学理论,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中国诗学追求“巧”与“拙”的互补,以期达到一种看似朴拙、实则高深的艺术境界。北宋诗人陈师道论诗提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注:《后山诗话》,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拙”与“朴”是相同的,“巧”与“华”则是相同的。陈师道偏执于朴拙,缺少巧拙相济的辩证精神。他的诗风也正体现出这种倾向。后山诗过于追求语言的质朴无华,从而产生了许多形象枯窘、缺少风神的作品,大大削弱了诗歌的审美功能。黄庭坚关于“巧”、“拙”关系的看法,比陈后山显得更为圆融。他说:“宁律不谐,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手括者,辄痛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注:黄庭坚:《题意可诗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山谷论“巧”“拙”,期于“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然就山谷本人的创作来看,仍不免他所讥讽的“然有意于为诗”。南宋初年的诗论家叶梦得认为诗歌创造的理想境界应该是“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他指出:“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著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风受燕斜之语。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若无‘穿’字,‘款款’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注:叶梦得:《石林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通过对杜诗的举例分析,倡言一种藏工巧于天然的诗境。周昂则以十分明快的语言对有关“巧”“拙”关系的诗论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提出了“巧拙相济”、“就拙为巧”的诗学命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以巧为巧”,这第一个“巧”,是指精巧的艺术手法,第二个“巧”,则是指所欲达到的高妙的审美境界,周昂认为靠精工巧丽的艺术手法,想要达到浑然高妙的艺术境界,是很难奏效的。理想的办法,便是“巧拙相济”、“就拙为巧”,是说真正的诗人善于在看似简古平易的风貌中创造出浑然高妙的艺术境界。“一文一质,道之中也”是借“文质”的概念来说明巧拙的辩证关系的。周昂又认为,过于细微地进行雕琢,过于惨淡经营,反倒会有伤于作品的浑全之气;正确的艺术法门,还有“就拙为巧”、“巧拙相济”,方能产生余韵无穷、令人不厌的审美效应。周昂关于“巧拙”问题的阐述,是在以前的有关论述基础上的升华,更具有概括性,使“巧”“拙”这对诗学范畴得到进一步的提炼,更具有了辩证思维的质素了。
关于“巧”与“拙”,周昂另一条诗论也颇值得玩味:“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注: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上。)这里批评的是那种文采工丽而缺少内涵、貌似惊人却并无个性的作品,这种诗可以哗众取宠,却耐不得“独坐”吟咏,经不住推敲,没有可供品茗的余味;可以得到人们的表面赞赏,却难以得到人们的内心肯定,这种诗缺少独特的艺术个性,缺少诗人的自我。这里其实从反面表述了周昂的诗学价值观,他认为好的诗作应该是能够“适独坐”、获“首肯”的,也就是具有深隽的余韵、独特的个性,而用不着“惊四筵”、“取口称”。这种反对哗众取宠的诗论,恐怕是针对当时逐渐兴起的浮艳诗风的。
周昂在前代诗人中最为推崇杜甫,这本来是与宋代诗学的主导趋势是一致的。杜甫在宋代诗人中所受到的尊崇无出其右,杜诗在宋代成为一代诗歌的审美范式。
对杜诗艺术的规摹推崇,无疑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最为有力。黄庭坚喜欢杜诗的一条重要理由便是因其“句律精深”(注:《潘子真诗话》,见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山谷有两句名诗谓:“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注:《跋高子勉诗话》,《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见出他对杜诗最为注意的是“句中有眼”这一类诗歌艺术手法问题。他还指导后学说:“请读老杜诗,精其句法。”(注:《与孙克秀才》,见《山谷老人刀笔》。)当然,山谷论诗,也还有推崇杜甫“无意为文”即浑成自然的一面,与其对诗法的重视构成其诗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顾易生先生曾指出:“黄庭坚论创作,非常重视法度的谨严,注意篇章结构的惨淡经营,字句的精意锻炼,然而他有其更高的要求,即达到自然浑成,即自由地合于规律、平淡而意境深远的境界。”(注: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页。)这个评价,是较全面而深刻的。 而周昂对老杜的推崇与江西派黄、陈诸人的角度是不一致的,他明确反对黄、陈等江西派诗人的学杜路数,也很少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评价杜甫,而更为心仪的是杜诗中那种浑茫雄阔的境界,王若虚回忆道:“史舜元(史肃,金代诗人)作吾舅诗集序,以为有老杜句法,盖得之矣;而复云‘由山谷入’,则恐不然。吾舅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也。若虚乘间问之,则曰:‘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于少陵初无关涉,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也耳。’”(注: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上。)
周昂的诗集《常山集》今已不传,当日诗人史肃为其诗集所作之序,也就无由得见了。但从王若虚的转述,可以较清楚地看出周昂的态度。周昂一向不喜山谷诗风,认为他虽然以学杜相号召,且多有过人之处,但却与老杜诗风并不搭界。这里有王若虚的观点在其中,但又是深合周昂诗学思想的实际的。周昂的《读陈后山诗》可作为有力佐证:“子美神功接混茫,人间无路可升堂。一斑管内时时见,赚得陈郎两鬓苍。”(注:《中州集》卷四。)
这里通过陈师道的批评,表达了他自己对于杜甫诗境界的认识。陈师道作为江西诗派的第二号人物,一直是以杜甫为诗学旗帜的。在他看来,杜诗之可学,是因为杜诗法度井然,有门径可循。他曾这样说过:“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注:《后山诗话》,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后山认为在杜、韩、陶几位大诗人中,杜诗是最以人工见长,有规矩可以循蹈的;而如韩愈、陶渊明等诗人,则是无法以人力学之的。后山学杜,也主要是从句法、命意、用字等方面入手。应该说,后山对杜诗的理解与学习是很深入的,但仍是从一些局部问题入手进行仿效。他对杜诗的精研多在这种命意炼字等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把握杜诗的艺术精神。周昂对后山的学杜门径大不以为然,他认为黄、陈等人专在句法、用字、使事等方面来学习杜诗,充其量只能是“管中窥豹”,见其一斑而已。“混茫”乃是指宇宙大千,杜诗有“篇中接混茫”之句。周昂的意思是说,杜甫的诗,乃是宇宙之呼吸,时代之脉搏,诗人之心植根于社会时代,仅靠江西诗派的那些“诗法”“句眼”一类路径,是无法登上杜诗之堂的。同时,周昂也有这样的意思:杜诗有着整体上雄阔浑厚的境界,这种境界是由诗人的独特气质与博大襟怀生成的,非是靠一些局部技巧手法可致。
周昂还认为杜诗有十分深刻而独特的艺术个性,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混淆其面目的。他对于杜诗领会既深,对于那些掺入杜集中的伪作,辄能精识而出。王若虚记述道:“吾舅自幼为诗,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尝与予语及‘新添’之诗,则频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无几矣;然谛视之,未有不差殊焉。诗至少陵,他人岂得而乱之哉!’公之持论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顾我辈未之见耳。”(注: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上。)
周昂认为杜诗的艺术个性是十分特出的,这正是大诗人的标志,别人是难以乱真的。由此也可见出他那种精湛入微的审美鉴别力。周昂强调对于杜诗的学习要从其艺术风格上加以把握,领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所在。
周昂本人的诗歌创作沉雄苍劲,气象阔大,而在艺术上又不粗糙,造语遣词颇见炉锤功夫。他的五言律诗最得老杜风神,如《晓望》:“晓树云重隐,春城日半阴。苍茫尘土眼,恍惚岁时心。流落随南北,才华阅古今。紫荆生事窄,宁忆二疏金。”《秋夜》:“高阁钟初殷,层城月未光。净空含宇大,卧斗带星长,暗觉巢鸟动,清闻露菊香。谁家砧杵急,应怯暮天凉。”诗人以浓重的忧患意识感时应物,情与景高度融合,凝成苍茫浑融的意象,而诗律又颇为工稳。周昂的七言律诗较之五律尤为气骨苍劲,如《登绵山上方》:“环合青峰插剑长,小平如掌寄禅房。危栏半出云霄上,秘景尽收天地藏。野阔群山惊破碎,云低沧海认微茫。九华籍甚因人显,迥秀可怜天一方。”颈联两句,气象雄阔苍凉而寓意深刻。方志有云:“绵山在昌平州东十五里,或名宜山。元混一《方舆胜览》载有绵山寺,金真定周昂题诗其上,有云:‘野阔群山惊破碎,云低沧海认微茫。’亦警句也。”(注:《全金诗》卷二十七《茅城小志》。)可见此诗为人们所看重。周昂称杜诗“子美神功接微茫”,实际上,他自己的诗也颇得杜之神髓,有“接微茫”的气象。
周昂的诗学观点对于后世诗坛颇有影响,尤其是通过王若虚的传播,在南渡后的金源诗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周昂诗论中对杜诗的认识,对黄庭坚与江西派诗风的批评,在金代诗坛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与认同。在明清时期的诗学界,也有诗论家成为周昂的知音。清人赵执信曾说:“余读《金史·艺文志》,真定周昂德卿之言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为之主,以言语为之役。主强则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词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余不觉俯首至地。盖自明代迄今,无限巨公,都不曾有此论到胸次。嗟乎,又何尤焉!”(注:《谈龙录》。)对周昂的诗论评价甚高,并认为其超过了明代以来的许多诗论家,不难见出周昂的诗学思想在中国诗学史上是有着自己的声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