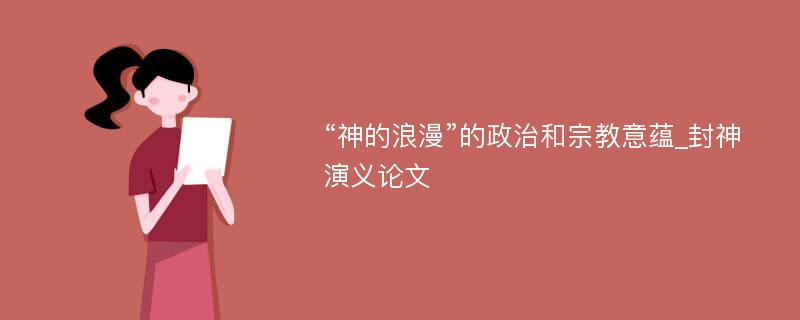
《封神演义》政治宗教寓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意论文,宗教论文,封神演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3-0071-07
一
神魔长篇小说《封神演义》创作于明嘉靖以后,大约在隆庆万历时期,(注:《封神演义》现知最早刊本为天启舒冲甫刊本,但此本并非初刻本。此本各卷独卷二署“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全闾载阳舒文渊梓行”,这是在舒冲甫刊本中留下的舒载阳刊本的痕迹。因此原刊本要早于天启年间。又《封神演义》受到了《西游记》的影响,如哪吒的形象乃《西游记》中哪吒与红孩儿的综合,等等。一般认为《西游记》成书在嘉靖年间。据此推断《封神演义》成书大约在隆庆或万历时期。)距今已有四五百年时间。俗话说“时过境迁”。作者当年创作时的语境,如果我们不穿越时光隧道去追寻往昔的情形,就难以获得对它的明晰的认识。而如果我们不能把握那语境,也就不可能真正走进作品,去准确地解读那故事情节所蕴含的所有的、尤其是那些微妙的信息。时间定格在隆庆万历,这时,影响有明一朝的三件大事已相继发生。第一件是“靖难”。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驾崩,由于皇太子已于六年前去世,皇位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是为建文帝。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以反对削夺宗藩为名,从北京举兵南下,称其师曰“靖难”,累战四年攻陷南京,即帝位,改年号为“永乐”。朱棣称“此朕家事”。但在以儒家思想立国的时代,无论朱棣怎样辩解,怎样残酷地杀戮,还是抹不去天下人内心深处的“篡逆”二字。“靖难”是对明朝人信仰的致命打击。朱棣去世约半个世纪,又发生“夺门”事件。英宗朱祁镇在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役中被瓦刺军俘获,北京岌岌可危。在皇太后的主持下于谦等人拥立英宗异母兄弟朱祁钰即帝位,尊英宗为太上皇帝。于谦指挥若定,击溃了城下的敌军。后来被瓦剌人释放回京的英宗趁朱祁钰病亡之机发动宫廷政变,复辟后不管是非功过和朝野舆论,杀害了保卫社稷的功臣于谦。此即“夺门”之案,是明朝的第二件大事。于谦这样一位公认的忠臣就这样被冤枉的杀掉,社会还谈何忠奸、功过?“夺门”是对天下道德信仰的又一次沉重打击。第三件大事是“议礼”。嘉靖皇帝朱厚熜本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从兄弟,由于朱厚照没有子嗣,朝廷便议立这位从兄弟即帝位。按封建宗法制,朱厚熜既然过继给朱厚照的父亲(孝宗朱祐樘),便应称孝宗为皇考,但自私偏狭的朱厚熜硬要尊自己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廷臣由是分裂成两派。尽管反对嘉靖皇帝此举的理据按宗法制度不容置疑,但反对派不是被廷杖,就是被囚禁流放,而逢迎皇帝之佞臣如严嵩则由此进用。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如此简单明白的是非竟遭到如此强横的颠倒。严嵩专权十四年严重败坏了朝政,但更重要的是它对人心和信仰的冲击所造成的长期和深刻的贻害。经历了“靖难”、“夺门”和“议礼”三大事件后的明朝社会,维持封建专制统治的儒家伦理道德已经失去了权威性和感召力,如果说当时是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大概不是过甚之词。《封神演义》产生在这个时代决非偶然。
《封神演义》写姜太公封神,不过这封神只是小说情节的大结局,主要情节是写殷纣王如何荒淫无道,周武王如何被逼举兵伐纣,最终以周代商。框架仍是武王伐纣那段历史。写这段历史的小说,《封神演义》不是第一部,最早的是元代的《武王伐纣平话》,平话中亦有一些神怪情节,但它的风格平实,主要是讲史。次之为嘉靖间余邵鱼编撰的《列国志传》,此书卷一讲述武王伐纣历史,它是以《武王伐纣平话》为基础加工编创的,情节较简,其中也有一些神奇描写,主要风格还是写实的。《封神演义》的作者在写作时肯定参照过《武王伐纣平话》和《列国志传》,但是他的创造远远多于因循,不只是在人物情节上别开生面更重要的是在创作方法上别辟蹊径。历史事件只是一个引子,只是一个虚空的框架,作者驰骋想象,吸纳了大量民间信仰的神仙故事,独具匠心地编织出人神共事的小说情节。武王伐纣,既是人世间西周与殷商的战争,同时又是神与魔的战争。神与圣君集结在仁义的旗帜之下,而魔与暴君则沆瀣一气倒行逆施,两个阵营经过你死我活的反复较量,正义得到伸张,邪恶被彻底消灭,人间归于西周一统,神的世界秩序也得以重新排定。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不论是善是恶,灵魂都统统归趋到封神台受封。似乎经过血的洗礼,所有的灵魂都得到超脱和升华。受封的神灵各领职司,就如周武王大封天下,天下诸侯的封建秩序从此而定一样,神界的品位职司的完整谱系也因封神而编制完成。这个神界的谱系对中国民间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和《封神演义》都以商周革命为题材,但是就小说类型而言,前二种是讲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是神魔小说。
《搜神记》谈鬼说怪,它的作者干宝在自序中声明,是为了证明“神道之不诬”,显有宗教的目的。《封神演义》写了许多道教神祗,其中一些如文殊广法天尊、慈航道人、燃灯道人、普贤真人等等是借用的佛教菩萨,小说中贯穿着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它详尽地解说了众神的由来,所有这些都迹近为神道设教。但是它也只是“迹近”而已,它与《搜神记》之类的志怪小说有本质的不同,神魔也好,宗教也好,都是小说情节之表象,它的意旨下在神道,而在藉神道之虚幻情节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封神演义》描写的神魔毕竟是附着在一段历史上的,而这一段历史对于明朝却有几分特殊的意义。
问题要追溯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那里。朱元璋尊崇儒家,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这是昭明的事实。但是这位开国皇帝却不喜欢孟子的某些思想,确切地说,他不喜欢《孟子》中的民本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其实是孟子思想中最有进步性和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他的这个思想是对孔子的三纲伦理思想的一个重大的发展。这个思想是从武王伐纣历史总结出来的。
武王伐纣发生在公元前1066年。武王的西周与纣王的殷商不是部族与部族的关系,而是侯国与中央共主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先秦典籍《尚书》、《诗经》中均有记载,而且在战国时代被公认。基于这种关系,武王伐纣,其性质便是以“臣”伐“君”,用儒家所坚持的君为臣纲的伦理纲常来考量,这是大逆不道。但是儒家又十分推崇周武王,这个矛盾如何解释?孔子《论语》对此略有回避,他只称赞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主德也已矣。”[1]对于武王则显有微词,“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韶》相传为赞颂虞舜的一种乐舞,《武》相传为赞颂武王的一种乐舞,孔子认为《武》“未尽善”,谈的是音乐,实际上是对武王伐纣略有批评。战国时代有些人就拿武王伐纣来诘难儒家,《孟子》记齐宣王问孟子曰: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2]孟子不像孔子那样对武王有所保留,他理直气壮为武王辩护,宣称君主不仁不义便不是君主而是独夫民贼,讨伐独夫民贼不能叫做弑君。民本思想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孔子之前,《尚书·泰誓》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管子·牧民》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不过,包括孔子在内的思想家强调得民心顺民意,都限定在君为臣纲的框架之内,君主对于臣民仍是主体和本位,顺从民心只是维护君主地位和统治的手段而已。孟子的思想显然向前跨出了一步,他还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2]他于是给儒家的君为臣纲的最高伦理原则加上了一个前提条件:“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2]结论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孟子的这种民本思想含有宝贵的民主因素,它虽然并没有悖离“三纲”,但却否认了“三纲”的绝对性,不但对封建君主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有所制约,而且为臣民推翻一个暴君提供了理论根据。
每个在位的君主,大概心里都不会喜欢孟子的民本思想,因为它无疑是悬在自己头上的一把利剑,而不能无所忌惮;然而它却是植根在历史和现实土壤中的理论,自夏商以来的改朝换代的事实不断证实这个理论的坚确性,从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着眼,还是要尊重它是儒家孔孟之道的一个组成部分。惟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公开表示不能接受它,朱元璋认为孟子的这些言论抑扬太过,失之偏颇,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诏令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将它们删节。祝允明说:“上万几之暇,留意方策。……又以《孟子》当战国之世,故词气或抑扬太过,今天下一统,学者倘不得其本意而概以见之言行,则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又命三吾删其过者为《孟子节文》,不以命题取士。”[3]周宾所《识小编》说得更具体一些:“洪武二十七年翰林学士刘三吾等奉上……又校《孟子》一书中间语言太峻者八十五条除之,命自今八十五条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其余一百七十余条颁之中外,俾皆诵习,名曰《孟子节》。”[4]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亦记载曰:“我太祖国初尝删‘国人寇仇’‘反覆易位’等数章不用……”[5]《孟子节文》七卷,今存洪武二十七年刊本。由是,武王伐纣的合理性至少在朱元璋时代给打上一个大问号。
既然“君之视臣如土芥,”人臣也不能视君如“寇仇”,明朝皇帝对君臣之道的实践便可想而知。纣王以炮烙、虿盆施于大臣,明朝皇帝自朱元璋垂范,廷杖、剥皮、凌迟、抽肠种种酷刑,无所不用其极,其暴虐程度决不亚于传说中的纣王。鲁迅曾愤激地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6]。明朝经历“靖难”“夺门”事变,至正德武宗,国势发生逆转。刘瑾“阉党”专权,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江西宁王叛乱,说明当时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已趋白热化,已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继武宗即位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并不思励精图治,不顾封建宗法昭穆制度,从而引发“礼仪”之争,弄得黑白颠倒,奸佞当道。嘉靖皇帝又迷信丹药方术,日以斋醮为事,长期不理朝政。嘉靖四十五年(1566)海瑞上疏指责说:“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嘉靖皇帝读疏勃然大怒,立即下旨逮捕海瑞,他身边的太监告诉他,海瑞已作好一死的准备,并不打算逃跑,他只得哀叹道:“此人可方比干,然朕非纣耳。”[7]可见在嘉靖皇帝头上还盘旋有武王伐纣的历史阴影,尽管他不承认自己就是那历史上荒淫无道的纣王。
汉代以来,各朝皇帝向自己的臣属施虐的事情并不少见,但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这样贯彻始终地、普遍地、毫不顾及士人尊严地残酷施虐。有明一朝就是按照朱元璋删节《孟子》并一度罢祀孟子的思路来处理君臣关系的,而他删节的孟子言论正是由武王伐纣历史而引发出来,可见在历朝历代中独明朝与武王伐纣有这么一种特殊的关系。
二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封神演义》的作者选择武王伐纣的历史,把它演绎成一部长篇说部,其对现实政治批判取向是不难体察的。诚然,元末即有《武王伐纣平话》,《武王伐纣平话》三卷的前二卷详细叙说了纣王不仁无道的种种暴虐,全书的重点不在“伐纣”的战争过程,而在战争的缘起。作者当然是站在武王这一边的,他的这个立场的彻底性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的贬抑态度上。书中借武王和姜子牙之口列述了纣王的十条大过,强调的是“论条律”。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处治皇帝的条律,作者实际上是把武王和纣王的位置颠倒过来作为前提,从而也就回避了伐纣所涉及的君臣纲常的伦理问题。早于《封神演义》的《列国志传》也写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全书的主要情节是东周列国争霸,武王伐纣在全书中只是一个序曲。讲历史总有鉴今的意指,余邵鱼在《题全像列国传引》中就说:“骚人墨客沉郁草莽,故对酒长歌,逸兴每飞云汉,而扪虱谈古,壮心动涉江湖,是以往往有所托而作焉。”《列国志传》所写武王伐纣情节,系由元刊《武王伐纣平话》编创,因袭痕迹十分显明。它对武王伐纣的合理性的解释,更多强调天命。书中一再描写周文王姬昌善理易卦,倡言说:“吾观商德将衰,不出二十年后有革命之象。”这也就是说商周革命乃是天意,皇权天授,武王伐纣也就无可指摘了。多少还是回避了君臣纲常伦理的问题。《封神演义》在描写纣王暴虐的故事情节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它的特点在于它搬用孟子的君臣纲常伦理来作为思想武器。第六回写纣王炮烙敢于直谏的梅伯,黄飞虎议论道:“据我末将看将起来,此炮烙不是炮烙大臣,乃烙的是纣王江山,炮的成汤社稷。古云道得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主上不行仁政,以非刑加上大夫,不出数年,必有祸乱。”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中那些被朱元璋删掉的话语,被《封神演义》捡了回来,还要加上“古云”云云。本来,《孟子》的原貌在朱元璋去世以后不久,篡了建文帝位的永乐皇帝朱棣就将它恢复了过来,这一点有永乐年间国子监颁刻的《孟子》版本为证。《封神演义》尽可以直书“孟子曰”,不必借用什么“古云”之类的话头来遮掩,可是它偏偏要说是“古云”,这是不是蓄意地点醒人们不要忘了《孟子节文》,不要忘了朱元璋践踏孟子的民本思想的历史呢?
《封神演义》对于孟子的民本思想决不只是点到而已,它把这个思想作为人物情节的基础,贯穿于作品的始终。它与《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之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生动地描写了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姜子牙以及他们统率的将领们,怎样从殷商的忠臣转变成殷商的叛逆和掘墓人这一个艰难痛苦的历程。《封神演义》演绎武王伐纣的艰难,与其说在战争,勿宁说是在观念的转变。
姬昌被纣王囚禁羑里七年,长子伯邑考被纣王剁成肉酱,做成肉饼,姬昌还被逼得忍着巨痛吞食自己亲生子肉身做的肉饼。姬昌之被纣王无端加害,而且加害手段之毫无人性,真是令人发指。可是姬昌对纣王并无反叛之意,他临终告诫姬发一定要恪守君臣之道,“纵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为,以成臣弑君之名。”《武王伐纣平话》描写的文王却是立意要伐纣立国安天下的,他临终对姬发的嘱咐是“不得忘了无道之君,与伯邑考报仇”。《封神演义》描写的武王也不是一开始就主张伐纣的,纣王派遣大军几次进剿西岐,西岐的姜子牙在抵御这几次大规模进攻之后,主张反守为攻,东征殷商,武王却拘于父王遗嘱,对举兵之事犹豫不决,他说:“虽说纣王无道,为天下共弃,理当征伐;但昔日先王曾有遗言:‘切不可以臣伐君。’……总纣王无道,君也。孤若伐之,谓之不忠。孤与相父共守臣节,以俟纣王改过迁善,不亦善乎?”经过姜子牙等大臣反复申述吊民伐罪的大义之后,武王才转变思想,准旨兴师伐纣。从文王到武王的转变,客观上是纣王无休止施虐所逼,但关键还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提供了精神支柱的理论武器。
从“忠”到“叛”是怎样一个艰难的转变,在黄飞虎身上体现得最丰富和最生动。黄飞虎的妹妹是纣王的西宫黄妃,他自己位居武成王,是殷商的股肱大臣。纣王宠信妲己,炮烙忠良,令黄飞虎义愤填膺;随即他的夫人抗拒纣王凌辱而跳楼殒命,他的妹妹黄妃也被纣王摔下楼去身亡。辱妻杀妹,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当他的兄弟黄明鼓动他反出殷商时,他却说:“黄氏一门七世忠良,享国恩二百余年,难道为一女人造反?”这种似乎不合情理的反应,使读者真切感受到黄飞虎心灵上的重压。后来他终于行动了,但也只是从殷商出走,投奔西周而已。在西行途中,他每闯一关,小说都描写必有一场恶战,而恶战之前又必有一场忠与叛的口头论战,这观念上的战争对于黄飞虎压力更大,考验也更大。最严重的事态发生在界牌关下,据守界牌关的守将竟是他的父亲黄滚,黄滚摆出一副殷商忠臣的面孔,斥责并威逼他:或者投降,庶几黄氏不至于满门罹难;或者弑父,以免作为殷商大臣的父亲落得个不忠的臭名。面对“义正词严”的父亲,黄飞虎那得之不易的“君不正,臣投外国”的信念顷刻发生动摇,几乎就有下骑投降之意。
与黄飞虎反叛君主相辉映的是哪吒忤逆父亲的故事。哪吒闹海以及他在与封建宗法伦理的种种冲突中所表现的天真和无畏,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然而哪吒却又不同于孙悟空,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进出来的,真是赤条条无牵挂,哪吒却有生身父母,因而哪吒也就不能像孙悟空那样天马行空,那样超脱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伦常关系,正是他与封建伦常的冲突,构成了他的性格之不同于孙悟空的独特之处。哪吒的父亲李靖是陈塘关的总兵官,此人求仙不成,却享有不浅的人间富贵,为了保守这份荣华富贵,李靖为人为官都从来是谨小慎微。不意他的第三个儿子哪吒却毫不理会他的苦衷,在外惹事生非,先是打死了仗势欺人的夜叉,接着又结果了不可一世的龙王三太子。哪吒此举是除霸锄奸,乃是大快人心之事。可是李靖并不问是非曲直,见是得罪了权贵,生怕招来灭门之祸,不仅一味指责哪吒,甚至要把哪吒交出去任由龙王处置。李靖的自私和胆小,使他自己几乎完全丧失了慈父之情。哪吒不愿连累父母,在龙王和父母面前切腹、剜肠、剔骨肉,以明朝所实行的残酷极刑来了却此案。在哪吒看来,骨肉既已还给父母,灵魂也就与父母没有了关系。可是祭祀他灵魂的祠庙,仍不能见容于李靖。李靖害怕沾惹“私造神祠”的罪名,害怕由此而断送自己的功名富贵,毫不留情地砸毁了神祠,使得哪吒魂灵无以依附。哪吒自认为与父母已脱离了关系,于是寻找李靖报砸庙之仇,打得李靖狼狈不堪。哪吒的二哥木吒跳出来帮助父亲,斥责哪吒是“子杀父,忤逆乱伦”。尽管哪吒陈述事实,但木吒认为儿子不仅骨肉属于父母,灵魂也属于父母,与父母论理就是大逆不道。木吒教训哪吒说:“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这个在封建宗法社会中被视为铁的定理,在此时的语境中从木吒口中道出,却含有浓厚的反讽意味。封建宗法的君臣之道,是从父子之道引申出来的,哪吒的故事是在人性的层次上批判了绝对化的君臣之道,它的理据还是孟子的民本思想。
《封神演义》用它的情节一再张扬被朱元璋删掉的孟子的民本思想,显然不止是一般的以史为鉴,而是有现实批判的目的的。它对现实的批判,除此之外,还蕴涵在神魔的故事情节中。《封神演义》以小说创作风格而言,它是政治斗争与宗教斗争的结合,人间世界和神魔世界的交融。宗教斗争和神魔厮杀,是《封神演义》作者的创造。按《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发生在公元前1066年,一月出兵,二月即攻下朝歌,这场战争简直就是摧枯拉朽,毫无悬念可言。《封神演义》把这场战争渲染得复杂化、曲折化和激烈化了,并且在这场战争中不仅注入了上述的政治伦理内容,而且注入了浓重的宗教内容。以武王为首的西周高举仁义的旗帜,辅佐西周的是道家的阐教。阐教之人都秉承天命,深悟玄机,支持仁义,征讨邪恶,他们团结道家的清流,同时还联合隐指释家的西方教主。阐教身上显有三教合一的特征。以纣王为首的殷商失道寡德,维护尽失民心的殷商腐朽统治的是道家的截教。截教之人如通天教主、申公豹之流,有的是有逆天道、不守清规、助纣为虐的名利之徒,有的是不解天意、不识时务的愚顽痴迂之辈,申公豹长得脸朝背后,便是他们倒行逆施的象征。
三
阐教与截教,道教史上并没有这样的教派,他们显然出自作者的杜撰。阐教、截教的取名出自何典,不得其详。鲁迅从字义上解释:“‘阐’是明的意思,‘阐教’就是正教;‘截’是断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谓断见外道。”[8]阐教为正,截教为邪,小说就是如此描写,毫无疑义。问题在于,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写的喻义何在?
武王伐纣时还没有道教,道教尊崇的老子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孔子同时的人,他们都在武王伐纣的五百年后才诞生,《封神演义》描写的宗教情形决不是历史的摹写,而只能是作者的虚构。作家的虚构,不论虚构得如何荒诞和虚玄,他的构思意想总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社会,他的情节编织总不能不依靠他那个时代给他提供的生活元素,这就像孙悟空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封神演义》情节魔幻之极,但它也必然只是作者那个时代现实的一种投影。问题还是要回到明朝。中国道教由多个派别发展到元末逐渐形成正一道和全真教两大派,正一道以符箓为主,全真道以内丹修炼为主。明朝立国后,朝廷正式将道教划定为正一、全真两大派,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4)作《御制斋醮仪文序》云:“朕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又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慈子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基于伦理教化以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朱元璋看重正一道。洪武五年(1372)御制之诰,命正一道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掌天下道教事”,事实上确认了正一道在道教中的至尊地位。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正式设道箓司总管全国道教,并确定正一、全真两派道士的身份,授予两派道士不同的度牒和职衔,使得正一和全真两派泾渭分明,并制度化和法律化。正一道的主流地位亦得到政府的保障。
明朝历代受皇帝宠信的道士,绝大多数都是正一道的人物。正一道掌管天下道教,很多首领不事性命双修,却热衷俗世的富贵荣华,并且仗恃权势胡作非为。史书记载,第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于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年间执掌天下道教事,“宠赍独盛,朝野荣之”,张元吉“素凶顽,至僭用舆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7]。余继登《曲故纪闻》记张元吉事云:“成化五年。以正一嗣教真人张元吉凶暴贪淫,或囊沙压人致死,或投之深渊,前后凡杀四十余人,为族人所奏,械系至京。”当时刑部依罪“当凌迟处死”,但并未能执行,仅发配肃州而已。而所谓发配,其实是游览名山之行,张家后人编撰的《汉天师世家》描叙这个发配是“辞归出游,历登名岳,探仙人旧隐之迹,去六载方还”。难怪余继登恨之而咬牙切齿地说:“当时不能执论绝其根源,致令其徒奉行,至今自若,深可惜也。”[9]后继者依然如故,第四十八代天师张彦頨“知天子好神仙,遣其徒十余人乘传诣云南、四川,采取遗经、古器进上方,且以蟒衣玉带遗镇守中贵”[7],云南巡抚欧阳重弹劾其不法,朝廷却不问。第四十九代天师张永绪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诰授“正一嗣教守玄养素遵范崇道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诏聘定国公徐延德女为妻,权势炙手可热。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张永绪其人“荒淫不捡”,“有害于民”[10]。正一派的道士之著名者,还有被《明史》列入“佞倖列传”的嘉靖时期的陶仲文、邵元节,他们都善于以方术、道法之类的骗术取得嘉靖皇帝的欢心,由此攫取富贵。尤其是陶仲文,他所得到的荣华富贵,非朝廷儒臣所能比。正一道以斋醮祈禳为职事,擅长符篆法术,又因为被朝廷封为主派,富贵荣华者甚多,在权力的腐蚀下道流素质江河日下,在道教理论教义建设方面反倒无甚贡献。
全真道在元朝也曾显赫一时,入明以后被排斥在边缘位置,这个流派的道士荣贵者寥寥无几。处在寂寞中的全真道士以修身养性为务,隐栖潜心苦修,与正一道士的功利主义相比,他们身上更多地表现出宗教信仰精神。诚如元明间道土王道渊《沁园春·全真家风》所言,“不恋功名,不求富贵,不惹闲非。盖一间茅屋,依山傍水。甘贫守道,静掩柴扉。读会丹经,烧残宝篆,终日逍遥任自为。”[11]他们对于道教理论教义的贡献远远大于掌教的正一道。明初武当山全真道士张三丰著有《大道论》、《玄机直指》、《道言浅说》、《玄要篇》等,明代中叶并未入道的陆西星(1520-1606)著有《玄肤论》、《参同契测疏》、《金丹就正篇》等,对于道教内丹学皆有重要建树。全真道和正一道同是道教,在教理教义上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正一道吸收全真道理论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全真道强调心性的修炼,倾心于内丹学,并且吸收佛教禅宗思想,在宗教实践上主张“苦己利人”,因而全真道士一般均能保持出家人的朴素作风,苦心励节,潜心修炼,与那些崇尚符箓、迷恋黄白之术的正一道士有显著差别。
《封神演义》描写的阐教和截教同属道家,第七十七回阐教元始天尊批评截教通天教主时,口口声声称“你我道家”,通天教主亦称元始天尊为“道兄”,阐教和截教为道家中的两派,在小说中写得十分清楚。截教助纣为虐,极力维护商纣的腐朽统治,对抗顺应天意的新兴的西周。在阐教中人的眼中他们都是不守清净的名利之徒。第八十二回“三教大会万仙阵”是阐教与截教的大决战,双方都摆出了自己的全部阵容。黄龙真人蔑视截教队伍说:“自元始以来,为道独尊,但不知截教门中一意滥传,遍及匪类,真是可惜工夫,苦劳心力,徒费精神。不知性命双修,枉了一生作用,不能免生死轮回之苦,良可悲也。”燃灯道人等指着截教徒众说:“人人异样,个个凶形,全无办道修行意,反有争持杀伐心。”鸿钧道人则指责截教领袖通天教主热衷名利,放纵邪欲,不守清净,“名利乃凡夫俗子之所争,嗔怒乃儿女子之所事”,岂是道家人的心性!《封神演义》中阐教对截教的批评,切中明朝正一道的要害,而阐教言论和实践则又反映了明朝全真道的立场和观点。由此得出结论说:《封神演义》所描写的阐教与截教的冲突,是明朝前期和中期全真道与正一道的现实矛盾的曲折反映,小说对截教的描写隐含着站在全真道立场的对正一道与腐朽朝廷沆瀣一气的现实的批判,这样说大概离事实不远吧。
《封神演义》对昏君与邪道结合之愤懑,反映了明朝中期酝酿于朝野的强烈情绪,当时的读者大概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上举成化年间天师张元吉凶暴贪淫被逮至京问罪,刑部尚书陆瑜等依律“凌迟”,在押之时,刑科都给事中毛宏等又上奏:“元吉于十恶之内,干犯数条,万一死于狱中,全其首领,无以泄神人之愤,乞即押赴市诛之。”[10]可见朝臣对邪恶道人的痛恨。嘉靖时道士龚中佩依于陶仲文名下而得宠于皇帝,此人入直内庭,在宫中酗酒闹事,连太监也不放在心里,终被诸珰所谮,诏狱杖死。沈德符记载此事时议论说:“世宗宫闱防范最严,何以容一醉道士出入禁籞,此与武宗朝西僧直豹房何异?虽即诛殛,已非礼矣。”[10]这议论中已透露出对嘉靖皇帝的批评。然而敢于面指皇帝的还是海瑞,海瑞上疏嘉靖皇帝说:“今乃行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臣下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术之!”[7]海瑞指出皇帝出于长生不死的私心而迷信正一派道土,一针见血,而且道出了正一道行时之缘由。皇帝与道土的不正常关系是明朝中叶政治腐朽的特征之一。这一点当时天下人尽知之,惟皇帝为私心蒙蔽一人不觉而已。《封神演义》取材于历史写的是神魔情节,但作者立足于现实,其魔幻情节所寓含的现实批判精神是不应该被今天的读者所忽略的。
[收稿日期]2004-03-30
标签:封神演义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天下父母论文; 明朝论文; 孟子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武王伐纣论文; 哪吒论文; 朱元璋论文; 列国志传论文; 国学论文; 截教论文; 正一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