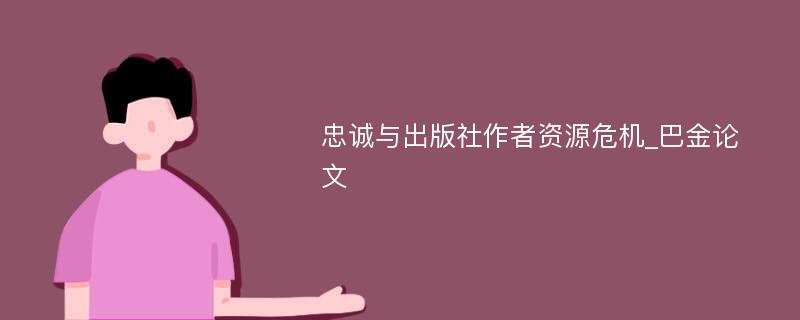
忠诚度与出版社作者资源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忠诚度论文,危机论文,出版社论文,作者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成为当前国家产业创新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产业的结构或质量,关键之点在于对核心知识产权的拥有。就此来说,作者恰属于出版业的核心资源,属于核心知识产权的创造者。在所有作者中,处于核心层中的、具有一定品牌的作者,因其影响性和极强的创造性,对出版社来说尤为宝贵。
对核心作者的高度重视,全世界的出版业都有基本相同的态度。当然,具体做法在不同国度、不同特色的出版社那里各有千秋。比如加拿大禾林公司推出的“禾林爱情小说”采用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出版社选定主题和写作模式,签约作家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填空”。但是,这种工业化的出版方式毕竟属于少数,更多成长为国际出版巨头的出版社始终以曾经拥有的伟大作者而自豪,也正是这些伟大的作者造就了出版社的辉煌历史。
美国人斯特劳斯之所以把一家小社变成了美国出版史上最具前瞻性的经典文学帝国,恰在于该社拥有一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46年,斯特劳斯在创办法劳·斯特劳斯·吉罗出版社(FSG)之初,还只能出版些历史小说和营养指南方面的读物。但在此后的17年间,经这家出版社推出的艾萨克·辛格、捷斯拉夫·米洛什、埃利亚斯·卡内蒂、威廉·戈尔丁、沃尔·索因卡、约瑟夫·布罗茨基、加米略·何塞·塞拉、南丁·戈迪默、德雷克·瓦尔科特和塞默斯·希尼等10位作家,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时,斯特劳斯又将早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吸引进来。到80年代中期,FSG的作家们还赢得了15个国家图书奖和6个普利策奖。尽管1994年这家出版社被德国霍茨布林克出版集团并购,但凭借其“美国文学帝国守护神”和“诺贝尔小分队”的称号和整齐、高质量的核心作者群体,在庞大的霍茨布林克集团内,FSG依然享有保持独立的特权地位①。
在我国现代出版业发展史上,伟大作家、学者与出版社之间共荣共生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1897年成立的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可以说,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大师,几乎都曾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作者。正是凭借这些作者,商务印书馆以文化的方式,直接参与并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能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屹立不倒,与近现代以来诸多文化名家的加盟有着重要关系。
紧密的情感联系、真诚的作风,以及双赢的结果,时常让作者与出版社形成珍贵的忠诚。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忠诚关系,在国内外的出版史上都不乏佳话。亚历山大(L.G.Alexander)是英国朗文公司的忠诚作者(其《新概念英语》自被我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后,在中国一直风行),他一生编写的英语读物都在朗文出版。当伊朗一家出版商重金相邀,请其专为伊朗读者编写一部英语学习读物时,亚历山大告诉对方,先向朗文公司交涉。其实,亚历山大完全有权让自己的经纪人处理此事,但对朗文的忠诚之心让其放弃了自主签约。亚历山大与朗文之间的忠诚既建立在情感之上,也建立在规则认同之上。出版机构与作者之间的文化认同,在我国盛行于“同人出版”的20世纪前半叶,如鲁迅之于北新书局,巴金之于开明书店。1949年12月,当巴金创办平明出版社时,正在诞生的新中国已经制定“公私合营”的文化出版政策。1953年平明出版社最终并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但就在这短短的4年内,凭借巴金的声誉,以及对作家的忠信作风,平明出版社聚集了众多优秀的翻译家。卞之琳不惜和领导闹翻,也要把稿子抽回交给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焦菊隐不仅表示“十分愿意尽微薄之力帮‘平明’,以后有稿子当尽先选好的送‘平明’”,而且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的新华书店的竞争,给巴金以支持和自信,“‘新华’的发行网大,‘平明’将会受点影响,但,他们的译本不太好,也就无关了……这得等批评家和读者来决定了。”②作家与出版社之间的忠诚与认同,由此可见一斑。
二
在出版产业的范围内,忠诚度不仅是个道义概念,而且是个综合了感情、品牌、文化价值观、经济,以及服务细节等方面的总体原则。忠诚度总体的立足点,主要在于文化情感、信义规则和经济利益这三个方面。考察作者对出版社的忠诚度,其中一个指标是看品牌型作家将多少有价值的作品交给了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下面分别选取巴金、余秋雨和郭敬明作为个案。
大致来说,这三位作家分别代表了三个有明显差异的出版时代。在现代文学大家中,巴金无疑是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比肩而立的文学大师之一,巴金同时还有主持出版社的经历。余秋雨由戏剧研究而文化散文创作,一部《文化苦旅》使其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和出版“转折期”的代表性人物。郭敬明身为“80后”的代表作家,与国有出版单位“转制”浪潮和民间出版“工作室”之风相伴而生。他们与出版社之间的“忠诚度”变迁,将折射出许多耐人深思的复杂因素。
巴金著作资料显示③,在1953年巴金创建的平明出版社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之前,巴金共出版了58部作品。其中,巴金在开明书店出版过11部作品,在1935年开始担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过12部作品。从数量来看,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作品超过开明书店,但深入分析发现,1935~1953年,巴金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作品仍有8部之多。巴金这期间最重要的《激流三部曲》没有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而是给了开明书店。上世纪50年代前的出版社基本为私人出版社,如巴金这样的作家及其重要作品对出版社来说,不仅意味着文化地位,还意味着私人出版社急需的经济利益。巴金将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交给开明书店出版,一方面出于对开明书店1926年出版其处女作《灭亡》的感激之情,是开明书店逐渐将热心社会活动的巴金引向了作家之途;另一方面,则因为主持开明书店的叶圣陶、夏丏尊为“文学同人”,开明书店属于“同人”出版社。胡愈之曾评价,“从办杂志开始,靠几个知识分子办起来的书店,开明书店是第一家”。“在编辑出版工作、团结作家、联系读者方面,开明书店积累了不少经验”。也许正是因为信仰、兴趣的相同,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理解和关爱,巴金甘愿舍弃自己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而对开明书店忠贞不渝。④
其实,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人在对出版社的选择上,大部分与巴金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如钱钟书80年代“复活”的《围城》。早在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围城》就连载于《文艺复兴》杂志。1947年5月,赵家璧主持的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围城》单行本。1949年后,《围城》在大陆被打入另册,直到1980年10月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这30年间,《围城》只在1979年由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过英文版。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围城》至今,无论是电视剧带来的巨大效应,还是其他出版社的盛情邀约,《围城》的大陆版本始终没有转移到第二家。以巴金、钱钟书等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先后延续了半个世纪前“同人”出版、忠心不移的优良出版传统。
余秋雨的学术著作《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和《艺术创造工程》(上海文艺出版1987年3月出版)为其在学术界奠定了重要地位,但让余秋雨家喻户晓的却是散文单行本《文化苦旅》。余秋雨没有选择出版自己学术著作的湖南人民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而是在1992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副牌社知识出版社首次出版。2001年,《文化苦旅》转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上海分社——独立建社后定名为东方出版中心——再版。《文化苦旅》给90年代的余秋雨带来了新的人生起点,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余秋雨本人更是意义非凡。但统计资料显示,在余秋雨此后出版的25部作品中,东方出版中心再也没有成为余秋雨的选择。事实上,余秋雨此后不断变换出版社,出版数量最多的作家出版社也仅出版了其3部作品(分别是1999年出版了《霜冷长河》、2000年的《千年一叹》和2004年的《借我一生》),其次是文汇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山居笔记》、2001年出版了《晨雨初听》)。就在变换于这两家出版社的同一时间,《余秋雨千禧日记》于2000年交给了光明日报出版社,《行者无疆》于2001年给了畅销书领域风头正劲的华艺出版社。在《文化苦旅》以来余秋雨个人的出版史上,似乎没有哪一家出版社能获得余秋雨的专注和钟情。⑤相反,余秋雨对国内出版环境的抱怨之声,乃至“封笔”之说则不绝于耳。与此相应的是,在2006年的调查榜上,余秋雨以1400万元的作品收入而位列大陆作家首富。⑥与巴金、钱钟书等相比,90年代以后当红文坛的余秋雨,无论是其学术著作或散文作品的初版者,都未能作为忠诚选择的对象;余秋雨一直在甄别选择,其结果则是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没有成为他的不二选择。
相对于余秋雨,郭敬明让我们更能看清出版社在作家心中的权重。巧合的是,郭敬明的小说处女作《爱与痛的边缘》也是由东方出版中心初版,出版时间在《文化苦旅》转给东方出版中心的同一年(2001年)。郭敬明同样在此后的出版中与这家出版社绝缘。200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让郭敬明风行大江南北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和《幻城》。这两部小说将热浪滚滚的“青春文学”推向了高潮,郭敬明很快拥有了自己庞大、固定的读者群。在巨大的读者群体和市场利益面前,郭敬明没有像余秋雨那样虽然不断变换门庭但对出版社依然“依靠”的做法,而是选择建立一个团队,在国有出版单位之外成立了一个相当于合作性质的出版机构——“I5land岛”工作室。以郭敬明为核心,由五人构成的这个小团体,采取类似一人创意、集体创作的方式,推出杂志和图书。春风文艺出版社曾推出了名为《岛》的不定期小说刊物,但这家出版社孱弱的经济实力甚至难以支付郭敬明的稿费。2006年开始,长江文艺出版社接手了由《岛》杂志改装而成的《最小说》。在郭敬明与出版社的关系更迭中,一种更为商业化、市场化的色彩扑面而来。如果说余秋雨的主动还只表现在对出版社的舍弃或重选,那郭敬明则以一种商业性的合作与出版社建构关系;余秋雨毕竟还只是单枪匹马,体现出90年代“过渡期”文化人的个体性,而郭敬明则以一个“杂志型”的写作团体,一个经营性的“工作室”,与出版社建立起基于个人权益但又非个体性的关系,国有出版社在郭敬明这里不再是文人传统中通常的倾慕对象,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成为被选择的弱势群体。
从巴金、钱钟书到余秋雨和郭敬明,出版社与作家之间那种牢固、稳定的关系日渐减弱,相互之间“一吻定终身”越来越成为记忆中的旧事。这一嬗变似乎属于微观问题或道义问题,但从宏观来看,其实又与我国现代出版业从初期的私营到50年代后的全部国营,再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制”为企业有关;还与出版社从“同人”办社、50年代后的文化官员办社,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理人身份办社有更深的关联。
三
如果说品牌型作家对出版社的忠诚度有所降低,出版社的核心作家资源出现了危机,那么,事情的另一面在于,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成为出版社的新作者。在2006年12万多种的新书中,品牌型作者之外的新作者、处于成长期的作者,无疑占有极大的比例,尤其是来自网络上的写手,在出版社那里不断涌现。但是,新作者及成长期作者的数量优势,与出版社可靠、稳定的作者资源建设属于两码事。大多数的新作者及成长期的作者又往往转瞬即逝,要么成为“一本书”作者,要么出书有明确的职称评定需要或其他功利。因此,出版社的作者资源建设,根本还在于对品牌型作者的养护。
必须承认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出版业的产业属性比文化属性更为突出之时,出版社核心作者资源的危机将成为必然的阵痛。忠诚需要对等,忠诚更要靠实力说话。作者对出版社忠诚度的高低,实则建立在出版社的信义基础、品牌影响和经济能力之上。因此,出版社核心作者资源建设至少应在四个方面做出应对:
首先,在坚持出版业的产业属性基础上积极“复活”或强化自身的文化属性。文化属性的弱化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出版实践中已经成为趋势。无论是90年代以前的科层化文化官僚体制,还是90年代以来产业化的形似经理人主政,都基本中断了50年代以前的“同人”出版传统。回到“同人”出版,在体制上没有可能,但接续其优良的作风和传统,尤其是从文化追求、文化理想上汲取其中的精华,努力营造良好的氛围,打造特色鲜明的出版品牌,让出版社成为文化人自觉聚拢的“精神家园”,则是出版社持续发展、建构核心作者资源的根本基础。
其次,在承认市场经济规则的基础上坚守信义原则和全面完善的服务。作者权利意识的全面觉醒、作者权利多样化的全方位释放,使出版社在获得作者出版权利方面受到了许多限制,比如品牌型作者会清醒地签署3~5年的短期授权合同,为自己保留电子版权、繁体字版权、影视改编权和其他语种版权等等权利,那种一劳永逸全面拥有作者版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出版社承诺给作者的一应权益如果不能实现,作者很可能马上收回版权。甚至说,市场经济下,作者最大的收益便是拥有了与出版社同等、甚至高于出版社的权利。这就要求出版社在作者有限授权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满足作者应享的权益。坦率地说,当前,许多出版社还没有从事业单位的惯性中走出来,经营能力和效率都相当低下,以至于在执行与作者的协议方面,要么违背信义原则,要么有心无力,从而造成核心作者早早地撤离。坚守信义原则和全面完善的服务,实际上从理念到运作都对出版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次,要有甄别作者的智慧,坚持出版物的去芜存菁。出版物的多品种、低印数、高库存、高退货等一系列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出版社良好的文化形象,也极度降低了出版社的选题门槛。数量繁荣与质量提升的负相关,无形中伤害了品牌型作者对出版社、甚至对文化建设的热情。要在核心作者资源建设上下工夫,减少盲目追逐利润的浮躁气,提高对作者的甄别力,既是基础性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不仅是对新作者的作品进行甄别,品牌型作者也不应例外。事实上,一些有名气的作者粗糙写作、频繁出书和重复出书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当代文化的健康形象。德国汉学家顾彬近来严厉批评中国文学,尽管引起余秋雨等人的反击,但他指出的作家“高产”和追逐财富等问题,可谓切中肯綮。⑦
最后,面对网络的冲击,对作者资源建设的方式和方向要有清晰的预判。网络对传统出版业的冲击,不仅在于批量涌现一大批高起点、高水平的年轻作者,还在于网络正与传统出版社并驾齐驱,日渐成为网络一代的“民间”新型的出版机构。网络杂志、网络视频、博客等等“聚合”型的虚拟空间,已经能够出产传统出版社也难以相比的丰富、新鲜内容。这里恐怕将成为出版社未来核心作者资源最为重要的园地,发现并维护这批核心作者资源,无论信义原则、服务手段和契约重点,都将有区别于传统作者的新特征。
总之,在这传统消失、现实复杂与网络编制的亦真亦幻未来斑斓共生的时代,出版社面临着许多新课题和新选择,也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而“作者崩溃”之痛,不断地撞击着诸多出版社的神经。有关核心作者的资源建设,不仅应该引起重视,即便是列为出版社的一项重大工程,恐怕也不为过。
注释:
①《文学帝国的守护神》,〔美〕伊安·帕克著,《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8日。
②《书局旧踪》,郭汾阳,丁东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③《巴金主要著作及版本》,赵兰英,新华网(www.xinhuanet.com),2005年10月18日。
④《书局旧踪》,郭汾阳,丁东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⑤统计来自中国现代文学馆“余秋雨”著作索引。
⑥《中国作家富豪榜出炉》,《财经时报》2006年12月15日。
⑦《顾彬先生的棒喝》,刘绪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