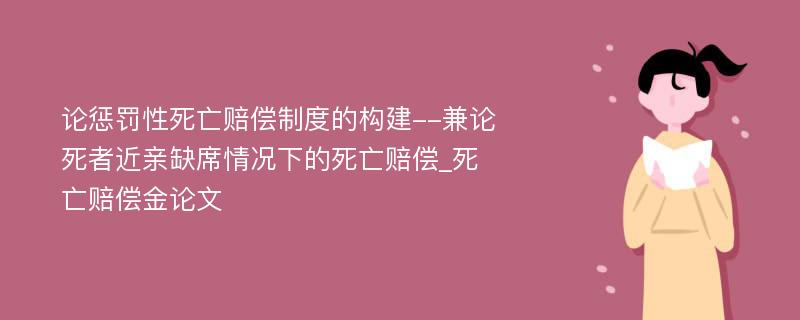
论惩罚性死亡赔偿金制度之构建——兼谈死者近亲属缺位情形下的死亡赔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惩罚性论文,赔偿金论文,死者论文,制度论文,近亲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5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07)05-0055-09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我国连续发生了几起民政部门为交通事故中死亡的无名流浪者向肇事者索赔的案件,一时间引起了媒体和学者的广泛重视:
2006年4月,江苏省高淳县民政局将3名肇事司机和相关保险公司告上法院,为两个在车祸中死亡的无名流浪汉索赔死亡赔偿金30余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民政局不符合原告主体资格,驳回其维权诉求。①
2006年5月,湖南省临湘市救助管理站向临湘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在车祸中死亡的无名流浪者维权,要求肇事司机所在单位和保险公司赔偿25万元。法院判令两被告分别赔偿54656.77元和10万元,并同时规定这两笔钱由救助站予以保管,如果5年内死者亲属仍然没有出现,将依法上缴国库。②
2006年9月,湖北省宜昌市救助管理站向法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在车祸中死亡的无名流浪者向加害人主张损害赔偿。经法院调解,被告同意赔偿62000元,其中2000元系为流浪汉支付的丧葬费用,6万元赔偿款则作为专账专户保存一定年限后方可使用,而且用途必须是公益事业。③
相似的案情,不同的结果,这反映出法官对此类案件的解决尚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的确,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死亡赔偿的权利主体为死者的近亲属,民政部门并无资格要求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就此而言,高淳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无道理。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难道在死者没有近亲属的情况下,加害人就无需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吗?果真如此,受害人岂不“死了白死”?这种结论显然有悖法理和情理。相比之下,临湘案和宜昌案的处理结果更能被人们所接受。但这种看似“合理”的结果之下所隐含的法理漏洞却不容忽视。在这两起案件中,法院虽对救助站提出的要求加害人支付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予以了支持,但却规定救助站对这笔赔偿金只能代为保管(为死者的近亲属),而并不能取得所有权,这意味着救助站实际上是在“代”死者的近亲属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这里的问题在于:其一,如果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存在的话,其是否行使赔偿请求权是他们的自由,而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国家机关强行代之“维权”是否有过分干预私权之嫌?其二,法院判决加害人需支付死亡赔偿金,但依学界通说,死亡赔偿金系对死者近亲属所遭受损害的赔偿。那么,如果经查实死者的确没有近亲属的话,或者说死者的近亲属提出放弃赔偿请求权的话,则救助站提起诉讼的理由当作如何解释?其以死者近亲属的名义索要的死亡赔偿金又当作如何处理?其三,既然死者身份不明,则法院判决书或调解书中所确定的死亡赔偿金数额是依何种标准计算得出的?其四,如果说民政部门可以为无名流浪汉维权的话,是否意味着交警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卫生部门等都可以在处理相关人身伤亡事故中为无名死亡受害人维权?④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无法从法院的裁判书中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事实上,在现行法律及理论的框架之内也很难对临湘案的判决结果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对我国现行的死亡赔偿制度及相关理论予以重新检讨就成为必要。在笔者看来,此类案件折射出我国目前相关立法存在的一个较大的缺陷,即现行的死亡赔偿制度是以死者近亲属的损害为核心构建的,而生命丧失本身则未纳入侵权法的救济范围之内,这直接导致了在死者近亲属缺位的情形下追究加害人侵权责任的困难。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对我国现行相关立法及理论分析检讨的基础上,提出重构我国死亡赔偿制度,并对死者近亲属缺位情形下的死亡赔偿问题提出自己的若干粗浅建议。
二、问题之所在:我国现行的死亡赔偿制度及其面临的理论困境
我国《民法通则》对死亡赔偿问题规定得极为简陋,但2003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则对此予以了明确的规定。依该解释第17、18条的规定,在受害人遭受人身伤害而死亡的情形下,死亡赔偿的项目主要包括:受害人死亡前所遭受的损失(包括就医治疗的各项费用以及误工减少的收入)、丧葬费、被扶养人的生活费、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与之前的法律规定相比,上述规定扩大了死亡赔偿的范围,提高了死亡赔偿的金额,凸显了司法界对生命权的重视。然而,在司法实践的检验中,该制度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其所面临的理论上的困境也日渐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亡赔偿金的性质难以合理界定
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此并未予以明确规定,但该解释第29条对其计算标准则设有明文。该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据此,学者多把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界定为以死者预期收入损失为内容的财产损害赔偿,至于其是对何人、何种财产损害的赔偿,学者之间尚未能达成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死者预期收入损失说
该说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余命年岁(即死者本可以正常生存的年岁)内收入损失的赔偿。该项请求权系死者在生前取得,而于死后由其继承人继承。⑤ 该观点把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对象界定为死者本人,这种理解存在重大的逻辑问题。因为受害人一旦死亡,他就丧失了民事权利能力,既不可能遭受损害,也不可能取得赔偿请求权;即使认为该项请求权系死者在生前取得,则一个活着的人如何能取得对自己死后损害的赔偿请求权?虽然有学者从法技术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间隙取得请求权说”、“同一人格代位说”⑥ 等学说,试图对该项赔偿请求权的基础作一个恰当的说明,但逻辑上的难题依然存在。正如日本学者末弘严太郎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大体上试图承认不使用难度很高的技巧就无法说明结果的做法,恰恰说明其本身存在的错误”。⑦
2.继承利益丧失说
该说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利益丧失的赔偿。因为受害人的不当死亡会导致其余命年岁内的收入“逸失”,而这些收入原本可以作为受害人未来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死亡赔偿金正是对这种继承利益丧失的赔偿。⑧ 该观点把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对象界定为死者的继承人,其实质是将死者正常死亡之前的法定继承人置于一个受法律保护的状态。但我们知道,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前,法定继承人实际上并没有“权利”去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他只是处于一个可以期待继承遗产的地位,但由于这种地位极易遭到被继承人的毁灭而过于脆弱(因为被继承人可以通过遗嘱或行为随时剥夺继承人的继承权),所谓的“期待继承利益”也就因其过于臆测和不确定而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对继承人继承利益丧失的赔偿,就使得原本并不能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仅仅因为加害行为的介入就上升为受法律保护的状态,难谓妥当。此外,如果依此观点,还会出现当死者为子女时,由双亲继承如果死者能够正常生活下去的话本应没有继承机会的利益(因为双亲一般早于子女去世)那样的怪现象。⑨ 因此,该说亦不可取。
3.家庭整体收入损失说
该说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家庭整体收入减少的赔偿。因为死者与其家庭成员是经济共同体的关系,死者的收入除去其个人消费部分,基本上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共同积累。受害人的死亡,使得其未来生存年限中的收入丧失,这导致了家庭可预期收入的减少,死亡赔偿金即是对这部分损失的赔偿。⑩ 这种观点把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对象界定为死者的家庭成员,其缺陷在于:一方面,家庭成员是否一定会遭受此项预期收入损失并不确定。因为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家庭成员之间除法定扶养义务之外,并不存在其他给付财产利益的法定义务,那么,除必要的扶养费之外,家庭成员是否能够获得死者的其他预期收入就具有相当大的臆测性;另一方面,该说的适用也会面临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冲突。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共同生活的配偶、父母、子女互为家庭成员,但如果把家庭成员之一的收入纳入家庭整体收入范围的话,则该财产应为所有家庭成员共有,这将造成与我国现行《婚姻法》上有关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制的不一致,并进而造成死亡赔偿金分割的困难。
综上所述,在把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界定为以死者预期收入损失为内容的财产损害赔偿时,无论将赔偿的对象界定为死者、死者的继承人、抑或死者的家庭成员,均在法理层面或操作层面存在一定的障碍,其合理性值得怀疑。
(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有失公平
在把死亡赔偿金界定为以收入损失为内容的财产损害赔偿的基础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9条对死亡赔偿金采取了区别定额计算标准,即分别对城乡居民采取不同的客观计算标准,并以20年固定赔偿年限为计算的时间。据说,这种采定型化赔偿和客观计算的方式,“旨在既与过去的法律法规相衔接,又不致因主观计算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11) 笔者则对该标准的合理性持怀疑态度。在一个制度涉及不同人的利益分配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该制度是否公平,即是否使人们受到了公平对待。而“公平”的检验标准,依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比例原则”,即要求同等的情况必须被同等地对待,不同等的情况必须按照不同等的程度被不同等地对待。(12) 如果依该原则检验我国现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则不能说城乡居民受到了公平对待。因为该标准实际上是把人划分为抽象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但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具体的存在,其收入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异,一个农民的收入完全有可能高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而一个长期在城镇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收入也完全有可能高于以耕作为生的农民的收入。如果把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界定为对收入损失的赔偿的话,则这些个体差异必须被不同等地对待,才能实现所谓的公平。而城乡二元赔偿标准正是因为无视实际存在的个体差异且选择了“户籍”这个极不合理的分类标准,才触动了人们那根关于公平的敏感神经,并且招致了社会公众和一些学者的指责。(13)
那么,如果在制度中体现了“合理差异”,是否就能够解决问题呢?例如,有的学者主张对城乡二元标准的适用予以适当放松,即对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农村居民也适用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14) 也有的学者主张以死者生前的个人收入情况作为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基准。(15) 上述建议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现行计算标准的缺陷,但在笔者看来仍有不足:第一种观点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第二种观点则面临着是否能够确定,以及如何确定死者的预期收入及赔偿对象的问题。而事实上,在把死亡赔偿金界定为以赔偿死者预期收入损失为内容的财产损害赔偿的基础上,无论采取何种计算方法,总会出现不妥当之处。究其原因,乃在于死者的预期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世界是多变的,任何人都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更不用说将来的收入,这一点在死者为幼儿或尚未参加工作的学生时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无论采取何种计算标准,计算结果均不可避免地具有盖然性与臆想性。侵权行为法也就很难对这种不确定的损失提供相应的救济。
(三)不能解决死者近亲属缺位情形下的死亡赔偿问题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条将死亡赔偿的权利主体界定为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然而,在实践中,有的死亡受害人可能没有近亲属,这种情况不仅在死者为无名流浪者时会发生,即使在死者的身份确定的情形下也会发生(例如,死者为孑然一身的孤寡老人等)。于此情形,由于无人能够向加害人主张权利,加害人也就不必承担侵权责任,这在正义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事情。而即使法院允许民政部门这样的单位提起诉讼,但由于现行死亡赔偿制度是以死者近亲属的损害为核心构建的,民政部门的赔偿请求权也面临着诸多法理上的困窘。
综上所述,之所以近亲属缺位情形下的死亡赔偿会成为一个“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加害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害后果是受害人生命的丧失,但现行的死亡赔偿制度却是以死者近亲属的损害为核心构建的,由此导致了所有的赔偿项目均从死者近亲属的角度出发予以设计,这势必造成死者近亲属缺位时死亡赔偿的难题,同时也使得死亡赔偿金性质的界定存在困难。欲解决上述问题,一个可行的思路是,突破目前单一的死亡赔偿制度,建立多元化的生命侵权救济机制,即在死者近亲属的损害之外,把生命丧失本身也作为侵权法的救济对象。由于这一建议与传统侵权法理论存在较大的冲突,对它的合理性尚需作更加细致的分析。
三、问题之厘清:生命丧失之侵权法救济的合理性分析
(一)生命丧失之侵权法救济的批判
如前所述,在现行死亡赔偿制度中,侵权法只对死者近亲属的损失提供了相应的救济,而对生命丧失本身的救济则未予以规定。由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每一个人都享有生命权,且把生命权置于权利的金字塔之巅;另一方面,在生命权遭受侵害时,却不存在相应的民事责任机制对其提供救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状况?据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生命权属于人格权,人格权所体现之人格利益与财产权所体现之财产利益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可以用金钱来计算价值,而后者则可以。(16) 因此,任何试图以货币的方式对人的生命进行定价都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贬低。
其二,民事责任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为目的,而生命的不可挽回性及终局意义上的不可救济性决定了任何赔偿都不可能使已逝去的生命得以恢复,民法也就无必要也无可能作出对死者进行赔偿的制度安排。(17)
其三,生命权所承载的生命利益已超越了纯粹私人利益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利益的领域。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18)
上述理由看起来如此不可动摇,以至于学者无奈地认为,“在生命权遭受侵害时,私法对生命本体的救济则是无能为力的”。(19) 并劝慰民法学者:“承认民法对生命权救济的局限,既是一种理智的清醒,也是对生命的谦逊和尊重。”(20)
(二)生命丧失之侵权法救济的合理性之辩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相反,笔者认为,侵权法应当为生命的丧失提供相应的救济机制。理由如下:
首先,侵权行为是一种在法律上应受谴责的行为,法律对其谴责的直接表现,就是责任的施加。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作为一种最为严重的侵权行为,加害人显然应当为此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否则,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显失均衡的状况:即在加害人仅造成他人伤害时尚需承担侵权责任,而在造成比伤害更为严重的死亡的情形时却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这显然有悖法理。也许有人认为,在致人死亡的情形下,加害人通常要承担刑事责任,这足以弥补民事责任欠缺导致的不足。但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一方面,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并非所有致人死亡的行为均会构成犯罪。这样,在加害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下,如果民事责任缺位的话,就会造成“死了白死”这样有悖社会正义的结果;另一方面,即使加害行为构成犯罪,则由于该行为同时构成侵权,那么,此种情形应当构成责任的聚合,行为人应当同时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由于两种责任的目的并不相同,因此彼此之间并不能相互取代。毕竟,“不同层次的相关罚则应是同类违法行为之不同危害性程度的相对反映。刑事罚则只能是对违法行为多层次制裁中的最后手段,而不应作为初始的和唯一的制裁手段”。(21)
其次,虽然加害人需要对死亡受害人近亲属所遭受的损害予以赔偿,但这并不能“抵销”其对受害人生命丧失本身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因为在致人死亡的情形下,受害人生命的丧失是加害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害,死者近亲属所遭受的损害只是因受害人死亡而引发的反射损害,(22) 对后者予以赔偿并不意味着对前者也同时予以了救济;另一方面,死者近亲属所遭受的损害虽然系因受害人的死亡而间接牵连引起,但其享有的赔偿请求权却系基于身份权受侵害而产生的固有权利,并非基于继承而来。就此而言,加害人对死者近亲属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并不能“抵销”其对死者生命的丧失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再次,虽然对加害人课加侵权责任并不能使受害人的生命得以恢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生命丧失之侵权法救济的理由。一方面,侵权责任固然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但损害依其性质无法恢复的情形也时而有之。例如,油画修补匠修补一幅价值昂贵的油画,而不慎将其彻底毁坏。于此情形,恢复原状虽不可能,但仍可采取其他救济措施如单纯金钱赔偿的方法予以救济。(23) 由此推论,既然已丧失的生命不可恢复,则在恢复原状之外寻求其他救济措施应属合理;另一方面,侵权责任不仅是保护受害人权利的方法,同时也是制裁侵权行为人的方法。如果仅仅考虑受害人已经死亡而没有必要进行救济,并因此免除加害人的侵权责任的话,就使加害人逃避了应有的法律追究和制裁。而从这一角度出发,则受害人死亡的事实并不构成对加害人施加制裁的妨碍。
最后,生命固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对生命丧失提供侵权法救济不可避免地存在赔偿金计算上的困难,但这同样不能成为否定该种救济机制的理由。毕竟,是否应当提供救济与如何提供救济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后者只是一个实际操作的困难,并非原则问题。而只要某一项违法行为被确定为应承担民事责任,那么操作的困难就不是反对的理由。诚如马斯蒂尔勋爵(Lord Mustill)所言:“在几个领域内,法官们已非常习惯于对无形的东西加以估算。只要是正义的要求,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操作上的不精确应成为障碍。”(24) 这在民法上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精神利益也不能用金钱予以衡量,而曾经发生的肉体和心灵的痛苦更是无法用任何形式消除,但在当事人遭受精神损害时,我们的法律不也同样以“慰抚金”的形式对其提供了救济吗?更何况,对“生命丧失”提供救济并不意味着就是给生命定价,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详述。
四、问题之解决:建立惩罚性死亡赔偿金制度之构想
(一)惩罚性死亡赔偿金制度的意义
1.惩罚性死亡赔偿金概述
接下来的问题是,侵权法将如何为生命的丧失提供救济机制?如前所述,在传统的以“填补损害”或“恢复原状”为核心的侵权责任模式之下,该责任的设计无疑存在着较大的理论障碍。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传统理论实际上是先验性地把填补损害作为民事责任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承担方式,而在侵权行为类型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一元化的责任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这在损害无法填补、原状无法恢复的生命权遭受侵害的情形下尤为明显。而在恢复原状技穷之下,唯有寻求他法以兹救济。(25) 对此,国外可资借鉴的立法或司法经验有两种,一是葡萄牙法院所采用的模式,即把生命丧失本身作为可以用金钱衡量和加以补偿的损害,由死者的继承人行使请求权;(26) 二是美国的亚拉巴马州法院所采用的模式,即对生命权遭到侵害的救济并不采补偿性原则而采惩罚性原则,支付惩罚性赔偿金是加害人唯一需承担的民事责任,赔偿金的数额系依加害人的有责程度而定,并不考虑死者或者死者近亲属所遭受的损害。(27) 虽然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这两种死亡赔偿制度都不占主流,其制度设计也都具有一定的缺陷(例如,前者对生命直接以金钱定价,不仅有违生命伦理,而且也会产生赔偿对象界定的理论难题;而后者则将对生命丧失的侵权法救济与对死者近亲属损害的侵权法救济混为一谈,在法理上尚欠严谨),但其中所体现出的对生命丧失予以救济的独特视角却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8) 对此,笔者的初步设想是,我国可以在对现行的死亡赔偿金制度予以改造的基础上,构建对生命丧失予以救济的惩罚性死亡赔偿制度。其具体内涵是使加害人对受害人生命的丧失承担惩罚性的侵权责任,而支付死亡赔偿金则为该种责任的承担方式。在这里,惩罚性的死亡赔偿金实际上是以“赔偿”的名义对加害行为的一种惩罚,其目的不在于填补死者或其近亲属所遭受的损害,而在于惩罚和抑止不法行为人的不法行为,同时也警示和教育其他人不要出现类似的情况。此外,该惩罚性的赔偿金可以由私主体主张并获得,这使其在性质上区别于刑事罚金和行政罚款,而类似于惩罚性的违约金。
2.建立惩罚性死亡赔偿金制度的意义
首先,惩罚性死亡赔偿金能够充分实现侵权责任的抑制功能。虽然侵权责任通常通过使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方式予以实现,但填补损害显然不是侵权责任唯一的目的和功能,抑制(或预防)和惩罚也是侵权责任的重要功能。在这三种功能中,传统理论一般认为填补损害是主要功能,而抑制和惩罚则属于次要功能。(29)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侵权行为法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损害的预防胜于损害补偿;(30) 更有学者认为侵权行为法必须把加害行为的抑制作为最高的指导理念,损害赔偿应当作为达到加害行为的抑制这一目的的手段加以运用。(31)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填补损害是侵权责任的目的,但这一目的却是为了抑制加害行为的再度发生而服务的,而惩罚的目的也大抵如此,因此,应当把抑制功能作为侵权责任的首要功能,在填补损害不足以抑制加害行为的情形,则应考虑通过惩罚功能谋求对加害行为的抑制。在生命权遭受侵害的情形,由于任何救济措施都无法使已逝去的生命得以恢复,因此,侵权责任的填补损害这一功能实际上已无用武之地,为充分发挥侵权责任的抑制功能,使加害人承担惩罚性的民事责任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惩罚性死亡赔偿金能够弥补刑事处罚的不足。一方面,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存在,并非所有不法致人死亡的行为均会受到刑法上的惩罚,在刑法不足以发挥惩罚和抑制作用的情形,依靠民事罚抑制加害行为就成为必要;另一方面,即使受害人已经被课以刑事处罚,但由于现行刑法对侵害他人生命权的犯罪并未规定罚金刑,从而单纯的刑事处罚并不能完全实现抑制加害行为的功能,惩罚性的死亡赔偿金制度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死亡赔偿金固然具有惩罚性,但这里所谓的惩罚并非在加害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之外额外地予以惩罚,而是针对“生命丧失”这一特殊的损害类型而设计的新的责任形式。因此,死亡赔偿金实际上是加害人本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而并非额外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民法与刑法同步启动并不存在双重惩罚的问题。
再次,惩罚性死亡赔偿金能够使死亡赔偿制度更具有正义基础。一方面,惩罚性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目的不在于复仇心的满足,而在于通过这种责任方式实现人们追求的公平正义的观念,并通过惩罚谋求对加害行为的抑制,对社会起到教育作用。因此,该制度是建立在社会正义而并非复仇的基础之上,这使其区别于远古时代的罚金制度;另一方面,惩罚性的死亡赔偿金有利于充分体现生命平等的价值观念。由于死亡赔偿金是对加害行为的一种惩罚,因此,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就无须考虑死亡受害人所处的地域、个人职业、收入等情况,而可由法律作出统一的规定。这可以有效地消除我国现行死亡赔偿制度中城乡二元标准所带来的弊端。
综上所述,虽然从表面上看,惩罚性的死亡赔偿金制度可能会造成刑法与侵权行为法之间边界的模糊,但从实质观察,该制度却有利于实现私法对生命权的救济,起到保护生命权以及抑制加害行为再次发生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社会利益始终是最高的法律,法律必须被解释为那些有利于社会的东西”。(32)
(二)惩罚性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主体
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主体首先应是死者的近亲属。这是由死者与其近亲属之间的亲密关系决定的。也许会有人认为,由私人获得惩罚性的死亡赔偿金缺乏正当理由并会导致不当得利;但是,由国家获得这笔赔偿金就一定合理吗?事实上,由死者的近亲属获得民事罚金,不仅可以鼓励私人对法律的实现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可以更好地弥补其因受害人死亡而造成的损害,是一个较为妥当的选择。
在死者近亲属缺位的情形下,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则应赋予社会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这是由于尽管生命从表面上看属于我们每个人,但“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33) 每个生命与整个社会都具有一种无法割裂的关系,生命的存在不仅维系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维系了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关系折射出的是一种法益资源,这种法益并非个体利益,而是一种社会利益。因此,在死者近亲属缺位的情形下,应当由社会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行使该项权利。对此,人们通常会认为最适当的主体是国家机关。不过,究竟应由哪一个或哪些国家机关来行使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却值得认真思考。笔者的观点是:首先,不宜把此项请求权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因为行政机关众多,赋予哪些行政机关以请求权主体资格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每一个行政机关均可为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死者“维权”的话,不仅导致社会利益的代表混乱,从根本上无法实现立法宗旨,也会导致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危害此种新型救济机制的科学性;其次,借鉴民事公益诉讼理论,笔者认为,在我国所有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适宜代表社会利益的主体。因为自检察制度出现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面目出现,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能够有效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赋予检察机关以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34) 对于此项请求权,如果死者确实没有近亲属,则检察机关可以直接行使;但在死者有无近亲属尚不能确定的情形下,为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可由公安部门发出公告,如果在公告期内并无死者的近亲属出现,则检察机关方可行使请求权。
值得说明的是,此处所谓由检察机关行使的请求权仅限于“死亡赔偿金”,而不涉及死者近亲属之外的第三人遭受的实际损失,如第三人为受害人支出了医疗费、丧葬费等。对于后者,第三人可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加害人予以返还。此处第三人的范围并无限制,无论是自然人,还是国家机关,抑或社会组织等均可行使该项请求权。
(三)惩罚性死亡赔偿金数额的确定
由于死亡赔偿金是对生命丧失本身承担的民事责任,其目的在于惩罚加害行为,而不在于填补死者或其近亲属所遭受的损害,因此,在赔偿金的计算上,应坚持两个原则:其一,生命平等原则。虽然人的能力、职业、年龄等各有差异,但就生命本身而言,其价值和意义都是相同的。死亡赔偿金既然是对生命丧失本身承担的民事责任,在计算上就应当坚持统一的计算标准,即采定额化的赔偿方式。在具体计算上可以参照《国家赔偿法》中的规定,以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作为死亡赔偿金的数额;但同时为避免一刀切所带来的弊端,应当允许法院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以及案件的实际情况适当变通。其二,惩罚原则。死亡赔偿金的计算还应当体现出其惩罚性的特色,即在加害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可以在上述定额的基础上,再增加适当的赔偿额,以达到惩罚的目的。
(四)惩罚性死亡赔偿金的分配
在由死者近亲属行使死亡赔偿金请求权的情形下,死亡赔偿金并非遗产,故不能按继承法的规定予以分配,可以考虑死者近亲属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死者的关系等因素制定妥当的分配方案。
在死者近亲属缺位而由检察机关行使死亡赔偿金请求权的情形,则可由检察机关将该项赔偿金交由专门的公益机构用于公益事业。例如,可以根据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目的设立专门的赔偿基金,给那些贫困的、不能从加害人处得到赔偿的死亡受害人(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提供救济,以缓解他们的经济困难,彰显和谐社会的人文关怀。如果检察机关是在死者有无近亲属尚不确定的前提下行使的请求权,那么,一旦死者的近亲属重新出现,则该笔赔偿金应如何处理?对此,笔者的观点是,由于死者的近亲属为死亡赔偿金第一顺位的请求权人,因此,应当赋予其返还请求权。但是,为稳定社会秩序,该项返还请求权的行使应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例如,自检察机关取得该笔赔偿金的两年内),超过这一期限,则人民法院不再保护。
注释:
①参见《江苏高淳县民政局替流浪汉索赔被驳案透视》,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6-12-21/084411848878.shtml,发布时间:2006年12月21日。
②陈轮:《死亡流浪汉的权利再现》,《民主与法制》2006年9月(上)。
③樊斯坦等:《流浪汉被撞身亡救助站保存6万赔偿款》,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 id=224164,发布时间:2006年11月20日。
④2006年12月,江苏省常州市交警部门为一起车祸中的无名死者维权,向肇事者出具了“代为收取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费决定书”,收取肇事者支付的赔偿金共计18万元。交警部门表示将继续寻找死者家属,如无法找到,赔偿费将依法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参见人民网天津视察:http://www.022net.com/2006/12-6/565920163393948.html,发布时间:2006年12月6日。
⑤王利明:《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9页。
⑥“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死亡乃是一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取得求偿权,当被害人死亡后,其求偿权依继承而转移;“间隙取得请求权说”认为,被害人从受伤到死亡有间隙,在此间隙中,被害人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同一人格代位说”认为,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二者的人格在纵的方面相连结,而为同一人格。故被害人因生命权遭侵害而生的赔偿请求权,可由其继承人取得。参见曹诗权、李政辉:《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法学评论》1998年第5期。
⑦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8页。
⑧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728页;张新宝:《空难概括死亡赔偿金性质及相关问题》,《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王利明:《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8—569页。
⑨同注⑦,第380页。
⑩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
(11)同注⑩,第366页。
(12)[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13)参见傅蔚冈:《“同命不同价”中的法与理——关于死亡赔偿金制度的反思》,《法学》2006年第9期;姚辉、邱鹏:《论侵害生命权之损害赔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覃家壬:《论死亡赔偿金与生命权保护》,《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等。
(14)该标准已在一些地方法院开始使用:2006年6月2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并向全省各地、各级法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涉及农民工权益案件审理工作、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意见》。该《意见》第15条规定:在受害人为农民工的医疗损害、交通肇事及其他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中,凡在城镇有经常居住地,且其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的,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河南省高法全国率先规定城乡赔偿同命同价》,人民网:http://www.hnsc.com.cn/news/2006/06/23/110901.htm,新闻日期:2006年6月23日);而在2006年成都市高新法院审理的一起交通事故致死案件中,死者虽为农村户口却已在城市生活、经商了10余年,法院以城市居民的赔偿标准作出了判决。(案件引自王仁刚:《车祸赔偿,打破“同命不同价》,《燕赵晚报》2006年7月11日第B08版)。
(15)傅蔚冈:《“同命不同价”中的法与理——关于死亡赔偿金制度的反思》,《法学》2006年第9期。
(16)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转引自姚辉、邱鹏:《论侵害生命权之损害赔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7)同注(16)。
(18)曹诗权、李政辉:《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法学评论》1998年第5期。
(19)同注(18)。
(20)同注(16)。
(21)张瑞:《刑民交错经济犯罪案件若干问题之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 ArticleID=35286.访问时间:2006年11月25日。
(22)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23)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页。
(24)Chaplin v.Hicks[1911]2 KB 786 at 792,转引自程啸:《违约与非财产损害赔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
(25)同注(22),第152页。
(26)[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张新宝审校,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27)Bonnie Lee Branum.,Alabama' s Wrongful Death Act:The Jurisprudence of Accounting,Alabama Law Review,Spring,2004,issue 55.
(28)目前世界上占主流的死亡赔偿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死者近亲属的扶养费损失以及精神损害为核心的死亡赔偿制度。该模式为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的大多州等所采纳;二是以死者预期收入损失为核心的死亡赔偿制度。该模式为美国一些州(如康涅狄格州、衣阿华州等)以及日本等国家所采纳。
(29)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30)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31)同注⑦,第48页。
(32)王军:《侵权行为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29页
(3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
(34)张艳蕊:《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