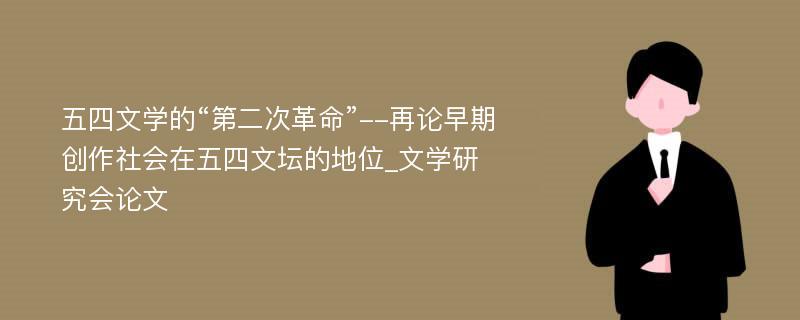
五四文学的“二次革命”——重评前期创造社在五四文坛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地位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们将创造社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背景之下,认为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它的作品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事实上,创造社主要成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密切。郭沫若在回忆创造社时曾说:“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突起的,因为这个团体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张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注:黄人影编:《创造社论》,光华书局1932年印行,第73页。)郭沫若这位未直接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诗人却一直与鲁迅并称为五四时期的两面旗帜,这里包含着我们对创造社的误读。本文试图考察创造社主要成员早期在日本的活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国内文坛之间的关系,以便重新认识创造社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一
虽然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但其主要成员的文学活动早已起步。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早期在日本对文学的探讨与国内五四文学革命是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并行发展的,他们以不同的运思方式开创了新文学早期的两大潮流——重视主观抒情的审美文学思潮与重视解剖社会和历史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潮,二者没有从属关系。1916年秋,郭沫若因与安娜恋爱唤起了他作诗的欲望,创作了白话新诗《死的诱惑》《新月》和《白云》(注:郭沫若本人对这几首诗的发表时间有不同的说法,目前学术界尚无人对其进行严格考证,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采用1916年说(见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上卷5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亦暂采此说。),这些诗后来都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其中,《死的诱惑》被译到日本后,厨川白村认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情调,是很难得”。这是最早得到国外学者首肯的白话新诗,标志着郭沫若白话新诗创作已经成熟(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2卷第110页。)。这时,胡适尚未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离他的白话诗尝试还有一年多。创造社的另一位作家张资平191年在同文学院读书时,曾写过一些总题为《篷岛×年》的见闻散记,从1914年开始,他就大量创作小品、杂感包括追求异性的经过感想,这时《新青年》(《青年杂志》)尚未创刊。正是初期这些文学活动为他的文学观奠定了基础。他自称:“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我的创作欲最初发展的时期。”而且形成了真正的文学认识:“在青年时期的声誉欲、智识欲和情欲的混合点上面的产物,即是我们的文学创造。”(注:引自《中国现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卷第545页。)这一文学观影响了他的一生。郁达夫到日本留学后就开始创作古体诗。1916年他将自己的诗作结集为《乙卯集》(未刊行)。在进行古体诗创作的同时,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郁达夫也开始了小说创作的尝试。计有1916年写的《金丝雀》,1917年的《樱花日记》《相思树》《芭蕉日记》,1918年的《晨昏》,1919年的《两夜巢》,以及“一篇记一个留学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恋爱的故事”等,这些作品尽管不够成熟,但这种文学尝试比国内新文学作家要早得多。毫无疑问,早期这些文学尝试,同样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准备了条件。
1917年在“五四”文坛上是值得纪念的,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橥义旗向古典正统文学发难,随后陈独秀发表充满火药味的《文学革命》,声援胡适,五四文学革命正式开始。但尚在日本求学的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对此并不了解。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爱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的尝试。1918年,《新青年》全用白话,五月,鲁迅发表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五四文坛第一篇白话小说,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6卷第238页。)。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文学革命为先导走向深入,《新青年》成为全国著名刊物,大受读者欢迎。这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都在日本高等学校从事非文学专业的学习。张资平因回国参加政治运动,大约阅读过《新青年》,但他对《新青年》很不满,认为“浅薄”,张资平的这一态度后来成为创造社成员的共识。张资平回到日本后,在博多湾海岸与郭沫若(已三年没有回国)见面,二人谈起了国内文坛,他们这段谈话更充分地说明了他们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态度:
(张资平生气地说)“国内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
(郭沫若)“《新青年》怎么样呢?”
(张资平)“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
其实,1918年正是新青年最为辉煌的时期,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文章都以雷霆万钧之势摇撼着古老的文明,可这丝毫也引不起他们的关注。于是,他们仿效日本文学界的样子决定“出版一种纯文艺刊物”,“采取同人刊物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郭沫若将这次谈话称为创造社“受胎期”(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2卷第48页。)。从这次谈话我们可以看出,创造社的“受胎”并未受到国内文坛的直接影响。相反,创造社在萌芽期就带有一种挑战者的姿态。他们决定用白话出版刊物,虽然看上去像步《新青年》的后尘,其实完全是他们自发的主张,并未受《新青年》的启发。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用白话进行创作,这时选用白话出版刊物是顺理成章的。另外,他们利用白话,只是为了进行文学创作,他们准备出版的刊物,是纯文艺刊物,没有明确的文明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目的,这与《新青年》团体提倡白话是不同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利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所包含的划时代的意义。后来的文学史家将他们的白话文学创作不加分别地与国内五四文学革命中的白话文运动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恰当的。
郭沫若与五四文坛第一次正面接触在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之后,为了响应这一爱国运动,郭沫若与陈君哲、徐涌明等人成立“夏社”,主要收集日本报刊上诋毁中国的言论和资料,译成中文,同时自己也撰写一些排日的文字,油印后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刊。“因为做这种义务的通讯社工作,国内的报纸便至少不能不订一份”,于是他们就订了上海的《时事新报》。《时事新报》创刊于1907年12月,其文艺副刊《学灯》创刊于1918年3月,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著名副刊,主要发表新文艺创作。正是从《学灯》上,郭沫若第一次读到了国内的白话新诗。他说:“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什么人上欧洲。诗里面有‘我们叫得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当稍有出入)。我看了不觉暗暗诧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么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2卷第64页。)郭沫若便开始向国内投稿,随即进入诗歌创作的丰收期。自然我们不能否认康白情这首诗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使他对白话诗产生了自信,对其诗歌的内容和风格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时常被称为五四时代号角的《女神》,其实并未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什么实质性的联系,其中有些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写出,这明显区别于《呐喊》。这说明《女神》中的早期作品所具有的现代性,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依靠郭沫若特有的禀性自发形成的。《女神》对自我个性的张扬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个性的呼唤在某些方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只能说明他们在反封建问题上的共同要求。呼唤个性自由,固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特征,却并非它独有。文学对个性的呼唤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是西方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即使在中国文学史上,对个性的呼唤也并未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始终。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女神》主要发表于1919年北京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其时新文化运动已近尾声;它结集出版于192年,这时《新青年》团体已经解散,文艺界开始进入“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期,被称为“号角”的《女神》在精神特征上与国内文坛并不同步,这也说明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源流。郭沫若并不以小说创作著称于世,然而他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起步较早。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四个月之后,郭沫若在日本创作了小说《骷髅》,投往国内的《东方杂志》,未被采用。《骷髅》采用了欧洲旧体小说体裁,借一个日本学生之
口讲述了一个盗奸女尸的故事。小说采用意识流手法,描写了人的潜意识和幻觉,已明显具有现代小说的特征,如果它得以面世的话,在1918年的文坛上,它会以其与《狂人日记》迥异的风格,成为浪漫抒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遗憾的是,对国内文坛来说,像《骷髅》这样的不速之客是不受欢迎的,它那副暴露情欲、无视社会使命的“创造脸”也不是国内进步文人所期待的,更何况《东方杂志》又不是一个激进的刊物,《骷髅》被拒之门外,也就可想而知了。小说没发表,此后也没能面世,它也就不再具有文学史意义了,但对研究郭沫若文学观的渊源是非常重要的,他预示着在与国内文坛接触以前,郭沫若的文学观已具刍形。
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在日本的文学尝试,从时间上看,并不晚于国内的新文学作家。由于他们远在日本,所学又非文学专业,所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准备阶段。在他们准备过程中,国内文学革命捷足先登,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从道理上来讲,郭沫若等人与胡适是同道,胡适们做了他们想做而未及做的事情,因此他们应该联手合作,共同拓展文学的新局面。可事实并非如此,胡适们倡导创立的新文学与郭沫若们期待中的新文学大异其趣,引起了郭沫若等人的强烈不满。为了实现自己的构想,他们只得将胡适们作为对手,重新掀起一场革命,以创立自己的文学天地。
二
创造社一诞生,就被看作是一支“异军”,一方面它们四面突围、频频树敌,另一方面也使自己陷入新文学家们的“围剿”之中。创造社的独异,显然并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样,仅仅由于其浪漫主义风格和突出的抒情特征,更重要的是,创造社在当时文坛是“无根的”入侵者,它与发难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之间没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在看重门派的中国文人中,创造社成了散兵游勇。有人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一起称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双生子”,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文学研究会是文学革命的嫡传弟子,那么创造社就只能算得上是一个“野生子”,这一特殊身份,注定了它必将成为既定秩序的破坏者。文学研究会和稍早一点的新潮社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立的,其中有些成员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文学研究会中后起的新作家如冰心、庐隐等也公开表示新文化运动对他们的影响。新潮社与文学研究会成立后都直接实践了文学革命的主张,正如鲁迅所说:“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6卷第239页。)创造社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就没有这种直接的血缘关系。它的成立是对其成员在日本几年间的文学活动的总结,也说明了这一重视主观抒情的审美文学思潮已具备了与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相抗衡的力量,是对五四文学功利主义倾向的一种反拨。司马长风在他的文学史中推测说,如果郭沫若接到文学研究会第一次发出的邀请,那么,就不会有创造社了。而我的推断与此不同,我认为如果没有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绝不会有文学研究会、新潮社,但未必不会有创造社,至少会有《沉沦》《冲积期化石》和《死的诱惑》。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的矛盾,过去常被理解为宗派主义情绪与相互之间的误解,其实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创造社从“受胎”的时候起,就具有明确的叛逆倾向和革命意识,对此郭沫若曾坦诚地指出:“他们以‘创造’为标语,便可以知道他们的运动的精神。还有的是它们对于本阵营的清算的态度。已经攻倒了旧文学无须乎他们再来抨击。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却是所谓新的阵营内的投机分子和投机的粗制滥造,投机的粗翻滥译。……他们第一步与胡适之对立,和文学研究会对立,和周作人等语丝派对立……”(注:黄人影编:《创造社论》,光华书局193年印行,第74页。)由此可以看出,创造社的一次次发难,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源于郭沫若等人对文学的理解与对文学研究会诸君的文学观有着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分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创造社在理论上的革命意义。首先他们对文学本质有着不同的见解。作为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家,茅盾对文学本质的论述具有极大的代表性。他认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的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注:《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8卷第9页。)在茅盾的理论构想中,人的解放、个性解放这些重要命题,在“社会”、“民族”这些群体概念面前被消解,最终使以个性解放为目的的文学,成为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工具。郁达夫及创造社诸君(前期)却坚定地守护着个体的本位立场,强调“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创作要本着“内心的要求”。谈到作家的责任与文学的审美问题时,茅盾说:“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注:《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8卷第414页。)“不幸近来的文艺者,捧出了美的神坛,做白话文的人们大家来讲究美,于是已经打破了的旧观念忽又团结……随成了今日的假唯美主义横行一时的局面。”(注:《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8卷第416页。)在论及西方唯美主义作家时,他对王尔德、康南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他们“异样鲜艳的‘唯美’之花”对人类没有什么用处;而郁达夫认为:“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自然的美,人体的美,人格的美,情感的美,或是抽象的悲壮的美,雄大的美,及其他一切美的情愫,便是艺术的主要成分。”从这种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观点出发,他进而认为艺术“没有国境的差别,没有人种的异同”,“现代的国家是和艺术势不两立的”(注:《* 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5卷第67页。)。这与茅盾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考虑文学问题也是相互对立的。然而茅盾的观点为当时大多数人所认同,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承传,在当时的文坛上享有“正宗”地位;创造社却不同,它是世界文学与日本文学这一大背景的直接产物,它在五四文坛上是个“外来户”,“为艺术而艺术”、“唯美派”、“才子”这些恭维的称号也都包含着冷嘲的意味。分歧如此之大,地位如此不平等,我们不必指望他们能够如胶似膝地共度蜜月了。
在选择和吸收西方文学的营养时,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在“胃口”上迥然不同。这种不同的价值选择,在当时文坛上形成了一种对立与互补关系。五四时期,文学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文学的西化——由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学向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学过渡。过渡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家直接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进行创作;另一种是译介西方的作品,作为样本来指导国内的作家——尤其是那些不能直接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青年作家。但这种译介是有目的的选择,而不是盲目的引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作家(或理论家)在广泛接触了西方各种流派的文学之后,从中选取在他们看来于我们民族“最有用”的作品加以译介、推广,而不一定选取他们个人最激赏的作品。鲁迅在日本译印的《域外小说集》就是明显的例证。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最欣赏的是“争天拒俗”的“摩罗诗人”,可他选择的作品大多是被压迫的弱小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茅盾在1920年写的《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一文中指出:“西洋新文学杰作,译成华文的,不到百分之几,所以我们现在应选最要紧要切用的先译,才是时间上人力上的经济办法”;“复次,我认为在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合于我们社会与否的问题,也很重要。”既然“合于我们社会与否”成了一个重要标准,那么像惠特曼的诗歌,日本的“私小说”,俄国的“多余人”以及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等,这些突出个人情感和个体灵魂甚至变态魂的作品就被堵在国门之外,而创造社作家的创作,正纠正了这一倾向。郭沫若以“泛神论”思想为基础,借鉴惠特曼的诗风,一扫早期白话新诗缺乏想象力和过于浅白直露的毛病;在小说方面,郁达夫借鉴了以佐藤春夫为代表的日本“私小说”的笔法大量描写“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又对俄国及流行于日本的“多余人”文学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作出“生则与世无补,死则与世无损”的中国式的“多余人”形象,再加上张资平对日本自然主义的效仿,使现代小说在性爱心理和病态心理的描写上走向了深入,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女神》《沉沦》与《冲积期化石》发表后,没有引起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支持和关注,正说明这不是他们所号召和期待的作品。但是,20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因为有了“创造社”这个“外来户”,才为性爱文学打开了一个缺口。
三
在人格建构上,创造社诸君更是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取代了当时文坛上盛行的“君子”、“圣贤”人格,将知识分子的拯救意识,转换为对自我价值的确立,这是创造社进行文学革命的精神支柱,也是最具魅力的地方。在五四文坛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与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作家都极看重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们极力维护着自我人格的崇高与正直。虽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受到严厉的批判,但传统文人所崇尚的圣贤人格与君子风范依然成为他们塑造自我人格的典范。以“内圣外王”为特征的圣贤人格,注重内在的修养与外在的事功,孔子所谓“修己以安百姓”就点明了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一致与和谐。这与五四时期渴望挽救民族危亡、改良中国社会人生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取得共鸣,使他们在反传统的同时又难以抗拒这一传统人格的魅力,便不自觉地认同了传统士大夫的人生选择。不过作为一介书生,地位卑微,他们难以介入军阀间的纷争,也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晋身之阶,不能“兼济天下”,为了“事功”,他们迫不得已选择了文学,自然会不遗余力地抬高文学的地位,文学遂成为其“事功”的一部分。后来有不少作家一旦有机会跃马疆场或掌握权柄便会毫不犹豫的放弃文学,盖出于此。理论上对“文以载道”的反对实际上只是反对载孔孟之道,这就难怪有人说中国新文学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了。鲁迅谈到为什么写小说时,曾坦白承认:“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注:《鲁迅全集》第4卷512页。)那么对于鲁迅来说,个人生平遭际都可深深掩埋,而社会的堕落与民族的沉疴就固执地占据着他的创作视野。到30年代,他放弃小说创作极力写杂文,也是因为他发现杂文比小说于社会更有利。与圣贤人格相类似,传统的君子风范深明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当时许多作家无论个人生计如何困顿,他们始终将目光投向社会,去关注芸芸众生的生存境况,去探讨民族与社会的兴衰与出路,很少在作品中直接倾诉私人化欲望,更不愿将个人隐私轻易在作品中泄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们把文学与某种崇高的历史使命联在一起时,他们不会因为损害文学而惋惜,相反他们以文学的这种依附沾沾自喜。当时不少作家
津津乐道自己作品的社会功利价值就反映了这一倾向。创造社作家却全然不同。他们似乎不顾及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在自己的传记或创作中对那些在中国人看来不道德的隐私加以详细的描述甚至夸大渲染,赤裸裸地表白自己内心的阴暗和个人的不幸,在创作中也不以“圣贤”“君子”自居,文学成为抒发内心感受的一种手段。郁达夫公开表示“文学是天才的创作物”,郭沫若认为“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张资平干脆将文学看作性欲名利的产物。它们从不隐讳个人对异性和金钱的渴望,于是“穷”和“色”成了他们的文学的主题——这正是不少作家所鄙视的。由此不难看出,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而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颠覆者。当年在博多湾海岸,郭沫若与张资平准备出版刊物时,他们心中就有强烈的冲动——取代国内文学的权威,构建自己的文学王国。在郁达夫起草的《〈创造季刊〉出版公告》上,直接把矛头指向“垄断”国内文坛的“偶像”,正说出了他们真实的愿望,只是不够含蓄而已。文学研究会作家很敏锐的感到这股异己力量对自身正统地位的冲击,也及时地作出了反映。历史的发展,常常使智者陷入尴尬的境地。以反传统为己任的《新青年》作家群与文学研究会作家,在人格上不自觉地重复着他们的批判对象,倒是在反传统问题上不如文学研究会激烈的创造社成员们,轻而易举地削弱了与传统人格的联系。
在创造社成立前的国内文坛,实际上是“人”的觉醒压倒了“文”的觉醒。从鲁迅的“遵命文学”到新潮社的“有所为”而发,再到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文学一直力不从心的充当了社会发展的开路先锋。尽管在理论上对文学自身的特质曾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但在具体的创作中,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例如,在文学创作的题材问题上,由古代的以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能事的贵族文学转向描写下层社会的国民文学,这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一系列文章中早已解决的问题,在实际操作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其主题似乎必须是崇高的、有价值的,说到底,即用普通人的生活题材反映圣贤者们的思想和心态,这是圣贤人格与君子风范对作品造成的直接影响。创造社的意义在于,它没有给文学套上金光闪闪的锁链,而是把文学的审美特征与个体生命的情感相结合,它不是居高临下把文学充当挽救社会的灵丹妙药,而是感同身受地展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它标志着文学意识的再一次觉醒,是五四文坛上的“二次革命”。
创造社是世界文学背景下的直接产物,它的诞生加速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1921年创造社成立后,其主要成员陆续回国,他们从世界文学这一大背景下进入了中国这个相对狭小的舞台。尽管他们大都已是名满天下的作家,但他们的个人生活异常艰难,又加上国内政治黑暗和文坛的纷争,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文学观,从1925年开始,他们转向了革命文学,基本放弃了最初的文学主张,走入极端功利主义的泥淖,文学创作随即衰微。
标签:文学研究会论文; 郭沫若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茅盾全集论文; 创造社论文; 郭沫若全集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读书论文; 女神论文; 鲁迅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郁达夫论文; 二次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