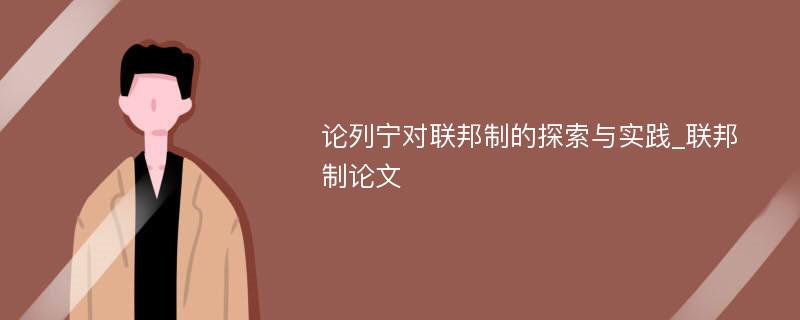
论列宁关于联邦制的探索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邦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列宁关于联邦制的探索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确定了“自愿、平等、合作”的联邦制原则缔建了苏联,并提供了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的建立国家结构形式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联邦制 国家结构 民族 联盟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采用什么国家结构形式建立新国家,列宁并无先例可援。对此,列宁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始而反对联邦制,主张单一制,继而重新认识联邦制,终而全力实行并捍卫联邦制,个中情由,学界鲜有力说,本文拟就此一论。
一
1903—1913年期间,列宁反对联邦制,主张单一制。
1903年2月,列宁针对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在其宣言中提出的在未来俄国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要求[①],明确提出,联邦制的前提是存在自治的民族的政治整体,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提出民族自治的要求。“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所有民族中尽可能广泛的工人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舞台上为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②]以后,列宁又多次说:“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决反对联邦制的和分权制的。”“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③]直到1913年12月,列宁在给邵武勉的信中谈及这一问题时仍坚定地说:“我们反对联邦制……你不要代我作决定,不要以为你有‘权利’要求成立联邦”。[④]
这一时期,列宁反对联邦制,主张单一制(即他所称的“中央集权制”),原因何在?我以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列宁曾说,“马克思关于公社(即巴黎公社——笔者注)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⑤]。考察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经验的论述,他确实没有谈及什么联邦制国家形式,他只是说公社这个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国家形式雏形的东西“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⑥]列宁同时认为,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联邦制的[⑦]。恩格斯本人在其《198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对现在的联邦制德国进行补充和改造”,“因此,需要单一的共和国”[⑧]。第二,这与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和1903年的代表大会上,崩得派(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曾要求按联邦制原则建党,以求得同党的中央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从而保持该派不受约束的行动自由。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坚决反对这一要求,主张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因而“代表大会坚决反对把联邦制作为俄国党的建党原则”[⑨]。这一时期,列宁把联邦制看作同民主集中制相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国家制度,他说:“我们无条件的拥护民主集中制,我们反对联邦制。”[⑩]第三,列宁认为,从无产阶级利益和经济发展角度考虑,实行联邦制也是不利的。他说,集中制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一国之内各民族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教育组织等之中打成一片。”[(11)]而联邦制却“把独立性和隔阂合法化,使之提高为原则,提高为法律。”[(12)]从经济上看,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集中统一的大国,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为了发展经济,更应反对中世纪的割据主义,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达到尽可能紧密的联合,如此,方有利于无产阶级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13)]1913年12月,他更明确地说:“我们在原则上反对联邦制,因为它削弱经济联系,它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不适合的形式。你要分离吗?如果你能割断经济联系,或者说得确切些,如果‘共居’所引起的压迫和纷争会损害和毁坏经济联系的事业的话,那么你能滚开好了。”[(14)]第四,列宁认为,民主集中制较之联邦制更能使地方上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民主。他说:“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更多。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地方、省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15)]正是在上述思想支配下,列宁这一时期否定联制国家结构形式。
但是,列宁在对联邦制提出异议的同时,丝毫也没有固执地认为无产阶级在任何条件都必须坚决反对联邦制。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6)],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开始重新认识联邦制。
二
这一重新认识(探索)的过程从1914年起到十月革命以前,大约持续了四年时间。
1914年初,列宁针对俄国资产阶级起劲地反对乌克兰人的最低纲领——实行联邦制和乌克兰自治制,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联邦制’即没有妨碍北美合众国的统一,也没有妨碍瑞士的统一呢?为什么‘自治’并没有妨碍奥匈帝国的统一呢?为什么‘自治’甚至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加强了英国和它的许多殖民地的统一呢?”“为什么不能通过乌克兰的自治来加强俄国的统一呢?”[(17)]这说明,列宁此时开始重新探索,重新认识联邦制了。到1916年初,他又说:“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在此基础上,列宁的看法又前进了一步,他说:“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18)]这里至少有两点思想比较明确。其一,列宁认为,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与其在尚未消除不平等的前提下建立单一的中央集权制,那不如先实行各成员国或民族政体褓有相当独立性的联邦制,在逐步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再向中央集权制进渡;其二,在一个尚未消除民族不平等的多民族国家里,无产阶级要求建立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新型国家,通过联邦制完成过渡是唯一的途径。到1917年6月,列宁更进一步指出:“甚至农民代表大会(即1917年5月全俄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笔者注)在这个问题上都比较接近真理,它谈到要建立‘联邦’共和国,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共和国不想用新的或旧的方式压迫任何一个民族”[(19)]。以上这些思想表明,列宁这一时期已不象前一时期那样坚决反对联邦制了,但也未决定实行联邦制,当时的党内也未对此形成一致的认识,1917年俄国党的四月代表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谈到民族分离权,谈到了在统一的国家范围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谈到了把反对任何民族特权的基本法律写进宪法,就是一句也没有谈到未来的俄国实行联邦制度问题[(20)]。在同年8—9月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专门研究了民族问题与国家结构的关系,探讨了马、恩等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观点,认为联邦制在原则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他认为联邦共和国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和共和国的过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正因为如此,恩格斯“丝毫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单一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21)]。恩格斯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对国家的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却非常细致地去分析那些过渡形式。以便根据各个不同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估计某一个过渡形式是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22)]。这就是说,在这期间,列宁虽然原则上还是反对联邦制,但同时也不否认在个别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采用联邦制的可能性,并且还注意到了民族问题与国家结构形式的关系,认识到了联邦制是向民主集中制过渡的一种形式。
促使列宁这一时期对联邦制的认识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两点:一是为了反对当时政府的需要。当时的政府对乌克兰、芬兰的联邦、自治要求严加拒绝,当时的资产阶级也起劲地反对乌克兰、芬兰的联邦、自治主张,大肆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压制、剥夺少数民族的民主、平等权利。为了反对政府的反动政策,为了团结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一切力量,列宁略微在策略上改变了一下对联邦制一味否定的看法。二是对国家学说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列宁这一时期对马克思、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关于国家的学说作了系统研究,发现并认识到联邦制并非想象的那么坏,在特殊条件下,即“民族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23)]的情况下,联邦制可以作为一种“例外”,一种向民主集中制的“过渡形式”。这一探索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为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行联邦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认识基础。
三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建立新型国家的实践中努力实行并坚决捍卫联邦制。
革命的胜利使以解决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为防止分裂,把国内“其它民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少数民族同俄罗斯民族组成统一的国家,列宁认为,正确的途径“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愿的协议”[(24)]。
1917年11月,苏维埃政府发布《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12月,发布《告乌克兰人民书》提出了关于俄国各民族自愿和真诚联盟的新的民族政策[(25)],1918年1月初,列宁起草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第一次提出把联邦制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方案,宣布“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主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26)]。同年七月,《宣言》全文载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之中。宪法明文规定,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同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一起,“都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唯一的根本法”,这个根本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27)]。至此,列宁所确定的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便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
1919年2月至3日,列宁在他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又明确地说,在民族问题上,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要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完全解放殖民地民族和其它被压迫的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从而与之建立起“自觉自愿的联盟”。[(28)]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肯定了列宁的这一联邦制思想,在通过的新党纲中写道:“党主张按照苏维埃形式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联合,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一种过渡形式。”[(29)]从此,列宁不仅在俄罗斯决定实行联邦制国家制度,而且还将这种制度运用于俄罗斯和其它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上,并将此写进党纲,在一定时期内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之一。
与此同时,列宁还确定了建立联邦制国家的基本原则,即“自愿、平等、合作”原则。
从1919年至1922年,苏俄在列宁领导下,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联盟,而最终建立了苏联。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成立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相互关系问题,列宁因病未能出席,但他写了便笺给加米涅夫,语气十分坚决,“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并要求“要绝对坚持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绝对!”[(30)]全会完全支持列宁的立场,通过了以列宁的建议为基础写成的新决议。
这样,12月30日,全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发表了苏联成立宣言,通过了苏联成立条约,指出“这个联盟是个平等民族的自愿了联合”,“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31)]。从而贯彻和捍卫列宁主张的联邦制原则。苏联正式成立。
十月革命后,列宁为什么如此坚决地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实行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呢?我以为系如下因素使然。
其一,国内因素。十月革命后,俄国各民族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他们大都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有一套与苏俄政府平行的政权机关,这种状况决定了列宁实行联邦制不仅是使各民族由分散趋于接近、联合的巨大进步,而且是各民族共和国已有的条约、协议联盟的顺乎自然的发展。并且,各民族人民在推翻旧政权,巩固新政权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因而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渴望反映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各民族共和国对待“自治化”方案的不同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就决定了十月革命后各民族联合的方法比以前想象的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联邦制,既尊重了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又有利于打击和克服大俄罗斯主义的残余。
其二,国际因素。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帝国主义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武装干涉,另一方面积极支持苏俄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正是他们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如果不建立各民族统一的国家,就会削弱反帝力量;如果照单一制立国,又会造成少数民族的误解,使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受到民族关系的制约。实行联邦制,则既可以加强反帝和粉碎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力量,又可以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信任和联合;另一方面,当时正值东方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广泛兴起,民族殖民地问题特别尖锐之时,他们都寄希望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如列宁所说:“他们大家仰望着一颗明星,仰望着苏维埃共和国这颗明星。”[(32)]因此,苏联在处理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时,不仅要正确对待民族关系,而且要面向东方,使苏俄和其他独立共和国联合的方式成为一种典范,直接影响和鼓舞东方被压迫的民族。
其三,实践经验因素。列宁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各民族国家的建设方面的实践证明,联邦制并非以前想象的和俄国各族劳动人民在经济上接近的目的那样大的抵触,如果联邦制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实行的,它甚至和这些目的并不冲突。正如他1920年所说:“无论在俄罗斯联邦同其它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中,或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同从前既没有成立国家又没有实行自治的各民族……的关系中,联邦制已经在实践上显示出它是适当的。”[(33)]
四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一)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结构形式的探索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形式的学说,他不仅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确立“自愿、平等、合作”联邦制原则,而且将理论付诸实践——用联邦制原则缔建了苏联,功不可磨;(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结构形式的探索和实践昭示我们,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采用什么结构形式立国,不能先定,必须从实际出发,相机而行,因势利导,否则,欲速不达。(三)我们应认识到,列宁最后实行的联邦制,并非他的最终目的。即使在他坚决地实行和捍卫联邦制时,他也只是将它当作民主集中制的“例外”,当作“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34)](四)我们还应认识到,由于联邦制理论上的欠成熟,时间上的仓促和列宁的早逝,列宁实行的联邦制并非尽善尽美,也不具有普遍性,它只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之一。
注释:
①②⑨(12)《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89、89、228、248页。
③(11)(13)(17)《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48—149、61、148、351页。
④⑩(14)《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379页。
⑤⑦(15)(21)(23)《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50、68、70—71、68—69、68、6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41—64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5—276页。
(16)《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29页。
(18)《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7页。
(19)《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3页。
(20)(29)《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46—447、535页。
(24)《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70页。
(25)《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40—142页;《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版3—4页。
(26)《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24页。
(27)《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89页。
(28)《列宁全集》第3版第36卷第101页。
(30)《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16页。
(31)《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73、79页。
(32)《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88页。
(33)(34)《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62页。
标签:联邦制论文; 列宁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国家结构形式论文; 民主集中制原则论文; 列宁全集论文; 苏维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