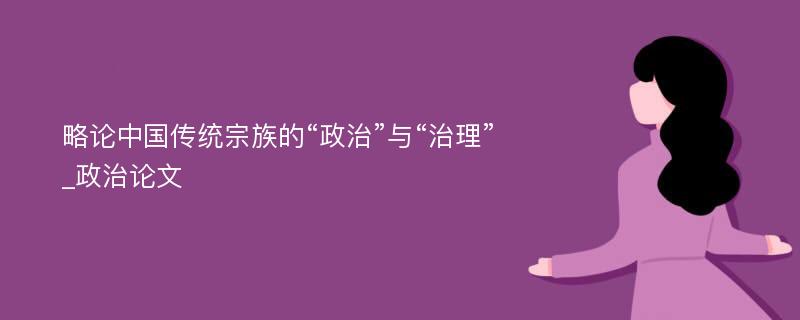
中国传统宗法“政”、“治”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法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牟宗三先生曾将政道、治道分别定义为政体的基本原理与政府基本职能之运作,这在总体上是确当的。“政”道是关于社会国家生活的基本原理法则,是如中国古儒所说的天、道、理,“治”道则是关于管理社会国家生活的基本方法手段,是如古人所说的法、术、势。
一
中国传统政治(尤其是“政”道)要义可谓博大精深,然在我看来,内圣外王、以德配天是其基本原理,家国一体、以家推国是其基本模式,伦理政治、仁政德治是其基本学理。
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分别以自己的《理想国》、《政治学》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各有所偏重的立场上,表述了对国家的乌托帮式的民主理想,这是一种大同的民主的国家。应当说这种对“政”道的最高问题的揭示在东方早期思想中亦不缺。孔子在托始于三代的复古面貌之下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这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礼运篇》)天下为公即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某人某夫之天下。那么,何种人才能主持天下之政道呢?只有那些替天行道、奉天承运者,他们即地上的君、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尽管也有“大同”,但已大大不同于古希腊的那个“大同”,这里不是民自作主,而是君王为民作主,故在对政道的最高理解上一开始东西方就存有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两种政治生活方式的差别)。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谁能当、凭什么当、通过什么渠道当这世间上的君王?孔子认为是以德配天,“有德者禀受天命”,他的逻辑次序是先有德后受天命而作君王。在他看来天有天道,有德者能得天道,得天道就能行王道与人道,于此又有两种可能,此有德者是天生的还是可以努力得来的?孔子倾向于后者,主张“下学而上达”,进行道德的努力去与天道感应,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由践“天道”之“仁”而及“圣”(君子),由践仁而外化为执“礼”,执仁、有礼必天下归顺而成王,这就是成王行天道的政治原理或逻辑。中肯地说孔子的这种思想内在地含孕着对宗法血缘世袭政治制度反叛的种子,甚至也包含着只有人民拥护才能有资格得天下的思想。对于后者,孟子作了进一步发挥,他提出了一个王霸之别,以德得天下者为王,以力得天下者为霸,以德得天下就是只有得到人民拥护的王才是合法的、替天行道的王,否则,即使以武力得到天下也无合法性,这就是孟子“天命说”中值得注意的合理内容(“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不过,孔孟对“内圣外王”、“以德配天”的这种理解逻辑到了汉代董仲舒那里则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以至整个逻辑次序被倒了个。在董仲舒那里,不是以圣定王而是以王定圣,“天以天下于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尧舜汤武》)君权来自于天,天有德,君有天之德,故君为圣。这样就以王权本身来注疏圣与神圣,所谓成者王败者寇就可以被进一步注疏为:成者为王为圣,败者为寇为士。一旦黄袍加身,就是真龙天子,圣明英主。所以,霸亦王亦圣,马上夺天下,马下治天下。董仲舒的这种政治哲学思想以后就一直流传与支配着中国的政治生活,并反复为封建帝王们所实践。天下为武夫的囊中物盘中餐,争来夺去,总是为的一家之利,天下不再属公,为天下亦不再是为公。不过,要改朝换代,总还得有点为公、为民才行,这才能换来民众的支持,才能替天行道南面称王。
这样,中国传统政道原则中就内含着致命弱点:a、 国不是民之国而是天之国,这就注定了民不能成为国之主,且这个天之国中人注定有人格等级差别,有天之子有天之奴,天之子替天行道牧羊民众;b、 一般的说以德配天、仁者得天下并不为过,但问题的关键是谁来判断、以何标准判断这仁否德否,如果说不是以民与民意,而是以一种高悬于民众之上的不可知、但却可以给予某种血缘关系解释的天与天意作为这至尚的判官,那么一切均有可能被披上仁与德的外衣,民众不仅在理论上会被剥夺一切权利,在实践中也没有任何机制能够有效地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c、既然以德配天可以解释为成者为王为圣, 那么这就意味着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为了夺取权力与巩固权力,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目的就是一切,手段没有任何规范性可言,即亦无任何规范性的“治”道可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不同意牟宗三先生的下述看法:中国数千年的政治生活完善了治道,空悬了政道,甚至治道发展至明清时期已臻至善,存在的问题只是治道与政道间的悬隔,治道得不到后者的支持,治道只是完善了一个君权之政道。治道总是政道治之道,因此它总是政道的,两者间不存在根本性的阻隔,中国封建社会确实发展起一套治国之策,这些治国之策也确实有时受到封建制度的根本规定而未能充分尽其用施其效,不过,这些治道在根本上是为维护那个统治制度与统治秩序服务的。政道乃治道之本根、灵魂,治道乃政道之具象与实施,彼此互为表里、互为依托,西方马基雅弗里在《君主论》中喊出的“政治无道德可言”似乎表明政治只有权术治道而无政道,其实不然,“政治无道德可言”之背后存在的正是君主专制制度这一政道。一切治道都以政道为核心并围绕其展开。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封建社会中之治道在另一个角度上看是说有则有,说无则无,说其有是因为其确实有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法,——不管这方法是什么,说其无是因为其又确实无定型或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它在根本上是人治,人治变化无常,行无定法,故恰恰是无治道。严格地说,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只是封建的治道而不是现代社会的治道,不能指望用现代民主政治之道去简单地接通传统的封建治道。封建的政道与其治道均是应当被彻底批判的。现代民主政治应当有其相适应的社会运作机制与方法。
内圣外王、以德配天,还只仅是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说明“政”之道的合法性,一方面它需要进一步展开丰富,另一方面它需要具象化,这就有赖于它的机理模型:家国一体、以家推国。
二
家庭是人社会性与自然性的连接点。无论是作为类的还是个体的人总是通过家庭进入社会的,按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家庭是人类最初出现的社会关系。家庭作为自然关系是以两性为基础的血缘关系,作为社会关系则是社会成员间的公民关系,作为血缘关系总是存在着血亲自然等级,因而,家庭成员作为家庭血亲关系总是存在客观的不平等,只有进入社会领域,家庭成员间的血亲自然等级才能消失,彼此间才能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存在,这就意味着若将家庭中的血亲关系带入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生活中就必然会出现等级与不平等,而人类最初的社会国家生活恰恰正是基于家庭血亲关系基础之上的,因而,最初的社会国家生活中就不可避免地存有等级与不平等。中国古代社会与其它民族相比,不仅表现出将家庭生活及其关系融合进国家生活的高度自觉性、圆通性,更表现出这种融合存在时间的悠久性,乃至全部国家生活的结构与运作模式均是以这“家”为模式,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小,家国一体。这样,家国就有“天然”的一致性,社会的规范准则、身份地位原本同于家庭的,人们无须为在社会与家庭之间的角色变化而操心,角色及其要求都是单一的,这确实是社会政治生活设计中的大智大慧,既简单又圆融、实用。而这也正是中国封建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的最隐蔽的秘密所在。
中国古代的政治始终没有从家庭(族)秩序中独立出来,相反,它不断地从后者得到滋养,不断地强化与后者的联系。从先秦到宋明,这种趋向显得极为明显。中国古代的国家首先由血族结构上升而来,故一开始就带有宗法的特征。华夏三代时,家国实为一体,国就是自然的家族(王族),家族的秩序就是国的当然之秩序,家族之血缘关系同时也就兼有政治关系的意蕴,族长在家族中所处的血缘环节与其政治地位是相一致的,这样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上下,也就同时成了政治生活中的尊卑高低关系。至春秋时期,宗法国家内部矛盾加剧,天下大乱。孔子疾呼:“克己服礼”,实乃是要在纷争之世重新确立基于宗法之上的国家政治秩序。其学理的核心是由“孝”至“忠”、由“亲亲”至“尊尊”。“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孝,礼之始也”(《左传·文公二年》)。“孝”原本是亲子关系,它与“慈”相对,二者的统一构成完整的相互责任关系,秦汉以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表达对祖宗的敬服,一是表现为对在世父母的奉养之责,但至后来“孝”则与“忠”相通。“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亲是为了忠君,“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以孝事君,则忠”(《孝经·士》)。这样,移孝作忠的学理逻辑就将亲子关系直接移植到君臣关系上来。“忠”在先秦之时,泛用于一般待人接物,其意旨在于尽力、真诚,它可包括对君负责、对民负责、尽职尽力等。然而,由于移孝作忠,使忠原来的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孝是亲子关系中的下辈对上辈的单向度的责任,故移孝作忠就将这单向度的责任移到政治关系之中来,使忠成为仅仅凸现臣民对君主服从的政治范畴,更由于孝是一种基于天然血缘关系上的近乎绝对的责任,这种忠也就自然地演绎出它的绝对性。由孝至忠即为由亲亲至尊尊,通过对家长权威的强化与维护,来强化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与尊严,君臣父子,君权即为家长权,这才有为西人所难以理解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谜面。由孝作忠,孝反过来又被忠所注释强化,在这互释的反复过程中,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宗法“政”之道。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移孝作忠,使原本存在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五伦,被董仲舒进一步从中提取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而这种三纲的提出,就通过前者对后者的绝对支配权力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以亲亲同化尊尊、以尊尊强化亲亲的宗法伦理与宗法政治体系。这种对尊尊的同化与强化,到了宋明时期就愈益强烈与系统。这尤其表现为,一是进一步强调宗法家国的一致性,所谓“夫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张载:《经学理窟·西铭》)“‘天子建国,诸侯建宗’,亦天理也。”(张载:《经学理窟·宗法篇》);二是突出强调父权与君权的同一性,所谓“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家者,国之则也”(程颐:《伊川易传》);三是突出强调家长之权威。这种步步逼近、层层深入的构架体系,使得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政道至炉火纯青之地步。概言之,以家推国,以孝推忠,将社会的政治关系转换为自然血缘关系,看起来似乎是对家的提升,实质上是国的沉沦。而这样一种构建,以君臣投射父子,以忠映照孝,将人们的父子关系转换为君臣关系,将对族权的敬畏转换为对皇权的顺从,君主即大家之家(族)长,家(族)长即为家族之君主,并将父子关系进一步扩展衍生为一系列人与人之关系,可谓疏而不漏,天纲恢恢,使家国处于完全同构与互补之中,使宗法血缘精神融入社会政治结构之中。而在这样的宗法政治之下,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会得到明确而又详尽的规定与制约,政治的触须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具体过程,从而进行有效的控制,故,中国古代封建宗法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政”道,它同时就内蕴有一种精微的“治”道,“政”与“治”合为一体,而此治道之精微恰恰在于此政道之家国一体的宗法要义。在这样对人的精神与行为设计控制严密得几乎无所不包的政治结构中,要想生长起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秩序,可想而知是多么的艰难。
由上亦可知,中国古代政治在学理上是伦理政治,即古人所说的仁政德治(这里的“仁”、“德”均是在伦理的角度上而不是善的意义上使用,它的具体内容亦可依据对仁、德的具体理解而不同,至于它的现象性存在更是可以千变万化),它所遵循的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这个逻辑完全是个体道德的逐级放大。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生活是建立在个人道德的基础之上,是以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的伦理关系涵盖与代替政治关系,因而尽管其政治构建精微致极且圆融实用,但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的政治之道是没有获得分化没有发育成熟的。没有获得相对独立性的事物总是幼稚不成熟的,这正是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伦理政治有两大特征,一是直接建立在血缘宗法伦理关系基础之上,且直接将这种血缘宗法伦理关系作为政治关系,以伦理代替政治;一是将政治建立在个体德性基础之上,希求通过个体的内在修养这一主观因素而不是社会客观运作机制来组织社会政治生活,所以它只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
三
政治不应当被伦理所取代。不过这里在学理上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政治是否有其伦理基础?如有,这个基础与政治本身的关系怎样?或者极而言之,政治是否可以完全游离于伦理之外?
确实,伦理是关于应然、意志的,政治是关于实然、事实的,两者有相当大的区别,不能混淆,更不能彼此取代,然而即使我们不一般泛泛地谈论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即使我们仅仅面对政治生活本身,我们也仍然回避不了关于政治生活、政治行为的价值基础问题。社会国家政治生活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结构组织方式的问题,故它本身就不似纯粹的自然现象那样,可以作为纯粹的实然事实存在,可以加以纯客观的观察(如果不是过于苛刻而可以这样讲的话),它直接就是有意志的个人所构成的有机体系,总是包含着个体居于自身利益对已经存在的事实与可能出现的事实的某种判断,构成关系的各个方面都会根据这种判断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进而调整这种关系体系结构,如果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曲折映射了人与人的关系的话,那么社会国家生活则直接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在构建自己的社会国家秩序时,总是以一定的价值前提作为出发点,总是以一定的理想状态作为自己的判断依据。这个判断依据在古希腊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在近代欧洲就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在现代就是罗尔斯的正义社会,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更是其突出代表;在中国古代则是大同、小康,是家国一体的融融血缘秩序。而作为价值前提的则是各种正义、公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各司其职的社会等级观同时就是一种正义观,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亲亲、尊尊,就是那种政治生活结构的正义观、正义准则,而在当代罗尔斯那里则是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显然,政治总是摆脱不了伦理的纠缠,总是以一定的伦理原则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础,人们也总是通过对社会国家政治生活的正义与否的判断而对现有的国家政治生活结构、秩序作出相应的反应,没有伦理基础的政治是不现实的。这里的关键在于:a、以什么样的伦理为基础;b、作为基础的伦理不能代替政治;c、应当在一定的价值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入政治生活的具体过程, 对其作科学、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能体现那价值理想的实际运行规则、程序、制度。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伦理政治其过失不在于以一定的伦理为基础,而在于以封建宗法血缘伦理为基础,在直接以这种血缘伦理代替政治生活及其关系,在于其没有也不可能对政治关系、结构、运行程序作科学实证的考察分析,在于其立足个体德性流于人治而不是立足客观机制立于法治。
在伦理是关于价值领域、政治是关于国家生活组织运行的意义上,也未尝不可以说伦理与政治之别是“仁”和“智”之别,也未尝不可以要求仁与智的分化,要求智这一关于社会国家生活的科学实证研究的相对独立生长发育,——这也正是我们当今所面临的重大而又紧迫问题,但却并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主张政治与伦理分离的二元并立格局(参见朱学勤:《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新儒家政治哲学评析》载《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6期)。那样,不仅割裂了实然与应然、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使社会国家生活失却善的价值方向与价值灵魂。那样,即使在今天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也会失却其价值合理性前提,因为民主政治建设毕竟是以承认个性、权利、自由等的伦理价值、人文精神为前提的。政治应当且必须从伦理中独立出来,没有这种独立就没有社会国家政治生活的现代化,但这种独立又不能绝对化,否则就没有社会国家政治生活的合理化、合乎人性,这种分化独立只不过是实现二者由原初幼稚混沌一体的原始状况向成熟完善过渡的中介环节。分化是为了更高程度的统一。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伦理为政治提供价值前提与出发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家生活之“政”道中的形而上内容,国家生活中“政”、“治”之道之形而下方面则是它的实证化与具象化。现代社会国家生活的结构及其运作程序的制度化、规范化,在根本上也可以说是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伦理精神、人文价值的制度化、规范化。
牟宗三先生针对中国伦理政治之传统的弊端,主张道德之仁与科学之智的二元对立,使之生长出现代民主政治,用他的话说是:道德理性之自我坎陷(自我否定):经此坎陷,从动态转为静态,从无对转为有对,从践履上的直贯转为理解上的横列。”通过此转变,“遂有‘道德中立’和‘科学之独立性’。”(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57—58页)牟先生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强调必须发展科学精神,必须克服道德君临一切、代替一切的现象,这是合理的,但是他却又进一步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科学能否完全独立于道德(这是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这一最重大问题)?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来说,克服其伦理政治是否在保留其伦理精神、道德理性要义基础上扩展一下其实证方面就行了?或者换个角度说,是否在保留传统的伦理道德基础上就有可能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借用毛泽东的话说不脱胎换骨恐怕是不行的。即使从牟宗三先生所注释的“天下为公”这一“政”道出发,结论也是显然的。天下为公作为价值理想蕴藏于政道之中,它意味着国家是“公”的,故天下为公之政道就不是以“家”为构建国之模型,而应以“民”为国之构建基点,家有家长,民则是民主,这正是两种政治原则、政治模式之根本区别。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不仅仅是操作层面的,更重要的首先是价值层面的,应当是在代表民意的合理的价值精神指导之下的科学精神的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