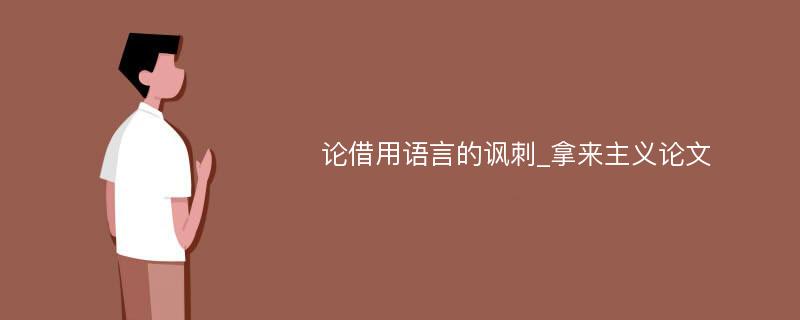
再谈《拿来主义》语言的讽刺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拿来主义论文,再谈论文,语言论文,讽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少人都谈过《拿来主义》语言的讽刺性,大都将笔力集中在反语、比喻、细节描写等方面。这些研究都抓住了重点,分析细致、深入,让读者受益匪浅。 比如使用反语手法的词语就不少。“发扬国光”原文加了引号,表示否定和讽刺,表明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投降媚外,丢国家的脸;“进步”是变本加厉的卖国行为;“丰富”和“大度”是卖国者为自己的卖国行为所找的借口和自我标榜;“吝啬”一词贬词褒用,提醒我们对自己的文物和资源要珍惜。 比喻的使用也非常精彩。如用“孱头”“昏蛋”“废物”比喻不能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几种人;用“鱼翅”“鸦片”“烟枪和烟灯”“姨太太”比喻文化遗产中不同的部分。 用细节描写的方法描摹人的动作,突出其丑态。如“捧”描写的是卖国者谄媚讨好别人时的毕恭毕敬;“挂”描写的是展览国画的人的大张旗鼓实际上却是极为寒酸的可笑;“蹩”本意是指脚腕子扭伤,这里指走路不稳,用在文中描写出了瘾君子的病弱和见了鸦片之后的猴急相。 理解了这些语言形式的讽刺性,对解读文章很有帮助。但是,在讲完这些内容之后,总觉得言不尽意。鲁迅杂文语言的讽刺性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再读文章,文中更多的语言正在发“投枪”,射“冷箭”。读懂了觉得很是舒畅、痛快;似懂非懂的时候却觉得若有若无,若隐若现,难以言说。所以,本文对《拿来主义》语言的讽刺性还要做一些补充论述。 一、词语错位,形成张力 词语一般都有固定的使用对象和使用情境,表达比较鲜明的含义。一旦词语使用于非正常的使用对象和情境之上,它就表达着远超原意和语境的含义,具有话外之意、弦外之音。《拿来主义》中第一段有这样一句话:“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古董”的含义是:“古代留传下来的器物,可供了解古代文化参考。”从上文可以看出,此次拿去展览的是“学艺”上的东西,能够到欧洲文艺发达的国家去展览,自然是精品中的精品,因此使用“文物”一词更为妥当。《现代汉语词典》将“文物”一词解释为“历代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从词义来看,文物的价值更高。从日常使用习惯来看,“文物”使用在更正式的场合,所指称的事物具有更重要的历史价值。“古董”多使用于非正式场合,泛指古代留下的器物,包含那些没有多少历史意义的事物。而且有时“古董”一词包含着对事物轻视的态度,如果指自己的,往往有谦逊自卑的含义,指别人的则有戏谑的味道,表示不认同或不欣赏。在词典中,“古董”还有一种含义是“比喻过时的东西或顽固守旧的人”,带有明显的贬义。文中,国际展览是非常正式的国际文化交流,展品一定是代表中国文艺精华的文物,而鲁迅故意使用“古董”一词,明显降低了档次,从而表达了对这种行为的不满和讽刺。 鲁迅在写到烟枪和烟灯时说“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背着”一词明显错位了。烟枪和烟灯代表文化中的旧形式,抽鸦片作为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早就被严厉禁止,基本绝迹了。但是工具毕竟只是工具而已,并不是落后文化的罪人。烟枪和烟灯代表着一段历史、一种生活,如果拿它们到世界各地展览,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坦然自信的,也应该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和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人的喜爱。烟枪和烟灯在世界各地展出,自然是坐飞机、火车、轮船、汽车、马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也应该在尊贵的文物场所有自己的容身之地。而“背着”一词则显出人才凋零、文化式微的穷酸相,也显出不被重视、不被理解的可怜相。而且还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些背着狗皮膏药的江湖神医、那些举着旗幡符箓的茅山道士,自欺欺人地做着招摇撞骗的勾当。因此“背着”一词着重刻画了文化“送去主义”者谄媚别人、以求施舍的可怜相。 二、模拟口吻,展示病态 鲁迅在文中有时并不直接批评人,而是模拟一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口吻和行为,突出这些言行和现实的矛盾,揭露他们的真实心理,让读者自然而充分地体会到这些言行的可笑,轻松地达到讽刺的效果。鲁迅在文中说“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摩登”是时髦的意思,在文中加了引号,就有了特殊的含义,指的是当时文化“送去主义”的潮流。中国在近代遭受了种种屈辱,容易产生媚外的心理、自卑的心理,只好拼命挖掘自己文化里的精华,讨好地展示给别人,甚至送给别人,求得别人的理解和同情。这种心态实质上是投降卖国,鲁迅模拟他们的口吻说“摩登”,显然是对他们的讽刺。 鲁迅还写道:“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这句话中有“阴功”一词,其含义是阴德,即人在世间所做的而在阴间可以记功的好事。这是典型的迷信思想,鲁迅向来反对愚昧落后的迷信文化,自然不相信阴功一事,只是模拟迷信人的口吻说出来,说出来又怕世人误解,就加了一个括号来解释。本段本来是要批评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却通过模拟口吻,顺便讽刺了人们的迷信思想。 还有一句:“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平民化”实际上是某些人的自我标榜。一些人在很多方面,包括在文艺上,脱离实际,远离民众;遭到批评之后,就故意作秀,公开表演自己的“平民化”,却丢不掉“贵族主义”的本质。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鲁迅的态度是毫不犹豫地吃掉,丢掉当然是极大的浪费。作者借此批评了否定一切文化遗产的态度,还顺便批评了那些高喊“平民化”口号的人。 在“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中,“当众摔在茅厕里”也是鲁迅见过的表演式的革命方式。在新文化运动中,对旧文化基本是否定的,连孔子也被打倒在“孔家店”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不是彻底革命,而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必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坑。在本文中,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有害与有益并存的部分,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全盘否定也是一种浪费。鲁迅在此主要批评的是这种错误的思想态度,也批评了那些非常极端的“革命”方式。 三、借用俗语,翻出新意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语言博大精深,正式的熟语和民间的俗语数量繁多,而且表现力极强,往往三两个字就能穷形尽相。鲁迅接受了新旧两种不同的教育,对各种熟语和俗语非常熟悉,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往往随手一点,却意味深长,讽刺得含蓄而深刻。文章开篇不久就写道:“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不知后事如何”是民间说书艺人的惯用语言,也是明清话本小说的常见用语。这句话本来是两回书之间的过渡语,作为上回书的结束,给听众或读者留一个悬念。鲁迅用在这里表示古董展览的结果,另有它意。到巴黎去展览的古董,也许是因为弱国的文艺不被重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最后也只能灰溜溜地回来,不好再说什么,展览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也许是因为弱国国民好欺负,说不清是我们主动送给别人的,还是别人强行留下的。所以这句说书人口中的俗语就变成了对“送去主义”者卖国行为的强烈批评。 鲁迅在写到鸦片时还写道:“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八个字想来该是鲁迅那个时代的人司空见惯的广告。鸦片已禁了近百年,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鸦片的危害都心知肚明,买卖鸦片成了既违国法又丢颜面的丑事,于是就有了这样含蓄的隐语,让圈内人心照不宣。当然后来圈外人也见怪不怪了。鲁迅在此借用这样常见的广告,实际上是对经不起金钱诱惑的人违背国法、违背道德的行为的谴责,也是对那些死守着文化糟粕、享受文化腐肉的可耻行为的揭露和批判。 四、借机揶揄,戳人痛处 鲁迅的杂文锋芒毕露,在文坛上乃至社会上树敌众多,经常遭人指责和奚落,但是鲁迅秉持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精神与之对抗,用手中的笔做毫不留情的反击。不过,以鲁迅的地位,用大篇幅的文章公开进行论战和攻击,似乎有失身份,于是很多杂文中经常有宕开一笔的时候,看似闲笔,实际上别有用意,是对自己看不惯的人或论敌的借机揶揄。这种揶揄往往时机恰当,又能戳中痛处,不明就里的读者觉得轻描淡写,明白个中情由的人往往能会心一笑。 在《拿来主义》的第一段中有这样一句话:“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句中提到梅兰芳,从上下文语境来看,鲁迅批判的矛头确实不是指向梅兰芳,而是指向当时政府奉行的“送去主义”的文化卖国行径。但是只要了解鲁迅和梅兰芳的关系,我们就能感受到鲁迅也有借机揶揄梅兰芳的意味。鲁迅从小就不喜欢传统戏曲,《社戏》中那种“咚咚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给他留下了非常枯燥无聊的印象。他对梅兰芳本人也很不欣赏,认为他的表演太“文雅”,脱离大众。在《论照相之类》中还点名批评梅兰芳演林黛玉,眼睛凸,嘴唇厚,形象不美。在该文结尾挖苦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鲁迅在本文特意挂上“博士”之名,也是一种讥刺。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期间,被美国波摩拿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授予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样的学位在鲁迅看来也是没有含金量的。 当然,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梅兰芳艺术成就极高,荣誉博士学位也无可非议,送他出国的是政府,他只是“送去主义”的工具而已。鲁迅对他的批评有些偏见,也是不合适的。我们今天解读这篇杂文,特别是向学生讲解这篇课文时,一般不谈鲁迅对梅兰芳的揶揄。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带挪揄嘲弄之意。 在写到那所大宅子时,鲁迅说:“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这句话看似闲言,实际有所指。这个“女婿”,鲁迅指的是邵洵美,而他的妻子盛佩玉是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盛宣怀的孙女。这里鲁迅在谈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时,宕开一笔,借机嘲讽了自己的论敌邵洵美。邵洵美是个有贵族气质的诗人,在山雨欲来的革命时代,他一味吟风弄月,追求“唯美”,鲁迅看不惯他不关注时代风云的创作态度,有时也借他的家庭生活攻击他,认为他做了富贵人家的女婿,成了暴发户,才有条件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只谈风月。在我们的文化中,女子向来只是男人的附属品,靠女人获得地位的男人向来不被人尊重,民间“吃软饭”一词就带有强烈的不屑。这里轻描淡写的闲笔,实际上是对论敌的无情嘲讽。 不过,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鲁迅对邵洵美的批评是过分的,邵洵美本人出身豪门,他的祖父邵友濂做过湖南巡抚、台湾巡抚,他的妻子盛佩玉跟他是表姐弟关系,说他靠做富贵人家的女婿而发达是不客观的。而且邵洵美本人开书店,办出版,对文化是有贡献的,他为人慷慨,有“小孟尝”的美称。中学语文教材以前的注解是:“这里是讽刺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现在删去了邵洵美的名字,也算是还他一个公道。 鲁迅的杂文是极富战斗性的,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的讥刺和揶揄等待我们发掘和领会。掌握了鲁迅惯用的方法,了解了相关的背景,我们就更能体会鲁迅杂文的讽刺性。标签:拿来主义论文; 鲁迅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梅兰芳论文; 读书论文; 邵洵美论文; 文物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阿芙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