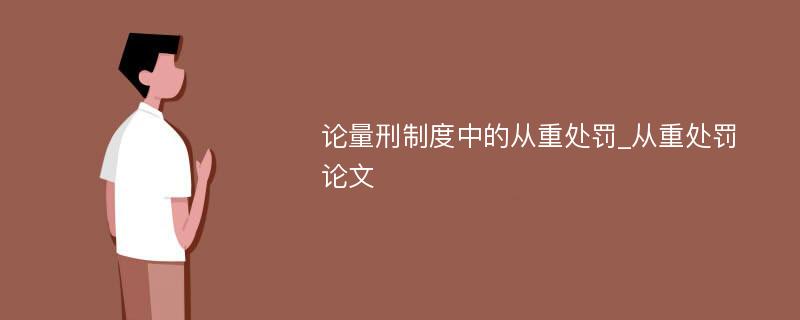
论量刑制度中的“从重处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重处罚,是刑法所规定的一种量刑制度。根据刑法第62条的规定,所谓从重处罚,是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较重的刑罚。从新刑法的规定来看,涉及从重处罚的条文达30余条,占有相当的比例,在司法实践中也大量存在着具有某种或多种从重处罚情节的案件。因此,正确理解从重处罚的含义,对于司法审判活动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根据刑法对从重处罚情节的表述,刑法学界通常把从重处罚的情节分为两类:(注:高铭暄《刑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第一是总则性的从重处罚情节,如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刑法第29条)、累犯(刑法第65条)等;第二是分则性的从重处罚情节,如非法拘禁他人,具有侮辱、殴打情节的,从重处罚(刑法第238条)。要正确理解上述两类情节,科学诠释从重处罚的内涵,必须围绕刑法第62条的规定,从理论上弄清楚三个问题:一是法定刑及其限度的含义;二是从重的含义;三是从重处罚的基本原则。
一 法定刑及其限度的含义。从重处罚必须是在法定刑以内判处刑罚。什么是法定刑,刑法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定刑是指刑法规定的某个罪名的刑罚幅度。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定刑应以刑法条文规定某一具体的量刑幅度为基本单位,一条文规定的某一具体犯罪的量刑幅度,即是该罪的法定刑。第三种观点认为,法定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定刑指的是刑法规定的该罪的刑种和刑度,例如刑法第153条规定走私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直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显然,它与第一种观点是相同的;狭义的法定刑,指的是与该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相适应的特定的刑罚幅度。显然,第三种观点是第一、二种观点的综合。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其理由如下:
第一,所谓法定刑,顾名思义,就是刑法规定的刑罚。这种刑罚总是针对某一犯罪而言的。它是立法者从静态的角度出发,针对某一性质犯罪的复杂性以及不可预测性而制定的与之相适应的具有模糊性与广延性的刑罚幅度,是司法实践的标准和尺度。至于刑法条文规定的某一具体犯罪的特定情节所应处的刑罚幅度,它只是法定刑的一部分,是针对这一特定情节作的量刑性规定,目的是为了维护刑罚的统一性与严肃性,已经属于具体的量刑活动,不具备法定刑高度概括性的特征。
第二,由于犯罪情节的复杂性,它需要刑罚具有相当的外延,这样在量刑过程中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精神。一定阶段刑罚幅度的确定是以某一性质犯罪的通常情况为根据的,而不可能反映该犯罪的一切情况。因此,立法者在确定法定刑时,总是将它划分为几个层次,将一些特殊的量刑情节排除在某一通常的量刑限度外,而安排在或较轻或较重的量刑幅度层次,这样就构成一个从轻到重的完整的法定刑限度。例如刑法第353条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这是刑法对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一般性刑罚。按照第二种观点以及按照第三种观点狭义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即是该罪的一个法定刑。假设某甲犯了该罪,根据其犯罪情节综合量刑,甲应处三年有期徒刑。若甲是累犯,又具有教唆、引诱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等从重情节,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刑法第62条的规定,对甲判处的刑罚只能是三年。显然,某甲所犯之罪行与所处之刑罚完全不相适应,而且无从体现从重精神。故只有将刑法第353条第一款规定的后半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作为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的一个完整的法定刑,才能从立法上做到罪刑相适应。
第三,若将某一片断的刑罚幅度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法定刑,与立法本身相违背。“从重处罚”所表述的罪状在很大程度上与“情节严重”的情节存在着竞合。某一片断的刑罚幅度只是针对相应犯罪的一般情节而言的。“情节严重”的情节,往往是刑罚幅度升格的主要原因。如刑法第254条报复陷害罪有两个量刑幅度:当情节一般时,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中的情节,不是指特定的某一方面的情节,而是指案外的情节,它当然包括从重处罚的一些情节。还是以刑法第254条为例:甲犯有报复陷害罪,排除从重处罚的情节,其综合量刑的结果是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如果甲是累犯,有的法官在量刑时可能会作为一个严重情节来考虑,量刑结果可能会突破二年有期徒刑的限制,与上述狭义说所蕴含的从重处罚要求就相矛盾。
弄清楚了刑法第62条所规定的“法定刑”的含义,对于“法定刑的限度”也就不难理解了。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一性质犯罪的法定刑,都有一个轻重不同的幅度,这种幅度就是法定刑的限度,我国刑法对法定刑限度的规定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单一的刑种与可供选择的量刑幅度。例如刑法第124条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话设施罪,其法定刑只有一个刑种,即有期徒刑,其量刑幅度则有两个:“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某人犯有该罪又具备从重处罚情节,在三年以上判处有期徒刑,都可以理解为法定刑的限度内量刑。第二,规定了不同的刑种。例如刑法第347条第2款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就将四种刑罚同时作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法定刑并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定刑的限度。如果某人犯有该罪并具备从重情节时,人民法院就可以根据案情在上述笼统的法定刑限度内确定较重的处断刑。
以罪名单位确定法定刑是否会造成法定刑限度过大,在从重处罚或从轻处罚时是否会导致量刑的畸轻畸重呢?笔者认为,从重情节或从轻情节只是诸多体现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一个方面的反映,它不能也不可能决定某一具体犯罪整个刑罚的水准,所以它在量刑方面的作用是非决定性的,对诸种情节综合评判、整体量刑,争取做到不偏不倚是由法官素质等诸多因素来决定的。至于能否做到罪刑相适应,不是法定刑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
二 从重的含义。关于从重的含义,抽象地理解是选择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有一个核心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既然是从重,则必定有一个用作比较的基准,这个基准是什么,则是一个十分复杂争议颇大的问题。刑法学界见仁见智,提出了几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从重处罚就是在法定刑范围内对犯罪的适用较重刑种或较长的刑期,这是理论界的通说。(注:《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第二种意见认为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对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比没有从重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注:张谷主编《刑法适用手册》,第287页。)第三种意见认为,不以特定的基准为参照物,而是对量刑情节逐个评价,定量积分,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销。(注: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第四种意见认为,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定刑幅度范围内选择比没有这个情节的类似犯罪相对重一些的刑种或刑期,即以估定的没有从重处罚和从轻处罚的情节时的应判处的刑罚为标准,具备从重情节时,则在此标准上适当地从重。(注: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笔者认为,所谓从重是相对于案件本身不具备从重情节而言的。因此,它就以某一特定的对象为参照物,离开了这个参照物,就无法体现对具体犯罪处罚的宽严,也无法体现从重处罚的要求,上述第三种意见漠视了刑法将某些特别情节单列出来明文要求从重处罚的精神,故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综合而言,笔者较赞同第四种观点。
第一种意见虽然提出了从重、从轻是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对犯罪人适用较重或较轻的刑罚,但这里的“较重”、“较轻”是以或应以什么为参照物呢?这种含混性不仅无法给司法实践予以明确的指导,而且也不符合定义概念明确性的要求。第二种意见不足之处在于,若数人犯罪,具有单一从重情节的犯罪分子比没有从重情节的犯罪分子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这种情节还可以适用,但如果一人犯罪且具有多个从重、从轻情节时,又该和谁来比从重呢?若与以往同类案件比,则存在着两个矛盾:1.我国法律在渊源上没有判例法,所以,同类案件的判例只能作为参考,而不是量刑的根据;2.即使是参照同类案件,由于犯罪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谁又能保证具有从重情节的案件与同类案件在其它方面刚好紊合呢?
以不具有从重和从轻的某一具体犯罪的情节为基础,科学地量出应该判处的刑罚,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的从重情节,适当增加刑罚的幅度,这就是笔者对于“从重”含义的理解。因为:第一,通过与本案不具备从重处罚情节时相比较,量化了立法意图。应当从重处罚的情节,其社会危害和人身危险性必定较大,刑法将其罪状表述出来,并规定了从重的处罚方法,就是为了体现重罪重罚的精神;第二,操作起来具有可行性。从重处罚的情节只是诸多量刑情节的一个方面,对量刑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行为人基本的犯罪行为、危害结果以及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所以法官在量刑过程中,可以先撇开从重情节独立地处断,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根据从重情节适当增加刑罚,这样就避免了第三种观点参照物含糊性的缺点,也可以较好地做到罪刑相适应。
三 从重处罚的基本原则。本文最后还想论述一下从重处罚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这对于司法实践有纲领性和倾向性的指导意义。从重处罚,作为量刑领域的一个范畴,理所当然地应遵循量刑的基本原则。但作为刑法的特别规定,它必须突出地贯彻两个独特的原则:一是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二是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第一,罪刑相适应原则:修改后的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它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定罪与量刑的根据,贯穿于量刑过程的始末。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精神便是“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从重处罚的规定便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和最基本原则的。
立法者在确定法定刑及法定刑的某一具体幅度时,只是针对某一性质犯罪的通常情况而言的,而不可能反映该犯罪的一切危害因素。因此,为了达到罪与刑的一致性,立法者在确定法定刑时,总是将法定刑的限度划分为几个轻重不同的区域。而从重处罚情节往往是导致法定刑升格的主要根据,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法定刑只能是某一犯罪的整体量刑幅度,而不是该幅度内的一部分。如果以法定罪的某量刑档次为法定刑,当存在某种或多种从重处罚的情节时,要做到罪刑相适应,就可能出现需要变更法定刑的情况,(注: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这又与刑法第62条的规定相违背,使量刑陷入两难的境地。
第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从重处罚”情节与“情节严重”情节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竞合。需要从重处罚的,往往是因为情节严重,只有情节严重,才导致结果的从重处罚。但严格来讲,“从重处罚”与“情节严重”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术语,在处罚时,不能就同一行为在法律上做出重复评价。
“情节严重”的情节在刑法上的功能主要有三个:第一,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情节严重的情节;(注:张明楷《论刑法分则中作为构成要件的“情节严重”》,《法商研究》1995年第1期,第14页。)第二,影响量刑幅度变化的严重情节,如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具备严重情节的,则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作为量刑综合考虑情节之一的严重情节。其中刑法对第一、二种情况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三种情况则表现在案件之中,属于酌定情节的一种。
要区分上述两类不同性质的情节,做到禁止重复评价,还是必须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刑法对从重处罚的情节(罪状)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处罚时必须体现从重处罚的内容,而不能以严重情节处罚或再处罚。例如刑法第279条招摇撞骗罪,量刑幅度有两个: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若某甲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依照刑法规定应从重处罚,在量刑时,就只能按从重处罚的原则进行,而不能以“情节严重”再重复量刑。排除刑法所明文表述的三十余种从重处罚的情节,其他情节严重的,则按照其在刑法条文中的相应功能进行处罚,而不能再成为从重处罚的事由。
标签:从重处罚论文; 法定刑论文; 法律论文; 量刑情节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法制论文; 有期徒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