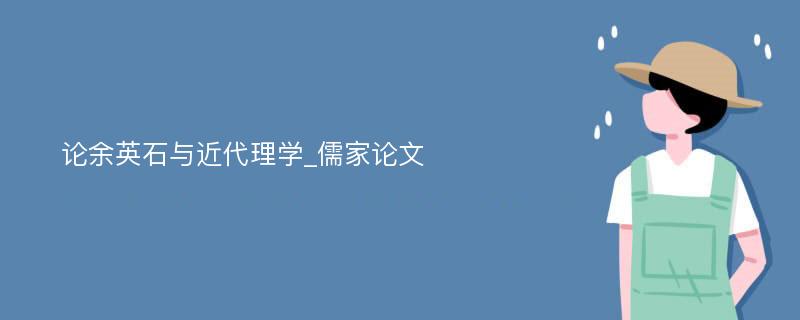
道不同不相为谋——论余英时与现代新儒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道不同不相为谋论文,余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5)02-0018-06
1986年3月,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七五”文科科研规划咨询会上,方克立先生作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发言;同年11月,以方克立、李锦全为负责人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确定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从此,新儒家成为文化讨论的一个热点,并在港台、海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引起了极大关注。在方、李课题组所圈定的现代新儒家名单中,包括了钱穆和余英时师生。1988年8月在香港召开的一次“儒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会议上,余英时先生看到了一份大陆有关“现代新儒家丛书”的出版计划,钱先生与余先生各占一册。余先生认为将钱先生称为“新儒家”是“尊之适所以侮之”;钱先生逝世一年后,余先生作了长文《钱穆与新儒家》,为乃师申辩,并阐述了自己对新儒家的认识。1990年8月余先生在美国Santa.cruz浩然营暑期研讨会上演讲接受提问时说:“我并不是在提倡儒家,我也许同情儒家的某些立场和观念,也认为儒家某些东西具有现代的意义,但是要问我是不是新儒家?我说:什么家也不是。”[1]
正像方克立先生所说:“界定现代新儒家的标准,主要不能看师承出身,也不能看本人声明,而是要看他的思想、言论、著作所表现的基本学术立场。”[2]因此,衡定余先生是否新儒家,就必须从余先生有关儒学问题的论述入手。在解读余先生有关儒学论述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大陆学人对“新儒家”所下的定义。在大陆学人关于新儒家的定义中,最早倡导对新儒家进行研究,同时也是大陆新儒家研究领军人物的方克立所下的定义,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方先生说:“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2](P19)这一定义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接续儒家“道统”,二是服膺宋明理学,三是援引西学入儒。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比照余先生的儒学论述,从而为余先生确定身份。
一、道统与心性
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是“返本开新”。所谓“返本”即返传统儒学之本。现代新儒家所要接续的儒家“道统”也就是他们所要返之本,即道德心性。新儒家以“心性论”作“道统”来概括传统儒学,认为这是儒学的“神髓”和“命脉”。对此,李泽厚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本人极少谈‘心’、‘性’,‘性’在《论语》全书中只出现过两次。孟子说了一些,但并不比谈社会政治问题更为重要。”“以心性道德的抽象理论作为儒学根本,相当脱离甚至背离了孔孟原典。”[3]在我们的通常理解中,朱熹是“道统”论说的正式建立者和道学的集大成者,因此余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根据朱熹及程颐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厘清了“道统”、“道学”、“道体”诸概念的流变及互相之间的关系。
余先生说,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中庸》是集中讲“道体”的文本,正式界定“道统”则见于《中庸章句序》。所谓“道统”,是“道”在人的世界的外在化,也就是“放之则弥六合”,内圣外王无所不包。“道统”之“统”与孟子所谓“创业垂统”(《孟子·梁惠王下》)之“统”是相通的。而能“接夫道统之传”者,只能是德、位兼备,即以圣人而在天子之位者。“上古圣神”即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以及商周的圣君贤臣都是有德有位者,所以能“接夫道统之传”,“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在这个阶段中,在位的‘圣君贤相’既已将‘道’付诸实行,则自然不需要另有一群人出来,专门讲求‘道学’了”[4]。但自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不复合一,孔子虽“贤于尧舜”,但因“不得其位”,便唯有走上“继往圣,开来学”的新路。孔子所“开”的“新路”,就是“道学”。如果说“道统”是儒家“内圣外王合一”的实现,那么“道学”则是儒家“内圣外王合一”的理想。秦汉以后,天理不明而人欲炽,不用说“道统”难以实现,就连“道学”理想也不传,只有到宋代,周、张、二程才接续孔子“道学”,但也不是上古圣王代代相传的“道统”。朱熹心中的“道统”和“道学”都是具有特殊的政治涵义的。余先生说,如果结合朱熹写《中庸序》的历史背景,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尧舜禹相传的“道统”,还是孔子以下的“道学”,都是和“治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道统言,朱熹之所以全力建构一个‘内圣外王’合一的上古三代之‘统’,正是为后世儒家(包括他自己在内)批判君权提供精神的凭藉……再就‘道学’言,他之所以强调孔子‘继往圣,开来学’也首先着眼于‘治天下’这件大事。孔子所‘继’的是‘尧舜禹相传的密旨’,所‘开’的则是阐明此‘密旨’(或‘心法’)的‘道学’。……上古‘道统’的‘密旨’不但保存在‘道学’之中,而且不断获得新的阐发,因此后世帝王欲‘治天下’,舍此便无所取法。这是朱熹的微言大义,旨在极力抬高‘道学’的精神权威,逼使君权就范”[4](P52)。但朱熹的大弟子黄斡用“道始行”与“道始明”二语辨别周公以上圣王与孔孟之间的不同,显示出他深知朱熹为什么要建立“道统”与“道学”这一重要的历史划分,然而他又故意将“道统”与“道学”打并归一,以“道统”二字统合《中庸序》“道统”与“道学”两阶段之分。余先生说:“上起尧舜,下迄朱熹,一贯而下,这样一来,‘道统’的涵义改变了,它不再专指朱熹构想中的内圣外王合一之‘统’或陈淳所谓‘道学体统’,这正是后世通行之义。”[4](P43)也就是说“道统”与“道学”二而一了,从此“道统”的尊号基本上便属于有“德”无“位”的儒家圣贤了。余先生说:“由于‘道统’的传承已公认是儒者所特有的责任,于是便有‘治统’一名相应而起,与‘道统’形成相持而又互足的一对概念。”[4](P44)
余先生同时又指出,朱熹在讨论“道统”时,特别突出“道体”的首要性。何谓道体?余先生说:“一言以蔽之,‘道体’是指一种永恒而普遍的精神实有,不但弥漫六合,而且主宰并规范天地万物。”[4](P53)宋代理学家们用种种形上概念作为“道体”的描述词,如太极、天理、性、心等皆是。余先生指出,“道体”的主要功用是为天地万物提供秩序,而最早发现“道体”而依之创建人间秩序的则是“上古圣神”,为此余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庸序》正式提出的‘道统’说便是为上古‘道体’的传承整理出一个清楚的谱系,以凸显孔子以下‘道学’的神圣源头之所在。自道治分离以后,‘道体’的阐发已转入儒家之手,即刘宗周所谓‘孔孟不得已而分道统之任’。”[4](P53-5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宋以前,一般都是“周孔”或“孔颜”并称,鲜见“孔孟”合称。但唐宋之际出现了周予同先生所称的“孟子升格运动”,熙宁四年(1071)二月,《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中,到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下诏褒赞朱熹曰:“朕唯孔子之道,自孟子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宋史·理宗本纪》)正式承认程朱“道统”上接孔孟。然而“道统大叙事”认为,“孟子升格运动”的关键在于宋儒上接孟子,提出了一个从尧舜到孔子的传授渊源系统,在于孟子思想学说中有发掘不尽的心性论素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二程、张载、王安石到朱熹、陆九渊,他们无不大谈所谓的心性与工夫,他们的心性论和工夫论,就是以孟子的思想为起点,整合了佛教中的心性学说”[5]。而现代新儒家所微的也正是将“心性”从“道学”中抽离出来,把它作为理学的全部内容并赋予它“道统”的功能。余先生认为,宋代理学家为重建秩序的可能性进行了双重论证,即宇宙论、形上学的论证,为人间秩序奠定精神的基础;历史的论证,要人相信合理的秩序确已出现过,不是后世儒者的“空言”,而是上古“古圣贤相”所已行之有效的“实事”。而为这一双重论证提供动力的经典正是《孟子》一书,因为孟子才是第一个运用双重论证的儒者。余先生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分别代表了孟子“内圣”与“外王”的两面,这才是孟子之后不传的“道统”。张载、二程不仅发展了“孟子道性善”,而且也继承了他的“言必称尧舜”。而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外王气概,更在宋儒心中激起宏大巨响。到了南宋,朱熹、陆九渊不仅都是弘扬“道体”的大儒,而且又都具有“致君行道”的抱负,也都肯定“道统”已出现在上古三世。他们都认为,如果没有“道体”,“道统”根本无法出现;如果没有“道统”,则“道体”只是孔子以下“道学”的“空言”,不足以保证它可以落实为人间秩序。也就是说“道体”、“道统”是理学家的共同信仰和基本预设。但朱、陆之间又有极可注意的同中之异,即朱熹认“理”为“道体”,陆九渊以他所构想的“心”为“道体”。在余先生看来,朱陆同在“外王”,同在“道统”,异在“道体”,异在“理”与“心”。余先生所认可并加以阐发的也正是朱熹所抉发出来的原始儒家“内圣外王合一”的“道统”。然而,与朱熹取径截然有异的宋以后的道统论的“大叙事”则认为,宋代儒学便是“道学”,而“道学”则专讲“道德性命”;不但如此,“道德性命”之学虽自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多年,但通过宋代道学家重续绝学的努力,它又获得了更明确的呈现方式,基本上不受外在事象变动的干扰。余先生认为,“大叙事”中的“道德性命”(或“内圣”)是一种超时空的精神实体,即“道体”,这种以“心性”为全部内容的“道体”,不仅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而且还逸出了儒家传统,成为一个圆满自足的绝缘体。现代新儒家以“心性”为“道统”,将“道体”当“道统”的运思方式,就是这种“大叙事”的“现代化身”[4](P156)。
二、宋明理学与内圣外王
与以“心性”为“道统”相关联的是,现代新儒家以“内圣”之学为“宋明理学”,并说宋明理学“内圣强而外王弱”。余先生则认为,宋明理学秉承原始儒家传统,经过一番“回转”功夫,使“内圣外王”成为一连续体。
唐宋之际,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宋初儒家士大夫以“治道”为大方向,以“三代”理想为依归,力图重建政治、社会秩序。宋初胡、孙、石三先生“推明治道”的努力,使后人感到“凛凛然可畏”(朱熹语)。而范仲淹则发挥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只有到王安石,儒家士大夫的“治道”蓝图才有了一次付诸实施的机会,最初包括程颢、张载在内的不同思想派别的士大夫都出来支持王安石的“新法”。但是,宋初儒家士大夫的注意力还没有贯注到“道德性命”之类的“内圣”问题上面,欧阳修则更是对“内圣”之学采取了相当消极的态度,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王安石推行“新法”有一套“道德性命”的精神资源,但正宗的理学家却认为王安石关于“道德性命”的议论或者距成熟之境尚远,或者近似禅宗,总之没有触及“内圣”之学的深处,理学家断言这正是熙宁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朱熹说“荆公学之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张栻说“介甫之学乃祖虚无而害其实用者”。推崇王安石的陆九渊也说“荆公之学,未得其正”。都是批评王安石“内圣”之学不足。于是“伊、洛诸君于盖欲深救兹弊也”(张栻《寄周子充尚书》),即在“内圣”上下功夫。但是正像余先生所说:“长期以来,在道统‘大叙事’的浸润之下,我们早已不知不觉地将道学或理学理解为专讲心、性、理、气之类的‘内圣’之学。至于‘推明治道’的‘外王’之学,虽非全不相干,但在道学或理学中则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这一理解在现代学术分类中呈现得更为明确,道学或理学已完全划归哲学的领域,通常所谓‘宋明理学’实际上已成为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同义语。”[4](P170)余先生还说:“道统大叙事’,特别是它的现代化身,把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束缚得太紧了。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只要提及理学家如二程、张载或陆九渊继孟子‘不传之学’的问题,论者除性善养气之外,其余一切几乎都‘匪我思存’。”[4](P182)余先生承认:“‘内圣’之学确是他们的精神源泉,至少他们是如此这般深信不疑的。他们不但持此为安身立命之所在,而且也相信这一精神源泉足以涤荡他们的胸襟,不断改善他们做人做事的能力。从这一角度看,‘内圣’之学的宗教性格是很明显的。”[6]但是余先生又指出:“若将理学定性为专讲‘心性’之类的形而上的‘内圣’之学,置人间秩序为‘第二义’,这也许可以满足‘小我’或‘自我’的某些‘终极关怀’。但这样一来,理学家和弃世与避世的释、老便难以分辨了。所以朱熹说‘自谓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7]于是余先生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上述的看法可信,我们又怎样理解大批理学家在孝、光、宁三朝权力世界中异常活跃这一现象?”[6](P26)
在余先生看来,秩序重建是贯穿两宋儒学的整体动向,理学虽然以“内圣”显其特色,但“内圣”的终极目的不是人人都成圣成贤,而仍然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重建,用原始儒家的语言来表达,便是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因此,王安石“得君行道”的范例时时在宋明理学家心中激起一种憧憬的情绪。可以说,“得君行道”是理学家的共同理想。为此余先生将理学家“得君行道”的言行作了一番细致的梳理。最早表现出“得君行道”倾向的是程颐,他所谓“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上仁宗皇帝书》),这正是两宋理学家争取“得君行道”的一种基本方式。朱熹平时对王安石与神宗的“千载一遇”更是称羡至再至三,他说:“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跋王荆公进邺侯遗事奏藁》)他说的是神宗,心中想的未尝不是孝宗。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六日,他第一次获孝宗召见。为了这次“登对”他准备了三个奏割,所谓“心欲一见,面论肺腑,不知如何可得?”(《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表现了他“得君行道”的焦虑心绪。与朱熹有“异”的陆九渊在他的“轮对”活动中,也表现出这种“得君行道”的意识。淳熙十一年(1184)冬天,陆九渊获得第一次“轮对”的机会,像朱熹“登对”一样,这也是他生平的一件大事,他准备了五个劄子,所谓“肺肝悉以书写”(《象山全集》卷三六《年谱》)。第一次“轮对”的顺遂无疑使他对孝宗产生了相当的信任,正因为此,他才耐心地盼望着第二次“轮对”,虽然他在敕令所中明明无所作为,但仅仅为了等待第二次“轮对”,竟“郁郁度日”至两年之久,这说明他对“遇合”的可能性有着很高的估计。不仅如此,陆九渊还把“得君行道”的起源上溯至孔孟,并对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十分钦佩。“得君行道”且“知其不可而为之”不仅是陆九渊一个人对原始儒家基本精神的独特领会,而且是宋儒的共同认识。可以说“行道”是朱陆的共同目的,“得君”不过是手段。但朱陆之间似乎不存在为“得君”而互相竞争的意识,相反的,彼此都好像愿意见到甚至帮助对方把握住“得君”的机会。淳熙十一年朱熹对陆九渊的“轮对”就表现出“待之太重,望之太过”的情绪。不独朱陆之间如此,朱熹对张栻、吕祖谦的“轮对”也十分关注,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战略性的默契,他们尽量利用时机,发动志同道合之士请对、轮对,不断地向皇帝进言,以争取“得君行道”的可能;他们之间还为请对与否的问题经常互通声气,以收感动孝宗之效。
那么明代的儒家学者是否如“道统大叙事”所议论的那样,完全坠入“内圣”而成了“自了汉”呢?目前我还未见余先生这方面专门的论说,据说余先生有《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一文,将与《朱熹的历史世界》之“绪论”合刊单行,我想在这篇长文中余先生必将对明代理学家的“外王”行为有所抉发。
总之,余先生通过对程、朱、陆、王理学思想的梳理,告诉我们:“行道”以实现人间秩序的重建依然是宋明理学家的“第一义”愿望;同时余先生又说,和北宋初期的儒家相对照,理学(或道学)增添了“内圣”这一重要向度,赋予儒学以新貌。理学之所以自庆历以后获得许多人的信奉,则因为它提供了下面这个有说服力的承诺:只有在“内圣”之学大明之后,“外王”之道才有充分实现的可能。因此它虽似“内转”,却仍与北宋以来儒学的大方向保持一致。既然理学家以救“新学”之弊而起,自然会在“内圣”方面有相对较多的强调,因此,如何从“内圣”转回“外王”便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余先生说,理学家同时也是儒家,他们不可能长驻陆九渊所说的“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的“内圣”极致之境而不返“经世”的领域,他们努力发展“内圣”之学以为重返“外王”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对“后王安石时代”的理学士大夫来说,他们显然多了一层“内圣”的曲折。也就是说经过这一“回转”,“外王”有了“内圣”的底蕴,“内圣”有了“外王”的托所。或者说,从范、欧、王到程、朱、陆是从“外王”转入“内圣外王”连续体,这是理学家的群体意识,因此,“内圣”和“外王”是不能不同时加以肯定的价值。当然,“从个人方面说,理学家或偏于‘内圣’取向,或偏于‘外王’取向,这是无可避免的”[6],但也只是偏向而已,不能舍去任何一端。建立秩序的唯一凭藉便是理学家发展出来的一套“内圣”之学;但“内圣”之学无论多么重要,都不能是理学的终点,它与“外王”之学紧紧连在一起,为建立合理的人间秩序服务,而且也只有在秩序中才能真正完成自己。余先生认为,朱熹以《大学》“明德”、“新民”分指“内圣”与“外王”两大领域,于是余先生创造性地将“内圣”“外王”代进“新民必本于明德,而明德所以为新民”之中,便是“外王必本于内圣,而内圣所以为外王”[7]。余先生这一“代”,将宋明理学家关于“内圣外王”的整体认识,一语道尽。
三、内在批判与援西入儒
如果说宋明理学在其“内圣”向度中吸收、融摄了佛学“心性”之学,那么现代新儒家则以援西学入儒为其主要特征。儒学就其本质来说无所谓新与旧,儒学之所以为儒的基本性质是不变的,是超时空的。然而“五四”以后儒学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后来又无奈地退居海外,成为“游魂”。为了使儒学与现代生活相适应,新儒家大师们重新调整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即本内圣之学开新外王。新儒家大师批评宋明儒者是“内圣强外王弱”,且不说这一批评是否符合实际,其所谓的新外王也非传统儒学以“家”为出发点的“治道”,而是“科学”、“民主”。新儒家大师所做的工作就是怎样使本土文化传统的“内圣”与当代新外王的“科学”、“民主”相贯通,从而使儒学与时俱进,不仅继续占据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还要挺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与西方文化平等互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现代新儒家大师们“通过德国唯心论的大哲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来突显对扬中国儒家的心性之学”[8]。然而,“尽管新儒学代表人物的本意是为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显学来充实中国的传统学问,以回应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但无意中却造成了新儒学极端形上化的倾向。……这些形上学追求的只是自身概念系统的统一与完善,而不关心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及其要求。新儒学在德国形上学的影响下,忙于编织自己深奥繁密的哲学体系,乐于从事概念的推理思辨,生活在自己构造的思想王国中,漫游于自己手定的逻辑系统里”[9]。这就像新儒家大师们议论西方哲学时所说的那样,“其界说严,论证多,而析理亦甚繁”,他们“属少数派哲学家,作遗世独立之思辨(Speculation)之事”,“欲自造一思想系统,穷老尽气,以求表现于文字著作之中。至欲表现其思想于生活行事之中者,实寥寥可数”[10]。
与新儒家大师“变相西化”(蒋庆语),从哲学的、形上学的层面阐述儒学不同,余先生认为:“中国如何重建儒家?不一定非采形上学的路线。”[1](P191)而且“儒学从来不是纯思辨的产物,只有放置在生活实践的历史脉络之中,它的意义才能全幅展现”[6](P33)。所以余先生阐扬儒学,取的是历史的角度,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从“形而下”的层面观察儒学变动。而不涉及形而上或宇宙论。
余先生认为:“十六世纪以来,儒家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各方面的观念都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儒家对西方文化所作的选择性的接受又有内在的关联。”同时,“近代西方文化对于儒学的挑战主要不在‘形而上’而在‘形而下’的领域之内。因此在西学东渐的前夕,儒学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各方面的思想新基调似乎更值得我们重视”[11]。余先生梳理明清儒学“形而下”方面的思想资料,揭示出儒家“形而下”的思想正在朝着中国本土的“现代性”的方面移动,从而提醒我们:中国近代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由西方挑战所激起的,而是有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的作用。为此,余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初期也是如此。”[11](P2)余先生认为,晚清无论是今文经学家还是古文经学家,虽然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西方观念的冲击,但显然并未意识到是站在西方思想的立场上进行反儒学的活动。相反的,他们自诩能发掘儒学的原始精神,不过借外来的观念加以表述而已。在今文经学家的想法中,他们是从儒学的内部来进行革新的工作的。古文经学家们也是一方面攻击儒学的流弊,另一方面则发挥他们所尊信的原始儒学精神,他们的立场,也属于内在批判。总之,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内在批判”,儒学吸收西方思想,也是出于它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余先生认为,他们所接受的西方思想主要是“抑君权而兴民权,兴学会、个人之自主”等,他们毫不迟疑地接受这些外来思想,不仅仅是由于救亡图存而追求西化。救亡图存是他们最原始、最迫切的动机,而儒家的政治社会思想发展到清代晚期出现了某种新倾向,恰好可以与外来的观念相呼应。余先生“深信明清儒家的政治社会思想产生了一种新倾向,而这一倾向对晚清儒家接受西方观点发挥了暗示的作用。但并不是说,明清儒家思想中出现了西方式的观念如民主、人权、个人自由之类。……而是这些观念背后的思想的基调恰好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希望不断扩大民间社会和个人的功能,并使之从国家或政府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但这一心态并非始于晚清儒家,也不完全源于近代西方。明清儒家的政治社会思想中便已发展出一种大体相近的基调;正是由于基调相近,晚清儒家才能驾轻就熟地接上了上述三种西方观念”[11](P7-8)。那么明清儒学的思想基调是什么呢?余先生指出,一方面,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的高峰时代,同时也是中央集权的高峰时代,受到专制和集权摧残的士人,便把注意力从朝廷转向社会,在民间开拓儒学发展的新空间;另一方面,明清时期人口猛增,而科举名额却应付不了士人数量的不断增长,便出现了“弃儒就贾”、“士商互动”等新趋向。正是在这专制皇权恶化的政治形势和“弃儒就贾”的社会运动的一拒一迎之间,儒学发生了新的转向。于是,乡约之类的民间组织受到重视,藏富于民的观念被正面发挥,尤其是经商得到公开的认可,“私”、“利”、“奢”等价值受到正面肯定。所谓“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良贾何负闳儒”等都表明明清时期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所谓“土商异业而同道”则使儒家的“道”因为商人的参加而获得新的意义。明清儒学的这些新倾向,“恰好构成了现代儒学接受西方观念的诱因”[11](P31),对于“现代儒家接受西方价值,既有接引作用,又有规范作用”[11](P26)。为此,余先生总结说:“晚清儒家处于君主专制最高峰的终结时期,又深受黄宗羲《原君》篇的启发,因此,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几乎是一见倾心。他们终于在民主制度中发现了解决君权问题的具体办法,突破了儒家传统的限制。……从文化心理层面说,他们都出身儒学系统,如果民主、民权、共和、平等、自由等西方价值和观念在此系统内不能获得定位,则他们将找不到途径去认同这些异质的外来文化因素。所以我们与其说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毋宁说他们扩大了儒学系统,赋予儒学以现代的意义。”[11](P36)
正像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发展只能在其固有理路上发展,背离其固有理路求发展,发展只能是歧出或变质”[9](P2)。余先生没有像“当代新儒家那样去汲汲建构理论的形上学,在抽象的观念上来‘会通’、‘融合’中西文化”,也没有像“牟宗三那样用西方哲学(康德哲学)作为‘钢骨’来‘支撑’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丧失自身的生命活力变为不能自立的瘫儿”[9](P290),而是将儒学置于政治社会历史变动的大背景下,揭示其“内在渐变”。余先生对这一“内在渐变”的发现,没有任何理论预设,也没有凭藉任何西方理论套在他的具体研究上,史料是余先生获至这一发现的动力。通过对明清至“五四”时期儒学史料的梳理,通过对这一时段儒学渐变的内在批判,余先生对儒学的未来命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儒学在私领域仍然可以发挥直接的效用,这是《大学》所谓‘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则属于公领域,已非儒家所能独擅,其影响只能是间接的。”[12]概言之,儒学的命运在社会,儒学的出路在民间,在于“日常人生化”。
以上三部分从狭义的“新儒家”概念出发,分疏出余英时与当代新儒家在学思路径上的不一致,这也正是余先生所说的“最多不过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已”[13]。但是自幼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余先生,即使到了利益至上的美国,仍不失儒者风范:为文,中正平和;为人,温良恭俭让。因此,从儒家实践的角度看,余先生是现代极少数真正符合儒家标准的知识分子之一。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朱熹论文; 王安石论文; 理学论文; 陆九渊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孔子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孟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