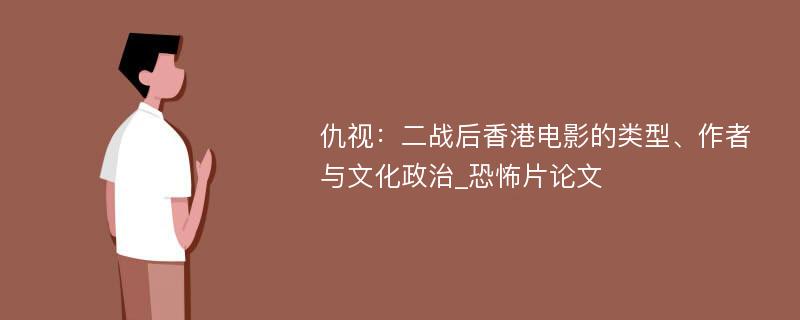
《琼楼恨》:类型、作者与战后香港电影的文化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香港电影论文,类型论文,政治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联沪港 1949年末,长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旧长城”)推出了影片《琼楼恨》,该片是这家雄心勃勃的独立制片公司制作的第三部作品,这部由“中国影坛上摄制恐怖片的著名权威导演”——马徐维邦执导的影片,制作周期长达数月,“旧长城”为此投入了“两倍于其它巨片的资力”,无怪乎当年的广告语不无夸张地宣称,这部“惊心触骨凄婉哀艳谋杀恐怖巨片”系该“年度影坛唯一巨铸”。① 对导演马徐维邦来说,《琼楼恨》也是其作品序列中的一部重要影片。从类型的角度说,《琼楼恨》属于马徐维邦最拿手的恐怖/惊悚片(这无疑是影片最大的“生意眼”),这位素来以拍片认真严谨著称的导演,在《琼楼恨》里倾注了不少心血,他“用了三个月的功夫,把所有镜头一个一个的分好,用极其新颖的手法联接起来,像一串珍珠那样,使全部剧情,缀成天衣无缝”,②冀望在香港东山再起。以“作者论”的角度观之,《琼楼恨》堪称马徐维邦个人风格最鲜明、主题最完整的影片之一。事实上,综观马徐维邦在香港阶段的创作,恐怕再也找不出另外一部影片能像《琼楼恨》这样,如此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导演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品格。然而,遗憾的是,长久以来,包括《琼楼恨》在内的马徐维邦在香港阶段的创作,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③ 马徐维邦是20世纪中国影坛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其电影活动横跨中国电影史的数个阶段,其拍片之多、影响之广,颇值得大书特书。马徐维邦原姓徐,1901年生于浙江杭州,④后因入赘马家而改姓马徐。马徐氏18岁到上海求学,1923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曾在母校及“杭州美专”、神州女校短暂任教。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马徐维邦考入明星影片公司(以下简称“明星”)开办的演员训练所,毕业后旋即加入“明星”,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进入电影界,直到1949年离开上海,马徐维邦在二十余年间辗转于“明星”、天一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新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艺华影片公司、中国联合制片厂股份公司(即“中联”)、中华电影联合股份公司(即“华影”)等多家制片机构,执导影片逾越20部,并凭借《夜半歌声》(1937)等影片建立了其在中国影坛独一无二的地位。⑤ 抗战胜利后,马徐维邦在上海电影界的处境颇不顺遂(部分原因是他在上海沦陷时期为“中联”及“华影”拍片的经历)。1947年的一篇报道称,“马徐维邦自入‘中电’,好几个剧本俱告流产,真有江郎才尽之叹”。⑥在完成《春残梦断》(1947,与孙敬合导)之后,他一度没有新戏可拍,原因是该片“意识甚深,赏识之人太少,终于售座力不能突破纪录,使中企当局没有请他再接再连的勇气”,以致要自资筹拍新作。⑦拍完《美艳亲王》(1949),马徐维邦再次陷入无戏可拍的窘境。恰在此时,他获张善琨之邀请,于1949年2月间搭乘邮轮赴港,⑧由此开启了他在香港的漂泊之旅。 邀请马徐氏赴港拍片的张善琨,是马徐氏的旧相识,二人在“新华”“中联”“华影”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经历,尤其是张善琨监制的《夜半歌声》,不但助力“新华”迅速成为“孤岛”前后上海最重要的制片公司,而且确立了马徐维邦“恐怖片权威导演”的地位,“标志着恐怖片作为一种类型在中国影坛的崛起”。⑨战后,张善琨因为背负“附逆影人”的罪名而无法在上海立足,遂于1946年来到香港。在成立“旧长城”之前,张善琨曾在1947年与李祖永合作组建永华影业公司,终因与后者发生龃龉而在1948年退出。 马徐维邦到达香港的1949年2月,“旧长城”正在积极谋求扩张。长袖善舞的张善琨克服了资金短缺、没有片场、人才匮乏等困难,一度将“旧长城”打造成战后香港影坛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国语制片公司。大体上说,“旧长城”延续了上海的拍片模式:在资金并不宽裕的条件下,仍坚持严谨制作,保证影片的品质;出品影片多为娱乐性的商业片,且类型多样;高度重视影片的宣传营销,充分利用大明星的号召力。⑩遵循这样的制片宗旨,在制作了教化意味浓厚的情节片《荡妇心》(1949,岳枫导演)及历史传奇片《血染海棠红》(1949,岳枫导演)之后,张善琨想到了在上海郁郁不得志的马徐维邦,力邀其到港拍片。 值得一提的是,《琼楼恨》的主创人员大都是来自上海的影人,包括摄影师董克毅,布景师万籁鸣、万古蟾兄弟,剪辑师王达云,化妆师宋小江、黄韵文,作曲李厚襄,以及主演王丹凤、顾而已、顾也鲁、洪波等。有“旧长城”主政者的全力支持,再辅之以技艺精湛、配合默契的创作团队,马徐维邦终于有机会实现艺术理想、展现个人风格,于是便有了这部战后香港最出色、也最富争议的恐怖片的诞生。 二、重塑“恐怖” 在早期中国电影史上,马徐维邦素有“权威恐怖导演”“权威‘鬼’导演”(11)之称。的确,在马徐氏1949年之前的一系列作品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当属以《夜半歌声》《古屋行尸记》(1938)、《麻疯女》(1939)、《夜半歌声续集》(1941)等为代表的恐怖片。通过出色的镜头调度、表现主义式的布光,以及(由化妆特技制造的)怪异人物造型,马徐维邦在这些打上鲜明个人风格烙印的影片中,成功营造出恐怖的气氛,他以近乎偏执的方式探索人物幽暗的内心世界,其间更透露出批判封建制度、反抗压迫、向往自由的社会讯息,堪称中国早期类型电影实践中的一道独特景观。 《琼楼恨》延续了马徐维邦上海时期的创作脉络,成功塑造了封建大家庭令人窒息的气氛,病态的人物关系、不圆满的爱情、人物毁容的母题,以及替代性的欲望投射,无不唤起观众对《夜半歌声》等马徐氏早年创作的记忆,影片一开场,便将观众带进一个典型的马徐式恐怖情境: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缓慢的横移镜头逐渐对准一所阴森可怖的老宅,伴随着画外紧张局促的音乐,画面叠化成老宅的内景,一名女子的身影从前景中一闪而过,惊恐万状地向景深处闪躲,窗外电闪雷鸣,一个黑黢黢的身影步步紧逼,在强烈的明暗对比中,女子的身体不断被黑影覆盖,简洁有力的剪辑表现了女子不断闪躲的情形,她最后退至角落,被一双手紧紧扼住颈部,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接下来,导演用一组叠化镜头开始影片主体部分的叙事,看护林玉琴(王丹凤饰)受邀来到高宅,照顾精神错乱的高家潭(这个代表父权制的角色是一名退休官僚,由顾而已出色饰演)。林一踏入高宅,便察觉出一种诡异的气氛。在万氏兄弟的悉心经营下,影片的布景层次分明、逼真妥帖,大到游廊厅堂、雕梁画栋,小到窗棂帷幔、物件陈设,无不传达出这个没落封建家族颓靡、压抑的气息。与此相应,导演多运用景深镜头及横移镜头,展示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林玉琴初到高宅之夜,同样显示了马徐维邦对恐怖类型的驾轻就熟:黑暗中,狂风吹得窗棂哐当作响,窗帘四处摇曳,镜头右摇,并缓缓推至在床上辗转不眠的女主人公。画面随即切至黑暗中一双男人的脚,导演在此处运用交叉剪辑,一面表现步履蹒跚的不速之客逐渐靠近,另一面表现惊慌失措的女主人公在床上抖作一团。画外的风声,瞬间照亮暗夜的闪电,状如行尸的身影,足以令人屏气凝神、毛骨悚然。从上述两个例子不难看出,无论是用光、镜头角度还是气氛营造,马徐维邦从外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恐怖片及德国表现主义)中吸取了不少养分,他自己坦承,“我的导演手法颇受了德国片和苏联片的影响,一直颇多和他们的出品所相同的作风”。(12) 值得注意的是,马徐维邦在处理恐怖片时,常常把文艺片的类型元素及叙事特征融入影片中,以缠绵悱恻、峰回路转的爱情悲剧揭露“时代的创伤”。(13)正如马徐维邦自陈的那样,《夜半歌声》“是有时代意识的”,其主题是“鼓动观众的革命情结”,因此“特别强调弱者的愤恨,强者的凶横”;而《秋海棠》(1943)则将一个“戏子私通姨太太”的故事,改写为表现“中国青年人在恋爱问题上的命运”(14)的悲剧。在《琼楼恨》中,导演将其擅长的恐怖/惊悚元素与恋爱悲剧相结合,经过他的铺陈,“这个剧本中的文艺气息与恐怖气氛更加浓厚起来”。(15) 通过片中人物的讲述,导演以闪回的方式揭开了高宅的隐秘,引出了一段残缺的爱情传奇:高家小姐高玲娟(王丹凤饰)与音乐教师方秋帆(受到新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顾也鲁饰)相恋,高父听信外甥陈耀堂(洪波饰)的谗言,对女儿的爱情横加干涉,最终酿成悲剧。从主题的角度讲,《琼楼恨》中主人公反对封建压迫、追求自由平等观念,与《夜半歌声》等马徐上海阶段的创作一脉相承,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不少“南来影人”在香港时期的创作中,仍“不厌其烦地讨论中国封建时代的旧问题,像五四新思想带来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反抗父权压制以及阶级门第的观念”。(16)事实上,“旧长城”出品的其他影片,如《荡妇心》《一代妖姬》(1950,李萍倩导演)、《王氏四侠》(1950,王元龙导演)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人物反抗恶势力、追求自由等主题,视之为“进步”亦未尝不可。 马徐维邦以鲜明的视觉符号呈现封建势力对主人公的摧残:方秋帆脸上留下一道永久的伤疤——毁容的母题以一种近乎无意识的方式出现在《琼楼恨》中,透视出导演幽暗而又绝望的内心世界。高玲娟死后,高父陷入精神错乱,为了治愈他的疾病,仆人请来与高小姐长相颇为相似的看护林玉琴。于是,林玉琴便成为片中几名男主人公替代性的欲望对象:对高父而言,林的到来,使那种病态的父女关系得以延续;对因痛失爱人而日渐沉沦的方秋帆而言,林犹如一个镜像般的欲望客体,唤起了他对过往爱情的记忆。两人初次邂逅的一场戏,将这种扭曲而自恋的关系升华到悲剧美的境界:方秋帆在恋人墓前喃喃自语时,画外传出一阵熟悉的旋律,惊诧不已的男主人公循声而至,恍惚间如见到爱人重生——在“恐怖”的外表下面,马徐维邦炙热的感情和悲悯的情怀呼之欲出。事实上,这个场景与《夜半歌声》中孙小欧(施超饰)在宋丹萍(金山饰)的授意下与李晓霞(胡萍饰)见面的场景何其相似!二者都有着马徐维邦作品中复现的结构性元素:毁容的男主人公,替代性的爱人,以及不完满的爱情。无怪乎有批评家指出:“《琼楼恨》无可争辩地表明,马徐维邦感兴趣的是执迷(obsession)的心理,而非影片的主题。”(17) 通过“扮演”高小姐,林玉琴终于弄清了前者之死的真相,由此也成为影片叙事的主要推动力量。有研究者指出,“马徐维邦电影的男女主角关系,并不绝对以先天上性别差异为依归: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正是马徐维邦所质疑的意识形态”,他相信“女性是救赎男性的主要力量”。(18)这一论断不无洞见。的确,较之林玉琴的冷静、理性和勇敢,片中的男性角色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负面的:或者颟顸粗暴(高家潭),或者软弱无能(方秋帆),又或者阴险卑劣(陈耀堂)。不过,笔者想指出的是,尽管林玉琴是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现代女性,但这一形象无法涵盖导演对片中女性的复杂形塑。例如,同样由王丹凤饰演的高玲娟,大体上不脱传统女性的窠臼,即便想逃脱封建家庭的樊笼,仍无可避免地沦为父权制的牺牲品。另一个女性角色——女仆惠姑(颜碧君饰),几乎被刻画成“蛇蝎妇人”的原型,她与陈耀堂私通,并充当了后者杀害高小姐的帮凶。在视觉表现上,导演常常将惠姑置于反差强烈的光影中,表现她内心的阴险狠毒和欲壑难平。 在戏剧冲突的高潮部分,反派角色遭到惩罚,精神错乱的高老太爷幡然醒悟,而象征封建势力的高宅也被熊熊大火付之一炬。影片结尾处,画面由化为一片焦土的高宅叠化为一片田野,获得高家潭资助的方秋帆即将展开他开办桑蚕学校的计划,影片最终定格在方秋帆与林玉琴伫立田野的画面。尽管《琼楼恨》全片笼罩着诡异、幽闭的气氛,但影片结尾实在不能算悲观,它多多少少透露出时代的讯息:腐朽的封建势力终将垮台,新的生活蓝图即将铺展开来。如果联系着影片的拍摄时间——1949年中期前后,那么这个结尾无疑是意味深长而耐人寻味的。不难看出,面对历史的转折,流落香港的“南来影人”对新时代的到来,仍抱以审慎的乐观。不过,这种乐观的情绪并未持续太久。 综观马徐氏的导演生涯,《琼楼恨》是少数几部最能体现其艺术野心和个人风格的作品。凭借精细工整的制作、完整的主题、鲜明的视觉风格,以及近乎执迷的情感,《琼楼恨》可跻身战后香港国语片经典之列,殆无疑义。然而,吊诡的是,该片既是马徐维邦在香港的首作,也是他最后一部在理想状态下执导的恐怖片。“旧长城”改组后,马徐氏厕身于数家独立制片公司,执导了好几部同一类型的影片,但大都素质平平,难与《琼楼恨》比肩。例如,他担任编剧及监制的《井底冤魂》(1950,洪叔云导演)便是一部粤语恐怖片,影片围绕一起“井内冤魂复出”的“恐怖奇案”,描绘“一个旧时代下的女人,如何地遭受着旧礼教的桎梏底悲剧”。(19)此后,马徐维邦为一家独立制片公司执导了《亡魂谷》(1951),该片“行的仍是恐怖剧的道路,着重画面的气氛烘托,渲染”,旨在对人性中的自私、狡诈等提出批判。(20)之后几年间,他又陆续执导了《午夜魂归》(1956,厦语片)、《雾夜惊魂》(1956)等小成本恐怖片。到了50年代末,马徐维邦的创作力已不大如前,其标志之一便是不断对旧作进行改编和再创作。例如,1958年,马徐维邦再次与张善琨携手,为香港新华影业公司执导了《毒蟒情鸳》(1958),这部由日本、中国香港及菲律宾联合制作的影片,翻拍自他上海时期的名作《麻疯女》,影片基本复制了原作的故事框架及人物关系,唯一不同的是,导演将原作中女主角因麻风病发而毁容的情节,安排在男主角身上。(21)在意外离世前,他一度准备再次翻拍《夜半歌声》(上、下集,1962-1963),可惜未及开镜便撒手人寰,幸得由弟子袁秋枫将其搬上银幕,算是了却了马徐维邦其生前的夙愿。 三、“南来”之困 早在上海时期,马徐维邦有“慢车导演”之称,即言其拍片严谨、细致,制作周期长,这已被电影界所公认。例如,他在执导《寒山夜雨》(1942)的过程中“所耗的精力,足可摄制二部影片有余”,幸得“中联当局很了解他的制作态度,故独予优待,不令限期完成”。(22)在客居香港时期,马徐氏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依然故我。当年在“旧长城”宣传部绘制海报的李翰祥导演在回忆《琼楼恨》时,以不无戏谑的笔触写道:“这部黑白片前后拍了六个月的工作天,拍得张善琨先生上气不接下气,拍得天怒人怨,鬼哭狼嚎,差点儿就拍掉了长城的半条命,哪儿是《琼楼恨》哪,简直是‘长城恨’!”(23)李氏的笔触或许有夸张之处,但大体上是符合史实的。 的确,“旧长城”原本期待《琼楼恨》能够延续《荡妇心》及《血染海棠红》的成功,以图在竞争激烈、环境复杂多变的战后香港影坛赢得一席之地。然而,事与愿违,1950年初,《琼楼恨》公映后卖座不佳,致使“旧长城”之“营业大不如前,经济周转顿告困难”。(24)张善琨的遗孀童月娟在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情况,“我们开拍了这么多片子,一心想拍好,结果负债也越来越多,短期之内,我们不免陷入一个循环的危机之中”。(25)不难推测,在此过程中,投资巨大、耗时耗力的《琼楼恨》成了压垮“旧长城”的最后一根稻草,进而促成“旧长城”的改组,为日后冷战气氛笼罩下的香港影坛埋下“左”“右”对立的伏笔。在这个意义上说,《琼楼恨》堪称战后香港影坛相当独特而重要的一部影片。 研究者将《琼楼恨》的票房失利归咎于观众对该片的“潜意识抗拒”:在“人心思定”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观众“根本不欢迎这种揭露过去创伤的电影”。(26)此外,尽管《琼楼恨》延续了马徐维邦最擅长的恐怖/惊悚类型,但影片的主题及类型实在难说有多少发展和创新。对导演而言,《琼楼恨》票房失利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如果不是灾难性的话):失去巨额资本的支持,一向有“慢车导演”之称的马徐维邦,从此丧失了执导巨片的机会,遑论对影片精雕细琢。事实上,他自觉难以在投机成风的香港影坛立足,一度有返沪的打算。(27) 与此同时,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香港影坛在1953年前后迎来“左”“右”对立公开化的局面,将包括马徐维邦在内的“南来影人”卷入政治论争的漩涡,并促成其政治上的分化与转向。在此过程中,原本属于中间派影人的马徐维邦,终于倒向右派阵营。在当时中国内地的电影管理者看来,马徐维邦“在政治上是倾向反动的”(28):他不仅出席了“自由影人协会”筹备会,而且身体力行地参与了右派的电影实践活动。例如,他参与执导的《碧血千秋》(1954),便是一部迎合台湾市场、体现国民党正统意识形态的影片。就连“只字不提国家和政治”的《新渔光曲》(1954),也被研究者解读为一部“带着政治寓言色彩”的影片。(29)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在严酷的市场环境下,马徐维邦被迫做出了有限度的妥协,但最终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他受雇于数家独立制片公司,除了恐怖片,他也接拍其他类型的影片,如武侠片(《宝剑结良缘》[1954])、历史片(《卧薪尝胆》[1956])、文艺片(《复活的玫瑰》[1957])及讽刺喜剧(《酒色财气》[1957])等。在借古讽今、嬉笑怒骂的同时,马徐维邦以近乎犬儒的心态抒发着南来的自怜与不适。透过娱乐的外衣,马徐维邦昔日作品的主题及对世事和个人际遇的暗叹隐约可见。例如,在《酒色财气》中,他一反严肃的主题和沉郁的风格,运用辛辣的笔调、夸张的表演和多个三角恋爱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的纸醉金迷、尔虞我诈,其用意与左派公司出品的《说谎世界》(1950,李萍倩导演)庶几近之。另一部作品《流浪儿》(1958)虽没有高深的立意,仍不失为一部体现“南来影人”复杂心绪的诚意之作,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之势利、投机、拜金的意图相当明显。影片的主人公——一群靠卖报、擦皮鞋、擦汽车糊口的流浪儿,几乎是导演人格的延伸:即便遭受践踏和欺侮,仍不改正直、自尊的品性。片中有一个有趣的情节,投机失败的资本家(王元龙饰)意欲谋夺流浪儿捡到的“中奖”马票,他精心筹划的记者会演化成一场荒唐闹剧:流浪儿的首领“大妞”(林翠饰)被包装成“归国名媛”,但她应邀演唱的《莲花落》却不折不扣地讽刺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奢靡(无独有偶,另一位“南来影人”卜万苍执导的《豆腐西施》[1958]中亦有类似的情节)——借人物之口,马徐维邦表达了他拒绝向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低头的立场。但所谓的“中奖”马票,不过是一张过期的废票,但这并不妨碍主人公以自信乐观的姿态面对未知的生活。影片最后,几名主人公齐声高歌,并肩前行,再次申明他们要靠双手改变生活的决心。如果比较《流浪儿》与李萍倩执导的《都会交响曲》(1954),或许有助我们理解“左”“右”阵营的某些共通之处:二者都以嘲讽性的基调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大加挞伐;只不过《都会交响曲》“神经喜剧”(screwball comedy)的类型特征更加明显,对资本主义社会之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嘲弄更加辛辣,而《流浪儿》更强调主人公的自尊及自立,显示了马徐维邦作为“文化民族主义者”(cultural-nationalist)的独特面向。(30)在他身上,我们可一窥香港右派导演的精神底色,较之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情绪、民族自尊,与对传统的怀疑与再肯定,对香港社会、文化的疏外与不适应”,才是马徐维邦等右派导演“普遍关注的焦点”。(31) 自1949年寄居香港以来,马徐维邦共执导了十余部影片,除了《琼楼恨》等之外,其他大部分影片都难以被电影史所铭记。总的说来,他在香港的创作经历仅是上海阶段的自然延续,在主题、风格、意识诸方面,均未见新的发展或突破。在战后香港影坛充满变数的环境中,他鲜明的个人风格不断遭到稀释,影片品质也参差不齐。他那特立独行、孤傲乖张的个性,更加剧了他在战后香港影坛的不适。在早年的一次采访中,马徐维邦曾吐露心迹:“我和环境是不大肯妥协的,譬如:一切无谓的应酬,我绝不参加;人家高兴,我并不一定高兴;一切大吃大玩的事,都没有我的份。有些人都谈我性情别扭,其实并不是别扭,实在我觉得做人太空虚了,老提不起过分热烈的兴趣。”(32)根据沈寂、李翰祥、鲍方等与马徐维邦有过合作或接触的影人回忆,在职业生涯的晚期,马徐氏早年的行事风格着实没有多少改变。(33)面对陌生的市场,马徐维邦的反应不是积极调试、主动迎合,毋宁说他仍旧自负而任性地延续上海的创作思路,遭到冷遇便在所难免。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由沪来港的“南来影人”,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群体,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以客居甚或“流亡”的心态来到殖民地香港,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电影的分流和裂变。在推动战后香港国语片创作观念、技术标准提升的同时,他们的创作亦流露出暧昧驳杂的家国想象。然而,受到市场、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南来影人”的际遇各不相同:成功者如朱石麟及李萍倩,不仅能结合香港的环境,实现创作上的新发展,而且风格日益圆熟,迎来艺术生命的第二春,最终成为香港左派电影的旗手;再如,岳枫导演由“左”而“右”,无论是在独立制片公司还是大制片厂,他都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产量亦相当可观;卜万苍则成为右派导演的代表,在战后香港影坛留下丰富的足迹,其创作虽不见得有多少创新,但至少称得上中规中矩。(34) 较之上述几位导演,马徐维邦无疑是同辈“南来影人”中“最不得意的一个”。(35)他的个案集中表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以来,沪港两地电影上的联系或传承,并非自然平缓的过渡,而是伴随着各种力量的艰苦博弈。马徐维邦,这位在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资深导演,最终在职业生涯的暮年沦为一段“褪色的传奇”(陈辉扬语)。事实上,20世纪从50年代中期开始,马徐维邦的职业生涯便开始走下坡路,到了50年代末,他在国语电影界的位置已日益边缘化,一度要靠拍摄厦语片维生——对于以国语片导演身份来港谋求发展的马徐维邦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1961年2月13日,落魄潦倒的马徐维邦在香港北角被一辆呼啸而过的巴士碾毙,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代传奇导演就此作古。这一悲剧性的事件本身,便是马徐维邦交织着颠沛流离与惶惑焦虑的香港电影生涯的隐喻。 ①《光艺电影画报》第20期(1949年12月),无页码。 ②《短镜头》,《光艺电影画报》第17期(1949年9月),无页码。 ③关于马徐维邦香港阶段的创作,最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是台湾学者陈辉扬的两篇论文《自我之伤痕——论马徐维邦》(载其所著《梦影集》,台北:允晨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5—39页),及《传奇的没落——马徐维邦香港时期的启示》(载香港市政局主办《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1990年,第58—63页)。 ④关于马徐维邦的出生年,另有一说为1905年,经查,不确,故不采信。 ⑤马徐维邦在上海阶段导演的影片如下:《情场怪人》(1926)、《混世魔王》(1929)、《空谷猿声》(1930)、《暴雨梨花》(1934)、《寒江落雁》(1935)、《夜半歌声》(1937)、《古屋行尸记》(1938)、《冷月诗魂》(1938)、《麻疯女》(1939)、《刁刘氏》(1940)、《夜半歌声续集》(1941)、《现代青年》(1941)、《鸳鸯泪》(1942)、《博爱》(1942,合导)、《寒山夜雨》(1942)、《万世流芳》(1943,与卜万苍等合导)、《秋海棠》(1943)、《火中莲》(1944)、《大饭店》(1945)、《天罗地网》(1947)、《春残梦断》(1947,与孙敬合导)、《美艳亲王》(1949)等.关于马徐维邦早年的电影生涯,可见《恐怖片导演马徐维邦小史》,《青青电影周刊》第5卷第2期,第13页;吕嘉《记马徐维邦》,《上海影坛》第1卷第4期,第31页,及陈维《访:千千万万观众所热烈崇拜的——马徐维邦先生》,《新影坛》第3卷第5期(1945年1月),第22—23页。 ⑥华英《抢生意!吴永刚马徐维邦失欢》,《新上海》第5期,第7页。 ⑦《马徐维邦四处活动——备自资拍戏》,《青青电影》1948年第2期。另,引文中的“中企”全称为“中企影艺社”。 ⑧《名导演马徐维邦离沪》,《青青电影》1949年第6期(1949年3月)。 ⑨李道新《马徐维邦:中国恐怖电影的拓荒者》,《电影艺术》2007年第2期。 ⑩关于“旧长城”的成立及创作概貌,可见拙作《上海传统、流离心绪与女明星的表演政治:略论长城影业公司的创作特色与文化选择》,《电影艺术》2013年第4期。 (11)《权威“鬼”导演马徐维邦》,《闻书周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12)陈维《访:千千万万观众所热烈崇拜的——马徐维邦先生》,《新影坛》第3卷第5期(1945年1月),第22—23页。 (13)“时代的创伤”是学者吴吴对马徐维邦早期作品的精准概括,见吴吴《时代的创伤:马徐维邦》,载《戏园志异》(第1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1989年,第68—74页。 (14)同(12)。 (15)《〈琼楼恨〉三主角的特写》,《光艺电影画报》第19期(1949年11月),无页码。 (16)焦雄屏《故国北望——九四九年大陆中产阶级的“出埃及记”》,载其所著《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5页。 (17)Stephen Teo,Hong Kong Cinema:the Extra Dimensions,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7,p25. (18)陈辉扬《传奇的没落——马徐维邦香港时期的启示》,载香港市政局主办《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1990年,第59—60页。 (19)斯人《沙漠里的绿洲》,《电影圈》第164期(1950年12月),第16—17页。 (20)《电影圈》第171期(1951年7月),无页码。 (21)见《〈毒蟒情鸳〉电影小说》,新加坡:友联书报发行公司,1957年。 (22)《〈寒山夜雨〉介绍》,《新影坛》第1期(1942年11月),第8页。 (23)李翰祥《影海生涯(上)》,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24)《张善琨退出“长城”》,《青青电影》1950年第5期,第5页。 (25)左桂芳、姚立群编《童月娟——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台北电影资料馆”,2001年,第93页。 (26)同(18),第59页。 (27)1950年10月的一则报道称,“名导演马徐维邦有信致沪上友人,决定于本月初由港来沪”,见《马徐维邦日内返沪》,《青青电影》1950年第21期(1950年9月);1951年6月的一则报道称,“马徐维邦于上月二十号那天返沪”,见《电影圈》第170期(1951年6月),第19页。但笔者并未查阅到马徐维邦1949年之后由港返沪的活动情况。 (28)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编印《香港电影界人物情况参考资料》(第一辑),内部文件,1954年,第25页。 (29)吴吴《爱恨中国:论香港的流亡文艺与电影》,香港市政局主办《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1990年,第28页。 (30)对“文化民族主义”的详细阐释,见Stephen Teo,Hong Kong Cinema:the Extra Dimensions,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7,pp23—25。 (31)罗卡《传统阴影下的左右分家——对“永华”、“亚洲”的一些观察及其他》,载香港市政局主办《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第14页。 (32)同(12)。 (33)分别参见《沈寂访谈录》,载周夏主编《海上影踪:上海卷》(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李翰祥《银海生涯(上)》,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94—112页;及《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二: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1年版,第99页。 (34)关于这几位导演在香港阶段的创作,可见黄爱玲编《故园春梦——朱石麟的电影人生》(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8年版)中的相关论述;黄爱玲《从三十年代到冷战时期——朱石麟和岳枫的电影之路》,载黄爱玲、李培德编《冷战与香港电影》,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9年版,第145—158页;罗卡《拈须微笑观世情——李萍倩中晚年创作》,《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及拙作《“南来影人”、流亡意识与传统的焦虑——卜万苍香港电影生涯侧影》,载《浮城北望:重绘战后香港电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96页。 (35)《电影圈》第170期(1951年6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