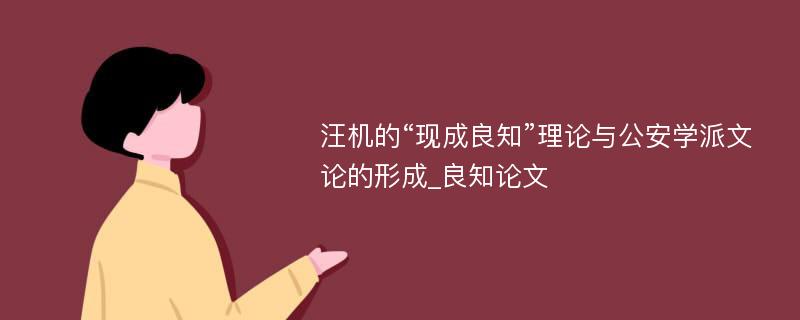
王畿“现成良知”说与公安派文论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良知论文,说与论文,公安论文,王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公安派文论,实受李贽(卓吾)的启发,这已为学界所熟知。除受李贽影响外,公安三袁还通过李贽接受了王守仁(阳明)后学王畿(龙溪)、罗汝芳(近溪)等人的思想。学界已有人撰文讨论公安派与阳明后学的关系①,但阳明后学很复杂。按阳明弟子龙溪的说法,分为“归寂”、“修证”、“已发”、“现成”、“体用”、“终始”等六派②;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将这六种说法加以分类,提出现成、归寂、修证三说③;黄宗羲《明儒学案》按地域分类,将阳明后学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王门。由是可见,阳明后学之间,思想有较多差异,笼统地谈论公安派与阳明后学的关系,不容易说清楚。应该具体地研讨公安袁氏与阳明后学各派究竟有何关系,才是正确的研究思路。最近几年,开始有学者研究袁宏道与泰州学派的关系④。但对于公安派与龙溪之学的关系,学界讨论还不够深入具体。本文认为,王龙溪的“现成良知”说对公安派文论的形成有较为重大的影响。从这个视角切入,或许更能深入理解公安派文学思想形成的学理机制。
一 龙溪“现成良知”说对公安袁氏心性论、人生观的影响
公安袁氏的性灵说与他们的心性论、人生态度都有密切的关系,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深刻理解公安文论何以形成。当然,三袁的人生哲学颇为复杂,随着他们人生阅历的不同而时有调整,其中有李贽的影响,亦有王守仁及其后学王畿、罗汝芳、焦竑、陶望龄、王时槐等人的影响。从远处看,三袁都很推崇白居易、苏轼的生活态度,他们濡染禅宗、净土宗亦甚深。但相对而言,王龙溪的现成良知说对公安三袁早期心性论与人生观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并深刻促成了他们性灵派文学主张的形成。
袁宗道(伯修)实是袁宏道(中郎)、袁中道(小修)心性之学的启蒙师。而伯修有志学道,亦有一个过程。入仕前的他,其实并不知道学为何物,虽也读程朱经注,但并没有将其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而是作为取科第、图富贵的敲门砖而已。据伯修自述,他早年鄙视理学家语录如“热月贩絮”。及至二十岁第一次科考落第,情绪很低落,于是受其舅父龚惟学先生的启发,喜读理学家身心性命之学,并感叹自己“廿载醯鸡,知瓶瓿外别有天地”⑤。伯修二十七岁官翰林之后,求道之心愈切,在京师问学于泰州学派的焦竑、精通佛学的瞿汝稷以及与李贽来往密切的僧深有(无念),从此接受了顿悟之学。后来伯修将其道学心得启发两个弟弟中郎、小修。据小修回忆说:“是年(万历十七年),先生(伯修)以册封归里。仲兄(中郎)与予皆知向学,先生语以心性之说,亦各有省,互相商证。先生精勤之甚,或终夕不寐。”⑥性命之学极大地改变了三兄弟的人生状态。据说中郎“自是以后,研精道妙,目无邪视,耳无乱听,梦醒相禅,不离参求。每于稠人之中,如颠如狂,如愚如痴”⑦。他的人生境界可见有了一个彻底的转换。
李贽是袁氏兄弟性命之学的引路人。自万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袁氏三兄弟曾一起先后三次拜访李贽。正是通过李贽,他们接受了阳明后学龙溪一系的心性理论,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世界。李贽对龙溪学术推崇备至,他称赞说:“世间讲学诸书,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龙溪先生者”⑧。又说:“予尝谓先生此书(《龙溪先生集》),前无往古,今无将来,后有学者可以无复著书矣。”⑨又云:“龙溪先生全刻,虽背诵之可。学问在此,文章在此,取科第在此,就功名在此,为经纶参赞之业亦在此。”⑩可见,李贽简直将龙溪视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学第一人;龙溪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王阳明。李贽自言:“龙溪之后当何人以续龙溪先生耳?”(11)可知,他不仅推崇龙溪,还隐然以龙溪传人为己任。三袁虚心地向李贽求学问道,而李贽也很自然地视袁氏兄弟为门人。李贽曾经对中郎说过这样的话:“世道由来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12)于是他毫无保留地“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13)。由于师生关系如此密切,可以想见,“无岁不读二先生(龙溪、近溪)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14)的李卓吾肯定会将他甚为崇拜的王龙溪学术介绍给袁氏兄弟。伯修的《白苏斋类集》卷二十二《杂说》与小修的《柞林纪谭》(见《珂雪斋集》附录二)都记载了李贽向他们讲述的王守仁如何收服放荡不羁的王畿为弟子的故事。这足以说明,李贽在袁氏兄弟面前对龙溪之学津津乐道,而且深刻影响了三袁对龙溪心性之学的接受。
龙溪是阳明弟子中“现成良知派”的代表(15)。他认为良知本来现成,不待修证,因此他反对同为王门弟子的罗洪先(念庵)等人主张的良知本体须待修证而全的观点。就致良知的工夫来说,龙溪主张顿悟以复不学不虑之良知本体,而反对采取渐修式的方法。在有名的“天泉证道”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而龙溪认为:“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16)这就是龙溪著名的心、意、知、物“四无”说。阳明本来说的是心之体无善无恶,并没有说性无善无恶;而龙溪在“四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认为性亦无善无恶。他主张“善与恶对,性本无恶,善亦不可得而名,无善无恶是为至善”(17)。龙溪对良知与心性的理解,得到了王阳明的首肯,认为“四无之说”是为“上根人立教”,是“顿悟之学”(18)。
李卓吾对龙溪“四无”说进一步禅学化,并深刻影响了袁氏兄弟对心性的理解。伯修说:“王汝中(龙溪)所悟无善无恶之知,则伯安(阳明)本意也。汝中发伯安之奥也,其犹荷泽发达磨之秘乎!”(19)关于对王守仁“良知”说的解读,阳明后学众说纷纭,人人自以为得阳明本意,而伯修惟独认可龙溪的说法,并认为只有龙溪才是阳明学的真正传人。在伯修《白苏斋类集》中,有《读大学》、《读中庸》、《读论语》、《读孟子》等哲学论文,其实很多是在发挥龙溪的顿悟之学。中郎的看法与其伯兄差不多。他说:“仆谓当代可掩前古者,惟阳明一派良知学问而已。”(20)而在阳明后学中,中郎最为推崇的亦是龙溪。他说:“王龙溪书多说血脉,罗近溪书多说光景。辟如有人于此,或按其十二经络,或指其面目手足,总只一人耳。但初学者,不可认光景,当寻血脉。”(21)可见,中郎虽受“二溪”影响,但龙溪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高一些。袁小修也说:“良知之学,开于阳明,当时止以为善去恶教人,更不提着此向上事。使非王汝中(龙溪)发之,几不欲显明之矣。”(22)小修在给二兄中郎的信中还说:“日在斋中,猢狲子奔腾之甚,一日忽然斩断,快不可言。偶阅阳明、龙、近二溪诸说话,一二如从自己肺腑流出,方知一向见不亲切,所以时起时倒。顿悟本体一切情念,自然如莲花不着水,驰求不歇而自歇,真庆幸不可言也。”(23)可见,小修视阳明、“二溪”的学说为烦躁人生的清凉剂。他又说:“国朝白沙(陈献章)、阳明,皆为妙悟本体。阳明良知,尤为扫踪绝迹。儿孙数传,盗翻巢穴,得直截易简之宗,儒门之大宝藏,揭诸日月矣。”(24)在小修看来,王学一系,发展至龙溪、近溪等传人,才真正揭开成圣的法门,到达了顶点。小修的思想虽然随其阅历而有变化,但直到晚年,他写作《论性》一文,坚持“无善无恶者,千变不化之性”的观点,这其实仍是龙溪性无善恶之旨;只不过小修又融合佛家业力轮回之旨,提出了“有善有恶者,千万世相沿之习”的看法。
龙溪的现成良知说对袁氏兄弟的人生观与生活态度有重大的影响。三袁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与真率自适的生活态度,实从卓吾转手而导源于龙溪。
龙溪的现成良知说有多方面的涵义。首先,良知是先天的道德本体,人人现成,个个俱足。他说:“良知良能,不学不虑,天之性也。故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取诸在我,不假外求,性外无学,性外无治,平天下者征诸此而已。”(25)即是说,爱亲敬兄等道德理性是人先天所具有的,是“不学不虑”(不需要后天学习与思考)而天然具有的“自然之良”。这个观点发自孟子,王阳明亦多次阐说。但王阳明视良知为本体,讲良知的现成性,只是在工夫论层面;而王龙溪“现成良知”则具有本体论意义。二者是有区别的。其次,良知有超越性。良知正是因为是先天的,为大自然所赋予,因此也就无所谓善恶可言,无善无恶是为至善。“(良知)知是知非而实无是无非。知是知非者,应用之迹;无是无非者,良知之体也”(26)。“知是知非”是就良知的道德功用而言,而良知本体乃天然自有,所以又“无是无非”;换言之,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这个“无是无非”的良知具有超越性,是大自然赋予的至乐心灵本体,王畿又称之为“寂”或“净”。他说:“良知者,心之灵也,洗心退藏于密,只是良知洁洁净净,无一尘之累,不论有事无事,常是湛然的,常是肃然的。”(27)正是因为有这种“无是无非”、无尘俗之累的超越性,龙溪认为,信得良知,不仅能成圣,还能了却生死:“一点灵明与太虚同体,万劫常存,本未尝有生,未尝有死也”(28)。
在龙溪看来,良知是先天圆成的,因此他格外推崇赤子之心与童心:“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无智巧、无技能、无算计,纯一无伪,清净本然,所谓‘童蒙’也。得其所养,复其清静之体,不以人为害之,是为圣功。”(29)童心保留自然赋予的天性具多,不为知识闻见所障蔽,所以大人君子应该向赤子学习,以复无是无非的良知清净之体。这个观点为后来李贽写作《童心说》提供了启发。龙溪“现成良知”说超越性的一面,又为李贽及三袁追求超越世俗羁绊和生死解脱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
王龙溪的现成良知说,本质上仍是道德哲学。他相信道德天然具足,认为只要悟到这一点,便自然会发之于日用,成为儒家式的圣人。他主张“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以笃信谨守,一切矜名饰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30)。龙溪不满罗念庵等其他王门弟子渐修式的良知修证法,反对人为地拘守道德戒律。他认为如果听信天然之良知,发之于行事,自能合乎道德的要求。他说:“良知是天然之灵窍,时时从天机运转,变化云为,自见天则。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何尝照管得?”(31)所谓“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便是不需要人为地进行道德自我约束,甚至也无须通过学习圣人之言来提升道德;而是听从良知的自为天成,以达到天然的道德之境。龙溪甚至认为,“六经”与《论语》中的道理原本天然地具于心中,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大道理。所以良知是本,经书为末。执经书为本以修身,不自信良知,便是“犯手做作”,便是“防检”与“穷索”。但龙溪式的顿悟法,在理论上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过分强调了道德之善的先验性,而忽视了人性“恶”的来源问题。比如好色、好货、自私利己是否也是先天的?龙溪时常以儿童天然爱亲敬兄以说明良知的自然天成,但在实际生活现象中,儿童骂父母、凌兄长者亦不鲜见。过分强调良知的先天性极有可能混认私欲为良知,走向自然主义的放荡一途。故清初理学家孙奇逢批评龙溪的现成良知“遂有认食色以为性者”(32)。黄宗羲亦认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33)黄宗羲批评龙溪“虽云真性流行,自见天则,而于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34)。更有学者指出,“泰州学派就顺着这一路发展出去,认为饥来吃饭困来眠,世间都是圣人,更无须修为研讨,于是不免被斥为‘无忌惮的小人’”(35)。
王龙溪这种自信本心,悬崖撒手,不待拘管的良知哲学,对公安袁氏最大的影响则是使他们对人生采取了一种“适世”的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袁氏三兄弟都很短寿,伯修寿四十一岁,中郎寿四十三岁,小修寿五十四岁,他们之所以短寿,恐怕不是家族基因遗传的缘故(36),而是因为纵情酒色,年寿不永。
伯修在三兄弟中算是性格“稳实”的人,但他也有放浪纵情的一面。在举进士前,伯修“性耽赏适,文酒之会,夜以继日。逾年,抱奇病,病几死。有道人教以数息静坐之法有效,始闭门鼻观,弃去文字障,遍阅养生家言”(37)。但他通过李贽接受了龙溪的顿悟之学后,很快放弃了这种静坐防检式的养生法,并认为静坐养生无异于“担雪填井,运石压草”,而“圣门为仁之真脉”乃是“不离情欲,而证天理”(38)。这种放弃防检、听任自然的态度显然是来自龙溪。龙溪不赞成陈白沙式的“静中养出端倪来”,主张“无动无静,无时不得其养”(39),反对舍“自然之良”而别求所谓“端倪”、“把柄”(40)。伯修视静坐、戒律为邪障,于是很自然地走向自适一途。他羡慕白居易、苏轼之为人,也向往白、苏式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心同、操同、趣同、才同、学同(41)。他有姬妾数人,喜欢谈谑浪笑,又沉湎于酒;只是到了晚年身体每况愈下,他才开始觉悟到李贽、王畿辈圆顿学术之非,忏悔自己“识劣根微,久为空见所醉,纵情肆志,有若狂象”(42),并深恶“圆顿之学为无忌惮之所托”(43),从而归宗佛家净土,持戒以求养生。
中郎早期亦狂放不羁,自称愿作“适世”之人:
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44)
这种“适世”之人,无拘无束,一任自然,认“作用”为性,极易走向享乐主义。中郎说:
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披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断以田土,二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45)
小修晚年自谓“二十年学道,只落得口滑,毕竟得力处尚少,以此深自悔恨”(46)。如果从学术上找原因的话,龙溪倡导的心无善恶、性无善恶说,很容易误导后学放弃对是非善恶观念的坚守。既然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最终只能是饥来吃饭困来眠,走向听任身体本能的自然主义。因此,小修年轻时通过李贽接受的龙溪式的无善无恶之道(按:初访卓吾时,小修时年十六岁),只是为他听从本能、生活放纵找到了借口。他后来回忆自己二十四五岁时,视金钱如粪土,“与酒人四五辈,市骏马数十蹄,校射城南平原,醉则渡江走沙市,卧胡姬炉旁,数日不醒。置酒长江,飞盖出没波中,歌声滂湃。每一至酒市,轰轰然若有数千百人之声,去则市肆为之数日冷落”(47)。终其一生,挣扎于情欲场、酒肉席中。他不仅姬妾多人,而且常赴青楼游冶之场,兼有“分桃断袖”喜好娈童之癖,自称“极难排豁”(48)。纵欲伤身,晚年多病,他才向朋友忏悔道:“弟之病,实由少年谭无忌惮学问,纵酒迷花所致。年来血气渐衰,有触即发”(49)。可见,小修自己承认他放纵的生活方式,实是受包括龙溪哲学在内的“无忌惮学问”影响所致。
当然,学者也可以从“狂禅”的角度来解释三袁放浪的生活方式,而且事实上三袁亦濡染禅学颇深。但如果从源头上来说,三袁这种“无忌惮学问”,应该主要来自龙溪。龙溪之学本来就如黄宗羲所批评的“近禅”,而且已突破了儒家之藩篱(50)。罗洪先、聂豹等王门弟子已经批评过龙溪的“现成良知”近乎无忌惮之学,唐顺之亦曾委婉地批评龙溪“以包荒为大,是故无净秽之择”(51)。龙溪晚年家中失火,他颇为惊惧,写自讼文,责备自己虽然一生讲学,但难免有“世情阴霭,间杂障翳”,严责自己“或恣情狥欲,认以为同好恶;或党同伐异,谬以为公是非。有德于人而不能忘,是为施劳;受人之德而不知报,是为悖义”。当时朝廷首辅夏言厌恶讲学,将这些王门讲学家斥为“伪学小人”,龙溪竟然在其子孙后辈面前承认了夏言的说法:“然在区区,则为深中隐慝。”(52)居然公开承认自己为“小人”!当然,龙溪自讼甚厉,综其生平,仍不失为品行端正的大儒,立身其实并不放浪。但其学术的流弊,容易混认情欲为良知,这是事实。龙溪之学经过李贽转手,更加禅学化了。三袁“无忌惮”自适式的人生观与生活方式实受其影响。
如果仅凭前述材料,很容易片面地认为袁氏兄弟为无行文人。事实上,三袁家境不错,享乐有资本;但他们“骨刚情腻”,仍不失为有气节的儒门中人。据记载,袁宗道在北京做皇太子的老师时,每次去上课,都是“鸡鸣而入,寒暑不辍。庚子秋(万历二十八年),偶有微恙,强起入值,风色甚厉,归而病始甚。明日,复力疾入讲,竟以惫极而卒。先生为人修洁,生平不妄取人一钱。居官十五年,不以一字干有司。……生平却百金者累累,或馈遗至十金,则惶愧不受”(53)。袁宏道为官亦极清廉,“居官十九年,不置升合田”(54),他作吴县令,深得民心,吴人称赞说“此令近年未有,惟饮吴中一口水耳”(55)。他在官吏部主事时,能严惩滑吏,清除积弊,而且颇有从政干才。小修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中郎死后,从其囊中,“仅检得三十金,其清如此,即弟亦不知其清如此也”(56)。袁氏兄弟的立身大节似乎与其放浪的生活方式很不协调,以至于后世学者对他们颇多误解,提到三袁总往“猖狂自恣”与“逾闲荡检”的一面去想。其实,如果从龙溪“现成良知”的角度理解,不协调的一面立即可以协调起来。立身廉正,固然是出自“现成良知”的道德理性;追求声色物欲之享乐同样也是“现成良知”的自然发用。龙溪虽然意在重建道德本体,表示反对有人“假托现成良知,腾播无动无静之说,以成其放逸无忌惮之私”(57);但其“不思善、不思恶”,丢弃拘管防检,信心直行的顿悟方式,又极易将“食色性也”、“生之谓性”搀杂进良知,从而给人欲找到了借口。因此,龙溪的现成良知说,实际效果是将德性之知与感性欲求原本不可调和的一面,奇特地统合成一个整体,在重视道德理性的同时,也给了人欲一定的合法性。从这个角度理解,公安袁氏清廉的公职形象与放荡的私生活之间的张力即可化解,看似矛盾,其实统一。
二 龙溪“现成良知”说与公安派文论的关联
公安袁氏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提出“性灵说”的文学主张,终结了前后七子近百年的文坛统治地位,从而给文坛带来崭新的气象。正如钱谦益所说:“中郎之论出,王(世贞)、李(攀龙)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58)《明史·袁宏道传》亦取钱说。四库馆臣也认为,“前后七子,遂以仿汉摹唐,转移一代之风气”,至“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诋之,……天下耳目于是一新”,从而使天下学者“又复靡然而从之”(59)。在七子派独霸文坛之时,如果谁不步趋于鳞(李攀龙),则“人争异之”,成为被嘲笑的对象(60)。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公安袁氏有巨大的勇气敢于向七子挑战,从而一新天下人之耳目呢?学者多从李贽或王阳明对三袁的启发这个角度进行讨论,其实龙溪“现成良知”说的影响更不容忽视。
有趣的是,三袁早年都有学习七子以拟古为高的写作经历。因为整个时代都是这样的风气,除非有大智慧,人很难和潮流抗争。伯修早年“喜读先秦、两汉之书。是时,济南(李攀龙)、瑯琊(王世贞)之集盛行,先生一阅,悉能熟诵。甫一操觚,即肖其语”(61)。中郎早年“上自汉、魏,下及三唐,随体模拟,无不立肖”(61)。小修“十岁余即著《黄山》、《雪》二赋,几五千馀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傅以相如、太冲之法,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63)。如果不是向李贽问学,袁氏兄弟极有可能顺着时代的文学潮流向前走,成为七子派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但问学李贽之后,中郎文境大变:
先生既见龙湖(李贽),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64)
可见,学术变了,人生境界变了,文学创作自然跟着变化。其中的隐秘应是通过李贽转手的龙溪之学启发他们产生了新的文学思想。如果将龙溪现成良知说与公安袁氏的文论进行比勘,便可发现其中有可以沟通的内在联系。
首先,龙溪“现成良知”说启发公安袁氏确立心灵主体地位,提出“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龙溪认为,良知为心之本体,是天然之则。在主客体的关系上,一切客体都要接受作为心灵主体“良知”的裁夺。因此王畿说“格物云者,致此良知之天则于事事物物也”(65)。程朱式的“格物”,是向外穷理;而阳明、龙溪式的格物,则是将天理拉回内心,将世间道德理性交由良知自然裁定,从而使人不再被动地匍匐于道德理性的脚下,而是成为道德伦理的立法者和仲裁者。这具有极大的思想解放意义。龙溪说“身之主宰为心,心之发动为意,意之明觉为知,知之感应为物”(66)。心的投射与感应最后一个层面才是世间万物,万象都是心中之物;心与意、知、物的关系上,心为主宰。这就坚定地确立了心灵的主体地位。因此,龙溪极为推崇自信与自得。当有人问:“人议阳明之学亦从葱岭借路过来,是否?”龙溪回答:
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禅家之路,禅家亦不借禅家之路。昔香严童子问沩山“西来意”,沩山曰:“我说的是我的,不干汝事”,终不加答。后因击竹证悟,始礼谢禅师。当时若与说破,岂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岂惟吾儒不借禅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说,人孰不闻,却须自悟,始为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言也。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证而已。若从言句承领,门外之宝,终非自己家珍。(62)
这里,龙溪借禅宗公案说明人应该自悟本心、自信良知,自悟、自得才是自家珍宝。即使是圣人之言,也不过是印证我的本心而已。在个我与圣人的关系上,应是以我为主,确立个人的主体地位;否则一味迷信圣人,“从言句承领”,终不过是别人的东西,成为“门外之宝”。因此,龙溪极端张扬心灵的主体性,甚至认为真正的学术,只能是心学。他说:“夫学,心学也。人心之灵,变动周流。寂而能感,未尝不通也;虚而能照,未尝不明也。此千圣以来相传之宝藏,人人之所同有,惟蔽于私而始失之。”(68)其意是说只有变动周流的心灵、良知才是人人具有的、千圣相传之大宝藏,只是常人不曾觉悟到而已。
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实际上是龙溪心学在文学理论上的延伸和转化。伯修于此发其端,中郎、小修继之,遂使性灵说在文坛独张一军,蔚为大观。伯修反对为文“泥皮相而遗神情”(69),主张“士先器识而后文艺”(70),提出“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71)。辞达与不达,要看对心的抒写如何,这就确立了以心为本、文笔为末的文学主张。在袁中郎看来,作文能否成功,要看作家懂不懂心性之学。他说:“余谓文之不正,在于士不知学。圣贤之学惟心与性。”(72)这种看法,实是受龙溪心学的启发。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即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73)的文学主张;至万历二十七年,他再次指出:“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74)。在给朋友的信中,中郎介绍自己的写作心得:
不肖才不能文,而心有所蓄,间一发之于文,如雨后之蛙,狂呼暴噪,闻者或谓之阁阁,或谓之鼓吹,然而蛙无是也。兄丈读而赏之,大约如古人听蛙爱驴鸣之类,声情所触,偶尔相关,岂真下俚之语,足以畅幽怀而发奥心哉?(75)
不仅作诗文崇尚求真求达,直探心源,而且世间一切信心直行之人,在中郎看来都是富有趣味和诗意的: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其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76)
趣味在于表现真实的内心。在中郎文集中,他喜为奇人、畸人、癖人立传,他认为这些人的可贵之处在于有真性情。他写自己信心直行、无拘礼法的诗文也颇多,并且时常以幽默的语言出之。如中郎《记药师殿》一文写自己带仆人跑到佛寺中去借锅煮肉,致使庙中的“锅甑瓶盘之类,为仆子所羶”,可谓狂放之极。无论为人、为文,中郎都藐视陈规,得大解脱。这一切正如他所说“善学者,师心不师道”(77)。正是因为要直探心源,在主客关系上,他以心为第一要素,认为只要心思灵动,万境自然纳入心中。中郎以山水鉴赏为例说明心的重要性,认为“善知山水者”不一定非要像隐士那样“岩栖而谷饮”。他说:“孔子曰:‘知者乐水。’必溪涧而后知,是鱼鳖皆哲士也。又曰:‘仁者乐山。’必峦壑而后仁,是猿猱皆至德也。唯于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足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纵终身不遇,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是之谓真嗜也。”(78)只要心到了,精神到了,即使不至山水实境,也能与山水之美相往还。心是第一性,境是第二性。正是因为将心置于诗文写作的突出位置,他由此对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说法提出质疑:“夫使穷而后工,曹氏父子当为伧夫,而谢客无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纨绮终也”(79)。他以曹操父子、谢灵运、萧统兄弟等大富贵人同时又是大作家为例,意在说明只要心思深沉,不论人生何种境遇都会产生伟大作品。小修的文论,多是对中郎性灵说理论的阐发,在直抒胸臆一点上,他与两位兄长的创作观点是一致的。他说:“楚人之文,发挥有余,蕴藉不足。然直摅胸臆处,奇奇怪怪,几与潇湘九派同其吞吐。大丈夫意所欲言,尚患口门狭,手腕迟,而不能尽抒其胸中之奇,安能嗫嗫嚅嚅,如三日新妇为也。不为中行,则为狂狷。效颦学步,是为乡愿耳。”(80)在小修看来,只要直抒胸臆,文章“蕴藉不足”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其次,龙溪“现成良知”说启发公安派提出了“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公安派鼓吹“不拘格套”,矛头其实是对准风行文坛近一百年的七子派拟古潮流的。敢于反潮流要有巨大的勇气,而龙溪之学正是袁氏兄弟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动力之一。龙溪在其文集中多次挞伐“乡愿”之风;伯修在他的《读中庸》一文中曾抄入一段龙溪骂乡愿的话,并评价“龙溪论乡愿,极细极彻”(81)。龙溪说过:“贤者自信本心,不动情于毁誉,自信而是,举世非之而不顾,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为。若乡党自好,不能自信,未免有所顾忌,以毁誉为是非,于是有违心之行,其所自待者疏矣!”(82)又说:“若是出世大豪杰,一语之下,便当了然。本无生,孰杀之?本无誉,孰毁之?本无洁,孰污之?本无荣,孰辱之?直心以动,全体超然,不以一毫意识参次其间。”(83)自我的良知、本心是衡量世间一切价值的唯一尺度,那些外在于本心的是非、毁誉、荣辱甚至生死其能奈我何!龙溪有这种狂狷的气概,自然不会被教条格套、陈规习俗所束缚。
龙溪将良知之知称为德性之知,知识之知称之为见闻之知。在他看来,知识只有资助于德性才有其存在的意义。龙溪说:“夫良知与知识,差若毫厘,究实千里。……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学虑而得,先天之学也。知识则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于多学亿中之助而已,入于后天矣。”(84)在龙溪看来,“子贡、子张多学多见而识,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是信心不及,未免在多学多见上讨帮补,失却学问头脑。颜子则便识所谓德性之知,识即是良知之用,非有二也。……苟不明根因之故,遂以知识为良知,其谬奚啻千里已哉!”(85)龙溪评价说,孔门弟子中颜回的境界比子贡、子张高明。在他看来,子贡、子张不能自信本心,所以只能借助于知识以闻道;而颜回却懂得了德性之知的妙义,无须借知识以致良知,故此颜回能够成为高明的“亚圣”。龙溪认为,如果自信本心,知识不过是良知之用罢了。知识仅是致道的筌蹄,得道之后,筌蹄也就失去了意义。他说:“唐虞之朝,所读何书?鱼兔苟获,筌蹄可忘。于此参得透、放得下,得其不可传之秘,六经亦糟粕耳”(86)。如果靠知识才能闻道,那么洪荒时代无书可读的唐尧、虞舜怎么也能成为圣贤呢?可见,心悟是致道的重要途径,读圣贤书不过是求道的工具而已。就此而言,良知心悟是本,得道之后,六经不过是糟粕。他又说:“夫良知者,经之枢,道之则。经既明则无籍于传,道既明则无待于经。昔人谓‘六经皆我注脚’,非空言也”(87);“一部《论语》为未悟者说”(88);“若只在知识上拈弄,便非善学”(89)。在龙溪看来,良知自能知是知非,具有天然之则,是一切道德理性的根源;如能自悟,甚至无须借助于知识。他批评汉儒式的通过博学多闻以求道的方法:“以遍物为知,必假知识闻见,助而发之,使世之学者不能自信其心,伥伥然求知于其外,渐染积习,其流之弊,历千百年而未已。”(90)因此,就求道而言,本无格套可寻,泥圣人之迹并不可取,自信本心才是根本。将知识与良知的关系进行引申,龙溪也谈到了他的文学观念:“良知不由知识见闻而有,知识闻见莫非良知之用。文辞者,道之华;才能者,道之干。……是故溺于文辞,则为陋矣,道心之所达,良知未尝无文章也。”(91)作诗文学习古文辞,仅是属于知识范畴,依靠良知才是作文的根本。王畿文集中有关文论的内容虽然极少,但“不拘(知识)格套,独抒(良知)性灵”的文学思想几乎呼之欲出。
沿着王畿重良知、轻知识的思路而转入文学,便出现了公安派“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在袁氏兄弟看来,七子派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只从技法和语言模拟着眼,通过揣摩文学经典学习作诗文,无疑是一种知识主义的路向;而且这种汩没灵明的路向毒化文坛近百年之久。伯修批评说:“空同(李梦阳)不知,篇篇模拟,亦谓反正。后之文人,遂视为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语不肖古者,即大怒,骂为野路恶道。不知空同模拟,自一人创之,犹不甚可厌。迨其后以一传百,以讹益讹,愈趋愈下,不足观矣。”(92)他批评七子“流毒后学,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93)。袁氏兄弟反对七子派的格调说,最初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在万历二十四年,中郎在吴县首标公安之帜,即遭到“济南(王世贞)一派,极其呵斥”(94)。直到万历二十七年,他“不拘格套”、“不肯从人脚跟转”的文学主张仍被七子格调派“戟手呵骂”(95)。但中郎既已接受了信心直行的王学思想,便蔑视一切陈词滥调和知识糟粕,置世间一切是非毁誉于不顾。他扬言“凤凰不与凡鸟共巢,麒麟不共凡马伏枥,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96)他系统发挥“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论文便是那篇著名的《叙小修诗》: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97)
中郎还说:“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98)他鄙视七子格调派之诗“其高者为格套所缚,如杀翮之鸟,欲飞不得;而其卑者,剽窃影响,若老妪之傅粉;其能独抒己见,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者,余所见盖无几也”。(99)
综上可知,龙溪在哲学上相信良知而轻视知识,中郎便在文学上主张师心而不师先辈,这其中的致思理路非常一致。在中郎看来,不论是秦汉文还是盛唐诗,都不过是文学知识的陈迹;文之美恶并不在于学前人的格调有多么像,而在于有没有真性情。妇人孺子没知识,但他们唱的民歌有真性情,其价值反而在有知识的拟古派之上。就文学而言,抒写心灵永远是第一位的,本不必受先辈格套、路数的束缚。龙溪在哲学上敢于视六经、《论语》为糟粕陈迹;中郎在文学上便骂七子派的本本主义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100),小修骂拟古派“专以套语为不痛不痒之章,作乡愿以欺世”(101)。因此,公安派的“不拘格套”说实是受龙溪学术的启发,这个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再次,三袁对龙溪学术流弊的反思间接促成了公安派后期文论的转向。前已述及,龙溪的现成良知说极易使后学混认情欲为良知,这在当时就已经招致不少王门弟子的批评。有人质问王畿:“若曰‘无善无恶’,又曰:‘不思善,不思恶’,恐鹘突无可下手,而甚者自信自是,以妄念所发皆为良知,人欲肆而天理微矣。请质所疑。”(102)龙溪本人对这个问题亦进行了反思:“世间熏天塞地,无非欲海,学者举心动念,无非欲根,而往往假托现成良知,腾播无动无静之说,以成其放逸无忌惮之私,所谓行尽如驰,莫之能止。”(103)龙溪早年主张顿悟本心,反对人为修证;但到了他的晚年,通过自我反思,在学术上也做出一些调整,开始承认渐修亦是圣贤之学(104)。虽然龙溪现成良知的本意并不包括人欲在内,但其理论上的缺陷的确为后学的纵欲提供了口实。三袁作为龙溪的信徒,早年都有放荡不羁的生活经历。龙溪之学促成了他们的思想解放,从而敢于挑战权威,抨击七子派拟古风气,致使文坛形势为之一变,成了性灵派的天下。钟惺曾这样描述文风递嬗的情形:“今称诗,不排击李于鳞(攀龙),则人争异之。犹之嘉、隆间,不步趋于鳞者,人争异之也。”(105)而中郎则是向李攀龙辈发起首难的旗手。性灵说流行天下之后,人人又步趋中郎,以致又出现新的流弊。小修对此评论说:“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中郎)少时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棘刺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乌焉三写,必至之弊耳,岂先生之本旨哉!”(106)而在天下都拾袁氏余唾时,袁氏兄弟的文学理论却悄悄地转向了。转向的原因我认为恰恰在于他们的学术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
先说学术上的变化。三袁早年放荡的生活,一个直接的后果是疾病缠身。病弱的身体促使他们反思王畿、李贽式的顿悟之学的危害。伯修晚年“深恶圆顿之学为无忌惮之所托”(107),并对友人热衷于谈论“本来具足,个个圆成”式的现成良知说而大为反感,并奉劝友人“不如且拔置此事,作些有用生涯”(108)。中郎在万历二十七年之后,其学术亦悄然发生了变化。据小修追述:“先生(中郎)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李贽)等所见,尚欠稳实。以为悟修犹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伦物,偭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109)中郎这段话提到的“龙湖等所见”,这个“等”字应该包括龙溪在内。中郎自言:“儒者借禅家一切圆融之见,以为发前贤所未发,而儒遂为无忌惮之儒。”(110)这说明中郎已深刻体会到顿悟之学对自己的危害,转而想通过渐修、自律来静心强身。据小修说,自万历三十七至三十八年,他和中郎时时聚首,中郎“论学,则常云须以敬持,以澹守”(111),这种修养方法已接近程朱“持敬”式的路子了。中郎告诉小修:“四十以后,置粉黛,纵情欲,便非好消息也。”(112)小修亦将类似的话告诫友人:“四十以后,便当寻清寂之乐。鸣泉灌木,可以当歌,何必粉黛?予梦已醒,恐殷生之梦,尚栩栩也。”(113)小修还对自己早年纵情酒色以致疾病缠身痛悔不堪,认为自己的病即是由于“谭无忌惮学问,纵酒迷花”所致。他对朋友仍在信奉圆顿之学,为纵欲找借口表示了反感:“若毛道所云‘酒肉不碍菩提,淫嗔无妨波若’者,弟深憎之恶之,惟恐其与此等意见人相亲近也。”(114)儒家式的渐修不能解决问题,袁氏兄弟就转而归宗佛家净土,以因果报应的恐惧强迫自己清心寡欲,以图强体健身,修身养性。袁中郎作《西方合论》,宣扬佛教净土戒律;袁伯修对此大为叹赏,并亲自为之作叙。他们兄弟都认识到倘若“以放恣为游戏,以秽言为解黏。赞叹破律无行之人,侮弄绳趋尺之士”,则“若不为魔所摄,定当永隔三途。刀山剑树,报其前因;披毛戴角,酬还宿债”(115)。袁小修作《心律》,亦大力宣扬持戒观念。针对自己的好色,他担心“一生学道,而以淫死,岂不痛心!”戒掉自己种种恶习的途径就是用因果报应、地狱惨象来恐吓自己:“后有铁床铜柱之苦,犯之则立至”(116)。从而迫使自己守规矩章法。总之,他们终于认识到,人活在世间,是需要纪律约束的,无忌惮放纵会危及生命,来世也会下地狱。
学术上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文学理论亦不像早年那样激进,而是做了一些调整,由原来激进地反对格调派转而向格调妥协;由原来诗文无忌惮式的不讲法度,而逐渐变得像七子派那样讲规矩章法。小修曾指出中郎这种文学上的变化:“学以年变,笔随岁老,故自《破砚》以后,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诘,有杜陵,有昌黎,有长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117)这种风格已经向讲法度的格调派靠拢了。小修曾告诫那些学中郎文字的人:“(中郎)学问自参悟中来,出其绪余为文字,实真龙一滴之雨,不得其源,而强学之,宜其不似也。”(118)这已说明,中郎的诗文得之于学术,他学随年变,自然地文学风格亦发生了变化。小修受其兄影响,生活上逐渐节欲自律,在诗文创作上开始重视古人法度。他对前后七子也有了新的认识,正面的评价逐渐多了起来。小修说:“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国初何(景明)、李(梦阳)变宋元之习,渐近唐矣。……仆束发即知学诗,即不喜为近代七子诗。然破胆惊魂之句,自谓不少,而固陋朴鄙处,未免远离于法。近年始细读盛唐人诗,间有一二语合者。”(119)又说:“少年勉作词赋,至于作诗,颇厌世人套语,极力变化,然其病多伤率易,全无含蓄。盖天下事,未有不贵蕴藉者,词意一时俱尽,虽工不贵也。近日始细读盛唐人诗,稍悟古人盐味胶青之妙。然求一二语合者,终无有也。”(120)“今之作者,不法唐人,而别求新奇,原属野狐。”(121)这些文字都对早年作诗不讲格套表示了一定的忏悔,表现出向七子格调派回归的倾向。总之,从学术上顿悟式的不阡不陌、信心直行转向渐修自律、持戒甚严,从文学上反对格套、直抒心源转向重视法度、讲求含蓄,这其中致思的理路非常一致。公安袁氏后期文论与创作上的变化是他们对李贽、王畿等人的学术进行反思和纠弊的一个自然结果。
综上所述,龙溪的“现成良知”说在公安袁氏兄弟的心灵境界与生命历程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对他们文学理论的建树和创作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袁氏兄弟特别是中郎和小修,思想解放,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作品既有对民生国事的忧患,对山水的热爱;亦有浪言谑语,不讳言酒色享乐之作。他们的创作,时常给人以破胆惊魂、冷水浇背之感;他们挑战世俗,信心直行,诗文中能见到剖肝沥胆式的真性情。后世不少人批评公安派俚俗不雅,品格不高,但却无法否认他们的作品有鲜活的一面,能感受到作家活生生的个性和灵魂。与拟古派很多作家掩饰自我,故作雅言相比,三袁的作品是真文学,是活文字。龙溪学术给了他们巨大的勇气以挑战七子的文坛霸权,从而提出“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并以创作实绩终结了七子派的霸主地位,进而给文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学风气。但是,王畿“现成良知”说是一把双刃剑,对公安派的影响亦是利弊兼存。就学术影响而言,袁氏得大解脱、信心直行的同时,也有放纵不羁之病;就文学而言,袁氏发抒性灵、不拘格套而闪亮登场的同时,也给文坛带来了粗俚率易之病。这种粗率的文风时为后世所诟病。明末清初,随着时代的变化,公安派的势力终于风流云散,并被崇尚理性、通经学古的文学思潮所取代。直到清中叶,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再次崛起,成为公安派在清代不绝的回声。
注释:
①参见吴兆路《公安派与阳明后学》(《浙江学刊》1995年第2期)、周群《阳明学派与公安派》(《长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第四章中的第四节“阳明心学与追求性灵的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16)(17)(18)(25)(26)(27)(28)(29)(31)(39)(40)(52)(57)(65)(66)(67)(68)(82)(83)(84)(85)(86)(87)(88)(89)(90)(91)(102)(103)王畿著,吴震编校:《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第1页、第69页、第2页、第6页、第184页、第139页、第160页、第129页、第79页、第152页、第138页、第425—426页、第42页、第133页、第163页、第153页、第353页、第249页、第446页、第130页、第255页、第429页、第427页、第152页、第157页、第339页、第340页、第123页、第393页。
③[日]冈田武彦著,吴光等译:《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④参见陈寒鸣:《袁宏道与泰州王学》,《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
⑤(19)(38)(55)(69)(70)(71)(81)(92)(93)(108)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第240页、第251页、第232页、第82页、第91页、第283页、第281页、第284页、第286页、第227页。
⑥⑦(22)(23)(24)(37)(41)(43)(46)(47)(48)(49)(53)(54)(56)(61)(62)(64)(80)(96)(101)(106)(107)(109)(111)(112)(113)(114)(116)(117)(118)(119)(120)(121)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09页、第451页、第891页、第988页、第455—456页、第708页、第533—544页、第709页、第1073页、第444页、第952页、第1048页、第710页、第763页、第1000页、第708页、第451页、第756页、第486页、第756页、第727页、第523页、第709页、第758页、第796页、第762页、第473页、第1062页、第952页、第521—522页、第523页、第458页、第1029页、第1097页。
⑧⑨⑩(11)(12)(14)李贽著,夏剑钦校点:《焚书·续焚书》,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45页、第117页、第311页、第308页、第252页、第122页。
(13)汤显祖:《玉茗堂全集》诗集卷十七《读锦帆集怀卓老》,明天启刻本。
(15)日人冈田武彦将王畿归为“现成良知派”的代表,而陈来不同意把心斋与龙溪同归于“现成派”,理由是“龙溪之‘见在’与心斋之‘现在’并不相同”(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页)。其实,在阳明学的语境中,“现成”亦常作“见成”、“见在”或“当下”,其例不胜枚举(参见吴震《现成良知——简述阳明学及其后学的思想展开》,《中国学术》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版)。而同为阳明弟子的聂双江批评过龙溪的“见在良知”,另一弟子罗念庵亦批评龙溪的“现成良知”(参见《王畿集》第134页、393页),可见,视王畿为“现成良知派”其来有自,冈田氏将其归为“现成良知派”并没有问题。
(20)(21)(42)(44)(45)(63)(72)(73)(74)(75)(76)(77)(78)(79)(94)(95)(97)(98)(99)(100)(110)(115)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38页、第1290页、第1707页、第218页、第205—206页、第187页、第697页、第187页、第786页、第779—780页、第463页、第700页、第1582页、第1112页、第695页、第782页、第188页、第700页、第699页、第502页、第790—791页、第1705页。
(30)(33)(34)(50)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9页、第703页、第240页、第240页。
(32)孙奇逢著,朱茂汉点校:《夏峰先生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37页。
(35)侯外庐等著:《宋明理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36)中郎去世时,三袁的父亲年已七十(见《珂雪斋集》第795页)。三袁同母兄妹共四人,排行第二为女,是伯修之妹、中郎和小修的姐姐。在她五十岁时,小修曾为她写寿序,其中谈到两位兄长寿不望五,而其大姐年寿“后来尚未有涯”(《珂雪斋集》第432页)。翻检小修文集,亦不见为其父、其姊写的墓志铭或行状。大概其父、姊俱享高寿,去世当在小修之后。
(51)唐顺之:《新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五《与王龙溪郎中》,四部丛刊景明本。
(58)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袁稽勋宏道》,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
(59)纪昀等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93页。
(60)(105)钟惺:《隐秀轩集》“文昃集”序二《问山亭诗序》,明天启二年沈春泽刻本。
(104)王畿在《松原晤语寿念庵罗丈》中说:“夫圣贤之学,致知虽一,而所入不同。从顿入者,即本体以为功夫,天机常运,终日兢业保任,不离性体,虽有欲念,一觉便化,不致为累,所谓性之也。从渐入者,用功夫以复本体,终日扫荡欲根,祛除杂念,求以顺其天机,不使为累,所谓反之也。”(见《王畿集》第3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