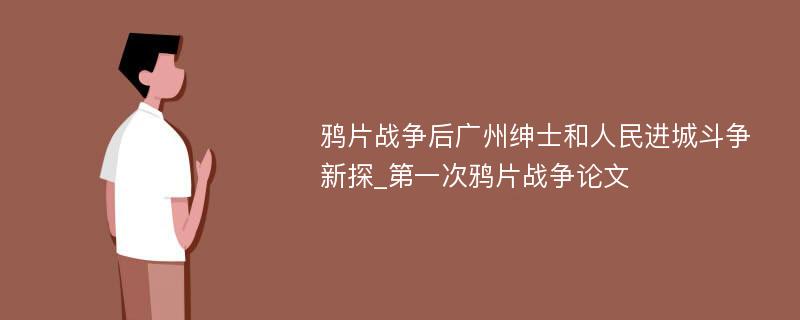
鸦片战后广州绅民反进城斗争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鸦片论文,广州论文,战后论文,绅民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5-0017-05
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定,英国人率先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对外关闭的国门,迫使清政府开放了东南沿海五个通商口岸。根据条约规定,英国人在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四口均按规定时间进城开市贸易。只有广州一口,原定于1843年7月27日开市,但因广州市民的坚决反对,英国人未能达到进城贸易的目的。对此事,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都予以充分肯定。“广州人民反进城斗争,是战后侵略与反侵略的焦点,这场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顽强斗争,对封建主义投降路线的坚决抵制。”(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9页。)广州“以升平社学为首所进行的反英斗争,一再地给英国人以打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注: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战后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主要表现为反英入城斗争,这场斗争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抗不平等条约的斗争。”(注:戴学稷:《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载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无疑,笔者赞同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人进城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面对外来之敌不屈不挠的英勇抗争精神的论述。然而,换个视角,将此事纳入近代工业文明产生,资本主义有如疾风暴雨般无情横扫世界各个角落的封建藩篱,整个世界无可避免地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巨变中加以审视,笔者不免对鸦片战后广州绅民的反进城斗争得出一些有异于前人的新论来,本文试作论述。
一、反进城斗争是一次重新关闭国门的努力
可以这样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于1840年是历史的偶然,然而,在这偶然的历史表象后面却蕴含着历史的必然,这就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战败是必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经典名著《共产党宣言》中以无可辩驳的分析,揭示了这一历史必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资产阶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歌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于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256页。)毫无疑义,中国的“万里长城”无论多么坚固,都不可能抵挡得住资产阶级商品低廉价格的重炮。在世界其它地方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后,尚有一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地方居然独立于市场体系之外,这对因不断扩大产品销路而“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的资产阶级实在是太有诱惑了。不谋而合,西方资产阶级虎视眈眈的目光一致地盯上了中国。挟“商品低廉价格的重炮”和货真价实的坚船利炮,以大英帝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双重大炮猛轰中国关闭的国门。中国绝对无法抵挡。战败、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不得不被迫打开已关闭多年的国门。
打开中国国门后,西方资产阶级战后开辟中国市场的努力遇到了中国朝野官绅民极为强劲的抵抗。可以说,鸦片战后,中国人中能够意识到鸦片战败,中国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前年未遇之强敌”,中国除了以开放的姿态改变自己,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免被时代大潮淘汰的有识之士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朝朝野野,上上下下,官绅百姓,相当一致的共识倒是:尽快把洋鬼子赶出去,然后重新关上被强撞开的国门,继续我们以中华为中心的“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令行禁止,四夷来王”的天朝上国之美梦。广州绅民的反进城斗争,正是此种思想指导下的一个典型案例。《南京条约》规定:“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广州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页。)条约规定广州城于1843年7月27日开市,外国人可以入城贸易。但令英国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自以为有国际双边条约为凭的行为竟然会在广州一挫再挫,广州开市竟至延缓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在广州扶植柏贵傀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之时。
请看英国人在广州开市贸易问题上的失败记录。
1843年7月27日,是《南京条约》规定的开市时间,英国人按约而来,要求入城贸易和在广州城河南地方“搭盖楼房,建造署衙。”(注:中国历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两广总督耆英准备按条约规定同意英人之请。不曾想,遭到以何有书(广州升平公所主持人)为首的地方绅士阻挠。耆英于是答复英国人曰:他本人是同意让英国人进城的,但现有80多个绅士联名致函他表示反对,虽然他已当面告诫他们,拒绝接受他们的意见。但是经过连日的考察,觉得民情的疑虑确实还没有清除,所以必须再等待一段时间,让他和其他官员设法使人安定下来(注: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6页。)。经耆英之解释,英国人同意暂缓进城。
1845年底,第二任港督德庇时又向粤督耆英提出入城要求,并“以缓交舟山要求挟制”(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080页。)。耆英派广州知府刘浔出城到英船上密商进城日期,事情被广州社学侦知。刘浔回来后,社学壮勇一千余人围冲知府衙门,并火烧该衙门。耆英为平息事态,撤掉刘浔知府职务,并再次向英人表示“舆情不洽”而拒绝了英国人第二次入城之请。德庇时只好再次退却,“将舟山如约退还”,表示“进城一节只可暂缓,不宜竟废”(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081页。)。
1847年3月,发生英美人结伴游佛山被当地人围殴一事。港督德庇时在英国政府同意后,带兵千余乘船驶入珠江并入住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有此番不进城不罢休之态。他照会耆英,因英国人被侮辱殴打,他将“进城惩凶”。“如不依允,伊将带兵闯入”(注:琴阁主人(华廷杰):《触藩始末》,《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第98-99页。)。闻此讯,广州社学又再次行动起来,防堵城门,坚决不准英国人入城。耆英不得不携广东巡抚黄思彤共赴城外与德庇时协商,达成协议。耆英保证对“欺凌”英国人的凶手予以查究并惩办,同时允诺“入城一事约在两年以后”(注:琴阁主人(华廷杰):《触藩始末》,《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第98-99页。),届时一定准允英人入城贸易。于是,德庇时率英军舰再度退回香港。时人如此评议耆英:“耆相……不敢竟许入城者,惧激民变;又不敢不许者,惧开边衅,不得已约以两年为期。意谓目前获无事,傥两年以后我仍官此,临时再作办法。况已经入阁,傥得离是任,则两年后与我无涉矣。”(注:琴阁主人(华廷杰):《触藩始末》,《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第98-99页。)
时人评述没错。果然,1848年1月耆英奉调入京,离开了他日夜忧心的是非之地——广州。道光帝任命徐广缙升两广总督,叶名琛任广东巡抚。1848年8月,香港总督也换了人,由文翰代替了德庇时。闻此讯,习惯人治的道光帝幻想,港督易人,新港督可能会放弃对广州入城的要求。因为1847年的两年只是耆英德庇时之约,现时移人易,情况会变的。但是,道光帝完全错了,他犯了以己度人之错。殊不知,法治国家,人常易,但制度不变,契约不变。
1849年2月,新港督文翰以耆英所允两年之约届满,要求按约入城。广州社学闻之立即行动起来。而这一次的反进城是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原来,早在1848年初,离约定的时间还差一年时,广州城内的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以梁廷楠为首,联合绅士许祥光等人,号召民众“出丁设械,为拒夷人入城之备。”他们联络“城厢内外街之团勇,户户出兵,合计不下十余万人,而且按铺捐资,储备经费,合计数十万金”(注:转引自戴学稷:《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鸦片战争史论文集》,第229页。)。总督徐广缙见社学准备早,力量大,反进城态度坚决,遂认定对英人的入城要求,“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必致内外交讧。”(注:转引自戴学稷:《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鸦片战争史论文集》,第229页。)于是,徐广缙一口回绝了文翰的入城之请。文翰震怒,带兵船到虎门一带实行恫吓。徐在群众支持下,亲自到虎门的兵船上坚拒文翰。与徐的虎门之行相配合,当夜“四城灯烛照耀,殆同白昼,枪炮声闻十里。”(注:梁廷楠:《夷氛闻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9页。)文翰见此,得“罢兵修好”,不再提进城要求。
从暂时看,广州绅民的反进城斗争获得了胜利。然而,西方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广州反进城斗争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更大的暴风雨必将再次降临,等待中国人的,只能是更大的失败,丧失更多的权利。果然,1856年,英国人以此为借口之一(注:1854年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华公使鲍令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要点有六,其中的第六点要求即为:“清帝应颁特旨,准英人按照道光二十七年耆英所约进入广州城。”),联合法国,发动了第二次侵华战争,彻底粉碎了中国人试图重新关闭国门的梦想。
二、反进城斗争是华夷有别之一元世界观的惰性延续
华夷观念是维护儒家以君权为核心,华夷内外的等级名分制的意识形态。历经3300余年无间断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中华文明在中世纪的农耕文明阶段曾表现出相当的先进性。直到鸦片战争前,清帝国已完善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与华夷有别的意识形态相匹配的制度层面上的朝贡国体系。这个体系大致呈三个同心圆展开。处在里面中心位置的是清王朝本土及边陲区(包括18行省、东三省特别区及内外蒙古、青、藏、疆等)。第二圈是朝鲜、琉球、越南、暹罗、老挝、缅甸、尼泊尔、苏禄等朝贡国。第三圈则是无幸淋沐沾浸儒家教化的化外夷狄蛮貊。故而清朝君臣的世界观,是以中华为中心的一元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天朝君临万国”,海内外莫与为对,亦即世界上不存在第二个与中国平起平坐的主权国家。在此种理念的基础上,清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是宗主国与藩属国不平等交往的原则。藩属国国王必须由清帝册封授权。各国必须依亲疏远近定期向清廷纳贡,国王和贡使觐见清帝时必须行三叩九跪的臣子大礼。否则,将被视为对天朝国体和宗主权的亵渎。
与清朝的一元世界观相对应,西方基督教文明影响下的欧美各国,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的划时代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起的航海热潮,催生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产业革命,形成了另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准则是有近代意义的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原则。这个世界体系是由多个并列的大树般的主权国家及其殖民地组成的多元世界。
一元世界观和多元世界观的碰撞不可避免。鸦片战争便是以儒家文明为基础的朝贡国同心圆体系与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多元体系的第一次剧烈碰撞和冲突。其结果是朝贡国体系被撞开一个巨大缺口。在南京、黄埔、望厦等一系列条约上,中国代表在英法美等国代表的威逼下,被迫痛苦地写上:两国及两国外交官之间“往来俱用平等”;“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注:肖致治等:《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等一干“大损天威”的条款。于是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暂时不得不并存两种对外关系制度。一方面,依据传统的朝贡国制度、宗属关系准则,处理与亚太地区原有朝贡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依据强加的条约制度和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准则处理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两种制度并存,乃是一种过渡形态。过渡期两种原则的经常混淆,令中国和西方各国均感到很不舒服。尤其对中国而言,条约制度、平等原则实在是对华夷有别秩序的核心——君臣主从、上下尊卑之关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给对内维系等级森严的专制统治造成致命之腐蚀。
除了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阶层痛恨西方强加的主权国家平等交往准则外,中国的士绅阶层在这一问题上和官僚阶层的认识达成高度统一。士绅可以定义为民间已经取得功名,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识礼之人。这是一股庞大的政治势力,是朝廷对全国实行统治的中介。他们的思想状况,上影响朝廷的决策,下影响农工商阶层的行动,他们思想的开放与封闭,是中国整个国家封闭抑或开放的风向标。
鸦片战后,士绅阶层固守华夷有别的一元世界观,反感、排斥、拒绝多元世界观的主权国家平等交往、自由贸易等现代观念。在广州这个对外交往的前沿,士绅们蔑称西方人为“鬼佬”,以与“鬼佬”交往为耻。士绅阶层的这种浸肌浃髓的愚昧观念,与理应在战后采取的理性考察西方,取法西方文明,变法自强,使古老帝国走向世界,力争在多元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理性思维背道而驰。使得中国继续在华夷有别的国与国交往的旧轨道下惰性延续着。广州的反入城斗争正是这种惰性延续之一次有声有色之演练。
当1849年英国人按与耆英之约重申入城要求,又一次被广州绅民挫败,不得不与广州绅民“罢兵修好”时,上上下下的中国人都沉浸在又一次挫败外国鬼佬的喜庆之中。请看道光帝的高兴与得意:“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朕深恐沿海居民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之。……本日由驿驰奏的入城之议已寝,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注:梁廷楠:《夷氛闻纪》,第166页。)。广州市民则陶醉于“此次官民一气,兵勇齐心,锋刃未交,梗顽顿解”(注:参见麦天枢、王先明:《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第五篇“结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448页。)的胜利之悦中。人们全然不察在旧轨下延堕愈久,只会使中国这只睡狮睡得愈沉,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取法愈是艰难。
三、反进城斗争是对国际交往中契约制度的本能抵制
广州反进城斗争的实质是中西文明的碰撞、冲突和斗争。从表层看,是英国人言之凿凿、振振有辞地要依据他们认定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大法——《南京条约》所载之内容要求进广州城开市贸易,而中国人坚决不准他们进城,也不管这是否已载之条约。从皇帝到士绅到农民壮勇,在这点上达成空前共识。这就是,《南京条约》是枪杆子逼迫下的屈辱和约,不是万不得已是不打算遵行的。从深层看,则表现为习惯专制独裁人治的中国人对自由民主法制的近代西方文化的产物——契约制度的极不理解与本能抵制。契约,看起来很简单,也就是两方面或几方面在追求各自利益时相互协商、妥协、订立的订约人须共同遵守的条文。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对契约之解释后面,却包容着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意识、风俗习惯的巨大内涵。在西方,经过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诞生前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在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中诞生了现代公民意识:民为邦本,一切公权均来自于人民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摆脱了以往的家庭、宗族、民族的血缘、亲缘、地缘的束缚,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解放了的西方人开始纷纷“奔走于全球各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相辅相成的是此自由以不得干预、剥夺他人之自由为行为之准则。在此基础上,个人追求自由与不干涉他人追求自由最基本的交往准则相应产生,这便是契约制度。规范公权执掌,涉及全体公民利益的契约是宪法、行政法等公共法律。而规范国与国交往行为的则是国际间的契约——国际双边或多边条约、公约。“条约应当遵守”是西方社会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公认,并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之一。当然,这一准则在西方也并非时时遵守,经常遭践踏。但一般而言,毁约者都是当自身力量足够强大,而条约内容于己不利而又修改无望时,方敢于去践踏条约。
与国际契约(国际双边或多边条约)的产生土壤——西方文明完全不同,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公民概念。中国的老百姓是只知尽义务而不知权利为何物的。每个人都被限定于家庭、宗族、国家的既定关系中,个人独立意志从不被承认,由此而形成一种天下一家的一统体系。与这个体系相适应的是政治上的独裁专制;思想上的君权神授;文化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扼杀思想舆论自由;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价值取向上的定于一尊、大—统;而表现在国与国的交往上,则很自然的就是一元世界观的同心圆体系。正因为在中国人的概念中从无平等主体之说,因此,中国人对诞生于西方文明中的契约制度极为陌生。当以大英帝国为首的西方人将一系列国家间的条约——南京、黄埔、望厦等国际条约强加于清王朝时,中国人对这种现代国际条约制度,先是掉以轻心,待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后又本能抵制,并尽可能拒绝执行。
首先是定和约时马马虎虎、不知轻重。在就中英南京条约谈判时,英国方面极为慎重,提出的条款都认真考虑过中国君臣的接受程度,定出了条款的最后底线。在最后底线的基础上再定出第二条防线、第三条防线,准备着和中国刚打完一场有硝烟的战争,再接着打一场无硝烟的定约谈判拉锯战。与英方代表对条约的极为重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方对条约细节的极无所谓。开始派去与英方接触斡旋的竟是中方代表之一—伊里布的一位管家张喜,由他来讨论涉及中国主权的若干重大问题。而中方的三位正式谈判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秉道光皇帝旨意,只想尽快结束战争,让英国人尽早离开中国,因而几乎是对英方提出的涉及中国重大权益的条约内容照单全收,惟独在条约定由皇帝批准(亦即所谓“用宝”)问题上纠缠不休,不肯让步。最后是道光皇帝同意“用宝”(盖玉玺),才解决了这一难题。中方代表在重大权益问题上的爽快让英方的谈判代表感到吃惊。“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的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中国的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849》,第98-100页。)以至英方代表“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849》,第98-100页。)于是,英方又利用中方的这一心理诱惑中国代表出让更多的权利。事后,英方代表高兴地向女王报告:“原以为要反复争取的权利,很轻易地就从中国的钦差大臣处得到了。”(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849》,第98-100页。)
其次是定合同后,对对方依合同办事百般不愿,并进而毁约。英国人签了和约后只顾高兴,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认认真真字斟句酌的谈判条款在中国代表这里一通即过,那是因为,中国代表及清朝君臣压根没有现代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概念,压根没有合同一旦签定,在没有什么“不可抗力”干扰的情况下,就得认真履行的观念。尤令英国人没料到的是中国人订合同也是一种“羁縻”手段,目的乃在于让英国人“迅速议定,全数退出大江。”(注:严中平:《英国纺织资本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鸦片战争论文集》,第17页。)故当英国人撤退后就要毁弃这枪杆子逼迫下的和约了。所以,1847年7月,当英国人要求依约进广州城时,广州绅民坚决反对,拒不按约办事。当1849年2月,英国人按与耆英议定的两年之约再度要求进城时,不但一般绅民,连总督都坚决毁约反对他们进城。
按照我们以往的看法,认真履行不平等条约理所当然是卖国主义,而奋起毁约抵抗则是英勇的爱国主义。因此,鸦片战争期间最早直言不讳的主和者——浙江巡抚刘韵珂一直戴着顶“投降派的帽子”。而此期间真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属凤毛麟角之列的《瀛环志略》一书作者徐继畲则由于将“泰西”说得比天朝还好,是有“乱心”而致其不可多得的优秀著述被封禁多年。稍后李鸿章、郭嵩焘、丁日昌等主张“信守和约”的洋务大吏更是长期背负“卖国贼”“丁鬼奴”等骂名。
殊不知,不遵守国际条约,而自身又无实力时,往往“爱国主义”导致更大权益的丧失。所以,当英国人在广州入城问题上一挫再挫三挫四挫的消息传回英国后,有着“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从而赚取最大利润之阶级本性的英国资本家们在国会咆哮:我们“必须教训中国人,要他们懂得条约必须履行的时候已经到了!必须教训中国人,要他们尊重条约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他们没有履行那个条约上的许多重要规定。他们不许(外国人)进广州城;他们强征条约精神所不许可的税;他们几次无缘无故地以最粗暴的态度污蔑不列颠国民。现在,他们必须受教训……要教育他们必须尊重他们所签定的条约。”(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849》,第98-100页。)更有资本家在国会怒吼:“我们应该鞭打每一个穿蟒袍而敢于侮辱我国国徽的官吏。”(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4-135页。)“要把这般浑身纽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般服装的坏蛋吊在桅杆上示众,以教训华人重视英国人。”(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4-135页。)而一些政客则用斯文些的语气鼓动战争:“中国人这样把外国人排斥于这个城市之外是违背了他们近来与英国签定的条约精神的。他们这种行为是不讲理的、愚蠢的、孩子气的和不可恕的,并给我们以充分的理由去向中国政府提抗议。”(注:广东文史馆编译:《鸦片战争事例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4页。)“幸好我们有能力强迫中国接受,我们要等到中国表示出它已老老实实地、分毫不差地履行条约的条款为止。”(注:广东文史馆编译:《鸦片战争事例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2页。)正是这些资本家和政客们在国会讲坛上的联声咆哮、怒吼、宣传、鼓动,终于让英国的上下议院通过新一轮的对华作战案,导致中国在西方列强英法俄美等国的联手打击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丧失更多更大的权益,遭受更惨重的损失。
标签:第一次鸦片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阿芙蓉论文; 中国英国论文; 南京条约论文; 近代史资料论文; 英国人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