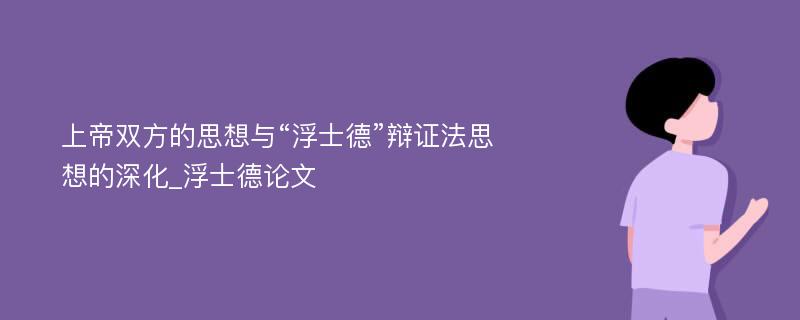
两面神思维与《浮士德》辩证法思想的深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浮士德论文,神思论文,辩证法论文,两面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德国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的诗体悲剧《浮士德》,其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已经不仅仅属于它所产生的那个古典时代,在思维模式的意义上说,它更富于现代艺术韵味。概而言之,它的现代艺术韵味的一个极其鲜明标志,是歌德在创作这部超时代的作品时体现出了思维方式的巨大更新和转化。
人们都承认,歌德是艺术领域中的辩证法大师,他的《浮士德》充满了极其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注:关于这方面的意见,请参见国内出版的众多的教科书中有关歌德及其《浮士德》的章节。)。以前国内外学术界,包括笔者本人撰写论文时,在谈到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表现的辩证法思想时,都看到了其“极为深刻”和“博大精深”(注:参见拙著《论〈浮士德〉思想体系的矛盾性》,刊于《国外文学》(京)1993年第1期。),但细究这种解读和阐释,又无一不是在所谓的二元对立统一的分解思维模式的层面上进行的。而我们又在有意无意之间,把这种二元对立统一的分解思维模式,看成是歌德辩证法思想得以在《浮士德》中实现的主要方式。这样,《浮士德》通过艺术和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丰富多彩的辩证法思想,实则变成了单纯的形而上学式的图解,变成了对事物内部相互排斥的两种因素对立与统一的机械解释。
就其本质而言,我认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不仅仅在艺术技巧上,而且在思维模式深处,均体现出一种现代性思维的强烈韵味。众所周知,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逻各斯中心主义出发,形成了二元对立统一的思维观。“逻各斯”(Logorentrism)是希腊哲学和神学用语,本义是指隐藏在宇宙之中,支配宇宙并使宇宙具有形式和意义的绝对神圣之理,是超然万物之上的“道”,是关于正确阐明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逻各斯”在本质意义上与“上帝”、“道”、“绝对理念”、“终极真理”等同一)。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乃至人的精神世界等万事万物都是“逻各斯”的外化。这样,当“逻各斯”外化为具体的自然界和人类世界时,换言之,当“人”背离“上帝”而下凡时,与“上帝”(道、终极真理)相对立的谬误得以产生,从而使“逻各斯”不再以纯粹的本真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整个世界呈现出一正一反(A与B,即正确与谬误、善与恶等))的二元对立,从而构成了事物的矛盾性的存在。而人类正是通过对“逻各斯”的现实转化物(自然,人类世界,包括人自身)矛盾的认识、发现和解决,祛除谬误,达到向终极真理的回归。我认为,我们以往的对《浮士德》的研究和对《浮士德》辩证法思想的揭示,均是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的(注:参见拙著《论〈浮士德〉思想体系的矛盾性》,刊于《国外文学》(京)1993年第1期。)。但是,随着人们对《浮士德》认识的深化,我们越来越看到,它在思想意义和结构意义上的关系之丰富与复杂,已经不能再被二元对立统一的分解思维方式所揭示出的辩证法思想所涵盖。因为《浮士德》给我们提供了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所解释不了的新东西。这就说明歌德在创作《浮士德》时,一定是超出了二元分解思维模式的限制,走向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加之歌德是诗人,是用形象来思考和创作的。而艺术作品的形象性以及形象的巨大包容性,也为他运用新的思维形式创作《浮士德》提供了可能。
由于任何艺术形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前提之一是人们的思维模式由前者向后者的置换。对歌德《浮士德》艺术世界的考察和评估,我们也应该而且必须从其思维方式转换的角度来进行。我认为,歌德在创作《浮士德》时,所采用的并不完全是当时已成时尚的二元对立统一的分解思维的模式,同时他也采用了现代思维科学的方式之一——两面神思维模式进行的。他的辩证法思想,正是这两种思维形式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二元对立统一的分析思维模式,如前所言,是以“逻各斯”为“最高本真”,以其分化后的二元对立为思维前提,以对实物的实际分析(分解)动作为基础,由两种信号系统协同活动所实现的。其逻辑语言形式表现为A与A(非A)的对立,具体地表现为相互排斥的两种现象、理论或观点的对立。在审美领域,它常常通过肯定事物的美或丑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这种思维模式也强调综合,或曰合成,但这种综合或合成又是在对立因素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也可以说,这种分析思维成为了传统思维的一种基本范式。
而两面神思维则是现代科学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科学的出现,现代科学的思维模式之一的两面神思维也走向了成熟。两面神思维主要是从总结爱因斯坦、玻尔等人的科学思维方式提出来的,因古代罗马时期朝两个相反方向视向的门神而得名。与分析思维一样,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也是两面神思维得以成立的基础和前提。两面神思维的主要内涵包括:(1)是指同时积极地构想出(而不是被动机械地分解出)两个或更多并存的、同样起作用或同样正确的相反的或对立的概念、思想或印象。(2)它对于A与(非A,不是B)的矛盾冲突是同时肯定A与(非A),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并由此获得整体性的认识。A与(非A)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强调其整合性。(3)从现代科学实践来看,两面神思维强调已有成熟理论的不完备性,即A中存在自身不能确定的问题,A的不完备处导致了(非A)的产生。(4)从认识的过程来看,直觉、想象、灵感等非逻辑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它们作用于A与(非A)冲突的悖论之中,从而发现新理论的萌芽。作为科学理论基础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不能从经验中归纳出来,而只能以经验事实为引导去直接领悟。
我认为,两面神思维与分析思维一样,其本质都是辩证思维,但它却是辩证法在认识上的一次拓展和深化。应该看到,传统思维强调A与B的对立及其对立的统一,这无疑是认识和思维领域中的一场革命,但也极易造成两个对立面机械对立和人为统一的思维范式。事物的复杂性还在于,在很多情况下,对立的统一并非是在成与毁、善与恶和爱与恨等两个极端上进行的,成与成、毁与毁、善与善、恶与恶等也可以构成对立的统一。而这种两面神思维正是在这方面深化了《浮士德》所采用的传统分析思维模式的辩证法的构成。
两面神思维其本质属于现代的符号思维之一种,它不仅对人们用科学的手段认识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样,在艺术和美学领域,也带来了人们艺术思维模式的激变。
应该指出,在歌德创作《浮士德》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是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辩证法产生时期,以辩证逻辑为内涵分析思维方式获得了思想界和文化界的自觉认同。而在此时,两面神思维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其思维模式还没有形成。但是,这并不说明,歌德在创作中完全排拒了两面神思维的使用。恰恰相反,歌德正是在其创作时,大量地运用了两面神思维的运作方式——尽管是不自觉的和是与分解性思维同时使用的。
二
当我们进入歌德所创造的博大而深邃的《浮士德》的艺术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其辩证法的思想充溢着这一艺术精品的各个层面。为了理解的方便,我想从两个系统层面—显性系统层面和隐性系统层面上做出分析,看歌德如何将传统的分解性的思维与两面神思维在《浮士德》中进行了有机的融合,从而进一步揭示出他对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卓越把握。
首先是在显性的系统层面上,歌德在《浮士德》中所展示的对立因素包括:天堂与地狱、天帝与魔鬼、浮士德与靡非斯特非勒斯、海伦与福尔基亚斯等等。在这些对立中,明显地显示出了善与恶、成与毁、美与丑两极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在作家看来,《天上序幕》一场中,天帝代表“至善”,魔鬼象征“至恶”;在全书中,浮士德与魔鬼靡非斯特是具体的“善”和“恶”;而浮士德自身也体现出“上升”与“沉沦”的明显对立。毫无疑问,在这种明显可见的对立因素的描写中,作家通过性质不同的矛盾对立双方的运动,体现着鲜明的辩证法思想。并且,我还要指出的是,这种辩证法思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是在以前的其他作家创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认为仅仅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解释,一方面不足以完全说明歌德在《浮士德》中所体现出来的辩证法思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实则贬低了《浮士德》作品中辩证法运用的崭新的方法论意义,扼杀了他凭借自己的聪慧和灵敏所领悟到的“两面神”思维的真谛。要了解和把握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对《浮士德》创作时体现出的隐性层面的东西,即两面神思维的运用所体现出来的东西,加以科学的说明。
所谓隐性系统层面的东西,是我们在阅读这部作品时,不能一眼看出,而是必须通过深入分析研究才能得到其微意的东西,是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东西。下面,我将从《浮士德》中,举出一些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
例证之一:在对《浮士德》的创作考察和研究中,关于“天帝”和“光明圣母”二者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很多国内外的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天上序幕》一场中,本来天帝坚信浮士德是个善人,不会迷途,并与魔鬼靡非斯特打赌,赌的是浮士德。但到了第五幕的最后一场《山谷,森林,岩石,邃境》中,拯救浮士德灵魂的则变成了奉旨而来的天使,带他“向更高的境界奋飞”的,是“光明圣母”。作家通过剧中人玛利亚宗之博士之口唱到:“处女哟天后,女神哟圣母,诚心皈命你,恩佑永不渝!”郭沫若先生看到了这一矛盾,指出,在浮士德死后,“天上的至尊者却是一位‘光明圣母’而不是上帝,这是一个有趣的表现”(注:参见拙著《论〈浮士德〉思想体系的矛盾性》,刊于《国外文学》(京)1993年第1期。)。又说:“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就在诗剧一头一尾的彼此之间也有矛盾,那便是一开头是男性的上帝,而一结尾是女性的光明圣母”(注:郭沫若:《〈浮士德〉简论》,见郭沫若译《浮士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页。)。尽管对这一矛盾的描写,郭沫若有他自己的解释,但我认为,在作家歌德的心目中,“天帝”和“光明圣母”的本质内涵应该说是一样的,都是观念中“善”的代表与化身。那么,歌德的这种写法是创作描写中的失误吗?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恰恰在这种貌似笔误的描写中,展示了歌德两面神思维的认识特点。在歌德看来,作为至善化身的“天帝”,本身虽然具有制约万物,吞吐太荒的功能,但它仍然是不完善的——即它只是一种最高的精神,是一种终极的“善”(至善)的观念。作为一种最高的精神或终极的观念,它只是“灵魂”而非“肉体”,它是“终极的价值尺度”而非是“终极的拯救动作尺度”。这诚如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中的圣灵与圣父、圣子的关系是一样的。这样,同样做为“至善”的观念,“光明圣母”也有着自身的不完整性。她与天帝的差异表现在:“天帝”内涵仅指向“至善”观念的最高概念性,“光明圣母”则指向至善救赎的最高具体性,正是这二者间的同质对立或互补,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的“至善”整体。换言之,肯定“天帝”作为“至善”的观念性和“光明圣母”作为“至善”的具体性,正是两面思维的特性。即是在肯定A的同时,也肯定,并发现其间联系的认识的反映。
例证之二:在隐性层面的对比描写中,同质对立还表现在天帝与浮士德的关系之中。我在此前写过的几篇论文中,曾谈到过这样的意见,即天帝是至善的化身,而浮士德则是具体的善的代表,是“神性的写真”。浮士德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恰好体现了具体的善向至善的复归。这样,在同属于“善”的“天帝”与“浮士德”这两个符号载体中,“天帝”只是“善的观念”而非“善的行动”,而“浮士德”的内涵则指向“善的行动”而非“善的观念”。这种各自的特征实则也是导致着两面神思维模式中A与(非A)的同时方面,展示着事物同质构成的两个方面。
从上述的考察中也可以看出,天帝、光明圣母和浮士德,它们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即均是“善”的代表与化身,但同时又是“善”的发展的三个阶段,或曰“善”的三个梯级层面。天帝为终极者,光明圣母作为救赎者和浮士德作为实践者,它们之间也形成了同质的矛盾关系。前面我们曾说过,两面神思维主要特征之一是积极构想出两个或更多并存的、同样起作用的概念、思想或印象,同时肯定A与(非A)。在这三者关系中,歌德实则也在有意无意之间,精妙地展现了两面神思维的精髓。
例证之三:魔鬼靡非斯特非勒斯是歌德在新的思维原则和审美原则指导下写成的崭新的艺术形象。他是消极、否定和恶的象征。很多学者曾深刻指出,他与浮士德构成了善与恶、成与毁、肯定与否定的矛盾统一体,从而体现了歌德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显性层面的背后,还隐藏着隐性层面的东西——自身同质构成中的对立的矛盾。
有这样一个现象引起了愈来愈多的学者的注意,即靡非斯特不权是浮士德的对立面,同时,他与天帝也构成了对立面。这种现象说明,靡非斯特作为“恶”的代表,他的符号指代可分为两种职能:一种是与天帝相对应的“至恶”的观念职能;一种是与浮士德相对应的“具体的恶”的行动或动作职能。当在《天上序幕》中,靡非斯特与天帝相对时,我们看到,他能成为天帝的对手,因为首先他本身就是“否定的精神”,展示的是“至恶”的观念性本质。在这里,他只有思想,没有行动。换言之,在这一幕中,他只是观念形态,而非形象状态。而到了第一幕他出现在浮士德书斋中的时候,先以“尨犬”,后以面目丑陋的人的形象伴随着浮士德的行动,这说明,此时他已由观念形态转化为具体形态,由无形变成了有形。这样靡非斯特实则就成了既是“天帝”所代表的“至善”的对立面——至恶,同时,他也是浮士德所代表的具体善的对立面——具体的恶。他实际上是“至恶”的观念和具体的“恶”之统一体。
那么,至恶与具体的恶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歌德看来,至恶作为事物发展的终极力量之一,如果不变成具体的恶,是难以起到“做恶和造善之一体”的作用的。实际上,在这部杰出的悲剧中,浮士德五个阶段的追求,始终是以靡非斯特作为具体的恶的不同化身,作为“至恶”的具体行动的承载者来作为推动力的。换言之,变形为或化身为不同面貌和不同形态的具体的恶,才是构成具体事物前进的动力。至恶的观念缺乏行动的缺憾必须要具体的恶的行动性来弥补;而具体的恶的不完整性和片面性则需“至恶”观念的宏观性和包容性来避免其局限。这样,“至恶”的“缺憾”和“具体恶的局限”使其各自都形成了自己的不完整性。而我们说,又恰恰是这种各自的不完整,构成了同质间的矛盾对立与统一。他们之间的相辅相成,构成了极富活力的“恶”的统一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歌德在塑造靡非斯特的形象时,也是深得两面神思维之意蕴的。
例证之四:在作品主人公浮士德身上,也存在着同质矛盾的构成现象。值得提出的是,现在,人们对浮士德身上的善与恶,上升与沉沦,灵与肉之间的异质矛盾构成看得很清楚,但对他身上同质矛盾的构成现象还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或者说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例如,永不满足,不断追求更高的理想,向至善的境界飞升,是他性格的主导方面。但这种对至极的追求精神又常常与他具体追求善的行动发生着矛盾。他本能地感到,最终达到“至善”,能够喊出“你真美呀”,是一种最高的幸福。但同时他又常常在行动中体现对人间爱情、政治生活、古典之美和所谓事业功勋的留恋和沉溺。这样,浮士德自身对至极的善的追求和对具体的善沉溺,也构成了同质矛盾关系。应该说,他在每一个悲剧中,都表现出了他所代表的善的不彻底和不完整性。每一次他都误以为洞悉“至善”的真谛,达到了“至善”的境界,其实质也不过是一场悲剧而已。这样,浮士德身上的永不满足,向更高的灵的境界飞升的宏大精神和奋斗目标,就同他的具体行动间构成了同质对立和互补关系。追求具体善的阶段性和这种追求的无限性相结合以及相互作用,就使得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这一形象符号,既不流于观念的空泛,又不局限于具体的所指,从而使其“追求善”的内涵极其厚重丰满。这样,浮士德形象的塑造本身,也体现出了两面神思维的鲜明特征。
三
两面神思维在《浮士德》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是对歌德辩证法认识的再一次深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通过反复细读《浮士德》这部作品,我认为,作品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实则是建立在两个系统与三个层面上。所谓两个系统是指:一是立足于传统二元对立统一的分解思维模式基础上的正反(A或B)两方面的对立统一;另一个系统是指建立在两面神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正正或反反(A与)两个同质方面的对立统一。在这两个系统中它们均有自己各自的构成对象、事物性质和构成方式,体现出来相对的独立性。所谓对立统一关系三个层面,应该说,(1)主要是指正反对立统一的层面;(2)正正或反反同质的对立统一层面;(3)由这两个系统所构成的对立统一的层面。
首先,歌德深谙不同质事物间对立统一的构成和规律。我在一篇论文中,曾指出:“在《浮士德》中,歌德以艺术和美学的方式,显示出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注:郭沫若:《〈浮士德〉简论》,见郭沫若译《浮士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页。)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汲取当时先进的哲学和科学思想,通过他所改造过的古老的浮士德的传说,表现了世界上和宇宙中万事万物中不同质所构成的矛盾及其性质。它的基本矛盾冲突之一,是《天上序幕》中天帝与魔鬼的第一场赌赛,这实际上是歌德所理解的至极对立。二者间的矛盾斗争是一切事物前进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另一个冲突和对立体现在浮士德和靡非斯特的关系中,一个要成,一个要毁。由于二者均是以具体的形象及其活动,特别是以在人世间的活动为特征,所以,这对矛盾可以看成是人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矛盾的艺术反映。作品中描写的另一个较有代表性的矛盾冲突是浮士德自身的矛盾。这是由人世间的矛盾转向对人自身矛盾的揭示。在歌德看来,在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有灵与肉的冲突:或追求灵的境界,向更高的目标飞升;或追求迷离的爱欲和短暂的欢乐。这种上升与沉沦、追求与停滞的矛盾,不仅在浮士德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就是在其他人物,如玛甘泪身上,体现得也是十分明显的。她渴求醉人的爱情,但又恐惧与浮士德的相爱。她与浮士德的不同,主要在于浮士德一生的活动是指向更高的肯定肯定,而她最终把这种爱情的追求指向了否定的方面而已。再如,“人造人”何蒙古鲁士的精神与实体之间的对立以及欧福良的狂热理想与行动局限的矛盾等等,都可以看做是人作为“小宇宙”内在矛盾的反映。由此,也可以看出,歌德在他的《浮士德》中,对不同质的事物间矛盾及其相互作用的把握也是极其深刻的。也可以说,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歌德对事物的同质矛盾构成也是极为看重的,认为这也是辩证法因素的重要内涵之所在。更重要的是,他还看到,同质间能够形成对立的关系,主要是由于同一性质的事物在程度、数量、形态乃至构造的对比差异中形成的。例如,他在《天上序幕》中就先以天帝的“至善”观念身份断言:“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之中不会迷失正途”。在悲剧正式开场后,则详细展示了浮士德的诸个阶段的追求探索历程,这就是善的差别。而魔鬼靡非斯特所代表的“至恶”观念的广泛性和在陪伴浮士德活动中所展示出的“恶”的具体性;以及浮士德本身的远大理想和对具体的“善”的事物的追求等等,都昭示着歌德的独特见解:在任何事物的矛盾构成中,不同质的对立面的某一方面本身,出现着差别,因此也就存在着矛盾。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差别的存在,使得其同质概念在更高一级上或符号的承载上,在不完整中体现着完整;同样也使得其在衍化为具体事件或事物时,能使矛盾的这一方面不断地互相补充。而这种不断补充的过程,也正是矛盾构成中对立双方自我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说,不同质对立的两方面的各自一方,通过其不断完善的演进,自我地推动着自己一方的发展。例如,天帝通过浮士德的活动将“至善”的内涵不断具体化;而代表具体的“善”的浮士德通过其具体活动一步一步地向至善靠拢和回归,就是这种完善过程和“善”的自身前进过程的具体体现。我认为,歌德的这种看法,构成了他全部《浮士德》描写辩证法的最基本要素之一。
在歌德看来,事物间的同质矛盾构成,也是一切事物得以构成的前提与条件。同时,这种构成也是事物本身发展演进最重要的动力形式之一。例如,虽然天帝与魔鬼在天庭上打睹,但倘若其赌赛的对象浮士德是一个“长足的阜螽”,一味“把鼻尖儿在粪坑里乱搞”的不求进取、自甘堕落者,那么,这“善”的一方就不能构成。天帝坚信人的向善性,而浮士德又坚信“泰初有为”,正因为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吸引,相互完善和补充,才使得浮士德处在不断的运动——向上的运动之中。换言之,同质事物间的相互吸引构成了其内在的演进运动力量。而靡非斯特作为“至恶”的观念与具体的“恶”的形态的相互补充,也才使得其本身符号指代内涵渐趋丰满和这一形象的不断完善。“恶”本身也具备着自身发展的内在自我的动力形式。这种事物同质间矛盾构成和动力形式的揭示,能够使我们避免把辩证法变为形而上学。
再次,在歌德看来,事物的发展仅有同质间的对立互补还是不够的。这种同质对立只有同矛盾的另一方面——异质方面——发生联系、相互作用,才能真正推动整个事物的发展和前进。这样,矛盾不同性质的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及其相互作用,就构成了他整个辩证法思想的核心。例如,天帝作为至善的化身,但在全剧中,他只能作为一个观念的存在。一般说来,这种单一的观念存在,是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的。天庭中出现的魔鬼也是如此。只有当二者之间相互作用,才引出浮士德的活动。而魔鬼靡非斯特与浮士德又构成一对异质对立统一的矛盾时,这种矛盾才推动着浮士德行动的不断展开。就浮士德自身的性格而言,他身上的“上升”与“沉沦”的矛盾愈加明显,冲突愈为厉害的时候,才有了他不断否定中的不断肯定。
歌德在《浮士德》中体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发展过程,实则就构成了同质间矛盾和异质间矛盾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过程。同质间的对立统一导致着异质矛盾中矛盾的各方面的自我强化,从而使异质间的矛盾冲突更为强烈和突出;而异质间矛盾的对立统一则使得同质间对立统一获得了真正的科学解释,使得事物真正进入了多种矛盾运动的层面。例如,当我们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再来把握作品中浮士德形象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自身所代表的善是不完整的,必经要将其内涵科学的把握。而浮士德与天帝所代表的完整的善的形态,又只有在进入了与恶的完整形态的对立的运动过程中,才显示出了其深邃的价值。
这样,在歌德的艺术视野中,辩证法的关系就是同质与异质(A与B),同质与同质(A与)以及同质系统和异质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之体现。
综上所述,这两个系统和三个层面实际上是一个关系问题,是辩证的新关系。在我看来,在歌德的视野中,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一切物质的、精神的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没有这种世界上万物间的矛盾的对立统一,就没有运动和发展。但歌德的伟大和思想的深邃就在于,他并没有把这种对立的统一规律仅仅形而上学的、机械化和片面化的理解为是不同质的概念、思想和事物(A与B)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他凭借其对各种事物现象的细致观察和对辩证法精髓的深刻把握,认识到了事物间矛盾的某一方面的同质构成(A与)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一点,他甚至比我们某些辩证法的研究专家也要敏锐得多,高明得多。这样,歌德的事物矛盾观或对立统一观,实际上是融合着两个系统、三个层面的辩证统一观。他的《浮士德》体现着更深刻、更广义的辩证法原则。
标签:浮士德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矛盾对立统一论文; 系统思维论文; 德国文学论文; 歌德论文; 国外文学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