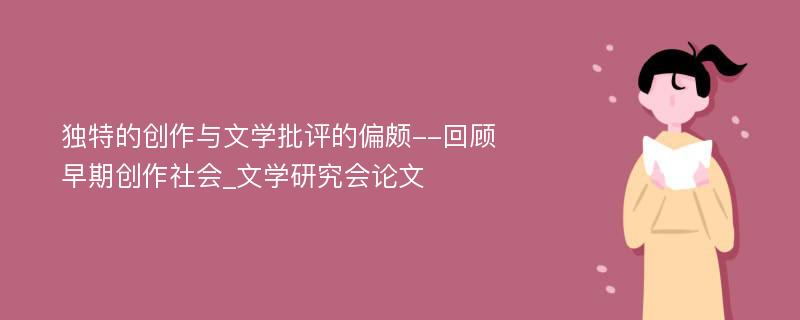
独具个性的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偏至——回望前期创造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创造社,是继同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之后文学界发生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倡导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和“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瞿秋白语)的创造社,双峰并峙,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初期耀眼的文学景观。
创作社成立的时候,虽然成员较少,势单力孤,如郭沫若所说,最初支撑创造社的,主要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三个人。但他们思想活跃,精力旺盛,创作准备充分,作品起点很高。《女神》的诞生,给新诗的创作带来了最大的冲击。早在1919年9月,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女神》部分诗作的时候,《学灯》的编辑宗白华1920年1月3日给郭沫若的信中就预言:“中国文化中有了真诗人了”;田汉1920年2月29日读了郭沫若的新诗后也说:“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先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我爱读这纯真的诗。”郁达夫更从文学史的视角,在《女神》出版一周年的时候,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判断:中国诗歌“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对于郭沫若来说,《女神》的飘然而至,更让他产生了“真是像火山一样爆发起来”的惊喜。1921年8月,《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短短的两年内,竟接连出了4版。同年8月,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作为创造社丛书第3种,也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女神》以高昂、激越、壮美的浪漫主义格调,让读者感受到了作家强烈的感性生命的骚动,倾听到一个民族的疼痛与愤怒;《沉沦》低诉感伤的浪漫主义内涵,又让读者获得了熟悉之外的陌生、焕然一新的发现,展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生机与活力。由此,创造社声威大震,卓然自立,确立了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沉沦》出版后的命运值得一提。一方面,它受到众多青年读者的欢迎;同时,也被人指责为“不道德的文学”。已经蜚声文坛厚道的文学研究会批评家周作人,立即站出来为《沉沦》辩护。周作人说:“《沉沦》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周作人郑重宣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我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
创造社的文学批评自有其个性。但与它的创作成就相比,却显得有些逊色。成立初期,创造社成员的精神,正处于自信而又压抑的状态里。自信,指的是他们多年的留学生活,对西方、日本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流行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含新浪漫主义思潮),有着一拍即合的认同。郭沫若《女神》创作的成功,郁达夫小说《沉沦》发表后引起的强烈反响,都使他们坚信自己的智力过人。由他们掀起一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正当其时。压抑,是对他们面临的现实境遇的忧虑。创造社成立初期,成员回国后,既无职业,又无资金支持,创办刊物,谈何容易?
天生的敏感气质,使他们对周围的世界保持着足够的警惕。1921年9月29日,在《创造》季刊出版前,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他们拟定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出版预告中,他们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公布“垄断”新文艺偶像者的名字,但戒心和敌意却显而易见。1922年5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期,郁达夫在《艺文私见》中,更是出言不逊,恶语相加,矛头直指文学研究会。郁达夫要“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都要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呢!”
在批评论文里,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诗歌创作,更采取了轻蔑、嘲笑的态度。成仿吾在《诗之防御战》中,说康白情的《草儿》是把演说分行“便算作诗”;俞平伯的《冬夜》中的《山居杂诗》“这真未免过于匆匆了,然则——不成其为诗罢”;批评周作人(《雪朝》第二辑)中的《所见》“这不说是诗,只能说是所见”;说徐玉诺的诗作《将来之花园》,“这样的文字在小说里面都要说是拙劣极了。”创造社成员对“五四”时的白话文运动,也持一种否定的态度。郭沫若在《创造周报》第3号发表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就说:“四五年前的白话文革命,在破了的絮袄上虽然打下了几个补绽,在污了的粉壁上虽然涂上了一层白垩,但是里面的内容依然还是败棉,依然还是尘土。Bourgeois的根性,在那些提倡者与附和者之中是植根太深了,我们要把那根性和盘推翻,要把那败棉烧成灰烬,把那粪土消灭于无形。……光明之前有浑沌,创造之前有破坏。”显然,“创造之前有破坏”应是他们当时开展文学批判运动的核心理念。对于创造社的进攻姿态,文学研究会成员当然不会沉默。郁达夫的《艺文私见》发表几天之后,损(茅盾)就写了《〈创造〉给我印象》进行反批评。
茅盾当时虽然也还年轻,但他经营文字的时间相对长一些。茅盾反驳郁达夫的文字中,自有一种从容豁达的老辣之气。在引出了郁达夫那段不讲道理的骂人话后,针对创造社创作的近况,茅盾表现上不动声色,实则语气讥讽,直刺创造社的痛处:“真如郁君达夫所说,大家说‘介绍’说‘创造’,本也有两三年了,成绩却很少,大概是人手缺少的缘故。治文艺的尤其少,更是实情。人手少而事情不能少,自然难免有粗制之嫌。……创造社诸君的著作恐怕也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罢。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而想当然的猜想别人是‘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更可不必。真的艺术家的心胸,无有不广大的呀。我极表同情于‘创造社’诸君,所以更望他们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出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笔战仍在继续进行着。创造社批评文学研究会,多在文学研究会的人善于变幻笔名,翻译著作中出现了笔误等具体问题上。双方在学理上并没有再进行认真的争论。后来,成仿吾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中声明:“文学研究会的那一部分人,若出来多言,纵有千万个‘损’先生来辱骂,我昌只以免战牌对付的。”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也有过休战的表态。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争论有时虽然激烈,但双方都还保持着应有的节制。1922年8月,当创造社举行《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包括茅盾、郑振铎在内的文学研究会作家,都应邀出席了招待会。1923年12月胡适日记记载,在文学研究会重要成员郑振铎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的时候,“到郑振铎家中吃饭,同席的有梦旦、志摩、沫若等。”胡适断言,“这大概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埋斧’的筵席了。”
创造社与胡适、徐志摩的争论,同样始于成仿吾对胡适《尝试集》的贬抑。在《诗之防御战》中,成仿吾对胡适的《尝试集》,几乎是作了不屑一顾的否定。成仿吾认为,诗集中的《他》,“这简直是文字的游戏。好像三家村里唱的猜谜歌,这也可以说是诗么?”成仿吾说,“《尝试集》里本来没有一首是诗,这种恶作剧正自举不胜举。”成仿吾还极力贬低胡适的《人力车夫》和《儿子》。他说:“《人力车夫》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自古说:秀才人情是半张纸。这样浅薄的人道主义,更是不值半张纸了”,《我的儿子》“还不能说浅薄,只能说是无聊”。成仿吾在文章结束时,用“哈哈,好了!不再抄胡适之的名句了”。毋庸讳言,《尝试集》的确有着初期白话诗的幼稚,但作为新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新诗集,自有其特定的文学史价值。对《尝试集》存在的不足之处,当然可以实事求是地作出具体分析。而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武断地把作品全盘否定,则是极不郑重的。
成仿吾的这篇文章,立刻就迎来了徐志摩的反击。徐志摩把矛头没有直接指向成仿吾,却指向了创造社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徐志摩在《努力周报》51期发表《杂记(二)坏诗,假诗,形似诗》的评论文章中,对郭沫若题为《泪浪》的诗里使用“泪浪滔滔”四个字进行了非学术性的挖苦讽刺:“固然作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并不曾经过重大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看到徐志摩的文章后,成仿吾于1923年6月3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4号,发表了致徐志摩信,双方的论战开始激化。成仿吾信中说:
你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射冷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以至于此!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的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我想你要攻击他人,你要拿十分的证据,你不是凭自己的浅见说他人的诗是假诗,更不得以一句诗来说人是假人。而且你把诗的内容都记得那么清楚(比我还清楚),偏把作者的姓名故意不写出,你自己才是假人。而且你既攻击我们是假人,却还能称赞我们到那般田地,你才配当‘假人’的称号。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人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
成仿吾的文章发表后,徐志摩1923年6月10日在《晨报副刊》又发表了《天下本无事》。文中说他的《杂记(二)坏诗,假诗,形似诗》惹了祸,“一面仿吾他们必说,声势汹汹的预备和我整个儿翻脸,振铎他们不消说也在那里乌烟瘴气的愤恨,为的是我同声嘲笑‘雅典主义’以‘取媚创造社’,这双方并进的攻击,来势凶猛,结果我也只得写了一封长信,一则答复成仿吾君,乘便我也发表联带想起的意见,请大家来研究研究,仇隙是否宜解不宜结……”但长信里,徐志摩仍立足于自我辩解,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不忘记对对方的嘲弄:
“至于我很不幸的引用那‘泪浪滔滔’……固然因为作文时偶然记到——我并不曾翻按原作——其次也许不自觉的有意难为沫若那一段诗,隐示就是在新诗人里我看来最有成绩的尚且不免有笔懈的时候,留下不当颂扬的标样,此外更是可想而知了。”
还说:
“最大的亦最可笑的悲剧,就是自信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人,永远不会走错路,永远不会说错话。是人总是不完全的。最大的诗人可以写出极浅极陋的诗。能够承认自己的缺陷与短处,即使不是人格伟大的标记,至少也证明他内心的生活,决不限于狃狃地悻悻地保障他可怜怜稀小畏葸的自我。”
徐志摩盛气凌人的态度,连持客观立场的梁实秋也看不过去。梁实秋致信成仿吾说:
“徐志摩的‘泪浪滔滔’的一段批评,在诗的原理上完全是讲不通的……,诗而可以这样的呆评,则古往今来的诗可存的恐怕没有多少了。我不是说沫若的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句句都是没有些微疵谬,我是说‘泪浪滔滔’这四个字是无论如何在不可议之列。”
成仿吾与徐志摩你来我往的争论,让胡适预感到,争论的背后,既凸显了双方文学观念的分歧,也夹杂着年青人争强好胜的习气。胡适首先站出来灭火了。胡适日记记录了化解分歧的具体过程,胡适1923年5月25日日记:“出门,访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结束了一场小小的笔墨官司。”胡适5月27日日记:“下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来。”来访谈话的内容,日记没有记录。但这应是创造社成员一次礼节性的回访。歧见化解并非一两次互访可以完成的。同年10月11日,胡适日记记载:“饭后与志摩,经农到我旅馆中小谈。又同去民厚里访郭沫若。沫若的生活似甚苦。”对于这次出访,徐志摩当天日记的记载更为详细,日记中说:他们步行去民厚里121号访问郭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郭沫若家里当时还有客人,“田汉、成仿吾在座。”日记显示,客主之间的关系较冷淡。徐志摩日记称:田汉“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仿吾亦下楼,殊不谈话”,造成了“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使胡适“甚讶此会之窘”。对于胡适的“窘”,郭沫若当然有所觉察。第二天,郭沫若就领着大儿子回访胡适、徐志摩。徐志摩日记用“今天谈得自然的多了”来记述会面时的气氛。紧接着,郭沫若等又宴请徐志摩、胡适。徐志摩10月15日日记:“前日(指10月13日)沫若请在美丽川,楼石庵适自南京来,胡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遽抱而吻之——卒飞拳投詈而散——骂美丽川也。”这则日记中的“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遽抱而吻之”一句,还见于胡适日记。胡适日记记载:“沫若来谈。前夜我做的诗,有两句,我觉得做的不好,志摩也觉得做得不好,今天沫若也觉得不好。此可见我们三个人对于诗的主张虽不同,然自有同处。”当晚郭沫若又宴请胡适、徐志摩。胡适日记记载:“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这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渴(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在郭沫若、胡适之间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之后,10月15日,徐志摩与胡适又回请郭沫若。胡适日记说:“与志摩同请沫若、仿吾等吃夜饭。田寿昌和他的夫人易漱瑜女士同来。”他们交谈融洽,大谈神话。
这几则日记,展现的是作家之间修复关系的自然形态,可以让读者从感性上认识“五四”后作家之间的微妙关系。把这一时期作家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描写为誓不两立的对立关系,看不到双方由论争到化解分歧的具体过程,文学历史的叙述就会显得简单、贫乏。
创造社当时对《礼拜六》等刊物也开展过批判。成仿吾在《歧路》一文判定《礼拜六》为“卑鄙的文妖所出的恶劣的杂志”,还把读这些杂志的读者,骂成是“助恶的行为”,是“蠢东西们”。其实,《歧路》也正是批评者的“歧路”。
前期创造社以及当时同他们开展论争的各个文学流派,他们在文学批评、文学论争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及出现的失误,都是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遗产。那时,社会学知识理论尚未转化为权力话语,尚未与权力,结构对接,争论各方的言说,都是具有主体性的自我选择行为。他们不愿意承认和接纳与自己不同的想法与存在,因而在争论中他们七嘴八舌,甚至言词苛刻,骂人,有一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傲慢。但也正是这样,才给我们留下了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文学传承记忆。史实是历史的灵魂。史料的客观性、正义性、先锋性不容置疑。在梳理创造社与各文学流派论争的原始史料里,我们感受到,“五四”文学经验,不仅仅是单一的某一流派的历史经验,这有助于我们在书写文学史时眼光的拓展,获得足够的启迪。
文学社团流派研究,是作家的精神史研究。在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中,优化思维模式,开掘新的文学资源,让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文学碎片(如日记等),化为有生命力的文学信息,是十分必要的。还应该加强对回忆录的解读与辨析。《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中所说:“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及《艺文私见》中所批评的垄断文坛的人,究竟指谁?目前出版的回忆录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经过》中说:“达夫的‘垄断文坛’那句话也被好多多心的人认为是在讥讽学研究会,其实是另外一回事……不幸达夫是初回国,对于国内的情形不明,一句无存心的话便结下了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不解的仇恨。”而郑伯奇在所撰《忆创造社》中却明确地说:“所谓‘垄断文坛’,当然指的是文学研究会。”按研究者通常的理解,郑伯奇的回忆是接近事实的,但事实真相究竟怎样,也许仍应该留给历史。
再如,谈到创造社和胡适、徐志摩的争论时,郑伯奇的一篇回忆录作了这样的描述:“创造社的刊物一出世马上招来了胡适一派的进攻,也可以说是并非偶然。创造社作家的那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和胡适一派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是格格不入的。胡适对于达夫指摘误译的短文章,不惜亲自出马挑战,给创造社这个不顺眼的初生婴儿来一个致命的打击”,“创造社胜利地回击了胡适一派的猖狂进攻”。作者还特意指出,这场斗争“属于敌我斗争的范围”。回忆录对创造社与胡适、徐志摩新文学阵营内部笔战的概括,显然不符合事实。在“五四”社团流派研究中,人们只有从惯常的你死我活,营垒分明的研究模式中走出,才有可能看到各个社团流派之间既有冲突对抗,又有分化融合的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状貌,从而使研究出现某种带有颠覆性的成果,较好地逼近文学生存的历史真相。
前期创造社的生命是短暂的。1926年5月,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的《革命与文学》中宣布:“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只有“在精神上是彻底表同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才是“最进步的革命文学”。至此,创造社的发展开始进入后期。
标签:文学研究会论文; 徐志摩论文; 郭沫若论文; 成仿吾论文; 郁达夫论文; 文学论文; 创造社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胡适论文; 尝试集论文; 女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