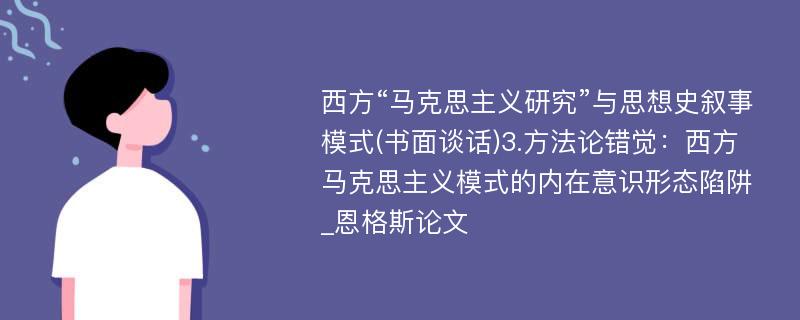
西方“马克思学”与思想史叙事的模式(笔谈)——3.方法论幻象:西方“马克思学”模式的内在意识形态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方法论论文,模式论文,笔谈论文,幻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毋庸置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苏联学者的研究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学”(以下简称“马克思学”)、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亦提出了不同理解,但并未对苏联马克思哲学解释的统治性地位形成实质的挑战。直到70年代,“马克思学”陆续提出了两个马克思和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得出了诸如恩格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等结论,这些结论直指苏联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理论禁区,犹如重磅炸弹,使得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为之一震。在其他流派、思潮还在观望的时候,苏联学界便齐集一切“兵力”谴责和打击前者的“反马倾向”;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本能反应”的后果,在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苏联马克思哲学研究出于坚守阵地的需要却同时或多或少强化了教条主义思路,未能根本变革其僵化的哲学体系。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一度激烈的争论悄然消退,然而昔日的荣辱则似乎在今天颠倒了。这段历史对今人来说,具有何种启示?我们认为,理论的探究不是“朝三暮四”式的算术,而永远是向历史深处的挖掘,简单地易弦更帜不是成熟的做法。因此,在今天讨论“马克思学”时,只有结合苏联的传统理论进行一些比较性研究,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作为一种模式的“马克思学”提出问题的逻辑前提和方法论构架,并发现其问题的实质所在,为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之处。
在对苏联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批判中,“马克思学”颇为引人瞩目之处有二:一、直接抓住马克思文本的异质性问题,攻击前者的目的论预设;二、采用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宣扬价值中立,打击前者的政治立场。具体说来,通过精细的文本解读,“马克思学”学者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苏联理解的世俗化的马克思形象。它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历史性地颠覆了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形象以及作为马克思代言人的恩格斯形象,试图通过对文本的精细化重读还原马克思恩想“原貌”,并在马克思身上涂上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所谓的差异分析方法和价值中立立场在理论上非常容易博得某种同情,甚至在反对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目的论预设、连续性解读等意义上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然而在“马克思学”那里,这一方法并未走入正果:理应产生更为合理成果的方法论仍旧没有摆脱无意识的束缚,甚至被贬低为建构新的同质性的工具,服从于一种新的道德上的唯意志论。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学”与苏联马克思哲学研究陷入了相似的泥淖。
首先,“马克思学”标榜自己的理论初衷是系统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主张以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来重读马克思文本,探求本真的马克思思想,而坚决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体系化理解。然而事实证明,这只能是它的一厢情愿。表面上看,“马克思学”的学院化研究作风,较之为革命服务的苏联研究以及仍旧保留“改造世界”冲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似乎更“严谨”一些。但是,这种“严谨性”始终被两个不易察觉的隐含假设所干扰:其一,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一种既成的事实与马克思主义无关;其二,马克思或恩格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具有思想上的同质性,同时他们两个人是异质的。虽然这两个假设指认了教条主义从领袖语录来构建体系的先天缺陷,但显然也违背了基本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长期致力于推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将其视为自身理论的使命,并在这一过程中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有一个思想上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他们采取了分工合作方式,但基本观点同出一辙,由两人共同创立和发展。如果不尊重这些事实,中立方法便会产生更大的扭曲后果,这非常类似于那种关于形式公平的悖论——“马太效应”,即起点上的不公平在平等的形式中,恰恰会产生更大的不公平。无论是两个马克思问题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问题,“马克思学”的提问方式本身注定了它无法摆脱教条主义的窠臼:通过对文本间差异的精细分析,“马克思学”学者在文本的变化之中确证了一个不变的马克思本真形象,但这个马克思却是离我们远去的、作为19世纪的道德学者的马克思;因而马克思为我们留下的最鲜活的内容——对社会历史的科学批判——也就随之被彻底取消了。
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学”模式与其理论竞争对手苏联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可以说殊途同归。后者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时也一直贯彻着一个理论目标即成熟的马克思及其思想,并搭建了一个绝对学科化的体系牢笼。它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马克思文本中的异质性问题,尤其是放弃了马克思不成熟的早期文本,将马克思看作一个在思想发展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斗争的天才,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要素就是他在头脑中逐渐累积而成。①对比两种模式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马克思学”模式和苏联模式都将现实的历史排除在自身的理论逻辑之外,总是幻想着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个固有的形象并以之灌注马克思所有的文本,因而都陷入一种单向度连续性的解读模式。二者虽然处在不同的层面并展现出不同的理论旨趣,但是其逻辑结构却是内在一致的。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学”模式试图通过纯化文本的方式来批判苏联模式中的政治滥用,虽然在显性层面上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在批判过程中它本身却也无法避免意识形态的控制。
其次,“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马克思学”和苏联马克思哲学研究两种模式之间互相攻歼的重要武器。前者对后者的批评无疑更加容易令人接受,因为后者的一条显性原则就是哲学党性原则,即哲学为政治服务。从第二国际和列宁哲学思想的传统来看,哲学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并附属于它是很容易理解的——政治上的领导权必须有理论上的解释权来支撑,“从理论上肃清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打着哲学旗号出现的宗派集团的政治流毒”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政治使命。列宁逝世之后,面对来自国际和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的挑战,以及党内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为了完成对“列宁主义”的论证,这一原则得到了片面的发挥,特别是“片面突出理论对实践的依从关系,弱化、甚至排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从而在根本上取消了理论的独立性,使理论成为政治的附庸”。②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由于历史事件以及各种修正主义和包括“马克思学”在内的西学话语的屡屡打击,苏联马克思主义原本坚实的正统性地位被严重动摇了。为了维护苏联哲学界的理论权威,今天国内广泛讨论的传统马克思哲学模式得以形成。在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建构成一种原理化了的绝对科学,重复着哲学为政治救亡的老路。尽管苏联后来出版的一些新著作中所带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已经开始弱化,但是由于之前受到长期的思想灌输,他们的理论无意识中依然留下了斯大林主义的印记。
“马克思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身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段历史在西方社会中的理论回应,它处处以价值中立的姿态自居,宣称自己是本着客观原则对马克思作品进行解读的。它认为,马克思的早期和未完成文本“隐藏着一个‘未知的马克思’,即苏联教条主义之外的马克思”,由此,“可以顺理成章地以纯化文本的方式来批判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政治滥用”。③但是已达成共识的是任何的人文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色彩,“马克思学”也不例外。仔细考察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其所谓的“客观”原则只是局限在表面上的,它对马克思话语的分析潜在地渗透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由于“马克思学”学者没有直接遭遇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问题,他们无法理解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因而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注定会忽视其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以致无法理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什么不可能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必须带有特殊的政治使命。另一方面,“马克思学”过分地崇拜排除了恩格斯的马克思文本(尤其是未完成的作品),特别偏爱其中体现了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段落;同时其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区分表明它试图将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中剥离出来,单方面强调马克思思想的伦理意义,这些可以说都是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的不经意流露。结合这一点,我们也更能理解“马克思学”为什么会先在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合法性。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学”学者尽管一再伸张自己的中立立场,然而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学”在根本上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力欲将其打扮成一种关于伦理道德的学说体系。
从上述两点看,作为一种理论模式的形成,除了“总问题”的确立之外,更为根本的是其所立足的社会历史经验。因此,无论是“马克思学”模式还是苏联模式,回到其现实的社会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它们的理解,也有助于进一步解释它们何以面对同一对象却产生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在总体上,苏联研究强烈地服从于外在意识形态需要,而“马克思学”则从对苏联的批评出发站到了中立立场,以中立的方式把自身的意识形态内化到理论方法之中。但是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意识形态终究作为一种无意识纠缠着自以为已经站到了真理之巅的那些幻象。也正是这一原因,我们说,“马克思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幻象。
可以说,无论苏联模式和“马克思学”模式在理论的外表上打扮得多么漂亮,它们都只能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下产生学术和政治效应,而不能长期占据真正的思想史舞台,更不要说推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今天,我们研究二者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批判它们,更重要的在于探索如何穿越它们的神话,确立真正科学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方法。苏联模式和“马克思学”模式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以政治结论代替学术研究,也不能奢望完全脱离政治立场的理论逻辑;同时较之于那种追寻所谓本真马克思的幻想,挖掘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也显得意义更加重大。因此,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从立场走向模式、从文本走向当代就成为当下研究的重中之重。
注释:
①参见张一兵:《何以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史》,《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
②张亮,《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历史形成:一种知识社会学审理》,《学术月刊》2005年第12期。
③胡大平:《穿越西方“马克思学”神话,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福建论坛》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