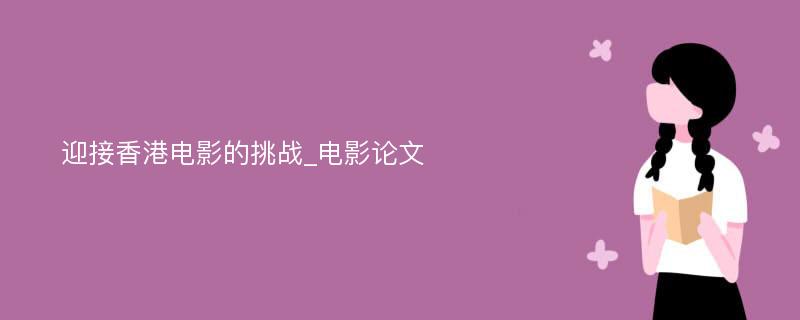
迎接港片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港片,香港电影之谓也,一个并不陌生的概念。然而,它在辽阔、深邃的大陆影坛上引起的震颤和反响是截然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可以说港片导致了两种效应。
一种是观众对港片兴趣盎然、热情不衰。想当年,热爱港片的影迷们,往往要被丑化为“闻香必至”,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那个时代港片的诱人程度。今天,港片变本加厉,依然是影迷们追风逐电的“基本点”。据《半月谈》九四年第十七期报道:“一些观众对合拍片抱着迷信心理甚至到了以产地和演员决定看与不看的地步”。这里合拍片可以说是特指香港片。93年全年生产的154部故事片中合拍片占到43部,其中相当数量是港台动作片,而位居上座率前矛的绝大部分影片都是这些港台片,它们为93年的票房作出巨大贡献,难怪电影放映公司对它们要情有独钟。
另一种是中国影人对港片的不屑一顾、冷嘲热讽。主流评论家谈到港片,立即步调一致,思想统一,异口同声地为港片贴上“媚俗、无聊和浅薄”的标签。
这两种效应对应地作用到中国影业上后,便形成了两种趋向:一方面是港片不事声张,忍辱负重,以获观众青睐为能事,在实践操作中所向无敌;另一方面是影人在斥责港片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快感以及胜利,并结成批评港片的“神圣”联盟。
然而,在这一切背后,却说明着我们影人的心理是自卑的,他们最为孱弱的补救措施就是用痛骂来维持自尊了。据介绍,《新白娘子传奇》剧组到大陆拍片就带有一种明显的优越感,中方协拍人员用以抗衡的只不过是搬出了政治口号“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拿不出艺术上的诱人之作,最终还是眼看《新白娘子传奇》在中国荧屏上长驱直入,过五关斩六将,掳去无数观众的关心和热心。
因此,我们不应对港片(包括台片,因不在本文叙述,故简略)犹抱琵琶半遮面作羞涩状,或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作鸵鸟状。我们应该跳出祖传的精神胜利法的无意识影响,正视港片的成功经验,宰割掉中国影视中的赘疣部分,轻装上阵,迎接港片的挑战。
前辈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不妨来看看围绕港片究竟旋转着什么样的尘埃和云雾。
中国影人轻蔑港片的心理基础
港片胁迫我们可谓历史已久,说来话长。五十年代,上影拍过巴金《激流》三部曲之一《家》。而国内上映的另外两部《春》、《秋》则是从香港引进的。看过《家》,再去看香港片《春》、《秋》的中国观众,真是身体力行地感知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的深刻内涵。原来港片能把故事叙述得如此活灵活现,连巴金先生也深表赞扬。这两部港片还在国内被评为全国优秀影片,男主角觉新的扮演者吴楚帆获选为全国最受欢迎的五位演员之一,而大陆版《家》中觉新出演孙道临却未闻有些殊荣。这当然不是孙的演技欠佳,实在是导演手法上不如人家。中国《家》一直未被影界认为是十分成功之作,前几年不是有人在报上呼吁把《家》列入优秀电影中去吗?这反证出《家》过去的评价并不是很高。
至于文革后港片更是浪涛滚滚激荡而来。《屈原》、《画皮》、《三笑》……往往给我们以重量级的震撼,这些影片在大陆影界所激起的批评声浪,反而化石般向今天保留着他们当初的轰动气派。而自《少林寺》之后,直到今天的《新龙门客栈》等新武侠片,它们创下的惊人的战绩,则无须我复述了。
但中国影人对港片向来很苛刻。当年《霍元甲》在大陆放映时,有人在《文艺报》慷慨陈辞,严加贬斥,称之为“用爱国主义的招牌,宣扬暴力和鼓吹盲目排外”;对《少林寺》,今天我们仍听到影人们要批评它内容粗糙。
中国影人为什么会形成对港片挞伐的共识?思来想去,我不敢贸然定论,但我总恍惚感到一点,就是中国影人似乎存在着一种高人一等的心理。对香港经济我们是俯伏看的,但在文化上我们则嘹亮地称之为“沙漠”,似乎自己顿时步入“雅士”之列。这种高等感,我们在85年5.19倾斜的足球场中也似曾触摸到。泱泱大国的足球队,岂可失手于弹丸之地的小兄弟?遂引发暴力。由此推而广之到影坛,既然是文化沙漠,怎能长出电影艺术的蓓蕾?似乎那儿只能丛生着平庸、无聊和低级趣味的野草。
但是,我们也看到香港的另一面。希望工程捐资、水灾捐献等等,使我们感动在港人“我的中国心”的真心实意面前。而香港艺术家,我们也常听到他们“为国争光”的理想。据94年第1期《大众电影》报道,第一位打入好莱坞主流电影体系的香港著名导演吴宇森称他“毕生的最大心愿”是为中国人拍一部史诗式的电影《战国时代》,其强烈的民族观溢于言表;香港怪才导演徐克也多次要使中国影片打向世界,为国人争光云云。在一味斥责人家趣味不高的同时,我们是否感受到他们对电影艺术的追寻和努力,以及在行动上日渐引起国际影坛所注目的事实。
也许我们应该看到港片导演的深刻和成功之处,而不是以轻蔑来漠视人家的存在和成绩。
从批评港片“俗”到悄然模仿
批评港片“俗”是大陆影人最常见的批评词汇。但俗和雅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往往是旁观者“糊涂”。仿佛有一个规律,一个新潮的被民众哄抬的事物往往是俗的,而一旦时髦过头,似有被抛弃之迹象时,便顿时摇身一变,刹时雅气弥漫了,专家们也便一改初衷,来了大转折,从反对到抢救,奋起绵力,挽救呈颓势的由俗转雅的“文化”了,当年牛仔裤何等之俗,今天雅人们完全视作雅的商标了;京剧进京时,是俗的,现在雅到急救的地步了,《三笑》当年公映时斥之为庸俗,而当更离谱的《唐伯虎点秋香》闯进来时,当年的《三笑》立刻香气袭人,高贵的了不得,最为典型、也最令人可乐的是金庸命运的巨大转折了,当年看金庸的人可谓是“地下阅读工作者”,报上声讨武侠小说之辞不绝如缕,然而今天风向突转,一向高贵逼人的三联书店也下嫁面子,一点不怕“俗气”地出版金庸全集了,成为大陆第二家经作者授权的正规出版社。而4卷本250万字《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更是一鸣惊人,把金庸排名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居四,有限的名额使茅盾公反而成了卢俊义了。金庸的变迁不是很耐人寻味吗?或许将来要在金学之外再设立一个“金学变迁学”呢。
这种俗、雅转换的规律同样适用于港片。尽管港片在正统者的心目中声誉不高,但是大陆电影却在不妥协的层面下悄然模仿了。
黄蜀芹是大家熟知的导演。她导演的《青春万岁》、《围城》、《画魂》皆影响颇大。这位女导演凭着职业的敏感,率先感受到港片的长处。当年《上海滩》在国内播放时,黄导演。对此片进行专门研究,反复观看,学习港片的镜头变换技巧。这种学习未尝不对她后来执导《围城》起到指导作用。
北影厂的女导演刘国权近年来拍摄的《虎兄豹弟》、《血祭黄沙镇》据说在不景气的国产片中一枝独秀。这位导演对港片学习的精神十分感人,据《大众电影》94年第3期介绍,“刘导演有感于大陆武打片拍得过拙,对香港武打片虚心学习。参照它大中小打的时间间隔掌握自己影片的张弛节奏。通过拉画格来研究人家对一个动作的拍摄、剪辑、特技”。近日她又拍成《梁山伯祝英台新传》,这可以说是对《新白娘子传奇》、《唐伯虎点秋香》类的港台片的跟风模仿,虽然评论界对那类嬉闹式港片感觉很不好,动不动就要发生金陵影评人士把《唐伯虎点秋香》送上最差电影席位那样的行为,但毕竟那些港片的成功诱惑太大,最终还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反而把更多的大陆影人拉下水。 港片的“威力”值得研究探讨
港片究竟为何有冲击力,那是学者教授们的论文题目。我们这里只不过是凭直感随便聊聊港片的一些长处而已。
港片观念更新快。港片有跟风起哄的习惯,这不是一个什么好毛病,但这也说明了港片接受新事物快,能及时感知世界电影的新技术、新潮流。《少林寺》放映时,带出一长串“光头”类型片,后来逐渐式微,枪战片又兴时一阵,徐克等人重新耍弄起武侠片,不过不是《少林寺》般的如实展示武功,而是竭力表现武功的神异性。这类影片在节奏上更快,造型上更怪,充分发挥了电影艺术的潜能,使观众赏心悦目。而我们大陆电影,风格几十年如一日,大部分电影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更久的影片看不出有什么技术上的创新、艺术上的进步,依旧散散漫漫、慢慢吞吞,深怕观众看不明白似的。这种陈旧的电影理论是过去时代的产物,随着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你仍是那么一副拖沓的模样,自然要使观众兴味索然了。
港片注重视觉效果。港片节省下冗长的介绍对话,而以激烈的影象组接在一起。近日新武侠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采用仰拍镜头,突出人物,虚化背景,其目的就是力图抛弃过去一场戏娓娓而谈的处理方法,力求打破戏剧性的框架结构,而是用不断变换的影象叙述内容。所以这类影片我们往往看不清周围环境和人物,只有主体人物的矛盾和交锋,而我们的影片,尽管在竭力效法港台片的打斗,但一旦进入到人物对话时,立刻节奏放松,缺少动作感。如刘国权拍摄的《血祭黄沙镇》中也有《新龙门客栈》中那种飞来飞去的打斗,但在室内戏的拍摄中镜头呆板,人物对话不紧不慢,一坐下来谈个没完,与全片的打斗风格极不协调。这说明动作片不仅要有快速的动作打斗,而且在文戏的处理上也要具有动作性,这才能连贯成整体的打斗风格。
港片富于创意精神。《新龙门客栈》、《新碧血剑》、《狮王争霸》等片的精彩打斗令我们感到港片十分富有想象力。港片很善于发挥道具的作用,用足用活一场戏提供的外界环境。《新碧血剑》尾声部分围绕风车展开惊心动魂的大战,展示了精彩的影象和丰富的想象力。《谁与争锋》中,描写方世玉踢凳救母一场戏,充分利用板凳这个道具,营造出一种不容喘息的惊险奇观。相比之下,我们的武打片打斗十分粗糙,毫无新意,无非是飞檐走壁,或是砸坏坛子,踢翻椅子,却没有利用一场设置的道具,来构置精巧的打斗。
港片镜头变换迅速。港片从不象我们大陆片那样酸文,它表现谁镜头就跟到谁,使观众不停地从画面上观看到所想知的内容,形成了目不暇接的效果。在武打动作中,镜头更加细腻、繁密,酣畅的镜头组接产生出神奇的蒙太奇效果。而我们大陆片,镜头仿佛总不能跟到位,前面似乎有一个戏剧舞台,制约着摄影机的切入。如电影《末代皇后》中,有一场表现婉容上台阶的戏,只用一个镜头表现主人公讲话,使对方是谁难以看清楚。这种毛病可以说在中国电影中俯拾即是。大陆电影的摄影机总象很懒,坐下来就怕动。实际上,比较一下港片和大陆片的镜头数,我们就知道两者的差异。
港片人物对话快捷。港片人物说话铿锵有力,朗朗上口,从不停地闪过的字幕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而我们大陆片人物对话口语不象口语,书面语不象书面语,而且台词带有很大的程式化,除了擅长发一通雷同的哲学感想外,很难有什么精彩的令人回味的对话。象大陆片《青春冲动》,人物谈话不是含蓄的,而是概念化的,表现女主角纯情就是让她故作小女孩腔,当她与男主人公吵架时,真是让人浑身难受,“对来对去”的都是恶声恶语的谩骂语气,这种吵架腔口,结合《京都纪事》等影视片,可以说是大陆片的流行语病。
港片充溢幽默和趣味。如果说烦恼就是智慧(张贤亮语)带有一种牵强附会的霸气的话,那么幽默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智慧。港片通过对话和影象的设计,制造出令人发噱的效果。《唐伯虎点秋香》尽管评价不高,但管保今日的痛陈批判者当时也忍俊不禁。王晶导演、李连杰主演的《新少林五祖》把庄重与诙谐交融于一点,使人在豪壮的背景下乐不可支。另外,港片在一段戏的结尾总要炮制一个笑料式的惊奇,不停地甩下包袱,使影片可视性很高。而我们大陆电影则死气沉沉,尤其是写到古装戏,更是一点趣味没有,满嘴之乎者也。大陆编导们塑造的古代人就是真实的吗?既然艺术不等于历史,我们倒不如到港产古装片中,获得一点现代味十足的乐趣。象新武侠片中的现代语汇的运用,很使一部分人反感,其实中国传统喜剧中就有这种即兴表演,行话叫做“抓哏”,比如有些丑角表演,插科打诨,时不时加上几句现实中的新名词,观众听了,不但不以为怪,反而十分快乐。这样说来,港片还是继承了中国戏剧的传统呢!
当然,大陆片也有幽默。最近流行的是王朔式调侃的幽默。港片是从生活中发现幽默,而大陆片则是歪用政治语汇,达到一种恶趣式的幽默。香港幽默因为从日常人生活发掘、设计而来,给人一种痛快淋漓的舒心之感,而大陆片调侃式的幽默则是胆大包天的正词歪用,往往令我们哭笑不得。
我们再次重申一句,我们的分析显然是一种印象式的,远不能代表港片的全部。当前合拍片方兴未艾,在电影院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冠以国内电影厂片头,内容却是全部港味风格的影片。我们大陆影人的对手正是这些港片们。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改革自身,迎接挑战,在技术上、艺术上加速与国际电影的接轨,努力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拍出无愧于中国出品,也无愧于翘首企盼的中国观众的影片。
标签:电影论文; 港片论文; 新白娘子传奇论文; 唐伯虎点秋香论文; 新龙门客栈论文; 少林寺论文; 影视论文; 香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