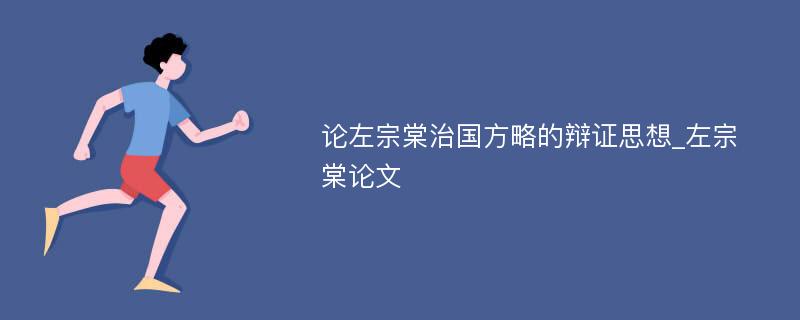
论左宗棠治国用兵的辩证法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左宗棠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左宗棠的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他能够运用普遍联系与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提出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综合治国论;“通筹”与“扼要”相结合的全局重点论;在用兵西北时所高度灵活运用的“层递灌运”与“缓进急战”相结合的军事运筹学;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所深刻看到的强弱、胜败、利弊、损益、治乱、盛衰等矛盾对立双方的互相转化,充分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这些辩证法思想因素,是左宗棠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关键词 综合治国论 全局重点论 军事运筹学 矛盾转化观
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清朝后期的所谓“中兴名臣”,也是所谓“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但是,纵观他一生的是非功过,称他为继林则徐之后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他在收复新疆,索还伊犁,以及在中法战争中积极主战,支援镇南关大捷,派兵援救台湾的反侵略斗争中,都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为备受屈辱、充满血泪的中国近代史写下了大振国威的光辉一页。左宗棠能立下这样伟大的历史功勋既不是侥幸的,也不是偶然的。这不仅与他强烈的求强御侮的爱国主义思想有关,也与他一整套军政方略中的辩证法思想方法有关。本文试图从中华民族哲理思维的角度,剖析左宗棠战略思想中的辩证法要素。
一 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综合治国论
左宗棠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贯穿着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这主要表现在他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外交、科技等,看作一个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环环相扣的统一整体。作为封疆大吏,左宗棠先后担任过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作为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他参加过满清中央政府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决策。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军旅生涯中渡过的,但他并不认为军事是治国平天下的唯一手段。他深刻地认识到,治国“不独在猛战,而在方略处置为远大之谋。”①即必须把政治、军事、教育、外交、经济等各种措施,互相配合,同时进行或交替使用,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我们对左宗棠总的政治思想不宜评价过高,但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1.深刻看到经济的决定作用
左宗棠一反宋明理学不言功利,空谈“理义性命”,“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观,绝无人色”②的遗风,始终对经济问题予以高度的注意。他从自己的军政实践中充分看到经济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惟粮食、盐菜、衣袴、巾履、医药,则生人日用所需,决难断缺。非时其缓急,源源支给,慈父且不能保其子,将帅安能蓄其士卒哉!”③“虽有良将,不能点铁而成金;虽有神兵,不能煮沙以当粥。”④所以,他每当在军事上收复一地,都注意及时招抚难民,安置战俘,借与种籽、耕牛,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因地制宜,开源节流,尽量减少国家财政支出。特别是在用兵西北时,他继承和发展了西汉赵充国“屯田实边”的思想,把“民屯”与“军屯”相结合,用经济的办法办经济,反对掠夺性的摊派征收:“一意筹办军食,何从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举行之初,须察缠头(指当地少数民族回民)现存若干,其力可耕垦无籽种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别发给,令其安心耕获。收有余粮,官照时价给买,以充军食。其必须给赈粮者,亦酌量发给粗粮,俾免饥饿。”⑤他认为:“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食用外,余粮可给价收买,何愁军食无出?官军能就近采买,省转运之费不少。”他认为只要让回民“有利可图”,那么“何事不办?”显然这是贯彻了经济利益的原则,“此民屯要策也。”他认为“军屯”也必须坚持经济利益的原则:“最要是照粮给价,令勇丁均分,庶男丁有利可图,自然尽力耕种。营哨官出力者,存记功次优奖,否则记过。如此,则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外又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此兵屯要策也。”⑥显然,这一整套“民屯”与“军屯”相结合的主张,是一种辩证联系,综合考虑,一举多得的利国、裕民、强兵的战略措施。他还主张利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来促进商业流通,保证粮食供应:“不勒定本境市价,人情趋利若鹜,境内价高,商贩闻风而至,粮价自当平减。”⑦他特别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早年就撰写过有关农业的专著《朴存阅农书》。他到西北后又亲自刊行《种棉十要》、《棉书》,大力推广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大办水利,广种草棉,提倡种树,绿化沙漠,改善西北自然环境。他还从外国引进机器,“制机轮挹河流注之园中”⑧;“并购开河机器,使施治于泾川上源”⑨,利用先进的机械设备,来抽水灌溉,治理河流,提出了一整套开发建设西北的战略设想。
2.学习西方,锐意求强
左宗棠在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立足于放眼世界,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的宏观系统中去考察,坚决反对那种孤立的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反对那种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顽固保守思想。他极力推崇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亲自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作序,宣传世界大势: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敏慧,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有专诣,盖得儒之数而萃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适泰西火轮舟车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竟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⑩这说明,他清醒地看到西方之强与中国之弱,不再以“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自居。在这“日新而月有异”的世界形势中,中国当然不可能孤立地永恒不变地存在下去。对此,他尖锐指出:“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11)因此,他既提出了学习外国、赶超外国(“藉外国导其先”)的战略任务,又批判了那种自甘落后、让外国垄断先进技术(“让外国擅其能”)的民族自卑感。
左宗棠还从哲理思维的高度,揭示中国与西方思想方法的根本差异:“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理义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12)他深刻地揭露了以“理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宋明理学的根本缺陷是“虚”,即空谈义理性命,不求实功实效,无益于国计民生,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了避免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他对当时激烈进行的“本末”、“体用”之争,采取“姑置勿论”(13)的态度。很显然,他的思想与后来张之洞等人所鼓吹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有所区别的,可谓挖到了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的思想根源。
左宗棠兴办洋务伊始,就明确指出是为了“自强”。他在请求设立福州船政局的奏稿中,首次提出“雇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的主张。他认为只有自己造船,才可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用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办之”(14)。主张以机器制造为轴心,带动和促进科学技术及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无事之时,以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厘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业贫民,舵艄水手足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有必设之防,用兵有必争之道也。”(15)这充分说明,他兴办“洋务”并不纯粹是从军事需要出发,也是从国计民生出发,更是与外国列强展开“商战”,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需要:“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洋船准载北货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南回,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浸至失其旧业。滨海之民,商居十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日减。富人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16)他还进而主张:“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而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大凡水师,宜常川操练,俾服习风涛,深其阅历,然后可恃为常胜之军,……且船械机器废搁不用,则朽钝堪虑。时加淬厉,则晶莹益出。”(17)因此,他认为“雇买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擅无穷之利”(18)。在这里,左宗棠辩证联系的思想表现得十分突出。他把平时与战时相结合,军用与民用相结合,漕运与商运相结合,军训与运输相结合,使用与保养相结合,强兵与富国相结合,形成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系统。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提出了全面近代化的初步设想。
正是在这“自强”思想的指导下,他于1866年设立福州船政局,发展我国造船事业;1871年设立兰州制造局,制造枪炮子弹,发展军火工业;1879年设立兰州织呢局,并“分行陕甘各属设局教习纺织”(19),发展我国纺织事业;1880年引进外国最新发明的鱼雷、水雷加强闽浙两省海防;1883年奏请架设陆路电线,发展邮电事业。他还多次派人去外国聘请“开河、凿井、织呢师匠,带购机器,来兰州入制造局教习西法。”(20)这一系列措施,为中国引进了第一批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
3.力主台湾、新疆建省,加强祖国统一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刚任闽浙总督,就高度重视台湾:“以台湾为沿海重镇,檄调吴大廷为台湾道,刘明镫为台湾镇总兵”(21),提出了经略台湾的战略设想。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他不仅积极请战,“广筹军火”(22),及时派遣得力部下王德榜赴越作战,配合老将冯子才取得了威振中外的镇南关大捷,而且不顾已是73岁的垂暮之年,亲赴福建海疆,英勇抗法。他先后派遣王诗正与杨岳斌,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突破封锁,冒险偷渡,有力支援了孤岛血战的台湾军民。他临死前的一个月(1885年6月),还上奏朝廷:“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镇摄。”(23)正是在左宗棠等人的大力提倡与推动下,促使清政府在这年10月将台湾设为行省。
左宗棠在平定新疆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24)他提出了治理新疆的一整套施政措施:“新疆善后事宜,以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数大端为最要。”(25)他一贯重视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主张“敬教劝学,卫国以中兴。”(26)为了消除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合,他大力提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认为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战略措施:“广置义学,先教以汉文,俾其略识字义。……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27)他特别重视儿童的教育,“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28)。为了逐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还“续发《孝经》、《小学》”,“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29)这些教育措施,无疑增进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增强了民族团结。
台湾和新疆设立行省,加强了祖国的统一和团结,维护了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这是左宗棠为之呕心沥血,一直奋斗到最后一息的宏伟战略目标,是左宗棠求强御侮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永远歌颂。
二、“通筹”与“扼要”相结合的全局重点论
“通筹”与“扼要”这两个政治军事术语在左宗棠的著作中反复出现,屡见不鲜。他说的“通筹”实指从战略全局出发,全面分析,通盘考虑;“扼要”就是抓要害,抓重点,抓关键。二者结合起来,就是全局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很显然,这既符合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的思想,又符合辩证法关于在多种矛盾中抓主要矛盾的思想。
左宗棠在进行战略分析的时候,总是首先从全局观念出发,表现出全面联系,环环相扣的战略整体思想。例如,他在“通筹”西北战略计划时指出:
“窃维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平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必合时与义通筹之,乃能权其轻重,而建置始得其宜。……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30)
他把整个西北看成一个“臂指相联,形势完整”,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当朝廷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时,他针对李鸿章提出的“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的谬论,严加驳斥: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关,亟宜熟思审处者也。论者又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致,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31)
左宗棠深刻地阐明了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想,指出西北、东南,“利害攸分”,任何一方失利都足以牵动全局。现在全世界都在注视我国西北的动静,以窥测我国力量的强弱。如果一味妥协退让,示人以弱,各国认为有机可乘,将更加激起贪婪吞并的欲望。只要坚决收复新疆,振我国威,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才能达到使“各国必不致构畔于东南”的战略目的。他还指出:“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我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32)
左宗棠的全局论,并不是处处等量齐观,而是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是全局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他在“通筹”全国海防的时候,把这一战略思想表述得更为清楚:
“然合七省通筹,则只此一海,如人一身,有气隧、血海、筋脉、包络、皮肉之分,即有要与非要之别。天津者,人之头顶;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之可护头顶腰膂,皆宜严为之防。以此始者以此终,不可一日弛也。此外视如髋髀,谓其无足爱惜固不可,谓其必全力注之,亦不必也。”(33)
这是运用我国中医全面联系、辩证施治的思维方法,分析军事战略形势,既着眼于全局,又突出重点,提出了把主要力量放在要害之处,实行重点防守,兼顾一般,而不是处处“全力注之”,分散兵力。这就是“通筹”与“振要”的辩证统一。左宗棠不仅在宏观决策中运用了这一辩证方法,就是在每一战役实施中,也贯彻了这一方法。例如,他在用兵陕甘时,就运用了这一全局与重点相结合的辩证法:“督臣总督陕甘,当筹两省全局。……今日在陕,固不能视甘肃为遐方。异日入甘,亦仍必以陕甘为根本。”(34)而决定陕甘全局的关键又在:“关陇安危机括,全在金积。金积一克,全局已在掌中。”(35)进军新疆,他更加熟练地运用了这种“通筹”与“扼要”相结合的战略战术,指出“乌鲁木齐各城为新疆关键”(36),“不复乌垣,无总要可扼”(37),“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蒙古将无息肩之日”(38)。只有先克乌鲁木齐,才能取得一个支撑西北全局的战略基地,进可攻,退可守,达到“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39)的战略目的。因此,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的作战部署。在进军南疆时,他又是实行“三路分兵”,“分派大支,扼其总要,然后直捣中坚”(40)的战略战术。
由上可见,左宗棠战略战术的每一个层次,都贯彻了“通筹”与“扼要”的辩证统一。从全国形势到局部战场,从宏观战略到具体战役,从前一过程到后一过程,环环相扣,层次分明,轻重缓急,井井有条,处处体现了全局论与重点论的高度统一。
三 “层递灌运”与“缓进急战”相结合的军事运筹学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正是由古代战争向近代战争过渡的时期。战争的武器从原始的大刀、长矛、骑兵、木船逐渐被自动化的枪炮、军舰、鱼雷、水雷所取代,引起了军队编制、战斗队列、训练与作战方法,以及后勤供应的一系列变革。左宗棠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优秀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而且也吸取了西文近代战争的某些经验,特别是掌握了周密的数学运算的方法,来分析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及其变化,尽量做到较有效较经济地使用兵力、财力,以制定最佳作战方案,初步体现了现代军事运筹学的一些基本思想。他说:
“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夷情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不应,并有贼算出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云‘多算胜少’及‘每一发兵而须发为白’者,非虚语也。”(41)
他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关于“知己知己”和“多算胜少算”的军事思想,越来越深刻地看到周密严谨的数学运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预先计算与战争结果相符合或相矛盾,以及符合程度的多种复杂情形。他既看到了战争过程中“千变万化”、“瞬息不同”的难以捉摸性,以及由此决定的“随机立应”、“胜负止争呼吸”(42)的灵活机动性;又看到了战争规模的相对稳定性与可测性:“至用兵之道,规模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商”。这就是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所作出的“层递灌运”与“缓进急战”的战略决策,就是我国近代战争史上第一次成功地运用军事运筹学的光辉范例。左宗棠在用兵陕甘时就尖锐看到:“窃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43)而进军新疆,这一矛盾就更加突出:“此次出关人马一万数千,嘉峪以西不但无可采买,且须筹赈。由肃七站到安西,十一站到哈密。道经戈壁,无水草,无民人,无牲畜,均须由关内筹划。”(44)特别是当时全国东南西北同时吃紧,政府财政困难万状,更加需要“通盘筹划”,周密计算,“撙节支用,无一浪费,无一冗食”(45)。正是这种客观形势,迫使左宗棠必须对战争规模,敌我双方,军饷来源,军火物资,粮食供应,运输路线,交通工具;进攻时间,气候变化,地理条件等多种复杂因素,进行分门别类的周密筹划与数学运算,然后综合起来,进行总的战略决策,制定出具体的作战方案,真正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首先,在战争规模和用兵人数上,左宗棠看到西北粮食的紧张与运输的困难,坚决采取了精兵减员的措施,把进军人数初步定为一万数千人,加上后勤人员,共两万余人,而阿古柏却拥有英国军火装备的四万余人的武装力量。这就面临着以少胜多的战争态势。
第二,在粮食筹运上,他从士兵、役夫每人每天的口粮、以及作为运输工具的骡马、骆驼的食量,到整个军队的粮食总量,都进行了周密的计算。在进军新疆之前,共筹备1700多万斤粮食。在运输线路上,以肃州为总后勤基地,在玉门、安西等地沿途设立粮站,分段向哈密运输。后来又开辟了从归化、包头,取道射台、大巴至巴里坤的北路运输线,“如此层递衔接,人畜之力方稍舒展,而士气常新”(47)。这就是“层递灌运”的方针。
第三,在运输工具问题上,他认为应以骆驼作为主要运输工具。这是因为新疆“地多戈壁,水草缺乏,非骡马所宜,亦非民车木轮所便”。(48)另从运输途中粮食消耗来看,每车需要一人两骡,每人每天吃粮2斤,每骡吃粮8斤,每车每天耗粮18斤。而每只骆驼每天只需粮3斤,每人可看管5只骆驼,如行至关外有水草的地方,骆驼只食草不食粮料,又可大大节省粮食。这样既可以增加粮食运输量,又可以减少沿途粮食消耗,一举多得。他经过周密计算,全军运输大约需要3000只骆驼。
第四,在运粮和用兵时间问题上,他根据西北粮食收获主要在八月的特点,所以把运粮时间定在八月之后。至于用兵时间,更受到西北冬季严寒气候条件的限制,因此,他把进攻北疆(1876年)与南疆(1877年)的时间都定在春季。这也是他制定“缓进急战”作战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在进军路线上,他制定了“先北后南”的作战部署,北路以古城和济木萨为前哨阵地,集中兵力,沿着阜康城——黑沟驿——古牧地,向西一路横扫,首克乌鲁木齐,“扼其总要”,“重防南路”,清扫各路流窜残敌:“凡山径小道可通人行者,应即严密扼截,务期滴水不漏,始策全动。”(49)第二年进攻南疆,则是三路分兵:金顺一军留防北路;刘锦棠一军从北向南,进攻达板、托克逊、阿克苏;张曜、徐占彪合军自东往西进攻吐鲁番。其中以刘锦棠一军为主攻方向,其他各路又各有自己的进攻重点。先后缓急,层次分明,互相策应,有条不紊。
左宗棠不但能够正确的预订作战计划,而且能够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自己的计划。如,进疆之前,他力主精兵减员,一次就裁军40余营。随着战争胜利发展,占地越广,战线越长,兵分越单,为了不使攻势成为“强弩之末”,他及时请求朝廷调金运昌一军进疆参战,巩固后路,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左宗棠进军新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始至终地运用了军事运筹学,从整个军队的总开支,到每个士兵、夫役以至每只骡马、骆驼的粮食消耗;从路程的远近,到气候的变化;从何时减兵到何时增兵等各个方面,他都进行了周密的数学运算,不打无把握之战,不打无准备之战。“缓进”稳如泰山,“急战”迅如烈火。连当时欧洲人编的《西国近事汇编》也惊叹不已:“当初陕甘总督左钦帅募兵于关外屯田,外国人方窃笑其迂。今乃观之,左钦帅急先军食,谋定而往,老成持重之略,决非西人所能料。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兵克乌鲁木齐,分略诸地,部署定,然后整军进征。……势如破竹,迎刃而解。其部伍严整,运筹不苟,如俄人攻基法一般。”“中国至喀什噶尔一律肃清,可谓神矣。其克喀喇沙拉也,兵以寡胜。其克喀什噶尔也,兵以合围胜。使欧人当此,其军律亦不过此。……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50)
四 矛盾对立双方互相转化的辩证发展观
左宗棠的辩证法思想还表现在他较深刻地看到,客观事物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天道不翕聚则不能发舒,无夜何以有昼,无秋冬何以有春夏,此恒理也。”(51)他从人间的贫富,社会的治乱,国家的盛衰,战争的胜败中看到,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不处在永恒的发展变化中。他深刻地分析了,贫富、盛衰、治乱、强弱、胜败、长短、远近、迟速、利弊、损益、刚柔、升降等矛盾对立的范畴,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转化的关键又在于,处在这些矛盾运动中的主体——人,特别是决定军国大事的人,能否掌握“自强之道”(52),以“自强”应万变。这实质上是坚持发展变化的“内因论”,也就是他一贯推崇的“范文正有云:‘吾知其在我者当如是而己’”(53),既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自强为急”,又指出必须符合客观变化的规律性:“实事求是”(54)。左宗棠辩证法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上述古己有之的矛盾范畴,用之于求强御侮的政治军事实践,与近代“日新而月有异”的世界客观形势相结合,与西方先进的机器工业、科学技术相结合,使其辩证法思想明显地打上近代自然科学的一些烙印。
首先,他敏锐地看到西方之强与中国之弱,而这种强弱又是西方机器、轮船、枪炮技术之长与中国技术之短造成的。同时,他还看到,外国之强,不是一切皆强,而是强中有弱;中国之弱,也不是一切皆弱,而是是弱中有强。长短也是如此。例如海战为外国之长,中国之短。至于“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不及也。”(55)他从当时号称“日不落”的最强大的英帝国主义的极盛中,看到其开始跌落的征兆:“泰西各国,均以经商为本务,而英吉利为之宗,所以雄视诸国者,该国之规模法度较西人本为整齐,又明避实击虚之略,故所向无前。……惟察英人近时举动,颇有志满气骄,易视与国之意,究亦外强中干,难以持久。”(56)这说明他清楚地看到大英帝国的强中之弱:“外强中干,难以持久。”他还深刻地看到,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并不是从来如此,也不会永久如此。当他看到明朝万历年间制的大洋炮时,曾发出这样叹息:“然则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以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57)这说明,在明朝万历年间,中西方武器生产的技术还相差无几,只是近百年才逐渐落后的。他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弱”与“短”,既不自甘落后,又不妄自尊大:“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58);同时又能认真学习人家的长处:“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59)这样发愤图强,“触类旁通”,“积微成巨”(60),“则洋人之长皆华人之长,实为永久之利。”(61)深刻地阐明了“弱”可变“强”,“短”可化“长”的辩证法。
在沙俄占我伊犁,蚕食边境,我国面临“日蹙百里之势”的严峻形势下,很多人担忧俄强我弱,开战必败。左宗棠严正指出:“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亦在势。”(62)从“理”这方面说,“我睦邻之谊,尽而又尽;彼餍足之道,加无可加(63)。我国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全国激愤,士气高昂;俄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师出无名,失道寡助。从”势”这方面说,“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64)由此,他得出结论:“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65)正是在这种强弱、长短能够互相转化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他在等待中俄外交谈判解决伊犁争端的同时,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为此,他还对战和、胜败的关系问题作了这样精辟的辩证分析:“主战固以自强为急,即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譬之奕棋,败局中亦非无胜着。惟心有恐惧,则举棋不定,不胜其耦矣。”(66)他深刻看到,战与和这两种貌似对立的斗争方式,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互相配合,相辅相成。至于战争中的胜与败更不是绝对的,而是胜中有败,败中有胜,胜败完全能够互相转化。其中关键在于“自强为急”,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从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眼光出发,指出中俄接界一万数千里,一旦开战,在从东到西的广阔战线上,由于客观条件千差万别,必将出现得地与失地,前进与后退,这个战场局部取胜,另一战场局部失败的犬牙交错的复杂情况。这就可以用围棋“打劫”的方法,造成“转换”和“劫活”。在给来犯者以沉重军事打击以后,最后通过外交谈判来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民族尊严。这一辩证法战略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左宗棠在分析利弊、损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时,同样贯穿了这种互相转化的辩证法思想。他在筹办福州船政局时指出:“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67)清楚地揭示了“损”与“益”,“一时”与“数世”即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收复新疆就是这种“始损终益”,“一时之费,数世之利”的光辉范例。他指出,虽然这在当时是“艰阻百倍”、“罕见其比”(68)的艰巨事业,但却是造福于中华民族的宏图伟业。它在政治上捍卫了国家主权,在军事上巩固了西北边防,在经济上也决不是如李鸿章所言“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是有着广阔的开发前途。左宗棠当时就指出:“至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牣者。……若全境收复,经划得人,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69)。“此外,南北两路物产,尚有药材皮张,吐鲁番之棉花,和阗之玉,库车之金铜铅铁,均应设筹及之。是新疆利源非无可开也。”(70)左宗棠能作出这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与这种辩证转化观和发展观是分不开的。他在平定新疆之后深感自慰地说:“而边塞任事之人,能见谅于后世,未必尽见许于当时。”(71)实际上左宗棠何只是“能见谅于后世”,而是应该受到后世永久的感激!
当然,左宗棠作为地主阶级改良派(洋务派)政治家,自有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其辩证法思想也不彻底,而是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天道循环论”的色彩。对此,我们不必苛求于前人。而且这些局限与缺陷,也并不妨碍左宗棠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收稿日期:1997-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