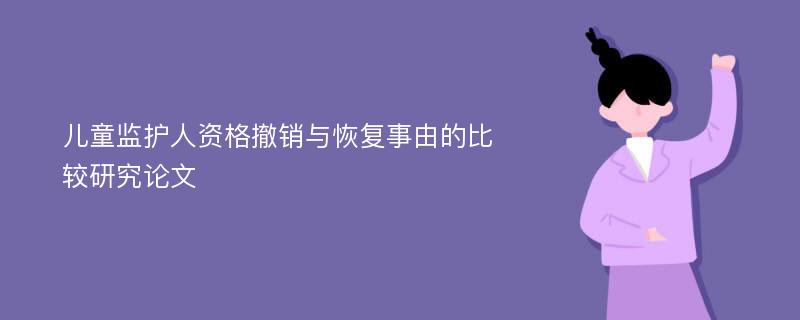
儿童监护人资格撤销与 恢复事由的比较研究
王雯雯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法学系,北京 102488)
摘要: 监护撤销与恢复的事由是私权设置的一道双向防护网,其在帮助保护儿童利益的同时也防止公权力坐大导致的撤销宽泛化,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域外大陆法系各国随着“私法公法化”的监护制度大变革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法活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在立法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监护撤销与恢复的事由规定,鉴于我国《民法总则》第36条第1款的规定存在撤销或恢复监护资格事由设置不够周全、忽视财产权保护等问题,建议将监护人侵犯儿童财产权利与客观事实阻碍纳入撤销制度保护的范围内,并增加恢复撤销实质条件的规定,以完善我国相关立法。
关键词: 儿童监护;监护资格撤销事由;监护资格恢复事由;民法典立法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公权力对于私领域的干预从未停止,尤其是在婚姻家庭领域。“然而传统法律中的国家干预,是一种选择性介入,其实是通过维护父权体制而存在的,即一方面法律承认和维护家庭中父权的统治,另一方面以尊重家庭为由不再介入。”[1]近代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继续固守较高程度的伦理自律性和专权自治性已不合时宜,仅依靠以自治理念为原则的监护制度也无法有效保护原本就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的儿童。①与此同时,随着福利国家理论的发展,保护弱者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对儿童的监护不再被简单归于私领域范畴,基于这一点,儿童监护人资格撤销制度应运而生,成为国家公权力保证监护制度正常运行的“最后一道防线”。
监护资格撤销制度②作为国家公权力免除、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制度,是公权力干涉私领域的体现。由于“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权涉足私权领域尤应谨慎。法律对公权介入的范围及力度务必要加以严格限定,以免有干扰私权自治之嫌”[2],而且儿童监护资格撤销对家庭的稳定和儿童被监护人的身心健康影响极大,一旦宽泛适用,会直接导致更多儿童脱离家庭,对儿童的成长极为不利。因此,对撤销规定严格的事由进行限制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同时,为了保护儿童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避免二次伤害,规定严格的恢复事由也必不可少。家庭生活对于儿童被监护人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监护资格撤销事由(以下简称“撤销事由”)消失和符合被监护人利益的情形下,恢复监护人的监护资格是尽量降低撤销监护人资格负面影响、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重要手段。综上所述,监护人资格撤销与恢复之事由对整个制度运行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这一点在各国立法中亦有体现,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经过多年发展已较为成熟。我国现行的《民法总则》虽已规定了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等三项事由,但不管从立法还是实践的角度都不能完全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因此,参考成熟的域外立法对我国儿童监护资格撤销制度的相关立法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拟就儿童监护人资格撤销事由和恢复事由两个方面对已积累了丰富相关立法经验的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与我国现行立法作比较研究,以期发现我国现行相关立法中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意见。
一、儿童监护人资格撤销的事由
儿童监护人资格撤销的事由归根结底是为了防止儿童遭受来自监护人的伤害,保护儿童利益,故而该事由体系亦围绕儿童保护这个核心利益而建立,这一点也表现在各大陆法系国家相关立法中。总结各国立法相关规定,共有七类事由较为常见,即监护人严重伤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监护人违反义务、监护人失职、监护人品行恶劣、监护人实施不当行为、监护人实施犯罪(非针对监护人)、客观事实阻碍。这些事由所规定的均为监护人出于主观故意或非故意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利的情形。另外,由于监护人品行恶劣、实施不当行为与实施犯罪行为三者之间有一定的逻辑联系,因此一并说明。
1.伤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
我们要从思想观念上将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并重,从教学理念上认识到人文素养缺失的严重后果;在顶层设计上完善中学课程设置,为学生修习人文学科预留充分时间;从就业层面完善就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以更多高薪岗位促进“重理轻文”这一思想观念的更新迭代。唯有如此,才能将“理工”与“人文”结合,走出“半个人”的世界。
儿童在行为能力方面有明显的缺陷,需要照顾与保护才能正常进行社会生活,而当父母或监护人出于无意思能力、失踪、患病等客观事实阻碍实际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继续保留其监护人身份不仅不能正常履行监护职责,甚至可能导致儿童陷入危困状态,使其身心健康难以得到保护,这也是其成为各国立法中常见的撤销事由的原因。但是与以上四类撤销事由不同,客观事实阻碍的特殊性表现在它是由不可控的客观因素导致的。《法国民法典》第373条针对这种情况规定,“父或母由于无能力、失踪或者其他任何原因,出于不能表现意思的状态时,剥夺其行使亲权”[4]116。《瑞士民法典》第311条也规定,“父母因无经验、疾病、残疾、失踪、暴力行为或类似原因,不能按照要求行使父母照护权者,儿童保护机构得剥夺父母照护权”[10]115。笔者认为,瑞士法中撤销无经验者照护权的规定值得商榷。育儿经验不同于其他难以恢复的事由,可以通过培训机构学习或上辈经验传授等方式习得,武断撤销此类监护人的照护权似有不妥。总之,通过法律手段禁止此类主体担任监护人,防止儿童“实际无监护人”的情形,对于儿童保护有着重要的作用,是法律应当且必须规定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亦有因客观阻碍导致监护人“有名无实”的困境儿童见于报端,如无锡5岁女孩因母亲离家出走,爷爷患病离世,父亲智力低下且经常酗酒而陷入困境。[14]对于此类现象的存在,民法总则第36条第2款⑥已有回应,但规定所涵盖的范围较窄,未来立法应当进一步完善。
如上所述,我国民法总则相关立法中有关儿童监护资格撤销事由的规定还有不尽完善之处,但由于我国民法典分编立法工作尚未结束,总则立法仍可修改。乘此契机,以这些问题的解决为依托,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儿童监护人资格撤销制度,完善民法典立法,更好地保护儿童最佳利益,是目前具有急迫性的重要任务。有鉴于此,笔者针对现行民法总则立法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BP神经网络是以普通人工神经网络为基础进行改进的预测数学方法,它具有反向传播的特征,是由20世纪80年代国外专家提出的,通过神经元之间的权值调整,控制预估值与实际值之间误差比例,当预估值与实际值误差缩小到规定范围内,则默认训练达到目的,该模型具有较高的精确度。在此基础上,进行预估可到达较为理想的预测效果。
监护人,尤其是儿童监护人,本质上是义务的承担者,是“负责执行监护事务之人”[7]490,其义务就是保护儿童被监护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而监护人违反义务往往直接或间接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因此,各国立法都将之规定为撤销儿童监护人资格的事由。但是,根据监护人违反义务造成被监护人权利损害与否,各国立法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德国、葡萄牙立法要求父母之违反义务需导致子女权利的损害,无损害结果的义务违反不能作为监护撤销的事由。如《德国民法典》第1666条第2款在对本条第1款中“财产受到危害”一词作解释性规定时指出,“有权进行财产照顾的人违反其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或其与财产照顾相关联的义务,或不服从与财产照顾有关的法院命令的”,这就将作为“财产监护者”违反义务的行为规定为剥夺监护资格的事由。[8]510该法第1886条还规定,“独任监护人职务的继续执行尤其因监护人违反义务的行为而会危及被监护人的利益……家庭法院必须免去独任监护人的职务。”[8]550与之类似,《葡萄牙民法典》第1915条规定,“父母一方因过错违反其须对子女承担之义务而使子女受严重损害,……则应……之申请,宣告禁止行使亲权”[9]344。另一类是瑞士、意大利立法直接将“父母违反义务”单独作为撤销事由。《瑞士民法典》在其第311条第1款中规定,“父母……或严重违反其对子女应尽之义务者,儿童保护机构得剥夺父母照护权”[10]115。除此之外,《瑞士民法典》还对剥夺父母探望权(瑞士法称为“个人往来”)的事由作了特殊规定,其第274条第2 款规定,“个人往来有害于子女利益,或者父母在往来时违反义务……得拒绝或剥夺其行使个人往来的权利”[10]101。《意大利民法典》第330条规定,“裁判官,于父母违反其权能内在的义务,……得宣告从其权能失格”[11]72,该法第384条还规定,“监护裁判官,在监护人……被证明其权限的行使不适当,得将监护人从其职务罢免”[11]81。由此可见,尽管两法均以违反监护人义务作为撤销事由,但瑞士法采取冠以“严重”等字眼作为限定的方法防止事由的宽泛化,意大利法则将判断的权力赋予法官(裁判官)。总之,两种类型均有其合理之处,但后者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形成实践难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前者规定更有确定性与指向性,有利于司法实践的展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儿童被监护人拥有一定数量的个人财产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监护人损害被监护人财产利益的行为亦不鲜见,然而我国现行立法中相关规定尚付阙如,究其原因还是由于现行法律对儿童财产权利的漠视。《德国民法典》中将违反财产照管义务规定为重要的撤销事由,这一规定为我国同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借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监护人失职
从世界范围来看,儿童保护与照顾提供者的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监护人与亲友,二是学校与相关社会组织,三是国家公权力机关。作为儿童最主要的保护提供者,监护人的失职行为极有可能造成实践中有监护人之名、无监护人之实的情形,导致儿童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甚至受到伤害。有鉴于此,德、法、葡、瑞,包括我国,现行立法均将监护人失职作为撤销儿童监护人资格的事由,但由于具体规定的切入点不同形成了两种模式,即行为描述型与主观意愿描述型。前者如《德国民法典》第1666条第1款规定,“子女肉体上、精神上或心灵上的最佳利益或其财产受到危害,且父母无意或不能避开危险的,家庭法院必须采取对于避开危险为必要的措施”[8]510,并在本条第3款第6项中将“部分或全部亲权之剥夺”规定为“必要措施”的内容之一。《法国民法典》第378-1条规定,“父与母,……或者因对子女不予照管或引导,使子女的安全、健康与道德品行显然受到危害时,可以在任何刑事判决之外,被完全撤销亲权。在对其子女已采取教育性救护措施后,父与母在超过2年的时间内故意放弃行使与履行第375-7条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者的,同样被完全撤销亲权。”[4]133《葡萄牙民法典》第1948条更是直接撤销此类监护人。[9]352以上“无意或无能力排除危害”“不予照管和引导”“故意放弃行使与履行义务”“未履行”等都是对监护人的具体行为的描述。后者如《瑞士民法典》第311条第1款则规定,“父母漠不关心或严重违反其对子女应尽之义务者,儿童保护机构得剥夺父母照护权”[10]115。这一规定所使用的“漠不关心”则完全是对监护人主观意愿的描述。尽管心理状态描述更能体现监护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采用具体行为描述方法规定失职的立法更多,其主要原因在于心理状态描述型的表述不够具体,“何为‘漠不关心’”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较难解决,这也是少有国家采用此类立法模式的原因。我国现行《民法总则》也采用了行为描述的立法模式,在第36条第2款中将“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与“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规定为监护撤销事由,并规定以上行为必须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后果,这与大多国家的规定具有一致性。另外,《民法总则》该款规定中还提出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的规定,这是对我国关于监护职责长期坚持的概括式立法的重要突破,也为我国监护撤销制度纳入部分撤销监护人资格以更好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提供了立法基础。有学者提出,我国实践中的困境儿童广义上包括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儿童,[12]监护撤销制度为改善危困儿童的权利保护贡献积极力量,是制度建设的应有之意。
4.监护人品行恶劣、实施不当行为或犯罪
“儿童尤善观察模仿身边成年人的行为,监护人,尤其是父母,作为与儿童关系最亲密、对儿童生活影响最大的成年人,对他们的行为与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13]。因此,尽管品行恶劣作为社会对人的道德评价,一般不被法律作为评价的依据,但实践中一些严重的道德问题,如吸毒、酗酒、赌博等,会导致儿童被监护人长期置于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甚至有可能模仿这些行为,从而对儿童的成长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品性恶劣者担任儿童的监护人对他们的成长极为不利。但由于品行是否恶劣是以道德为判断标准的,而道德在不同的国家,甚至一国内的不同地区都甚为不同,且受到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更勿论被社会主流道德与价值观确定为品行恶劣之人会否一定不能胜任儿童监护人的问题也值得商榷。因此,除酗酒与吸毒这两类品行特别恶劣者被法④、俄⑤等国立法撤销监护资格以外,罕有立法将品性恶劣规定为撤销事由。我国虽在《意见》第35条第4款有类似规定,但《民法总则》中并未提及,这也说明《民法总则》作为我国重要立法更为审慎的态度。
建国以来,反腐败罪名体系随着刑法的打击半径越来越宽,打击程度越来越深,打击力度越来越大,“经历了从单一的贪污罪到贪污罪、贿赂罪的两罪并立;从单一制裁‘侵犯所有权’到兼而制裁‘侵犯使用权’;从单一制裁‘利用自身职权受贿’到兼而制裁‘利用他人职权受贿’;从单一制裁‘在职时受贿’到兼而制裁‘离职后受贿’的立法历程”。[10]为进一步加大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的密切合作,努力构建更加开放、更加适应现实、更加“国际化”的反腐败罪名体系,需要修改完善腐败犯罪刑事法律,进一步跟进和加强国际合作,满足国内反腐败的法律需要。
在观察镜下标本时,应养成双眼同时睁开观察的习惯[4]。在实验课上,我们经常发现刚接触显微镜的学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使用显微镜,教师要及时纠正这种错误做法。首先把目镜间距调整到与双眼距离相等的宽度,如果有眼镜一定要摘下,之后把双眼尽量的靠近目镜,轻微调整目镜间距使双眼中可以呈现出一个完整且不重复的成像。这样观察镜下标本既可以增加视野的宽度和完整性,而且更接近于我们平时的自然用眼方式,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视疲劳。
注释:
如上所述,监护撤销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对被监护人利益的保护,因此如果恢复监护人资格符合被监护人的利益,应当予以恢复,但撤销事由的持续存在可能导致监护侵害的再次发生,因此为了避免重复伤害,满足“撤销事由消失”是首要条件。撤销事由消失是监护资格恢复的实质要件,也是必要事由,大多大陆法系国家也将撤销事由消失规定为监护恢复的唯一事由。如《德国民法典》第1696条第2款规定:“对子女最佳利益的危害已不复存在,或措施的必要性已消灭的,仅在对于避开对子女最佳利益的危害为必要或对于子女最佳利益为必要时始得采取的《民法典》第1666条至1667条或其他条文所规定的措施(子女保护法上的措施),必须予以取消。”[8]517《意大利民法典》第332条也规定,“裁判官,对于从全能失格的父母,在宣告其失格的理由消灭,对子女损害的一切危险已经除去时,得使其权能恢复”[11]72。与上述规定类似,葡萄牙民法中也有“法院宣告之形式亲权之禁止,在导致禁止之原因终止时须予终止”的规定。[9]352日本立法也基本相同。可见大多国家在监护恢复裁判中均以撤销事由消失与否为核心标准,它是撤销恢复的实质要件。
5.客观事实阻碍
随着全球能源的逐渐枯竭、大气污染的不断加剧以及气温上升带来的危害加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节能减排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电动汽车应运而生,并迅速得以广泛应用[1]。电动汽车作为电力负荷,其充电行为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在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由于充电器本身包含各种非线性特性的电力电子元件,会向电力系统注入谐波,当谐波超过一定范围,将会给电网带来谐波污染,从而对电网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同时也将缩短电池的寿命,因此对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的谐波进行分析和检测具有重要意义[2-4]。
儿童为弱势群体,是被伤害与凌辱的高发群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9条第1款规定,“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顾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规定为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保护儿童不受父母、监护人或相关人员伤害的情形。这些行为大多是父母或监护人主动采取的伤害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往往直接损害儿童身心健康,造成对被监护人的极大伤害。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将其作为撤销儿童监护人资格的重要事由规定在立法中。《日本民法典》第834条规定,“因父亲、母亲虐待或者遗弃,或者父亲、母亲行使亲权显著困难或者不适当而损害子女的利益时,家庭法院可以……做出亲权丧失的审判”[3]204。《法国民法典》第378条规定,“父母作为对其子女人身实施之重罪或轻罪的正犯、共同正犯或共犯被判刑,……得因刑事判决的规定而被全部取消亲权”[4]。《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规定得更为详细,第69条第4款将“虐待子女,包括对其实行肉体或者精神上的暴虐,对其性的不可侵犯性的侵犯未遂”规定为撤销监护的事由之一 。[5]490我国首部相关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1条第1款规定将“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规定为撤销事由。而后于2017年生效的《民法总则》受《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5条第1款③的影响,也在其第36条第1款将“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规定为撤销事由,这也更加直接具体地在立法中对这一事由进行了确认。当然,此类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大多为虐待、遗弃、性侵害等暴力行为,尽管性质恶劣,但因其中部分行为属于刑法规制范围,所以一些立法并没有在民法中将其规定为撤销事由,而是选择在刑事裁判的同时撤销犯罪者的监护资格,如《葡萄牙刑法典》在其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第152条第6款中规定,“被认定构成本条规定之罪的人,在考虑其行为的具体严重程度与该行为与其所行使的职能之间的联系后,可以禁止其行使亲权、监护权或者保佐权”[6]105。当然,必须明确的是,撤销监护资格并非刑罚的一种,而是由于实施了特定种类犯罪者被法律认定不再适合担任监护人一职,其核心是为了防止监护侵害、保护子女权利,而非惩罚犯罪。
除了以上几个事由,滥用监护权这样的概括性条款也规定在意大利(《意大利民法典》第330条)、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39条第3款)等国的相关立法中。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事由,如俄罗斯法典中有关“利用监护关系达到私利的目的”被作为撤销事由,该规定原意似在防止被监护人权利受损,但究其严重程度似乎还不足以单独作为撤销事由来规定,有过于宽泛化的嫌疑。当然,关于未成年人监护人资格撤销的事由,除较为详尽、细化的立法外,还有一些国家立法采取了概括立法的手段,较为笼统地对撤销事由进行了规定,如《奥地利民法典》第18条第1款规定:“父母的行为有危害未成年子女福祉之虞者,受诉法院应本于保障子女福祉的原则作出必要的决定。特别是,法院得全部或部分剥夺其对子女的照管权,包括法律规定的同意权”[15]31。综上所述,监护人资格撤销事由设置的核心即保护儿童利益不受侵害,这符合现代儿童监护制度建立的核心——“儿童利益最佳原则”的要求,而撤销事由对于撤销制度适用的限制无疑也体现了“必要性原则”的核心价值,这两条原则在该制度中不仅体现在各国有关撤销事由设置立法中,更体现在撤销资格恢复事由的设置立法中。
二、儿童监护人资格恢复的事由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但家庭却仍然是这些关系产生发展最基本的单位之一,因此,人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学认为这句话中“包含着一些稳定的意义:(1)它是社会初级整体;(2)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3)它是个人与社会联系的桥梁”[16]。一个儿童最初置身其中的就是家庭,在由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共同生活构成的家庭中,双方共同达成了一个稳定的生活共同体,但撤销决定一旦作出,这个共同体就会破裂。有学者指出,“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最好监护人,撤销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17]由血缘联系编织的亲情纽带决定了大多数情况下家庭监护的不可代替性,尽管时有不周之处,但依旧天然胜过其他监护提供者,这是监护撤销制度应当作为穷尽一切救济手段后才能适用的特别制度的原因,也是撤销恢复制度存在的基础。监护资格恢复作为整个监护资格撤销制度的一部分,依附于资格撤销存在,是资格撤销的补充与完善。
监护撤销程序严格且繁复,是出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作出的,因此恢复也应满足严格的事由,以防止对被监护人的二次伤害,这也是各国立法中设置严格的条件以限制撤销恢复的原因。撤销恢复的条件一般有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两个部分,学界一般还会将限制恢复的“除外条款”纳入探讨,当然关于这一点各国法律并没有类似规定,只有个别立法规定“彻底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但类似规定在实践中达到了禁止恢复资格的效果,发挥了“除外条款”的具体效果。我国《民法总则》也在第38条中将“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规定为彻底撤销的条件,采用如此严格的规定在我国缺少儿童保护基础设施的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对儿童权利的保护发挥重要的作用。
品行恶劣与实施不当行为发展至更为严重的情形即为犯罪,除上文所述的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实施暴力行为被规定为撤销事由以外,部分国家立法也将监护人实施的非针对被监护人的犯罪作为撤销事由。《法国民法典》第378条将监护人帮助被监护人实施犯罪规定为撤销事由,该条规定,“父母……或者作为其子女本人实施的重罪或轻罪的共同正犯或轻罪的共同正犯或共犯被判刑,……得因刑事判决的规定而被全部取消亲权”[4]133。《葡萄牙民法典》也在其第1913条中规定,“因所犯之罪被法律定为具有禁止行使亲权效力且被确定犯罪之人禁止行使亲权”[9]352。我国民法典中虽并未将实施不当行为与犯罪规定为撤销事由,但如上文所述,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将“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规定为撤销事由,这在实际上就将与家庭暴力相关的不当行为与犯罪作为撤销事由规定在立法中。综上所述,除上述少数国家以外,大多国家立法并未将监护人实施的非针对被监护人的其他犯罪作为事由规定,但这并非是指实施犯罪对监护人职责的履行毫无影响,犯罪记录在监护人选任中作为“监护人经历”受到审查,可能对监护人的选任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除了实质要件,撤销恢复的事由还包括形式要件,一般体现为对时间的限制。尽管不被部分国家或地区立法所重视,但以法国、葡萄牙及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依旧规定了撤销恢复的时间限制。《法国民法典》第381条第2款规定:“仅在宣告‘完全或一部取消亲权’的判决成为不可撤销的判决之后至少经过1年,才能提出恢复亲权的申请”[4]127。《葡萄牙民法典》第1916条第2款也规定,“除了检察院提出恢复无期限限制,父母任一方提出恢复监护人资格的,应当在宣判1年后提出。”[9]352尽管《意见》第38条中曾提出撤销后3个月到1年的申请恢复期间,但我国《民法总则》相关规定同大多国家立法类似,其中并未有时间限制的规定,我国学界对这一规定尽管在立法阶段有诸多讨论,支持者提出设置时间限制更有利于保障新形成的监护关系的良性运转,反对者则坚持实质要件的决定作用,如今尽管立法并未规定时间限制,但其是否适合我国实践的问题仍然值得商榷。
现代立法中,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不仅是私法调整的范围,国家公权力出于保护儿童利益的考虑正在全面参与儿童监护。各国立法在未成年人监护人监护资格撤销与恢复的事由设置上虽各有特点,但都围绕着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核心展开,这不仅是对私权的保护,更是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是对20世纪中期以来儿童利益最大化趋势的回应。我国民法典立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其中涉及未成年人监护撤销制度的规定对比实践与域外成熟立法仍有缺漏之处,值得未来立法重点回应。
三、监护撤销制度相关立法的完善
2.监护人违反义务
在此背景下,以智能快递柜为突破口的先行军企业自然受到行业和用户的青睐。以中邮速递易为例,经过6年的潜行,其当前的市场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截至2018年7月,中邮速递易累计派送包裹量突破17亿,覆盖城市225个,终端数达到8.4万,日均投件量225万(含易邮柜)。
首先,就本质而言,监护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综合体,其内容主要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个方面,即所谓的人身照护权与财产照护权。前者一般包括监护教育、居所指定、惩戒、身份行为的同意权、身份行为代理权(部分)等,后者则包括财产管理权、财产法上的代理权、对被监护人财产行为的同意权等,均为监护资格撤销制度保护的核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儿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财产的情况越来越多,儿童拥有巨额财产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法律忽视监护人滥用监护权侵害被监护人的财产权利,不仅不符合儿童的利益保护,也与我国当今社会实践背道而驰。但我国法律并未关注这一问题。考察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立法,各国民法典除了对儿童财产权利保护作专门规定外,⑦还以监护撤销制度作为用尽一切救济手段后的最后手段,将被监护人财产受到侵害作为撤销事由,如上文所述,《德国民法典》第1666条第1款就将“子女……或其财产受到危害,且父母无意或不能避开危险的”规定为撤销事由。[8]510当然,这一问题的出现也与我国当前仍坚持概括型的监护责任立法有关,如果法律明确允许部分撤销监护资格,法院便可以根据侵犯子女或被监护人财产权利者的具体情况剥夺其全部或与财产相关的亲权以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权利。因此,笔者建议将我国《民法总则》第36条第1款第1项中“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改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与财产安全的”,并参照《葡萄牙民法典》立法,在我国《民法总则》第36条第2款前加入“撤销应为全部撤销或仅撤销与子女财产相关的监护资格”的规定,将儿童财产利益保护纳入监护撤销制度的保护范围。
其次,儿童监护人资格撤销制度的设立核心是为了保护儿童的利益,而并非惩罚父母和监护人,客观事实阻碍作为撤销事由是为了防止由于恶劣的客观情形导致儿童权益受损,“考虑的是未成年子女利益是否实际能够得到保护的问题,至于父母的主观状态不在立法考虑之列”[18]。目前我国社会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客观事实阻碍导致许多儿童遭遇“实际无监护人”情形的问题,如上文所述,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已通过将客观阻碍规定为监护资格撤销事由以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相关立法虽有规定,但仅将“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全部或部分监护职责委托他人”作为撤销对象,这一规定看似合理,但实则为通过假意委托实际不变更监护者留下了操作空间。为绝此患,笔者建议参照上文法国与瑞士的立法,架构《民法总则》第36条第2款中“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的规定删除,防止因父母或监护人失踪或无意思能力导致的“实际无监护”的情形,切实保护被监护人的权利与利益。
最后,关于恢复事由的规定首见于《意见》第38条,其中仅有撤销后三个月至一年的时效规定,并未作实质要件的规定,而《民法总则》将“确有悔改表现”规定为监护资格恢复事由,这一规定较《意见》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悔改”作为对监护人主观意愿的描述,以之为撤销事由实质上依旧坚持了我国监护立法一贯坚持的监护人中心主义,更多体现了监护人的意志,而忽略了受到监护侵害的儿童自我意思的表达。另外,“确有悔改表现”不具有长期性,并不能保证监护侵害不再重复发生,因此这一规定实难回应制度设计的核心——儿童利益保护。纵观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大多以“撤销事由消失”为标准,这一规定比“确有悔改表现”更具客观性,且保证儿童无再受撤销事由困扰之嫌,更宜作为恢复事由。因此,笔者建议将《民法总则》第38条规定中的“确有悔改表现”改为“撤销事由消失”,以更好保护儿童权益。
四、结论
《民法总则》中规定了监护人资格撤销与恢复制度,这是我国完善监护制度与儿童保护的重要立法举措。然而,《民法总则》相关规定尚不能完全满足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与国外成熟立法相比仍有完善空间,主要体现在目前我国立法在儿童财产监护侵害方面尚付阙如,社会实践中广泛发生的“客观事实阻碍”未被纳入监护撤销的事由,撤销恢复实质要件的规定也尚属空白。这导致我国儿童权利保护出现权利“黑洞”,儿童权利无法得到完善保障。因此,我们殷切期望未来民法典相关立法能够进一步完善财产权保护与撤销恢复实质要件规定空白,关注“事实无监护”儿童的权利保护,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
监护制度经历了“由宗法家族法,而移于个人的社会的监护法”、由维护父权家族权利到维护儿童个人权益的发展过程,这也导致儿童监护人的地位从监管者逐渐成为照管者,这就要求合格的监护人能够以保护儿童利益为核心适当履行监护职责,这也是监护人实施不当行为危害被监护人利益被多国立法规定为撤销事由的原因。《法国民法典》第378-1条规定:“父母因……行为明显不轨……显然危害到子女的安全、健康与道德品行时,可以在没有任何刑事判决的情况下,被完全取消亲权”[4]133。《日本民法典》第846条规定“监护人有不当行为、严重劣迹及其他不适合继续监护任务的事由时,家庭法院可以根据……请求解任,或者以职权解任”[3]208。由上述两国立法可见,单纯以不当行为作为撤销事由未免会造成撤销事由宽泛化的问题,因此有此规定的法律一般都以损害子女或被监护儿童的权利为条件,防止撤销广泛化,更好保护儿童的利益。
①关于儿童的年龄标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已经作了相关规定,确定了18周岁以下的人为儿童的标准,我国作为该公约的成员之一也接受了这一标准,但由于我国法律文本中多采用“未成年人”的表述,为免理解错误,本文统一使用“儿童”一词。
我们的皮肤表面有一层透明乳状薄膜,叫“皮脂膜”,主要由皮脂腺、汗腺的分泌物乳化形成,在润泽皮肤、缓冲酸碱度、保湿、抗感染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② 监护资格撤销制度不仅包括对监护人资格的撤销,也包括资格的恢复。监护资格恢复不是一项独立的制度,它是依附于监护资格撤销制度而存在的,是监护资格撤销的后续制度与补充,因此也是整个制度的一部分。
③《意见》第35条第1款规定,“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规定为撤销儿童监护人资格的事由。
④《法国民法典》在第378-1条中规定撤销显然危害到子女的安全、健康与道德品行的酗酒者与吸毒者的监护资格。
贝伐单抗多囊脂质体的处方优化及体外释放特性研究…………………………………………………… 王毅云等(7):922
⑤《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规定,“为病态的习惯性嗜酒或者麻醉品吸食者,可以剥夺亲权”。
⑥《民法总则》第36条第2款规定,“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
你们年轻人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说完这话,老陈看一眼我,又说,你知道吗?前些日子,二十米桥那里死了一个人,都上电视了。我惊出一身冷汗,说真的死了?老陈说,电视台都报道了,我还能说瞎话。我的身子晃了一下,差点从沙发上跌下来。老陈说,那个开车的撞了人,居然跑了。真是个畜生!
⑦如《法国民法典》在亲权编专设一章对与子女的财产相关的亲权进行规定。
参考文献:
[1]李立如.法不入家门·家事法演变的法律社会学分析[J].中原财经法学,2003,(6).
[2] 彭刚.剥夺与回归:我国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制度的建构机理及其完善[J].宁夏社会科学,2015,(4).
[3] 日本民法典[M].刘士国,牟宪魁,杨瑞贺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4] 法国民法典[M].罗结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C].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6] 葡萄牙刑法典[M].陈志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7] 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8] 德国民法典(第4版)[M].陈卫佐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9] 葡萄牙民法典[M].唐晓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 瑞士民法典[M].戴永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11] 意大利民法典[M].陈国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2] 吴国平.完善我国困境儿童救助立法问题研究[J].北京青年研究,2014,(4).
[13] 桂楠,李娟.儿童模仿行为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6,(33).
[14] 无锡新吴区引入团队 精准帮扶高危困境儿童[EB/OL].中国江苏网.http://js.cri.cn/20180408/5da99583-d355-1c45-5994-20b23642b077.html,2018-04-08.
[15] 奥地利民法典[M].戴永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16] 曹诗权.未成年监护的制度关联与功能[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1).
[17] 张加林.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研究[J].学术论坛,2010,(9).
[18] 金眉.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人资格撤销制度比较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6).
收稿日期: 2019—06—03
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儿童本位的亲子关系立法研究》(编号:18BFX186)。
作者简介: 王雯雯(1992—),女,甘肃天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亲属法。
中图分类号: DF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62(2019)06-0123-08
DOI :10.13977/j.cnki.lnxk.2019.06.017
责任编辑:曹艳红,朱海波
标签:儿童监护论文; 监护资格撤销事由论文; 监护资格恢复事由论文; 民法典立法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