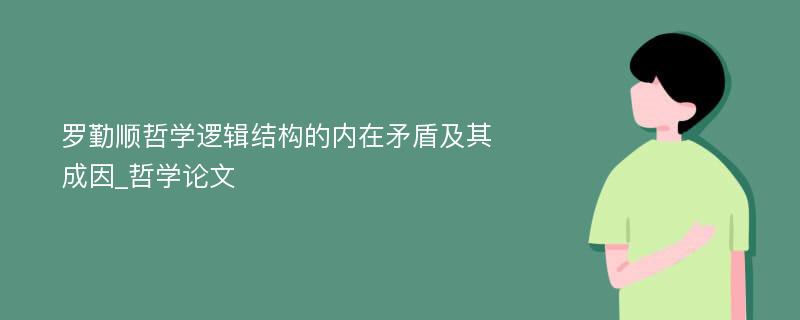
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的内在矛盾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矛盾论文,哲学论文,原因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钦顺以对程朱理学“审求其是,补其微罅,救其小偏,一其未一”(罗钦顺:《答陈侍御国祥》丁酉春)的小心修正为己任,里居二十年,足不入城市,穷究程朱理学之归趣,潜心钻研理气心性之学,并用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作为统一其自然界之理气观与人生界之心性观的逻辑前提,力图在“理”、“气”、“心”、“性”问题上构建一个相互照应、会归一处的哲学体系。系统研究罗钦顺哲学体系,可以透过其范畴与范畴及命题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探讨其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框架;可以透过其哲学逻辑结构探讨其哲学思想中论证主题与立论根据的内在矛盾;可以透过其论证主题与立论根据探讨其哲学逻辑结构内在矛盾的深层原因。
一、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框架
哲学逻辑结构是由一系列有逻辑关联的哲学范畴和哲学命题构成,体现了一个哲学家,或一个哲学流派,或一个历史时期,或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之众多哲学范畴与哲学命题之内在的逻辑关系。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构件是哲学命题,哲学命题是哲学逻辑结构中的线。哲学命题的基本构件是哲学范畴,哲学范畴是哲学逻辑结构中的点。哲学逻辑结构正是由众多有逻辑关联之哲学范畴的点与众多有逻辑关联之哲学命题的线所构成的哲学思想之逻辑体系。系统地研究罗钦顺的哲学逻辑结构,细心梳理其哲学逻辑结构中范畴与范畴之间及命题与命题之间所存在的逻辑关系,有助于把握其哲学思想的主线,避免不分轻重地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头绪繁多的枝枝蔓蔓上面;有助于把握其哲学思想的全貌,避免因集中注意力研究某一领域而完全忽视了其他相关问题;有助于通过其重要的范畴和命题较为全面准确地把握罗钦顺的哲学思想体系。
在罗钦顺哲学著作和往来书信中,“理”、“气”、“心”、“性”是四个最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对理气关系和心性关系的探讨所形成的哲学命题是其最为重要的哲学命题。其中,“心”、“性”范畴是其哲学思想里最为核心的一对范畴,“心”、“性”关系是其哲学思想的中心命题,也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论证要旨之所在。“理”、“气”范畴则是其哲学思想中最基本的一对范畴,“理”、“气”关系是其哲学思想的基础命题,也是其“心性之学”这一中心命题的论据之所在。
虽然罗钦顺在其哲学著作和往来书信中还论述了其它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如“体”、“用”、“知”、“行”、“本”、“末”、“动”、“静”、“道心”、“人心”、“已发”、“未发”等等,但在阐述罗钦顺哲学思想时,应该重点把握其“理”、“气”、“心”、“性”这四个最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应该重点把握作为其哲学思想之根据和论旨的“理”、“气”与“心”、“性”之间的逻辑关系。而通过梳理其“理”、“气”、“心”、“性”这些重要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梳理围绕其“理”、“气”、“心”、“性”问题而演绎出的重要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大体勾勒出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框架是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罗钦顺说:“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人固万物中一物尔。‘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人犹物也,我犹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罗钦顺《困知记》卷上第六章,第二页,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1版,阎韬点校。下引《困知记》只注书名、卷次、章序、页码)可见,宇宙中一“气”循环及其化育流行都遵循着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理”。宇宙界之“气”落实到人生界就是“心”,宇宙界之“理”落实到人生界就是“性”,人生界与宇宙界是相互贯通的,人生界是宇宙界的一个特殊部分,既然“心即气”且“性即理”,那么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
二、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的内在矛盾
层层梳理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时可以发现,罗钦顺虽然极力追求其哲学体系的圆满统一,但事实上其哲学体系是自相矛盾的。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1.罗钦顺哲学思想中“性”本论与“气”本论的矛盾
罗钦顺在其哲学著作中多次阐述了他“天人合一”、天人一理的思想。如他说:“所贵乎格物者,正要见得天人物我原是一理,故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人物之性各在人物身上,而吾乃能尽之者,非以此理之同故耶?”(罗钦顺:《答刘贰守焕吾》乙未秋)“盖天地人物,原无二理,故此理之在人心者,自与天地万物相与流通,是之谓仁。”(罗钦顺:《又答刘贰守焕吾》乙未秋)按照这种天人一理的思想去推演,天人物我,自然社会在大原大本上应该是统一的,人生界应该是宇宙界的一部分,人生界同宇宙界在本体上应该是一致的。正因为人生界与宇宙界是同一个本体,是可以达到“会归一处”的,所以说罗钦顺人生界“心”“性”之学与其宇宙界的“气”“理”学说便有了圆满统一的前提和可能。
但在罗钦顺哲学体系中却出现了人生界“性”本论与宇宙界“气”本论的明显矛盾。他在宇宙界的“气”、“理”学说上是持有以物质之“气”为本体的正确的观点,那么按照“天人合一”,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的思路,在人生界的“心”、“性”之学中,也应该持有以物质之“心”为本体的“心本论”(这与陆王心学以精神之“心”为本体的“心本论”是有本质区别的)。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罗钦顺反复强调:“道心,性也,性为体”(罗钦顺:《答林正郎贞孚》乙亥秋),坚持以“性”为人生界本体的“性本论”。从前面对罗钦顺哲学命题的推演中,可以得出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中“性非气”的结论。罗钦顺既视“性”非“气”,“性”与“气”不是同一归属的概念,又视“性”为人生界本体,“气”为宇宙界本体,“性”与“气”皆是本体,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2.罗钦顺哲学思想中“心”、“性”二元论与“气”、“理”一元论的矛盾
程颐、朱熹把“理”看作独立的精神本体,同时又不否认“气”的真实性,所以有“理与气决是二物”,“理泊于气上”等具有二元论倾向的思想。罗钦顺从来视“理”、“气”为一物,认为“理只是气之理”,在理气观上,他持坚定的“气”一元论,批评程朱的“理”、“气”二元论。那么罗钦顺在心性观上态度如何呢?罗钦顺认为“心”与“性”不能混而为一,“性”是体,“心”是用,“性”之体常静,“心”之用常动,“性”是形而上者,“心”是形而下者,“惟就一物中剖分出两物来,方可为知性”。只有这样剖分心”、“性”为二物,才能看到“性”与“心”一静一动,一体一用的本质区别。
在这里不难看出罗钦顺的心性观与其理气观是自相矛盾的,罗钦顺剖分“心”、“性”为二,一“体”一“用”,一“静”一“动”,“心”、“性”之间再也不像“理”、“气”之间那样绝无隙缝,从来一体了,而是如同程朱的理气观和心性观一样,表现出明显的二元论倾向。罗钦顺在《困知记》中首起一笔就说到“心”与“性”不能混而为一,此后著文及来往书信中大讲“心”、“性”之辨也表明他视“心”、“性”为二元的坚定态度。他说“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困知记》卷上第一章,第1页)然而,罗钦顺既然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生界即宇宙界之一部分,推演其哲学逻辑,又必然得出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为什么又在宇宙界坚持视“气”、“理”为一元而在人生界坚持视“心”、“性”为二元呢?这是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中的自相矛盾,是其哲学逻辑结构主要框架中“心”“性”之学与“气”“理”学说不能圆满统一的矛盾。
可见,罗钦顺哲学体系中论证主旨和理论根据之间难以相通。黄宗羲在著《明儒学案》时看出了罗钦顺哲学思想中这“心”、“性”二元与“理”、“气”一元的矛盾,如他说:“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文庄罗整庵先生钦顺》)针对这一问题,《明儒学案》又说:“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是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罗整庵钦顺》)黄宗羲对罗钦顺人生界“心”、“性”二元论与其宇宙界“理”、“气”一元论自相矛盾的批评是很有见地的。在今天看来,罗钦顺的理气观正确地坚持了以物质之“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但罗钦顺未能把他自然界的“气”、“理”学说之“气”一元论思想贯彻到人生界的“心”、“性”之学中去,因此在“心”、“性”之学上,罗钦顺又退回到程朱理学心性观的思想中,如同二程朱熹一样,有“心”、“性”二元论的错误倾向,从而同作为其哲学理论基础的“气”、“理”学说自相矛盾。这正如黄宗羲所说:“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文庄罗整庵先生钦顺》)
3.罗钦顺哲学思想中“气”为体、“理”为用与“性”为体、“心”为用的矛盾
罗钦顺哲学中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体”;“理”是“气”运作流行的规律、属性和作用,是“用”。那么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按照罗钦顺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的哲学思路,宇宙界的“气”、“理”落实到人生界当为“心”、“性”,如同“理”是“气之理”一样,“性”作为“心”之运作发用的规律法则和人际交往的伦常秩序与道德规范,当是“心之性”。如同宇宙界物质之“气”是本体,是“体”,“气”之运动规律的“理”是作用属性,是“用”一样,在人生界,物质性范畴的“心”当为本体,为“体”,而“心”之运作生理的“性”当为作用属性,为“用”。也就是说,按照天人相通的理论,在罗钦顺“心”、“性”之学中,应该是“心”为体,“性”为用,“心”体“性”用,应该是以“心”为本体的“心”本论,而不是以“性”为本体的“性”本论。
当然这里所说的“心”体“性”用的“心本论”,是与陆王心学的“心本论”截然对立的。陆王“心本论”的“心”是精神性范畴,“心”是能够化生宇宙万物的主观精神和自我意志,是一种精神本体,因此陆王心学营建的是以主观精神的“心”为本体的“心本论”哲学。而按罗钦顺理论前提正确推衍出的“心本论”的“心”是“气”聚而成的物质之“心”,是万物之一物,是一个物质性范畴,是人生界一切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物质本体。这种“心本论”认为此“心”的运作思维化生出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演化。这种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演化都应遵循称之为“性”的儒家仁、义、礼、智的伦常秩序和道德规范,在这里“性”很明显是本体之“心”的作用和属性。“心”与“性”的关系也当然是“心”为体、“性”为用的“心”体“性”用的关系。
然而,罗钦顺并没有按照这条正确的思路走下来。当他把哲学视野真正投放到人生界的“心”、“性”领域时,却完全颠倒了“心”与“性”之间“心”体“性”用的体用关系,而恰恰相反提出了“性”为体“心”为用的“性”体“心”用的思想。从总体上考察罗钦顺的哲学逻辑结构,就不难发现罗钦顺“性”体“心”用的思想与他的“气”体“理”用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而这种矛盾的产生正是由于罗钦顺在“心”、“性”之辨上完全颠倒了“心”与“性”之间的“心”体“性”用的体用关系。
4.罗钦顺哲学思想中关于“性”范畴与“理”范畴规定的矛盾
程朱理学中的“理”范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周濂溪所言形上光明之本体,是一种可以化生宇宙万物的精神本体;其二是程伊川所言宇宙变化之规律,是宇宙万物运作流行中所体现出的秩序性和必然性。程朱理学把这一宇宙界“理”范畴落实到人生界便是“性”范畴,认为“性即理也”,“性”范畴也具有本体和规律这两层含义。罗钦顺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批评和修正,在“理”范畴的规定上,他否定了“理”范畴的第一层含义,否认“理”是形上光明之本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精神本体,而只肯定“理”范畴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理只是气之理”,是“气”之化育流行的规律法则。罗钦顺对程朱“理”范畴的改造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在理气观上把被程朱理学颠倒了的“理”、“气”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而站到了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的立场上。
但罗钦顺在心性观上对“性”范畴的理解却仍然退回到程朱理学,这使其“心”、“性”之学最终不能完成对程朱理学的超越。罗钦顺哲学思想中的“性”范畴如同程朱理学的“心”范畴一样,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未发之道心,是寂然不动、静正有常的形上光明之本体,是人生界的精神本体;二是人之生理,是人之作为人类,之作为生命个体运作交往所应遵循的人的生理、心理、事理、情理、伦理、道理,是人们所应遵循的仁、义、礼、智这些规律准则、伦常秩序和道德规范。很显然,罗钦顺把他在理气观上所否定的“理”范畴的第一义,又带回到“心”、“性”之学中“性”范畴的规定上。罗钦顺充分肯定“性”范畴的第一义,从而导致其“性”范畴与其“理”范畴内涵上的显著差异和自相矛盾。
三、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内在矛盾的原因
罗钦顺身后,盖棺而定论,很多人极力推崇其修身齐家治国卫道的风格节操。黄芳在《困知记序》中说他“官至冢宰,家居泊然,锐意营道,老而不倦。”林希元在《罗整庵先生困知记序》中感叹道:“噫,当今人物,舍先生吾谁与归!百世之下,使本朝史册烨然有光,如先生者,得几人哉,得几人哉!”这类评价很多,人们对其为人为官治家治学之端庄贞肃是推崇备至的。但从学者勤奋治学一生而得已无几这一点来说,从罗钦顺视心性之学为其哲学体系之中心且自谓“研磨体认,日复一日,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困知记》卷下第四十一章,第三十四页),可他学问又偏偏失在“心”、“性”之学这一点来说,罗钦顺治学的结果是不成功的。在分析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内在矛盾后,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导致其内在矛盾的原因。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探究人生界意识活动的“心”、“性”领域要远比探究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理”、“气”领域艰难复杂得多
罗钦顺在宇宙界理气观上批评了程朱理学“理本气末”、“理体气用”、“理主宰气”的以“理”为本体的“理”、“气”二元论,提出了“理气为一”、“理在气中”、“理者气之理”的“气”一元论,坚持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坚持认为“理”只是“气”之运动变化的规律;而在人生界的心性观上却极力捍卫程朱理学“性本心末”、“性体心用”、“性主宰心”的“心”、“性”二元论,坚持以精神性的“性”为本体,坚持认为物质性的“心”只是“性”之发育流行的妙用。
为什么罗钦顺在宇宙界能对程朱理学的理气观进行适当的批评、调整和改造,却在人生界对程朱理学的心性观又极力地捍卫并全盘继承了呢?这是由于探究人生界意识活动的“心”、“性”领域要远比探究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理”、“气”领域艰难复杂得多。罗钦顺说:“盖心性至为难明,象山之误正在于此,故其发明心要,动輙数十百言,亹亹不倦,而言及于性者絶少。间因学者有问,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笼罩过,并无实落,良由所见不的,是以不得于言也。”(《困知记》卷下第四十一章,第35页)又说“盖心性至为难明,是以多误。谓之两物又非两物,谓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无性,除却性即无心,惟就一物中分剖得两物出来,方可谓之知性。学未至于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困知记》卷下第五十二章,第40页)可见,罗钦顺自己也认识到意识活动是至为复杂的。他说陆九渊是在这里犯了错误,而事实上,他自己的错误也正在于此。罗钦顺本人也正是对“心”、“性”领域复杂的意识活动认识不清而导致其哲学逻辑结构中“心性观”与“理气观”的内在矛盾。
2.程朱理学本身已蕴含着从以“理”为本体的“理”、“气”二元论向以“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转化的逻辑契机
罗钦顺主要是在理气观上对程朱理学进行了一些修正和改造,从而提出了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思想。但确切地说,罗钦顺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和修正只是因为程朱理学自身的必然发展已蕴含着从“理本气末”、“理体气用”、“理主宰气”的以“理”为本体的“理”、“气”二元论向“理气为一”、“理在气中”、“理者气之理”的“气”一元论转化的逻辑契机。
在程朱理学中,“理”范畴有本体和规律两层含义。到朱熹理气学说正式完成时,“理”范畴中规律这第二层含义已特别突出,竟占“理”范畴全部意蕴的重要位置。朱熹在构筑其理气学说时,往往强调第二义,不顾第一义,进而又言“理泊于气上”、“堕于气中”、“气强理弱”等等,视“理”、“气”为二物,有一种“理”、“气”二元论倾向。因此,就思维走向来说,从以精神性的“理”为本体的“理”、“气”一元论到包含物质性的“气”的“理”、“气”二元论倾向,这一过程本身就预示着程朱理学有向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转化的趋势。
从罗钦顺的理气观可以看出,他是沿着程朱理学这条思路一直走下来,触摸到程朱理学向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的“气”一元论转化的逻辑契机所契之机关,进而在其哲学理气观上推开了通向“气”一元论的大门,并建构了“气”、“理”一元的“气本论”。在这一过程中,罗钦顺并没有走到“气本论”、“气一元论”的领地,他只是本着对程朱理学的尊崇、信奉和捍卫的宗旨,为补其微瑕,至求归一,而穷其极致,潜玩深思,不自觉地多走了一步,从而涉足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的哲学领域。如罗钦顺所说:“吾辈之尊信朱子者,固当审求其是,补其微罅,救其小偏,一其未一,务期于完全纯粹,而毫发无所恨焉,乃为尊信之实,正不必委曲迁就于其间。”(罗钦顺:《答陈侍御国祥》丁酉春)如果罗钦顺是一个自觉的“气本论”、“气一元论”者,那么他是自觉地开端了明代“气学”,本着他对学术的真诚,他会极力倡言“气学”,或以“气学派”自居,并高举以物质之“气”为本体的“气学派”旗帜批陆王心学,斥禅宗佛学,反程朱理学。
然而,历史事实却恰恰相反。罗钦顺从来以程朱理学派自居,高举程朱理学派的旗帜,极力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通观罗钦顺的哲学著作和往来书信,专门言“气”者少,其“气”范畴的规定和描述也是在言“理”或言“理”、“气”关系中带出。《明史·罗钦顺传》中说:“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可见,在“气”、“理”、“心”、“性”四个方面,罗钦顺一生专心致志的是“理”,是“心”,是“性”,而唯独没有致力于“气”,说罗钦顺是自觉的“气学派”哲学家,在事实、在情理都很难说通。或许有人认为,罗钦顺虽然出于程朱门户,尊崇程朱,但对程朱理学多所批评,他更多地接受了张载的思想观点,在他所进行的批判心学的理论斗争中,不仅批判了陆王心学和禅宗佛学,同时也逐步清算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成为对程朱理学反戈一击的一位“气学派”哲学家。这种看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虽然罗钦顺哲学中的一些思想与张载有一致性,但这些思想非张载所独有。就“理”与“气”的关系而言,周、邵、程、朱都有议论。朱熹更有“气强理弱”,“于上面犹隔一膜”之叹,在程朱理学内部也已经有了向以物质之气为本体的“气本论”、“气一元论”转化的逻辑契机。罗钦顺自己也说得十分明白,“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臆决也。”(罗钦顺:《答林次崖佥宪》壬寅冬)罗钦顺对程朱理学是有批评、改造和修正,但批评、改造和修正的目的,正如罗钦顺自己多次说明的,是补缺与捍卫,发扬而光大,而不是所谓的“逐步清算”和“反戈一击”。如果说罗钦顺继承了张载气学,但罗钦顺哲学著作和往来书信中,不仅专言“气”者不多,而且言及张载之处也很少,偶有所言,也多半是“周、邵、程、张”北宋五子一并带出。
如果罗钦顺真是承继张载气学反戈程朱理学的话,那么以罗钦顺的人品风格和治学之真诚,必不至如此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历史事实,从第一手材料下结论,还历史之本来面目,而不应该不顾事实地照搬西方哲学模式去对中国古典哲学进行人为的安排和臆说。罗钦顺不是一个自觉的“气本论”者,因此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气一元论”者。他是半截子“气本论”者,半截子“性本论”者,在宇宙界的理气观方面是属于“气本论”、“气一元论”者,而当他再向前行进一步,走到人生界意识活动的“心”、“性”领域,便不自觉地中止了脚步,继续尊奉和捍卫程朱理学的“性本论”和“心性二元论”,从而导致其哲学逻辑结构中理气观与心性观的内在矛盾。
3.罗钦顺在对程朱理学之理气观作了一些调整的同时全盘继承了程朱理学之心性观
罗钦顺一生孜孜不倦,致力于排斥佛教禅宗和陆王心学之非并捍卫二程朱熹正统儒学之是的卫道事业。凡细观《困知记》及其来往书信者,都不难体会出,罗钦顺立场坚定,对程朱理学与对陆王心学和禅宗佛学之感情色彩迥然有别。罗钦顺攻陆王心学,是口诛之,笔伐之。罗钦顺辟禅宗佛学,在口诛笔伐之余,更有咄咄逼人、杀气腾腾之势。而罗钦顺评程朱理学,即便略有微词,也是委婉流转,惟恐说重了一分,其用词、其语气均是以程朱理学派自居,以承继道统、专心补缺修饰为己任。
明代中叶,很多学者悦新奇,忽平实,反攻程朱,罗钦顺则以其卫道的精神讥评说:“自昔有志于道学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时以道学鸣者,则泰然自处于程朱之上矣。然考其所得,乃程朱早尝学焉,而竟弃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贤所弃以自珍,反从而议其后,不亦误耶?”(《困知记》卷上第十三章,第6页)又说:“夫世之妄议朱《传》者,其始盖出于一二人崇尚陆学之私。为其徒者,往往贪新而厌旧,遂勇于随声逐响,肆为操戈入室之计。姑未论夫至道,就其师说亦何尝有实见也!浮诞之风日长,忠实之意日微,世道所关,有不胜其可慨者矣!”(罗钦顺:《答陈侍御国祥》丁酉春)罗钦顺对当时的学风表达了无限的感慨和深深的忧虑。
罗钦顺一生尊奉程朱理学,是程朱理学真诚的执着的卫道士。但程朱理学是一种以精神性的“理”和“性”分别作为宇宙界和人生界之本体的“理本论”和“性本论”哲学。程朱理学在“理”、“气”问题上把“理”绝对化抽象化为先天地而生的绝对精神并作为宇宙的精神本体,进而建立了“理”本“气”末,“理”先“气”后,“理”体“气”用的理气观,并有“理”、“气”二元论倾向。程朱理学在“心”、“性”问题上,认为“性即理”,把“性”也绝对抽象化为绝对精神并作为寂然不动、精微纯一的精神本体,进而建立起“性”为本“心”为末,“性”为体“心”为用的心性观,并有“心”、“性”二元论倾向。罗钦顺哲学的出发点是程朱理学,他虽对程朱理学作了一些批评、修正和改造的工作,但他修改的底本仍是程朱理学的本子。他修改的目的不是发难、不是挑剔、不是批驳,而是使其更加完善,更加无懈可击,以便竭力捍卫并发扬而光大之。
程朱理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相互照应、圆满统一的哲学体系,罗钦顺只对其理气观作了一些调整而对其心性观却全盘继承,从而导致其哲学逻辑结构中“性本论”与“气本论”的矛盾;“心”、“性”二元论与“理”、“气”一元论的矛盾;“性”为体、“心”为用与“气”为体、“理”为用的矛盾;关于“性”范畴与“理”范畴规定的矛盾,并最终导致其哲学逻辑结构中作为中心论旨的心性观与作为立论基础的理气观的内在矛盾。
标签:哲学论文; 程朱理学论文; 一元论论文; 逻辑结构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罗钦顺论文; 宇宙结构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二元论论文; 本体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