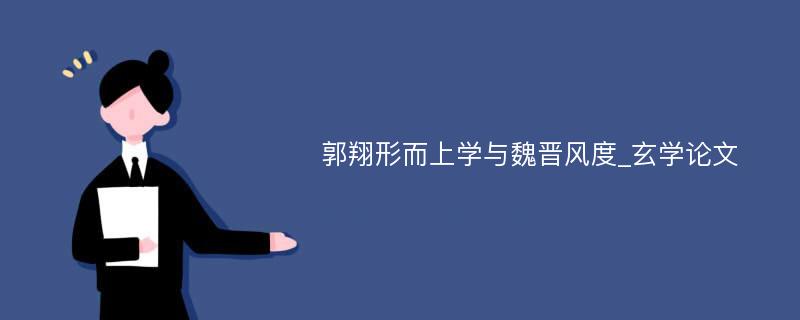
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学论文,魏晋论文,风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6 文献标识码:A
魏晋玄学对魏晋人的自觉和魏晋风度的形成前人早有精辟之论,但魏晋玄学并非一派圆满自洽的哲学,玄学在曹魏至东晋的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先后至少有四个主要派别:其一是正始时期王、何玄学,其二是元康时期的郭、向玄学,其三是东晋支愍度的心无义,其四是僧肇的不真空义。这四派玄学立意迥然有别,王弼贵无,主要以老子为本;郭象崇有,大体以庄子为宗。后面两派则明显具有了禅宗色彩。这四派玄学对魏晋文学和文艺理论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影响最著者宜属郭象玄学。
王弼玄学和郭象玄学都以调和儒道,解决名教和自然的矛盾为目的,但王弼主要以注《老子》立意,着眼处在政治;郭象以注《庄子》立意,着眼处在人生。因此,郭象玄学更有益于人的自觉。
魏晋玄学是依傍老庄哲学而兴起的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的问题,在对老庄哲学进行阐释的同时,玄学家们揉进了儒家思想。《老子》《庄子》《周易》为玄学三本,但无论是从对玄学的理论贡献还是它们在当时实际产生的影响来看,《庄子》无疑是玄学最主要的文本。但意味深长的是玄学的生发并非从注《庄子》开始。汤用彤云:“溯自杨子云以后,汉代学士文人即间尝企慕玄远,凡抗志玄妙者,‘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注: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48页。)汉代的学士文人清谈玄远一般只及《老子》而鲜提《庄子》,如冯衍“抗玄妙之节操”而“大老聃之贵玄”;仲长统“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而刘安的《淮南子》,严君平的《道德指归》,扬雄的《太玄》,王充的《论衡》等,都十分明显地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据杨树达统计,两汉注《老子》者多达五十多家,而注《庄子》者则未之有闻。东汉初,班嗣写信向桓谭借阅《庄子》,可博学强志的桓谭竟连《庄子》都没有见过,庄子之无闻可见一斑。对此汤用彤也曾说:“重玄之门,老子所游,谈玄者必上尊老子。”(注: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48页。)逮自建安、正始,这种情况并无多大的改观。何晏对《老子》的情有独钟颇能说明问题: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注:《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107页。)
何晏虽知自己的注释远不如王弼,但依然不能割舍对《老子》的兴趣。可见《老子》一书在当时魅力之大。而同时的夏候玄著有《本玄论》,钟会著有《老子注》,相比之下,《庄子》明显被冷落了。《世说新语》曾云:“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穷其旨要,向秀于旧注之外为《解义》,妙析奇辞,大畅玄风。”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向秀注《庄子》之前,只有崔撰一家注释过《庄子》,不过也确实由此伊 始,《庄子》犹如一颗土埋尘封的明珠美玉突然间被发掘出来从而光芒四射,吸引了几乎所有文人的心。闻一多说:“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崔撰首先给他作注,接着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都注《庄子》,像魔术式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注:《闻一多全集》第2卷,开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279页。)可以说从竹林七贤开始到东晋,庄子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经过郭象改造了的庄子哲学成了这数百年中文人学士立身行事的哲学根据。在思想上,王弼贵无思想依然为人信奉,但在个人的立身行事上,却几乎全部是庄子那样的逍遥游放,不落俗套,不为物累,不拘礼法,学贵自然,宅心玄远。
魏晋名士这种放达通脱的人生态度与老子彻底“知其雄,守其雌”,“不敢为天下先”,韬光养晦的立身之道,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与庄子逍遥游放不为物役、法天贵真、率性任情的精神却是一脉相通。
玄学在兴起之初以《老子》为中心,十分冷落《庄子》,其中缘由今人张海明已有详论,兹姑不议。但历史在走入魏晋之后,为什么《庄子》会在突然之间成为玄学的中心文本,庄子精神会占据整个时代的心灵却是必须澄清的问题。
玄学中心文本从《老子》到《庄子》的转换,其间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条,其一是由于汉末社会大动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两汉谶纬神学的土崩瓦解,而学术上,繁琐而肤浅的两汉经学被弃之如敝履。从神学目的论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人面对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现实,痛感生命的短促悲苦,人生的坎坷无常,并由此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古诗十九首》正是这种意识的流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钟嵘称这些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几乎一字千金。”无论是叙离别,说相思,怀故乡,悲行役,这些诗都强烈地传达了诗人对人生坎坷、生命无常、欢乐少有,悲伤常多的深切感叹。
雄如魏武,于横槊赋诗之际,也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贵为世子,曹丕也悲吟:“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凡此种种,足可见他们对生命的爱恋和珍重。活生生的生命感受,是人生在世最基本的东西,一切行为取向莫不由这种生命感受最本源的地方出发。而两汉人基本上没有这种生命感受和体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汉魏之际的人开始了个体生命的初步觉醒。当然这种觉醒尚处于萌芽状态。
玄学中心文本由《老子》到《庄子》的转换的第二个原因是老子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而庄子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关于人生的美学。李泽厚说:“与老子大不相同的地方,在于他(庄子)第一次突出了个体存在,他基本上是从人的个体的角度来执行这种批判的。关心的不是伦理、政治问题,而是个体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问题,才是庄子思想的实质”,而“个体存在的形(身)神(心)问题最终归结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构成了庄子哲学的核心”(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183页。)。 庄子对整个人生采取的是一种审美的态度,他要求做到不计利害,不遣是非,不分成毁,纵身大化之中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对死亡,庄子也不采取宗教性的解脱而取审美性的超越,他不把死当作拯救而当作解放,所以庄子哲学不但是人生哲学,也是关于人生的美学。因此,庄子对魏晋人来说无疑更具有人格魅力。
随着两汉谶纬神学的瓦解和统一的汉帝国的崩溃,魏晋人关心的重点问题、首要问题已不在社会而在个人,不在环境而在内心,不在形质而在精神,而庄子哲学恰好能适应这种需要。因此,在历史继续向前发展,个体如何安身立命日益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时,玄学便必然要将中心从《老子》转移到《庄子》上来。云遮雾掩数百年的庄子哲学终于经郭象等人的改造、阐释,照亮了整个时代的心灵。
魏晋名士立身行事的态度与庄子逍遥游的精神一脉相通,这一点已前有所论。但如果我们思考再深入一些,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庄子在行为实践上把社会作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两分。在现实世界里,他悲观绝望,主张安命无为,但在精神世界里他乐观真挚,积极追求,逍遥游放。庄子这种“外化而内不化”的矛盾正是其哲学思想的一大特征。在庄子哲学里,“外化”是“内不化”的前提和条件,“内不化”是外化的目的。随顺万物、自然无为是保证精神超然宁静的最好办法。“内不化”既是庄子的精神自由实现的条件,也是他的精神自由的实质内容。因此庄子的逍遥游是思想在幻想中的遨游飞翔,是精神在想象中与天地万物相交流,内外兼忘,物我为一,与道为一。因而,庄子的逍遥游并不实现在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庄子是一点也不逍遥的,不但不逍遥,他还主张和光同尘:“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而魏晋名士恰好相反,他们不仅要在精神上逍遥放达,而且还要把这种逍遥落实到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上,即所谓“学贵玄远,行尚放达”。换言之,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对立和紧张对魏晋士人并不存在。这种对立和紧张的消弥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语境,然而其在理论上的完成却是通过郭象对《庄子》的创造性误读而实现的。那么郭象是如何实现这种由精神世界到现实生活的落实的呢?
庄子的逍遥游是“游心”。《人间世》说:“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德充符》说:“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应帝王》也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害私焉。”庄子屡屡非常夸张地说要“乘云气”,“骑日月”,“乘天地之正”,“乘莽眇之鸟”,“御飞龙”,“御六气之辩”以游乎“四海之外”、“尘垢之外”、“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最终达到与道为一,与天地万物为一的境界。庄子使用这些恢诡宏丽的词句并非出于修辞的需要,而是确有深意的,表明庄子的逍遥游内含对万物万象的超越之意,这一点可以从庄子一贯强调“物物而不物于物”中清楚地见出。而且,这些奇丽恢宏的用语表示了庄子的逍遥游高深莫测的神秘主义色彩。郭象是如何消解庄子逍遥游的神秘色彩,而将之由精神世界落实到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的呢?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作详细地探讨。
首先,郭象赋予“逍遥”以全新的内涵。《庄子·逍遥游》云:“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郭象注云:
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之二虫又何知”注云:
二虫,谓鹏蜩也。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夫趣之所以异,岂知异而异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为也。此逍遥之大意。
郭象玄学的宗旨是“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由此出发,他对庄子哲学作了全面改造。当然,他对庄子“逍遥”的改造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郭象以“自然”释“逍遥”,赋予其全新的内容。既然“逍遥”就在于“自然”,那么事物无论大小,只要他“足于其性”,“自尽其性”,那么就是“自然”的,因而也就达到了“逍遥”的境界。所以就“足于其性”(自然)这一根本点来说,大鹏与蜩都是逍遥的。显然,这种解释与庄子的逍遥义是完全相反的,不过郭象这一移花接木之举确实做得非常高明。庄子逍遥游的神秘性还在于他实现逍遥游的方式的恢诡宏丽,如“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等等。郭象的第二步行动就是剥离这些逍遥的神秘性。《庄子·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郭象注云:
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然,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
《庄子·应帝王》“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旷垠之野”,郭象注云:
任人之自为。莽眇,群碎之谓耳。乘群碎,驰万物,故能出处常通,而无狭滞之地。
《庄子·齐物论》“乘云气”注云:
寄物而行,非我动也。
“骑日月”注云:
有昼夜而无死生也。
“而游乎四海之外”注云:
夫唯无其知而任天下之自为,故驰万物而不穷也。
“乘天地之正”成了“顺万物之性”;“御六气之辩”成了“游变化之途”;“莽眇”只是“群碎”;“乘云气”不过是“寄物而行”。至此,庄子这种诡谲奇幻的神秘之举丧失了其全部神秘性和浪漫主义色彩。郭象执行这种剥离的手术刀仍然是“自然”、“顺物之性”。郭象的下一个步骤是消解庄子因逍遥游而达到的与天地万物为一这种崇高境界的神秘性。
《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郭象注云:
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则天地之生又何不并,万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庄子·大宗师》“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郭象注云:
安于推移而与化俱去,故乃入于寂寥与天为一也。
须知郭象的“天”乃是“万物之总名”,丝毫不具有神秘性。在郭象看来,“与天为一”、“入于寥天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种境界丝毫也不神秘,不过也就是人“足于天然”,“安其性命”,“安于推移”,顺应自然而已。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庄子称之为“神人”、“圣人”、“真人”。庄子的“神人”、“圣人”、“真人”都具有超凡的品格与才能,但郭象同样消解了他们的神秘色彩。
《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郭象注云: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瘁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
《庄子·逍遥游》“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郭象注云:
俱食五谷而独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谷所为,而特禀自然之妙气。
《庄子·大宗师》“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郭象注云:
言夫知之登至于道者,若此之远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陆行而非避濡也,远火而非逃热也,无过而非措当也。故虽不以热为热而未尝赴火,不以濡为濡而未尝蹈水,不以死为死而未尝丧生。
郭象的解释几乎全部与庄子原意相悖,但他的解释确实高明。不过,经郭象高明的误读之后,庄子原义中的神秘性被全部消解了。
庄子的逍遥是精神世界里的绝对自由,内含着对万物万象的超越,即“物物而不物于物”。而郭象以“自然”释“逍遥”,强调顺应万物之性,这就失去了庄子原义中对万象万有的超越之意,而且,郭象以“自然”释“逍遥”,消解了“逍遥”的神秘性,人只要按本性行事,自足其性,自尽其性,即可达到“逍遥”的境界。“自然”有两个方向的针对性,对外部世界是顺万物之性;对自己,是顺自我之性,为所欲为(无贬义)。对此郭象《人间世》“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注云:
足能行而放之,手能执而任之,听耳之所闻,视目之所见,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为其自为,恣其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此无为之至易也。……率性而动,动不过分,天下之至易者也,举其自举,载其自载,天下之至轻者也。
顺万物之性,与物无忤,就无需超越万物;顺自我之性,率性而为,就无需超越现实世界到“四海之外”、“尘垢之外”、“无何有之乡”,而这是“天下之至易”之举。这样,郭象就把庄子的逍遥游从精神世界落实到了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之中了。
这种落实的结果便是使魏晋名士在日常生活中高标逍遥,法天贵真,率性任情,不拘俗礼,充分回归自我,体认自我,高标主体人格,张扬个体精神,说真心话,做真心事,吐真感情,写真文章。此即所谓魏晋风度。当然,魏晋风度的形成首先是因为特定的历史语境,郭象对庄子“逍遥游”的阐释主要是从哲学上为消弥庄子原旨与魏晋现实之间的不和谐与冲突。然而另一方面,郭象这种创造性的误读又反过来为魏晋风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哲学支持。
收稿日期:1999—05—06
标签:玄学论文; 逍遥游论文; 郭象论文; 魏晋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魏晋风度论文; 文化论文; 庄子论文; 老子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