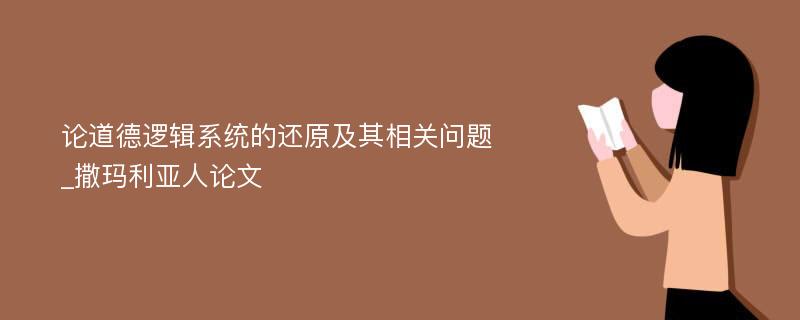
论道义逻辑系统的归约及其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及其相关论文,逻辑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1)02—0022—(05)
道义逻辑是本世纪50年代兴起的一个新兴逻辑分支,属广义模态逻辑的一种。它是研究含有“必须”、“允许”、“禁止”等道义词的道义命题的逻辑特征及其推理关系的学科,与法学、伦理学等学科关系密切,又称规范逻辑、义务逻辑。1957年,芬兰逻辑学家冯·莱特(Von.Wright )在其经典性文章《道义逻辑》中提出了第一个可行的道义逻辑系统,成为道义逻辑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冯·莱特本人也因而成为现代道义逻辑的开创者。在冯·莱特的工作的影响下,普赖尔(A.N.Prior)安德森(A.R.Anderson)、欣迪卡(J.Hintikka)、齐硕姆(R.Chisolm)、伊文(A.A.ИВИН)等人也相继对道义逻辑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构造出多种道义逻辑系统,或者是对道义逻辑提出了具有深刻见解的批评与驳斥,促进了道义逻辑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随后出现的道义逻辑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绝对道义逻辑系统与相对道义逻辑系统,前者又可分为朴素绝对道义逻辑系统和真值道义逻辑系统两种。所谓朴素绝对道义逻辑系统,就是由重新解释真值模态逻辑中的某些算子,从中去掉那些在道义逻辑中不成立的公理或规则,并适当增加新的公理或规则而得到的逻辑系统。所谓真值绝对道义逻辑系统,是指在真值模态逻辑中添加一个安德森常项S(意为“惩罚”、 “制裁”),并通过定义引入道义模态词O、P、F, 从而得到的道义逻辑系统。通常说的标准系统OT,OS4,OS5,OT[*],OS4[*]及OS5[*]等都是朴素绝对道义逻辑系统;真值绝对道义逻辑系统如OT’、OS4’、OS5’等。
安德森在《标准系统归约的形式分析》和《从道义逻辑到真理论模态逻辑的一种归约》中提出依靠归约模式Op←→□(~p→S)能把道义逻辑归约为真理论模态逻辑(真理论模态逻辑即真值模态逻辑)[1] (P254)。安德森认为,在实际的规范系统中惩罚(Penalty )或制裁(Sanction)起了重要作用。据此他在三个真值模态命题逻辑系统T、 S4、S5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表达由于不履行义务而导致的“制裁”或“坏事”概念的命题常项S。上式的涵义就是一事件p是必须的,当且仅当不履行p而遭受惩罚是必然的。另外再添加一条新公理~□S,其涵义是制裁不是必然的,或者也可说成并非每件事都是禁止的。依据这些安德森构建了OT’、OS4’、OS5’三个模态逻辑系统,且他们都把道义逻辑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另外,根据“必须”与“允许”、“禁止”之间的关系,又有Pp←→◇(p∧~S),Fp←→□(p→S)。前者的涵义是p是允许的,而且仅当做p而不致受惩罚是可能的;后者的涵义是p是禁止的,当且仅当做p会导致惩罚是必然的。
我认为,安德森的这种做法是值得怀疑的。他这样做基于对必然与必须,可能与允许这些概念的混淆与误解。必然它体现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具有客观性,排斥人的意志、情感等主观的心理因素在外。虽然有绝对必然与相对必然等说法,但是可以说,在一定条件的适应范围内p是必然的,毫无疑问p必定为真,否则就不成其为必然了。而必须是表示事理上或情理上对某事、某物的必要,与人的社会性、主观性相关联。虽然我们也可以说相对某些条件、某一规则必须p,但是p是否为真有时(往往)与这些条件、规则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可能与允许之间的区别也是如此。可能p是p变为现实在客观上有一定的因素、条件,p的实现有潜在的趋势。而允许p意指是否履行p 有着主观上的自由。两者的联系仅在于,在理想世界中,一事件p是允许的, 则其实现有其可能,而一事件p是不允许的,则p就不可能会实现。在现实世界中,通常只有在p的实现有可能的前提下我们才讲允许p。明知 p为不可能而说允许p有失恰当性。在这两对概念间只有某种表面上的、 外在的形似,没有内在的、实质性的神似,也就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一个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另一个是社会伦理规范中的用语,用前者去定义后者显然太牵强了。
我认为,必然与必须之间惟一的联系在于有一类必须之规则是依据客观事物本身的必然规律制定的,以顺应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寻求人类社会与客观自然界的和谐,促进人类的发展。遵守此类规则其实也就是要正面地、积极地与客观世界相共处,避免人与自然发生剧烈冲突。如“保护森林资源,严禁滥砍滥伐”就是依据地球生态平衡的需要制定的,但也有人藐视法律大肆滥伐,破坏森林资源。很难说滥伐者就必然会受到惩罚,但是却可以肯定,当地居民将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因为对于规律,我们只能积极地利用,正面去遵循它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利益;相反若是无视规律,得到的将是规律从反面给我们的报复、灾害。我们是不可能逃脱规律对我们的约束的。只有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一件事是必须的、应当的,当且仅当不履行该义务必然会导致惩罚、制裁。这也即为合理的应当之则要有必然之理为其根据。
另一类必须之规则并不是依据客观规律制定的,而是依据人的社会性,为维护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社会关系,为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而制定的。例如,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就是如此。如果不遵守这类规则就“必然”受到惩罚,这里的“必然”的依据是什么呢?无非也是人们为保证这类规则的顺利实施,迫使大家都遵守而制定的必须对违规者进行制裁及如何制裁之类的规则。我把前者称为“协调规则”,把后者称为“惩罚规则”。它们都不是依据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而是依据人的社会性,为维护一定的社会生活秩序而制定。就这点而言,它们属于同一类型,有一共同特点,那就是,不像第一类必须之规则那样以客观事物本身的必然规律为依据,协调规则和惩罚规则背后都没有受到某种客观规律的支持,违反它们并不意味着没有正面地去遵守客观规律,因而也就不会有某种规律将必然地去从反面惩罚违规者或他人。而且,安德森的系统无疑是要刻画现实世界,因为刻画的若是一个理想世界就无需惩罚。由上述,我可以问,既然协调规则能够被违反,那又有什么理由说惩罚规则就必然会被遵守,不会遭到违反呢?很显然,安德森没有明白,惩罚规则也是可以违反的,不具有必然性,对于惩罚规则我们也只是能说“必须遵守”,即对违规者必须制裁。据此分析,安德森的归约模式是不能成立的,只能写成Op←→O(~p→ S),而这样的一个形式只是对“必须p”说明而已。
现实社会中违反惩罚规则之事也是有的,因为逍遥法外总有其人。另一方面,若惩罚规则真是具有必然性,那么现实世界距理想世界也不会太远了,因为现实世界中一般不会有人明知必然会受惩罚而去违规的,人们违规犯法多半是受到逍遥法外有其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这一思想而去冒险以身试法的。而且对某人违规犯法我们一般都是说,“他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说“他必然受到应有的惩罚”。后者一般被认为属于用词不当。
若对安德森的做法仅仅做如上分析,则还未完全堵住某些人企图为其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通道。这种辩护可摘录如下:
“但也不妨假定S 只是包括在一给定的规范法典内的义务没有履行,也就是指道义上完善的境界没有实现……。S 的这种解释似乎最接近康格尔把Q(Q既~S,引者注)当作“道德吩咐的事”的解释,如果Q(“道德吩咐的事”)和S(违禁境界的实现)借助于某一特定规范系统T来定义,而Of是指f按T是务须的,那么(G1)(G1即Op←→□(~p→S),引者注)和H1(H1即Op←→□(Q→S), 引者注)的这些解释就不成问题。在这种情况,(G1)和(H1)中所含的必然性概念尽可作为分析的或逻辑的必然性来看待。”[1](P256)
乍一看,这种辩护确实为安德森的做法找到了绝妙的解说。它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前文对之驳斥的基石:把S解释为制裁或惩罚, 似乎使得刚才试图通过对必然与必须的分析以驳斥公式Op←→□(~p→S)的不合理性的努力变为徒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将让我们看清即使对S采用后一种解释,安德森的做法仍是行不通的。
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这一问题是普赖尔于1958年提出的。后来达尼尔森(Danielsson)、伍德伯格( Wedberg)、冯·弗拉森( Van.Fraanssen)、卡斯塔尼达(H.Castaneda)等都对该问题讨论过。普赖尔原来表述该悖论的公式是Fp∧□(q→p)→Fq。该公式是OT’,OS4’及OS5’中的定理,如果遵守从安德森把“π”读作衍推的话,上述公式就是说,能衍推禁止行为的行为本身也是禁止的。举例来说,抢劫毫无疑问是禁止的,而帮助一名被抢劫者无疑衍推抢劫发生了,这样根据上述公式,帮助被抢劫者的行为也是被禁止的。这当然是荒谬的。英文the good Samaritan指“见义勇为者”、“乐善好施、慈悲怜悯之人”,因此, 公式Fp ∧□(q →p )→Fq 所含的悖论被称为 the good Samaritan paradox,即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国内也有人意译为“乐善好施者悖论”。
为了弄清产生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的根源,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真值绝对道义逻辑语义学是如何解释该公式的。首先根据安德森的定义把该公式还原为真值模态公式□(p→S)∧□(q→p)→□(q→s)。在此处就把S解释为使得Op←→□(~p→S)“不成问题”的那种含义,即违禁境界的实现。按其语义学,□(p→S)是说p, 即抢劫的发生,衍推违禁境界的实现。□(q→p)是说,q衍推p,即帮助一名被抢劫者衍推抢劫发生。□(p→S)∧□(q→p)→□(q→S)的含义就是,如果□(p→S)和□(q→p)均成立,那么就有□(q→S),即帮助一名被抢劫者衍推违禁境界的实现,也成立。上述这种语义学对替换后的公式的解释跟我们的直觉显然是相符合的。人们完全能够接受。那么问题肯定就是出在公式的替换环节上,更明确地说,悖论的产生是由于把Fp定义为□(p→S)。因为事件p的发生可以衍推违禁境界的实现, 但该事件p不一定就是被禁止的。例如上例中, 显然地帮助一名被抢劫者衍推违禁境界的实现,但是帮助一名被抢劫者却并不是被禁止的。而且,由于Fp和Op可互相定义,所以这种悖论同样会在Op←→□(~p→S)中体现出来。就以刚才的例子来说,帮助一名被抢劫者衍推违禁境界的实现,但是,不帮助一名被抢劫者是应当的,这根据我们的常识无疑是不能成立的。所以Op不能由□(~p→ S)来定义,即使把S解释为违禁境界的实现。顺便指出,即使在此又把 S解释为惩罚或制裁,撒玛利亚人悖论也仍是源于安德森的定义Fp←→□(p→S),其分析类似上述把S理解为违禁境界的实现的分析。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起源于安德森定义Op为□(~p→S)而欲把道义逻辑归约为真值模态逻辑。因此,可以说,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彻底破灭了为安德森的定义Op←→□(~p→S)的可行性进行辩护的希望。
当然,OT’、OS4’、OS5’中含有的悖理性的定理远不止Fp∧□(q→p)→Fq一个,其他的如□p→Op、~◇(p→Fp、Op→◇p等。 第一个公式的涵义是,某事是必然的,那它也是应当的。这里就明显有问题。因为大千世界中客观事物总有其自身客观必然规律,而这却是无所谓应当不应当的。以唐山大地震为例,据当时唐山地区的地质构造等多种地质因素,可以说唐山大地震的发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是若说成唐山大地震应当或必须发生就显然太不合情理,因为这明显含有说话者的主观情感在里,似乎隐含着唐山居民该受此劫难这一层意思。后两个也有类似的问题[2]。 但是我认为这些定理之所以不能接受并不是导源于必然化规则,而是源于安德森混淆了“必然”与“必须”这样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而把道义逻辑归约为真值模态逻辑。我认为虽然道义逻辑可以从真值模态逻辑中借鉴许多经验,但却不能归约为真值模态逻辑,因为道义逻辑涉及的是法律、伦理道德规范中如“允许”、“应当”等社会规范性概念,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色彩,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而真值模态逻辑涉及的是哲学领域里的“必然”、“可能”等形而上学概念,距现实生活相对较远。我认为不可能把一个命题逻辑系统归约为一个研究对象、涉及领域都与其不同的另一个命题逻辑系统。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引申出相关的两个问题。首先,通过上面对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的分析,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在OT’之类的系统(当然也就在所有标准系统)中都不能将“帮助一名被抢劫者是应当的并且禁止抢劫”这个据我们常识是正确的命题形式化为系统的定理。据其语义学,帮助一名抢劫者是应当的意味着在一个理想世界中人们都做到了帮助一名抢劫者;禁止抢劫意味着在这样的理想世界中抢劫是没发生的。但是由刚才的帮助了一名被抢劫者成立是一定能推出在这样的理想世界中抢劫已发生了的。矛盾由此产生。
这种矛盾的产生实质上同齐硕姆二难相似,也是源于这些系统形式语言贫乏,未对渎职命令与非渎职命令进行区分,相应地语义上对理想世界未区分层次。齐硕姆二难的例子大致是这样的。某人去帮助他邻居,这是应当的;而且如果他去帮助,那么他告诉他邻居他要来,这也是应当的;如果他不去,那么他就应当不告诉他要来。这些据我们的道德标准都是正确的。我们用p表示“某人去帮助他邻居”,用q表示“他告诉他邻居他要来帮忙”。所以有:1.Op;2.O(p→q);3.~ p→O~q。现假定那个人没有去帮助他邻居,即4.~p。这样据1、2 和标准系统的公理O(p→q)→(Op→Oq)可得5.Oq;据3和4可得6.O~q。 于是也就有7.Oq∧O~q。但是在标准系统OK[*],OT[*],OS4[*]和OS5[*]中我们可做如下推导:├~(q∧~q)=>├O~(q∧~q)=>├P~(q∧~q)=>├~O(q∧~q)=>8.├~(Oq∧O~q)。 这样我们得到了一对矛盾的公式7和8。与齐硕姆的例子不同的是,这个例子中的渎职者不一定就是渎职命令的执行者,比如X抢劫了Y,帮助Y者未必就是X,而多半是第三者Z。 我认为一个形式系统只有能刻画下述情境才能够将上述命题形式化而又不至于与人们的常识相悖:在最理想的世界中没有抢劫发生;但如果抢劫事件发生了,较好的理想世界是人们都做到了帮助被抢劫者;而最差的世界是发生了抢劫而又无人去帮助被抢劫者。
需要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的表述形式问题。“有人使用这样的例子:X抢劫Y后帮助Y,禁止抢劫, 因此禁止给予帮助,但是这个论断的精确形式表明,它不是悖论。”[3](P398)我赞同这种观点。用p表示“X抢劫Y”,用q表示“X帮助Y”,该例子中前提就是p∧q∧Fp,在OS5’之类的系统中由此是推不出Fq的, 也即p∧q∧Fp→Fq并不是这些系统的定理。当然更精确些可以用道义谓词逻辑,甚至基于时态逻辑的道义谓词逻辑表述该例,但这样就更不会出现悖论。
“伊文认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应该理解做Fp→F(p∧q)(5.5)。它是Fp∧□(q→p)→Fq的逻辑后承。‘如果禁止说粗鲁话, 那就禁止说粗鲁话和道歉’是公式(5.5)的代人示例。”[3](P398)
然而我认为伊文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Fp→F(p∧q)不是悖论, 起码实质上不是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伊文认为Fp→F(p∧q )含有悖论,我认为这是因为他误以为F(p∧q)→Fp∧Fq在OS5’之类的系统中成立。例如刚才的例子中,从“禁止说粗鲁话和道歉”能推出“禁止说粗鲁话并且禁止道歉”进而也就推出“禁止道歉”了。可是由F(p∧q)能推出Fp∧Fq这仅仅是人们直觉上的思维,F(p∧q)→Fp∧Fq并不是 OS5’之类的系统的定理。在这里又是人们直觉上的思维在误导人们。这完全类似于罗斯悖论。
我认为卡斯塔尼达对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理解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他认为该悖论是这样产生的:
“假定下述原则有效,
(P’)如果X履行A遗传Y履行B,那么X必须做A遗传Y必须做B。
而(P’)直接导致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例如,假定, 阿瑟今天法律地(道德地)必须包扎他的雇主琼斯,而一个星期后阿瑟将杀死琼斯。于是有
(1)阿瑟法律地(道德地)必须履行行动C,即包扎一个星期后他将杀死的人。
显然
(2)阿瑟做C遗传他做一个星期后的杀人的行动。因此根据(P ’)从(1)和(2)得出
(3)阿瑟法律地(道德地)必须在一个星期后的杀人行动。”[3](P400)
首先,据上文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并非由(P’)所导致,而是由安德森的定义Op←→□(~p→S)把道义逻辑归约为真值模态逻辑所致。
其次,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属于这样一类悖论,在某一形式系统中公式A为定理,但A的一个代入实例却不能为人们所接受。我们现在就来分析(P’)是否为OS5’之类系统的定理。由于未能找到卡斯塔尼达对(P’)中“遗传”一词的逻辑涵义的明确解释, 所以在此只能借助其所举之例来确定“遗传”的逻辑涵义。
在OS5’之类的系统中, 能替换“遗传”把卡氏所举例子中的阿瑟包扎其雇主与其后来杀其雇主两者联结起来的联接词可能的只有“π”。因为除了“π”替换“遗传”能使(P’)((Op∧pπq)→Oq, 即Op∧□(p→q)→Oq)成为OS5’之类的系统的定理外, 其余的联结词均不能做到这一点。可是,阿瑟的包扎其雇主行为会在逻辑必然的意义上蕴涵(导致、推出)其一周后杀其雇主的行为吗?按正常人的思维绝不会的!所以,“遗传”也不能被“π”所替换。因此,(P ’)并不是OS5’之类系统的定理, 当然也就谈不上能够表述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他所举之例只不过是一个貌似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的难题而已。类似卡氏错用一个并非表达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悖论的例子来讨论该悖论的情况在《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Logic》中也有[4]。
安德森通过定义Op←→□(~p→S)而欲把道义逻辑归约为真值模态逻辑的做法是失败的,无论是把S解释或制裁,还是把S解释为违禁境界的实现。对于前种理解,通过对必然与必须的关系分析足以令人信服OP只能以O(~p→S)来说明,而不能定义为□(~p→S)。 而通过对撒玛利亚人悖论的分析我们发现,该悖论是源于安德森的定义Fp←→□(p→S),在此就是把S理解为后一种涵义,当然在此即使对S作前种理解该悖论也仍是源于安德森的这个定义。
收稿日期:1999—0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