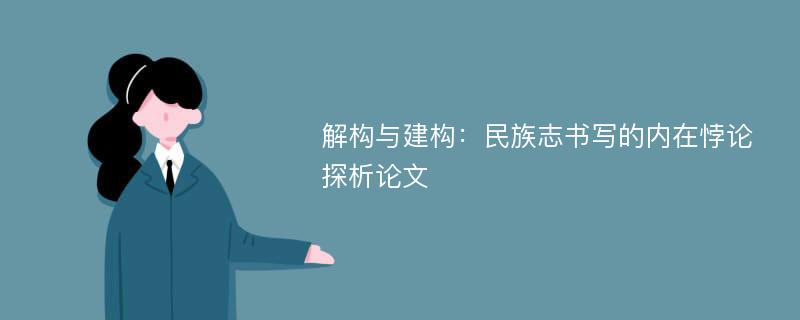
解构与建构: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探析
李银兵,曹以达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 ]民族志书写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受到持续不断地批判与反思,是与其内部存在的诸多悖论有关。“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权宜”书写与“权威”书写、“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以及书写“神秘”与“神秘”书写等诸多矛盾,就是民族志书写场中矛盾复杂性的最好表征。因此,只有不断地对这些矛盾进行解构,探究出产生这些矛盾的逻辑和实践机理,才能为当代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论证。
[关键词 ]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逻辑机理;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
当前,“人类学者、批评家、女权主义者以及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关注真理及其社会定位的问题,关注想象力与表征的形式的问题,关注统治与反抗的问题,关注道德主体和成为道德主体的技巧的问题”[1]309。因而,当代人类学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中心问题,就是关于如何对这个急速变迁的社会现实的表述和描述,这就直接导致在人类学学科内部,田野调查工作和民族志写作已然成为了学界理论探讨与实践创新中最活跃和敏感的竞技舞台[2]8。在西方,有的学者从现实入手去建构新的民族志书写范式;有的学者落脚于解释人类学,关注文化背后的解释性象征符号分析;有的学者关注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理论和实践。总之,“它们都被民族志的实践所鼓舞,并且反过来激励着民族志实践,民族志实践是它们在分化时期的共同的标准”[2]35。在中国,诸多学者从理论、实践层面对民族志书写进行了多维视角地探讨,在民族志书写范式、方法、路径、方向及目标研究中,提出了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想法和思路,推动了中国民族志理论与实践研究向前发展。毫无疑问,中外学者们在民族志书写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民族志研究,大都关注民族志书写危机表象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民族志书写实践,而很少从元反思视角去探讨民族志书写内部存在的悖论及其背后潜藏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因而很难从根本上去理解和解决民族志书写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争论。基于此,本文在对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各种矛盾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析民族志书写内部矛盾产生的逻辑和实践机理,力图达到认识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目的,最终为现代民族志书写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论证。
一、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表征
悖论是指同一命题或推理在表面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并且这两个结论都还能自圆其说,进而导致形式逻辑思维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出现。学术上比较有名的悖论有康德的“二律背反”、罗素悖论等。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知性认识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为混淆主观和客观、事实和价值等关系,最终导致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总之,悖论就是指人们认识论上出现的看似自相矛盾的认识,但这些矛盾又能得以自圆其说,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因而只要把人们的认识进行分类,理清思维内容和表达形式的区别和联系,悖论就能得以解悖。具体对民族志书写来说,其内部存在的悖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并立。“零度”书写是由法国著名思想家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和思想,其基本意思就是要求写作者在写作中以一种零度感情投入,但这不是说写作不带有感情,只是要求这种感情在理性指导之下要降到最低。巴尔特认为任何作家的写作都脱离不了“零度”写作与“非零度”书写,写作是两者的有机统一。因此,写作是作家和社会关系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书写的“阿基米德基点”,正如他所说:“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存库中去进行寻选择的自由。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3]这就是说,从表面上去看,写作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其背后则体现着时代和阶级对写作的要求和控制。在业余民族志和科学民族志书写中,写作的“科学性”直接规约了历史制约性在民族志作品中的体现。比如,马林诺斯基说道:“民族学研究经常被人误解为无聊者的嗜古癖,或有闲阶级在‘野蛮人的风俗和粗糙迷信’的原始古怪的形式中的游荡。其实,它可以成为一门高度哲学化、具有启蒙性、使人高尚的学科。”[4]因此,他极力主张只有靠客观化、条理化、系统化的调查,才能保存和保护那些即将消亡的文化。但随着《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出版,马林诺斯基主张的写作伦理却被其日记中体现出来的狭隘自私、目中无人等替代。在其日记中,马林诺斯基身上具有的人格分裂特征暴露无遗。比如,“消灭这些畜生”“我处理得不太准确,表现得也很愚蠢”“黑鬼”等之类的语言在其日记中都有出现。总之,这都说明了民族志写作会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后来,萨义德的《东方学》对西方写作的揭露和批评,使得先前民族志作者声称的“零度”书写也被击得粉碎。比如,萨义德在分析西方学者福楼拜作品时,这样写道:“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但却不严重)行为的怪异性具有取之不尽的来源;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是与其保持着距离,总是等着看《埃及志》所称的‘怪异的快乐’(bizarre jouissance)的新的例证。”[5]135此外,在实验民族志阶段,我们看到了民族志作者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但作品中的“零度”书写和“非零度”书写并存的现象依然存在,并在无形中影响着民族志书写。总之,书写的初衷是想达到客观、中立的书写,但在书写的实际中,却内涵着很多主体的色彩。比如:书写作者的故乡与他乡界分、作者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主体的生活方式差异、书写目标中的价值性诉求,都无不存在着这对悖论。因此,书写本身就应该是“零度”书写和“非零度书写”矛盾下的产物,这是我们在否定中又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
其次,“权宜”书写和“权威”书写并存。民族志书写就是对异文化的翻译和解释,而这种翻译和解释都“只是与各种语言的陌生性(foreignness)达成妥协的一种近乎权宜之计”[6]。我们暂不去说科学民族志通过民族志书写去彰显大理论的书写方式、西方社会相较于东方社会而言所展现出来的西方优越性的书写诉求,仅就解释人类学大师格尔茨所认为的,对文化解释工作来说,其是一个永不见底的“乌龟驮乌龟”的故事去分析。在其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他在想方设法地去说明或证实其书写对于文化理解的绝对真实性和客观性。而且,他还不断倡导应该从方法论上的多重主体性视角去保证民族志书写的可信性。但结果却是,在其作品中,一直都是他这个“主体”在发声,真正的主体却被淹没和替代了。比如,在警察“突袭”他们夫妇俩所调查的田野地之际,格尔茨夫妇仅仅是通过一次“入乡随俗”的逃跑作为,就完美地完成了从西方人向巴厘人的身份过渡。至此以后,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用巴厘人的口吻对当地斗鸡游戏进行主位性描述了。金钱、权力、性别关系,在他笔下通过斗鸡游戏而被演绎得绘声绘色。描述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就是,巴厘斗鸡变成了一个观察和理解巴厘社会组织的巨大隐喻。正如有的学者评价道:“尽管格尔茨用现象学——解释学作为伪装,但其实在‘深度游戏’中并不存在从当地人视界(native’s point of view)出发的对当地人的理解。有的只是对建构出来的(constructed)当地人的建构出来的视角的建构出来的理解。”[1]107的确,不管民族志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所为,在人类学内部,往往都存在用权宜书写去证明权威书写的悖论情形。比如,米德在《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中说道:“我们终于认识到,人类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在目前,正用许多途径解决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有了这种认识,却不能改变仅仅对一种生活准则加以接受的信仰,那将是不可思议的。”[7]但米德的研究却被很多的人类学家认为是对其老师博厄斯提出的文化决定论做论证,因而遭到譬如弗里曼等人的质疑。总之,大多数民族志作品都存在权宜性书写和权威性书写并存的现象,并且一般都是用权宜性书写去证明权威性书写的存在,这是书写理想与现实在民族志中的反映,间接地表征了人类学这个经验性学科的“归纳主义”属性。
在一年级开展亲子阅读的同时,学校也开展了跨年级阅读活动,五年级学生与二年级学生进行“同伴阅读”,每两周进行一次,每次一节课的时间。
再次,“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原则交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管是对异民族进行描述和研究的传统民族志,或是现代民族志对本民族的分析与研究,它们内部都存在着一对永远也解不开的矛盾:如果被调查者与调查者不同,那么调查者研究被调查者对理解他们有什么意义?如果被调查者与调查者相同,那么调查者倒不如研究他们自己好了。就是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同”与“不同”的矛盾交织中,民族志书写“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原则在人类学不同发展历史中都得到了体现。在书写中,如何真正做到“变生为熟”和“变熟为生”的自由转换,则又成为了民族志书写场中的矛盾之一。在“变生为熟”的原则中,民族志作者要使陌生的事物具有意义,就必须要把陌生变为熟悉,但在熟悉中又要保留事物的陌生性,不然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就得不到彰显。因此,人类学研究的主位和客位相结合的调查和书写方法随之产生,但要真正做到主位和客位的自由转换,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比如,格尔茨用“解释解释者的解释”“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等写作视角去“译释”事物,但在具体的理解中,他如何来划分主位和客位的界限和标准、怎么能达到解释的客观公正性等问题,最终结果则会使其所谓的“对理解的理解”变得越来越空洞和模糊。而在“变熟为生”的原则下,西方学者普遍采取“认识论的批评法”和“泛文化的并置法”两种方法和策略去达到“变熟为生”的目的。但在弱式文化批评法中,很多的人类学者对方法论的处理都具有一种天真的特色。比如,在马克斯·格拉斯曼和艾理·笛凡合著的《封闭体系与开放思想》一书中,作者遇到了将民族志研究对象限定在早已被研究过的社会中所引起的解读问题,因而作者主张人类学者以天真无知的态度进入田野,这样才能保证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殊不知,这种“故作天真”的结果仅仅只能是达到我们对异文化的直接摹写,而没有达到写作人通过对自我进行比较、反省而达到变熟为生的效果,因而其民族志书写的结果必然是肤浅和简单的。在强势文化批评中,民族志作者又面临着比较和批评的对象之间关系的平衡性问题,因而大多数人类学者只有采取夸大其词或者是神话式的方法去书写民族志。比如,“为了建构一种文化批评并置法,米德把萨摩亚文化描述成与美国生活惯例形成极大反差的东西,这便有意无意地把民族志描写抽离于萨摩亚人的生活情境之外了”[2]219。因此,在“变生为熟”和“变熟为生”的原则中,不仅两个原则间的转换存在矛盾,就是其中一个原则内部也存在着矛盾。
首先,内在悖论下当代民族志书写理念的建构。从宏观视角去看,民族志书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种对人类社会的不断增大的复杂化和更多的认识之中;从微观视角去看,民族志书写的发展又是建立在民族志作者对自我和他者的充分把握之中。因而,对于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内在的主客观原因,人类学界应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比如,对于促进人类学发展的宏观因素,人类学界只有做到接受、认识和把握,而不能想办法去阻碍,因为那些因素对于民族志书写来说都是积极的;而对于微观层面上的民族志作者认识上的主观不足等因素,人类学界则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理念的视角为矛盾的解决和民族志书写提供思想基础。具体而言,人类学界应该怀着真实、真诚和真心的信念去书写民族志。“真实”的意蕴在于人类学者对自我和文化有个客观性把握,而要达到这种科学性,就要求民族志作者不断地对自我进行批评和反思,因为“现代性的特征正是在于:人作为主体既是他所建构和控制的世界的基础,又是这些世界的中心”[19],进而在实践中把握事物的更多具象,才能为事物的进一步抽象奠定坚实基础。“真诚”的意思是说人类学者要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用真诚的态度去对待矛盾。只有人类学者真诚地做到了对矛盾的认识,才有足够的勇气去说出“民族志的真理因此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有承诺的,不完全的”[1]35之类的话语来,这对于民族志的发展大有裨益。“真心”的内涵主要是指人类学者在对以往的书写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其书写真正做到为“文化多样、人性普同”的人类学发展服务。虽然“西方人类学家一度深陷于难以自拔的‘知识政治学忏悔’之中,以为西方霸权的‘忏悔’能自动地促成‘文化良知’”[20],这些做法虽有些偏激,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有一些欧洲批评家攻击人类学家竟敢用研究野蛮人的术语和方法来研究欧洲人自己,从而在自身的文化和社会情景中对文化等级现象加以考察并予以揭露,但随着近来对‘西方社会’的日益关注,人类学起源时颇为难堪的种族主义沉渣污垢被洗刷了不少”[18]5。因此,只有做到从真实、真诚和真心“三真”理念入手去正视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才会为民族志书写的创新建构提供基础和条件,也才会为民族志书写悖论的解决提供思想基础。
此外,在“变生为熟”和“变熟为生”的转换中,书写“神秘”慢慢也演化成了“神秘”书写。当然,前一个“神秘”指传统民族志对于异民族独特文化的追寻,后一个“神秘”则是指现代民族志中多种书写修辞方法的广泛使用。虽然两个“神秘”书写的初衷都是为了达到书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但是书写“神秘”和“神秘”书写却增加了达到这些书写目的的困难性,特别是后现代的“神秘”书写,更为民族志书写增生了诸如现实与幻想、形式和内容、神秘和日常等诸多矛盾,这是民族志书写历史与现实碰撞的结果,也是民族志书写内部自我发展的产物。
其次,民族志作者认识活动的有限性所致。民族志书写是建立在民族志作者对异文化的认识基础下的实践行为,认识活动是民族志书写的前提和基础。但“人不能完全地把握=反映=描绘整个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总体’,人只能通过创立抽象、概念、归路、科学的世界图景等永远接近于这一点”[16]。这就说明了人的认识活动具有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有限性,而这种有限性产生的根源在于实践活动的不确定性的一面。这也就是说,实践是认识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本身也存在受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制约的事实,这会导致人的认识活动的相对性、有限性和不确定性的产生。民族志书写中悖论的存在,就是这种人的认识论上的有限性所致。同时,认识不仅仅是简单的摹写,最为根本的是创造,创造性比摹写性更为重要,主体因素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就民族志书写来说,对于异文化的认识和描述,其书写受到了外在的客观条件和内在的主观因素的共同制约。当然,这些条件对于民族志作者的影响或是通过潜在的,或是通过显在的方式展现出来。比如,我们很难从实质上去认清马林诺斯基对人类学及其民族志的本质和特征是真了解还是假了解、其对西方中心论究竟是持反对态度还是支持态度、其对异文化究竟是持欣赏还是厌恶立场,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否认,那就是在民族志发展的三个阶段,民族志作者通过语言有意或者无意地对文化主体传达了不同的文化权力,即语言霸权、语言集权和语言平权思想[17]。总之,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内在悖论,是民族志作者认识活动的有限性和无限性、有意为之和无意使然等诸多矛盾碰撞的结果。因此,民族志作者在认识活动上的有限性是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产生的主体性条件。
二、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产生的缘由
首先,人类学中的文化逻辑相对性使然。人类学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学科,“人”这个主体本身就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主体的多元复杂性决定了这门学科研究的复杂性。民族志书写主要针对的是人的文化,而文化概念的广博和精深也会使民族志书写陷入困境。从文化的逻辑根源上去看,文化本身就具有一种相对主义色彩,也就是说文化逻辑具有相对性或者说逻辑文化具有相对性,就与民族志写作有关的思维文化来说,很多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志作品都表现出了这种文化相对性。比如,列维—布留尔(Levy-Bruhl)认为:“我们(现代文化群体)所接受的逻辑规律并非具有普遍性,某些边远地区土著居民具有与我们不同的逻辑。”[12]后来,在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中,这种认识得到了进一步阐明。他认为未开化人具有的具体性思维与开化人具有的抽象性思维是分属不同类别的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植物有“野生”和“园植”两大类一样,思维方式也可分为“野性的”和“文明的”两大类[13]。当然,对这种认识最好的论证就是普理查德对于阿赞得人的巫术的分析,鞠实儿教授从社会因素、文化元素、目的与语境因素及规则制约因素入手去解析阿赞得人对于巫术形成原因的理解,最后得出“阿赞得人的广义论证在其中毫无问题的社会文化背景,既塑造了阿赞得人逻辑的独特形式,也为它们的合理性提供了基础”[14]的结论。这就是说,逻辑相对于文化,文化不同,人的思维逻辑也就不同。因此,当代人类学家萨林斯用“文化图式”一词去说明一个特定文化体系中人们心中存在的宇宙观和文化逻辑(或是文化秩序)等,他不同意进化论、功能论、结构功能论等从功利的角度去看待文化及“文化图式”,他认为人对生活的看法并不是受特定的物质条件决定的,相反,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即人类学者眼中的“文化”)决定着人们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方式[15]。总之,人本身的复杂性、文化逻辑相对性的现实是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存在的客观基础和前提。
任何矛盾的产生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有着极其广泛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等基础,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的产生也不例外。正如有学者所说:“与一开始借助于日渐精确或可检验的知识(也极有可能是提问的那些)被用来简单地去填补无知所造成的漆黑一片的空洞的自然科学不同,行为科学面对的是已经被问过并且由文化作了回答的问题。其结果是民族学在确定自己作为主题事物的一个方面以及试图使自身能有足够的余地来表达尚未被接受为来自其文化当中的‘智慧’的事物时,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消极被动的角色,而且难度很大。”[11]401-402而对于这些悖论,有的学者认为会对人类学学科发展造成阻碍,而更多的学者则看到了其对人类学和民族志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因素。但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应该从学理上入手去弄清楚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进而找到解决和认识这些矛盾的途径,最后才能为民族志发展找到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本文主要是从人类学、认识论和发展观三个方面入手具体探析民族志书写悖论产生的原因。
总之,民族志作为一种表征其他人如何体验世界的常识性观念的产物,其在追求客观性时具有双重的或然性(problematic):其一,因为它是以一种文化上的相对方式来构成经验的,而并非唯一可能的方式;其二,因为尽管如此它仍然相信它自身是一种对事物本来面目(things-in-themselves)的普遍描述[8]。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权宜书写与权威书写、变熟为生与变生为熟及书写神秘与神秘书写等诸多矛盾是当前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的集中体现,而这种悖论为民族志当代书写中种种“幻相”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今天的民族志书写呈现出来的“多元化”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民族志书写“不仅涵盖了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化、无我性、反讽、混杂性等文化品性,而且转达了戏剧式的、荒诞的精神气质”[9]。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多元化”特征,为民族志书写提供了动力和源泉。“人类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历史地变化着的实践,这些实践与人们所认为的‘人类’和‘学’(logoi),即与界定和形塑这一学科和话语,联系在一起并动态地相互作用。”[10]中文本序11因此,只要有人类学和民族志实践,书写中就会有内在矛盾的产生;而只要书写内在矛盾的产生,就会推动人类学和民族志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类学实践与民族志书写的内在矛盾,是一对在本质上具有逻辑一致性而又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
从人类学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历史去看,其内部存在的争议从没中断过,人类学界研究的重大问题和观点几乎都涉及其中。比如,人类学理论研究上出现的多元化趋势,就是人类学界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民族志书写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不仅引起了西方人类学界的广泛争论,也引发了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文化是先天而来的生理现象,还是后天形塑而成的社会问题;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矛盾体问题等。但比起其他学科来说,人类学争议所引起的学科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败都不是问题,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性恰恰就在于其对事物的抗拒性,这一点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它通过通常是否定的、零碎的,而且是很难用三言两语就能向公众阐释清楚的方式去进行论证,得出一种其他更可能的、更复杂的假设的替代形式,这一点是真实和异常重要的[11]401。因此,对于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内在悖论,我们应该抱着乐观的心态去对待,用理性的眼光去思考和解决当代民族志书写上出现的相关问题。在战略上,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熟视无睹;在战术上,既要高度重视,也要落到实处。
再次,人类学和民族志的发展要求所引起的。人类学是以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为核心的学科,因此,人类学的发展和民族志书写是同步和一致的。众所周知,随着后现代民族志的出现,其对传统民族志书写所进行的解剖与对新的民族志书写范式的追求,使得人类学者自身认识能力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求真至善的民族志诉求得以进一步彰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传统的民族志方法、民族志理念和诉求由于内部存在的这样那样不足而受到了学界的广泛批判与反思。比如,萨义德说:“实际上,后殖民研究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发展是对经典的文化作品进行重读,其目的并非试图贬低这些作品的价值,而是对它们的某些假定前提进行重新审察,超越某种主人/奴隶式二元对立关系对它们的控制。”[5]452非西方的人类学者对人类学殖民化服务的历史进行的批判与一些西方学者所进行的辩护与反驳的对立态势应运而生。同时,随着多种修辞方法在人类学中的广泛使用,以前那些潜藏的矛盾慢慢浮出了水面。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悲伤地描绘了在与一种强势文化发生接触的冲击下,各种有差别的社会结构正在瓦解成全球的同质性,由此而思考西方的殖民主义活动及其影响。而拉比诺在通过自身在返回祖国后的不适应去反思西方社会和自己开展的田野工作,用比较的方式去展示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不同及其自身独特的民族志书写方式。此外,随着人类学田野调查范围的扩大,对他者的研究开始转向对自身的认识,这会引发和唤起人们对“变生为熟”和“变熟为生”原则的进一步思考,最终把对如何做到既是他者又是作者的悖论相关问题的认识推向了学术前端,成为了民族志真实性的前置性、前端性问题。总之,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没有矛盾,事物就得不到很好的发展。人类学和民族志发展所引发出来的各种矛盾,看似对人类学和民族志发展造成了一些困难,但总的来说,是会推动人类学和民族志的进一步发展的。
传统评书都有民间口头文学特征,而口头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每个时代各有千秋。也就是说,评书并不是对历史故事的简单重复,而是将历史故事与当下语言特点、受众心理进行有机结合的结晶。打个简单的比方,即便是近代评书“开山鼻祖”柳敬亭的作品放到今天,也只会令听众一头雾水。
总之,人类学既不能简化为田野作业,也不能简化为民族志叙事,更不能简化为哲学人类学思考,而应该如赫斯菲尔德所说的那样,人类学是理论的实践和实践的理论的统一体[18]24-25。因此,随着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的不断实践和发展,造成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出现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多重主体的倡导而产生的不同主体素质和能力的差异性、文化主体和书写主体的一致性以及学科发展所带来的书写混杂性等问题都可能使民族志书写陷入困境。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任何一次民族志书写实践活动,主体、客体和实践中介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三大因素。因此,上述三大原因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解析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产生的合理理由。
三、内在悖论下的当代民族志书写
五防服务器与调控D5000系统采用专用接口程序以TCP/IP方式进行信息交互,五防系统服务器与五防主站、五防主站与五防子站间采用已开放的标准规约,利用其自带网口,做IP配置就能实现主子站间的防误通信,信息交互如图2所示。
无论是在竹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还是在全面发展的成熟阶段,通过建筑设计进行创新可能是竹文化推广的最有效方式,因为它技术水平不高,可以简单地利用原始材料。竹子作为用途最多的天然材料,在中国和印度已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但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中国,竹产业的发展与政府推动的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位于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其他42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学习中国,并已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他们的竹产业。在这个方面,墨西哥依然落后。
其次,内在悖论下当代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建构。当前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的种种实践,很好地表征了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的实践性特征。而在其实践中,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和价值性诉求得以彰显。因此,对于当前民族志书写的范式建构而言,一方面要顾及民族志书写的当前实践,另一方面也要尽力去找寻民族志书写规律,最终建构起一个求真至善的书写范式来,这是人类学界认识和解决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的有效途径。当前,随着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的揭露,在民族志书写实践场中,出现了范式多样化和主体范式缺失、修辞方法多元化、主题体裁小说性、视野和范围广博化以及价值人性化等趋势,但总体来说这些实践告诉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可以从众多的实践中去自由地选择,并能找到一个更加适合我们的选择[21]。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些实践仅仅是在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刺激下的产物,其本质上并不能对认识和解决这些悖论服务,因而需要我们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及由表及里的辩证思维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志书写的当代范式建构提供一个合理的发展模式。“人类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历史地变化着的实践,这些实践与人们所认为的‘人类’和‘学’(logoi),即与界定和形塑这一学科的科学和话语联系在一起并动态地相互作用”[10]11,因而笔者认为实践民族志理应顺势而成民族志书写的最佳范式。理由如下:实践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能很好地表征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的一般性和开放性特征,很好地展现人类学学科特点和优点;实践民族志是对以往民族志实践所做的总结,也是对当前实验民族志的种种范式进行概括的产物,具有坚实的历史和现实基础;田野工作、批评与反思、过程性认定以及求真至善目标都能说明实践民族志的本质;“实践出真知”的哲学基础能使实践民族志具有扎实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性属性;实践民族志具有宏观意义上的气魄,也有微观视角下的可操作性。总之,基于实践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上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的作用,笔者认为当前人类学界建立起实践民族志不仅可能,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实践民族志建立是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认识和解决民族志书写悖论的操作基础。
显然,与上世纪后期相比,无论陆海间还是在陆上的东西部间,剩余可采储量分布的不均衡性趋于降低。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全国原油勘探开发第二次战略展开已基本完成。
再次,内在悖论下当代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建构。对于民族志书写来说,我们也可以从矛盾视角入手去述说其意义的产生和发展,进而达到书写与社会表达和要求的一致性目标。矛盾即对立统一,对立统一属性要求我们在全面看待问题的基础上,一定要承认事物间的“和而不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要看到事物的共性,也不要忽视事物的个性,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告诉我们要抓住事物发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观点的这些属性和实践原则要求我们在民族志书写方法上,要真正做到和谐书写和书写和谐的相互交融;在民族志书写价值诉求上,一定要践行好“文化多样、人性普同”的理念;在民族志书写的当前实践和未来发展上,则要彰显人类学的“公众”和公共人类学的价值取向。简单地说,和谐书写就是指要处理好人类学书写实践中的各种关系,比如,主体与客体、主位与客位、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社会、真实与价值等矛盾。书写和谐是从民族志书写的内容和终极目标入手去言说的,是指民族志书写要为理解和尊重他者、和谐社会的建构服务。民族志书写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对人性普同诉求的初心,真正做到理解和运用好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这对矛盾关系。当前,中西人类学发展的最大趋势是如何面向日益扩大的“公众”,这个“公众”既不是人类学家们想象中出现的公众,也不是各种赞助人或学院派们所支持的公众,而是特指在研究过程中,民族志自身复杂路径和知识体系下的独特公众。这个“公众”是公共视域下的公众,其对于公众事物有着自身独特的见解和认识,并能将这些认识传递给人类学者。总之,这个“公众”不是传统人类学研究意义中的客体的公众,而是在人类学不断发展过程中,处于学科主体地位的公众。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这种源泉是建立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不同作用发挥之上的产物。因此,就民族志书写中的悖论来说,其价值追求还要考虑到民族志书写发展这一价值维度。这就是说,在民族志书写悖论中,我们要去找寻民族志书写中的一致性和原则性,也要看到民族志多样化发展态势对于民族志发展的推动作用。总之,处于悖论之中的和谐性、人民性及发展性这三个价值追求,实质上是民族志书写意义表达的另外一种方式。因而,对民族志书写来说,书写上的要求及其达致的意义对民族志书写及其悖论解决起着目标导向的作用。
此外,处于矛盾丛生下的民族志书写要顺利进行,一方面要对实践的理念、活动范式和目标导向有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另一方面则要充分相信这一点,即文化价值虽没有普遍性,其仅仅在特殊地域、特殊群体和生活世界中才有效,但这不等于说人类无法在价值与审美中取得最低限度的一致。就如哈贝马斯认为真理是“有效性主张”,真理成为真理就在于它被普遍同意,“当且仅当任何其他能与我讨论的人也能将同一个谓语归于同样的对象时,我才有资格将一个谓语归于一个对象。……陈述的真理的条件是每一个他人潜在的同意”[22]。和谐书写本质上是人际和谐的代名词,只要人与人之间关系达到了和谐,和谐书写也就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和基础。因此,文化研究虽然倡导相对主义,但绝不是将这种相对主义绝对化,这种相对性是紧紧依靠着孕育它的母体文化——现代文化而言的相对性。
总之,本文主要从元反思基础上对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进行解构,看到了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几对核心矛盾,并对这几对矛盾进行了逻辑和实践机理的分析。笔者认为民族志书写中矛盾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受书写实践中存在的主客观条件限制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学对不断扩大的社会条件的复杂化和知识的不懈追求的产物。因此,基于对民族志写作和人类学具有的实践性本质一致的理解,笔者倡导建构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去应对当前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矛盾和范式杂糅现象。只有这样,在解构和建构的变换过程中,现代民族志书写的价值目标才会得以倡导和张扬,公共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及人民性才能成为人类学学科内部的价值共识和发展基础。因此,民族志书写实践及其内在悖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推动民族志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参考文献 :
[1]克利福德,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3]巴尔特.写作的零度[M]//王潮.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李幼蒸,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204.
[4]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47.
[5]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6]BENJAMIN W.Illuminations[M].New York:Schocken.1969:75.
[7]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做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M].周晓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63.
[8]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M].张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96.
[9]佟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310.
[10]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1]瑟维斯.人类学百年争论1860-1960[M].贺志雄,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12]LEVY-BRUHL.The Notebooks ofLucien Levy-Bruhl[M].trans.P.Rivere,Oxford:Blackwell,1975:43.
[13]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中译者序5.
[14]鞠实儿.论逻辑文化的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J].中国社会科学,2010(1):35-47.
[15]王铭铭:萨林斯及西方认识论反思/甜蜜的悲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序言9.
[16]列宁.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7.
[17]李银兵,甘代军.民族志语言的象征性权力探析[J].学术界,2016(12):107-116.
[18]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M].刘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9]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1.
[20]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名著摘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13.
[21]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M].黄剑波,李文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89.
[22]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46.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An Exploration of Internal Paradox in Ethnographic Writing
Li Yinbing ,Cao Yida
(School of Marxism,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Gui zhou,550001)
[Abstract ]Internal paradoxes of ethnography writing give rise to continual critique and reflections in modern society,of which zero degree writing vs.non-zero writing,expedient writing vs.authoritarian writing,mutual transfer between the unfamiliar and the familiar,and writing mystery vs.mysterious writing are the best representations in the complex field of paradoxes.Therefore,constant deconstruction and probe into their logic and practical mechanism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ontemporary establishment of practical ethnography writing paradigms.
[Key words ]ethnographic writing;internal paradoxes;logic mechanism;practical ethnography;writing paradigm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9)01-0001-08
[收稿日期 ]2018-11-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化创新视域下西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研究”(项目编号:14BSH057)
[作者简介 ]李银兵,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历史人类学研究;曹以达,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文化哲学研究。
编辑:李晓丽
责任校对: 李晓丽)
标签:民族志书写论文; 内在悖论论文; 逻辑机理论文; 实践民族志论文; 书写范式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