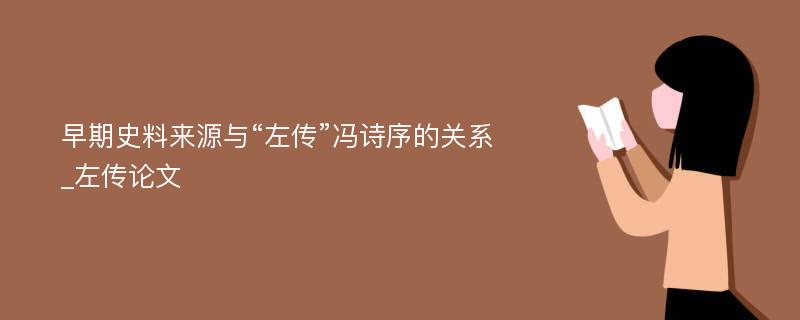
《左传》早期史料来源与《风诗序》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史料论文,来源论文,关系论文,风诗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左传》成书十分复杂,古今学者在其成书年代等问题上讨论殊多,但其材料来源问题因为古文献的缺失,相关研究较少。《左传》不同时段、不同类型、不同诸侯的历史记载互有多寡,其文体亦有差异。叙事的多寡和详略不仅仅出于“作者”的选择,还决定于史料的存佚及丰富程度。就《左传》而言,详于晋楚、聘问、战争、弑君等事,此种选择,恐怕还是取决于史料的多寡。
今本《毛诗》中《邶风》至《曹风》部分的编纂相对较晚,仅从诗文与序文的对比上看,这部分《风诗》的诗与序表面距离为最大。故部分《风诗序》与《左传》的关联,遂成宋代以后“废序”者攻诘的主要对象之一。本文重提《左传》与《风诗序》的关联问题,并非要阐述“挺序”或“废序”主张,而是在“真伪”探讨的思路外,将其历史叙事作为研究的重心,从《诗序》“历史化”叙事与《左传》叙事之间的联系中,窥探《左传》春秋早期历史史料来源的一种可能性。
同时,本文并不否认,《诗序》所述未必全是“真实的”诗之“本事”,许多《诗序》很可能出于《诗》编纂者的“编《诗》之义”,甚至是杜撰。但是,本文不是考究《左传》、《诗序》所述是否为“真”,而是关注其叙事本身,力图从二者的历史叙事之间独特的、整体的联系,发现与史料的撰述、流传有关的史料背景。
二《左传》与《风诗序》叙事的整体性相关
在叙事层面,《风诗序》各国风诗出现的时代,《左传》中与之相关的叙事都相对比较详细。而且,《序》所言诗作的“本事”,在《左传》中多有详细记载①。限于篇幅,本文仅以《邶》、《鄘》、《卫》三风与春秋时代卫国历史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其他风诗与诸侯历史则略作介绍。
(一)《诗序》卫诗背景与《左传》卫国历史之关系
卫国历史主要见于《左传》和《史记》,其中《史记·卫康叔世家》系统整理了包括《左传》在内的先秦卫国史料,是汉代最为完整的卫国史料的汇编。《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最为详细的历史有两段,第一段从卫庄公至卫文公时期,第二段从卫献公至卫庄公蒯聩时期。两段历史有各自的连贯性,也均依据《左传》。《诗序》所述《邶》、《鄘》、《卫》各篇的出现时代,除了《邶风·柏舟》、《鄘风·柏舟》、《卫风·淇奥》三篇之外,均集中于卫庄公至卫文公时期。
《绿衣序》称“卫庄姜伤己”,(《考槃序》称“刺庄公”,《硕人序》称“闵庄姜”,这三篇在郑玄《毛诗谱》中归入庄公时期。郑玄虽远在后汉,但其所编《毛诗谱》当是据两汉之间沿袭不断的《毛诗》旧说,有关诗篇的意旨的诠释,相信不会在流传中发生根本性变化,故其说多数当与毛公等早期经师相同,应可信据。卫庄公之后的州吁执政时期,据《诗序》,则有《燕燕》、《日月》、《终风》、《击鼓》四篇②。
卫庄公执政晚期至州吁篡政之时,大约也是《左传》记事的开始。这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自鲁隐公元年至四年,但却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庄姜和州吁之事。尤其是州吁篡政,《左传》记载极为详细。这也是公元前6世纪之前《左传》记载卫国历史最为详细的三段之一,另外两段则是宣姜之乱和狄人灭卫及其复国。这三段记载的形式类似于《国语》中的文体,为独立叙事,在《左传》中属于最详细的“记载”之一。卫庄公时期与州吁时期的诗,除了《考槃》、《凯风》外,毛、郑认为均与庄姜和州吁有关。
《毛诗谱》归入卫宣公时代的诗,《诗序》无确指的最多,《雄雉》、《匏有苦叶》、《谷风》、《静女》、《氓》、《有狐》等诗,毛、郑认为乃是刺卫宣公与夫人的淫乱,及其对卫国民风的感染。而《新台》、《二子乘舟》则直接指刺宣姜乱政前后的具体事件。《式微序》、《旄丘序》所说黎侯寓卫之事,已不可考。卫惠公时代的诗与宣公时代有连贯性,除《芄兰》外,毛、郑认为均属宣姜之淫乱及卫国民风背景下的作品。联系《雄雉》、《匏有苦叶》等诗,宣公纳宣姜、宣姜之淫乱是宣公、惠公时代最主要的风诗背景。
卫戴公时期,有《载驰》一诗,《载驰序》与《左传·闵公二年》可以互证,当无问题。《毛诗谱》归入卫文公时期的诗,除了《河广》,《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木瓜》的《序》均明言文公。而《河广序》曰:“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笺》云:“宋桓公夫人,卫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义不可往,故作诗以自止。”宋襄公即位在卫文公十年(前650),据《序》、《笺》,此诗当作于公元前650年,属文公时期。
综上所述,《邶》、《鄘》、《卫》三风中,除了《谷风》、《简兮》、《泉水》、《北门》、《北风》、《静女》、《竹竿》、《有狐》难以确考外,其他各篇《诗序》、《诗谱》所言各篇的政治、历史背景,主要与州吁篡政、宣姜乱政、卫灭国与复国三段历史有关,这三段历史也正是《左传》“《诗经》时限”内仅有的对卫国的详细叙事的部分。
(二)《诗序》其他各国风诗背景与《左传》记事之比较
《郑风序》称《郑风》中绝大多数作品的创作背景是郑庄公至郑厉公复位之间的郑国历史。《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三篇,按照《诗序》的理解,它们均属共叔段之乱前的作品。《羔裘》、《遵大路》、《女曰鸡鸣》作于庄公国政衰败之时。《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讽郑太子忽拒齐婚一事。《萚兮》、《狡童》、《扬之水》等诗乃是讽喻昭公时政之作。《褰裳》、《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据《诗序》未知作于何时,郑玄将其系之于郑昭公。《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三诗,《诗谱》系于郑厉公。除了《缁衣》、《清人》外,《毛诗》传统解释认为《郑风》中的作品主要集中于郑庄公至郑厉公时期,又特别与共叔段之乱、“公子五争”相牵连。反观《左传》,“共叔段之乱”、“郑忽拒婚”、“公子五争”等事均非常详细。
再看《齐风》。《诗序》称《鸡鸣》、《还》两篇为齐哀公时期诗作,时代在《左传》载录的历史之前。郑玄《毛诗谱》则将随后三篇(《著》、《东方之日》、《东方未明》)列入哀公时期。除了上述五篇诗作外,《诗序》认为《齐风》中的诗篇多产生于齐襄公时代,且多与襄公之弑、文姜之乱有关。文姜之乱与齐襄公被弑均属“弑君”类的详细记录,此段齐国历史多由鲁国史官角度记录,故《齐风序》与《左传》的相关度亦颇高。
《唐风》共有十二篇作品,《蟋蟀序》称“刺晋僖公”,《葛生》、《采苓》“刺晋献公”,除此之外,《唐风》诗篇的历史背景,多与曲沃代晋有关。晋国历史是《左传》记载最为丰富的部分,但晋国系统而详细的记载始于晋献公时期,即晋武公并晋之后。晋献公之前的记载不如卫、郑、宋丰富。曲沃代晋是晋献公之前《左传》记载最为详细的晋国历史。
《王风》中的作品背景为东周前三王(平王、桓王、庄王)时期,其中《兔爰》、《葛藟》、《丘中有麻》三诗涉及了某种历史境况:《兔爰》指向“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葛藟》是哪一王之诗虽有异说③,但“弃其九族”似有所指;《丘中有麻》则指向“贤人放逐”。《诗序》所云,除上述三诗外,其他诗篇均是东周初大环境下的指刺,似并无具体史迹背景。《王风序》中最具体的是《兔爰序》,而《左传》中前三王历史最具体的正是对“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的记载,从隐公三年至桓公五年。隐公三年,“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六年,“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十一年,“王取邬、刘、蒍、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攒茅、向、盟、州、陉、隤、怀。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桓公五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繻葛”,王师败,“祝聃射王中肩”。马骕《左传事纬》称此段叙事为“周郑繻葛之战”,并引《兔爰》论之。《兔爰序》所言桓王时期的“王师伤败”正是“繻葛之战”,此战也是《左传》东周前三王时期唯一的细密叙事。
《诗序》所言《秦风》之作,涉及秦仲、秦襄公、秦穆公、秦康公四位君主。秦仲、襄公均在《左传》时限之外,《诗序》与《左传》在时间上相重合的是《黄鸟》至《权舆》。《黄鸟序》与《左传》记载相呼应,《左传》的记载也是一则独立叙事。但是《晨风》、《渭阳》、《权舆》之序,均指向某种历史背景,却失载于《左传》、《国语》。只有《无衣》指刺其君好攻战,与《左传》中记载的秦康公时期,秦、晋之间发生的多次战争相符合,但文献稀缺,不足征信。故《秦风序》除《黄鸟》外,与《左传》之相关度并不高。
在《诗序》时限内,《左传》有关陈的历史有三段较详,一是陈佗之乱,二是陈完奔齐,三是陈灵公之弑。据《毛诗谱》,《陈风》中有西周厉王、宣王之时陈幽公、陈僖公的诗,也有春秋时代陈佗、陈宣公、陈灵公时的诗。《诗序》春秋时代相关序言分别对应陈佗之乱、宣公信谗、灵公之弑,与《左传》记载详略正好对应。
《诗谱》序《曹风》之作云曹“十一世当周惠王时,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变风始作”。《诗序》所言《曹风》之诗,《蜉蝣》乃昭公时期,《候人》、《鸤鸠》、《下泉》则属共公时期。据《春秋经》记载,曹昭公时期,曹频繁参与齐、宋、鲁、陈、卫、郑、许等国的会盟及征伐,在此之前,曹并未频繁出现于诸侯会盟之中。在《春秋》的撰录者笔下,曹是每次会盟或征伐参与国中地位最低者,故每条记录均列曹伯于末,甚至处于许男之后。可见此时曹之国力已经十分卑微,故多依靠齐、宋两大国。曹昭公虽然频繁参与会盟、征伐,但《左传》中此时并无涉及曹国情况之记载。曹共公时期,曹的史迹进入《左传》,则与共公偷窥重耳沐浴、重耳返国后征伐曹有关,此时,曹、卫已经成为晋、楚两国政治军事之砝码,其地位继续下降。《左传》的记载与《诗序》之间无明显相关。
综合来看,《风诗序》时限内,《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陈风》与《左传》相关度最高,《齐风》、《唐风》次之,《王风》、《秦风》、《曹风》再次之。《周南》、《召南》、《魏风》、《桧风》、《豳风》因产生年代早,不在此列。《左传》早期叙事,卫、郑、鲁、宋等国较详,晋在献公之后其记载也变得丰富起来,齐、楚、周、陈的详细记事则较少。故《风诗序》与《左传》的相关度与《左传》中诸侯史迹的多寡,大体上呈正比。即《诗序》与《左传》相关度高的诸侯国,它们春秋早期历史在《左传》的记载就比较详细,反之,则简略。
相比于齐、晋、陈,《左传》中卫、郑史料与《风诗序》的高度相关性尤其值得关注。原因在于齐、陈分别与鲁国、楚国的历史相联系,且多从鲁、楚的角度叙事,鲁、楚与晋是《左传》史料最丰富的三国,当有丰富的史料来源。但春秋早期,《左传》中卫、郑的历史叙事却相对独立,且多细节叙事,又与《风诗序》有着极高的相关性,因此它们的史料来源与《诗》的关系就显得非常特别。
三 《左传》史料用《诗》与《毛诗序》理解的一致
那么,《风诗序》是否如叶梦得所言,乃是取材于《左传》?范处义、马端临等对此考论甚详,兹不赘引④。需略作说明的是,《左传》所记载的春秋人引《诗》、赋《诗》,在对《诗》的意旨理解上与《风诗序》存在一致性。《左传》中人物的引《诗》和赋《诗》绝大多数都可以用《诗序》或《毛传》来解释。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即用《毛诗》来解释春秋时代的用《诗》,他的解释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契合度非常高,这说明春秋时代对《诗》的接受和理解与汉代的《毛诗》基本一致。
举三例以作说明,《左传·成公二年》:
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⑤
《毛诗序》曰:“《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鲁成公二年,楚国人对《桑中》一诗的理解已经与《诗序》一致。
若纯从诗文分析,恐怕很难看出申叔跪对申公巫臣所言的“桑中”之喜与“窃妻以逃”的关系。如崔述《读风偶识》即不用序,而曰:“《桑中》一篇但有叹美之意,绝无规戒之言。”闻一多云:“《桑中》,思会诗也。”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亦断此诗乃是“一首男子抒写和情人幽期密约的诗”⑥。反观“《桑中》之喜”与“窃妻以逃”的表述,可知《桑中》指刺“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的解释,在春秋时被理解为《桑中》的基本意旨。《左传·襄公十四年》:
(士鞅)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⑦杜注:“召公奭听讼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树,而作勿伐之诗,在《召南》。”《诗序》曰:“《甘棠》,美召伯也。”鲁襄公十四年,晋国人对《甘棠》的理解也与后来的《毛诗序》一致。
《毛传》:“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韩诗外传》卷一、《说苑·贵德》篇引古《甘棠传》、《孔子家语·庙制》、《史记·燕召公世家》、《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汉书·王吉传》均有类似记载。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第十五简有:
及其人,敬爱其树,其保厚矣。《甘棠》之爱,以邵公
此数语正与上文所引各古书评述《甘棠》之文、之义相同。可见对《甘棠》的解释模式出现确实非常早。春秋末至战国时代已经颇为流行了。《左传·昭公十六年》: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⑧
这次外交场合的赋诗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国力弱小的郑国需要强大晋国的庇护,因此郑国诸卿以赞美晋使韩起,或表达愿结盟晋国为主题。《野有蔓草》,《诗序》曰:“思遇时也。”杜注:“取其‘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羔裘》,《诗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杜注:“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彦兮’,以美韩子。”《褰裳》,杜注:“《褰裳》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言宣子思己,将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岂无他人。”《风雨》,杜注:“《风雨》诗取其‘既见君子,云胡不夷’。”《有女同车》,杜注:“《有女同车》,取其‘洵美且都’,爱乐宣子之志。”《萚兮》,杜注:“《萚兮》诗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将和从之。”杜注的解释基本可通,但也有滞涩之处,如在听完子游、子旗、子柳三人的赋诗后,韩起云:“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但杜注选取的三句诗却主要表达三人对韩起的爱戴之意,似无法看出以“君命”求“燕好”之意。
如果我们联系《诗序》,从整诗的意旨上理解郑六卿所赋,会发现也符合当时情境。《诗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时也。”整诗也是表达“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之意,因此杜注的解释非常合理。《羔裘》,《诗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全诗正是借赞美古之君子,讽喻郑国时无君子之意,子产赋之,即颂韩起为古之君子也,亦暗示韩起可帮助郑国加强与晋国之关系,为郑国所需之君子也。故韩起辞曰:“起不堪也。”《褰裳》,《诗序》曰:“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子大叔赋之,即希望晋这样的大国“正己也”,故韩起答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意为“我在晋执政,不致使汝劳累服事他国,必能护郑”⑨。《风雨》,《诗序》曰:“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子游赋之,以表达乱世思君子之意。《有女同车》,《诗序》曰:“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萚兮》,《诗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这两首诗均是讽刺郑忽拒绝结姻强大的齐国,之后遂有“公子五争”之乱,故子旗、子柳赋之,暗示郑会汲取之前忽之教训,愿与晋加强联盟之意。可见,郑六卿的赋诗,依据《诗序》,从整体上理解,更能契合当时情境。
除了《风诗》外,《左传》中对《雅》、《颂》的使用也多数与《毛诗序》相合。仅以一例为证,《左传·文公元年》:
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⑩
秦穆公所引诗句出于《大雅·桑柔》。其序曰:
《桑柔》,芮伯刺厉王也。
《郑笺》曰:“芮伯,畿内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秦穆公云《桑柔》乃芮良夫所作,与《毛诗序》一致。
但《左传》论《诗》也有少数与《毛诗序》不相符合者,如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周王之辞,以为《小雅·常棣》乃是召穆公所作,在周厉王之时。但《诗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序》言“管、蔡”,故将此诗置于成王之时。《毛诗正义》引《韩诗外传》曰:“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韩诗》又将此诗之作归于周公。郑玄《笺》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之以亲之。”郑玄当据《左传》而作《笺》,“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一句即取自富辰所论。但他所受师说,乃是周公作此《常棣》,故调和二说,以为“周公作诗,召公歌之”。不论后人如何弥合《诗序》与《左传》叙述的裂痕,其记载之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春秋时代对《诗》旨的理解与《毛诗序》确有不同之处。
从《左传》引《诗》、赋《诗》综合分析,判断《诗》的原始之“序”(对《诗》旨的解释或理解)产生于孔子之前似无问题(11),也合常理,即《诗》的编纂在孔子之前,其序意自然会产生于孔子之前。问题是,早期的序意会有多少存留于后代的《毛诗序》或三家《诗序》中?至少从《左传》所载春秋时代人对《诗》的使用来看,《毛诗》之序还是多数与早期理解相同或相近,即使是所谓“续序”部分的阐释,也多与《左传》中的用诗一致,可见《风诗序》完全依《左传》等相关史料附会而成的推断恐怕难以成立。它们虽可能成文于后世,但多数亦属古已有之的解释,或成说于春秋末战国初之前。郑玄所谓“变风”的十三《国风》的编纂,至迟也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完成(12),每篇诗旨的解释也当同时出现。《诗》的早期的“序”当出现于《左传》之前。
四 《国语》与《风诗序》整体叙事上的不相关
与上述问题相反,《国语》与《风诗序》在整体性的历史叙事上几乎没有关联、对应或重叠。
《国语》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一篇,与今本卷帙相同,此书经韦昭注释以来,略有残缺(13),但其传本变化不大。韦昭《国语解叙》称左丘明撰述《左传》之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14)。但是今本《国语》中最晚的材料似已入战国中期,“如《晋语》谈到智伯之亡,谈到赵襄子的谥号,就不是左丘明所能了解的。《国语》中也有一些预言或占卜之类,如《晋语四》中的姜氏之语:‘商之飨国三十一王,《瞽史之记》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今未半也。’……晋亡于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年(前376年),这当然不是左丘明能看到的”(15)。
虽然《国语》晚期材料的年代不好确定,但是其主体时限与《左传》还是重合的。其中《周语》、《晋语》、《郑语》、《楚语》及《鲁语上》五部分时代较早,与《左传》有密切关系。洪业先生《春秋经传引得序》利用引得成果,详加考验,发现《国语》有与《左传》几乎完全相同之文字,尤其是《晋语》与《左传》有高度相关性(16),《左传》更有明显裁切删减《国语》的文字,故知《国语》部分材料确属《左传》之史源。
《国语》可能与《风诗序》有关的部分是《周语》、《鲁语》、《齐语》、《晋语》和《郑语》。但与《左传》不同,《国语》与《诗序》的相关性非常小,甚至让人怀疑它的取材有意避开《诗序》的“叙事”。
《诗序》称《王风》之诗出现于平王、桓王、庄王时期。但《周语》始于周穆王,终于周敬王,平王、桓王、庄王正在这一时限内,但此三王时期的“语”却是空白。《周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条之后,即是“惠王二年”条,正好跳过了东周前三王的时期。
《诗序》称《齐风》之诗讥刺齐哀公与齐襄公,其中齐襄公时六篇亦多与鲁桓公之弑相关,但《齐语》叙事始于桓公返齐,《鲁语》始于长勺之战,正好分别避开齐襄公与鲁桓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语》,《左传》鲁隐公、桓公时期,鲁国之事亦有记载颇详细者,但今本《国语》对此二君时期却未涉及,只是开始于桓公之子庄公时期。
《唐风序》称《唐风》多为晋昭侯至晋武公时作品,只有最后两篇《葛生》、《采苓》为晋献公时。但《晋语》与《左传》一致,详细的记载始于晋献公,只有第一章为晋武公之事。可见二者详略正好相反。
《郑语》则主要记载郑桓公之语,时在《郑风序》时限之前,二者没有关联。
除《国语》外,《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亦与《左传》有联系,但因二者汉代以后传本所载史迹少而史评多,难于考验。
《史记》主要依据《左传》、《国语》等文献,因此《风诗序》时限内,其叙事密度近于《左传》,与《序》亦有很高相关度,上文已有涉及,兹不赘述。
可见,同为以载录春秋诸侯国史料为主的典籍,《国语》与《风诗序》的相关性却非常低,二者在史料上亦无同步性。但它们却都与《左传》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同步性。
鉴于《左传》、《国语》之关系及《国语》汇集诸侯国“语”类文献的特点,若有与卫、郑、齐、鲁等国关系密切的史料,不可能仅见于《左传》,而罕见《国语》。或者说,为何与《风诗序》相关的史料仅见于《左传》,而罕见《国语》呢?必须承认,《国语》仅仅是战国前期流传的部分“语”类材料的结集与编纂,近年新出土的简帛文献,如上博楚简,其中就有类似于“语”的文献,多数不见于《国语》。另外,韦昭《国语解叙》曰:“左丘明……以为《国语》……遭秦之乱,幽而复光。贾生、史迁颇综述焉。及刘光禄于汉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谬。”(17)《国语》经秦乱,亦有部分材料散佚之可能。即便如此,《国语》也不可能对《风诗序》“躲避”得如此干净。
被广为引述的申叔时教育楚太子之论中(18),或存解释可能。从申叔时之论看,在春秋时代太子、公子等贵族子弟的教育中,《诗》和《语》是重要的两种并列的知识类型。其中,《诗》在春秋时代,尤其是春秋中后期,是外交、政论等重要“对话”场合,卿大夫乃至国君使用的“通行”的经典文本,引述一方不需要向对方解释所引或所赋《诗》的含义,对方在“答复”时也不需解释自己是否已经理解其意,而是直接就对方所赋《诗》的意义作答,且多默契地以诗回应。如《左传·文公四年》: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19)
鲁文公与卫宁武子均对《湛露》、《彤弓》二诗之义及诸侯燕宾之乐制十分熟悉,故有《传》中之描述。此种使用模式,说明春秋时代《诗》在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卿大夫、士中间已经十分“普及”。《诗》若有相配之“本事”史迹流传,亦当十分“普及”,其他类型文献似无必要载录之。故与《诗》并行之“语”不见此类史事便可理解了。
洪业先生已经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即《国语》的某些材料是《左传》的史源。而《国语》与《诗》“本事”类史料又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文献,故《风诗序》与《左传》的相关性也指向此种可能:与《风诗序》相联系的某些史料也是《左传》史源之一。但是,与《国语》不同,《风诗序》绝大部分序文均十分简略,无法与《左传》的记载相比照,是没有具体文献证据的。因此,还需要有其他的旁证。
即如果上述推测成立,那么《诗》在春秋至战国初年的流传中,当有非常详细的历史故事文本并行。不然,仅以今日所见《风诗序》之规模,是无法成为《左传》史源的。
五 春秋战国时代引《诗》的故事情境与《诗》、史的并传
《诗》在流传中有没有相配的故事文本,已无可靠的文献可查。但通过对古人引《诗》的分析,还是可以看出某种端倪。
除了上文所述明显的《风诗序》与《左传》的联系外,《左传》、《国语》叙事中也可寻见《诗》的流传中的“本事”史迹。如《左传·昭公十二年》:
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20)
《祈招》乃属逸诗,春秋时代有流传。左史倚相除了能够颂其文句,还对其本事清楚,所谓“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也,这与《诗序》的叙述模式是非常接近的。又如《国语·楚语》:
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诗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21)
韦昭注曰:“《懿》,《诗·大雅·抑》之篇也。”倚相对《大雅·抑》之作的“本事”也非常了解,知当时与《抑》并行流传的还有其“本事”。且倚相所述,亦有与《诗序》相合者。《序》称:“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22)倚相亦称:“作《懿》诗以自儆也。”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有《耆夜》一篇,简文讲述的是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之后,“饮至于文太室”,武王、周公作诗的故事。武王作《乐乐旨酒》以酬毕公,作《輶乘》以酬周公。周公作《赑赑》爵酬毕公,作《明明上帝》举爵酬王,见“蟋蟀跃降于堂”而作《蟋蟀》。其中,《蟋蟀》一篇与今本《毛诗·唐风》中的《蟋蟀》大体相同,二者虽未必是同一首诗,但至少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此简所述恐怕并非西周实录,但至少说明战国时代有类似于“《诗》本事”一类的文献存在。
除《左传》、《国语》外,稍后于二书的《孟子》也大量引述《诗》。欧阳修曰:“孟子去《诗》世近,最善言《诗》,推其所说《诗》义与《序》文意多同,故后世异说为诗害者,尝赖《序》文以为证。”(23)《孟子》引《诗》诸例中,特别引起笔者关注的是孟子对文王历史与文王《诗》的称述。文王是孟子政治哲学的偶像。孟子在阐述自己理想的政治模型时,总是要引述文王的历史,屡称理想政治乃是“师文王”。《孟子》一书除了以圣人形象泛指文王外,涉及到的比较具体的事迹主要与《诗》密切相关,如“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一事与《灵台》相关;“文王事昆夷”与《绵》相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与《皇矣》相关;“文王以百里王”与《文王》相关等等。有几处孟子对文王事迹较为详细的描述没有引《诗》,与《诗》的联系也并不直接,但仍能看出这些事迹来自于对《诗》的敷衍。如《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的说法是否确实,孟子回答“于《传》有之”。《传》是哪种文献,很难确知。但《毛诗传》解释《灵台》一诗有云:“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可知,孟子所说的《传》似与此诗有关。因此《孟子》之时,借《诗》流传的文王历史应较丰富,如《孟子》中提及的灵台、园囿、事昆夷、安天下之民、治岐、养老等事迹。
先秦文献引《诗》虽然多数都没有直接涉及背后的故事和历史,但不加解释地引用本身就说明作者、读者双方对《诗》义的理解有共同的基础,而《诗》义理解是离不开《诗》的创作史和内容所指的历史的。具有史诗性质的《生民》、《绵》、《公刘》、《大明》、《皇矣》等诗就是后世叙述早周历史的主要资源。如《史记·周本纪》武王之前的历史几乎完全依靠上述几篇《诗》。这些细节、内容上都比较详细的历史事迹,应该就是《诗》的缘起、训义和衍生。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先秦两汉时代,有“以诗为史”的传统。如被广为引述的《孟子·离娄下》中的著名论断:“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在孟子此论中,《诗》与《春秋》均是不同时代历史的记录者,只不过《诗》记王者之迹,而《春秋》载录齐桓、晋文之事。闻一多《歌与诗》一文即依据先秦两汉文献判断“诗即史”,并说“《诗序》好牵合春秋时的史迹来解释《国风》,其说虽什九不可信,但那种以史读诗的观点,确乎是有着一段历史背景的”(24)。虽然“《诗序》好牵合春秋时的史迹来解释《国风》”之论略显武断,但闻先生还是敏锐地发现,早期《诗》的使用中存在以史解《诗》的传统。那么,在这种传统中,自然有为解《诗》而存在的“历史”。
故笔者以为春秋时代至战国中期,的确存在与《诗》的“本事”或“背景”有关的历史或故事,至于这部分历史是“口说”还是“著于竹帛”的形式,则不可考见了。
综上所述,本文以为考虑到《诗》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流传及国史“独藏周室”的情况,《左传》与《风诗序》历史叙事的“同步”和《国语》对《风诗序》的“躲避”,说明《诗·国风》部分的某些“本事”或“背景”历史,应是《左传》春秋早期历史,尤其是卫、郑历史的史源之一。
注释:
①《诗序》的历史背景分析,详参朱冠华《〈风诗序〉与〈左传〉史实关系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
②《燕燕序》:“卫庄姜送归妾也。”但汉代学者多接受卫夫人定姜所赋的观点。刘向《列女传·母仪传》载称《燕燕》乃是卫定公夫人“卫姑定姜”所作,《易林》所述与《列女传》之义基本一致,兹不赘引。《礼记·坊记》郑玄注亦称:“此卫夫人定姜之诗也。”《毛诗正义》引《郑志》答炅模云:“为《记》注时就卢君,先师亦然。后乃得毛公《传》,记古书义又且然,《记》注已行,不复改之。”郑玄称定姜所作《燕燕》的观点“先师亦然”,可知汉代三家《诗》都是此种认识。另外郑玄在《毛诗笺》、《诗谱》中已经接受了《诗序》的观点,即《燕燕》乃是“卫庄姜送归妾”之作,并补充了其原委。
此诗若如三家诗之说,则至早作于卫定公卒后,即卫献公元年前后,此时已至周简王十年、鲁成公十五年(前576),据卫季札赴鲁观周乐的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也仅有32年。从时间上看,此诗若如三家之说,实在是太晚了。《左传》记载鲁文公十三年(前614)子家赋《载驰》,鲁成公二年(前589),申叔言及《桑中》,八年(前583),季文子引《氓》,九年(前582)穆姜赋《绿衣》。即自鲁文公十三年起,《邶》、《鄘》、《卫》三《风》已经开始作为经典被引用了,由此判断,此三《风》应在文公十三年之前已经结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十、十六简均论及《邶风》之《绿衣》、《燕燕》,与今本顺序一致,这两篇之前,孔子论及的诗是《关雎》、《樛木》、《汉广》、《鹊巢》、《甘棠》,也与今本顺序一致,可知《燕燕》是被当做《绿衣》同时稍后的作品。因此《诗序》近于古义,所谓“三家诗说”恐不可信。
《日月序》:“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终风序》:“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击鼓序》:“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诗中有“从孙子仲,平陈与宋”句,与《序》合。
③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见古本、崔灵恩《集注毛诗》、颜师古《毛诗定本》及敦煌P2529写卷,均作“刺桓王”。《诗谱》以为平王诗。
④详参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诗序”条按语,朱彝尊《经义考》“诗序”条。
⑤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4页。
⑥上述三则材料均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1页。
⑦《春秋左传诂》,第531—532页。
⑧《春秋左传诂》,第724—725页。
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81页。
⑩《春秋左传诂》,第352页。
(11)马银琴在《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中详细排比了《诗序》和上海博物馆竹书《孔子诗论》,发现“《诗论》与《诗序》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与发明的情况占有压倒多数的明显优势”,由此判断《毛诗》首序“产生在孔子之前,与诗文本的形成过程相始终”。其说可从。
(12)此年吴公子札赴鲁请观于周乐,鲁使工为之歌《诗》,十五《国风》已经齐备。
(13)《太平御览》卷七一○引《国语》曰“诸侯之师”、“蒍启疆曰”两条不见于今本《国语》,详参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收入《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4页。
(14)徐元诰撰、王树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4页。
(15)王树民《国语集解前言》,《国语集解》,第4页。
(16)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按今本《国语》二十一卷,而《晋语》得其九。《左传》叙列国事,亦独于晋事为详。《晋语》五,晋成公之立,当鲁宣公之二年,郤缺之聘于齐,当宣公十七年。中间十五年,《语》无文,而《左传》于此十五年中,述及晋事者,亦至简略。即此一端,可疑《国语》为《左氏》之重要史料矣。”(第272页)
(17)《国语集解》,第594页。
(18)《国语集解》,第485—486页。
(19)《春秋左传诂》,第358页。
(20)《春秋左传诂》,第703—704页。
(21)《国语集解》,第500—502页。
(22)卫武公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被立为卫君,并不在厉王时期。倚相称卫武公九十五岁作《抑》,必是晚年。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即位,武公直到前758年卒,他在平王时代尚执政十三年,故《抑》当是训诫周平王之诗。
(23)林庆彰等编审,许维萍、冯晓庭、江永川校《点校补正经义考》卷九九,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第三册,第695页。
(24)详参《闻一多全集·文学史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2页。
